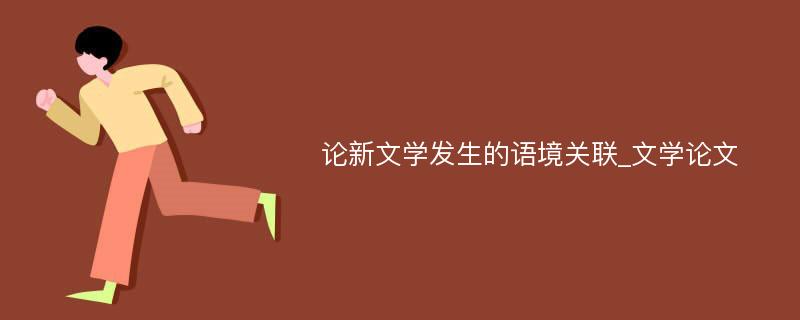
彼与此:新文学发生时的语境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语境论文,与此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3)05-0078-08
“哈佛味”及留学生与新文化运动的疏离
上个世纪2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不少,“学衡派”成员中就有近十位。若以林语堂的界说,他们回国后多少都带有“哈佛味”。林语堂、汤用彤、陈寅恪、楼光来、张歆海、梁实秋、郭斌龢可以算是“四年毕业”,而梅光迪、吴宓则始终没能“毕业”,即患上了“哈佛病”,没有摆脱“哈佛味”。
林语堂有过哈佛大学一年学习的经历,本与汤用彤、陈寅恪、楼光来、梅光迪、吴宓等人坐一个长凳听课,因不满白璧德的保守而转学。他在《哈佛味》一文中强调,文章有味,大学也有味。他引美国著名幽默家罗吉士(WillRogers)的话说:“哈佛大学之教育并非四年。因为是四年在校,四年离校,共是八年。四年在校使他变成不讲理的人,离校以后,大约又须四年,使他变成讲理的人,与未入学时一样。”他说自己初回国时,所作之文,患哈佛病。后来转变了,不失赤子之心。于是,他骂人的话出来了:“许多哈佛士人,只经过入校之四年时期,永远未经过离校四年之时期,而似乎也没有经过此离校四年时期之希望。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知有俗人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我见此辈洋腐儒,每每掩袂而笑,笑我从前像他。”[1](p.120)
林语堂是胡适的朋友,也是新文化派。他日后嘲笑哈佛学子,与新旧文学之争有关。胡适在与梅光迪、任叔永论辩时说:“我辈不作腐儒生。”[2](p.31)此乃话中有话。温源宁在英文著作《一知半解》中有《吴宓先生》一章,说吴宓的病在“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的立场。雨生不幸,坠入这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圈套。现在他一切的意见都染上这主义的色彩。伦理与艺术怎样也搅不清。你听他讲,常常莫名他是在讲文学或者是在演讲道德”[3](p.98)。林语堂对此文有特别的兴趣,将其译为中文。
是受导师的影响太深,还是自己的信念执著?究竟什么是“哈佛味”?白璧德、穆尔的中国学生的“哈佛味”又表现出什么特点?有学者注意到了梅光迪、吴宓身上在为人处事方面体现出的白璧德、穆尔“不苟言笑、执著专致和严肃认真”[4](p.509)的风格,和除张歆海、范存忠外,白璧德、穆尔的中国学生,像导师一样,“也都以获得硕士学位为满足,而没有攻读博士学位”[4](p.511)。
据潘光旦在《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1号上所写的《今后之季报与留美学生》示,在留美学生界,有两种名义上足以代表全体的定期出版物。一是英文的《留美学生月报》,二是中文的《留美学生季报》。前者是对外的,后者是对内的。而《留美学生季报》是1914年据原《留美学生年报》改刊的,在国内的上海印刷发行。这时的《留美学生季报》是广大留美学生的一个公共空间,后来成为“学衡派”成员的胡先骕、梅光迪、吴宓、汪懋祖、徐则林(陵)和主张文学革命的胡适、陈衡哲、赵元任等都曾在上面发表言论。1915年《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4号的“诗词”栏目中有胡适的《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其中有“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箠”的诗句。这是与国内新文化运动同步的“文学革命”的开始,“文学革命”一词首先在胡适的诗中出现。另有唐钺、任鸿隽、杨铨、胡先骕的诗。这时候,文学革命开始在美国胡适的朋友中讨论。
1917年1月,文学革命的火焰在《新青年》上由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而点燃。反映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是作为该刊主编的胡适的东西特别多,同时作为刊物编辑陈衡哲的白话“记实小说”《一日》也在1917年第4卷第2号上发表。正是这篇小说,被美国著名学者周策纵视为早于鲁迅《狂人日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该期有胡适的诗八首、词三首,如诗《尝试篇》、《蝴蝶》,词《沁园春·生日自寿》、《沁园春·新年》等。“笔记”栏目中有胡适的《江上杂记》和记录他和梅光迪讨论文学的《新大陆之笔墨官司》。而《新大陆之笔墨官司》是胡适后来写《逼上梁山》叙述文学革命在美国由讨论到孕育成熟的最初底本。另有任鸿隽诗六首、词一首、文一篇,杨铨的词三首、文两篇。陈衡哲除小说外还有诗两首、文一篇。可以说,此时的《留美学生季报》是和文学革命的讨论、发端同步的。他们这些留美学生是中国新文学的催生者。胡适的这些诗词在他回国后都收入《尝试集》。
随着胡适回国,总编辑易人,1918-1919年的《留美学生季报》是相对沉寂的。在国内新文学运动高涨,刊物纷纷刊登新文学作品的同时,1918-1920年间的《留美学生季报》仍大量刊登旧体诗词。作者中有胡适的朋友任鸿隽,也有反对新文学的吴宓、汪懋祖。如汪懋祖在1919年3月第6卷第1号上刊登的《送梅君光迪归圜桥(CambridgeMass,U.S.A.)序》(归国后,此序又刊于1922年4月《学衡》第4期)就明确表示和梅光迪意见一致,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他说与梅光迪相识而成知音,且恨相见时晚。他对神州新化,吾国学者“泊于既狭且卑之实利主义。论文学则宗白话,讲道德则效报施”表示极大的不满。因为新文化运动导致数千年先民之遗泽被摧锄以尽,中国人的灵魂丧失。而梅光迪要“以文救国,驯至乎中道。当不迷其同而放所异”。汪懋祖最后说他“将攘臂奋首,以从君之后,而助成其业也”。并以“坚其盟”为志向。这个“盟”即后来的“学衡派”,“业”即梅光迪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起创办的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学衡》杂志。他们在1922年以后果真因《学衡》而聚到一起,因为梅光迪的保守在1914年第1卷第3号上刊载的《民权主义之流弊论》一文中就显示出来。
吴宓主要是写旧体诗词,并坚持终生。如第5卷第1、3号、第7卷第3号上的诗,第7卷第2号上的文(《曹君丽明传》)、第7卷第3号上《英文诗话》等。但这些都无法构成与新文化—新文学的对抗。因为白话新文学的主流话语,此时已经构成大众话语的霸权,林纾、章士钊等试图抵抗、瓦解,都没能成功。
1920年第7卷第2号,孟宪承发表《留美学生与国内文化运动》,他引陈独秀的话:“西洋留学生,除马眉叔、严几道、王亮畴、章行严、胡适之几个人以外,和中国文化史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班留学生对于近来的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成绩,恐怕还在国内大学学生、中学学生的底下。”(注:陈独秀此话出自《留学生》一文。原刊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期“随感录”。原话的后面有“至于那反对新文化的老少留学生,自然又当别论”。又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7页。)对此,孟宪承表示:“我们对于这样老实的公平的评判,要坦白地承受,积极地欢迎。”因为“从去年五四学潮以后,国中知识阶级,传播新思潮,速率很快了。在一年的短期间内,发生了许多有趣味有价值的问题的讨论——如孔子问题,礼教问题,文学的改革问题,贞操问题,戏剧改良问题,新村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在这‘如火如荼’的运动中,留美学生是比较的沉寂了。我们加入的讨论很少,差不多表面上没有什么贡献。并且有时发现反对新思潮的言论,如关于国语文学,虽在国内已不成问题,在我们中间,怀疑的人还不少。”最后,孟宪承呼吁:“我们应该觉醒,应该奋起。”“我们对于国内文化运动,应该具更深的同情,感浓厚的兴味。”“应该有分担一部分文化事业的志愿,作相当的有意识的准备。”“也应发抒意见,自由讨论。”
到了1921年,“发抒意见,自由讨论”开始后,《留美学生季报》便从第8卷第1号始,设“思潮”专栏,并有署名“记者”写的《发端》作为引言。“记者”在《发端》中希望留美学生中有思想者,对于国内的新文学运动,无论赞成或反对,当共同研究,尽情发表。《发端》作者特别强调,新旧思想之交接,往往发生冲突。新文化运动实不始自今日。思想虽有新旧之分,惟适者乃存。“余深愿中国人士,保守固有更预备现在及将来”。《发端》还指出,崇拜古人的实际是两种人:泥古者和知古者。前者忘现在及将来,弊病甚大。后者能善用古人之长,为现在及将来之准备。
在展开的“留美学生与国内文化运动”的讨论中,吴宓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章首先刊登出来。他在第8卷第1号刊出了《论新文化运动》,一方面这是他反对新文学—新文学的主要言论,也是他的基本文化立场。此文在他回国主编《学衡》时又被转载(注:吴宓将《论新文化运动》的全文和《再论新文化运动》的大部分内容合而为一,名为《论新文化运动》,刊《学衡》第4期,1922年4月。吴宓同时说明此文是“节录《留美学生季报》”。)。另一方面是他针对孟宪承《留美学生与国内文化运动》所指责的留学生不响应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不知近世思潮的言论有感而发。他说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计。沉溺于淫污之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就新文学而言,他说文学的根本道理及法术规律,中西均同。文章起于摹仿。“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Verse”。“浪漫派文学,其流弊甚大……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他说中国的新文化简称之曰欧化。清末光绪以来,欧化则国粹亡,新学则灭国粹。“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西洋正真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采”。吴宓认为对于西洋文化的选择,“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按之事实,则凡夙昔尊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实验主义者,则必谓墨独优于诸子。其他有韵无韵之诗,益世害世之文,其取舍之相关亦类此。凡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而于西洋文化专取糟粕,采卑下一派之俗论者,则必反而痛攻中国之礼教典章文物矣。”最后他说:“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示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他希望国内的学子之首,宜虚心,不要卷入一时之潮流,不要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
这些言论和五年前梅光迪与胡适讨论文学革命、批评胡适时所说的一样,也是留学生中攻击新文学运动最为激烈,也最具有颠覆意义的一篇。日后在《学衡》发表时,没有能够引起注意,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早已过了讨论期,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段,由旧的破坏到新的建设,并开始寻求对中国问题的彻底解决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说,现实已经超越了文化层面的关注,而进入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用胡适的话说,文学革命早已胜利,且已牢牢占据中国新文化的统治地位了,几个留学生的反对,已毫无力量。
到了1921年的第8卷第2号上,有陈克明的《留学生对于祖国之责任论》一文,她将留学生分为文士派、尚外爱、流学派、名誉派、求学派,并分类评说。最后她强调留学生要“善择求学派,据爱国之精神,坚持道德,以谦恭为本,忍耐为心,踊跃牺牲。以博爱为主”。为中国的振兴而尽其责任。
吴宓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新文化运动》一文发出后,立即引起尖锐的批评。同年第8卷第4号的“思潮”专栏,有邱昌渭的《论新文化运动——答吴宓君》一文。邱昌渭首先指出,吴宓骂新文化运动是“非牛非马”,与其维持“圣道”的苦心相印。说他把文学的意义和用途误解了。他质问吴宓:“以我国数千年的文字专制,始有今日新文化来开放。就进化上而论,英人已远我国百年有余。我国的新进化,恰如呱呱坠地的小孩,带着一团的新生气。你不独不为这新生命作保姆,反来摧残他,置他于死地。你真是一个忍人呵!”同时,邱昌渭也承认,在欧洲,“浪漫派”文学的流弊甚大,但有18世纪的Pope的专制,始有19世纪的“浪漫”来开放。浪漫派在英国以外国家的势力很大,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化、艺术、教育的开放和发展。如今,我们决不能因其有流弊而完全否认其历史作用。最后,邱昌渭向吴宓进言:“所有不能采取的学说,或你以为不可采取的学说,请勿目为‘邪说’。因为西洋学说不是‘白莲教’、‘张天师’类的学说。”
对于邱昌渭的批评,吴宓在同期上发表长达17节的反批评文章《再论新文化运动》[5],对于邱之批评有详细的答复。最后,他对邱昌渭说他维持“圣道”的话,感到“此其名如何之美。此其事如何之大”。他认为要维持的“圣道”,不单是孔子之圣道。耶稣、释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所教,从根本上说都是圣道。要一并维持,不分中西门户之见。
孟宪承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及中国教育研究会的成员,自然也是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奉者,也是中国实验主义教育思想主导下的“新教育”派。吴宓此时是哈佛大学的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的信奉者,这两大思想,在美国学院之间也是矛盾对立的。美国的实验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矛盾斗争,由求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接受而体现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后来,两人都在东南大学任教,分野与《学衡》的人文主义和《新教育》(与《新青年》、《新潮》相呼应)的实验主义对立阵营之中。
另外,顺便提一下,《留美学生季报》在1926-1927年间,由在清华学校的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留美学生来主持,一度思想、学术十分新锐,文学也完全是白话新文学了,不再有旧体诗词。如第11卷第1号上所登的闻一多的著名诗篇《七子之歌》。
旁观者清与当事人的反应
“学衡派”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的一部分,其内在的文化本位精神是上承张之洞、“国粹派”、严复、林纾、梁漱溟、辜鸿铭等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其语境的错位和文化背景的改变(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已颁布法令,小学生教材改用白话文),使得他们反抗的话语和行为陷入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剧境地。面对新文化运动主帅人物的话语霸权,他们陷入了“落伍”和“保守”的困境。当“学衡派”还在反对“文学革命”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已从整理国故的路径走上“文化建设”。海外其他留学生的反应虽是旁观,却有立场。
王徵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胡适的朋友,他在日本时有一封信给胡适,谈到他对胡适、梅光迪之争的看法。他说:“你对于老梅的态度,我始终佩服……我尝讲:文化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与人以新趋向……但趋向不是生活,也不是资生之具……所以我也曾为新运动下一符语,说:‘新文化运动之后,就要学术建设。老梅的反动思想,我极不赞成。我与一班同志,可是要不动声色的往学术建设上一方面去了。’”[6](p.485)事实上,胡适正是走着一条由革命到建设的路。从《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不主义”,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提出,以及《新思潮的意义》中所说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系统主张,可以明显昭示出从革命到建设的内在理路。
1920年4月13日,林语堂在哈佛大学致信胡适,说:“近来听见上海有出一种《民心》是反对新思潮的,是留美学生组织的,更是一大部分由哈佛造出的留学生组织的。这不知道真不真,我这边有朋友有那种印刊,我要借来看看。但是我知道哈佛是有点儿像阻止新思想的发源。”他读了胡适的《尝试集》自序后,对胡适说,梅光迪与胡适争论时所讲的许多问题都是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东西。白譬德这个人对近代的文学、美术,以及写实主义的东西,是无所不反对的。梅光迪师从白璧德几年,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本来我想白话文学既然有了这相配有意识的反对,必定是白话的幸福,因为这白话文,活文学的运动,一两人之外,大多数人的心理,有意识中却带了许多无意识的分子,怎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学理想。但是现在我想有意识的反对是没有的东西;所以反对的,不是言不由心,便是见地不高明,理会不透彻,问题看不到底。”[6](pp.313-315)查《民心》周报,“学衡派”成员在此刊发文章者主要是吴宓。前文说及林语堂曾在哈佛大学听过白璧德的课,但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较大,是胡适的朋友(他留学的部分费用是胡适暗中垫支的),因“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标准说”[7](p.75),在哈佛只读了一年,便转学了。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一年级的学生杨鸿烈(后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在读了《学衡》杂志后致信胡适说:“近阅《学衡》杂志,不胜为新文化活动前途惧!如梅光迪之褊狭嫉恶,固不足论,若胡先骕先生之评文亦应有详密公正之讨究,俾白话诗得无本身动摇之患。”[6](p.189)
出于师承效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学生,不少人受柳诒徵、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的影响,是反对白话新文学的。在美国留学的江泽涵曾写信告诉胡适说,自己同学中的情况:“还有一位郭斌龢君,他是同我同车到美国的。他的言论性情最与梅光迪先生相近,学问或者还高些。他当然是最痛恨你们。他回国后主办《学衡》杂志,并在东北教书。他在哈佛学拉丁文与希腊文,从IrvingBabbitt学。他也许不去见你们(这里的东南大学的学生很有几位,很奇怪的是他们都反对白话文)。”[6](p.159)郭斌龢和范存忠是吴宓1927年7月在清华主持留学美国庚款考试西洋文学门时亲选的两位学生。郭斌龢在南京教书时即与吴宓成为朋友,同时也是《学衡》的作者,范存忠是东南大学梅光迪、吴宓的学生。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新潮派”与东南大学的“学衡派”的对立,在后来的文化视野里越发明显。
《学衡》出现后,新文学家自然有积极的回应。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翼谋、胡梦华的言论都引起了批评。这里仅以周氏兄弟为例。鲁迅以“风声”的笔名在1922年2月和11月的《晨报副镌》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一是之学说”》,是针对吴宓在1922年10月10日《中华新报》增刊上发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动》而发的。吴宓所列的反新文学的刊物为七种:《民心周报》、《经世报》、《亚洲学术杂志》、《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学衡》、《湘君》。其中,《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学衡》三种为东南大学所办。《对于批评家的希望》,是针对“学衡派”的批评家“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弃,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8](p.401)意指“学衡派”借助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思想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是批评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对汪静之《蕙的风》的道德评判。
周作人则以“式芬”的笔名在2月4日《晨报副镌》上登出《评<尝试集>匡谬》一文。胡适在日记上认为周的文章是持中的、公正的。随后周作人又登出多篇批评文章,其中,《复古的反对》、《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是批评胡梦华的。《复古倾向之加甚》、《童话与伦常》是批评柳翼谋的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五伦。《国故与复辟》是批评《学衡》作者、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标榜“注重国故”的言论。《<东南论衡>的苦运》是讽刺胡先骕在《东南论衡》第28期上所作的《半斤与八两》的短文。
周作人对新文学的系统反思是30年代的事,当然集中的体现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其实,他自1928年始,已开始对新文学“探源”,先后有《杂拌儿·跋》、《燕知草·跋》、《枣和桥的序》、《杂拌儿之二·序》、《现代散文选·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近代散文抄·序》、《近代散文抄·新序》、《重刊袁中郎集·序》。其中《现代散文选·序》一文涉及《学衡》。他说:
古文复兴运动同样的有深厚的根基,仿佛民国的内乱似的应时应节的发动,而且在这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五四时代林纾之于徐树铮,执政时代章士钊之于段祺瑞,现在汪懋祖不知何所依据,但不妨假定为戴公传贤罢。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正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更胜一筹了。[9](p.348)
周作人还进一步分析了与“非文学的古文运动”的关系:
非文学的古文运动因为含有政治作用,声势浩大,又大抵是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一支,与思想道德礼法等等的复古相关,有如长蛇阵,反对的人难以下手总攻,盖如只击破文学上的一点仍不能取胜,以该运动本非在文学上立脚,而此外的种种运动均为之支柱,决不会就倒也。但是这一件事如为该运动之强点,同时亦即其弱点。何也?该运动如依托政治,固可支持一时,惟其性质上到底是文字的运动。文字的运动而不能在文学上树立其基础,则究竟是花瓶中无根之花,虽以温室硫黄水养之,亦终不能生根结实耳。古文运动之不能成功也必矣,何以故?历来提倡古文的人都不是文人——能写文章或能写古文者,且每下愈况,至今提倡或附和古文者且多不通古文,不通古文即不懂亦不能写古文者也,以如此的人提倡古文,其结果只平空添出许多不通的古文而已。[9](p.348)
另外,沈雁冰(茅盾)针对梅光迪及其他“学衡派”同人也有尖锐的批评。(注:郎损(沈雁冰):《评梅光迪之所评》,《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29期,1922年2月21日。郎损(沈雁冰):《近代文明与近代文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0期,1922年3月1日。雁冰:《文学界的反动运动》,《文学》周报第121期,1924年5月12日。此三篇文章均收入《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学衡派”主张“文学的古文运动”的失败,与政治无关,是生不逢时,语境错位。郑振铎在为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所写“导言”中,同样强调了“时势”的因素,与周作人之说基本相同。他说:
复古派在南京,受了胡先骕、梅光迪们的影响,仿佛自有一个小天地——他们当时都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教书,仿佛是要和北京大学形成对抗的局势。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的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声势当然和林琴南、张厚载们有些不同。但终于“时势已非”,他们是来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决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撼动其万一的了。[10](p.13)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文化的强化,以往鲁迅、茅盾的批评话语,被政治权力渗透,更具话语霸权。为此,吴宓在《自编年谱》中,特别回味当年《学衡》反抗新文学的语境下,“与《学衡》杂志敌对者”[11](p.235)如鲁迅、茅盾。
虽然说旁观者清,但回放历史时,尤其要看当时的语境。不可单看当局者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逼上梁山》中的“台上喝彩”,更不可只见吴宓日记中对新文学发出的极端仇恨和谩骂[12](p.90,129,144,152)。对于梅光迪多年后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13]一文中的怨天尤人,当以同情的理解。
历史潮流有时就是这么无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的确是时势造英雄。胡适及新文学运动的成功,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3-07-16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吴宓论文; 梅光迪论文; 新青年论文; 学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