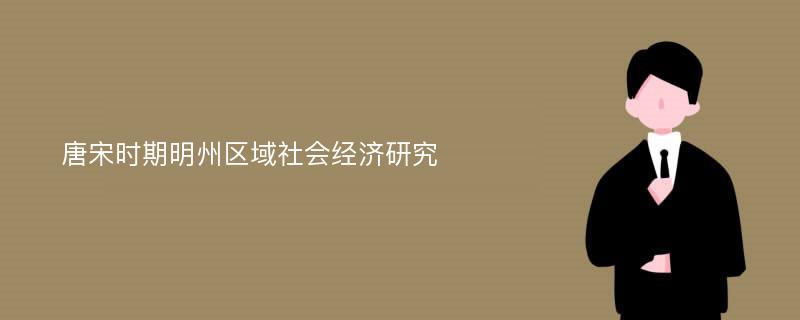
刁培俊, 刘佳佳[1]2010年在《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说法”和“做法”——《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读后》文中研究指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叙事框架"的探索,通过对地方历史的图景描述去发现蕴涵的区域史研究问题等等"说法"及其具体"做法",能否成为中国帝制时期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颇值得认真研讨。如何全面提炼议题、需要讨论哪些议题,方可构建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大致体系?区域史、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哪里?亦即其"说法"在理论层面上的提升与"做法"具体落实问题等,均有待追寻和丰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路。
陆敏珍[2]2004年在《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宁波是今天浙江省的重要港口,其城市的形成始于唐代。由唐至宋,它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州城为中心的亚经济区域。本文的重点是讨论这一亚经济区域的形成过程,试图分析其动力因素,以展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描绘其中的特点。 文章主要从人口、交通、水利建设、技术和制度的变迁及城市建设这五方面着手,将之作为经济区域形成的动力要素加以分析。在传统社会,人口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标志,唐宋时期,明州人口的增长及其分布区域的变化,反映出地区定居模式的改变。交通网络的形成不仅加强了经济区域内部的经济关联,而且在地理意义上确定着宁波及其腹地的范围。水利事业的发达,既是为了扩大居民的定居点、解决粮食问题;同时,因用水而形成的水利共同体也成为区域社会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地方水利工程修建过程中,地方力量凭借着手中的经济实力寻求官府的承认,并得以建立自己势力范围。因此,区域的开发过程也是地方社会的整合过程,表现出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关系。随着人口的增加、水利的建设、交通网络的形成,明州地域开发不断深入,行政秩序的确立,既肯定了这种经济发展,同时又促进了区域经济空间秩序的形成。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以明州为中心的新的经济亚区的出现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构架,经济区域的形成是人类对区域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资源及其自然人文环境进行综合利用、规划、布局和保护的总称,在这一过程中,其动力要素是多样的、复杂的、变化的。本文的目的是展现一种经济发展动态,而不是一幅白描式的叙述画卷,因此,如能勾勒出其中的大致要素,目的也就达到了。
廖伊婕[3]2015年在《宋代近海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科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宋代经济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急速成长,表现在商品化生产的明显加强、市场贸易的网络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手工业的大发展、海外贸易的拓展等诸多方面,这些深层次变化,使宋代经济被喻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宋代商品经济向广度和深度发展,鲜活地体现在市场发展的多种方面。这一时期,以城市、镇市和墟市构成的多层次、网络状的地方市场日益发展,近海区域因与国内外区际经济交流的扩大,逐渐形成其区域经济特色,近海市场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区位和市场特征的区域市场开始出现并不断深化发展,明清时期,近海市场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宋代近海市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下,作为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得以崛起,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内部的重要变化。宋代近海市场是一个长期被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区域市场,它兼具海洋市场与内陆市场的双重特征和双重功能,以海外贸易为支撑,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研究宋代近海市场,对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两岸统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刁培俊, 刘佳佳[4]2009年在《《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读后》文中认为近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史学界蔚然成风。作为形塑区域经济的个案研究,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下文简称陆着)一书,不但史料翔实、论证严谨,而且对区域历史的勾勒和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启人良多。陆着近30万字,除绪论和结
王旭[5]2017年在《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县下基层区划形成“双轨体制”,即以乡为代表的“乡村型”体制和以镇为代表的“镇市型”体制,该体制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北宋中期。前者以管理农业居民为主,包括乡、里、耆、管、都、保、团、社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片状分布的特征;后者以管理工商业居民为主,包括镇、市、务、墟、步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本文选取两类体系中层级最大且最为稳定的乡、镇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体系的形成、运作、管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空间范围则框定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乡篇分为叁章。第一章首先对元丰叁年(1080)太湖流域苏、湖、常、秀四州的乡进行名称考证和空间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宋乡的幅员、边界、户口、层级、“官员”等地理和人文区划要素进行阐释。第二章在全面梳理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划变动和调整事例的基础上,对调整的对象、原因、方式、原则、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几乎所有的基层区划调整都是以乡为基本单位进行,并且乡的性质和职能在宋代时存在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趋势。第叁章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对城市外围特殊的附郭乡进行探讨,包括附郭乡与城墙、城市之经济关系、城市之人群关系等内容,认为附郭乡既是城市向乡村延伸的前沿地带,又是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区,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职能及景观特色。下篇镇篇分为四章。第四章在广泛搜罗宋代太湖流域建制镇的基础上,明晰这些镇的建置沿革、确定地望、绘制成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些镇的时空演变规律。第五章以海盐县澉浦镇为中心,探讨唐宋时代镇由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细节问题,如转变方式、特征、影响等,并通过这一案例对宋镇的政区形态变化、县镇关系、“皇权下县”等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在梳理南浔镇崛起原因、乌青镇兴衰过程的基础上探索两镇关系的演变轨迹,以期加深对新兴经济镇崛起与外部竞争这一命题的认识。第七章首先归纳出归安县东林镇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发现这些特征不仅在宋代的江南市镇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多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市镇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时段且具有继承性的过程。结语部分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并对皇权与县下基层统治、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基层管理中的分权(分责)与兼职特征进行统筹性思考和分析。附录两文则跳出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分别选取“乡村型”体系中的“团”及“镇市型”体系中的“坊”进行个案探讨。
李鑫[6]2014年在《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爪哇海域黑石号、印坦号、井里汶号叁艘唐至北宋时期的沉船资料的分析,结合宁波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以及明州港与东南亚、东亚诸国的贸易材料,我们得以对唐宋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的发展及贸易模式有所了解:8世纪晚期开始,明州作为越窑的启运港,是扬州港对外贸易的附属港口;9世纪晚期,明州作为越窑产品的主要外销港口,直接面向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诸国。明州港和东南亚的贸易模式是与室利佛逝巨港间的转口贸易,其主要商品即越窑瓷器。这种贸易方式保持着一种连续和稳定的状态。而发现于西亚、中东的越窑产品,主要是从巨港运出而非明州港。而在跨越印度洋贸易的过程中,伊斯兰商人作为一股重要力量,不但参与海上贸易过程,还可能通过订货的方式影响到包括长沙窑、越窑等瓷窑产品生产的面貌。
邬莎[7]2017年在《宁波古代城市规划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古代宁波的城市规划史研究,可以透视古代水乡港口城市类型的规划特征,完整体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发展阶段,丰富并深化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历史的整体研究。使用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及历史地图转译等方法,构建以纵向时间轴为线索的基本脉络,确立以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规划制度、城市规划思想为中心的主题内容。采取断代阶段划分的方式,分析不同阶段的宁波城市规划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阶段城市规划的历史传承,对比同类型、不同等级城市的规划异同,探索历史进程中、时代背景下城市规划的变化及其原因。主体内容按划分的阶段分3个部分:一,唐城奠基:“子·罗”双城格局形成。分析唐代明州“中心+片区”空间结构的形成,探讨唐代宁波“子城制度”的形成、“水乡特色”的坊市规划制度的设立以及前沿的罗城城墙规制的探索,分析“堪舆风水学”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与设计方法在子城规划中的运用、因地制宜与尊重自然的思想在罗城规划中的作用以及坊市制度下以子城为核心的“中心式布局”思想模式的使用;二,宋-元转型:子城消失与坊市规划制度变革。分析这一时期政治职能外溢、祭祀功能分散以及港区空间转移等现象,发现城市空间结构较唐代发生“双中心-分散式”的变化,认为宋元是城市空间结构调整、重组的漫长时期。以此为基础,分析子城制度嬗变与坊市规划制度变革的过程。提出新的厢坊制度是用全新的“方位区划”取代“中心区划”布局模式的过程,宋元是这种布局模式的试验期和调整期。提出空间布局及制度变化的根源是官居隔离思想的逐渐消失;叁,明-清演进:街巷制度成熟与空间秩序确立。分析全面的商业网络建构、街巷系统建立及分区格局确立的过程。“北政”是子城选址的延续、历史时期政治职能加剧及儒学礼制建筑发展等作用;“东商”是港贸发展及港口空间的“磁力”;“西居”则与公共游园形成、明清“宅第”盛行及北政、东商的格局限定等有关。明清是街巷(厢坊)规划制度成熟、深化及空间秩序完全确立的时期,是空间发展规律与人为适当引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后提出,宁波古代城市规划史完整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中后期这一发展阶段及州府级地方城市规划的阶段特征,州府城市的定位超越了水乡肌理、港城等特性,创造了行政、军事职能较经济发展的绝对权威,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有性质;古代宁波为近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宁波所城市历史的延续性,亦是中国城市历史的缩影。
王旭[8]2017年在《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县下基层区划形成“双轨体制”,即以乡为代表的“乡村型”体制和以镇为代表的“镇市型”体制,该体制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北宋中期。前者以管理农业居民为主,包括乡、里、耆、管、都、保、团、社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片状分布的特征;后者以管理工商业居民为主,包括镇、市、务、墟、步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本文选取两类体系中层级最大且最为稳定的乡、镇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体系的形成、运作、管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空间范围则框定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乡篇分为叁章。第一章首先对元丰叁年(1080)太湖流域苏、湖、常、秀四州的乡进行名称考证和空间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宋乡的幅员、边界、户口、层级、“官员”等地理和人文区划要素进行阐释。第二章在全面梳理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划变动和调整事例的基础上,对调整的对象、原因、方式、原则、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几乎所有的基层区划调整都是以乡为基本单位进行,并且乡的性质和职能在宋代时存在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趋势。第叁章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对城市外围特殊的附郭乡进行探讨,包括附郭乡与城墙、城市之经济关系、城市之人群关系等内容,认为附郭乡既是城市向乡村延伸的前沿地带,又是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区,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职能及景观特色。下篇镇篇分为四章。第四章在广泛搜罗宋代太湖流域建制镇的基础上,明晰这些镇的建置沿革、确定地望、绘制成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些镇的时空演变规律。第五章以海盐县澉浦镇为中心,探讨唐宋时代镇由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细节问题,如转变方式、特征、影响等,并通过这一案例对宋镇的政区形态变化、县镇关系、“皇权下县”等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在梳理南浔镇崛起原因、乌青镇兴衰过程的基础上探索两镇关系的演变轨迹,以期加深对新兴经济镇崛起与外部竞争这一命题的认识。第七章首先归纳出归安县东林镇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发现这些特征不仅在宋代的江南市镇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多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市镇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时段且具有继承性的过程。结语部分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并对皇权与县下基层统治、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基层管理中的分权(分责)与兼职特征进行统筹性思考和分析。附录两文则跳出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分别选取“乡村型”体系中的“团”及“镇市型”体系中的“坊”进行个案探讨。
魏亭[9]2011年在《明清浙江海洋社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从界定海洋社会概念入手,进一步探究明清浙江海洋社会形成诸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明清浙江沿海民众的海洋生活、海神信仰和海洋意识等方面。认为在这一时期,浙江沿海民众对海洋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海洋已经是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之一。随着沿海民众对海洋开发和驾驭能力不断增强,在浙江沿海民众心理和生活中已形成内容庞杂、名目众多的海神信仰体系,海神信仰体系的形成表明明清时期浙江沿海民众已经具有非常浓厚的海洋意识。浙江海洋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并趋于成熟。本文第一章首先对海洋社会概念进行界定,这也是是文章首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浙江海洋社会形成的标准进行探讨,认为在明清时期浙江海洋社会已经形成。浙江得天独厚的海洋生产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为浙江民众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随着浙江沿海民众对海洋的不断认知和开发,在明清时期,浙江沿海民众“以海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形成,这为本文第二章的内容。第叁章则是对浙江民众海神信仰的研究。认为在明清以前,浙江沿海民众虽已有多海神信仰,但这些海神的职责和神格尚未固定下来。到明清时期,浙江沿海民众信奉的海神已经有了固定的职责和神格,有着各自的管辖范围和管理区域,表明浙江海神信仰体系已经形成。第四章是对浙江民众海洋意识的研究。早在河姆渡文化和跨湖桥文化时期,浙江沿海民众的心理上已经出现海洋意识的萌芽,人们把海洋作为猎取生活必需品的基础之一。宋元时期,一些文人的诗作中流露出浓郁的海洋文化意识。明清之际,海洋意识根深蒂固于浙江沿海民众的头脑中。同时,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也进一步繁荣,涉海民众与海外诸国的接触渠道和方式进一步拓宽,中国也因此被更多的海外国家所熟知。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路线的成熟使更多的浙江民众走进大海,明清浙江海洋社会已经形成并成熟,即为本文第五章内容。
参考文献:
[1]. 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说法”和“做法”——《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读后[J]. 刁培俊, 刘佳佳. 史林. 2010
[2]. 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D]. 陆敏珍. 浙江大学. 2004
[3]. 宋代近海市场研究[D]. 廖伊婕. 云南大学. 2015
[4]. 《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读后[J]. 刁培俊, 刘佳佳.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9
[5]. 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D]. 王旭. 暨南大学. 2017
[6]. 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J]. 李鑫.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4
[7]. 宁波古代城市规划史研究[D]. 邬莎. 东南大学. 2017
[8]. 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D]. 王旭. 暨南大学. 2017
[9]. 明清浙江海洋社会研究[D]. 魏亭. 宁波大学.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