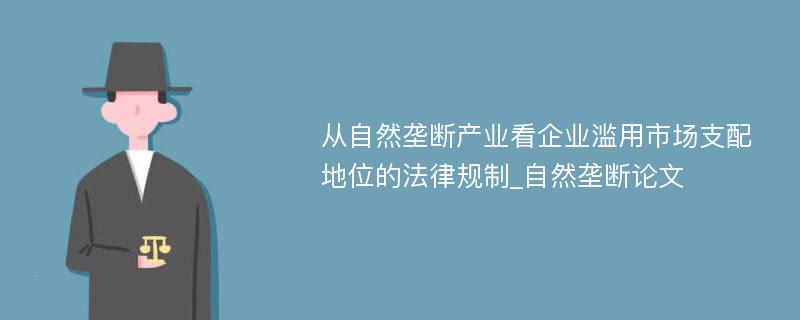
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以自然垄断行业为分析视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制论文,垄断行业论文,地位论文,自然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一则案例引发的法律思考
1990年,新西兰电信行业一家名为克力尔(Clear)的公司决定进入本地电话业务。它与在位企业新西兰电信(Telecom)就互连互通价格的确定方法发生了争议。后者提出按照有效要素定价原则(又称“Baumol-Willig法则”)支付接入费。克力尔认为它过多地保护了Telecom的利益,不同意这种接入费用定价方法,并提出按B & K(Bill and Keep)方式确定互连费用。根据这种方式当“双向”网络互联互通时,每一个网络运营商只向自己网络的发话端用户收取话费并且自己保留,不必向对方支付接入费用。这种方式忽略了在位企业扩张的机会成本,自然也得不到新西兰电信的认可。
双方的分歧明显,无法达成协议,从而引发了诉讼。克力尔以新西兰电信滥用支配地位为由向高等法院起诉。高等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克力尔又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法院支持了它的诉讼主张,判决新西兰电信违反商业法第36条,构成滥用支配地位。新西兰电信不服这一判决,上诉到枢密院(最终裁决法院)。枢密院认为,新西兰电信向克力尔收取连通本地业务的机会成本的行为,不构成滥用支配地位。竞争性市场内的企业在向竞争对手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时,同样会寻求弥补机会成本的损失。商业法第36条只是通过确保充分竞争来消除垄断利润,并不直接规制垄断定价行为(monopoly pricing)。因此枢密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督促诉讼双方重新寻求达成协议。遗憾的是,长达5年的诉讼结束后,诉讼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直到1996年3月才在新西兰政府“如果在限期内不能够达成协议就对本地电信业实施严格监管”的“威胁”下达成妥协(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按照Bill and Keep方式定价)。①
这则案例漫长的诉讼过程和最终的判决结果,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缺乏对竞争行业监管的前提下,反垄断法及其执法机构对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正是由于新西兰政府对电信服务价格的确定不进行干预,互联互通价格由运营商之间达成协议来规定,因此发生争议后,没有行政的救济渠道,只能诉诸法庭。基于反垄断法自身制度功能的局限,及法院面对技术性很强的平等接入、互联互通争议行业知识的匮乏,对自然垄断领域的滥用市场地位行为的规制效率低下。因此,即便竞争法非常完善,并且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单纯依靠这一种规制方式效果也难令人满意②。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制度构建才能实现对自然垄断行业内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有效的规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各国现存的规制模式进行类型化的概括和对比,探索其发展趋势,寻求经验性的答案。然后对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进行深入的制度分析,论证双重规制模式的制度合理性。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制度架构。
二、规制模式的类型化与趋势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这一地位,在相关市场上实质性地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自然垄断行业③引入竞争的阶段,这种类型的限制竞争行为最为普遍。目前而言,按照规制依据及管辖机构的不同,其规制模式大抵可以类型化为:反垄断法与行业法(行业监管制度)共同适用的双重规制模式与反垄断法的统一规制模式。
(一)双重规制模式
所谓双重规制模式,是指反垄断法和行业法都对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规制,反垄断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共享这一问题的管辖权。这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简称“GWB”)第19条、第20条是规制企业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一般竞争规则。德国电信法(简称“TKG”)同时规定了具体规制电信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力行为的条款。根据TKG第33条第1款,任何GWB第19条界定的具有支配地位企业在特定条件下都有义务使竞争者在公平条件下获得它自身享有的和提供给市场的服务。根据TKG第24条第2款,具有支配地位的电信企业决不能仅仅凭借支配地位就额外收取服务资费,除非能有明显证据证明这样做的客观正当性。在执法权限上,一般而言,电信监管机构(简称“RegTP”)和竞争执法机构联邦卡特尔局(简称“BkartA”)共同享有对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管辖权。如果某一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不属于电信法规制范畴,则GWB仍然可以适用,BKartA有权处理这样的案件。
德国邮政行业对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的立法、执法情况和电信行业几乎相同。铁路行业内,基本上也是BKartA和该行业的监管机构(联邦铁路局)共同规制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电力行业是一个特例,没有制定相关的行业性条款,也没有设立独立的行业监管机构,④GWB第19条、第20条毫无任何限制地适用于该行业⑤。
双重规制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反垄断机构与监管机构的积极性与专业性,实现政府的多重政策目标与多种价值追求。但可能会存在不必要的规制重复或冲突。
(二)统一规制模式
所谓统一规制模式,是指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法律规则集中规定在竞争法条文中,行业法中并无涉及,并且不设置独立的行业监管机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执行行业法。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自然垄断行业在总体上被视为竞争性行业,在反垄断法适用及执法中并不能获得特殊待遇。新西兰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以电信行业为例。新西兰电信行业普遍适用竞争法,其执法机构(商业委员会)同时负责执行《电信法》(2001),但最终的行业监管权由法院享有。⑥政府对行业的竞争监管趋近于零,不存在准入限制,对电信服务价格的制定不进行明确的干预。只是在电信法中规定,本地电话服务的价格上涨幅度不能超过通货膨胀的幅度,对其他运营商没有费率限制。互连互通是由运营商之间制定的商业协议来决定。对网络经营者也不设定普遍服务义务,只要求其必须提供与私有化之前相同程度覆盖率的住宅电话,且不能向乡村电话用户收取高于城市电话用户的电话费。
这一模式是考虑到了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的改革趋势,保证了反垄断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减少了不同执法机构之间的摩擦和纠纷的可能。但缺点更加突出:首先是引发了反垄断法的普遍适用性与行业监管的具体制度需求的冲突,及法院执法的广泛自由裁量权与监管规则应然的确定性的冲突。⑦其次,除了跨行业适用的反垄断法外,政府缺乏在必要情形下直接纠正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垄断问题的合法依据,从而导致了竞争法及其执法机构、法院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低效率。
(三)趋势:双重规制模式的广泛采用
现阶段,世界各国对于滥用支配力行为的规制,更多倾向于采用双重规制模式,并明显体现在反垄断法和行业法的立法趋势上。
1.行业法的竞争法化
与反垄断法在自然垄断行业的总体性适用的司法实践交相辉映,行业法逐渐呈现“竞争法化”的趋势。在实体法层面,新行业法引进了促进竞争的规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具有该特定领域“特别竞争法”、“个别竞争法”的特点。⑧行业法在滥用行为发生之前,对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克以平等接入、互联互通的义务,虽然不同于反垄断法对违反行为事后禁止及处罚被动的救济,但在规制要件和违法要件(支配地位、相关市场及有关行为标准的界定)上却存在共同性。在程序法层面,建立类似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业监管机构,似乎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监管机构有着充分的独立性,并且拥有类似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权、准司法权和准立法权。在法律适用上,也吸收、运用了一般竞争法发展至今的成熟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竞争的进一步推进,特定行业内特有的竞争规制的价值不复存在,所有自然垄断行业内企业的竞争行为都纳入一般竞争法的规制范畴。
2.竞争法对相关法律规则的引入
反垄断法不断吸纳行业竞争规则。随着引入竞争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反垄断法对自然垄断行业从“一般豁免,例外适用”变为“一般适用,例外豁免”,适用范围大大拓展。原有的制度框架,在日益拓宽的适用范围下,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德国反限制竞争法(GWB)第六次修订中同时引入了基础设施原理:在第19条第4款关于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行为规定中,增加了第4项“拒绝进入网络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规定。目的是要在两个方面实现协调:一方面是在与网络或者基础设施相关的经济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另一方面是要保护对网络或者基础设施的所有权。⑨
可见,基于统一规制模式在规制实践中的低效率,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双重规制模式,并且明显体现在反垄断法与行业法的制定和完善过程中。因此,从借鉴各国经验与符合制度构建的国际趋势的角度而言,我国应作出类似的选择。当然,这样的分析可能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影响制度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看制度是否符合规制实践的诉求。换言之,还要通过判断类似的经济实践基础上的制度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来确定自身的制度范式。
三、双重规制的制度合理性
传统上,反垄断法与监管制度水火不容。为什么在对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中,能够共同适用?会不会因为制度之间的差异导致规制效果的弱化?笔者认为,在对自然垄断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力行为规制中,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价值相互融合,为双重规制提供了前提;制度元素间的互为补充,为双重规制提供了制度运行基础。两种制度同时适用,实现法律规则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提高了规制效益,最终决定了双重规制的必然性。
(一)双重规制前提:制度价值的融合
随着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的不断深入,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价值,呈现交叉与融合。自然垄断行业的反垄断规制的价值是一个多层的体系。就基本价值层面:反垄断法是通过保护竞争或维护竞争秩序来实现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率;⑩作为监管制度主要依据的行业法,是“通过引入竞争促进行业的稳定运行与提高效率”,(11)确保社会公共利益。实质公平和整体效率,恰是社会公共利益的表现。就具体价值层面:反垄断法和监管制度还有着相似的具体目标:实现低廉的价格、促进创新与高效的产出。(12)
(二)双重规制制度运行基础:制度间的互补性
第一,制度功能的吻合。首先,反垄断法主要功能在于维护(有效)竞争(maintaining competition)。它并不禁止企业支配地位本身,无法凭借一己之力使垄断行业变成竞争性行业。(13)即使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违反了反垄断法,也不一定必须被拆分。监管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引入(促进)竞争(promoting competition)。它通过按照业务类型的拆分,打破一体化的市场结构,为竞争创造条件。可以认为,在促进竞争与保护竞争之间,监管与反垄断至少在电力市场,围绕着实现竞争这个共同目标,能够互相满足对方需求或补足对方缺陷。(14)
第二,规制条件的互为补充。反垄断法侧重事后(ex post)救济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结果,以恢复市场竞争秩序;行业法侧重行为的事前(ex ante)直接控制,引导、监督企业遵守价格制定、平等接入等法律义务,从而构建市场竞争秩序。反垄断法只有在证明了企业行为的反竞争性以后,才进行一种个案性的被动规制;行业法的适用,是持续监管的过程,无须以证明企业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为前提条件。在制度上,反垄断法执法的事后性与监管的事前性紧密结合,提高了规制效率。
第三,制裁和救济方式互为补充。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救济形式有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民事救济。民事赔偿责任可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行政制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罚款)着眼于竞争状态的恢复和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刑事责任意识在更高的层面对违法行为的发生进行震慑。而行业法,一般而言只是规定了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不具备反垄断法的一些有力的救济手段,比如刑事处罚,三倍赔偿。(15)
综上,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在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共同规制中,价值相互融合,使彼此共同促进有效竞争成为可能。在对企业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中,为制度功能、规制条件和救济方式的相互依存,奠定了提高规制效益的制度基础。
(三)双重规制的制度意义
1.实现法律规则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反垄断法是规制整个经济领域竞争关系的法律规则,相对于适用于个别行业的行业性法律,它赋予了执法机构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反垄断法的这种灵活性,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技术条件日新月异的条件下,对自然垄断行业企业行为规制的需要。相对而言,行业性竞争规则更加明确和具体,可以降低企业陷入诉讼泥潭的风险,有利于在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行业吸引巨额投资。(16)显然,这两种制度的同时存在且彼此协调,可实现法律规则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2.提高规制的效益
一方面,行业监管制度的存在可以克服反垄断法的不足,提高规制的有效性。德国的执法经验表明,尽管GWB关于滥用支配地位的条款越来越多地适用于自然垄断行业,但是该法在这些行业的执行中却遇到了困难。尤其体现在分析和证明两个环节。剥削性滥用的结论,只有通过相关市场的价格对比才能得出。但当自然垄断行业竞争并不普遍的时候,相似竞争性市场很难获得。虽然法院后来作出裁决:类似的判断,通过价格与成本的对比而不是相关市场对比就可以得出。这虽增加了灵活性,可通过竞争法规制有关价格性滥用行为仍然是非常困难和不确定的。面对企业的抵制和分析的复杂性,评估和确定相关成本,不会比相关市场的比较容易多少。而且,拒绝交易或者拒绝接入,往往在法院被延缓强制执行。尽管有关争议的细节可以很快发现,但调查和证明行为的违法性的过程是缓慢的。即使已经作出适用竞争法的决定,通常执法行为还要被上诉程序延缓。(17)
另一方面,行业监管的存在,可以降低规制成本。基于与被监管行业长期的密切联系,监管机构掌握有关行业技术、发展动态等方面丰富的信息,拥有大量相关专家。但具体行业监管机构相对于跨行业执法的竞争执法机构,更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与之相对,反垄断执法机构虽然在掌握行业技术信息方面有所欠缺,但独立性更强,对这些行业与一般竞争行业具有的共性的竞争问题判断效率更高。因此,结合二者的优势,无疑更能降低规制成本。
综上,无论是对各国规制实践经验的借鉴,还是对两种制度关系的分析都表明:双重规制模式是对自然垄断行业滥用支配地位行为有效规制的必然选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具体的制度构建,避免不必要的规制重复,以降低规制成本;增加规制的统一性,以减少冲突。
四、双重规制的具体制度构建
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自然垄断行业是垄断与竞争的并存,既包括垄断性业务又包括可竞争性业务。在这两个业务领域都存在企业滥用支配地位的可能。由于两种业务领域的不同性质,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制度在各自范围内规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制度建构理应有所区别。但必须围绕促进有效竞争实现这一目标,合理协调两种制度,使之互为补充。具体而言:
(一)垄断业务领域制度构建
垄断业务领域,主要是指网络业务。因其明显的规模经济性、固定成本沉没性,采取垄断经营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垄断法对垄断市场结构予以豁免。但为了克服垄断弊害,反垄断法严格禁止网络经营者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行业监管机构同时对其进行严格监管。
1.反垄断法对具有支配地位企业的规制
(1)垄断市场结构的豁免。一般而言,自然垄断行业的网络规模越大,竞争性厂商进入市场、销售产品、提供服务的能力越强;系统自身的稳定性,也会因可调度容量的增加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资源可以从过剩的地区供给到需求出现短缺的经济发达地区,提高配置效率。“竞争虽然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但有些市场因其特殊的条件,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只有在限制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作实现合理化就比自由竞争更可取”,(18)毕竟“效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19)反垄断法不但不反对网络业务的垄断,还积极促进网络间的互连互通。
(2)滥用支配地位之禁止。整个自然垄断行业,作为垂直的供应链结构,网络传输是竞争业务无法逾越的环节。反垄断法对如下几种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都必须严格禁止。
第一,歧视行为。它是指经营网络业务的企业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不适当地对条件完全相同的交易对象,就所提供服务的价格或其他交易条件,采取不同的标准或待遇的行为。歧视行为是一种纵向行为,它通常会影响到其前置或后置经济阶段上企业的竞争,会使受歧视者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第二,拒绝交易。它是指某个经营网络业务的企业无正当理由,不适当地拒绝与特定其他网络企业或经营竞争业务的企业交易的行为。前者称为拒绝互连互通;后者称为拒绝接入。拒绝交易行为“既可用来对付横向同业竞争者,又可用来削弱纵向交易者,属于掠夺和阻碍行为的混合物”。(20)在一般性竞争行业,反垄断法主要关注纵向滥用行为。在自然垄断行业,拒绝横向的互联互通和纵向的拒绝接入一样为反垄断法严格禁止。
第三,垄断价格。反垄断法之所以会关注价格,是因为价格可以反映出市场的竞争程度。它关注的是价格是否在有效竞争中形成,价格自身是否合理不在反垄断法的视野之内,(21)需依据行业法中的价格监管规范判断。网络经营者滥用其法定范围内的定价权,限制、消除了竞争业务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或者损害消费者的整体福利,而消费者却无力抗争,反垄断法自然要对市场主体的自主定价权进行限制。
第四,内部业务交叉补贴行为。在改革的初级阶段经过横向拆分后,经营垄断业务的企业往往还同时拥有非自然垄断业务,它极易通过提高垄断业务的价格并降低非自然垄断业务的价格排挤竞争对手。而非自然垄断业务因价格下降而受到的亏损,则可由该企业提高自然垄断业务价格而增加的利润予以弥补。所以改革的初级阶段一方面要做业务的剥离工作(监管问题);另一方面反垄断法更要严格禁止交叉补贴行为。
2.监管制度存在的空间
(1)平等接入和互连互通的监管。自然垄断行业网络企业之间规模并不对等,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状态。一些企业为了保持市场优势地位,只希望通过自身的网络向其覆盖的竞争业务经营者提供服务,联网很难自动实现。而互联互通是经营竞争业务的企业之间增进竞争的前提条件,也是减少重复建设、增加网络效用的有效手段。单纯依靠反垄断法执法,事后规制此类问题,明显缺乏效率。(22)因此,需要监管机构事前克以网络企业平等接入和互联互通的法律义务,为经营竞争性业务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保障生产与传输领域的顺利连接。
(2)普遍服务的监管。普遍服务,是指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应无歧视性地提供的、用户能够承受的服务。自然垄断行业内的网络初始投资成本极高,远远超过可变的边际成本,生产规模越大,单位用户分担的网络固定成本就越少。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者缺乏在地域偏僻、人员稀少等高成本地区的主动投资意愿。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方式是内部交叉补贴,它与引入竞争的改革方向及反垄断法基本制度冲突。借鉴国外解决这一问题的经验,需要政府直接干预,在法律上界定网络企业的普遍义务;同时,建立统一、透明的基金机制:明确基金的来源(以法律规定行业内所有企业都要按营业额提取的比例、程序等)、普遍服务的范围,以及通过竞争机制(如招投标)选择高效使用和管理基金的企业。
(3)激励性价格监管制度。经营垄断性业务的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力,如果不存在任何外部约束,它们会成为市场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就可能会制定大大高于成本的价格,以攫取垄断利润,结果是扭曲分配效率。因此,必须由政府进行有效的价格监管。(23)经济学理论和英美等国监管实践表明,根据各国国情、行业特点适当修正的“RPI-X”(24)价格上限模型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二)可竞争业务领域的制度构建
在可竞争业务领域,反垄断法的适用与一般竞争性行业并无不同;(25)同时,需要监管制度的补充,尤其是在刚刚引入竞争的初级阶段。
第一,市场准入、退出监管。市场经济体制下,进入、退出市场是企业经营自由,一般无须特定机关许可或履行法定手续。但自然垄断行业的可竞争业务有其特殊性:属于可竞争范畴,又不能过度竞争,需要政府适当地准入限制。电力行业售电领域的竞争,会引发所有小用户的结算成本和培训成本。零售准入(retail access)虽是售电端竞争的发展方向,但仍要权衡竞争引入成本与带来收益,从批发性竞争逐步过渡,以免引发过度竞争。
第二,滥用支配地位行为事前监管。对可竞争业务领域的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主要是通过反垄断法的适用来规制。这只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机制,在难以全部禁止或暂时很难奏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由监管机构直接规制。措施包括:制定价格上限;进行利润控制,通过限定利润来抑制市场操纵力。
第三,过渡性不对称监管。在从打破垄断到形成充分竞争的过渡时期,为了尽快改变不对等竞争的局面,需要政府对原有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实行不同待遇的规制。(26)现实的可竞争业务领域,常常存在着进入障碍:新进入者较之拥有优势地位的在位企业明显处于劣势,后者很可能通过限制竞争行为威胁潜在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对称监管制度相对放任自由竞争更具效率。这种非均衡的监管体现了监管者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幼稚力量的保护,培育和激发潜在的市场竞争性。当真正有效竞争的市场形成后,此类监管随即被中性的监管制度取代,以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
第四,业务环节间的协调监管。垄断行业的各业务环节间存在紧密的垂直关系,在一体化经营的情况下,各个业务环节的协调是企业内部事务。基于业务类型不同进行产业结构重组之后,由统一的独立行业监管机构协调不同业务环节,不仅是物理形态上保证垄断行业整体安全、稳定运行的需要,也是保证反垄断规制统一性、有效性的基本要求。
任何制度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对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需要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的同时适用。但这一范式内两种制度可能存在的规制重复或冲突,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构建加以减少或避免;同时发挥两者的优势,彼此相互补充、互为促进,才能最终实现规制效益的最大化。
注释:
①有关案件的详细情况,请参见:Geradin Damien,Michel Kerf,controlling market power in telecommunications:antitrust vs 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29-132.
②Jean-Jacques Laffont,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02.
③现代经济学以成本弱增性为基础的重新界定,只有当一个企业生产整个行业产品的成本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分别生产该产品的总成本更低时,这个行业才是自然垄断性的。See Alfred E.Kahn,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New York:Wiley,1971,ii.ch.4.
④德国电力行业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由作为天然气、电信、电力、邮政和铁路行业共同的监管机构的网络监管局(BNetzA)监管。
⑤Nauta Dutilh,Dealing with dominance:the experience of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ie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pp.158-159.
⑥尽管2001年新西兰电信规制制度作了重要改革,但是法院的最终规制作用仍未改变。Geradin Damien,Michel Kerf,controlling market power in telecommunications:antitrust vs 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27,157-158.
⑦Geradin Damien,Michel Kerf,controlling market power in telecommunications:antitrust vs 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4-157.
⑧栗田诚,张军建译:《日本的规制改革与反垄断法·竞争政策》,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⑨王晓晔:《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的第六次修订》,载《德国研究》2000年第1期。
⑩王先林:《论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11)See Colin robinson,Utility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2,p.167.
(12)Stephen Breyer,Regulation and its Refor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156-157.
(13)Albert A.Foer,Diana L.Moss,"Electricity in Transition: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Energy Law Journal,pp.99-100(2003).
(14)Fabiana Di Porto,Comment:The Concepts of Competition in Electricity Regulation in Italy,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Whose Regulation,Which Competition? ededited by Hanns Ullrich,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6,p.272.
(15)See Robert A.Jablon,Mark S.Hegedus,Sean M.Flynn,"Dispelling myths:A real world perspective on Trinko",The Antitrust Blletin:Vol 50,NO.4/Winter,p.611(2005).
(16)Sebastian Farr,Vanessa Oakley,EU Communications Law,2nd edition,published London,2006,p.33.
(17)Michael wise,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Germany,OECD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Vol.7,No.2,pp.30-31(2005).
(18)Suddeutsche Zementwerke,WuW/E,Bundeskartellamt,421,422.转引自王晓晔:《德国竞争法中的卡特尔制度》,载《法学家》1995年第4期。
(19)[美]理查德·A·波斯纳,孙秋宁译:《反托拉斯法》(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20)参见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21)参见张瑞萍:《反垄断法视野内的价格问题——兼评我国现有相关立法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3期。
(22)See Michael wise,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Germany,OECD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Vol.7,No.2,p.29(2005).
(23)参见王俊豪等:《中国垄断性产业结构重组分类管制与协调政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4-97页。
(24)最高限价模型(RPI-X):其中RPI为零售价格指数(Retail price index),有时RPI也用消费价CPI(Consume Price Index)表示;X为效率因素,代表预期技术进步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参见注(23)王俊豪书,第98—104页,第209—212页。
(25)A.Douglas Melamed,Network Industries and Antitrust,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p.147(1999).
(26)参见常欣:《放松管制与规制重建——中国基础部门引入竞争后的政府行为分析》,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1期。
标签:自然垄断论文;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论文; 网络监管论文; 价格垄断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法律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垄断竞争论文; 监管条件论文; 反垄断法论文; 竞争法论文; 经济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