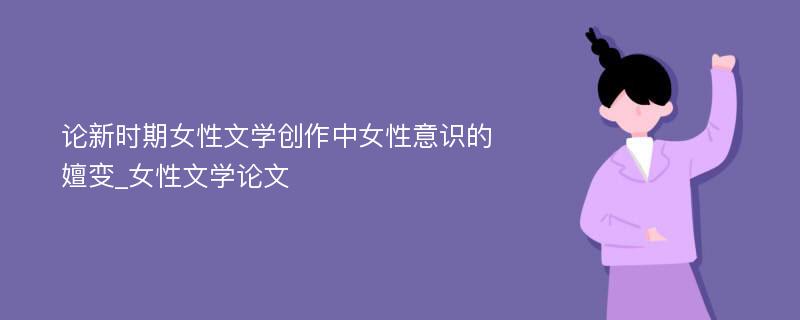
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新时期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也开始悄然萌生。尽管这种萌生完全处于不自觉状态,但也正由于这种近于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可以看出社会发展变化对女性文学的制约及影响。本文力图通过以女性为主角并且注重审视女性心理特征和生存境遇的女性写作,去探索、思考这一时代女性文学的特征,也通过这些作品去发掘我国女作家具有什么特殊的女性意识,并以此对新时期女性文学进行宏观、历史及理论的把握。
“男女平等”神话下的选择与困惑
无庸讳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千千万万的女性走上社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女性的基本生存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获得了彻底解放。男女平等的法律权益,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这种差异基于生理,源于历史,逐渐成为当代触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其中对女性来说最为突出的就是家庭和事业的矛盾,“女人的天职”与“为人的主权”之间的矛盾。新时期女作家最早最集中也最具代表性的反映这类矛盾的作品首推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方舟》戳穿了以往笼罩在我们生活中“男女平等”的神话,小说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令人深思。
对于传统女性来说,家庭往往是囚禁她们的牢笼,是衡量其价值的永恒标准和出发点,同时她们也往往沦为丈夫淫欲的奴隶和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妇女解放的首要一步总是“打出幽灵塔”,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总是对父权、夫权的否定与反叛。《方舟》中所描绘的三个女主人公的丈夫,不是把妻子当作生孩子的机器,就是把妻子当作性的对象,或是把妻子当作自己的花瓶。张辛欣的《同一地平线上》的“他”不满于“她”的努力,只“需要她温顺、体贴、别吱声、默默地做事,哪怕什么也不懂”。而《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那个导演不也因为不满意女主角的粗线条和过于强硬的性格才离开了她的吗?可见社会革命虽然铲除了滋生封建意识的经济土壤,但却很难改变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基于这种情况,她们毅然决然地冲出了家庭。虽然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会发生如鲁迅笔下子君那样的悲剧,然而她们依然不幸,这种不幸是因为旧有生活方式规定的性别角色与新的主体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所产生,是觉醒的女性意识与滞重的社会意识错位所引起,是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观念与先觉者超前的新思想、新追求之间无法同步的矛盾所造成。精神的自由与行动的不自由,理想的高扬与现实的制约,觉醒着的人和不成熟的历史条件,这里正有着构成悲剧基础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女作家对这种自身处境的表现与揭示,无疑隐秘地表现了对“男女平等”的质疑与否定,同时通过女性一己的遭际和苦闷的描写,也折射出整个民族和社会以及意识观念所面临的变革。
与那些美丽、温柔、贤慧而又无私的被男权文化臆造出来的“永恒的女性”不同,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往往是外表强悍、粗糙,没有任何女性魅力的角色。如那个同孟加拉虎一般与男性争高低的女导演(《在同一地平线上》),还有口出村野之语,作风大胆泼辣的女理论家(《方舟》)……这些女性不愿接受男性社会对其性别角色的规定,她们想证明“她们是什么”而不是听从“她们应该是什么”的男性指令;她们不想凭姿色取胜,而是要凭知识、智慧在男女两性的斗争中占一席之地。无疑,这种心理反映了女作家对自身的维护和强烈的自尊、自信、自强精神,但同时也反映了女作家自我认识上的偏颇和局限。这种局限一方面使女性将自身的主体意识断送在似乎是平等的“人”的概念中,同时也使她们的创作很难突破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观念。
英国文学评论家乔·刘易斯在谈到英国的女性文学时指出:“迄今为止,妇女文学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模仿文学,这是出于一种非常自然而又极为明显的弱点:妇女在创作中总是把像男子一样写作当作目标,而作为女人去写作,才是她们应该履行的真正使命”[①]。无疑,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的女作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点。尽管时代的大潮推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这种觉醒是被动的、不自觉的。她们的女性意识仍被一些虚幻的甚至是美妙动听的虚假意识所遮蔽,她们的视域的大部分仍重叠在男性主流意识形态的阴影后,她们尚不是独立于男性主体之外的另一观察主体,她们常常倾向于概念上的人的自觉,而忽略、轻薄女人的自觉。
这种状况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个性意识的进一步张扬而得到明显的改变。从而女性文学也开始由偏激走向冷静,由主观走向客观,由幼稚走向成熟。
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
在《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中,王安忆曾这样说过:“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②]文学既然是“人学”,那么,它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就无法回避这个源于人类心理和生理本能的生命现象。女作家对此的关注既是自然而然的,又有其进步意义。不同于男作家对性的政治性、社会性关注,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作家更注重性之于人生,之于女人的重要意义。王安忆的“三恋”正是以性爱为聚集点,集中透视在纯粹的情与欲的纠葛中,人,特别是女人本体的生命意识和文化内涵。
在《小城之恋》中,王安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经过热烈情欲的骚动与洗礼后,在母性的皈依中圣化自己,达到对男人、对本我的超越,充分表明了王安忆对性爱之于女性人生重要性的一种深刻理解;在《荒山之恋》中,作者同样洞穿了许多女子为不配她们那样挚爱的男人去牺牲去奉献的心理奥秘,因为“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自己的爱情理想”;在《锦秀谷之恋》中,王安忆把女主人公在婚后重新渴望浪漫激情又自我幻想自我陶醉的心理,剖析得淋漓尽致。女性在性爱面前比男性更注重、更强烈需要的不在于性本身,而在于一种关系的体悟,是一个只有女作家才可能有的理解与体悟。因此,尽管王安忆没有高擎着女性主义的大旗去从事创作,尽管她对女性的探索,掩盖在对“人性”的探索之中,还没有明显的女性视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女性批评的角度来阐释她的作品。
同样是性爱描写,如果说王安忆是将人的性欲作为一种本体,一种核心,一种存在,一种动源来描绘,借以探索社会化了的人的自然本质的话,那么铁凝则更注重挖掘表现在传统文化环境的制约下,作为类存在的女性的生命本相;如果说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视点还不明显,还被遮蔽的话,那么铁凝在作品中则用了一种较明显的女性视角,一种女人味极浓的叙事口吻。这突出表现在她的中篇小说《麦秸垛》和长篇小说《玫瑰门》中。
可以说,在《麦秸垛》中,作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从喧嚣的地面勃然而起,挺挺地戳在麦场上”的麦秸垛是大有深意的。“春天、夏天、秋天的雨和冬天的雪……那麦秸垛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依然挺拔”。这一象征意象与女性用乳房哺育一代又一代生命有着何其的形似和神似,它那勃起的力和生生不息的永恒,不仅是女性所代表的土地,生命力和文化的象征,同时更是女性命运轮回的象征。发生在麦秸垛周围的故事,无论是那个作为偷情交换的老效媳妇,非要和前夫“生个孩子”的大芝娘,把鲜血洒向麦秸垛的大芝,抑或不断在自己腹内带上生命种子的四川盲流花子,还是扮演性恋悲喜剧的沈小凤,怀着焦渴感的杨青,他们之中谁又能离开“麦秸垛”和像“麦秸垛”一样的生存呢?尤其是大芝娘与沈小凤那宿命般的命运——她们在明知所爱的人已抛弃了她们的情况下,却执意地恳求对方给予她们一个孩子,对此,作者并没有一味指责她们的愚昧麻木,反而有一种深深的认同、理解和无奈。
作为一个普通农妇的大芝娘,她的面前并没有通向成就、地位、功名的道路,她只有用生育来证实自己为人妻的价值。在这里,母性的行为成了作为第二性的女人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定的唯一可能。如果说这是那个特定时代和文化给大芝娘造成的悲剧的话,那么知识青年沈小凤并没有因为时代和文化风尚的变化从本质上拒绝重演上一代妇女命运的悲剧。她同样以母性行为的渴求作为证明自己性经历的成果,想以此留住与陆野明那短暂而又迷茫的爱情,也使她人生仅有的一次处女代价的付出不被贬值和落空。她的形象无疑体现了一种古老的妇女性态度和性行为的轮回。作者对女性这种认同母性原欲心理的揭示,更深入地触及了女性意识中生命本能和社会文化积淀的影响。
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女性对生命的圆满,对自己给大地应尽的义务,对延展生命的本能的感人的热忱,这种潜藏的、直觉的、无私的母性心理,使女人在似乎“永劫不复”的生命轮回中重复着自己的命运。即便它是残酷的,但女人却能平静、隐忍地接受。对此,作者不胜感慨又不无困惑。作者借《麦秸垛》中的杨青写出了这种困惑。在杨青的意识中时时出现胸脯(乳房)的意象,杨青在潜意识中认同了自己也有的情欲和母性本能,但在意识层面她又竭力想抗拒女人这种本能这种轮回,困惑由此产生,其实这是两种文明冲突形成的困惑,也是意识与潜意识内心交织、互斥的困惑,其基础是对女性生命本能和女性意识的一种既认同又排斥的心理。它象征着女性与传统文化的缠绕比起男性来说要更为根深蒂固,因而女性意识的现代转变也更为痛苦和艰难。
如果说在《麦秸垛》中,作者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大背景下的作为类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它往往是一种共性的描写,而非个性的观照,那么长篇小说《玫瑰门》则不同。在这篇小说中,铁凝更突出更注重作为个体的、个性的女性性心理的剖析。她深入到了女性生命世界最隐秘的角落,勇敢地打开了那扇曾经紧闭的闺门——玫瑰门,从性别的角度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及其脉动。这对于女性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玫瑰门》以一个童年的女孩儿在荒芜而喧嚣的岁月中,生涩迷茫地穿越人生的玫瑰门为线索,在全知叙事人的视点中连贯起婆婆司猗纹这个“永不定格”的女人的一生。它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女人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却没有温馨,也没有欢乐,没有爱,也没有幸福,有的只是丑恶、卑琐、压抑和痛苦。作者一方面开掘出了历史的烟尘和现实的污垢掩蔽下的女性生命特有的柔韧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开掘了女性生存状态中与女性相互关系中特有的狡诈、卑琐和丑恶。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它真实地展示了“一种女性的状态,女性的生存方式和一种生命过程”。无论是司猗纹,还是姑爸、竹西,她们都不是什么优化、净化、美化了的女性,而是处在某种生存状态下,用自己的方式真实地生活着的女性,在她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一个由虚假锻造的“太圆满太坚强”的真实的时代,同时也看到一个个被重重涂饰的真实的人的灵魂,那是被历史的重负和现实的压力挤压得扭曲变形的女性的灵魂。铁凝对这样灵魂的剖析,使文学对女性的透视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
张抗抗在一次谈及女性文学时指出:“我想‘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点,就说明社会尚未具备‘女性文学’产生的客观条件,女作家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假若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爱的怪圈。”[③]这一段精辟的议论恰好说明女作家的自我意识发生了质的转变。女作家由对性的回避到对性的关注再到对女性性心理的揭示,正表明了女性生命意识觉醒的历程。
女性自我的发现
社会的转型,中心价值的分崩离析,自我意义的难以确定,这种主导话语空缺、意识形态功能压抑弱化的时代背景,无疑为当代女性文学寻找自我、发现自己和建立女性话语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机遇。那种非常个人化的女性写作,那种直率的性别话语方式,那种执拗地探索女性隐秘的内心冲动,标志着女性写作立场的移位。如果说在张洁、铁凝她们的小说文本中,女性作家一直是在某种社会政治的历史背景下讲述着她们的女性经验女性故事的话,那么在林白、陈染的小说文本中在,我们所读到的乃是一种极为纯粹的几乎与社会、政治不发生什么联系的女性经验和女性故事。这些女性故事的讲述其意义不在于题材的拓展,也不在于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而在于读者通过“独白式”的叙述,透视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由写作女性传达的对世界、人生的另一种观照方式,以及女性自我发现的艰难历程。
在《与往事干杯》中,陈染叙述了“我”的两个性爱故事,塑造一位通过性爱体验成长起来,拥有独立思考世界和人生能力的青年知识女性肖檬。在叙述中,陈染对青春少女性意识觉醒后既惧怕男性而自守,又渴望男性而脉脉含情的躁动不安,以及女性在生命内部重大变动时期(如初潮)既张皇失措又甜蜜沉静的矛盾心情做了极为细腻、清晰的描述。同时作者还用了大量篇幅描绘女性原欲觉醒之美,传达出女性认识世界即从认识自身身体开始的女性独有经验。
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这个名字颇耐人寻味:新奇、大胆、热烈。将针头与男性生殖器、嘴唇与女性性器官类拟,隐含着作者对独特的女性性经验的张扬,尤其是阳光的引入,更是陈染的一种创造和无所顾忌的女性性态度的标识。女性作为两性关系中性主体出现在陈染笔下,她们不再是男性小说和一般传统小说中被玩赏的欲化对象,也不是一般守身如玉的传统女性形象,更不是张洁小说中禁欲的女性理想者。陈染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敢于以女性性别角色去体验、认识世界,探索两性关系中灵与肉的存在,传达出女性的自我省悟。这正是陈染小说的独到之处。
女性根植于自身性别的复杂性而产生的情绪——情感和生命状态的体验是完全有别于男性的。女诗人翟永明曾经说过:“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甚至私下反抗的心理。事实上,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开启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④]可以说,林白的小说,正把我们带入这样一个世界。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堪称其代表。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回忆的叙事口吻对林多米——我三十岁以前的人生历程进行一次反省式观照。从五岁时开始的手淫,到很早就对自己身体隐秘处的兴趣,到对别人生孩子的好奇,多米——我从小就有很明确的性别意识和那发自女性生命本体的强烈欲望。少年时期对美丽女人的着迷和对同性恋的逃避,青春期朦胧的肉体及精神的觉醒,青年期的第一次性爱经历和成年期的那次“傻瓜爱情”……。作者向我们描述的纯然是一个女人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那独一无二、刻骨铭心的体验。从来很少有人把女性的隐秘世界揭示得如此彻底,如此微妙复杂,如此不可思议。那种坦率和真诚无疑是出于一种执拗地追寻自我、认识自我的渴望。作品中一再写到:“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否天生就与别人不同呢?这些都是我反复追问而又永远搞不清楚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迷惘和困惑,使女作家一次次把眼光投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她对过去、死亡和时光的流逝,比男人有更切身的经验;她对内心的,肉体的以及脑筋里的起伏历程,均感到莫大而深沉兴趣。”[⑤]女作家在寻找她们自己的表现空间的过程中,将笔潜入到女性个体的心灵世界之中,那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作者的内心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女性独白,是一次女性的自我迷恋,是女性话语期待已久的表达。这样一种女性写作,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认为的那样: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其自身就带有“革命性”,它可以进一步证明传统社会的秩序有可能从其内部得以转换。因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女性“一直被摈拒于自己的身体之外,一直羞辱地被告诫要抹煞它,用愚蠢的性谦恭去打击它”[⑥]。“如果某位女作家写的是妇女,她就有可能被戴上‘偏爱’、‘狭隘’、‘妇女的书’等帽子,如果她试着写出她自己最深切的感受,特别是关于性生活方面的,她就会为暴露‘自己的肉体上的体验’而担忧或者为‘亲身感受做一名妇女而忧虑’。”[⑦]然而,今天,女作家摒弃这种观点,大胆地无所顾忌地自由抒写,这本身就表明一种解放,同时也意味着女性意识开始独立并成熟。诚如她们自己所言:“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必否认自己是女人。”因为“只有正视自己才能开拓自己,每一次开拓自己即是对世界的又一次发现”[⑧]。或许正是因为有女作家的这种自觉,才迎来女性文学的繁荣。
结语
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曾经说过:“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⑨]的确,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是女性心理的、情感的、生命的历程,是女性自我追求、自我生存的心灵记录。从“男女平等”神话下的选择与困惑到女性性意识的觉醒,再到女性的自我发现,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女性意识由混沌朦胧到觉醒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而新时期女性文学前后的流变,从根本上不是由粗放到纤细的情感特征的变化,不是由精巧到朴质的艺术风格的变化,也不是由己及他的生活面的扩展,而是创作主体观照方式的质的蜕变:由对外在社会的机械观察、模拟到对内宇宙的探寻;由对特定民众群体言行的记录到对自然素朴的个人及女性经验的体认;由对人情世故的简单划一的政治道德判断到对丰富多彩人生的感知;由集体的大众的遵命文学到一种个人的、女性的写作。无疑,这些同新时期整个文化背景的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使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在恢复“五四”现代女性文学的同时又超越了它。但无庸讳言,女性文学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日臻完美的境界,它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文学一定会不断的走向成熟走向繁荣。
注释:
①转引(美)埃莲、育瓦特《女性文学的传统》,李小江译《中州文坛》1986年第1—2期。
②王安忆、陈思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
③张抗抗、刘慧英《关于“女性文学”的对话》,《文艺评论》1990年第5期。
④转引谢冕、唐晓渡主编《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第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第41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⑥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⑦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7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⑧铁凝:《女人的白夜》第26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