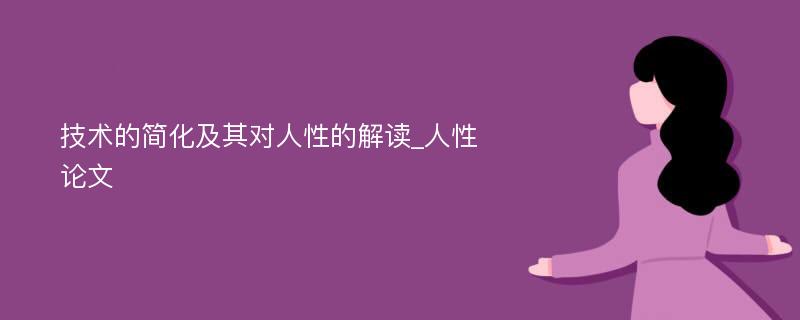
技术的简单化复归及其对人性的解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时间和空间存在形式的技术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且日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决定性力量。人们的各种需求的满足都需要借助于不同的复杂的技术系统,因此人们似乎也普遍接受了技术的这种复杂性。但是复杂性技术在不断提高效率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前提下也剥夺了人的某些本性需求。因此,技术可以走一条简单化复归的道路。
一 技术的简单化复归
1.历史上的简单之美
就像朱光潜先生所讲的“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和哲学的人们如果忽略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1]不仅在今天,从科学诞生之日起人们对美的有意无意地追求就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的过程,并渗透到了科学研究中的各个领域。所以也可以对朱先生的话稍做改动,“研究自然科学技术的人如果忽略美学,忽略了对美的追求,或丧失从美的启示中提高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缺欠”。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们对美的追求无非体现在适度、匀称、和谐、有序和简单几个方面。本文仅从简单性视角入手,通过回朔历史上人们对简单之美的追求,面向现代技术的复杂化现实,探讨技术的简单化复归的必要性。
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学科领域都有大量的案例能够体现人们对简单之美的追求,在此我们仅列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说明。
古希腊时期人们对世界本原的探讨就体现着一种对简单之美的追求。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都试图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如“水”、“火”、“气”等。这种归纳和推测不可避免地体现了他们思想的局限性,但从这里我们不可否认他们的这一努力实际上也是在追求一种和谐和简单(不管在他们认为这种和谐和简单由谁来创造的)。
在中国中代也有相同的认识倾向,在《周易》中就有所谓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说法,认为“太极”是世界的本原,由太极生出天地两仪,由天地生出春夏秋冬四时(四象),四时运行形成“八卦”(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另外,老子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有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陈述。从人们对世界本原是什么的探讨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人们从自己的实践生活中领悟到自然界总是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进行物质构造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清楚明了。在天文学史上,哥白尼体系之所以能够挑战并战胜托勒密体系,就是由于坚持了我们的“宇宙有一种最终的简单性和美”[2]这一最初设想,在与复杂性相比较的过程中科学家坚持了简单性是美的一个标准的结果。“对于现代物理学家来说,相信宇宙有一种最终的简单性之美,更是他们的最高信仰。”[3]罗森(N·Rosen)在回忆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时也提到:“爱因斯坦一生都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获得正确描述各种物理现象的理论。在构造一种理论时,他采取的方法与艺术家所采取的方法具有某种共同性,他的目的在于求得简单性和美(而对他来说,美在本质上终究是简单性)”。[4]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从简单性原则出发构造的理论屡见不鲜。奥卡姆剃刀原则就是非常好的应用简单之美的实例,“‘应该淘汰多余的概念,并建议在说明某类现象的两个理论中应该选择更简单的。’所以爱因斯坦说,‘自然科学的简单性也是一种事实,而且正确的概念体系必须使这种简单性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保持平衡。’”[5]
2.技术自身发展的简单化复归需求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种观点:没有先进的技术我们似乎什么也做不了。在这部分人眼中先进与复杂也有一定的正比关系,越复杂的技术似乎越高级。如果把我们现在应用的技术置于古希腊的时空框架中,那么这种技术还能否称之为“高级”呢?我认为称为“不可及”或许更恰当一些,因为技术高级与否是要与应用它的人的知识结构、生活境况相对应而谈。对于大众来讲,所谓高级的技术应该是在人们对它有能力并且有可能理解和革新它的时候才能更恰当地称为高级,否则在两者之间存在有太长的时间间隔就不能称之为高级的技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技术的物化形式非常简单,表面看仅仅是许多不同的按钮而已,就像亚里士多德(B·C·Aristotle)所预见的那样,“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只须一个指令,甚或预知人们对它的要求,完成它所胜任的工作。”[6]为此,有人评价亚里士多德是预言自动化的第一人。与此相比较而言,我们现在所应用的机器只是比他所预见的要复杂一些而已,“按钮”代替了“逐步的手动指令”即为现代自动化的普遍现实。可以说,现代机器就是用无数按钮掩盖了工作原理。
实际上,“现代技术不仅掩盖或模糊种种事物的物性,它还掩盖或模糊存在物的存在,最后掩盖或模糊它自身的存在。技术不能用更多的技术来解释。”[7]这样就导致了技术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除非专业性的人才,否则某一项特殊的技术就以一个具体物体一样呈现在人们面前,对某些人来说,它所包含的技术要素就是一个黑箱,人触及到它的机会非常少。就像数控机床一样,每个工人都能熟悉地将一切参数输入进去,这样一个毛坯就会制成一个成品。如果我们假设这部机器的可靠性非常高,那么尽管每天都应用它,经过几代人的应用之后,人们(哪怕是当时最能熟练应用它的工程师)对它的内部结构和功能也会越来越陌生,以至于把它当成是一种陌生的机器。这种掩盖性的实质就是一种隔断,隔断了机器和人之间的那种联系,从而更深层次地使技术对于人来讲更为复杂。
技术本身的发展是复杂的,技术的进步不等于不同技术之间的简单的组合,有些技术是不能用广义的文字表示出来的,这就是我国学者所定义的隐性技术,因为即使最好的“翻译”,总是会译丢一些思想,有些意思也不可能译出来,所以技术要持续发展,首先就应该被人们所掌握,这里我们不妨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探讨技术的传播问题。只有在人类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以及人从用广义语言对技术的记载中对技术进行了解和掌握,这样才能促进其发展,否则单凭徒弟的自我实践是不够的。另外,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所能接受的技术也应该属于不同阶段,所以对特定的人群应该有特定的技术发展形态,这里还需要提到舒马赫(E·F·Schumacher)所定义的“中间技术”,即一种大众生产的技术而不是大量生产的技术,大众生产的技术的应用可以缓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两者的一种动态平衡,实际上,这种技术的采用目的是为了帮助人,而不是使人成为机器的奴仆。
对于真正复杂的技术,当它不具备简单化的可能时,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对它进行简单化处理,即每个人都应尽自己所能相应地对这种复杂技术的一部分进行适当的理解(技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能以多种多样复杂的技术集合体形式而存在)而不应该畏惧它的复杂形式,只有这样才是技术真正的进步的前提。
现在学术界一直都在探讨技术创新问题,这里我们不妨也做一个纵向比较。技术越复杂,技术本身的创新周期就越长,我们可以引用一个调查结果来分析这个问题。加尔布雷思对福特公司的调查发现:从一项计划开始到任务完成的周期大大增加了,另外固定性也增加了,“加尔布雷思评论说:‘如果福特和他的助手(在1903年)决定在任何时候将汽油动力改为蒸汽动力,而金工车间只需几个小时就能够适应这种变化。’那么现在,即使想变换一个螺丝,也得几个月的时间。”[8]当然古代的技术很简单,容易产生出创新成果,同时也正是因为它的简单性才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思考和改善它。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主体是人,而技术则是客体,主客体相互依赖,主体对客体有能动地把握,将客体放在主体的认知框架中,在主体实践技能和所掌握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主客体很恰当地融为一体。这样在适当的条件下创新才有可能。所以,从技术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技术应该走一条简单化复归的道路。
二、技术对人性的遮蔽与解蔽
1.复杂技术对人性的遮蔽:现实人与个体自我的分裂
通过劳动,人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种群。同时,劳动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发展个性的极好环境。但是这里的劳动与现在技术生活中的劳动不同,前者是人的心身共同参与的活动,而后者则是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规则化动作而已,也可以说现代技术生活中的劳动对人而言是一种间接的生产性工作。“在现时代,人们是像沙粒一样被搅和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一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这架机器中,他们时而占据这个位置,时而占据那个位置。他们不是这样一种历史实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历史实体中,他们注入他们自己的个体自我。”[9]
技术的发明和利用过程最初让人体验到了获得自由的可能,但随着技术自身的发展,它逐渐演变为一种破坏自由的恐怖。人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强,而这种情况与人的本性正好相反。人已经变成了一只可随便替换的齿轮,那么哪里还有个性而言呢?无个性当然也就没自由,变化着的生活带来了生活的变化,同样,变化着的生活也造成了认识者自身的变化。当人被拉到物的水平上,被限制于机器时,他已经丧失了人的实质。技术的应用使人摆脱了体力劳动,使体力劳动在人的劳动中所占的比重降低,这似乎是使人的生活变得简单化了。但是在今天这种简单化却隐藏着人对自己本性复归的复杂化程度的意识,人不能摆脱技术,但人确实需要获得自由,满足个性。
技术的复杂性也使得“这些事物与人疏离了,人所面对的无非是一些可转换的功能而已。技术已使人不能直接‘在场’。新的任务就是,通过技术现实化的诸方法而再次达到人的实存在世上所有事物面前的直接‘在场’。”[10]也就是说,技术虽然是物化为人可操作的实物形态,但人在操作它们时需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个性、也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人在场。所以,表面上看人的日常生活变得简单了和快乐了,“人似乎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可以听他所喜欢的音乐……可惜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对技术系统构成挑战,甚至技术为人类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但这些多样化仅在技术的作用范围内才有效”。[11]从更深层次上看,人的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空虚了,以至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追求那个被忘却了的“真正的个体自我”。
尽管我们都不愿意承认,但是“现实的人是规则化的人”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劳动的快乐逐渐被程序化和高效率的工作所替代。“如果正确理解与应用劳动的特征,那么……它孕育更高尚的人,并使他生气勃勃,激励他尽力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它将他的自由意志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陶冶他的动物本性,纳入进步途径。劳动为人提供了显示自身价值高低与发展个性的极好环境。”[12]用劳动来丰富和满足自己个性的生活方式被阻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是自由发展的个体。所以,现代的人已经不是理想中的个体了,他逐渐变成了规则化的人。
2.简单技术对人性的解蔽
人与技术的矛盾引出许多现象,这里我们仅谈人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人与技术之间的矛盾的现实。关于人与技术的矛盾人们不能忽略它,也不能超越它,只能面对和解决它。人与技术是否能和谐发展呢?这个问题如果放在技术发展之初的背景下,那么它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但是技术在不断发展,技术所能触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大,人在不断的进步,并且人已经脱离了“吃、穿、住的满足”是“幸福标准”的时代,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自由——发展个性的自由、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自由。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尽管技术把人固定在机器上,但人所追求自由的能力却是无限大的,所以矛盾出现了。此时的人与技术需要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和水平上重新达到一种和谐。人们不能期望去彻底消除技术而获得自由,人也不能希望完全依靠技术来获取自由,一方彻底地依赖另一方就等于加速了自己的毁灭过程。遗憾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现实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熟练操作按钮的现代人不会解决真正的技术问题(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专业的技术工作者来解决。这种解决方式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社会中人力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并不能很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而且纯粹的技术工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也没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需要大致了解技术,以便在适当的场合和条件下自己也能充当技术工作者的社会角色,这种不同社会角色集于一身的事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体现出人与技术和谐发展的态势,同时它也是解决人与技术矛盾的一个方式。在多数情况下,“当技术问题被处理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沉默无言,但这并不是一种意义深刻的沉默,而只是空虚的表现。”[13]所以,与其说矛盾解决了不如说从表面上看矛盾解决了,但它仍然存在与人与技术之间。
总之,在技术与人的矛盾的解决不应该采取“分”的形式,而应该采取“合”的态度,做到“万物相遇而不相害”的程度。这种“不相害”的出现主要依赖于人的把握。按照道家所说“常”的概念,我们认为人只有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同时有效地调节自己这样才能达到“恒常”,要保持这种“常”的状态,人还应该学会“明变”,不能总用一种方法和一种模式来处理问题和看待事物。技术自身的这种复杂性也抹杀了人对它进行全面理解和实际掌握的可能性。所以为了“明变”技术还应该走简单化复归的道路。
如果按照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来看,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将是经历了“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对物的依赖阶段”的“人的全面发展阶段”。也就是自由个性的获取和满足阶段。可以看出,人们现在所从事的劳动与人类所追求的“自由个性的获取”应采用的劳动不同,这种不同也就是现代复杂技术造成现实人与个体自我分裂的一个主要的体现。就像马尔库塞(H·Marcus)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技术还为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很大的合理性,并且证明,自主、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14]当然,他的论断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现代技术有必要调节使其复杂程度与现实人所能接受的程度相适应,以使现实人成为真正的“个体自我”确是一种合理的倾向。
三、结语
技术美可以体现在多种不同的方面,但是简单性一定是它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恢复简单明了比沿着越来越高级和复杂的方向前进更为困难。任何一个第三流的工程师或研究员都能够增加事物的复杂程度;但要使事物回复到简单化却需要某种真正的洞察力”[15],专业化程度越高创新就越难实现,所以技术的简单化复归就显得更为重要。就像舒马赫所预想的那样:“可以做到给技术发展规定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新方向使技术发展回复到满足人的真正需要,这也意味着适应人的真正大小。”[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