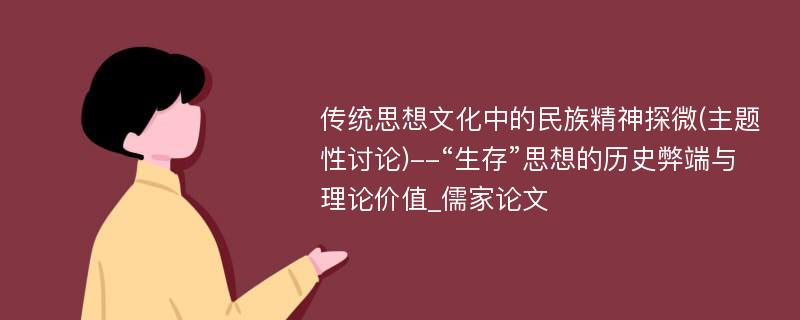
探寻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专题讨论)——“立德”思想的历史流弊与理论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弊论文,思想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民族精神论文,立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立德”是古人所谓“三不朽”之一。“三不朽”思想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范宣子与鲁国的叔孙豹的一段对话。在此,叔孙豹完整地述说了他对于人生价值的理解:此生此世有无价值,活的是否值得,就看在现实世界中,生命价值是否得以实现,而生命价值的实现可以通过立德(成就德性)、立功(建功立业)、立言(著书立说)三项事业来达成。在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中,儒家特别重视和强调的是立德,所以说“大上有立德”。在儒家看来,人首先要立德,即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具备高洁的道德品质,从而生前受到赞颂,死后有人推崇,达到“不朽”。儒家立德思想在其演化中曾产生过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但是,它也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意义,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道德建设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思想资源。
一
尽管儒家的人生价值观自孔子起即带有鲜明的泛道德化倾向,但早期儒家对于人生价值的设想还是比较全面完整的,并没有将人生价值等同于纯粹的道德价值,“三不朽”的理想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对于人生价值相当完善的设想。换言之,早期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是全面型的而非(道德)“单向度的”(马尔库塞语)。但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儒家思想在其发展中逐渐强化了立德在人生价值方面的重要性,这种倾向在宋明理学那里达到极致。“儒家以天道的名义将人伦关系无限地泛化,再用泛化了的人伦准绳作为评判价值的唯一尺度。这种天人不分的道德主义,除了抽象化和绝对化以外,同时还意味着简单化和片面化。”[1]儒家立德思想的流弊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其一,在权利主体上,将人与天相分离,将道德的权利归于天,将道德的责任和义务留给人,因而形成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的分离。比如,在宋明理学家所倡导的三纲伦理中,建基于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不合理要求被当成“天理”而加以颂扬和维护,而属于人的基本权利范畴的合理需要则被当成“人欲”而要求人们“克之、克之而又克之”。
其二,在义务主体上,将个人与群体、社会相分离,把全部道德责任都落脚于个人“修身”,看不到道德与社会结构、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之间更深刻的联系,因而导致长期忽视公德体系(法制、社会体制、公共规范)建设,或公德私德不分。
其三,在道德的内容上,割裂义利,强调“利”是低于“义”的价值,未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物质价值、经济价值是精神文明价值的必要基础,因此产生在人格上卑视甚至排斥物质、经济和技术的倾向,导致义利、理欲之间的对立互斥。由于人生的价值取向失去了现实的利益和权利基础,导致道德教条下的人格与现实生活产生对立。
其四,以思孟学派为主的儒家心性论有见于“正面心性”,而无见于“负面心性”,结果只倡导人人努力成德成圣的“最高限度的伦理道德”,漠视“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起码的、约定俗成的法律与秩序等等)。对立德的强调,隐含着过于重视人性“高层”的一面,忽略人性“低层”与“深层”的一面,导致把“外在的社会规范”与“内在的价值之源”混而不分。
其五,儒家所宣扬的道德理想主义有夸大伦理原则的绝对性而压抑人的个性的一面,到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用来宣扬禁欲主义、维护封建官僚统治的工具,甚至酿成“以理杀人”的人间惨剧。伦理原则本身一般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如果赋予它的具体历史内容是不合理的,则此伦理原则往往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例如,“存天理,灭人欲”作为一般命题的合理性被程、朱赋予它的三纲伦理要求所湮没和窒息。在程、朱这里,三纲就是“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不得僭越,不容亵渎。这样一来,其结果就极其严重了。君纲、父纲自不必说,单是“夫为妻纲”一条,在历史上就不知枉送了多少人的青春性命。
其六,作为一种典型的世俗道德学说,儒学因缺乏工具理性或工具价值这种现代社会最为急需的价值观念,而难以独立开出现代资本主义这一较高级较先进的社会形态。儒家是以人的崇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为目标而致思的,现代以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与人观念,完全不在儒家的视野之中,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关于人的基本预设,如人是“理性人”的观念、理性计算的合目的性行为方式的观念,在儒家这里完全付诸阙如。“这种缺失在稳定是尚的伦理政治理论推导中并非是致命的,而是跳出这圈子,到以发展是尚的现代社会,这种缺失才影响理论前途。”[2]
其七,以人类社会主体自身为认识视野的极限,以主体内省代替对外在对象的观察认知,这种哲学传统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儒家确认人是伦理人,而伦理内源于心、外推于人。内源于心而圣,外推于人而王。因此,它没有必要拟定一个对象化世界的存在。同时,由于伦理内源于心,也就没有必要建构一个认知心。切己自反,反躬自省,是伦理人伦理觉悟的“方法”。因此,有一颗圆善的道德心是伦理人的本质特征,理性认识的建构在伦理政治思路中完全没有必要。这造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举步维艰。
二
虽然儒家立德思想衍生出很多弊端和危害,但立德思想也具有其显而易见的理论价值。对立德的强调,使得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为一个德性伦理主导的社会,并直接间接地形塑了中华民族精神。
其一,不为物役的价值取向。儒家人性说暗含了一种观念,即“人性”或人性之“善”本身是有层次、有等级的。这些层次、等级依其包含和体现天道之充盈圆满程度而形成,精神生活(精神价值)比物质生活(物质价值)具有更高的价值。儒家肯定食色物欲、功利之求乃人性所固有,但认为它们并不代表人性之善的本质,不能体现人之天性的完满和充足,所以是等而下之的东西;仁的需要、礼的需要、义的需要等等,则是高层的、最具人性特征的、能够体现人性之善的需要,应该受到崇尚。例如,孟子认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3](《滕文公上》),强调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有价值。孟子还区分了“天爵”与“人爵”。“天爵”是人的“仁义忠信”等善良本性,这是不能让渡的人的尊严之所在;“人爵”则是指权势、财富、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等。就人之所以为人而言,重要的是实现“天爵”而不是追求“人爵”。所谓“孔颜乐处”,是指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乐观情绪的高尚精神境界。
其二,自作主宰的人生信念。儒家一贯强调,自我生命的拓展和升华,并不附丽于外在的价值,并不建筑在他人的肯定之上。也就是说,自我生命的超越本身就具有自主性,毋庸他人的褒扬。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4](《述而》)强调人在意志上可以自做主宰,人本身就是价值意识的创造者。每个人都可以主宰自己,选择自己的生命方向。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同时每个人也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桀纣和盗跖一类的人只是由于未能“尽心”、“尽性”、“知性”[3](《尽心上》),所以才沉沦了。在为人的态度上,儒家一向肯定每个人都有自我超越、变成圣贤的内在动力。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肯定人的自我超越的无限可能性。孟子引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3](《滕文公上》)荀子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5](《性恶》)他们都肯定每个人只要立志,皆可以成圣成贤。在为学的态度上,孔子强调“为己之学”,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在于自我生命的升华,为此他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4](《宪问》)。
其三,舍生取义的生命情怀。《易传·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人生价值学说的初始点,是对人的自然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肯定。“子之所慎:齐、战、疾。”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侮者,吾不与也。”[4](《述而》)荀子说:“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5](《强国》)儒家向来贵生重死,对人的生命深表关切和珍重。不过,儒家在肯定人的自然生命价值的前提下,更为重视人的精神生命价值,即仁义,认为后者才是生命存在的本质,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固然应该追求肉体生命的欢愉,但更应该追求真理、德性和事功,后者才是人生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是高于自然生命价值的价值。没有精神,没有人格,就没有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的超越,在于对精神生命价值的显扬。个体生命的真实性和完整意义在于进于德,止于至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儒家把追求高尚精神境界和人格尊严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不论外在条件如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道德境界,“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人格意志,是做人最重要的。孔子的“杀身成仁”之说和孟子的“舍生取义”之说,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典型表述。《孟子·告子上》所说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是说人格尊严比生命更为可贵,人格屈辱比死亡更令人厌恶。这都是强调一个人的人格价值比生命更为宝贵,人格价值超越生命价值。
三
对于“立德”的现实意义之探讨,应该基于对儒家立德思想所具有的正负两方面价值之清醒认识。立德思想具有的理论价值,完全可以继续在现时代发挥其威力,而立德思想曾经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危害,我们仍然需要慎加防范。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对儒家立德思想加以扬弃,它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有价值的精神资源的。儒家立德思想可能具有的现实意义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挺立个人尊严。立德,意味着人应该有志向、有尊严、有成就地活着,真正地作为一个人活着。这就是要力求担当道义,仁爱民众,弘道于天下;力求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那样,为后世树立一个做人的榜样;力求能在修身的基础上齐家治国,平治天下(“立功”、“立言”),追求生命之“不朽”。正是有了这种人生价值观,有了这种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才“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6](P641),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和英雄人物,出现了许许多多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典范。他们都是从不断的“修身”、“立德”中获得异乎寻常的精神力量的。
其二,正确对待物欲。立德思想强调义利之辨。在义利的对应性规定中,义是基于纯粹伦理原则的行为取舍标准,而利是对伦理原则的纯粹性有危害性影响的对应范畴。在此,义是与利相排斥的一种伦理实践原则。“君子义以为质”[4](《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4](《阳货》)。儒家特别强调在伦理意义上义远胜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里仁》)。重义还是重利,由此也就成为君子与小人得以划界的分界线。在当今时代,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功利与道义的矛盾冲突依然十分突出,而儒家立德思想在义利之辨上的观点当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其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对德性的主要规定是仁,而“仁的基本内涵是爱”[7]。爱包括亲亲之爱、对他人的爱和爱物之心即尊重、爱护、保护自然界。其中,爱物之心尤其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将对自然万物的爱护作为仁的内容。宋儒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按照儒家的这一传统,仁的发用流行,不能仅限于家庭(家族)和人类自身,而应扩展到自然界。一种更普遍的爱才是完整的、终极性的爱。这一点,在当代生态伦理学出现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当代人类生存环境出现危机,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的儒家伦理,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儒家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决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做自然界的“主宰”。人当然具有主体性,但人的主体性只在于“为天地立心”、“参赞化育”,即放开胸怀,破除物我、内外的界限,完成自然赋予人类的职责和义务。这也是人的终极目的。这种价值观念,无疑有助于人们调整和控制物质需求,减少和避免恶性消费,从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立德”为上、“立德”为大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看重精神生命价值的倾向,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以主体性之实现和德性之实现为其价值观重点的倾向。这种人生价值观培养出无数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高洁之士,激励着人们不断开拓进取、自强不息。儒家以“立德”为主的“三不朽”人生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指归。这种人生价值观进而凝聚为一种民族精神,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