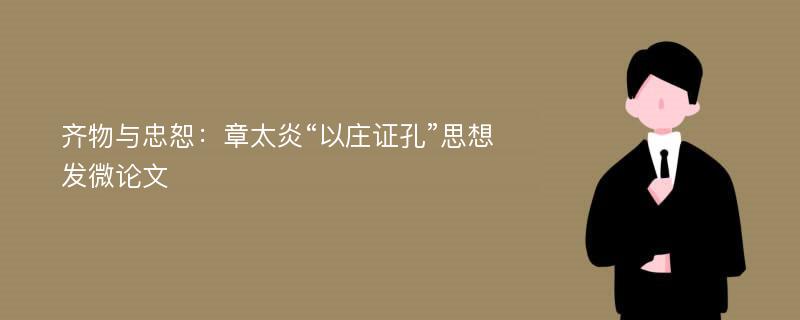
齐物与忠恕:章太炎“以庄证孔”思想发微
李智福
(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西安710000)
摘 要: 章太炎曾自称其学为“以庄证孔”,即以庄子的“齐物”哲学解释孔子的“忠恕之道”,他因此提出“尽忠恕者是惟庄生能之”“齐物即忠恕两举者”等理论。太炎将“齐物”与“忠恕”相贯通的内在理路是:他先以佛学之“真如”——“平等”证庄子之“无我”——“齐物”,再以庄子之“无我”——“齐物”证孔子之“忠恕之道”。如果说传统学界对“忠恕”的解释是“有己之忠恕”,那么,太炎基于庄学和佛学的“忠恕”则是“无己之忠道”与“有己之恕道”两相并举,传统解释重“恕道”,太炎更重“忠道”;传统之“忠道”是反己尽己,太炎之“忠道”是虚己尽彼。他强调以“恕道”推度他者之时,同时需要以“忠道”整全地观照他者,此庶几有补儒学“絜矩之道”之所可能产生的为孔子所始料未及的种种负面影响。太炎先“以佛证庄”再以“以庄证孔”之思想关怀,是以东方古典思想对所谓公理、自由、平等等近代西方启蒙理念进行批判和重建。
关键词: 章太炎;孔子;庄子;忠恕;齐物;《齐物论释》
章太炎(1869-1936)自况其治学心路历程云:“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1](P71)他早年投身革命,以法后王之荀韩、尚古文经之刘子骏[2](P47)对抗康有为法先王之孔孟、尚今文经之刘子政。故仅仅是作为“良师”和“良史”的孔子在其心目中地位并不高,甚至还多有诋訾,比如《訄书重订本》引日人远藤隆吉言称孔子为“支那之祸本”[3](P132)。太炎后来“转俗成真”,精研庄佛;又“回真向俗”,重估孔孟,并最终将孔子提升到“阶位卓绝”之最高位置,甚至承认半部《论语》治天下,非尽唐大无验之谈[1](P71)。这种真俗之转,后者不是对前者之扬弃或否定,而是对前者之摄纳、补救或新证。民元三年,太炎因詈骂袁世凯称帝而被囚禁北京龙泉寺,此期间他开始重估《周易》《论语》等儒家经典,并以其佛学和庄学为背景对孔子思想进行新证,其自许为“以庄证孔”[1](P70),并最终提出“尽忠恕者是惟庄生能之”,“齐物即忠恕两举者也”[1](P70)[4](P262)等“以庄证孔”思想。究竟在何以意义上,太炎有这种惊世骇俗之论,其曲款原委、苦心孤诣及其思想境域不可不深察。
我们自拟的“宣肺通窍汤”中:荆芥疏风宣肺,苍耳子、辛夷开鼻窍,芳香化湿开窍,黄芩清上焦之热,藿香、石菖蒲、公丁香芳香化湿浊,有化浊宣壅,开窍通闭的功效,赤芍凉血清热,活血散瘀,有利于充血的消退;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辛香善升,能上行头目巅顶。《珍珠囊》认为其能“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为“血中之气药”;黄芪益气升阳;升麻、葛根与路路通相配,升清降浊,调畅气机。
一、有关“忠恕”之解释及其可能产生之歧解
关于“忠恕”“恕”等思想,儒家原始经典至少有以下之陈述:
经本次历时两个月的创作,我们成功制作出盲人用温度计,我们还申请报名参加学校科技创新比赛。在实验中,同学之间互相协助,在体会到成功的同时,我们同学之间的情谊也得到了增进,也学到很多知识和技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5](P72)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P166)
对于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来讲,虽然在可靠性、可行性方面较高,但是必须对看管和监督工作高度关注,这是两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是出现了很小的不足,都容易对全局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挑战。第一,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初期阶段,必须坚持在日常维护上不断的进行,无论是水源的滋养,还是害虫的处理,都要尽量选用天然手段来进行,减少化学成分的融入,这样才能促使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无污染水平获得更好的进步。第二,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监督工作实施,要求定期开展汇报分析,发现损害情况,或者是成长状况未达到预期标准,都要给出正确的答复,要加强生物技术的分析和利用,最大限度的对监督内容保持足够的丰富性。
基于发挥出纪检监察队伍的作用目的,需要做好第二步工作,依靠利剑消除腐败现象。不同党支部进行选举的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相关流程规定选举纪检委员。其中以廉洁公正、勇于担当且严于律己作为评判标准。从当前对企业的了解可知,该公司中的17个基层党支部都配备了专门的纪检委员人员。依据相关规定加以严格考核,对各个基层纪检委员发放相应的岗位职责规定,凸显出一定的监管效果。
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5](P23)
如若本着“文本循环”的解释原则解释“忠恕之道”,《里仁》篇所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并没有给出“忠恕”之具体解释;《卫灵公》篇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似仅指“恕”而不是“忠恕”。另外,《颜渊》篇“仲弓问仁”、《公冶长》篇“曾子曰”等都有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重复强调,《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显然从《论语》而来。但此处却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解释“忠恕”二字,显然是将“忠恕”理解为偏义复词。特别是上文引《卫灵公》篇孔子将“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称之为“恕”而非“忠”,可见孔子心目中“恕道”比“忠道”更重要。这样,《中庸》以偏义复词即偏义于“恕”而释“忠恕”并非没有根据。所谓“忠恕之道”实则即主要强调“恕道”,而“恕道”之义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三致其语,《中庸》再次强调,殆非偶然。那么学术史对孔子之“忠恕之道”如何诠释,我们看几种代表性诠释。
(一)王弼、皇侃之诠释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其中有引王弼注)云:
总干渠全长26.2 km,设计流量25m3/s,涉及张店、淄川、临淄3个区的4个乡镇。除灌溉外,总干渠还担负着向一干渠及二干渠提供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任务,现状最大放水流量达10m3/s。总干渠多为傍山渠道,弯道较多。渠道为浆砌石矩形断面,有7 m宽、4 m宽两种。总干渠上主要建筑物有土洞12条,石洞7条,箱形渡槽2座,U形渡槽6座,砌石渡槽16座,水闸16座,主要桥梁15座,灌溉自流口42个。
1. 潜艇组与岸勤组肾结石的患病率:某部官兵肾结石患病率为3.1%,潜艇组与岸勤组肾结石的患病率分别为3.2%和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另做亚组分析:低、中、高年资官兵潜艇组与岸勤组肾结石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生:我觉得“( )”里的文字,写的是人物说话的语气和神态,而“ [”后的文字,我觉得好像是人物的活动。
按,皇侃解以“尽中心”解“忠”,以“忖我以度于人也”解“恕”;王弼以“情之尽”解“忠”,以“反情以同物”解“恕”。二者之解,名相有异而无实质不同,二者皆将“忠”视为“恕”之前提,只有“尽中心”“尽己情”才能做到“以我度人”“反情同物”,最后实现“推身统物,穷类适尽”之儒者抱负。这种解释始终是以“己”为出发点,无论是“尽心”“反情”还是“推身”,都是尽己之心、反己之情、推己之身。这种诠释不足之处是,它潜在地蕴含着以己推彼、强彼合己之可能性。
参考李娟的实验方法,采用Mixolab混合实验仪对空白和加酶全麦粉的热机械学特性参数进行测定。实验条件选用 Chopin+标准。试验前,首先需对待测粉样的水分含量进行测定。整个测试过程获得的参数(C1、C2、C3、C4、C5、α、β、γ)释义见文献[12]。
(二)程子、朱子之解释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云:
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 。”[5](P72)
无论是“忠恕之道”还是“絜矩之道”本身都是一种很理想的接人待物之则或为政经国之方。但这种原则潜含着歧解的危险,如果将这种原则不顾境域而抽象为一般的为政原则和人际原则,可能会造成以己出发而强以彼合己,从而忽视“己之外”之他者存在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丰富性,以己矫彼,以我夺人,结果恰恰会戕害他者存在的自然权利、个体自足性,这样,以忠恕出发而走向忠恕之反面。可见,学术史上对“忠恕”之解释始终没有从根源上对这种可能导致的“忠恕悖论”进行彻底消解。换言之,无论是《论》《庸》《学》元典还是晋宋以至于晚近之解释者,想必都不会承认“忠恕”或“絜矩”本身会导致“恶”,但经典未言之处或解释未尽之处恰恰造成思想的“留白”。这种“留白”一旦为别有目的者所使用或者为理解不通透者所使用,潜在的歧解难免变成一种现实的恶。原因在于,学术史上对“忠恕之道”之解释始终是以“己”为出发点而推扩言之,如前文引王弼言“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果然如此吗?而导致现实之恶者正是这个出发点之“己”没有被好好地正视、规约、批判和反思。章太炎所言“尽忠恕者是惟庄生能之”正是在“己”上大作文章,为“忠恕之道”所面临的歧解和危险进行拔本塞源。
(三)邢昺、刘宝楠之解释
邢昺《论语注疏》云:
孟子云:“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尽焉。”[5](P350)
忠,谓尽中心也。恕,谓忖已度物也。言夫子之道,唯以忠恕一理,以统天下万事之理,更无他法,故云而已矣。[7](P52)
刘宝楠《论语正义》云:
道在一贯。持其枢者,忠恕也。躬行莫先,而方迻以为学,则守文者所不省已。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夫彼是之辨,正处正位正色正味,其候度诚未可壹也。守恕者,善比类。诚令比类可以遍知者,是絜矩可以审方圆。物情之纷,非若方圆可以量度也。故用矩者困,而务比类者疑。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以知忠恕于学,犹鸟有两翮,而车之左右轮。[10](P433-434)
邢昺之解释受王弼、皇侃影响甚深,尽中心为恕,忖己度物为忠,以己方物,当无新意;刘宝楠则以《论语》篇章内部循环之解释为主,并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基础再加推扩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刘宝楠这种解释将学术史上诸家“推己及人”所蕴含的解释悖论明朗起来: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尽己之性”)而推扩至他人(“尽人之性”)是不是意味着只见其同而不见其异?如果只见其同而强以“己之性”加诸“人之性”,则如何解释为孔子所认为端木赐难以企及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5](P78)之圣人心印?这样的“忠恕之道”可能会走向“忠恕之道”之反面。这就需要我们以一种批判的、反思的方式来理解孔子之“忠恕之道”。
(四)“忠恕之道”与“絜矩之道”
与“忠恕之道”相关的另一种儒家重要传统即“絜矩之道”。“絜矩之道”见于《礼记·大学》:“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第,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5](P10)郑玄注云:“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耳。治国之要尽于此。”[9](P1869)朱子解释为:“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5](P10)郑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与朱子所言“因其所同,推以度物”都是强调以己出发而推己及人,可见“絜矩之道”之哲学基础实则亦是“忠恕之道”,二者并无大异。
当前,从沿黄景区所在县城到沿黄景点的交通问题仍是困扰众多景区发展的瓶颈。交通建设,首当其冲的是全面升级沿黄地区的二三四级公路、增发县城到景区的客运班车或建设快速路,与沿黄公路相结合,满足自驾游客和散客出行需求。
程朱之解释,一方面继承王弼、皇侃之“忠”为“尽己”、“恕”为“推己”之义;另一方面则上升至“忠体恕用”“理一分殊”之存在论高度。程子“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之出发点依旧是“己”,这种“体用”还是“己之体”与“己之用”之关系,由“忠”至“恕”还需要“以己及”“推己及”;朱子虽然强调“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这种存在状态不必以“推”知,但终究还是承认“借己推己”不失为一种方便法门,故他在《中庸章句》中云:“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5](P23)程、朱之解比王、皇之解虽然有所突破,但其出发点并无二致,仍旧是以“己”为发轫点。
二、“体忠恕者独有庄周《齐物》之篇”
由于意识到传统学界对孔子“忠恕之道”所潜含的歧解或危险性,太炎在继承传统学者解释之基础之上,给予“忠恕”一种全新的理解,并将对孔子“忠恕之道”的唯一体认者许以庄子,他认为庄子的“齐物”哲学实是“忠恕两举”之道。
(一)“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
相比于作《訄书初刻本》(约完成于1900年左右)时代,太炎在作《检论》(完成于1916年左右)时代已经锋芒渐掩,他乃能以更理性之眼光审视传统。《检论》一书将孔子视为“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10](P430),并慨叹其“洋洋乎美德”[10](P430)非孟荀所能及。因此,当他以这种眼光观待孔子之时,孔子不再仅仅是“良师”和“良史”,他将“东方四圣”(浮屠、老子、孔子、庄子)与“西方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提[10](P433),可见他心目中之孔子已然是“圣人”兼“哲人”。作为哲人之作,太炎给《论语》下评骘云:“诸所称说,列于《论语》者,时地异制,人物异训,不以一型锢铸,所谓大道固似不肖也。”[10](P433)不难发现,太炎笔下之《论语》颇有老庄之风。太炎看来,孔子其道之核心即“忠恕之道”,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忠恕”?传统以“絜矩之道”定义“忠恕之道”有没有不妥之处,太炎云:
君子忠恕,故能尽己之性,尽己之性,故能尽人之性。非忠则无由恕,非恕亦奚称为忠也? 《说文》训“恕”为“仁”,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即为仁,引申之义也。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8](P153)
这段文字,太炎首先肯定孔子之“一贯之道”即“忠恕”,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忠恕”,太炎给出定义:“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如果说他以“心能推度”定义“恕”是对传统说法之继承,那么他以“周以察物”定义“忠”,则与传统提法完全相反。古来学者皆将“忠”定义为尽己心、反己情,太炎则将其定义为“周以察物”,即周尽地体察并还原他物。他进而以治学为例,指出“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闻一知十、一隅三反都是“恕事”,但仅仅用类比之方法探究万物总不能得其究竟,因为不能作到对他者之“文理密察”,规矩可以考察方圆,但万物丰富差异绝非方圆之能穷尽之,岂能以规矩而范围之。因此,他指出,对万物之体察不能仅仅用“恕”去比推,关键还要用“忠”去切察,只有用“忠”才能“辨其骨理”。这样,“忠”与“恕”就形成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关系,仅用“恕”不能知万物存在之具体殊相;仅用“忠”则不能疏通知远,举一反三。只有“忠”“恕”并举才能真正地知天地、懂他人、识万物。这种“忠恕”之可贵之处就在于既承认从己出发而起推度作用之“恕道”,又强调以虚己之精神而切察他者之“忠道”。学术史上对“忠恕”之理解皆是以己推人,太炎对“忠恕”之理解是以物为物,以人为人,将“己”暂时悬置。太炎批判荀墨之学云:
荀卿盖云:“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此谓用忠者矣。“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此谓用恕者矣。夫墨子者,辩以经说,主以天志,行以兼爱、尚同。天志、尚同之末,以众暴寡,惟尽恕,远忠也。荀卿虽解蔽,观其约束,举无以异于墨氏。[10](P434)
太炎看来,墨子以“天志”“尚同”“兼爱”为说,只知“恕”而不知“忠”,忽视殊相或少数,因此走向“以众暴寡”之专制;荀子表面上是既知“忠”也知“恕”,但将其一分为二,故其实也是只知“恕”而不知“忠”,没有意识到“忠”与“恕”之间是彼此摄纳、互为前提之关系,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一样缺一不可,荀子未能明乎此故其政治上也最终走向专制(“约束”)主义,“举无以异于墨氏”。那么真正能既能做到“推度”又能做到“周察”的是哪位哲人呢,太炎看来非庄子而莫属:
体忠恕者,独有庄周《齐物》之篇,恢诡谲怪,道通为一。三子之乐蓬艾,虽唐尧不得更焉。此盖老聃之所流传,儒道所以不相舛牾,夫何掩昧良哉!《三朝记》小辩亦言忠恕。[10](P434)
太炎固然没有将孔子之“忠恕”的继承者许以墨荀,但也没有将盛言“强恕”和“推恩”的孟子许以善体忠恕者,何以故?如前文所言,太炎这里对“忠”之定义已经看不出前人“尽中心”“反己情”之解释,而是将前人颇多强调之“己”抽拔出去,而庄学正是不以“己”作为“忠恕”推扩之本才能意识到“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如以己去推扩,则万物必有“恢诡谲怪”之分,相反,以无己之精神体察万物,就会发现万物皆有其自足之价值,大者不多余,小者无不足,蓬艾不为野蛮,唐尧不为文明,癞女不为丑,西子不为美,此所谓“道通为一”,因此,太炎得出“体忠恕者,独有庄周《齐物》之篇”之结论。特别是,太炎还引不被古代学者所重视之《三朝记》引证庄子:“‘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内思毕心曰知忠,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此言以忠恕为学,则无所不辩也。周以察物,疑其碎矣。物虽小别,非无会通。内思毕心者,由异而观其同也。”[10](P434)太炎以“由异而观其同”解释“内思毕心”,当是以虚灵不昧之心体认万物从而让万物同异互见。总之,如果说传统学者对“忠恕”之诠释多强调“同”,即“己”与“人”之共相,那么太炎对“忠恕”之理解更强调“异”,即“己”与“人”之“殊相”,“夫食味、别声、被色者,物之大情也。木豕奄不知燕昵之好,喑聋不知笑语之欢,而馶戾转甚者,以其远人情”[10](P437),意识到每一个存在者都是一个独异的个体,并周尽地理解他者,尊重他者,“忠”不是忠于己而是忠于彼;“恕”不是以我出发推其同而是以彼出发见其异,而庄子之“齐物”哲学正会归于此。
(二)“有己之恕道”与“无己之忠道”
可见,对“己”之悬置或虚化而行“忠道”重“忠道”是太炎之解与前人之解之最大不同。章太炎在《菿汉昌言》引《史记》相关记载,认为老子传授给孔子者主要就是“毋以有己”一语,并指出“毋以由己,无我也”[11](P78);《检论·道本》则直接认为孔子之“忠恕”来源于老子,[10](P437)合参此两说可知太炎所理解之“忠恕”为儒道之共法。如果说前人之“忠恕”是“有己之忠恕”,那么太炎看来,“恕道”之推扩不能无己,而“忠道”之尽物则不能有己,换言之,“忠恕之道”是“无己之忠道”与“有己之恕道”两相并举。太炎在《检论·道本》篇重申其“忠恕”义云:
人与飞走,情用或殊,转验之人,蚳醢,古人以为至味,燔鼠,粤人以为上肴,易时异地,对之欲噬,亦不应说彼是野人,我有文化,以本无文野故。转复验之同时同地者,口之所适,则酸腐皆甘旨也,爱之所结,虽嫫母亦清扬也,此皆稠处恒人,所执两异,岂况仁义之端,是非之涂,而能有定齐哉。[17](P122-123)
本文选用多个方向的音源对所设计的算法进行了性能测试。测试中信号的方位以(x,y,z)的形式给出。测试环境为本人工作的实验室,实验室中充斥着混响、回响、键盘鼠标敲击声及一些人的细语等噪声。测试中采用48 kHz的采样频率对语音信号进行采样,实验中选择语音帧长为32 ms。
这段文字,太炎认为后世儒家和佛家对物之观照或有高下亲疏之别,如儒家讲求爱有差等,亲亲之杀,尊尊之别;释迦有有情无情之判,六道高下之别;在老子则一视同仁,刍狗万物,太炎看来老子这种思想实在是孔子忠恕思想之源头(按太炎多次称孔子出于老子)。老子之所以有这种哲学造境,乃是他能做到“不持灵台而爱其身,涤除玄览而贵其患”,“不持灵台”与“涤除玄览”都是在对“己”之扬弃,而以虚灵不昧之心、以无我之我来观照天下万物。太炎在解释《老子》第十三章“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时云:“谓贵用其身于为天下,爱用其身于为天下,所谓施身及国也。此则讼言贵也。诸言生死无变、哀乐不动乎胸中者,谓其至无贵爱其身,宝穑大患而不辞者,谓其供物之求。”[10](P435)《老子》原文颇有儒家推恩的味道,太炎则作出反常识之解释,认为老子之言是以“无我”的精神来“供物之求”,这才是真正的“忠恕之道”,只有此道之发用流行才能实现《中庸》所言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P37)。太炎复引《庄子·天运》之“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来证明庄子正是老子此道之持护者。可见,太炎看来,老、孔、庄三家“忠恕之道”了无二致,与晋宋诸公“有己之忠恕”正好相反。太炎这种“忠恕”观在《菿汉微言》里再次被强调:
仲尼以一贯为道为学,贯之者何?只忠恕耳。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恕则已尽矣。人食五谷,麋鹿食荐,即且甘带,鸱鸦嗜鼠,所好未必同也。虽同在人伦,所好高下,亦有种种殊异。徒知絜矩,谓以人之所好与之,不知适以所恶与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职耶?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齐物即忠恕两举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厌弃己身,而以头目脑髓与人,是以自己所不欲施人也。诚如是者,鲁养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财及无畏施人,忠之事也。[1](P70-71)
⑩⑰世界贸易总差额、世界贸易出口总额和世界贸易进口总额数据均来自IMF下属的DOTS商品贸易数据库。世界贸易总额由世界贸易进口与出口总额加总算出。计量单位均为百万美元。
太炎此段文字是其思想中极吃紧之文字。太炎首先肯定孔子之“一贯之道”即“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徒知絜矩”只是“恕”而不是“忠”,因为世界千差万别,万物所好未必尽同,即使同在人伦其所好亦有酸甘美丑之异。仅仅是从“己”去推扩可能会导致“以人之所好与之,不知适以所恶与之”,我之所好可能即彼之所恶,可见“推己及人”“絜矩之道”并非为周延而无懈可击的“忠恕之道”,以“己”出发去推扩去絜矩只是“恕”而非“忠”。针对《荀子·非相》篇所言“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太炎提出与之相反之观点,并给出“忠”之进一步解释:
顾凡事不可尽以理推。专用恕术,不知亲证,于事理多失矣。救此失者,其唯忠。忠者周至之谓,检譣观察,必微以密,观其殊相,以得环中,斯为忠矣。今世学者亦有演绎、归纳二涂,前者据理以事量,后者验事以成理。其术至今用之,而不悟孔
忠谓尽中心也,恕谓忖我以度于人也。言孔子之道,更无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己测物,则万物之理皆可穷验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推身统物,穷类适尽,一言而可终身行者其,唯恕也。[6](P49)
子所言,何哉
这里,太炎看来荀子式之“推度”自有其不足,只是“恕”而没有“忠”,并进而给出“忠”的几种内涵性特征:亲证;周至;观其殊相;以得环中。“亲证”即设身处地地想彼之所想;“周至”即让万物自在地整全地呈现;“观其殊相”即观察其特殊性并尊重其特殊性,承认世界之多样性并体谅个体之差异性;“得其环中”正是庄子哲学认识论之最高造境,而“得其环中”必须以“吾丧我”之“无己”为前提,太炎看来庄子“得其环中”正是孔子所言之“忠”,实则亦即“无己之忠”。《齐物论》之“吾丧我”是“忠”之前提,“齐万物”是“恕”之造境,只有以“无我”之“忠”才能有成就天下万物之“恕”,没有“忠”之“恕”可能会出现鲁君以养人之方式养爰居之笑话;没有“恕”之“忠”仅仅执著空言而不能真正以平等之眼光、以还其自身之方式来观照万物,职是之故,太炎称庄子之“齐物”为“忠恕两举”之道,“忠恕两举”即互为条件,彼此摄纳,“恕道”强调普遍性,“忠道”强调独异性,“忠恕两举”即普遍性与独异性之统一,不过太炎更强调独异性,即“忠道”。太炎并借故批评二程,按程伊川曾以为佛法的出世主义是厌弃己身,以自己之厌弃己身而号召天下人皆厌弃己身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10](P462)。太炎看来,佛法本来“无己”,了悟生死实相,因此以“法”施人,并不是“推己及人”和“絜矩之道”,而是让众自由选择,随缘布施,绝无外在之逼迫。同时,“非自出生死外,孰能无死?非自出生死外,必不能抍入于生死中,又何自私之有”[10](P462),由于大乘佛法能谛视缘起性空,万法唯识,因此以“无己”之精神施财于人并以无畏之精神救人,完全为他人着想,这才是真正的济天下赈生民之“忠事”。换言之,大乘佛学之出发点是“人”而不是“己”,因此是真正的“忠”。况且,“出世法中,哀愍众生,如护一子,舍头目脑髓以施人者,称菩萨行,而未尝责人必舍。责以必舍,便非哀愍。在世法中,有时不死节者,不齿于人,是乃责人以必舍也”[10](P462)。这里,太炎认为,大乘佛学发悲悯心,会舍身救人,但“未尝责人必舍”,他们之所如此,是因为佛学不会以“己”出发去推度别人,即其“己”被消解;相反,世间法中,自己“死节”的同时也会“责人必舍”,别人不死节就会被低看一等,这是以“己”出发来推度别人,“己”被执著着。
总之,太炎看来,佛学和庄学的真精神才是孔子“忠恕之道”的真精神,这种忠恕之道与传统忠恕诠释学有三大区别:其一,传统的“忠恕之道”偏义于“恕”,而太炎的“忠恕之道”偏义于“忠”;其二,传统对“忠道”之理解是反身尽己,太炎对“忠道”之理解是虚己尽彼;其三,传统解释往往“忠”“恕”分举,太炎则将之两相并举,缺一不可。宋儒朱子曾经云:“天地是一个无心底忠恕,圣人是一个无为底忠恕,学者是一个著力底忠恕。”[12](P685)庄子“齐物”哲学所体现之“忠恕”正是“无心底忠恕”或“无为底忠恕”,学者在“著力”于“忠恕”时时刻需要反思自己“著力”处会不会强加于人而违反“天地”和“圣人”之“忠恕”。
转化投入机制制约了成果能够产业化的前期孵化 在整个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主要涉及二次开发、中试、小规模生产等一系列环节,而这个过程中呈现出周期较长、前期投入巨大、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就从当前学校在科研方面的实际情况而言,在科研成果转化上经费不是很充足,首先是由于事业经费与其相独立,不作为投资经费支出,而其他的投资渠道还没有建立或形成;其次是社会化的投资主体也十分缺乏,渠道也不畅通,特别是当社会资本投入后,涉及学校知识产权保值增值方面受制度上限制,使社会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不高;最后,一些相对来说大型的企业的有效介入以及相应的一系列风险投资方面的有效形成与运作,使得转化过程中所需的环境没有形成。
三、《齐物论释》与“忠恕之道”
大致说来,辛亥前后数年,章太炎之学经历从古文经学、荀韩之学到法相学(世亲、慈氏一派)、再以法相学之“真如”解释庄子之“齐物”,终以庄子之“齐物”证孔子之“忠恕”之过程,从这一思想历程来看,大概的确与其自况之“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暗合。太炎以法相唯识学解庄,但其问题意识远不是传统庄学如何会通庄佛之问题,甚至也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如严复一样以所谓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接应西方民主、自由、民权、进化、启蒙等主流价值之问题,而毋宁说是对近代盛行的一系列西方主流价值之批判、消解、反思和重建。太炎在以佛解庄之前,对佛学特别是唯识学评价极高,认为慈氏、世亲之说“理极不可更改”[13](P192);但他慢慢意识到以涅槃寂静为归趣的佛学自有其弱点,指出“若专用佛法去应世务,规划总有不周”,“(佛学)方法论实在没有完成”[13](P159),即佛学没有给出具体之应世方法,故开始以庄学提撕佛学,以庄学之“俗”补救佛学之“真”,以庄子之“外王”补救佛学仅言“内圣”之欠缺,并因此认为《齐物论》为“内外之鸿宝”[1](P26),更提出“命世哲人,莫若庄氏”[14](P149)这一振聋发聩之口号。太炎之所以如此推重庄子乃是他看来《齐物论》可以赈救“人与人相食”[15](P3)之天下,可以“经国”[16](P102),可以“衣养万物”[17](P76)。而其保民治国救天下之术实则即“忠恕之道”。《齐物论释》四万余言,谈不上卷帙浩繁,但的确头绪繁复。本节只能围绕“忠恕之道”择其要而言之。
(一)不齐而齐:真如——齐物——忠恕
如前文所言,章太炎对孔子“忠恕之道”的理解与前人之“一——多”关系相比更表现出“零——多”关系之特色。这个“零”大体即基于佛学之“真如”和庄学“丧我”而构建,这个“多”即指佛学所谓“众生平等”与庄子之“万物一齐”,“真如”——“平等”、“丧我”——“齐物”、“无己”——“忠恕”此三对概念基本可以一一相印证。这里,章太炎特别突出并始终强调的是万物之“不齐”,太炎指出:“(《齐物论》)先说丧我,终明物化,排遣是非……因物付物,所以为齐。”[17](P73)此处所谓“丧我”和“物化”都是“无己”,在这种造境观照之下,因物付物,万物为齐,这种齐物不是像许行一样将万物划为一齐。太炎坚信“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1](P169)的法相学是科学,他之所以以法相学解庄,就是冀图在“科学日益昌明”[13](P192)之世让庄学变成科学。因此,《齐物论释》基本是在以法相学“名相分析——名相排遣”这种既具方法论又具存在论特色的思辨中完成。太炎认为世界一切皆阿赖耶识所变现,换言之,一切存在都不过是自心影现,而见分与相分皆无自性,世人不悟,触相生心,心体起灭,恒审思量,这最终成为个人不自在之源,也是人类苦难、国际倾轧之源。庄子《齐物论》所言与法相学所言了无不同,“齐物本以观察名相,会之一心。名相所依,则人我法我为其大地,是故先说丧我,而后名相可空”[17](P78),是非本是名相,名相背后是法我二执,“吾丧我”既破我执,又破法执;法我皆破,则名相即空;名相既空,则是非不起。唯当是非不起、见相兼空之时,方能亲证一如,万物各以其本色涌现自身,再以是其所是、以物付物之方式平等地观照万物,成就他人,尊重异俗,这是太炎《齐物论释》以“真如”证“齐物”,复以“齐物”证“忠恕”的内在思路。他在《齐物论释》中指出:
最观儒释之论,其利物则有高下远迩,而老聃挟兼之。仲尼所谓忠恕,亦从是出也。夫不持灵台而爱其身,涤除玄览而贵其患,义不相害,道在并行矣。[10](P437)
此段文字中,太炎以异时异味、异地异俗、酸腐随人、美丑不定等一系列事例证明人类存在之丰富性、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其中不应有文野、高下、美丑、尊卑之分,“若转以彼之所感,而责我之亦然”,这里隐隐有与孟子所言“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5](P330)相颉颃之意。如果说孟子以众人之同为基础证成其“推恩”“强恕”之可能性及其“絜矩之道”,那么可以说庄子正是以众人之异为基础证成庄子式之“忠恕之道”。孟子之“推恩”“强恕”并非没有意义,只是这种“推恩”或“强恕”始终不能成为绝对原则,而时刻需要批判性地、反思性地理解,庄子式之“忠恕”正可为其提供一种反思和批判。如前文所言,太炎强调“忠者周至之谓”,“忠”是“得其环中”,此即认为真正的忠恕应该是周至地整全地理解他者之存在,并给予理解、尊重或裁辅,而不是以我之所是而责彼之当然。总之,《齐物论释》正是以法相学之“泯绝人法,兼空见相”这种“真如”之学为庄子基于“吾丧我”之“齐物之境”提供进一步之哲学支撑,这种“齐物”始终强调的是“不齐而齐”。太炎云:“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17](P73)他看来以“不齐而齐”之方式尊重差别、观照殊相正是孔子“忠恕之道”之真精神。《齐物论释》在理论上会通真如(佛)——齐物(庄)——忠恕(孔)之同时,更展开一系列直面当下“人间世”的反思与批评,而太炎作《齐物论释》之主要用意正在于斯。
(二)“忠恕”与近代政治之自由与平等
太炎曾批评严复将中学与西学进行盲目比附是“知总相而不知别相”[1](P48),因此他没有直接以庄子之“逍遥”与“齐物”去格义近代视域中之自由与平等而是首先给予严格之区分。太炎云:“(《庄子》)维纲所寄,其唯《消摇》《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15](P3)太炎自觉地区分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与中国古典式之“逍遥”与“齐物”不可同日而语,二者不仅是不同层面之问题,而且其本质亦大不同[18](P37-38)。但这绝不意味着庄子《齐物论》与近代自由平等无关,就《齐物论释》以及太炎相关论著来看,太炎对“齐物”与近代自由平等之关系之考察主要有二,其一,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与平等如何可能;其二,政府如何来保证公民之自由与平等。此两问题皆与其抉发的庄子“忠恕之道”有关。
其一,就民与民而言,太炎认为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人与人之关系中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底自由,人亦不应侵犯我底自由”[18](P37-38),这种理解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自由的本质实则即是人与人之“权界”。那么如何保证这种自由真正在人与人之间实现,西方哲学家认为要靠宪政、民约甚至要靠强大的“利维坦”,但太炎看来这些虽不可否认,但毕竟有所不足。人类古今种种不平等不自由首先不是由于法律不足,也不是没有民约政府,甚至也不是缺乏儒家之仁义和墨者之兼爱,那么问题究竟是什么?太炎指出:“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虽复泛爱兼利,人我毕足,封畛已分,乃奚齐之有哉?”[17](P73)太炎看来,“情存彼此”“智有是非”这是人类一切不自由不平之根源。每一个人心中都横亘着一个“毕足”“封畛”的我,“苟各有心,拂其条教,虽践尸喋血,犹曰秉之天讨也”[17](P73),有我就有我之私利私欲,这样不期而然地导致人类种种不自由、不平等。人人有我,就不能设身处地地为人着想,也就不能真正地尊重别人的权利、利益甚至尊严,换言之,有我就不能践行真正的“忠恕之道”,故,要想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必须首破我执。太炎曾以母子关系为例,母亲爱子,能做到“无我”者多,子之爱母,能做到“无我”者少,故“世间之慈母恒多,而孝子恒少”[19](P450),因此他得出结论:“然则能证无我,而世间始有平等之大慈矣。”[19](P450)“能证无我”即行“无己之忠恕”,人只有体证无我才能做到“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19](P437)。如此,彼此互相尊重,时刻体谅,才能实现普遍之自由与平等。总之,“无我”意味着对自我权利的自觉划界和对他者权利的尊重,只有这种时时在反省和反思地内照中才能保证不对他者的自由造成威胁,也才能不僭越他者的权利,可见基于庄佛孔所会通的“忠恕之道”对近代政治之自由平等实有遮拨和补救之供。
其二,就政府与民之间而言,太炎指出:“以道莅天下者,贵乎微眇玄深,不排异己。不知其说而提倡一类之学,鼓舞泰盛,虽善道亦滋败。李斯之法律,平津之经术,西晋之老庄,晚明之王学,是已!……且以琴瑟专一,失其调均,亦未有不立獘者。”[1](P67)鼓琴不能调一宫,为政不能排异己,治国不可定一尊,为一言堂定一类之学者必滋其败,这实则就是忠恕之道。章太炎作《齐物论释》时已经超越前些年作《五无论》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而成为一个理性的民约论者,但其对政府对民人之钳制和压迫始终保留着过人的警惕。太炎在《齐物论释》中云:“有君为不得已,故其极至于无王,有圣或以利盗,故廓然未尝立圣。”[17](P76)太炎看来,庄子“非圣”“无王”等思想并非意味着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相反,庄子在以这种极端的言说方式来消解政府或人君的权利,政府的作用应该是消极的、不得已的、被动的,最好的政府是权利最小的政府。只有将政府的权利限制到最小的程度,才能保证民人的权利不被侵犯,如此民人的自由才能实现。不难发现,这里与他在《国家论》里所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19](P484),“个体为真,团体为幻”[19](P485)等如出一辙,所谓“团体为幻”与“个体为真”之关系正好就是“零”与“多”之关系,这就需要政府或人君践行真正的“忠恕之道”。章太炎也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庄子)特别志愿本在内圣外王,哀生民之无拯,念刑政之苛残,必令世无工宰,见无文野,人各自主之谓王,智无留碍然后圣。”[17](P141)太炎看来生民之苦难莫不归罪于政府或人君,而政府或人君之所以给民人带来苦难是因为他们莫不以“工宰”自居,“工宰”取自《荀子·正名》:“心也者,道之工宰也。”杨倞注:“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心之于道亦然也。”[20](P423)“工宰”与“真宰”相反,这里隐喻无道之人君以一己之心为主宰而凌驾于万民之上,“绳墨所出,较然有量,工宰之用,依乎巫师”[17](P73),惟以有我故,不能体贴民心听取民声,不能尊重民人之个体性和差异性,此即有违庄子因“无我”而以“齐物”治国的理想方式,当然实则也即有违“因物付物”的“忠恕之道”。太炎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言兵莫如《孙子兵法》,经国莫如《齐物论》”[16](P102)。这里所谓以“齐物经国”即以“忠恕之道”治国,“庄周明老聃意,而和之以齐物,推万类之异情,以为无正味、正色,以其相伐,使并行而不害”[16](P115)。这种“忠恕之道”实则即对君权或政府权利在最大程度上的消解,以“智无留碍然后圣”之“内圣”而开出“人格自主之谓王”之“外王”,即让政府以“智无留碍”的虚己精神来还民自由,平等观照,尊重个体,不排异端。太炎云“夫齐物者,以百姓心为心”[17](P143),这难道不是对“忠恕之道”的最好注脚么!章太炎在这里将佛学、庄学、儒学、近代自由主义进行很好地绾结,其核心就是“忠恕之道”。
(三)忠恕观照下之民族独立与文化多元
庄子曾预言万世之后会出现一个“人与人相食”的世道,太炎看来当时那个世界正好就是庄子笔下那个“人吃人”的世界,可谓“适逢其会”[15](P3)。太炎进而认为,造成近代大国倾轧小国、文化沙文主义泛滥的原因之一即“忠恕之道”之缺失。近代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独裁者以公理、文明、进化为名,以“推己及人”为“善意”而行侵略褫夺之实,而庄学之“忠恕之道”正可揭露其丑恶而“破其隐匿”[17](P118)。王汎森因此指出太炎“齐物哲学”的主要思想之一即“不行絜矩之道”,因为“太炎早已从人类惨痛的历史经验中看出这种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的‘善意’所造成的大灾难”[21](P162)。晚近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蒲鲁东主义、黑格尔主义盛极一时,宣扬种族优劣的大国沙文主义泛见,无论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黑格尔的“德意志至上主义”都认为“优秀民族”征服“落后民族”、“文明文化”征服“野蛮文化”是其来有自,理所当然。章太炎看来,黑格尔的“理性发展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三者是互为表里、互相支撑的进化论[19](P404-405)。如斯宾塞以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解释社会进化论,认为民族或种族之间的优胜劣汰符合“自然法”;黑格尔则承认日耳曼民族和德意志国家是“绝对精神”在目前世界中的担当者,因此有理由去征服那些野蛮国家,给世界带来自由和文明。太炎认为这些哲学都是强权主义之先声,“原其立论,实本于海格尔氏,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采色有殊,而质地无改。……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一切不自由”[19](P470-471)。事实上,所谓的“文明民族”以“文明”“公理”“进化”为名去倾轧吞噬他们看来的所谓“野蛮国家”,恰恰是没有行“忠恕之道”。他们高自标持,以己度人,没有尊重他者和异者,将民族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视为优与劣、高与下甚至是文明与野蛮之对立,此匪夷所思,庄子的“齐物”哲学正可批判或消解这些荒谬之说。庄子的齐物哲学与黑格尔的“事事皆合理”在形式上有些类似,但前者因不同而任其不同,后者强调这种不同是“绝对精神”的不同开显,然则通过进化,由异趋同,因此二者根柢又绝远[19](P475)。太炎看来尊重差别、提倡个体的庄子齐物哲学与当时所谓追求普世价值的“公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他明确提出黜“公理”而尚“齐物”[19](P470)的思想。
庄子哲学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以“无我”的“忠恕之道”来谛视各种文明、文化、种族之间的差异和殊相,以“不齐”而见“齐”,提倡互相尊重,互相体谅,平等对话,文野共存。太炎于《齐物论》三千余字中最推重“尧伐三子”章,他看来此章正揭橥这种“文野平等”之精神,太炎在《齐物论释·释篇题》云:
(《齐物论》)终举世法差违,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于娴,两不相伤,乃为平等。小智自私,横欲以己之娴,夺人之陋,杀人劫贿,行若封豨,而反崇饰徽音,辞有枝叶。斯所以设尧伐三子之问。下观晚世,如应斯言。使夫饕餮得以逞志者,非圣智尚文之辩,孰为之哉!”[17](P76)
太炎对“尧伐三子”章下注云:
任昌奎今年30多岁,是土生土长的彭水土家族自治县干田村人,大学毕业后,虽然一直在外经商,但家乡一直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做生意积累起一定的资本后,就义无反顾地返乡创业来实现小时候的梦想。故乡的时刻召唤,竭尽全力改变她的落后面貌,是候鸟式返乡人才的家国情怀。
原夫《齐物》之用,将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齐,文野异尚,亦各安其惯例,无所慕往。飨海鸟以大牢,乐斥鷃以钟鼓,适令颠连取毙,斯亦众情之所恒知。然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17](P118)
太炎认为,庄子之学能“内存寂照,外利有情”,这种“外利有情”的方式即是以其“齐物”哲学推演出的“世情不齐,文野异尚”理论。宗、脍、胥敖虽然草昧未开,但舜看来,即使如此也不应该以文明、开化、仁义等高义去征伐。因为即使这些小国在“后进”之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比所谓“先进”大国略低一等,先进者固然有文明之传统和风俗,而后进者也未尝没有自己的传统和风俗,二者各有惯例,并行不悖,不会互相艳羡,更无高下之分。因此,如果一些国家以开化者自居而以“使彼野人获与文化”为名去开化、征服这些小国,恰恰就是没有践行“忠恕之道”。他们是以己国出发而推度别国,即他们以自我为绳墨标准去丈量他者,这样就不能周尽客观地了解他者,也就不能很好地尊重他者。这样,名利兼收,既能得兼并之实,又能得高义之名。这种提倡文野高下之理论实则是桀纣暴行之先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大概都属于这种先声。
在《齐物论释》中,太炎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葛伯仇饷”为例说法。无论是《国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还是《礼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之说,都强调“祭祀”是当时华夏主流文明之传统,但葛国似乎并没有这种祭祀传统,商汤、伊尹君臣最终以葛伯“放而不祀”为理由并用种种计谋最终征服葛国。“葛伯仇饷”事件为儒者所津津乐道,孟子虽然强调“善战者服上刑”,但承认商汤以“放而不祀”为理由消灭葛国是“仁义之师”。太炎指出:“风纪万殊,政教各异,彼此拟议,率皆形外之言,虽其地望可周,省俗终不悉也。”[17](P76)因此指出“放而不祀,非比邻所得问”,即祀与不祀是一国之风俗惯例,他国无权过问和干涉,换言之,他国不能以自己重视祭祀这种风俗传统而“推”出他国也应该如此。但商汤为找一个“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理由,最终以“放而不祀”为名而将葛国夷灭,这是商汤征服天下之第一战,因为师出有名,天下诸侯纷纷盼着商汤来征服,孟子说就如大旱望雨一般。这里,葛国本无祭祀传统,但商汤、伊尹君臣二人想方设法、威逼利诱去让葛国行祭祀之礼,这是典型地对“忠恕之道”的误解,这种“推”的前提是以“己”出发的,因此就不能很好的观照“彼”。太炎看来,“葛伯仇饷”这一历史掌故就是典型的以“忠恕”为出发而最终走向“忠恕”之反面的案例。
以传统忠恕观推扩而言,祭祀为文明之行,“我们”将祭祀视为“国之大事”,彼葛伯如何能“放而不祀”,如此自甘野蛮,故杀之不赦,灭国有理;相反,若将“有己之恕道”与“无己之忠道”合参而推扩之,“我们”固然以祭祀为文明,彼葛伯“放而不祀”亦非野蛮,人家有人家之传统和风俗,“我们”岂能干涉之,更遑论杀伐之,寡固然不能暴众,众也不能暴寡。太炎看来汤灭葛伯并未给出实质理由,仅仅以“放而不祀”就夷灭人国是古代版的“文明灭国”。如果这种历史记载为真,那么正好可以检讨传统将“忠恕之道”诠释为“以己及人”“以己推彼”“絜矩之道”之有限性或危险性,如章太炎云:“小智自私横欲,以己之嫺,夺人之陋,杀人劫贿,行若封豨。”[17](P76)这是“有己之忠恕”所可能蕴含之恶果,而庄子式之“无己之忠道”大可补充“有己之恕道”之种种弊端,让“推己及人”者真能做到“无己尽人”以防患于未然。
结语
在“忠恕之道”的观照下,太炎将儒、释、道以及西学熔铸为一炉,钩深探赜,返本开新,其学术资源是传统的,其问题意识则是现代的,可谓是“旧内圣开出新外王”。传统忠恕观以推己及彼、忖我度物之诠释大义为主线,这种诠释始终以“己”为推扩之出发点,晋人宋人、宋学汉学大同而小异,并以此开出儒者所津津乐道的“絜矩之道”。这种理论本身可能并没错,至少诠释者本人并未意识到其所可能潜含的种种歧解。但事实上,如果将这种“忠恕”变成一种绝对原则,可能会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比如强人合己、以己方物甚至还会产生成汤灭葛或黑格尔主义之“文明灭国”那样的不义之举,或许正是意识到此种种不足,章太炎认为庄子之齐物哲学才是真正的“忠恕之道”。由于庄子“齐物”的前提是“吾丧我”,故太炎的“忠恕”是“无己之忠”与“有己之恕”两相并举,“恕道”是以己出发而推度他者与自己的普遍性,“忠道”是悬置自我而观照他者存在的特殊性。与“有己之忠恕”相比,后者更强调以虚灵不昧之心去“周至”地体察他者,尊重他者,还原他者,亦太炎所谓“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1](P70),而不是强以彼合己或将己强推于人,孔子不是也以“绝四”为后世所箴言吗?应该说,太炎强调“忠道”之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恕道”的推恩原则,而是以“忠道”对“恕道”所未尽之处防漏补缺,从而成为一种更周延的“忠恕之道”。至少,这种“忠道”为“恕道”提供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参照,当我们在推己及人、自命絜矩、“举斯心而加诸彼”之时首先需要反思:己之需、己之好、己之絜矩、己之心岂是真的彼之需、彼之好、彼之范式、彼之心吗?如果不是,这种“推恩”就要三思而行,《论语》不是有“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之拳拳忠告么?更何况曾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夫子之“忠恕”向来被学界称为圣人之“一以贯之之道”。故可以说,“忠道”与“恕道”构成一种交互限制关系,如鸟有两翮,车有两轮,因此章太炎说《齐物论》为“忠恕两举”之道,良有以也。就学术史而言,“忠恕之道”作为孔子之重要思想贡献,庄子《齐物论》“不齐而齐”之思想的确是对其一种遥契,太炎正是抓住此核心而会通庄孔,这就不仅仅是名相附会,而是内在地谛视其一致性,这种诠释属于深度诠释,故其声称“以庄证孔”洵非虚说。
参考文献:
[1]章太炎.菿汉微言[A].章太炎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3]章太炎.訄书重订本[A].章太炎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章太炎.演讲集[A].章太炎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7]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章太炎.检论[A].章太炎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1]章太炎.菿汉昌言[A].章太炎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2]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章太炎.菿汉三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14]章太炎.庄子解故[A].章太炎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5]章太炎.齐物论释[A].章太炎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6]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7]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A].章太炎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8]章太炎.国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9]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A].章太炎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0]王先谦.荀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1]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Equality Philosophy and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On“Explaining Conf ucius Philosophy with Zhuangzi Philosophy”of Zhang Taiyan
LI Zhi-f u
(The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Nort h 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 w ,Xi ’an 710000,China )
Abstract: Zhang Taiyan once clai med that his acade mic thought was“Explaining Conf ucius philosophy with Zhuangzi philosophy”,in that he explained Conf ucius'doctrine of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for ot hers(忠恕之道)with Zhuangzi’s equality philosophy.On this basis,he pr oposed t hat“Only Zhuangzi can f ully understand the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and“The equality philosophy contains both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Taiyan’s internal rationale of linking“equality philosophy”with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is that he explained“selflessness”-“quality philosophy”of Zhuangzi with“anatta”-“reality”of Buddhis mfirstly then he explained Conf ucius’principle of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f or others with Zhuangzi’s“selflessness”-“quality philosophy”secondly,by which it could avoid negative influence fro m “The way of mo ment”(絜矩之道)of Conf ucianis m that Conf ucius never expected.Fro m “Explaining Zhuangzi wit h Buddhis m”to“Explaining Conf ucius with Zhuangzi”,Taiyan’s ideological concer n was criticizing and redefining wester n thoughts such as justice and freedo m and equality by easter n classical thought,which is concentrated in t he book Note on the Theor y of Equality (《齐物论释》).
Key wor ds: Zhang Taiyan;Conf ucius;Zhuangzi;doctrine of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equality;Note on the Theor y of Equality
中图分类号: B2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2018)06-0024-11
收稿日期: 2018-02-20
作者简介: 李智福,男,哲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观澜
标签:章太炎论文; 孔子论文; 庄子论文; 忠恕论文; 齐物论文; 《齐物论释》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