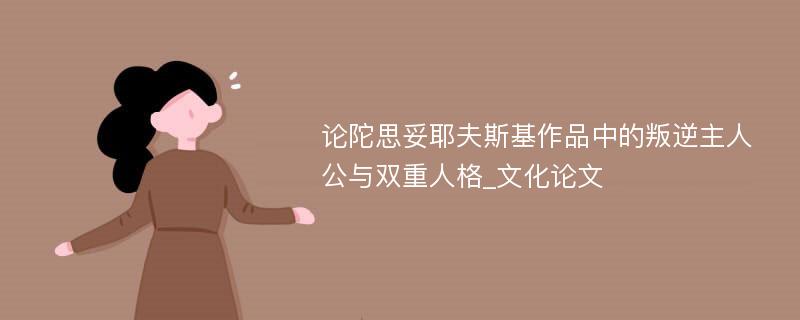
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反叛主人公与二重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基论文,主人公论文,耶夫论文,人格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人物中的一类特殊人物反叛主人公,系统分析他们个性分裂、二重人格的特征。从而探讨陀斯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特点。
〔关键词〕反叛者 二重人格 人道主义
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俄国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把注意力从现实社会的一般描绘转移到人的心灵世界。在他笔下,人的精神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现。他把笔触探伸到人性中最隐密的角落,在展现美好、闪光品质的同时,也挖掘出人的灵魂中病态、腐朽、丑陋的东西。早在19世纪40年代,陀氏就已经表现出心理分析的才能。别林斯基认为他有一种客观地观察生活现象的巨大才能,即渗透到他所完全陌生的人物的内心的才能。陀氏不象托尔斯泰塑造道德上营垒分明的人物,更不象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充满诗意。他要展现资产阶级邪恶的毒素是怎样浸蚀到一颗蕴藏着善良和同情的心里,怎样让人性变得扭曲和分裂的悲剧。陀氏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在完全采用现实主义的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人们称我是心理学家,这是不对的,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类心灵的全部隐密。”①在这方面他是如此爱好执着,因此,陀氏在作品中除继承普希金、果戈理和“自然派”作家传统,描写大城市中的“小人物”外,在《双重人格》之后的作品里,加进了自己塑造的另一类新型人物。陀氏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到,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传统道德观念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原有的小人物中增添了城市贫民、小公务员、小知识分子等下层人民,也出现了另一类人物,他们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心灵被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和传统道德良心两股力量撕扯得破碎不堪,承受着另一类不能言说的痛苦和人格分裂的折磨。
这类人物与“小人物”不同,他们不是忍受,徒然挣扎,而敢于反叛,否定俄国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力图在令人窒息的社会中为自己开辟一条生存的出路,做“拿破仑”、“罗特希尔德”(犹太财阀家族)式的人物,诸如拉斯柯尔尼科夫(《罪与罚》1866)、伊波利特(《白痴》1867-1868)、阿尔卡季(《少年》1875)、基里洛夫(《群魔》1871-1872)、伊凡·卡拉马佐夫(《卡拉马佐夫家族》1879-1880)等就是这类人。他们身上凝聚着陀氏对社会现实的哲理性思考。本文拟分析反叛主人公的二重人格并由此看陀氏的人道主义思想。
《二重人格》里戈里亚德金不愿象《穷人》里的杰甫什庚那样被人当作破布,他随时都感到自己地位的岌岌可危,在做一个为所欲为的人的引诱和做一个任人所为的人的威胁之间徘徊不定,为了摆脱“破布”的处境,获得巩固独立的地位,他要抛弃一切人性的东西,这些无耻、下流、不择手段与他本性的安分、善良发生着不断的冲突,最终以发疯的悲惨结局告终。
这种冲突也折磨着拉斯柯尔尼科夫、伊波利特、基里洛夫等人。他们栖息在孤立的荒岛——城市中(伊凡很少在乡村逗留),龟缩在没有门牌号码的斗室,在四壁包围中痛苦地思索。供他们穿行的街道那么拥挤、狭窄。陀氏从未向我们展现过托尔斯泰的那种乡土和自然,供他们出入的只有彼得堡干草市场这类贫穷区域,他们居住的狭小空间暗示着窘迫不如人意的生活,道路的狭窄象征着他们出路的渺茫。在陀氏笔下,最为鲜明突出的是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矛盾、分裂的心理世界。现实的存在以如此沉重,令人可畏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藐视着芸芸众生。在层层异己力量的包裹中有没有人不甘心个性的同一,被奴化?有,反叛者就是。他们不愿被生活的车轮碾得粉碎。他们怀疑既有秩序、一般原则,敢于胆大妄为,是为了人的活生生的个性,人的价值、尊严而敢于撞墙的人。反叛首先从思想领域内发起。善于思索是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对陀氏妥耶夫斯基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中是什么。”②陀氏笔下的主人公都是思想家,思想在作品中与人的个性紧紧结合在一起,难怪有人把陀氏的小说称为思想小说。
然而在陀氏笔下,具有拿破仑气质的反叛者大多是狂热的、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们的人格很难做到完整、一致和稳定。这种人格的分裂在陀氏看来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破碎的愿望与处境决定的。反人道的社会观念与规范必然使人的生存存在着极大的罪恶感与社会忧虑,本能需要与伦理范围的心理冲突又普遍造成人格扭曲的二重人格。反叛者们痛恨社会的不平等,却又拾起资本主义的产物——个人主义做武器,视统治阶级的准则为准则,导致自身个性分裂,甚至毁灭。陀氏对反叛者们的心理描绘、精神分析,给我们展现了空前丰富的人的精神领域。使得我们不仅看到俄国社会中“拉斯蒂涅”们的形象,更从心灵上展现了他们的堕落和毁灭。
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潜伏着善良的因子,他原是一个不忍心看着马被打死的人,曾帮助别人赡养老父,生存迫使他做了当“拿破仑”的试验。他因为没钱付学费不得不离开大学,而心爱的母亲和妹妹正有饿死之虞。绝望的处境加剧了他对整个虚伪不合理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反抗意识,使他产生了任性妄为的念头。或是作超出地下室人所说的一般人,除“我”之外的其余人之上的人,“或是完全抛弃生活!”,“顺从地接受随便什么样的命运,永世不得翻身,扑灭心里的全部感情,抛弃行动、生活和爱情的一切权利!”要想得到心里的全部感情,行动的自由,生活和爱情的一切权利,于是他只得选择了前者。他把世界上的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不平凡的人可以恣意妄为,驾驭平凡的人,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于是他杀掉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由于偶然的缘故又杀死了温柔的丽萨维塔。陀氏把内心冲突放在第一位。《罪与罚》中凶杀事件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活动描写篇幅远远超过对这一事件本身的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为自己的行动辩解:“据说应该如此。据说,有这么百分之几的人每年必须滚到……什么地方……魔鬼的地方去,让其余的人精神愉快,不妨碍他们百分之几的人!说实在的,他们尽有这些好听的文明词;这些字眼是能使人安心的,科学的,说是有百分之几的人,就不用操心了。”③可他内心良心所在的一面却告诉他是一只虱子,比所杀的那只更卑鄙一些,更恶一些,他早就预感到杀人后自己会找出很多合乎科学的话来安慰自己。他在资产阶级市侩卢仁身上看到自己以科学、理性来辩解的罪恶,在人面兽心的、无视任何道德良心的好色之徒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身上看到自己的化身。在犯罪之后,他整个人崩溃了,仿佛“用剪刀把自己跟一切东西和一切人割断了。”丧失了人性,将使他永远处在良心的惩罚之中。用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亚的话来讲:“……你将会到这样的一种界限,如果不跨过去,将是不幸,如果跨了过去,就将更是不幸……”④不跨过界限,安于现状,象马尔美拉多夫一样承受生活注定要加在身上的重负,是一大不幸。可跨了过去,试图用世上强者们的手段来实现弱肉强食规律,改变自己的奴隶生活,对于还保留有人性,保留有一切崇高和美的信念的人来说,则更是不幸。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这种不幸的人。
《白痴》中伊波利特承受着同样的痛苦。他冷漠、自私,对所有的人都摆出一副恶狠狠的态度。他为自己心中善的一面感到不好意思,竭力掩饰。因为在他看来,现在应该是权力的社会,权力是第一位的,完全排斥其他一切,包括良心、道德、感情。他认为那些温良驯顺的人物,在强大的社会法则下,只是束手待毙,而不去做罗特希尔德,应归因于他们自己的错。但他心灵深处还是潜藏着美好、诗意的东西。他热爱自然、树林、太阳,尽管他离不开禁闭他的迈耶尔大楼,看不起软弱的苏里阔夫,而对他一面蔑视,一面却怀着一种奇怪的怜悯。正是出于这种怜悯,他帮助受词讼之累来彼得堡申冤的外省医生摆脱了官司,并替他在外省另谋了职位。这位外表凶狠,叫嚷着“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的人也珍视人心灵中美好善良的品质。他对好友说:“当您投下种子,行善或做任何形式的好事的时候,您就将您的一部分个性交付出去,承受下另一个个性的一部分,你们互相联接起来了。”⑤更甚的是,他看透了主宰现行社会的是以强凌弱的残酷法则。却无法忍受这种蜘蛛般丑陋,充满毒素的可怕的力量,感到生命的弱小,并且以死来抗议。伊波利特是个参悟了存在的荒谬而又被这种荒谬捉弄的人。做强者的引诱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他留存在心里的善良无法忍受的,因此这个18岁的少年的心灵被恶势力喧嚣蒸腾的社会挤压得支离破碎,在折磨他人和自我折磨中毁灭。
如果说伊波利特还只是在迈耶尔大楼的围墙里幻想如何独立奋斗成为罗特希尔德的话,那么少年阿尔卡季就开始着手实现这个梦想了。他怀揣着自己的秘密和渴望来到彼得堡开始他的试验。大城市生活的诱惑、肮脏和恶臭,面对新的生活法则的茫然、畏惧和厌恶,挟带着个人在情感世界的潮起潮落,把这个单纯的少年卷进纷繁的印象中去,把他撩拨到狂热、不能自已的地步。这个一开始就主张个人自由应放在首要地位,其余的事一概不管,毫不客气地为自己活着,哪怕大家全都完蛋也没关系的少年心里充满了对“端庄仪表”的向往。目睹了周围的黄金迷、冒险家们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不择手段地掠夺,道德良心荡然无存后,他也开始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目的,利用与公爵女儿利害相关的文件威胁她与自己结婚。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灵魂中恶的毒素在膨胀,蔓延,那也是他梦见并深深厌恶的蜘蛛灵魂。他一面诅咒自己,一面又卷到为争夺利益设置的阴谋事件中去。
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拿破仑式人物始终没有好的命运。基里洛夫自杀了。这个谈起梦见的一片绿叶会激动万分,对生命有着强烈眷念的人最终却选择了死。他没有选择杀人,对自己扣动了扳机。基里洛夫向往自由,但他的死亡时间却由他所鄙视的人来指定,这对于他的自由是多大的讽刺。基里洛夫根本上是被个人主义的原则毁坏了,他只专注于自己,从而违心地充当了无政府流氓集团的帮凶。
伊凡·卡拉马佐夫被这种矛盾折磨得发了疯。要么当万人之上的人,要么做被统治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在《魔鬼》一章里,伊凡的两重人格表现得最为集中。虽然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怀念嫩汁树叶和蔚蓝天空,诅咒上帝对人们的欺骗,却无法摆脱灵魂中的那部分肮脏丑恶的东西,没有阻止斯麦尔加科夫,潜意识里做了弑父的同谋。
鲁迅曾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给人看,陀氏这位“残酷的天才”描写了这一毁灭过程,把人心灵中的斗争渲染到使人感官上感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巨大的震荡,一切都停顿了,一切都在腐败,似乎一切都被否定和不存在。而且不像西方只限于表面,而是在内部,在道德上。”⑥资本主义的丑恶的蛆虫已经吞噬了俄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一切良心温情等人性中善的东西土崩瓦解。犯罪、利己事件日益增多,拉斯柯尔尼科夫为它杀了人,伊波利特为它而自杀,少年卷入诈骗案,基里洛夫与造成社会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混在一起,伊凡下意识里成了弑父的帮凶。陀氏这么执着地描写人的心灵的破碎,人格的分裂,实际上蕴含着陀氏对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存状况、生存意义的思考。人道主义传统的中心就是关于人格的全面发展的观念。陀氏给我们展现了人格健全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艰难。一个健康的人格,必定有日神主宰,他冷静、理性地关照着目力所及的疆域;一个强壮有力的人格,必定活跃着一位野性的狄奥尼索斯,他不停地要冲毁日神划定的疆界,不接受一切限定生命的形式。陀氏对于资本主义的日神精神不屑一顾,他也同样厌恶和惧怕酒神精神发展到极致的个人主义、犬儒主义原则对社会道德、良心、温情的破坏。在作品中反复描写人格分裂表明了陀氏对人格发展的深深的忧虑。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陀氏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人道主义有所不同。西方的人道主义是以个体的解放为基础,而陀氏既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切僵死、限定自由发展的教条、原则下为个性的生长求一条出路,又不象西欧那样偏重于个人主义。他把人们的解救寄托于宗教(东正教),因此他在每一部作品里都安排了一个圣徒式的人物,他们可以拯救人的灵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就介于西方的人道主义和俄国的东正教这二者之间。
本文1994年10月23日收到。
注释:
①②巴赫金著,钱中文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P99-100;P82
③④叶尔米洛夫著,满涛译:《陀斯妥耶夫斯基论》,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P153;P151
⑤陀斯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白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P501
⑥冯增义,徐振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P373
标签: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