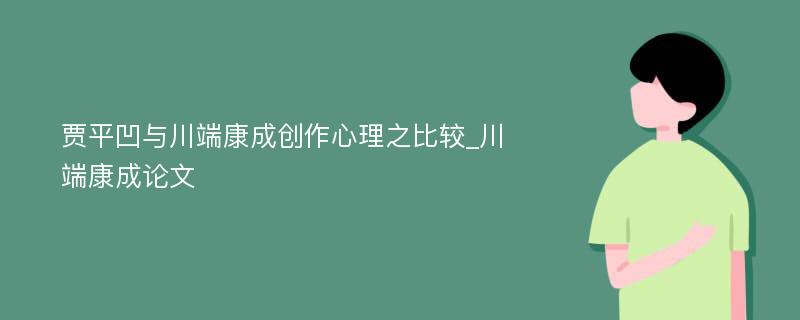
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川端康成论文,心态论文,贾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文章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出发,着眼于作家创作心态的演变历程,对比论述了川端康成和贾平凹忧郁气质的成因和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对创作的趋同性影响,并结合作品从禅宗的角度分析了两位作家创作上的得失,最后探讨他们在创作上走向低谷的原因。
关键词 创作心态 趋同性 禅宗
美国印第安大学教授亨利·雷马克认为,世界文学史上有一种“回转现视”现象,意即某些文学潮流会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重现,其条件是相类似的历史文化环境①。而文学的繁荣往往又是以巨大的历史灾难为前提的。本世纪日本历史上的十五年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十年浩劫都促成了本国文学的长足发展。40年代后期的日本文坛,70年代末80年初的中国文坛,就是基于近似的历史文化环境,奏出了痛定思痛、控诉历史灾难的最强音。这样,在这两个有着深远历史文化渊源的国度里,又面临着“相类似的历史文化环境”,势必产生出一些美学旨趣相近的作家。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作家在反思潮流中独善其身,更执著于文学审美价值的探求,或者在经历浩劫和战争,识尽愁苦之后,“却道天凉好个秋”,更多的是为心灵寻找慰安的艺术空间,追求感觉表现的唯美主义。在这些逸出于反思文学潮流的作家群中,川端康成和贾平凹是两个较为突出的代表。
这两个作家的相似并不止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和相应的创作态度,他们还有内在气质和禀赋上的相近。而且两个人的成长经历、美学观念、甚至创作历程也颇多类似。他们都是孤儿性情,抑郁、内向且多愁善感,哲学观上倾心于对生命本体的参悟体味,企图以艺术至境勘破生死之关,创作上执著于本民族艺术传统的阐发,以传统的手法表现现代的意味。贾平凹近期作品,如《太白》、《人极》到《废都》,与川端康成晚期作品《睡美人》、《一支胳膊》等有某种规律性的趋同。这一切给两位作家创作心态的可比性提供了契机。而且,川端康成晚年似乎已步入艺术与人生的双重绝境,最后不著一字遗言,于1972年4月自杀身亡,其无言的死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话,的确引人深思。
本文拟从两位作家孤儿气质的成因、人生观和美学追求的演变过程中追溯他们创作心态的轨迹。以期在他们的相似中寻觅到一些带规律性的创作借鉴。
一、人生心态
一个人年少时期的生活经历往往能影响他一生的行为处事和面世心态,天性善感的艺术家尤其如此。“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抑郁敏感如川端康成,孤僻内向似贾平凹者,这种影响则来得更加久远和深刻。
川端康成少儿时的生活,可说是悲惨之极、凄惶之至。人未成年,亲人都相继去世,十四岁那年,失去了所有至亲骨肉。他后来在《十六岁的日记》里悲叹道:“我自己太不幸,天地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这种身世,使他的童年少年生活渗进了太多的悲哀和忧郁,人生的幻灭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养成了他乖僻忧郁、强烈自卑的孤儿气质,也正是这种孤寂落寞的性情使他去亲近自然,潜心读书,滋生了对文学的憧憬。川端康成自小就承袭了日本民族“多情善感”的民族禀赋,对花鸟雪月、山川草木情有独钟。他小的时候,常常一人跑到空寂的山陬,眺望风景;并爱爬到树上,放声朗读《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古典名篇。川端康成后来追忆这种读书生活时写道:“这样的朗读使少年的我沉浸于淡淡的多愁善感之中。即当时我是在唱不懂意思的歌曲,……少年时代唱的歌的旋律,直到今天,每当我提笔写作时,便在心中回荡,我不能辜负那歌声。”②这种爱读书,喜好亲近自然的生活,不仅培养了他的感受力,丰富了他的幻想力,同时也孕育了他超凡的诗人气质。川端作品中氤氲着的那种忧郁和凄凉,淡淡的寂寞和哀愁,都与此不无相关。
苦孩子的命运都大抵相似。步入而立之年的贾平凹曾在《商州初录》的后记中写道:“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家庭的反应连锁的遭遇,构成了我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培养了一颗羞涩的,委屈的甚至孤独的灵魂。”③幼年的贾平凹,其孱弱孤僻与川端康成颇相近似,小小年纪,也就在向大自然投注自己的内心:“我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条台阶上,看着远远的疙瘩寨子山顶的白云,就止不住怦怦心跳,不知那云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只很大的鹰在空中盘旋,这飞物是不是也同我一样没有一个比翼的同伴呢?”④上初中后,他过着“更孤独更困顿更枯燥的生活”,“这期间,祖母和外祖母已经去世,没有人再偏护我的过错和死拗”,“班里的干部子弟皆高傲,……用一种鄙夷的目光视我”,“那时候,操场的一角呆坐着一个羞怯怯的见人走来又慌忙瞧一窝蚂蚁运行的孩子,那就是我。”⑤“文革”开始后不久,少年的贾平凹辍学回乡,成了一名小社员,家本穷苦,当中学教师的父亲又被诬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回乡劳动改造,家庭的更趋败落,使“本来就孱弱的我更加孱弱”。辛苦的劳作长时间折磨着他的身体,家中吃喝难继,其母又犯重病,作为长子的贾平凹吃尽了苦中苦,读书的渴望又得不到满足,一颗孤寂的心从此变得更加孤寂。
青少年时期的不幸与创伤,一旦在心灵生根,就会激发出人的非凡意志力和创造力。年少的川端康成和贾平凹在饱尝人生之味的辛酸苦涩之后,已有一种超越自卑自怜的上进心促使他们在人生的低谷中奋然前行。对文学的倾心,则成为他们走出孤儿心态、走向成功的坚实后盾。
如果说,家庭环境和个人遭际铸成了作家敏感脆弱的性情,而对作家人生观念有更重要影响的还是时代气氛,它加剧了作家主体意识中的感伤因素和消极遁世心理,这就必然导致作家审美重心的偏向,直指内心,浸淫于非现实的幻想世界中去寻找心灵的归宿。面临时代的重大变故,作家作为社会中最敏感的神经元,无时不关心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即使是某种避世隐忍的人生态度,也曲折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总体气氛。同时,时代的种种动乱和变故,必然促使作家对自身多舛命运的思考,对社会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寻。
川端康成表示既“不那么相信战争时期那套政治说教,也不大相信战后现今散布的言论”⑥,所以他对政府的高压采取“最消极的抵抗和最消极的合作”,自谓只能回到自古以来的悲哀中去,这种悲哀与他的心境相吻合,对他是一种慰藉与解脱。这种人生态度,与作家向来接受的作为儒道佛综合体的日本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这三者互为补充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结构,影响了作家基本思想的组合。因而川端康成对待事物更多的是强调同一本原,等美丑,一寿夭,对立面之间是渗透和协调,而非排斥和冲突,这种中庸调和的人生哲学使他常常能超然于事物矛盾之外,在乱世中得以保全自身,保持超脱的创作心态,悠然忘我,从更深层次上去关注文学。
与川端康成近似,中国传统的儒道互补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贾平凹的面 世态度,庄子的审美人生态度和传统士大夫的适意人生哲学更多地代表了贾平凹早期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唯心,唯美,喜好对宇宙自然的寂然观照,沉迷于内心与外界的融合与交流,追求总体人生的审美境界,醉心于生活与艺术的协调统一。这种人生观比之川端康成,要显得健康达观。贾平凹在创作旺期所承受的心灵负荷比川端康成要少,但他对文学的钟爱丝毫不逊于川端康成的赤诚,几乎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用孙犁的话说:“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中来了。”⑦
川端康成与贾平凹的创作历程,同时也是他们的生命、人生历程,其中的艺术探求与试验,既是对自己生命力的享受和渲泄,又是自身灵魂的搏斗与挣扎。他们的美学态度与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文学创作几乎成为他们生存的全部依托。他们作品中的那种寂寞情绪,幽玄意境,生的神秘,死的莫测,寂灭无常的深层悲哀,特别动人魂魄,或许作者达到了一种生命体验的极致?贾平凹在论及三毛之死时说:“三毛死于天才的孤独,凡进入大境界的人都是孤独的。”⑧后一句话或可作为作家自我心态的表述。正是这种倾注生命的真诚和他们独特的艺术禀赋,使他们很早就步入神圣的艺术殿堂,在“大境界”中体味孤独,尤其是以禅意浸润人生和创作,使他们的作品风味别具,突出地展现了东方艺术美的无尽底蕴。
二、文道禅宗
孤心向禅,以禅入文可说是两位作家美学追求的主导走向,禅宗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是相通的,它承继了印度式的冥想,纳入了老庄的思维方式,以对空灵澄澈的“本心”体验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以神秘的直觉主义为特征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它重直觉观照和瞬间顿悟,追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致,正好吻合了作家要表现自我细腻情怀、微妙感受的意图。尽管禅宗在中国和日本有着众多细微的差异,但它在与两国传统文化相合流的过程中产生出本质相通的旨意,禅境成为东方艺术所追寻的至高境界。
日本传统的美学思想,有“物哀”和“幽玄”两个与禅宗旨趣相通的美学理念贯穿其间。物哀,是心与形,主观与客观,自然与人生的契合,表现一种 优美而典雅的情趣,又具有悲哀的意蕴。幽玄之美,内涵丰富,比之物哀,更重“心”的表现,闲寂的内省世界,超脱的心灵境界,作品的韵外之致、超逸之趣,人生观的空无死灭、虚幻哀怨,都可集于“幽玄”的意味之中。
川端康成的审美情趣,更多地继承了“物哀”、“幽玄”的精神,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他自己也说:“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下成长的,”“那古老的佛法的儿歌和我的心是相通的。”⑨1968年,川端康成在接受诺贝尔奖的仪式中,发表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说,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美学追求。在演说辞中,川端康成引了不少禅师的著名诗句,如“春花秋月夏杜鹃,冬雪寂寂溢清寒”,“冬月出之暂相伴,北风劲厉雪亦寒”,“试问何物堪留尘世间,惟此春花秋月山杜鹃”等等。认为这些诗不仅是对四季之美的讴歌,也是对大自然以及人间的温暖、深情和慰藉的赞颂,表现了日本人慈怜温爱的心灵。“试问”一诗,不仅表达出日本文明的精髓,还展露了一种脱然无累的旷达胸襟,诗人那颗宗教的心灵,已达到一种澄怀静虑、物心合致的禅境,继而升华为一种诗境,一种至高的艺术境界。由是可知,那种希图通过对自然和人生的寂然观照,达到某种彻悟,求得精神解脱的思想,已深深渗透在日本的审美理想之中。这也构成川端康成审美意识的主体部分,对其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川端康成在作品中尤其善于将自然景物的变化与人物心灵的喜怒哀乐交融契合,达到浑谐一体的“忘我之境”。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一开头就以自然物象中最富传情因素的“雨”,作为美好理念和观照的主要形象,来增加人物的精神、情绪的深度。如写夜雨听鼓声,以缠绵的雨引起“我”对舞女的无限思情,鼓声一息,“我”就好象要穿透黑暗看透这安静中的意味,心烦意乱,生怕今夜舞女被人玷污。这里以夜雨、鼓声烘托“我”内心的咏叹变化和对舞女关注之深、爱恋之切。同样优美的笔触和融情入景、以景言情的手法在其名作《古都》、《雪国》等篇什中亦多次出现,流露出浓厚的日本式的抒情风味,这种风味熔“物哀”美与“幽玄”美为一炉,匠心独运,切实达到了外物与人心高度合谐的“意境”。如《雪国》开头的名句:“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寥寥数语,完美地说明主人公岛村已到达雪国,写出了雪国的自然景象;接着又写了远方的“那边的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的自然状态,马上给人一种冷寂、凄怆的感觉,暗示和象征岛村去探望的驹子的不祥的未来。
贾平凹受禅宗思想的浸染亦深,散见于其作品中的种种艺术见解即是对文道禅宗的一种解说。禅宗直觉的静默观照、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渗浸了他的艺术思维,表达上追求质朴单纯、真切自然,营境造意,似不经意而为之,而又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自由灵动,率真而又含蓄。他早期的散文和小说,性灵独具,自成一家,就得益于这种禅思的神妙。在他《文外谈文》的系列篇什里,对此作过精当的表述,“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 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⑩,“明月照在山巅,山巅去愚顽而生灵气,明月照在山沟,山沟空白而包涵了内容。这个时候,我便又想起了我的创作,悟出了许许多多不可言传的意会。”(11)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然适意、澹泊空灵的心态,一种超逸旷达的隐士情怀,禅意似已浸入作家的意识深层,内化于心,外化为文,始终禅以贯之。正所谓“学诗大略似参禅”,“禅同一切门类的艺术都是密切相关的,真正的艺术家和禅师一样,是知道如何领略事物之妙境的人。”(12)贾平凹在创作中,充分运用老庄的直觉思维方式来体察世风民情,他驻足商州,借助古老的观物方式,保持一种虚静的审美态度来实现在作品中对人生的体验和对生存的感悟。他的《浮躁》、《商州初录》等作品,既有对汉唐文化遗风的承袭,也有对民族民间古老思维方式的溯寻。而《太白山记》、《逛山》等作品,淡化了具体的时空背景,使人物处在一种自然古朴的原生状态中,“志怪传奇”式的客观叙述更趋强化了作品中的超然意识和旁观态度,在这些作品里,善恶是非观念和法律政治因素是受到嘲弄或无关紧要的,“空”、“无”的禅宗意识为作品建构了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意境,也为美的表现埋下了尴尬的伏笔。
尽管都是禅意与文心的融合,由于个人经历和社会氛围以及传统文化的某些差异,川端康成与贾平凹的审美意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审美意识基调的“哀”与“乐”的区别,颓废与健康的差异。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青少年时期,川端康成在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接触了太多的死亡,深怀着对死亡的恐惧,觉得生去死来都是虚幻,生命从衰微到死亡,在川端康成那里被看作是一种“死灭的美”,他就是从这种物的死灭中去体会心的深邃。日本十五年的战争之苦,使川端康成完全执著于古典文学美的探求之中,他所挚爱的《源氏物语》,带有浓厚的“物哀”色彩。川端康成在对“物哀”理念的继承和阐发过程中,常常轻“物”而重“哀”,将时代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同自己的悲哀融合在一起,追求悲哀美、死亡美,从而在这种悲观虚无的审美境界里寻求心灵的超脱,作为顿悟成佛,参禅得道的途径。贾平凹则不然,他的人与文,多带有“清净适意,超然自得”的旷达情怀。青少年时期的创伤没有川端康成那么深入骨髓,时代的变故也未将他逼入绝境,而且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讲究调适折衷、优游冥如,善于将主体情绪投射外物而达到心理平衡,闲适和疏放更易成为艺术家心灵的主旋律。他的参禅,可于山石草木、花鸟人物的一得之趣中获得。在小说集《太白》序中他说:“有一种应无所住的平常心,于文学却十分有益。”同为禅宗意境的爱好者,这种寻求心灵归宿的途径,却与川端康成殊异,一个“乐”生,一个“爱”死,这也是他们艺术旨趣的根本区别所在。同样是对爱情的表现,川端康成在作品中的表达渗透着彻底的虚无感和死寂感,那种宿命的苦闷、生死爱恨的无常观,在川端康成晚期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显露。即使最负盛名的《雪国》,其中玩世不恭的男主人公岛村把人生和爱情视为虚幻,把女人当作玩物,流露出虚无和颓废的情调;岛村把艺妓驹子对自己的爱视为一种美的徒劳,偏偏倾心于年轻美貌的叶子,而故事结尾,叶子在一场大火中死去,表达出作者对人生的悲凉感触。在川端康成看来,爱情是虚妄的,因为在他自己,从未真正得到爱情,死才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起点。据统计,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同“死”的形象联系的就有50多篇,几占全部作品的40%,足见佛教厌世空无观念对川端康成的影响何其深刻。贾平凹最见艺术功力的几个中篇小说,如《美穴地》、《白朗》、《五魁》等,不仅穿插着动人的爱情传奇,世事莫测、人生无常的宗教虚无观也是时隐时现,对人物和情节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美穴地》中的柳子言和四姨太,从相爱到结合,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悲欢,然而他们毕竟结合了,虽然四姨太备受折磨和摧残,以至于毁容,柳子言成了断腿的残废,他们还是过上了“安静可心的日子”,情感未被抽空,尚不乏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当然,贾平凹后期的一些创作,又有不同的面貌,此不赘述。
三、走入困境
艺术家毕竟不可能因参禅而羽化登仙,他还得食人间烟火。东方的禅宗过于注重人的内心,讲求“自心是佛”,“适意自然”。然而人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尊重心灵的自由,无疑是给七情六欲的放纵开了方便之门。受禅宗思维影响的文艺也必然受到这种思潮的冲击。中国明朝中后期的狂禅之风和《金瓶梅》之类的文艺作品的出现,正是这一心理变迁的表征。从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也可算作明代文学潮流的“回转现视”。在明朝中后期,由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大兴金钱拜物教之风,伦理观念日益淡泊,一度信奉禅宗的士大夫们此际一反过去内向、封闭的心理习惯,变得开放甚至放纵起来。他们大胆地追求尘世的幸福、尘世的欢乐、尘世的情欲,于心理与肉体的放纵之中寻觅人生寄托,真隐者不必在山林,红尘大千,照样参禅,那些“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房,未还酒债”的禅师们,也引得不少士大夫文人的青睐。(13)这种禅理文风必然导致艺术家美学追求上的迷误,川端康成和贾平凹的“放浪”之作即是这种美学追求的产物。
有人将贾平凹的创作分为三阶段,早期创作重于社会政治层面,80年代中期探索历史文化层面,80年代末则开始切入人生的体验,注重生命本体的意义的探寻。这种探寻是有作家的心理背景的。他在《四十岁说》中说:“在美国的张爱玲说过一句漂亮的话:人生是件华美的睡袍,里面长满虱子。人常常是尴尬的生存,我越来越在作品里使人物处于绝境,他们不免有些变态了,我认作不是一种灰色与消极,是对生存尴尬的反动、突破和超脱……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诞一切,自在而为。”(14)“变态”和“放诞”的背后,隐藏了作家心底无限的悲凉,然而它是否能与艺术的特性合流呢?直露、大胆、放浪和变态的性描写除了消解美丑的界限,表述彻底的颓废和虚无,安妥作者“破碎的灵魂”之外,不知背后还隐藏了甚么东西?给读者如我,只有痛惜作家“江郎才尽”的感受而已。
在川端康成晚期的创作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形。二次大战给日本人民留下深深的创伤,在经历了生与死的重大磨难之后,还有什么真正值得信奉的价值观可依赖的呢?历史的灾难只会加重人们对生存意义的怀疑和迷茫,甚至于否定。川端康成此际,忧郁、感伤、颓废和放荡的美学观积淀在他的心理深层,其作品如《睡美人》、《一支胳膊》描写传统道德、理念、理性乃至于生命自然的规律对于情欲的压抑,描写性虐待和性变态,以期发现人的天性、人的本能的东西。中日文学传统中的“好色”的描写是有渊源可寻的。川端康成这种“生命即官能”的美学追求把这种传统又加以夸张和变态的发挥,他说:“我的作风,表面上看不明显,实际上颇有些背德的味道”,他“最感不满的,就是道德上的胆小怕事”,“作家应该是无赖放浪之徒”,“要敢于有不名誉的言行,敢于写违背道德的作品,做不到这一步,小说家就只有灭亡。”(15)确乎是心理失态后的危言耸听,才思枯竭后的歇斯底里。
川端康成和贾平凹的放诞也与他们潜在的心性有关。川端康成据说是“由于家中没有女人,对性的问题也许有点变态,自幼便喜作淫乱的妄想。”(16)贾平凹自剖时也说:“见人遇事自惭形秽的多,背过身后想入非非的亦多……甚至梦里曾去犯罪,偷盗过、杀人过、流氓过……。”(17)自卑内倾的心性往往将作家引入自恋式的狂想,作品,则给他们的狂想提供了渲泄的空间。
两位作家走向创作低谷还有其他的原因,甚至还有巧合式的相似。首先是名气对作家才思的阻碍。年近70的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曾在《夕照的原野》一文中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荣誉和地位是个障碍,过份的怀才不遇,脆弱得吃不了苦,甚至连才能也发挥不了。反过来,声誉又成为影响发挥才能的根源……我希望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18)创作《睡美人》等几篇小说之前,他已在日本文学界获得了巨大声誉,获奖之后川端康成仅写过三个短篇小说和几篇随笔。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一个内向木讷、孤僻古怪的名人是难于对各种事体应付自如的,而且在功成名就之后,价值的丧失会产生人格的真空,人的心态就更加郁闷失常,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作家的才思。名气也使贾平凹大受其害,他曾著专文《名人》来言说名气所致的种种尴尬和无奈,并在《废都》后记中说:“出门在外,总有人知道了我是某某要说许多恭维话,我脸如烧炭。当去书店,一发现那儿有我的书,就赶忙走开。我愈这是样,别人还以为我在谦逊。我谦逊什么呢?我实实在在觉得是浪了个虚名,而这虚名又使我苦楚难言。”
社会、家庭的缺憾,生理上的疾病,也是促使作家的心理失衡、创伤力不从心的重要原因。川端康成膝下无子,仅收一养女,由于自幼以来的身世创伤,家庭的天伦对他而言总打了些折扣。他的学生、理想的接班人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支持警察头子秦野章竞选东京都知事的失败,使他受到更深的刺激,晚期创作又接连受到理论界的批评,这些打击严重影响了川端康成活下去的信心。而且他长年情绪失常,靠吃安眠药度日,更加深了他的精神障碍。此时的川端康成身心交瘁,倍感生的徒劳和死的绝对,这种情况下,创作显然难以维继,最后只好以自杀而告终,以“死亡的美”为自己的人生和艺术划上句号。
40岁的贾平凹也充满了宿命的悲哀。他在《四十岁说》中写道:“我是一个山地人,在中国的荒凉而贫瘠的西北部一隅,虽然做够了白日梦,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逼我无限悲凉……。”《废都》后记中的表白更充斥着沉痛的凄苦和悲哀:“这些年来,灾难接踵而来……,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我没有儿子,父亲死后,我曾说过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现在,该走的未走,不该走的都走了,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唏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为何物。”其心境之颓唐,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实不多见。
此外,川端康成与贾平凹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借鉴有所失度,如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偏颇理解和滥用,不仅未给作品增色,还给作家自己带来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概言之,川端康成和贾平凹创作心态的相似和相异,可追溯到他们童年孤儿气质的养成期,走上文学之路后对禅宗的迷恋浸淫,以及与之相关的避世逍遥的心理。传统文化、社会环境、家庭婚姻、生理和经历等外在因素构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促成他们内倾禀性的病态发展,对世态人生的偏执看法。这种人生观上的矛盾心理和艺术上的成败得失相互影响,左右着他们心理的天平。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接合点上一度追寻到了艺术与人生的价值,同时又在这种结合中迷失了自己,陷入美学观与人生观的双重迷惘。其个中原因,殆难言罄。作家创作心态的“黑箱”,至今还是无法解开的“斯芬克斯之谜”,本文论述所及,多不过是“隔靴搔痒”。然而人们不可能因此而停止对艺术之谜的探究,美总是指向未来,艺术为人生所必需,川端康成因其骇人听闻的文学主张而使创作步入死胡同,倍受读者青睐的贾平凹也曾四面楚歌,褒者寡而贬者众。前车之辙,当不重覆,但愿他不会就此步入江郎才尽的绝境,早偿夙愿,把大石头推向奥林匹斯山的峰顶,吃到天国的糖果。
收稿日期:1994年12月5日
注释
①《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②《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页。
③④⑤⑧⑩(11)(17)均见《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558页、597页、598页,617页、560页、580页。
⑥(15)(16)黄卓越:《二十世纪艺术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页、408页、406页。
⑦《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序》,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⑨(18)叶渭渠:《川端康成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229页。
(12)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13)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14)《贾平凹自选集》,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一卷,第398页。
标签:川端康成论文; 贾平凹论文; 文学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日本禅宗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禅宗思想论文; 美学论文; 雪国论文; 废都论文; 睡美人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