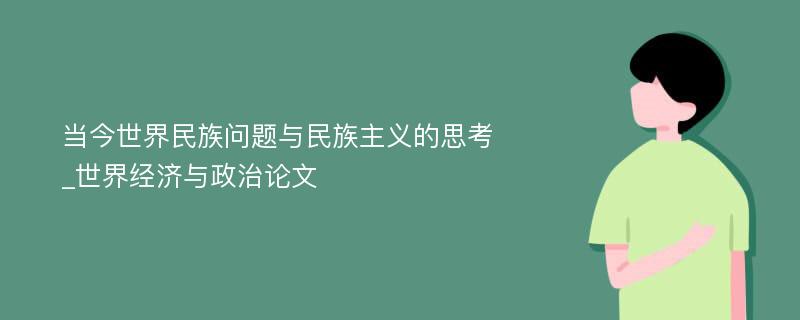
关于当今世界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当今世界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主义问题早已存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高潮,民族主义问题因而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关注的课题。在国外,不仅已有新的力作出版,而且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世界名牌大学中,自1992年起已在尝试为研究生开设民族主义专业课。近几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刊更是在积极组织讨论如何将民族主义整合到大学本科的历史课程之中。参与讨论者均赞同在大学开设民族主义课是当务之急,因为不了解民族主义则不仅不能了解近、现代世界,而且也无法了解所谓的后现代世界。(注:参见罗厚立:《民族主义感言》,载《读书》,1999年第12期,第93页。)这说明民族主义问题已再次受到国外学界的关注。在国内,民族主义问题同样成为研究的热点。如1997年11月由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在北京大学组织和主持召开的“当今民族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有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讨论结合世界各地具体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主要围绕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民族主义的类型和表现形式、民族主义的性质、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以及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问题等主题展开。(注:参见张顺洪:《“当今民族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侧记》,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第111页。)除了召开学术讨论会以外,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民族主义研究的成果。本文在吸收有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侧重就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类型和表现形式、世界民族问题泛起的原因、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走向等进行阐述与分析。
一、民族主义的类型和表现形式
民族主义本质上是“18世纪晚期以后才产生的现象”。(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第144页。)民族主义意味着“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自由、自决和为了某种共同物质利益而结成的一种团结。民族主义是为了实现一致的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自治共同体(self-governing community)”。(注:D.D.Pattanaik,Hindu Nationalism in India,New Delhi:Deep & Deep Publications,1998,P.X.)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民族利己主义”;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的筹码,民族分离主义者的王牌”。(注:张西山:《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载《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1-252页。)
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什么是民族主义”这个问题的观点不尽一致,因此对民族主义的类型和表现形式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分为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对于保存人类的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是颇有价值的”;(注:李少君:《关于民族主义》,载《东方文化》,2000年第1期,第74页。)有人把民族主义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类型,(注:参见李永刚:《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载《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12期,第25-28页。)李兴博士就曾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视角来论述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注:参见李兴:《“文化民族主义”:论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36页。)国外则有学者把民族主义区分为“东方式和西方式两种不同形态”。(注:参见徐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载《读书》,2000年第11期,第143页。)这些对民族主义的类型和表现形式的不同看法,从一个侧面说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民族主义问题具有复杂性。
综观全球,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大致呈现出以下几种发展类型和表现形式:
首先,民族分离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民族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分离主义已导致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据有关资料统计,1923年欧洲共有23个国家,而到1999年初欧洲大陆的国家已增加到50个。(注:参见邓浩:《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第41页。)而车臣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更是直接缘于民族分离主义。此外,英国、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塞浦路斯、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许多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民族分离主义的困扰。(注:参见〔委〕《国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文:《民族主义爆炸》。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2月16日。)
其次,种族暴力冲突不断增加。在毁灭苏联的民族危机开始变得明显之前,许多国家就已经受到种族冲突的威胁。1989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和解体,进一步导致在全世界发生无数边界争执。前南地区的战争于1991年6月最先在斯洛文尼亚爆发,1991年8月扩展到邻近的克罗地亚,1992年4月战争又扩展到波黑境内。自1991年以来,战争使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共有25万人丧生,30万人受伤,20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他们的最直接的避难所——克罗地亚——目前正在寻找由于塞尔维亚人的占领而从克罗地亚被驱逐出境的25万克罗地亚人和从波黑被驱逐出境的30万人。据欧共体的报道,在这场战争中估计有2万名妇女被强奸。克罗地亚、波黑的城市和乡村惨遭战争蹂躏。(注:参见Christoph Bluth,Emil Kirchmer & James Sperling,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Sydey: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95,p.153。)俄罗斯也亲身体验了苏联解体给它带来的痛苦。在车臣共和国死了3万多人。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的种族屠杀是具有暴力性质的极端事例;1993年底至1995年底,在布隆迪由种族仇恨导致的屠杀使10万人丧生;在卢旺达,1994年4月共和国总统被杀害之后共有80万人死亡。在利比里亚,以明确的种族集团为基础组成的各个派别之间发生了血腥的内战。除此之外,在加拿大,魁北克的分离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注:参见李鑫炜:《体系、变革与全球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3-114页。)在比利时,瓦隆人和佛拉芒人之间的对立威胁着这个富裕的国家。
第三,宗教民族主义异常活跃。马瑞映先生指出:“宗教作为信仰的指归,在制度、体制的作用无奈时,就成为推动民族和民族意识的‘宗教替代’。如,中亚冲突、波黑战争和非洲战乱都与这一因素有关。”(注:马瑞映:《论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兼评民族主义终结论》,载《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第138页。)又如,巴以冲突中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总是与宗教有着复杂的关系”。(注:T.G.Fraser,The Arab-Israeli Conflict,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5.p.153.)再如,在苏联解体的多种原因中,宗教冲突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众所周知,宗教信仰是形成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俄罗斯民族信奉东正教,中亚诸国和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信奉伊斯兰教,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信奉基督教。壁垒分明的宗教信仰扩大和加深了各民族间的裂痕,强化了民族矛盾和冲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解体前后,凡是宗教争端尖锐的地区,几乎都成为民族主义高扬和民族冲突的热点地区,甚至兵戎相见。”(注: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47页。)由宗教问题引发民族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注:参见邓浩:《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第41页。)
第四,在有些地方如非洲存在一种突出的现象即地方民族主义。李安山教授在《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一文中对地方民族主义下过一个新的定义:“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和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注: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第44页。)过去,我国的学者多把其称之为“部族主义”。在一些非洲国家,地方民族主义之所以发展,主要在于“殖民主义遗产、国家政策的实施、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国家政权的弱化”。(注: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第44页。)地方民族主义在一些非洲国家引起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和地区持续动荡,如卢旺达、布隆迪的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部族仇杀就是明证。在1994年的流血冲突和内战中,人口只有750万的卢旺达,竟有100万人被屠杀,200多万人逃亡。在布隆迪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内战。到1999年,内战在只有500万人口的布隆迪,已造成20多万人死亡和近百万人逃亡。(注:参见李巨廉:《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二、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泛起的原因
对于当今世界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原因,学术界有多方面的解释。有人认为,制衡民族矛盾的冷战机制的瓦解,打开了民族主义肆虐的“潘多拉”盒子;全球化刺激了民族主义;历史的惯性作用,如西方殖民主义在非洲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非洲地区不断发生民族冲突,并延续至今,同时大国的干涉和国内政府的错误政策也导致或加剧了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也有人指出,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盛行于世界各国,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问题,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此外,还有人认为,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也容易导致和激化一国之内的民族矛盾。一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利益往往成为这种议会民主模式的牺牲品。西方国家前些年热衷于在非洲推行西方式的多党议会制,加剧了非洲国家民族主义的急剧发展,导致局势的严重动荡。(注:参见张顺洪:《“当今民族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侧记》,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第111页。)
上述诸多见解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当今民族主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泛起的原因应着重从以下几点上来把握:
首先,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段先发展起来,形成发展的“中心”;后发展地带成为“边缘”,受“中心”剥夺。为摆脱这种地位,“边缘”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以地方主义来号召反抗“中心”,而这些条件如果带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就很容易发展成一种“地方民族主义”。于是,一种新的意识产生了,新的“民族”有可能形成,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则是其奋斗的目标;而整个过程的根本目的是后发展地区企图改变从属地位,变“边缘”为“中心”。西方学者对欧洲民族裂解的现象十分注意,有些西方学者声称:“是民族主义产生民族,而不是相反。”民族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民族与国家等同,如果用某种概念来表达,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同一个民族应当组织在同一个国家里,同一个国家也应该只有同一个民族。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随着历史的进展,民族间的混居现象十分普遍,要想在各民族间清清楚楚地划出一条线,建立纯而又纯的单一“民族国家”,在实践中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民族主义的这种追求就使民族间的龃龉永远不会消除,并随时可能发展成公开的冲突。(注:参见钱乘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4页。)
第二,冷战结束为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先对立的两大阵营土崩瓦解,不仅是发达国家失去了明确的敌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对抗张力的消失而使曾经居于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衰微败落,导致了文化价值的缺位,民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统帅和生活意义的寄托”。(注:李永刚:《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载《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12期,第25页。)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民族主义乘虚而入,力图填补冷战后的意识形态真空。大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日里诺夫斯基鼓吹的大俄罗斯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正是冷战后意识形态转换的直接产物”。(注:邓浩:《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第44页。)勒纳精辟地分析道,民族主义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凝聚力和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在进入现代化的“门槛”之后,原先的社会支撑物和社会结构发生崩溃,这使人们充满了压力和痛苦。民族主义作为进入现代化“痛苦门槛”的一种表达,具有两种功用:一是授予人们尊严与保持社会稳定;二是为现代化提供动力,并最终在实践中解决这种痛苦。(注:参见李永刚:《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载《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12期,第25页。)笔者认为勒纳的分析颇有道理。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在原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境内接连发生了12场缘于民族主义因素而爆发的战争,形成了新的热点地区。事实上,原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问题,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和多年积存下来的现实原因。过去,由于受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强烈对抗的压制,受到在此背景下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控制,还受到苏、美尖锐对峙的“冷战”国际格局的束缚,这些国家内的民族问题一直没有爆发出来。而一旦失去了原来的控制和束缚,其民族主义就泛滥得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厉害和更为野蛮。(注:参见李巨廉:《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第201页。)
第三,全球化浪潮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和挑战,民族主义思潮和全球化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全球化是指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世界各国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和趋势,表达了一种民族国家对“整个世界的总问题”或“人类的困境”的关注。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意义尤其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范围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经济的无国界活动,无疑对传统的国别经济构成巨大冲击,并迫使各民族国家面对这一冲击做出各种反应,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反应。特别是二战后世界经济随着资本和生产的国际化趋势的加强而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成为一种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地球村经济”。从文化理念来看,经济全球化由于知识经济、信息革命而得到迅猛的发展,导致了改变民族国家观念的“全球主义”思想的形成。(注:参见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这种全球化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通过全球化的经济与信息交流,整个世界趋向干整齐划一。但是,全球化在突破国家间边界的传统阻隔的同时,也造成了分裂。各种宗教和种族-文化组织拒绝牺牲其个性,并正在试图从它们所在的国家当中分离出来。
全球化还使国家的传统作用(即保持统一的作用)削弱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于尔根斯迈尔在接受委内瑞拉《国民报》采访时说:“在国家构架脆弱时,地区性组织就有机会从事分裂活动。”他以车臣危机为例解释说:“在前苏联非常强大的时候,车臣决不会图谋分裂。一旦苏联解体,莫斯科的中央集权被削弱了,新的分裂和种族活动也就开始了。”(注:〔委〕《国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文:《民族主义爆炸》。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2月16日。)应该说,这位社会学教授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使西方的意识形态得以推广,这一点激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的抵制。“全球化推动经济一体化、地区一体化,但是文化的融合极其困难。不同民族国家充满了摩擦和冲突,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民族精神、宗教传统、生活方式的存在使民族主义进一步凸现。”(注: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250页。)有些西方学者指出,人们的社会生活由"nation-state"这样的政治单位来分割的传统,正在被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文化影响的“全球化”所取代,这个尚未完成的过程引起人们传统认同意识的反弹,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近年来各地“民族”意识以及宗教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注:参见Rex,John,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 State: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Multi-Cultural Societies,Social Identities,Vol.l,No.l,1995。转引自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136页。)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和侵入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旨在维护民族尊严与独立地位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一种对抗意识。但是,民族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如何保持自己民族国家的本色而不被全球化浪潮所吞噬,是当前民族主义的一种普遍诉求。
第四,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非洲大陆的许多跨界民族(部族)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就是由殖民主义势力人为造成的,它为非洲地区的民族(部族)冲突埋下了祸根。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以及东帝汶问题也深深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原苏联、东欧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仇怨则更是与昔日列强在这一地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关。历史上巴尔干地区曾长期遭受外族统治,诸帝国对该地区各民族实行“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等政策,加剧了该地区的民族隔阂、仇视和宗教冲突,为该地区持续不断的民族厮杀埋下了伏笔。(注:参见邓浩:《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第44页。)目前,南斯拉夫联盟面临彻底分裂,塞尔维亚总理佐兰·金吉奇说,“北约”和“欧盟”特别是德国大力推进了这一进程。(注:参见德国《青年世界》网络版2001年7月3日文:《南斯拉夫面临彻底分裂》。转引自《参考消息》,2001年7月 5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本国切身利益的考虑,打着“人权”、“人道主义”的旗号,散布各种霸权主义论调。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A.Baker)说:“我们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我们能够并必须做的是,为了我们真正的切身利益,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和智略放在关键的挑战上。这包括巩固民主和东欧以及原苏联的自由市场,加强开放的全球经济制度,重新确定西方联盟。所有这些挑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我们对付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将直接影响未来美国人的生活。”(注:Keith Philip Lepor,After the Cold War,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7,pp.72-73.)
美国等西方势力还以民族问题为由干涉他国内政。如联合国自1991年以来对柬埔寨、前南斯拉夫和索马里等国家实行“新干涉主义”。(注:参见James Mayall,The New Interventionism 1991-199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冷战后,美国的“新干涉主义”愈演愈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次数趋于频繁:1990年出兵海湾;1991年实施“沙漠风暴”行动;1992年出兵索马里;1993年出兵马其顿,空袭伊拉克,发兵海地,出兵波黑;1995年增兵巴拿马,出兵波黑;1996年空袭伊拉克;1997年武力威胁伊拉克;1998年空袭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注:参见申华、王春永:《从“沙漠之狐”看美国“新干涉主义”》,载《国际展望》,1999年第2期,第11页。)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均是美国“新干涉主义”战略的具体表现。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外因,更多地是来自西方国家。美国为瓦解苏联,多年来一直拨出巨款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扶持所谓民主势力。西方不惜花费大量资金动用“美国之音”、“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等舆论工具,用俄语等数十种民族语言播放节目,给民族分离主义撑腰打气。西方势力还支持居住在国外的苏联侨民,资助他们成立组织和出版刊物,与国内的民族分离分子遥相呼应。在东德的政局变动过程中,西方国家特别是西德更是进行了毫不掩饰的干预。美国总统布什命令驻西德美军和大使向西德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表示“英国完全支持东德人民关于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的要求”。(注:张蕴岭:《欧洲剧变与世界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8-69页。)由此可见,来自外部的影响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和平渗透,是苏联、东欧变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另外,受发达国家所控制的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世界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不利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并且在继续扩大本已存在的南、北方的巨大差距。与极端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关的民族问题正好出现在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造成了强烈的离心倾向;而这些国家内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认为付出太多而心理失衡,要求得到更多、更大的自主权并谋求独立。因此,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当今世界民族问题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密切相关。
第五,民族国家在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增强。二战以后,南斯拉夫政府放任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结果是助长了阿族人的独立倾向。当1989年东欧剧变时,南斯拉夫又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权,这样便招致阿族人的强烈反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一度无暇顾及车臣的分离主义活动。1994-1996年车臣战争后,俄罗斯更是赋予车臣事实上的独立地位,致使车臣人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愈演愈烈。(注:参见邓浩:《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第45页。)在一些非洲国家,“法律的非道德性使一些地方民族的基本权利遭到损害。有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歧视甚至仇杀丝毫未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这种在国家法律庇护下对本国公民实施伤害的行动必然为被伤害的民族所不容”。(注: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第49页。)由于国家政权的滥用,民族冲突在所难免。还有,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出于尽快实现民族一体化的愿望,而在这一进程中“采取了某些过激的或不适宜的行政干预措施,从而忽略了国家利益与族体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注: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3-64页。)操之过急的结果是事与愿违,并由此引发或加剧了部族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矛盾冲突,这是人类应该总结的教训。
三、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走向
对于21世纪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民族主义正沿着聚变和裂变,或者说聚合和离散两种模式同时并行发展着。这两种模式或趋势既是对立的,又是并存的,而且往往聚变中包含裂变,裂变中包含聚变,相互交织,交叉发展”。“聚合的民族主义在以欧共体为核心的西欧国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典型,东盟国家集团也属此类,拉丁美洲也有此类现象”。“这种聚合型民族主义或称地区民族主义,主要以跨地区的经济合作为主,政治联合为辅。这种聚合型民族主义代表了民族主义的长远发展趋势”。“离散性民族主义则在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前南斯拉夫表现得最为突出。从发展前景看,民族离散趋势是不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注: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68页。)另一种意见认为,就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而言,由于当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它更趋向于保守而不是开放,趋向于回顾过去而不是前瞻未来,趋向于破坏而不是建设,趋向于民族自利而不是全球共荣”。(注:李永刚:《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载《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12期,第28页。)第三种意见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有相当多的国家并非自觉地进入一体化进程,而是不自觉地被卷进去。这些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风险在物质和思想准备上都严重不足,尤其是这些国家对全球化的风险认识不足,一旦全球化过程出现了危机,这些国家将首当其冲,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主导国家急于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对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的国家采取打压政策,因此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必然导致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而使全球化出现挫折。(注:参见李容华:《从全球化与理性主义的关系看全球化下的民族化趋势》,载《社会科学》(上海),2001年第5期,第42页。)
那么,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走向究竟如何呢?笔者认为有五种发展趋势:
1.经济一体化构成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导趋势,各国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为经济的发展创造环境。这种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其一,在国内进行调整和改革,把重心转向经济发展;其二,对外实行开放,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扩大对外联系,进入国际市场和参与国际分工;其三,利用地缘优势,与邻国合作,组成联合和一体化组织,推动组织内部的自由贸易,开放边界,实行资源的跨国流动、配置和利用。”(注:张蕴岭:《欧洲剧变与世界格局》,第16页。)这三方面的发展共同加强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进一步增强。这种联系、依赖与合作,在西欧国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并构成了一种“聚合型民族主义”,它代表了民族主义的长远发展趋向。
2.局部冲突的民族主义以更激烈、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民族冲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一种是一国内部的冲突。而冲突又分两种,一种是表面化的冲突,另一种则是目前尚未表面化的潜在冲突。”(注:张蕴岭:《欧洲剧变与世界格局》,第72页。)民族冲突造成的分离趋势不仅在原苏联、东欧地区非常明显,而且在西欧也存在类似现象。在西欧国家中完整性受到挑战最严重的是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其他存在分离主义运动的国家是英国(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以及法国(科西嘉)。德国不存在以民族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各州不断迫切要求在国家和欧洲联盟的政策中有更大的发言权。随着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中、东欧国家开始走上地区自治之路。在这种形势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的少数民族更有可能试图离开原来的国家加入另一国家,而不可能另立新的国家。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国家,其分裂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目前,俄罗斯联邦的人口近80%为俄罗斯人,这在俄罗斯数个世纪的历史中是罕见的。然而,占总人口 20%的非俄罗斯人口依然有3000万,他们多聚居在自治区或半自治区内。虽然 1992年的《联邦条约》规定,俄罗斯有89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但现实情况表明,俄罗斯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并未得到有效遏止。原苏联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容易遭遇分裂危险,当它们受到俄罗斯的外来干预时更是如此。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半岛有大批俄罗斯人,该国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方面易受到分裂的威胁。(注:参见〔美〕扎尔米·卡利扎德、伊安·O·莱斯著,张淑文译:《21世纪的政治冲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0-171页。)
世界其他地区也程度不同地遭受分离主义的困扰。库尔德人的叛乱是对土耳其国家完整的一个主要威胁。叛乱反过来又影响到土耳其与其主要邻国如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在由近1.8万个岛屿和500个不同民族的近2亿人口组成的国家——印度尼西亚,随着东帝汶的独立要求,也开始了分裂的进程。(注:参见〔委〕《国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文:《民族主义爆炸》。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2月16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什么会出现趋向冲突的民族主义呢?这是因为,“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发展模式尚未定型,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民族、种族、部族、地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因历史上的纠葛和现实利益的不同,由于协调机制的不够健全或领导层决策的失误或外来因素的干涉而导致冲突的不断产生”。(注: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68页。)
但是,极端民族主义不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因为分离主义不符合历史潮流,“随着民族意识的成熟,民族理性的发展,社会协调机制的健全,国际社会的协调和干预,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类生活全球化趋势的进展,民族离散终究会向民族聚合方向逐步转化的”。(注: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68页。)李巨廉教授在谈到今天的世界仍然存在不同层次的多种力量之间构成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威慑的关系时指出:在这种相互制约和威慑的关系中,“既有大国之间的制约和威慑关系,也有中小国家之间的制约和威慑关系;既有大国对中小国家的制约和威慑关系,也有中小国家对大国的制约和威慑关系;还有国际社会中多种势力的制约和威慑作用”。(注:李巨廉:《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第218页。)历史与现实证明,各国、各民族之间只有加强合作、彼此信任,才能走上共同发展和繁荣的道路。
3.民族主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综观20世纪的世界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族主义是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并驾齐驱的第三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正在超越近一个世纪以来被人们顶礼膜拜的政治意识形态,正在使意识形态的传统‘制度拜物教’不再神圣。”当代世界上有些国家正在寻找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家的实践方式是,“一方面接受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某些思想,选择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对在本质上被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舶来品’加以拒绝,或用民族主义加以改造”。(注:王新刚:《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世界历史》,载《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第136页。)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把经典的社会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根据本国国情来选择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因此,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均是: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促进民族发展和繁荣,“把民族政治、思想、文化传统视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将超民族的政治意识形态置于次要地位”。(注:王新刚:《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世界历史》,载《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第136页。)如俄罗斯的内在动力,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它并没有完全也绝不会照搬西方的经济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在具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5-10年内其内向型民族主义有可能更强烈。杨伯江在分析其原因时讲到了这样三点:一是日本国内综合性危机短期内难以消除;二是美国加强对日控制将激化“新民族主义”;三是中国崛起使日本感到压力。(注:参见杨伯江:《当前日本社会思潮与“新民族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第11页。)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被当作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则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这就是所谓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把掌握本国经济命运、自主行使经济主权视为民族国家勃兴的必由之路;政治民族主义把“追求国家身份”、争取民族主体地位作为政治实践的目标;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注:参见李永刚:《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载《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12期,第24-28页。)这是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理性做出的选择,也是未来民族主义发展的走向。
4.宗教性民族主义成为引发民族暴力冲突的重要诱因。目前,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从尼日利亚到黎巴嫩,全球各地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与宗教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当今世界上,信仰好像已经变成一种制造混乱的因素。例如,伊斯兰国家已经变得更加偏激和正统,在许多地区发生了很具爆炸性的、危险的活动。“哈马斯”和“真主党”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塔利班”主张在阿富汗推行最正统的穆斯林传统。在美国,也存在一些基督教运动的暴力行为,例如,1995年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大楼遭到了炸弹袭击。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恰帕斯州,发生了土著人的萨帕塔革命运动,原因是他们感到其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体系中受到被同化的威胁。萨帕塔主义者并不明显地具有宗教性,他们是在试图保护其文化传统。(注:参见〔委〕《国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文:《民族主义爆炸》。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2月16日。)在科索沃地区,阿族和塞族的矛盾分歧不仅表现在民族的不同上,也反映在宗教(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相异上。波黑的穆族人不是克罗地亚人就是塞尔维亚人,仅仅因为信仰伊斯兰教而自成一族,并与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人以及信仰天主教的克族人进行了三年战争。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宗教分歧也加剧了车臣冲突。(注:参见邓浩:《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第43页。)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于尔根斯迈尔的预言,这些具有威胁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21世纪继续下去。
5.民族主义问题的国际化趋向日益突出。“由于民族的政治地图和文化地图并不总是完全重合,因此关于民族问题的多国纠纷冲撞跌荡。”(注:马瑞映:《论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兼论民族主义终结论》,载《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第138页。)为什么民族问题和国际势力联系在一起呢?一方面,“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己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促使其要求国际化”;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打着“人权”的旗号,大肆干涉别国内政,在民族冲突中采取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做法,以达到肢解一个主权国家的目的,结果造成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乃至内战、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因此,“在当今世界上,一国之内的民族问题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干预已越来越难以避免国际化”。(注:邓浩:《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第43页。)
展望未来,我们清楚地看到,民族主义浪潮已经过去,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亲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和联合正在不断加强。但是,世界上的民族问题是复杂的、长期的,只要民族存在一天,民族问题就会长期存在。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利于国际范围内民族问题的解决。“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势力、组织机构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和侵入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唤起民族对抗意识时,民族主义无疑是很有号召力的旗帜”。(注: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136-137页。)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种族民族主义,西欧许多近代国家就不会产生。”(注:Michael T.Klare & Daniel C.Thomas,World Security:Trends and Challenges at Century's En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228.)但是,像极端的、封闭的和倒退的“原教旨主义”明显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相违背,很容易引起所在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总之,今后由民族问题引发的局部冲突不可能避免,从而不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在理论上应当加强民族主义的研究,总结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使民族主义朝着温和、理性的方向发展;在实践上,应当“加强预防武装冲突”,(注:顾震球:《安南: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武装冲突》,载《瞭望》,2001年第27期,第60页。)为促进入类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和建立非对抗性的、公正而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奠定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