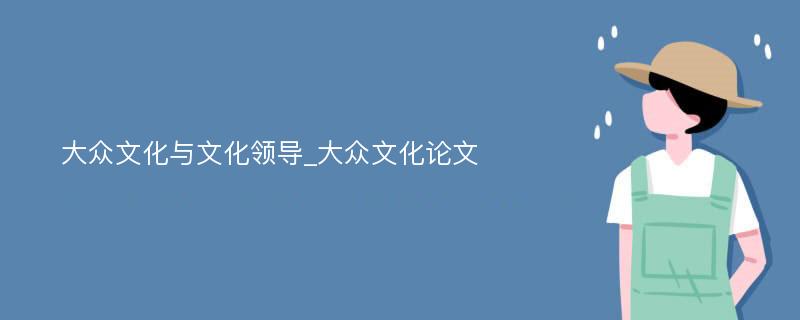
大众文化与文化领导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大众论文,文化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获得了空前的机会和条件,实现产业化的大众文化,因其活跃、多样和对娱性功能的肆意张显,已经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主流。不仅在青少年群体那里获得了狂欢式的呼应和反响、和大众一起制造着社会生活的时尚和偶像,甚至严肃作家或“主旋律”的作品,也从大众文化那里汲取了部分表达策略和表意形式。但是,这个业已无可阻挡的文化现象,却始终像一个不明之物:它受到来自精英阶层的抨击和批判,却受到了普通消费者的青睐和欢迎,但作为文化产业,它似乎并不介意评价和理解,而是自行其是地生产和发展。普遍的看法是,大众文化的兴起缘于文化市场的形成,或者是商业化促成的文化的非正常发展,这一看法主要来自精英阶层。但是,大众文化的全部复杂性并没有在这一简单和表面的批评和判断中得到揭示。在我看来,无论对大众文化持有怎样的态度,在当下中国它必然要以这样的形态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下的大众文化,是延安以来红色文化的“转译”形式,延安文化就其表达策略和表意形式而言,本质上是大众文化的。不同的是,红色文化负载着鲜明的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当下的大众文化置换了它的意义和功能。但它们都与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相关:红色文化帮助民众认同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从而使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共和国建立前就得到了确立;后者则表达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遭遇危机后重建的决心和自信。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根据雷蒙·威廉斯的考察,来源于希腊文,通常指的是支配他国的领袖和统治者。它具有政治支配的涵义,指的是一个国家宰制另一个国家。(注:[美]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巨流图书公司,2003年版。)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著作里,hegemony这个词非常重要,它不仅包含着政治、经济的因素,而且包含了文化的因素。这个词中文翻译多译为“霸权”,比如“文化霸权”,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同汤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极为相似。但在理解葛兰西的理论时,研究者和译者使用了“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就是“文明的领导权”,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单一愿望,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接受。因此,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就像“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互为接受的。
一、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确立
传统东方国家的强权专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由于东方国家市民社会的欠发达,不存在对抗革命的强大堡垒,无产阶级不必进行细致、漫长的精神和道德渗透,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在东方,无产阶级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完成。这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葛兰西的这一设定,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不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以暴力的形式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城市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它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获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前,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或从家庭叛逃,或从国统区奔赴延安。这里除了个人要求和对生活状态的不满之外,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精神感召不能说没有联系。
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曾分析过中国革命成功的独特性,他热情地赞颂中国革命的象征性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像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极为不同而困难得多的各种革命任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注:[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这一描述隐含了两方面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暴力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但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也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其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而是通过中国最广泛的民众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但是,当民族战争结束之后,在同国民党的战争中,到处都出现了“支前”的民众队伍,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是民众无条件地支持了要“解放”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仅从民众缺乏理性,易于受“战时文化”煽动这一点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机器,他们的“煽动”条件要远远优于共产党,但民众没有支持国民党,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从共产党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释民众对它的认同和追随。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释者是毛泽东。但毛泽东对“新文化”的阐释并不一定为民众所理解,他说:“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2页、388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2页、388页。)这种断裂式的文化变革,其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但形式却必须是民族主义的。对于没有文化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说,要他们在理论上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是困难的。这时,新文化的提出者为了让最广大的民众接受这一想象,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事实上进行了两次同步的“转译”:首先是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同时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感伤、浪漫、痛苦、迷惘的情调“转译”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因此,“新文化”又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在新文化的内涵被确定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形式的问题:“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涵?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3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注:[美]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一卷第217—218页。)这一资源后来衍生出了有关“新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应该说,这是一条建设“新文化”的卓有成效的途径。在迈向这条道路的过程中,白毛女、小二黑、李有才、王贵与李香香、开荒的兄妹等,这些活泼朗健的中国农民形象,不仅第一次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那一时代,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毛泽东也可以抽出时间亲自过问他历来重视的文艺问题。
毛泽东的新文化观念,正像后来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注:[澳大利亚]王衮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毛泽东》,见《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这的确是一种政治上的缘故,但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对于民众来说则是“偏爱”中蕴涵的道德力量。在毛泽东处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达中,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民众一边。他对民众运动的热情赞颂,对农民思想品质的想象性构造和倾心认同,都使知识分子相形见绌。而且,知识分子“五四”时期建立起的“个人主义”在与农民的比照中,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内部异己。而葛兰西那里,他对“有机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他们负有回答“卑贱者”提出的问题的义务。但是,在毛泽东那里,知识分子并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准确地说,他们没有资格,或者说在毛泽东看来他们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任务。知识分子只负有阐释和宣传的义务。我们还注意到,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毛泽东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所塑造的可效仿的“典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军人。他们纯粹、透明、乐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种“新文化”所期待的人物,在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这些人物在毛泽东的热情赞颂和诗性表达中,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在文学艺术领域,“新的人民文艺”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构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谱系。这些表达道德理想的形象在民众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为他们是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民众那里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是无须怀疑的。
二、大众文化与民族性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在民众对这个领导权认同的过程中,大众文化起到了超乎想象的重要作用。大众文学是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而通俗小说又是大众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文体。这一文体在精英立场支配下的文学历史叙事中,尽管表达得很不充分,甚至多有轻慢,但事实上它在民间的影响力超出了文学史叙述者的想象。这与民间对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是大有关系的。陈平原曾分析过“史传”、“诗骚”入小说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他分析说,“诗骚”传统自然与历史形成的诗歌正统地位有关。不在小说中写几句“有诗为证”就会显得作者很没文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小说形式的发展受到历史著作的深刻影响。以至于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在评《水浒》、《三国演义》、《金瓶梅》时,无不以《史记》相类比。(注: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222页。)这一传统不仅为文人阶层普遍认同,而且在普通读者那里也是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读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自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注: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04页。)由此可见普通读者不仅对历史故事兴致盎然,而且也多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
进入当代之后,把小说当作“历史”来理解的传统,在民间仍然普遍存在,文学创作也将“史传”传统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再度复兴。于是便出现了创作与接受/生产与消费相适应的关系。当然,这一局面的形成,背后隐含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多年探索、实验、积累的艰难过程,同时也是延安经验由局部放大到整体的成功实践。1949年9月5日,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布成立,但文艺界“争取小市民读者”的工作已经先期展开。这一天,刚刚组建不久的《文艺报》邀请了平津地区过去常写长篇小说的部分作者开座谈会。会议主席陈企霞说会议的意义就在于研究通俗小说形式的写作经验和读者情况,讨论怎样改革这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当其被很多人所欢迎和注意上时,我们就不能置之不问。”对通俗文艺的关注,不仅与延安经验相关,而且同时注意到了“在敌伪和国民党统治时代,这种小说盛极一时。各个报纸副刊抢着登这一类小说。印刷厂排字工人也抢着排这一类稿子。好多店员一翻开报纸首先看昨天没有读完的小说。”因此与会的赵树理说:“哪一种形式为群众所欢迎并能被接受,我们就采用哪种形式。我们在政治上提高以后,再来研究一下过去的东西,把旧东西的好处保持下来,创造出新的形式,使每一主题都反映现实,教育群众,不再无的放失。”但如何才能在政治上提高呢?他“希望大家详读每天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新的文艺理论书籍。”(注:《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载1951年《文艺报》1卷1期。)因此,大众文艺或通俗文学成为共和国时代的主要文艺形式,不仅这一形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的是它对于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构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所具有的功能性价值。
进入共和国以来,我们发现,最为发达和成功的大众文学是革命历史题材。也有人认为还应该加上农村题材。这一看法的可商榷之处就在于,说农村题材发达是对的,但说它成功则未必可靠。这是因为,农村题材因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关,当文学艺术努力表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时候,他们发现,要想证实它的合理性是极为困难的。《创业史》被普遍认为是一部经典性的成功之作,但后来作家柳青无法再去表达他心爱的人物如何迈进新的历史阶段。那个新的历史阶段后来被认为是必须纠正的。这一情况限制了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而革命历史题材则不同,它是胜利者在回顾或重现自己已经被证实了的历史,对它的重新叙事不仅进一步激起了历史书写者的自信心和光荣心,重要的是,它更隐含着过去/现实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民众通过历史进一步理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把历史/现实理解为一种必然的关系。因此,大众文学对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领导权的确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这一领域始终密切关注。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397页。)因此,强调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的民族性,是毛泽东指出的方向。此后有关“民族性”、“民族化”、“民族形式”的讨论,事实上都是对毛泽东关于民族文化论述的具体解释和落实的技术性处理。(注:关于民族形式、民族性、民族化的问题,就中国的语境来说,它最终的目标诉求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汪晖曾在《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一文中说:“就中国而言,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自决的过程,而且也是创造文化同一性的过程,即创造超越并包容地方性和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同一性。文化同一性的创造不仅诉诸种族、语言和传统,而且也诉诸时代,因此,这种文化的同一性被理解为‘新’的同一性。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民族形式’的讨论就是形成和创造现代民族文化同一性和主体性的努力之一。”汪晖所关注的这一论争,进入共和国之后仍然在进行,不同的是,这一时代的讨论已经仅仅限于操作层面,理论探讨已为如何落实所置换。)所谓民族的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文化。自这个时代起,有关文学艺术的思想路线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坚持民族性和大众化这一点上,始终没有变化。共和国时期的文学,严格地说除了少数试图建构“史诗”的作品外,大都是通俗的大众文学。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如《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就是传奇章回形式中的民族性。这些作品延续了传奇小说的叙事形式和内部构造,它们在装进了“新的内容”,起到了教育人民、建构民族的防卫屏障的同时,也替代了过去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娱性功能。
通俗小说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模式化。事实上,所有通俗的、大众的文化都一定是模式化的。一个被大众熟悉的模式才有可能被大众所接受,他们阅读、观赏、倾听的过程中,就是他们的心理期待不断的兑现和落实的过程,也就是获得快感和满足的过程。写通俗文学的人说:“写武侠小说是,先写出一个本领很大的人物,但又必须有另一个比他本领更大的人来制服他,于是便造出一个更神怪的人物来。这样叠宝塔式地堆上去,本领大到顶点怎么办呢?只好搬出神仙鬼怪来压服所有的人物。”而对于接受者来说:“中国老百姓一向是要求有头有尾、布局周到的。譬如在农村演戏,演到捉住汉奸特务,舞台上的群众一声喊打喊杀,立刻就闭幕了。而老百姓看到这里却不肯走,他们认为还没有完,‘汉奸特务到底杀掉没有呢?’”(注:《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载1951年《文艺报》1卷1期。)这一接受心理使新的通俗文艺在注入新的内容的同时,仍然在旧的模式内展开。(注: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认为:“自从传统小说《三国演义》首设‘五虎将’模式以后,五种性格构成的主要英雄人物常常是古典武侠小说的基本人物模式。”“在当代战争小说里,有些作家不自觉地运用了‘五虎将’人物关系的模式。除了《林海雪原》外,还有如《铁道游击队》中刘洪、王强、林忠、鲁汉、小坡的‘五虎将’,《烈火金刚》中史更新、丁尚武、萧飞、孙定邦、孙振邦的‘五虎将’,等等。”这一概括是很有趣的。见《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73页。)民间接受心理的坚不可摧,使经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作家的观念、情感以及受到的写作影响和训练,必须大大地妥协以适应他们的接受对象。“五四”时期彻底否定的旧文化一部分的通俗小说写作模式,又逐渐地得到了光大。因此,文学的现代形式,是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得到确立的,五四彻底反传统的路线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不可能被贯彻到底。它的影响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超出知识分子阶层。像刘之侠、曲波、刘流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家,大都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他们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哺育,这一经历本身不仅使他们具有了一种“身份”的优越,同时他们接受的文化,旧“形式”始终是相伴随的。《林海雪原》出版之后,何其芳说:“在当时读完后我就想,作者一定很得力于我国的古典小说,因为从其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学习古典小说的写法的痕迹。学习而还有过于明显的痕迹,或许也可以说是缺点,然而我国的古典小说的这种突出的艺术特点,情节和人物给读者的印象非常深,读后就不能忘记,却是十分值得学习和发扬的宝贵传统。”他进一步援引作者曲波的看法说:”在写作的时候,我曾力求在结构上、语言上、故事的组织上、人物的表现手法上、情与景的结构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我这样作,从目的性来讲,是为了要使更多的工农兵群众看分队的事迹。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非常喜爱这些文学名著,深受其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道德及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它们使我陶醉在伟大的英雄气魄里,但叫我讲给别人听,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水浒》、《说岳全传》,我可以像说评词一样的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可以背诵!在民间一些不识字的群众也能口传;看起来工农兵还是习惯于这种民族风格。”(注: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文艺水平的提高》,《文学研究》1958年2期。)这些建立在语言、故事、人物、情与景描述基础上的“民族风格”,使大众感到了熟悉的亲切,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在阅读感知中建立起来,这就是“形式的意识形态”。人民在原有的形式框架中找到了和民族传统的历史联系。
当然,民族性的建构,最后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民众重新提供一个熟悉的、可供消遣娱乐的“形式”,它最终要达到的是民族独立和民族防卫的屏障意识。像《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作品,在阅读中既体验到了神出鬼没、智勇双全、血腥暴力的快意恩仇,同时在这种津津乐道的刺激中,又受到了民族自尊自强、为维护族群不惜流血牺牲的无畏精神的教育。
强调民族的共同利益,在外来侵略面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思想路线和斗争策略。在五六十年代,维护民族独立的战争已经胜利完成,但动员民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则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似乎是一个现代化的要求,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国家行为,但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含有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诉求。在这样的时代通过文学作品强调民族性,是进行新一轮民众动员的现实需要。因此民族性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内容之一。用德里克的话来说,就是:“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其全部历史中都表现为中国民族纲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为了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不可避免同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发展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形式出现在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而无法和摆脱帝国主义霸权而获得解放的斗争分离开来。”(注: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邓正来译,见萧延中等编《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在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建构中,民族性、理想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构成了这个空间的支撑性主题。以至于从90年代至今,批判社会风气和金钱拜物教时,仍有人与50年代进行对比,认为那仍是有效的历史资源,这一文化的久远影响由此可见。
三、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
大众文化在80年代以来的发展,集中表达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重建的事实。或者说,文学一体化时代的终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格局。但是,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经验的完全放弃。文化领导权的重建,仍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文化传统的惯性延宕,一是全球化、商业化、市场化的深刻影响。文化传统在不断建构的情况下,在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仍然具有支配性的功能。但全球化、商业化、市场化作为世界性的时代潮流,也具有解构传统、建立新的文化时尚和文化霸权的可能性。
在这种新的文化处境中,大众文化与经过“转译”的、为了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大众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的消费性、商品性和最大限度地赚取剩余价值的目标诉求,成为它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消费性质的、软性的大众文化,被普遍认为是“带菌的文化”。它在夹缝中生存并腹背受敌。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文化类型里经常含有的“不健康文化”,于社会来说是有害的,它普遍流行的后果无疑与“伤寒病菌”相类似,作为文化疾病,尤其对青年的毒害更是后患无穷;在知识分子文化看来,这是一种“低俗的文化”,是与学院文化和经典文化不能相提并论的文化垃圾。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想到大众文化与“伤寒玛丽”的相似性关系:玛丽的身份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她不是美国本土公民,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她的身份本来就是可疑的,或者说,她的“不洁”与她的身份先天地联系在一起;作为“爱尔兰人”,种族的问题也隐含于“带菌者”的叙述中,或者说,“伤寒病菌”是外来的,对于美国的沙文主义来说,他们顿时拥有了另一种恐慌。一位医学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到:“从去年好几个星期到今年冬天,亚洲霍乱光顾了欧洲人民,在俄国尤其如此。每天早晨,美国的读书人、领导人、杰出的务实家、还不包括像小鸟一样早早起来翱翔的自由人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人,这些美国公民们一边浏览报纸,一边为那些遭受着痛苦的不幸者感到悲悯,他们因为无知和懒散而不得不承受痛苦。美国公民像往常一样,在早餐的咖啡杯面前庆幸自己没有像那些盲目的、糊涂的、和迷信的帝俄农民一样无可奈何地承受和死于霍乱。这样美滋滋地思索着的美国公民在他的某个阈下意识层上搁置了或不再考虑美国的伤寒病。”(注:[美]普利西拉·瓦尔德:《文化与带菌者——“伤寒玛丽”与社会控制科学》,见王逢振主编:《“怪异”理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在这样的叙述中,美国幻想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跃然纸上。但是,“伤寒玛丽”使美国和帝俄的农民的区别变得困难和复杂;性别歧视也同样隐含在“伤寒玛丽”的叙事中。这个爱尔兰女性因这个恶名而被妖魔化。她被描写成一个丑陋的女人,一个壮实的如同男人一样的女人,一个老处女却同肮脏的男人睡觉的女人。在这样的叙述中,“伤寒玛丽”的恶名被一再放大,于是她也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带菌者”。
大众文化的不被信任,源于意识形态和经典文化的优越感,就像美国沙文主义面对亚洲霍乱一样。意识形态的秩序和国家民族关怀叙事以及知识分子经典文化信仰,使处于边缘的大众文化不仅在文化“等级”上倍受歧视,而且因其对文化尊严的冒犯也始终难以确立其合法性地位。大众文化一旦被指认为“带菌”之后,它动荡不定的“身份”和命运就几乎是宿命的。在学院经典文化维护者那里看来:大众文化是“通俗的(为大众欣赏而设计的)、短命的(稍现即逝)、消费性的(易被忘却)、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诙谐的、色情的、机智而有魅力的恢弘壮举……”(注:[美]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0页、第90页。)这些特征以凯旋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文化支撑点,并以“文化幻觉”的方式制造了新的意识形态。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注:[美]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0页、第90页。)这些文化英雄主义的判词,使大众文化命定地成了文化结构中的丑角。然而,这一揭示对中国大众文化来说却并不全然有效。
大众文化的面目始终是“中性”的,它并不主动地去攻击什么。它的出现应该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对这一文化的接受已不止是普通民众,在知识界,喜欢言情、武侠作品的大有人在。90年代,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的专题课并大受欢迎;在黄金时间,消闲性的影视作品几乎在所有的电视台播出;软性小说是出版社获得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这说明,市场文化已被知识界和国家意识形态传媒部分地接受。因此,这一文化形态已经完全普泛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有巨大的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以中性的面目出现,没有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它只有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利益原则。它使日常生活变得亲近可感,无论什么趣味和爱好的人,都可以在今日的文化市场上找到自己的读物或音像制品。市场文化的无所不有,无形中解构了“一体化”的文化统制,它分散了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关注和热情,使“一体化”的文化霸权在无意中被分解。但是,大众文化本身是幻觉文化的一部分,它所有的温情脉脉和刺激,都是以想象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它与人们生存的现实并不发生直接关联。尽管如此,心灵疲惫的人们仍愿在这种文化中实现个人的向往和趣味,他的浸染力把世俗生活渲染得令人无可抗拒。大众文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占有市场并获取事业利润就是它最大和最后的目的。在利益的驱使下,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这一文化形态纳入市场,经过新的发掘和包装后,使其变成文化消费品。这一策略甚至使“红色经典”和严肃文学作品也在这样的策划中转化为消费。
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体现了重建中的文化领导权的包容性,它为多种文化共生奠定了合法性依据和公共环境。应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是符合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和未来发展要求的。但是,令人关注的是,开放的文化环境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已不单纯地表现在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它同时还存在于在这些观念影响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性的选择中。“自我塑造”在这个时代已成为相当普遍的文化信念,从服饰、职业、形象、情趣等,个人化与个性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它的进步无须赘言,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公共话语和共同关怀的日趋淡薄。文化冲突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不仅有必要描述它,同时也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立场。两方有的学者指出:“现代化可能是具有整体性的,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整体,它必然包含着紧张、压力、混乱和骚动。”(注:[美]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344页。)
大众文化在90年代以来得到迅猛发展。80年代初期,在港台文化的“反哺”下,以港台歌曲为表征的大众文化,从“地下”迅速浮出地表,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港台和海外华文电视剧在中国电视传媒的广泛传播,被民众迅速认同。因此,就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力和支配性而言,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主流文化”。尤其是电视文化,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电视文化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展示以及它在农村的普及,使农村青年更加向往城市生活。农村生活在近年来的电视剧中几乎已经成为空白,农村这个最值得关注、最需要安定的领域,恰恰在电视文化中被做了边缘化的处理。“民工潮”的出现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与电视文化对农村的遗忘不能说没有关系。因此,要处理好“主旋律”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必须改变当前对“主旋律”的狭隘理解和对农村题材的忽视。或者说,无论哪个领域,哪种题材,只要是表达了对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维护,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表达了对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感的向往,并有较高的艺术水准,都应该纳入“主旋律”的框架之内。也只有这样,才能扩大“主旋律”的合法性边界,从而淘汰文化生产中“政治上正确”但艺术性苍白的问题。
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强势文化或全球化、“同国际接轨”等文化语境有密切关系。值得我们警觉的是,所谓全球化事实上就是美国化。在当下中国,到处充斥的美国文化现象,其背后隐含着的帝国主义的文化支配和无处不在的美国价值观。在好莱坞的影片中,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它把美国的想象强加于全球,并试图遮蔽接受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文化经验和现实关怀。在对年轻一代进行“美国情结”的培育过程中,破坏或摧毁了他们原有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气质。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对美国的想象和奇观的肆意夸大、对美国生存现实和情调的渲染,都会压抑他们对本土生活的切实感受,对本土文化的疏离甚至抱怨。全球化的文化处境虽然对民族文化构成了冲击和挑战,但同时也为中国电影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华民族悠长的历史和多难的现代经验,培育了我们民族对本土文化的亲和关系,培育了我们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方式。只有我们加快电影生产机制、审查制度的改变,尽快建立有效的文化生产战略和具体措施,才有可能突出强势文化的重围,有效地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和垄断。
“文革”结束之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开始了重新建构。它在形态上改变的标示,是将强烈的道德理想追求转变为现实的物质积累。激进的“新文化想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覆盖下,几近自行崩解。文化公共空间的拓展,使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有了重新阐释的可能。它具有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新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这种重建的文化领导权,分解了“文化霸权”的一体化统治。这既符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冷战结束后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各种传媒包括权威传媒对大众文化态度的变化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开放性和宽容度还仅仅限于市场号召和消费主义的引导。利益的驱动已经不加遮掩,娱乐性节目和报刊有惊人的收视效率和发行量,而它的背后则是巨额的商业广告在拉动。特别是白领趣味的文化,它们事实上已不关心读者的真实需要,他在悄然地改变着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培育着他们狂热消费,享乐欲望的同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广告商人或跨国投资者的趣味,广告收入已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主要利润来源。它在无情地将不具有市场号召力的文化挤出市场的同时,也以其对现实问题的拒绝触动而获得了“合法性”。事实上,它的意识形态宣传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因此,一种隐形的支配正在形成新的文化“领导权”,这也正是当下学界对大众文化持有批判态度的原因之一。
市场利益的竞争和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起,使更多的大众文化制作直接同经济利益结缘。事实上,即便在文化市场已经形成的今天,文化产业仍然是特殊的产业,文化产品仍然是特殊的商品,它除了具有商业价值、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负载着处理人类精神事务、彰显进步价值观念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文化活动又是关乎世道、浸润人心、引导人类走向进步的精神工程。正是基于上述看法,我认为,大众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重建过程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多年的大众文化生产实践,既为我们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也有不可忽视的教训。因此,在重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框架内的大众文化生产,有必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
一、在强势文化覆盖全球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和西方文化带着它的意识形态将“合法”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在不作宣告中将进一步加剧。对西方廉价的大众文化仅仅诉诸于情感抗拒和意识形态批判是没有力量的。我们在批判西方大众文化支配性的同时,也要汲取西方大众文化的生产经验。这个经验一方面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一方面是对制作经验的学习。大众文化既然是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那么就应建立市场竞争机制,让作为商品的大众文化在竞争中进入市场。这是体现大众文化生产公平、公正,避免行政干预的有效途径;对抗西方必须先学习西方。以美国好莱坞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所以在全球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制作经验。这个经验在形式上就是“模式化”。大众文化必须建立成熟的模式,就像好莱坞大片、金庸小说、港台电视剧、世界杯足球赛、美国NBA等大众文化一样。只有成熟的模式,才会不断地抵达观众、读者的欣赏、阅读期待,才会获得消费者的接受和热爱。
二、对无产阶级文化遗产的研究和继承。无产阶级文化的兴起和终结,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当急风暴雨的革命成为过去之后,作为遗产的无产阶级文化并没有成为过去。特别是在现代性的过程中,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情怀和批判性资源不断耗尽,但无产阶级文化中却蕴涵着丰富的上述资源。在商品社会中,人们在享受丰裕物资生活的同时,精神上仍然渴望和崇拜英雄主义文化。不然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美国战争大片格外受到消费者青睐。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实践过程中,已经注意到民族性的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性,那么,当下的大众文化生产有必要继承无产阶级文化中合理的东西,这不仅建立了文化的历史联系,丰富了自己的现代文化传统,同时,也是获得文化独立性、占领文化市场的手段之一。
三、注重对传统资源的再开掘。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大国,但我们仅仅引以为骄傲是不够的。事实上,当今的文化市场,谁占有了巨大的资源谁就会占有巨大的市场。20世纪以来,我们在建立新文化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我们巨大的文化破坏性格。我们曾批判一切,打倒一切、摧毁一切。这个破坏的文化性格在今天虽然得到了遏止,但仍然阻碍着我们文化建设意识。其实,曾被我们打倒、推翻、摧毁的传统文化,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遗产和可以重新激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我们在台湾、香港乃至韩剧、日剧中,总是会清晰地发现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世风代变,但人类基本的价值尺度不会改变。在价值观、伦理观日见混乱的今天,重新回望传统并将其激活,肯定是一条令人感到鼓舞的道路。而且,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大众文化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对大众文化在重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的作用,应该怀有乐观和自信。
标签:大众文化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铁道游击队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林海雪原论文; 烈火金刚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文艺报论文; 新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