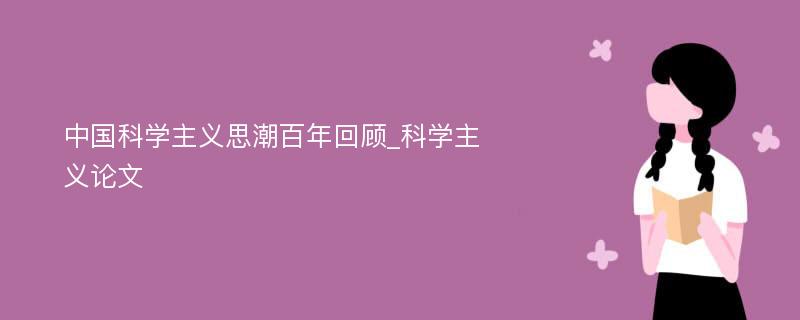
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百年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1999)12-0016-05
科学主义思潮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主要思潮之一。它在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中是最早发生的。其基本点在于强调并放大科学意义和科学方法,认为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对宇宙人生作出正确的认识和说明,主张把哲学建立在实证和经验的基础上,使哲学沿着科学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科学主义思潮的出现与发展、影响和演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以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为背景的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百年来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双重哲学运动。
一、科学主义思潮的崛起
科学主义思潮的发生,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戊戌维新中的严复。作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严复与同时代的康有为、谭嗣同都重视科学,但他们对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理解。正是这种理解的不同,使得严复成为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开启者,同时也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启者。
康有为、谭嗣同主张把西方近世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结合起来,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实际上,他们是把西方近世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哲学传统框架中,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论与本体论相结合的特点推向了极端,如康有为认为:“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孟子微》);又如谭嗣同主张:“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仁学》)。康、谭的哲学体系,被梁启超称之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见《清代学术概论》)。
严复则打破了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哲学范式。他继承了西方近代经验主义传统和现代实证主义原则,认为“可知者,止于感觉”(《穆勒名学》按语),只有在经验范围内的东西才是可知的,而离开了经验的“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之类则不可认识、不可思义的(见《天演论》按语)。因此,他主张解构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论与本体论的结合,把能够作经验证实的宇宙论与不能够作经验证实的本体论分离开来,并由此而引入经典力学和生物进化论的框架,加以变形和放大,建构起科学宇宙论。严复的科学宇宙论,不仅是一种自然图景及其解释系统,而且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唤起中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存,从而在上个世纪之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一来,严复就第一次把中国哲学置于近代科学基础上和框架内,使哲学沿着实证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主义思潮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席卷了中国思想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曾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但他们对科学的推崇与提倡,比严复要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是指导人们认识宇宙人生、进行健全思维的框架,而且成了反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的最重要的旗帜和武器。正如陈独秀所宣称,唯有“德先生”与“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有其积极的意义。它对科学和理性的高扬,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对于封建蒙昧主义无疑是猛烈的冲击,起了振聋发聩、启迪人心的作用。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通过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科学代替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权威地位,实际上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五四”以后的各种政治思想派别,都承认科学的这种崇高地位,对科学作了不同程度的接纳。用胡适的话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序》)。
二、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发展
由严复所开启的科学主义思潮,经过五四时期的空前发展,特别是经过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形成了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丁文江和王星拱。
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力图从哲学上建构科学主义思潮的内核,其基本纲领可以用他们的两句话来概括:“哲学是假科学”(胡适语),“科学是真哲学”(丁文江语)。所谓“哲学是假科学”,是指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是非实证的、非科学的,应当加以拒斥;所谓“科学是真哲学”,则强调哲学应当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建立科学主义哲学体系。然而,胡、丁、王在理论上又各有偏重与特点,从不同方面对这一纲领进行了发挥或修正。
丁文江深受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和现代实证主义原则的影响,从经验出发,对于形而上学作了坚决的批判。他指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史,是一个科学各部门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获得独立发展的过程。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形而上学作为根本哲学,包罗了宇宙人生的一切重大问题,但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各种科学部门相继独立出来,哲学只剩下本体论这块地盘;而进至20世纪,哲学又出现了科学知识论这一新的科学的哲学,主张感觉经验是我们知道物体的唯一方法,而感觉经验之外的物体则是不可知的,应当存而不论。这种科学知识论成了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从而使得本体论在哲学中已无立足之地,不能再混下去了。他强调:“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玄学与科学》)。
胡适也强调经验的意义,但他讲的经验与丁文江讲的经验有所不同。丁文江对经验的理解来自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把经验看作是依靠瞬息的、原子的和单独的感觉构成的;而胡适对经验的理解来自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把经验看作是人、自然、社会交互作用下所产生的连贯而有意义的活动,这种活动也就是生活。胡适认为,把经验看作是感觉构成的,又需要理性主义者提供理性,来综合、组织这些细碎散漫的感觉经验;而把经验看作是生活,那就意味着“经验的活用,就是理性,就是智慧,此外更没有什么别的理性”(《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主张的实用主义科学方法,包括了两个内容:一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二是“历史的态度”。由此,胡适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那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实验主义》)在他看来,古今中外形而上学家所说的“道”、“理”、“气”、“无”、“上帝”、“太极”、“无极”之类,都不能断定哪个说得是,哪个说得不是,只好由他们乱说罢了。同时,胡适力主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建立起一种包括宇宙论在内的“科学的人生观”。
如果说胡适的“科学的人生观”尚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框架,那么王星拱则建立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科学宇宙论。这个体系体现在他于1930年出版的《科学概论》一书中。在书中,王星拱总结了经验论科学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从现代物理学出发描述了新的宇宙图景,一方面发展了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基本思想,一方面又对经验论科学主义作了一些合理的修正。如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他就力图克服丁文江、胡适提倡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偏激情绪,认为科学与哲学是不同的学问,都有存在的理由。在他看来,尽管哲学应当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但并不意味着哲学就因此要为科学所取代。哲学可以作为“科学之科学”而继续存在,一者可用综合的眼光考察各门相互分离的科学,二者可为科学提供关于宇宙人生的价值观。这实际上暗示着对新的形而上学的呼唤。
在这个基础上,金岳霖基于对时代和哲学的感受,不同意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对于形而上学的拒斥,主张重建本体论。在金岳霖看来,一个哲学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知识论的态度,另一是元学(本体论)的态度。知识论的态度,指在知识论研究中保持客观性、实证性,不带入哲学家本人的情感;元学的态度,指本体的观念凝结着主体的理智、情感、意志,反映着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自觉。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知识论的态度当然是重要的,但元学的态度也是不能少的。从元学的态度出发,金岳霖于30年代后期写了《论道》,建构了他的“道论”本体论。从知识论的态度出发,他又于40年AI写作了《知识论》,建构了他的“知识论”体系。金岳霖在建构本体论和知识论时,也同样看重经验的意义,力图以经验作为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基础,但同时又赋予了经验以客观的内容。在“道论”中,他以“道”为本体概念,作出了“道是式—能”的规定,认为“能”作为既非共相又非殊相的东西虽不能用言语直接地传达,但却能在“宽义的经验”即“有推论有想像的经验”中抓住它;他又认为“道”体现于本然世界之中,本然世界的变化、时间、先后、大小等情形都是可以经验到的,“只要有经验,它们都不会是假的”。在“知识论”中,他批评了经验论上的“唯主方式”,强调经验能够获得对象的实在感,提出“所予是客观的呈现”。这些都表明,金岳霖一方面保持了与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超越了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限制。可以说,经验论科学主义发展至金岳霖,已近于终结。
三、唯物论科学主义的出现
在经验论科学主义兴盛的同时,又出现了以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为代表的唯物论科学主义。其特点在于明确地宣称应当把科学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同时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以融铸成一种新形态的哲学。
张申府是中国把逻辑主义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的第一人。30年代,他即提出:现代世界哲学的主要潮流有二,“一为解析”,“二为唯物”。逻辑主义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现代哲学主潮,最根本一点,在于它们都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当然,它们也有不同点:“逻辑解析不免要有所分,照例是根据原子论的观点的;而辩证唯物论侧重于全,于变,于事象的相关关联。”这种不同,正好相互补充,既可克服分析哲学的割裂破碎之弊,又可匡正辩证唯物论的笼统模糊之弊。因此,他认为:“最近世界哲学界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以上见《现代哲学的主潮》)张申府又提出,哲学有党派性是不容否认的,哲学有民族性也同样是不容否认的。这种新的哲学创造,还必须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仁”、“易”、“生”三个字上。中国哲学家重视宇宙的运动,追求生命的意义,而将这种仁的精神贯穿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之中。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基本精神,是合乎辩证法和唯物论的,也是这种新的哲学创造所当吸取的。
张岱年则进一步试图把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构造三个“三结合”的哲学体系。他在40年代完成的《五人五论》就是这种努力的成果。在这里,张岱年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论证了唯物论的合理性。他指出,哲学史上的哲学系统,根据它们对基本范畴的理解、选择的不同,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是物体论系统或唯物论;二是心本论系统或唯心论系统,三是理本论系统或理性论系统,四是生本论系统或生命论系统,五是实证论系统或经验论系统。通过对这五种类型哲学的分析比较,他得出结论说:“从基本观点言之,物本论实为正确。物为根本,此乃真理,而心本,理本,生本,实证论,皆以非本者为本,其宗旨皆误。物本论而能免于机械论之偏失,予理、生、心以适当的说明,即足以解释生活经验而无憾。”(《哲学思维论》)张岱年又努力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现代唯物论在中国生根、发展的结合点。他认为,这个结合点应首先从明清之际以来近三百年的哲学思想中去寻找,因为这三百年中有创造贡献的哲学家都是倾向于唯物论的。其中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即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王、颜、戴的哲学都不甚成熟,但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很对的。新的中国哲学,应顺着这三百年来的趋向而前进。
由于历史的原因,唯物论科学主义没有像经验论科学主义那样在理论上作比较充分的展开,因而其影响也小得多。但作为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派别,唯物论科学主义有其自己的特点和贡献,则是值得重视的。
四、走向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思潮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其他一些思潮,如人文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国民党哲学,都受到科学主义思潮不同程度的影响。属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冯友兰,就以科学主义思潮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为基础,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建立了影响很大的“新理学”体系。他明确宣称:“新理学的工作,是要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而重新建立形上学。”(《新知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也表现出不同形式的科学主义倾向。陈独秀在解释唯物史观时认为,哲学是属于社会科学的学问,因而是一种科学。但这里的哲学,“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科学与人生观〉序》)。瞿秋白在传播辩证唯物论时主张,宇宙的唯物性质在科学的研究上可以完全证明。他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归根到底,‘存在’的根本,始终是电子组成的物质。”(《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毛泽东在延安研究哲学时,突出了“实践论”及“矛盾论”,尤其看重认识论、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在晚年更明确地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强调认识论、方法论是哲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在国民党哲学中,科学主义思潮也很有影响,不仅孙中山论知行关系的发展是按照进化论模式来讲的,而且蒋介石还有一本题为《科学的学庸》的讲演集。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思潮的崛起和发展,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潮哲学家的怀疑和批判。王国维是第一个敏感到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矛盾的哲学家,他认为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困惑。章太炎是第一个怀疑科学进化论的哲学家,他提出“俱分进化论”对理性与科学必然引导人类趋于至善表示了怀疑。而从熊十力开始,明确地提出了科学与哲学的划界工作,认为哲学有自己永远不能被科学所夺去的领域,这就是不可能科学化、实证化的本体论,冯友兰讲“真际”与“实际”、贺麟讲“逻辑的心”与“心理的心”都是做这一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哲学家开始对科学主义的合理性及其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进行反省。金岳霖的学生冯契就是这样一位力图走出科学主义的先行者。冯契在40年代师从金岳霖时,就感到金岳霖主张区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类似于王国维讲的“可爱者”与“可信者”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继续发展着;但随着中西哲学的交流与会通,是否有可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解决两大思潮的对立问题,这是值得哲学家们郑重考虑的大问题。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冯契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思路: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吸取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的一些合理因素,建立一种不仅在于说明知识而且在于阐明智慧的“广义的认识论”。这个被冯契称为“智慧说”的“广义的认识论”,一方面主张“化理论为方法”,另一方面强调“化理论为德性”,从而把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打通起来。这样就改变了金岳霖的“知识论”和毛泽东的“实践论”只讲知识不讲智慧、只讲认识对象世界不讲主体人格追求的局限,也就超越了科学主义的限制。冯契的这些思想在他的《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书)中得到了较系统的阐述。他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说:“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进而会通中西,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便应该能达到一种新的哲理境界。”通观冯契的哲学遗产,确实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境界。
冯契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也是富有启发性的。如何扬弃、消化、吸取科学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与其他中西哲学的思想资源融汇贯通,创造新的中国哲学,追求新的哲理境界,将是值得21世纪中国哲学家们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标签:科学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知识论论文; 金岳霖论文; 本体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胡适论文; 哲学史论文; 经验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