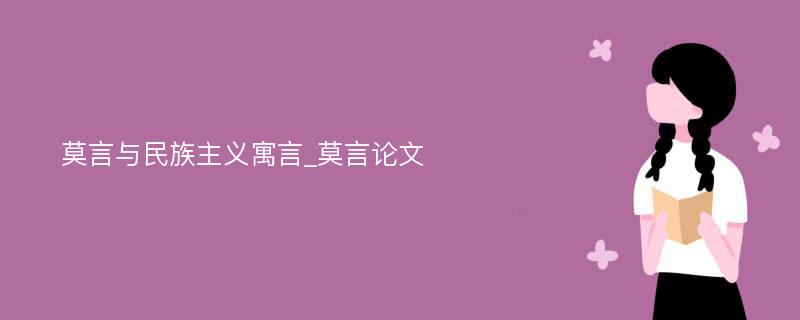
莫言与民族主义者的寓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言论文,民族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按 《莫言与民族主义者的寓言》(“Mo Yan and Nationalist Allegory”)译自内森·C·法里斯(Nathan C·Faries)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撰著的《当代中国的基督教叙事》(The Narrativ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ity,2005)。法里斯藉该书指出,当代美国读者倾向于搜寻、翻译、购买、阅读适合他们口味的中国文学作品,因此,“真实的中国”(real China)不免被忽略。他引用W·J·F·詹纳(W·J·F·Jenner)的论见说,学者、译者们往往别无选择,只能挑选那些不一定能代表中国文学概况的作品,但是“如果不能萌发、滋长对现代中国写作的兴趣,英语读者就鲜有可能直面他们完全不习惯的另一种文学传统。”①在该书第五章《基督教与当代中国小说》(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中,法里斯就认为,在美国人的想象中,“上帝之死”对中国和西方的意义及影响是一样的。 法里斯说,这种接受上的国际间差异,既存在于大众中,也发生于学界。史学家们已开始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回潮,这一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费正清及其门生,但西方的文学学术界严重忽略了现代中国文学(1911年-1949年)中的基督教运动,也完全忽略了它在当代“新时期文学”(1979年至今)中的回潮。英语读者尚未“习惯”中国文学的一个方面即是,中国作家在20世纪末不时会以相当“不西方”和“不后现代”的方式书写上帝。 在法里斯看来,礼平、张笑天、冯骥才、莫言、王安忆、史铁生、北村这七个作家构筑了中国学者所称的“中国现代小说自诞生以来最复杂的二十年”②,表明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就像现代早期的一些人,注目着国族忠诚与宗教信仰相互通约的可能性。他发现,就像詹纳在分析文学翻译市场时指出,那些以当代为背景,严肃讨论“西方”宗教的中国小说在西方卖得并不好,除了内容,其中某些作品的风格也不是英语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法里斯认为,礼平、北村、王安忆、张笑天、史铁生这五位作品较少被翻译的作家可能承受了美国文学界的偏见,因为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普遍缺乏对中国基督教的了解和兴趣。 反之,法里斯说,冯骥才和莫言从未在他们的小说中严肃地考虑信仰问题,而只是着眼于艺术。他看到,无巧不巧,在当代作家中恰是冯骥才和莫言——他们都刻画了19世纪帝国主义传教中的罪恶,都未清晰言说中国今日的基督教——能亲见自己的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具有相当影响力,他们所写的历史小说可读性颇高,行文幽默而又有英雄气质,故事元素具有普适性。 论及莫言笔下的基督教,法里斯指出,其作品的电影改编争取到广泛的国际观众,增添了莫言的知名度。这个以小说《红高粱家族》为美国人所熟知的中国小说家,在其稍后的作品《丰乳肥臀》中,以一位无魅力可言、伪善的马洛亚牧师作为中心人物,像冯骥才笔下邪恶的天主教神父一样,他的形象肇自可耻的帝国主义百年侵华史,但更丰满也更复杂。法里斯认为,莫言刻画的这一人物,以及《红高粱》中古怪晦涩的基督意象,比冯骥才小说中的基督教更复杂;莫言的作品大概最堪称寓言,它无意于严肃评价19世纪传教士运动的侵略性。莫言看待宗教是出于美学目的——或许同时也来自一种爱国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基督教叙事》之《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基督教》一章所讨论的当代作家中,莫言在美国最广为人知。通过张艺谋的著名电影,以及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随之而作的翻译,莫言的第一部小说《红高粱家族》被引介到西方,他的短篇故事也入选了《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和葛浩文的中国大陆当代短篇小说译文集《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③。《红高粱》(1987年)④在中国发表的那个时代,现在被视作寻根文学的高潮期和收尾期,以及先锋文学的生发期,而当时的莫言已经先后在两所学校里学了几年。中国的先锋文学借助短篇故事的形式,强调语言的游戏,主张抛弃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学之“负担”⑤。寻根的过程往往持续较久,趋向于较长的文学篇幅,以表达国族历程和沉重的国家问题,这种主题对中国严肃作家来说一直都很有分量。尽管莫言在其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许多短篇小说中已涉及并认同先锋文学,但他那些以长篇历史小说形式写成的重要作品,以及他的大多数中篇小说,仍然承载着寻根者那迫切的国族困境。 赵毅衡将“寻根者”(赵译为“Roots-Seekers”)那“虚构的追寻”描述为“一种挫败感的无意识宣言,由中国文化显而易见的不举和不育造成”⑥。在《红高粱》中,这种挫败感却绝不是无意识的;莫言掸下他对当下中国的不满,回望故乡神话般的英雄们,以此作为他对中国复兴的期许。旧日“无拘无束的激情庆典”是他为之自豪的;“性与暴力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呈现为隐喻,以激活中华民族紧绷的神经。”⑦在《红高粱》的结尾,高产的科学杂交作物取代了昔日纯种的红高粱,隐喻着中国失落了旧时威风和血性激情: 我反复讴歌赞美的,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冲激得荡然无存,替代它们的是这种秸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的杂种高粱了。它们产量高,味道苦涩,造成了无数人便秘。那时候故乡人除了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外,所有的百姓都面如锈铁。 我痛恨杂种高粱。 杂种高粱好像永远都不会成熟。它永远半闭着那些灰绿色的眼睛。我站在二奶奶坟墓前,看着这些丑陋的杂种,七长八短的占据了红高粱的地盘,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辉煌的颜色。它们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它们用它们晦暗不清,模棱两可的狭长脸庞污染着高密东北乡纯净的空气。 在杂种高粱的包围中,我感到失望。 我站在杂种高粱的严密阵营中,思念着不复存在的瑰丽情景: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光洋的血海。如果秋水泛滥,高粱地红成了一片汪洋,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如果太阳出来,照耀浩淼大水,天地间便充斥这异常丰富,异常壮丽的色彩。 这就是我向往着的,永远会向往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 但是我被杂种高粱包围着,它们蛇一样的叶片缠绕着我的身体,它们遍体流通的暗绿色毒素毒害着我的思想,我在难以摆脱的羁绊中气喘吁吁,我为摆脱不了这种痛苦而沉浸到悲伤的绝底。⑧当被问到“在哪儿可以见到《红高粱》中那些勇气过人、没有羞耻感的男人和女人”,莫言的回应使人联想到萧乾给《皈依》的附言:“他们在今天的中国寻不着,但他们曾经存在过,并将再次活在这片土地上。”⑨ 赵毅衡等人批评过寻根文学的这种印记如同“浪漫的逃避主义”(romantic escapism)⑩和“自欺”(self-delusion),但通观莫言后续的作品,它们为他赢得了东方和西方的尊敬,并似乎注定要幸存于寻根文学的尾声,在可见的将来维持其受众。他最近被译为英文的小说是《丰乳肥臀》(写于1995年,译于2004年)(11),在其母国赢得了评论界的赞赏和“《大家》文学奖”。就是这两部小说,《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是我们将要在此稍为注目的。在莫言这些有关中国历史的宏大神话叙事中,他利用了一个单纯的基督教意象,以及一个“基督徒”角色,来分别道出他心目中基督教植根于中国时的处境。冯骥才在讲述历史时多有逗趣,而《丰乳肥臀》涉及基督教时则似乎是全盘批判的,至于莫言以往的寓言式小说,这一话题又要复杂得多。 《红高粱》中的基督教意象,即使在表面上,也不容易理解。这个意象是十字架,是殉难,明显指涉基督的十字架。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十字架一般都被用作和视为一种自我牺牲的意象。为了某种原因牺牲自己,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美德之一,陈独秀等激情澎湃的文人们相信,基督为中国人作出了榜样,为了中华民族,要仿效他的精神。在《红高粱》中,那个十字架的意味独立其间,不过,它发生在一个虚构的、20世纪30年代的村镇上,看似与基督教毫无关系,人物死亡时的情景也不太像是有目的的牺牲和殉难。纯然、直接地提及基督教上帝,与那一堆有关传统儒家道德、祖先崇拜、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情节是格格不入的。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大多能自如地游走于时间、章节的闪回和快进中,与此不同的是,那个引出基督教元素的人物独独出现在第五章,这一“家族史诗”(Family Saga)——该书中文原版的副标题——之最后一章。他出现在此章的第二页,唤作“老耿”,死在此章邻近结尾处,唤作“耿十八刀”(12)。他的故事,在小说中不同寻常,以直截了当的时间顺序来讲述,他死后也不再被提起。 就是这一死亡场景令读者瞠目而立。这个老头找不着可以帮他要到配给口粮的人,他突然疯狂地把自己扒光,裸身倒下,在雪地上翻滚,抓住结冰的铁栅门上的棍子。第二天早晨,他就是在这儿被人发现: 胸前钢笔很多的小伙子清晨起来扫雪,偶尔抬头一瞥铁栅门时,不由得大惊失色。他看到,昨天晚上那个自称耿十八刀的那个老头赤身裸体地把在大门上,好像受难的耶稣。老头的面色青紫,肢体舒展,瞪着大眼盯着公社大院,乍一看,谁也不敢相信他是个冻饿而死的孤独老人。 青年人特意数了数老人身上的伤疤,果然是十八块,一块不多,一块不少。(13)他死时的姿势被描述为“好像受难的耶稣”,看似微不足道、漫不经心,仅是一种节外生枝的书写。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指涉基督教时通常不会如此漫不经心,但莫言显然执著于描绘一个张扬而血性的中国乌托邦,在这种语境中突然出现一个“外国的、西方的”宗教,就显得很刺眼。 我们忍不住要试着将这一描述巧妙地嵌入小说其余部分里关乎中国历史、基督教之历史地位的那些段落。整部小说分为五章,它们的主题和总体情节是沦落,是中国昔日荣光的丧失,她步入了荒芜的当下,其中只有往昔光彩、声响所投下的光秃秃的阴影。 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14)莫言的叙述者在小说一开头就陈述了这段话,在小说的最后几页,通过比较杂种高粱与昔日纯种红高粱,又清晰地回到对这一主题的复述:“这就是我向往着的,永远会向往着的人的极境与美的极境。”尽管大多数情节都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那段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莫言在描写这些故事所呈示的缓慢颓败、渐趋衰落时,并未按着它们的时间顺序来。换言之,尽管这些故事都有关辉煌的往昔,莫言通过堆叠过去最糟糕的部分以迈向小说的末尾,来预见衰朽的当下。当我们读到第五章,即独有老耿和孤零零基督教元素的那一章,衰落几近完成。 中国从天堂跌落的主题宣示于第五章的标题,也呈现在其内容中。从第一章开始,“红高粱”象征“我永远会向往着的”,下到第五章,“奇死”。更关键的是,这种降落并不仅反映在“死”这个词上,也表现在“奇死”所暗指的插曲中。此处直接指向的不是老耿之死,而是二奶奶之死,她一生的经历直接指涉第一章中的辉煌往昔如何沦落到第五章里的衰朽现状。我们在第五章最后一节看到这种指涉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叙述者直接将她的死联系到现在及将来: 她以她诡奇超拔的死亡过程,唤起了我们高密东北乡人心灵深处某种昏睡着的神秘感情。这种神秘感情只有处在故乡老人追忆过去的,像甜蜜粘稠的暗红色甜菜糖浆一样的思想的缓慢河流里才能萌发、生长、壮大,成为一种把握为知识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5)第二,当这种精神的变化在这一历程中显出积极意义,甚至还可能对村镇存活于“未来世界”是必要的,我们很快发现这只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此处的“奇死”和“暗红色甜菜糖浆”意味着村里的人们就像是杂种的高粱,他们说不出旧日的强健话语,而只能吐出非我的话语,恰似二奶奶被占有时: 我的嘴巴里的确在发出不是属于我的声音,就像二奶奶临死前发出的声音也不属于她一样。第三,她的死关联着这种失落和变迁,叙述者在书的结尾来到她的坟前,显然是希望以此为桥梁跨越回过去。然而,在幻象中,二奶奶从坟墓中起来,以她自己的声音诉说着过去与现在之间不可沟通的隔阂:“并非我生的子孙,照照你的尊容吧!”(16)这个第五章,书写了“恋儿”——二奶奶的名字,也是莫言用以形容昔日辉煌中国的一个词(17)——最终成为葬送二奶奶之“奇死”的一章。 莫言对物种衰退的不满也表现在小说中狗的形象上,这在关键的最后一章里达致极点。从起初轻易战胜村附近一群野狗,以及用“日本狗!”来描绘兽性,到中间的第三章“狗道”,可见狗被人格化成有力而聪明的勇士,靠自己的力量击败敌对的人类。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人类最终彻底沦落,胶高大队队员披上狗皮,学狗叫,让日军措手不及(18)。变形成动物可以被理解成是对人类有好处,但它总体上无济于事,小说中贯穿着暴力和死亡,而在这最后一章里,日本人作为胜利者出现,天堂的失落成为终局。在这一章里,日本人摧毁了盐水河沟的村子,分别强奸和杀害了二奶奶与小姨。就是在这一章里,人变成了狗,泯灭了所有的人性。 莫言这样写意味着什么,堕入地狱的最低一层,联系着老耿的死,并将此比诸基督?这情景可被阐发出多重意味。我们可以把这一指涉划到第五章,因为在中国以往传奇体系中的天堂没有基督教的一席之地。基督教,一个“外国的”宗教,最后恰当地被安放于此,在腐坏的“现在”,此时中国被日本占领,被杂种高粱和大城市占领。基督教元素进一步脱离了往昔的中国,进一步附着于叙述者所处的现时代,以它的特性,以它与这部小说所涉其他宗教截然不同之处:它不是中国的。叙述者所提到的所有其他宗教,从相对主流的佛教和道教,到民间宗教及迷信,对情节和角色的生活而言,是个浑然一体的部分。是角色们自己提到了他们的信仰,或者有些角色本身就是这些宗教的执行者。而基督教元素对这小说来说是异国的,是与众不同的。基督教是故事中唯一只存在于叙述者意识和声音中的宗教。其他宗教贯穿在故事中,并构成了故事,一如以往;而基督教则搁在故事的表面上,它来自某个其他的时代或地方,来自现在,来自叙述者所书写的城市。 我害怕自己的嘴巴也重复着别人从别人的书本上抄过来的语言,我害怕自己成为一本畅销的“读者文摘”。(19)这是叙述者在最后独白中的呼喊,基督教也许是不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之一,是二奶奶所言非己的声音之一,不属于这个地方和时代。 十字架这个意象,确实在小说中指涉那个令人怜悯的中国老头之死,它驳斥着一种反基督教的过度读解,看上去更认可那种中立而单纯的诠释。基督之死的意象不就象征着往莫言所挚爱的中国传奇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根钉子?通过这种读解,基督之死被引申为中国之死的异曲同工,并且,就像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的通常做法,排开教义和历史的深厚本义,解开它们与帝国主义的纽带。基督的殉难被用来强调普通中国人在苦难中国这一十字架上的牺牲,也许还能为这一章的“奇死”主题在象征意义上加重。这是中国作家使用基督教意象时最惯常的用法之一。正如王本朝所述,这些作家“并没有建立起‘基督教’对于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而只是将宗教用作“这些作品的比附力量和借鉴对象。”(20) 如果《红高粱》中的基督教意象是微小而含混的,那么《丰乳肥臀》中的基督教角色虽然不那么复杂,却是显明的。马洛亚牧师是个下流、放纵的“基督教”传教士,他有很多私生子,在中国以各种方式挥霍人生。他是一个蹩脚的主人公,大家族的一家之长,这个家族的历史从19世纪贯穿到整个20世纪。马洛亚牧师一点都不像冯骥才笔下那个邪恶昭然的天主教神父,他更接近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大家长,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中国当代作家大多受到这部小说的影响,而莫言对中国历史的神话化经常引起此间的比较。与马尔克斯的大家长相比,莫言笔下的许多角色有一种伟大性——《红高粱》中的爷爷与此处的马洛亚牧师——他们毫不遵循传统的道德标准,遑论基督教义。反之,就像激情、性爱及暴力部分地构成了莫言所书写的中国的正面价值体系,他笔下人物的地位与他们所属文化传统中的美德观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的关系。马洛亚牧师虽然没有什么值得钦羡之处——一个20世纪初期的西方传教士,行事却像莫言笔下那些激昂的中国人,又显然没有这些中国英雄所蕴藉的文化意味——尽管他不像《红高粱》中的中国英雄那样让我们听见赞赏声,但这一角色至少此处没被批驳。正如马尔克斯通过一个升格为神话的家族故事,让我们有兴趣去重读他国家的历史,莫言也以上官家庭一个近似寓言的神话引发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再阐释。就像标题所示,《丰乳肥臀》首先应指涉强健的中国妇女,此处的代表是母亲的形象(21),马洛亚之父亚伯拉罕的女家长。对马洛亚的寓言式解读,深刻地关系到莫言视野里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颇能支持《红高粱》中那个对基督故事的反基督教式读解。 一如马尔克斯,莫言常使用宽大的肉体和巨人形象,虚幻的半人半神或恶棍,以此对应他故乡的广袤。在《红高粱》里,莫言哀叹当代中国文化黯然丧失了生命力,为此他唤醒了1949年之前那些嗜血好色的英雄,以及迷人而独立的女英雄。安在(Ubi sunt)?他问,这些昔日的英雄人物如今何在?为什么现在我们如此衰朽?我们能够重现中国曾经的生命力吗?如果我们镜鉴同样的寓言式读解来看这后一部小说,马洛亚牧师和他的九个孩子——九在中国的数字命理系统中是一个帝皇之数,一个完美完善的数字——成为当代中国的父亲;莫言指出,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和西方杂交所生。马洛亚代表了严肃却伪善的群氓,即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和帝国主义。因此,个体角色在信仰上的抱憾,既不是在批评当代基督教,也不是在批评特定的基督教义,而是在指责传教士19世纪在中国犯下的某些错误。焦点更像是固定在中国上,集中描述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这又让我们想起他在《红高粱》中不喜欢杂种,大概他就像冯骥才那样,一直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西方之“用”中寻找纯正的中国之“体”。 注释: ①W·J·F·Jenner,"Insuperable Barriers? Some Thoughts o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Writing in English Translation," World Apart: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ed.Howard Goldblatt(Armonk,NY:Sharpe,1990) 184. ②“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中国小说50强编委会《长征·序》,见北村《长征》,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③莫言:《秋水》(Autumn Water),trans.Richard F.Hampsten and Maorong Cheng,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ed.Joseph S.M.Lau and Howard Goldblatt(New York:Columbia UP,1995) 429-43.莫言:《灵药》(The Cure),trans.Howard Goldblatt,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ed.Howard Goldblatt(New York:Grove,1995) 172-81. ④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 ⑤Jing Wang,Introduction,China's Avant-Garde Fiction,ed.Jing Wang(Durham,NC:Duke UP,1998) 2. ⑥赵毅衡,Introduction,The Lost Boat:Avant-Garde Fiction from China,ed.赵毅衡(London:Wellsweep,1993) 12. ⑦Joseph S.M.Lau and Howard Goldblatt,introduction,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ed.Joseph S.M.Lau and Howard Goldblatt(New York:Columbia UP,1995) xx. ⑧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72-373页。 ⑨⑩赵毅衡,Introduction,The Lost Boat:Avrant-Garde Fiction from China,ed.赵毅衡(London:Wellsweep,1993) 13. (11)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12)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18、352页。 (13)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58页。 (14)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页。 (15)(16)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71页。 (17)英译者将二奶奶的名字“恋儿”译“passion”,有“激情、受难”之意。——译者注 (18)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64-365页。 (19)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71页。 (20)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21)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标签:莫言论文; 红高粱家族论文; 基督教论文; 红高粱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小说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冯骥才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