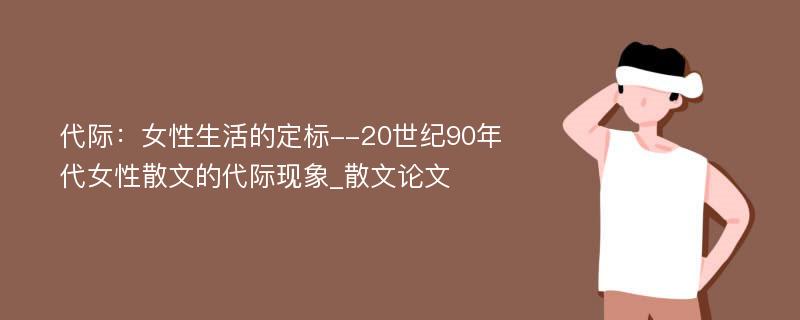
代:女人生命的刻度——90年代女性散文中的代际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刻度论文,散文论文,现象论文,年代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喜欢用“年轮”来比喻“代”。时间这个无形的匆匆过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树的横断面上留下一圈一圈的年轮,若干圈年轮共时态地呈现在同一个平面上,与树的纵剖面即各个年轮的历时性纵横交错成一棵树的主干。年轮是时间在树干上留下的痕迹,代便是岁月在女人生命的流程下雕刻出来的直观的刻度。女人对无形的难于把捉的来无影去无踪的时间,它习惯于通过代、通过个人家庭角色的转换、递进来认知,所谓“儿孙催人老”等等。女人记忆中难忘的“生命故事”常常是和“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代”是女人的生命之镜和岁月之。她们从这里看到了什么呢?
一、岁月如圆
《岁月如圆》(周小娅)从一幅标题为“你和你的影子”的祖孙两代女人的照片上看到了女人生命的刻度——小女儿青春烂漫的面容和老女人的白发、皱纹,也看到了站在祖孙两代人之间的作为母亲的“我”的责任,意识到“现在该由我来向女儿张开暖烘烘的翅膀”了。蒋子丹的《岁月之约》和丹娅的《心念到永远》可以看作是“岁月如圆”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它们都选取了一个特定的瞬间来表现三代女人代际角色的转换、交接。《岁月之约》是在“我”作为女儿护送年迈力衰的母亲回家,《心念到永远》是在作为女儿的“我”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分娩之痛终于也做了母亲之际。作家所捕捉到的这样的瞬间,是伽达默尔所说的“独特的时间”,是超越了日常生活在连续进行中的琐碎重复而成为一种被体验和被审美化了的时间,是足以让女人永远记住的造型化和“仿佛停住了”的“真正实现了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时间中,两代女人实现了责任和爱的相互承续和交接,实现了“岁月之约”。
如果说“岁月如圆”是女人“代”的承续交替中对圆满的一种期望,那么“岁月之约”便是这种期望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岁月的“圆圆的脚步”是用女人的爱和责任、用一代又一代女人辛苦操劳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这是女人对时间的空幻感生命的虚无感的一种抗拒和超越,也是女人对代际关系中的责任和缘份的自觉。冷色调的纯生物学的“代”的交替在这里经由女作家们切实的母爱体验被暖化了。周小娅的许多散文都给人以这种“圆”和“暖”的感觉,有的只看题目就觉得温暖:《我是妈妈的小棉袄》、《山那边是外婆家》、《鸟窝和鸟妈妈的孩子》、《人在世上走》等等,都是在为这流逝的岁月画圆,也是为孔子“逝者如斯夫”这几个字写下一个饱满温馨的注脚。
生命的意义,自我的价值是什么?女人一千次一万次这样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是抽象的或仅就自己一个人孤立的来看,的确不好回答,何况在生的尽头,无例外地有死的阴影在那里等着你。现在女人抓住了代际关系中一个特定的时间结构,而且让站在祖孙两代人之间的母亲和母爱作为这个结构的核心、中介、纽带和动力源泉。向前,她看到母亲或外婆的衰老、死亡,向后,她看到女儿、儿子的出生、长大。这就好比是走进了一个照相馆,你同时照了三张照片,一张是你的未来,一张是你的过去,一张是你的现在。母亲就这样在女人的生命流程中成为这样的“照片”,成为女人在时间之流中一个生命意义的定格。90年代女性散文中,有那样多的女作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这张“照片”,是因为人人都有母亲,人人都有太大的可能成为母亲。
在这个世界上,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心灵里,有太多的地方刻着母爱的踪迹,你不能抹掉她不能漠视她不能忘记她就像你不能抹掉你自己漠视你自己忘记你自己一样。台湾女作家林文月的《白发与脐带》对母爱做出了高度集中的艺术概括:母亲去世后,子女们清理她的遗物,发现了写着五个子女名字的五个纸盒,里面分别装着他们各自的一截脐带,还发现了一包用白纸包着的母亲的一团白发。这一意外的发现,令子女们惊讶和感动。他们将那一团白发也分成五份分装在各自的纸盒里和自己的脐带放在一起带去珍藏。“这样,母亲就可跟着她所疼爱的五个子女分散在各地而无所不在了”。“无需任何语言,这就是母爱的最原始的诠释”。“多么奇妙啊,这一段萎缩成寸许长的细带,竟是生命的隧道,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甚至另一端已经泯灭了,却仍然完整地叙说着薪火传递的故事”。这是母爱的信物,母亲就是为了这五个生命的出生、成长,把满头乌黑光泽的华发累白了。母亲已逝,可她的肉体生命曾经这样存在过的“信物”从此在她的子女们心头永驻,在母爱不灭的烛光照耀下,他们将继续未完的生命之旅,学着像母亲那样爱自己的子女和天下人的子女,这不就是整个人类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整体象征吗?
《母亲的羽衣》(台湾张晓风)捕捉到的是一个独特的瞬间。作者抓住哄小女儿睡觉时女儿向她提出的一个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是:“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呢?“我”在心里这样回答女儿。在这个答句中,天下所有的母亲和自己的母亲(女儿的外婆)的少女时代、自己的少女时代、女儿现在的少女时代聚扰在一起,展现出天下所有的女人曾经有过如花似锦的年华,都曾经“惊讶于自己美丽的羽衣和美丽的肌肤”。“而有一天,她的羽衣不见了,她换上了人间的粗布衣——她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在这里,具象的个体的母亲(“我”的母亲和我自己)和抽象的整体的母亲(天下所有的母亲)、过去的母亲和现在的母亲未来的母亲汇合聚集,从母亲的“羽衣”和母亲的“粗布衣”这两个意象的转换中得到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审美表达。“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这个稚气可掬的提问,得到了一个确定的哲理的和现实的回答:妈妈曾经是一个仙女,外婆也曾经是一个仙女,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曾经是一个仙女,可她们现在都不是。现在只有女儿是,然而女儿将来也不是。因为女儿也会做母亲。
作为“羽衣”与“粗布衣”这两个意象的补充,也是这其间的一个过渡,作者又找到了另一意象,“一个被弃置的木质砧板”:
我一直想把它挂起来当一幅画,那真该是一幅庄严的画,那样承有过万万千千的刀痕和鉴印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把它挂出来……
天下的母亲不都是那样平凡不起眼的一块砧板吗?不都是那样柔顺地接纳了无数尖锐的割伤却默无一语的砧板吗?(注:张晓风:《母亲的羽衣》,引自《中国文化名人忆母亲》,第397页,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版。)
“白发”、“脐带”、“羽衣”、“砧板”还有梅洁的“那一脉蓝色的山梁”(《那一脉蓝色的山梁》)等等都是象征,母亲一生的辛劳、一生的心血,在这里获得了符号化、审美化的确证。而象征是什么呢?按照伽达默尔的阐释,那是“如半片信物一样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所显示出的“与它的对应物相愈合而补全为整体的希望”,是“对一种可能恢复的永恒的秩序的呼唤”。象征的本体论特征是“共同性”或“共通感”,是“一句向作出反应的心弦说出的话”,“一种向情感和思想发出的呼唤”,“一块共振板”。它就是意义本身,“它的意义就永驻象征里”,(注:《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第292-293页。)永驻在世世代代的女人心底。在这里,女作家们在“代”的范畴里,在母女之间的相互认同中写出了母爱的跨时空的普泛性意义。
岁月如圆
二、身体经验的延伸
“身体经验”这个词在这里只是为了强调“身体”之于“经验”的本体论意义,强调作为女性文学的基础的女性经验无不来自女性之躯。身体是一切经验的发源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甚至认为身体就是女性写作的起点和归宿。然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过去了,“身体”这个字眼却仍然处在暧昧不明和讳莫如深的尴尬境地。视女人的身体为不洁为邪恶的观念至今仍然变换着花样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女人自身身心的解放。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难道不就是要打破封建愚昧而争取人身自由,争取自己支配自己的身体的权利吗?女性的自我发现自我认识,难道能够脱离开对自己的身体的发现和认识吗?“躯体是个人的物质组成,躯体的存在保证了自我拥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实体。任何人都存活于独一无二的躯体之中,不可替代。如果说,‘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了一系列语言秩序内部的复杂定位,那么,躯体将成为‘自我’涵义中最为明确的部分”。(注:南帆:《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文艺争鸣》1996年第9期。)应该承认,中国女性文学在80 年代后期之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这个“自我涵义中最为明确的部分”,一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在冲出“身体禁忌”的勇敢的女性文学激昂之旅上,真正的起点是90年代的女性小说和女性散文。小说方面的先行者是林白、陈染、徐小斌等人的一些中、长篇小说,散文方面的先行者是叶梦。而且就开始探索的时间而言,女性散文先于女性小说,这大概和散文与小说各自的文体特征不无关系。
叶梦是从写于1982年的《羞女山》开始她的女性身体经验言说的。没有《羞女山》,叶梦后来的散文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她发现了陡峭如削、状如裸女的羞女山,也就是发现了只属于女人的那种蓬勃恣肆的生命创造力和无与伦比的肉体的美。她否定了强加在羞女山身上的“羞”字和“弱”字,也就预示着她将战胜自己超越自己,成为精神上心智上成熟的健全的真正的女人。以《羞女山》为起点,叶梦远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完成了她对女性身体经验的写作,那是女人生命史上人人都会经历而人人都羞于言说的对个人来说真正重大的事件,如出生(《紫色暖巢——关于我出生时的浪漫回想》)、初潮(《我不能没有月亮》、《潮》)初吻(《月之吻》)、初夜(《今夜,我是你的新娘》)、受孕(《生命的辉煌时刻》)、人工流产(《失血的灵肉苍白如纸》)以及妊娠、分娩、哺乳、育儿(创造系列之一之二之三),再加上她写自己的童年和写外婆的衰老和死亡的《静静的栗树山》、《护生草》等,叶梦写出了女人身体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并由此回答了我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追问。叶梦以后的一些女性散文作者,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达成了不约而同的共识,都把自己生命的来源追溯到母亲的身体,认为那是一种最伟大和神奇的创造:“我一己生命最切近的源头,来自我母亲。她不仅给我以生命,同时也赋予我一颗对一切美好之物分外敏感的心灵”,“饱经沧桑,历尽艰辛,我满头银发的老母亲身影,叠印在苍凉远景之上,在我生命之河的源头”(马丽华《犹如北方的土地》)。
《紫色的暖巢》是对母亲的子宫的诗性赞颂。正如此文的副标题所示,这是通过对“我”出生时的“浪漫回想”来实现的。而“回想”之所以可能,则是建立在“我”自己也有了生育经验,建立在“我”与母亲经验的融合。所以,最好是先看她的《创造九章》再回过头来看《紫色暖巢》,就会深深理解并完全认同叶梦把女人受孕、妊娠、分娩、哺乳这一系列生理过程上升到生命创造的高度来赞颂。
这里充满了女人新鲜活泼的身体感觉和母性情怀:
从这以后,我便换上一副温柔的慈母情怀,全心全意地守望着一粒生命的胚苞,眼巴巴地望着从我身体的黑土地上炸出一根青葱的绿芽来。
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春天里疯长的植物,又像一团隔夜放了酵母粉的面团。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无声地膨胀开来。
我的脚切切实实地踩到了温暖而且坚实的大地上。我的手真实地扪及了腹部微微凸起的那拳头大的一个实体。这不是一块石头,一个赘物,这是我创造的一个生命。我用我的手长久地贴着腹部,我希望我手心的磁场和手温传达我最初的母爱。(注:《创造九章》,《叶梦新潮散文选》,第147、149页,漓江出版社1993年5月版。)
以这样切实而鲜活的身体经验为基点,她想到了自己的出生,想到了母亲的子宫(《紫色暖巢》)和外婆那饱经沧桑的怀抱(《走出黑幕》):
我一游进那座倒梨状的宫殿,我便自然而然地吸附于温厚柔软的宫壁上,我初级的生命从此有了根,此乃真正的生命之根。
那个子宫,曾经属于我的宫殿是我真正的温柔之乡啊!
这无疑是我与母亲最早最成功的默契。我在母亲的呼与吸之间张弛进退,眼看我的长满黑发的头颅已经数次抵在门边,然而,冲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
从剪断脐带的那一瞬开始,我的人生圆环便从母亲腿间的那一处空间开始了。
人生圆环从痛苦伊始,时光的利刃开始一点一点地切割生命。我在一刀一刃的切割中无师自通地领略了生命的哲学。(注:《紫色暖巢》,《叶梦新潮散文选》,第10、11、13页。)
《走出黑幕》写于外婆去世8年之后。叶梦说8年里“老外婆的肉体和灵魂像巨大的无所不包的黑幕,整个儿地遮蔽了我,我无法摆脱她”,“外婆已潜入我的精神骨髓,我无法忘却”。这个黑幕是关于女人身体和衰老死亡的秘密的。她说“外婆的身体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我从外婆的身体上认识了女人,我对女人的身体有一种敬畏和暗暗的恐惧。”这样一个创造过13个生命的身体怎么会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萎缩了、衰老了、死去了呢?她走入生命边缘时“那茫然的眼神和永久的伫立给我一种深刻的刺激”。“她在想什么呢?”把《紫色暖巢》、《创造九章》、《走出黑幕》连接起来,恰恰是叶梦对女人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的审美化追溯和钩连。叶梦说她由此而“无师自通”地领略了“生命的哲学”。这句话要加以必要的补充或限定。应该说,这个“无师知通”的条件是自己的生育体验,而母亲和外婆实际上是女人由生育体验而领略生命哲学的不可缺少的启蒙者。因为仅凭“我”这一代有限的时间性的身体经验,不可能感同身受从生到死、从初生到长大成人再到衰老死亡的全过程。个人有限的身体经验必须得到延伸,必须在几代女人的经验的融合中才能实现由经验到超验的提升。叶梦承认尽管如此,她也并未完全走出“黑幕”,因为她还没有从外婆的死而洞悉死亡的秘密。死亡的秘密是不可体验不可洞悉的,或者说虽可体验可洞悉但当死亡一旦来临时已不可言说和无以言传了。叶梦散文中,有好几篇是写想要体验和洞悉死亡而不可得的。对此,她也只能探取“悬置死亡”的办法,暂且要求自己紧紧把握住这由生到死之间的一段此岸里程。她把这个过程叫做棋盘上白子和黑子的对弈。叫做“极地飞行”。那么除了下好这盘棋,“除了从生到死的极地间穿过,别无选择”。既是别无选择,那就让有限的生命飞起来,在飞行中感觉到“肉体在阳光中散发出芳香”,感觉到“生命有一种充盈的快乐”(《极地飞行》)。叶梦散文出在80年代末,作为当时女性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她的惊世骇俗,不仅在于她对女性身体经验这个禁区的挑战,还在于她以女性经验为基点所升华出来的这种积极的创造的生命哲学观。
而那个曾经让女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难道不就在这里,在这生命的“极地飞行”的过程之中吗?
对于这个问题,其他女作家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感悟。她们的人生经历和身体经验不尽相同,但最终都汇聚在“敬畏生命”、“珍惜生命”这一思想的亮点上。张欣的一本散文集,标题便是《敬畏生命》。冯秋子的《婴儿诞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里写了外婆的生与死、母亲的生和“我”的儿子的诞生,并从中体验着和确证着生命的价值:
中午,你出生了。你的父亲在雪地里等了一夜,又一个白天。
孩子,你的出生,排除了多少可能遇到的不测,是个偶然。 因为这一点,你的生命本身就有了价值。不管你将来怎么理解你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只是生命长河的一个过渡。但是,几乎所有人,为了这一过渡,在生命长河里的这一过渡,都尽心竭力。(注:冯秋子:《太阳升起来》第5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从人类生命长河的整体来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只是也只能是一个过渡,然而这其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唯一的过渡。因为女人知道这每一个“过渡”都是多么艰难,多么值得珍惜。对于母亲,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是唯一,都是此生此世永难复现的“这一个”。古哲人所谓“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就是把人的生命这个生生不已的“过渡”,化约为不可再化约的个体生命而为生命的价值定位的。正是因为不可能两次跨过同一条生命之河,才应该倍加珍惜这只有一次的“过渡”,尽心竭力好好地活着。这个道理,女人比男人容易懂。池莉说她正是在生了女儿之后,才知道“尽量宽厚待人”“对天下的父母都永存一份敬意”(《怎么爱你都不够》)。王小妮说这是因为她自己生育并带大了一个孩子。她的一本题名为《目击疼痛》的散文集,按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排列记述,全是她“亲眼看见的各类疼痛”。“疼痛”是她的身体感觉,是她以个人的身体经验去感同身受他人的不幸和苦难,是女人与他人与人类生命体验的相通与相知。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人间情怀,一种更广大的身体经验的延伸,也是《圣经》上“爱人如己”的爱的哲学的体现。
舒婷说,她在旧金山高速公路立交桥上看到了一个四米高的大广告牌,那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我刚刚看懂他旁边的英语,眼泪立刻汹涌。它写着:你见到过这个小男孩吗?下面是他父母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舒婷说:“作为一个母亲,我在地球那边找到了同一泉位。”“倘若有一天我的儿子遭到同样的不幸,我决心要强迫自己吃饭、睡觉,以便有足够的体力和清醒的头脑走遍天涯去找回他。”(注:《舒婷文集·梅在那山》第8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
三、母与女:理解和超越
在外婆——母亲——女儿这一母亲代际结构中,包括了一组祖孙关系和两对母女关系,其中每一个角色都是相对的和双重的:外婆相对于外孙女而言既是外婆又是母亲;母亲相对于女儿而言既是母亲又是女儿;女儿相对于母亲而言既是女儿又是外孙女。位于中间的母亲在这一结构中是核心和中介,关联着两对母女关系,一般来说母系代际关系主要的便是母女关系。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母女关系,本该是女性文学极为重要的人际关系和基本母题,而我的阅读印象却有些空泛模糊难以把握。女作家每言及此,其语态往往闪烁其词欲言又止。他们或者如冰心、苏雪林、冯沅君那样以圣洁化的母爱来代替具体的母女关系,或者如萧红、白薇那样保持沉默缄口不语。张洁在自己的小传中宣称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的祖籍,(注:据我所知,张洁是唯一一位宣称随母亲祖籍的女作家:“张洁,女,1937年生于北京。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祖籍辽宁抚顺章达区下哈达村。)可见母亲对她至关重要,可是在她的散文中,那些写给母亲的至情篇章包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扇关闭了的门》、《坐在石头上等姥姥的小松鼠》、《母亲的厨房》、《又挂新年历》、《不忍舍弃》、《这时候你才算长大》、《无字我心》、《幸亏还有它》、《哭我的老儿子》等等,全都写在母亲离去之后,是在母亲的离去所留给她的永难弥合的伤痛和愧疚几乎要把她压垮的情况下写出的。宗璞的《花朝节的纪念》、马瑞芳的《等》、吴宗蕙的《诀别母亲》以及笔者的《昨夜梦见母亲》等痛彻心肺的怀母散文,均写于永远失去母亲之后。叶稚珊的《慈母身上衣》是写她的婆婆、30年代著名女记者子岗的。婆婆自然也是母亲。文中写到了她和婆婆对这种母女关系的相互认同:作为女儿和儿媳的作者说:“在千里之外,有两个母亲在同时关注着我们。”作为婆婆和母亲的子岗说:“从现在起,我多了一个女儿,你母亲多了一个儿子。”然而,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到“慈母身上衣”,这中间隔着一道无情的岁月之墙,只有在慈母苦难一生的尽头,儿女们为她置办后事时,才完成了这种反哺式的改写。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普天下为人儿女者永久的遗憾。(注:据韦君宜《思痛录》中回忆,子岗即彭子岗,解放后新闻界四大才女之一(还有浦熙修、浦安修、弋扬)。子岗解放前就写了许多歌颂解放区的散文、通讯,如《漫步张家口》等。反右时只因说了句“咱们现在大家相互之间朋友来往少了,还应该有一点”,就被划成了右派。子岗的遭遇,叶稚珊文中亦有涉及。)
难道这一切只有当母亲不在了才成为可能?
母亲是我们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女人,是生我养我疼我为我操劳一生把心都操碎了的女人,可是说到与母亲的关系,我们却有口难言说不清道不明心中一片混沌莫名。母女关系也是一种具体的人和人的关系,母女关系中的真实是“人在其真实、在其在的深层里所遭遇到的那种真实”,“它显然是真实的,而不是那种人尽可以置之不理的非真实”,“它显然是被经验到的”和“始终是特殊的”。(注:H·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第44、43页,三联书店1994年6月出版。 )面对这样的真实,仅仅如维坦根斯特所说“保持沉默”是不能使我们的内心平静的。应该承认,对于类似母女关系这种人的存在的“深层里的真实”,这个充满了心理张力的空间,我们始终处在“保持沉默”与“打破沉默”的张力之间。母亲的永远离去成为打破沉默的一个最后的契机,使作为女儿的当事人觉得继续沉默成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张洁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后记中记下了她写这个长篇散文历时一年又九个月,写的时候常哽咽不已难以自持,其间还无缘无故丢失了并未发出删除指令的八万多字。她相信,这并不是“母亲不愿意我在这些文字里跋涉”,而是“上帝的意思,他要我在这些文字里再煎熬一次”。她知道除了写别无出路,她只能在神的暗示下承受一份心灵和肉体的煎熬“日夜兼程,更兼重病在身”,终于完稿。“随着这些文字的了结,我才走出恍惚”,“算是了我的一份心债”。《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在母女两代人生离死别的临界线上重写母女关系,母亲以她的死这一生命的最终完成呈现出母与女之间那种骨肉相连生死契阔的亲密关系,乃是女人与女人关系的极致,是人的关系中最有亲合力的关系,也是任何力量所不能割断的最为柔韧恒久的关系。
在“外婆——母亲——女儿”这一女人代际结构中,不言而喻还有一个相关联相对应的男性家庭角色结构存在,如外祖父/祖父——父亲——儿子等。前述母女关系的暖昧难言,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母女关系永远不只是母亲与女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男性家庭角色及其所携带的社会角色社会信息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母女关系,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母亲和女儿的命运。然而,在女性文学中,这种不言而喻的男性角色结构呈现为“父的缺席”,并且大体上从“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世纪末的女性文学。男性角色在女性小说里或者非死即病或者“退居二线”一闪而过,在小说的情节叙事中基本上失去了功能性作用。在陈染的《私人生活》等小说中,则干脆是两代挣脱了婚姻锁链的女人相依为命,她们形同姐妹时而相亲相爱时而又相互猜疑窥探,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女性城堡里上演着“仿男性斗争”。香港李金凤的《八月烟花》,为女性文学中这种“父的缺席”现象,找到了一个涵盖力极强的隐喻;三个女人坐在空荡荡的餐桌旁一言不发地用餐,餐桌对面是一面空空如也的墙,墙上有一处显出淡白轮廊的空白,那里原来是一张水墨画,被“另有一处外室”的父亲摘走了。这是另一种“空白之页”,为女人的上场、为她们自己写自己提供了空间、背景乃至必要的前提。
“父的缺席”在90年代散文中稍有不同。也许是散文的非虚构性所致,在我所读到的正面的直接的书写母女关系的文本中“父的缺席”就成了“半缺席”,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以一个具体的男性家庭角色出场,但是却形同不出场,或者只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在场”。《我和母亲之间》(尹慧)“我”的生父在她没有出生时就与母亲离异从来没有见过面,继父的社会身份不明,而且经常不在家,难得回来一次,后来又得了一场重病,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的“长不大的男婴”,不久就去世了。《月正中天》(小宛)中的父亲倒是个老干部,却精神萎缩、“窝囊了一辈子”,“蒙着遮羞布,徘徊在高墙深院里”,“像个笨笨的大玩偶”。他“至死也未敢把理想中的水份挤掉”,并且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整个身子泡在这个兑了大量水分的“理想”里老死而终,让人想起张爱玲小说中那个在酒精瓶里泡大的男婴。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是孱弱的,人格是不健全的,心理上是残缺的。在家庭之外的一个更大的权力结构中,他们都是“弱者”。如此的“父权之父”,已然在文体的功能上实现了一场“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悄然消解,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实际上是终日操劳的母亲。那些飘浮在空中俨然不可冒犯的父权意识形态,在女性文本中形同虚设。这种不易觉察的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父权的颓败”,为90年代女性散文改写母女关系准备了现实的生存论方面的铺垫。
《我和母亲之间》、《这个春天这个冬天》、《童年往事》(尹慧)和小宛的两篇同题散文《月正中天》,由于“父”的这种“半出场”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母女关系的空间,使我们得以在家庭这个舞台上看到它那若隐若现的社会布景。尹慧的文本触及到“我”自童年以来二十余年母女之间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恩怨、磨擦,包括为丢失三分钱和碰洒一碗鸡蛋汤这类事情而挨打,包括“我”的逃学、退学和离家出走伤了母亲的心,包括母亲的火爆脾气等等,琐碎而又尖利,稠密而又缓慢,一点一滴地在母女之间积累着灰尘和痛楚、嫌隙和膜阂。然而“我和母亲之间”却自始至终没有构成冲突双方的对阵,没有曹七巧、司绮纹式的那种两代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那种性变态式的占有、算计、报复。这里的大大小小的碎片式的日常生活现象,被一种可以称之为“理解”的精神现象所照亮,母女之间的一切纷争、差异、矛盾,被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理解之光消解了。
理解作为经验的提升,是母与女这两个“主体间性”生命感觉的关联和交融,它的发生是一个不易觉察的逐渐积累的过程。一般来说,理解与经验所关联的事件不是同时态的。它发生在一种独特的被心灵所反复体验过的时间。
尹慧对母亲的理解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呢?
孩子出生那天我终生难忘,我从头天晚上开始疼痛,到第二天下午阵痛,又从晚上9点没停声地喊到夜里1点。我没法控制自己,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撕裂。候产室里只有我和妈两个人,我抱着她不停地变换着姿势,不知是站,是坐,是卧好。妈陪着我一身接一身地出着汗,和我一样衣服全粘在了身上,腾不出手来擦把脸……我第一次没有任何退路。有一个瞬间我看着床边和窗户,是三楼,窗子开着,我就真的迈出了一条腿。我是那样的人,我从来不肯一开始就承受现状,我不大考虑后果,妈死死地抱着我,使着全身的力气、和我共同经历着那一刻。我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我终于进了手术室,除了我的喊声,窗外一片寂静……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正离开我,我使着全身的力气,我感觉我就要完了……然而最后一只脚丫出来了,带出一股温暖的水流,我空了,我从没如此舒服过。那感觉好像几秒钟就过去了,就在那么舒服的几秒钟里,我望了一眼四周,看见妈正趴在手术室的玻璃上瞅着我。(注:《这个春天这个冬天》第41-42页。)
理解是否从这时开始的呢?这是人与人的关系中最直接和最纯真的面对、凝视和承担,是对两个主体间生命与生命的关联的自觉,是“我和你”生命价值之光的相互证明和朗照。尹慧接着写道:就是在那一刻,在她经历了如此艰难的分娩之后回到病房,很快就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看见妈还坐在床边凳子上,一张苍白的脸。妈问我是不是饿了?我说是。妈起身去给我买早点”。紧跟着,她说:
我靠在床上,想着妈是如何在20年前一声没吭地生下了我,想着我也还要等20年才能让女儿明白我今天的心情。那是我处在两代人之间的第一天。(注:《这个春天这个冬天》第43页。)
很可能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就是从具备了“代”的自觉意识开始,我和母亲之间种种过去习焉不察的无所驻心的事件、细节在记忆中复活重现,被一一回味、反省、观照、体察,理解这种在现代阐释学里被认为是“整个人类世界经验的一部分”和“人的存在的实质”的精神活动便发生了。理解构成了《这个春天这个冬天》全部散文的叙述经纬,它的基本言说方式是回想和感悟:“童年过去了,可往事留下了痕迹。像葡萄酒穿过水一样,起初是混沌的,随后逐渐清晰。”“那些碎末溶在你的血液里,软化你一生的骨骼。那当中,有你所有的偶然和必然,你想接受的,你不想接受的,你想要的,你不想要的……全在那儿”(注:《这个春天这个冬天》第120页。)正是在这样的感悟中, 她知道了母亲对于她意味着什么:
我现在太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始终如一地支撑着我的——肩上、身上的重负,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曾经磕磕碰碰了不少年而依然不改初衷的妈。我知道有一天,我的面前没有了她,我也会照样往下活,就像她没有任何人也会继续生活下去一样。但那一次,我肯定会哭……我会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自己松开,痛痛快快,不管不顾地让自己毫无保留地嚎一场——因为让我受不住的不会是她的死,死很平常;而是她身后,那一片让我看得更加清晰却从此再也摸不着了的一切。(注:《这个春天这个冬天》第59-60页。)
这就是“意义”从理解中生成的过程吧?意义不是摆在河滩上那些现成的先验石子,等着你只要弯弯腰把它拣到筐子里便是。意义是人这样一种有理解能力的存在在理解中赋予对象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妈对于“我”,从磕磕碰碰到无可替代的“唯一”,经过了反复的回味、反省这一精神活动过程,终于达到了相互的谅解、承担、责任和爱。
长大成人的女儿对母亲婚姻生活的理解在女性文学中始终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影子,我们只能从女作家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一点恍惚的行踪。凌叔华那个作为“四太太”的母亲终日愁眉不展,张爱玲那个像飘萍一般来去匆匆“总是不快乐”的母亲,都是作家深藏于心的隐痛,她们的笔一写到此,文字便都变得滞重和吝啬,刚刚开了个头便突然打住。台湾琦君60—70年代的一些散文名篇如《母亲新婚时》、《一朵小梅花》、《髻》等以女儿的视角写母亲那种郁郁寡欢的婚姻生活,笔致含蓄委婉,一夫多妻男权中心时代里女人那种只有婚姻没有爱情甚至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的生存现实,只能以蜻蜓点水式的曲笔出之。在众多的90年代女性散文中,触及到这个问题的作品依然屈指可数。小宛说,她在写《月正中天》的时候颇费踌躇,“确实拈量了许久”,但终于还是写了。她写到了父母那种半包办的结合又离异又无奈地复婚的阴差阳错的婚姻,写到了他们那种因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而带来的枯燥无味苦多乐少的夫妻生活,写到了母亲的性压仰:
说到男人时,母亲脸一灰,从鼻孔里哼出满腔的轻蔑。然而,我总能从字句背后,嗅出那曾经血涌过的干瘪了的芳香。
我妈妈每天跟我睡,我爸跟我的两个弟弟睡。当我终于明白,这样一种洁白无瑕的生活,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我的心是很疼的。
我不敢想象母亲是怎么熬的。母亲和父亲都对我说过,他们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我信。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的美德,上一代人为了下一代人,不顾自己塌陷和萎缩了的人生。(注:《女人谈女人·月正中天》第167页。)
这就说到了理解和超越。理解不等于认同,至少不等于全部认同,也许在真正的理解中就包涵着超越,也许,这是理解这一人类精神现象的创造性格所决定的。消极无奈地认同、重复不是真正理解,“一旦理解了,理解就会出现不同”(伽达默尔)。上一代人为了下一代人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下一代人是上一代人命运的重复,这种代的循环何异于生物性的传宗接代?早在40年代,张爱玲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把她的一篇小说命名为《连环套》,这个命名本身就说明她对这种一环套一环代代陈陈相因的“代”的宿命有所恐惧又想要有所超越。可是这篇小说她没能写完。在尹慧和小宛的文本里,一种对代的轮回和命运的重复的恐惧弥漫其间。她们对母亲既理解又希望有新超越。尹慧说:
我看到母亲饱经风霜所剩的疲乏和焦燥如何又在我身上蠢蠢欲动,就像我看见一场狂飙强掠小草的风暴过后苍凉还在继续。有些东西可以被物质文明所掩埋,而有些不能。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我的孩子,我们在精神和肉体上曾经被消磨的种种痕迹又要在他们身上重现。(注:《这个春天这个冬天》第150页。)
她说:这是她的“一点入骨的忧伤”。
怎么办?轮回或者超越,究竟哪一种是命运的必然。或者说,女人超越命运的重复、轮回,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可能性在哪里?
四、走出宿命的阴影
台湾台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为了赶紧“抢救”阿妈(台湾将外祖母、祖母称为“阿妈”)那一代人的生活故事,以征文比赛的形式广泛征稿,选出得奖作品中的16篇及约稿的8篇集结成书, 题名为《阿妈的故事》。阿妈这一代女人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三种政权的交替,到本世纪80年代已进入耄耄之年,有的老者就在她的晚辈执笔为文期间等不到稿件杀青便撒手而去了。这是历尽艰辛在贫困中胼足胝手辛劳一生的一代人,是悲情的一代,也是精神上体力上超负荷运转的一代。书前的编序中说,“许多台湾女性长者没有接受过教育,终其一生未曾踏出过家门,让封建礼教笼罩她们的一生。家当然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对于来自男性和年长婆婆的权威,只有逆来顺受”。“什么是自我,对于阿妈们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名词,阿妈们的一生都是为别人而活,而且至死方休。她们不知道她们的不知道”,(注:《阿妈的故事》第7 页,江文瑜编,台湾玉山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9月版。 )她们的自我意识还在沉睡。在入选征文中,有一篇题为《记忆与想象的碎片》,作者为英子。这是全书唯一一篇以祖孙三代两对母女关系为视域的文章。由于作者开始执笔时阿妈已经去世,她失去了直接进入阿妈内心世界的机会,只能以外孙女和女儿的双重身份和视点,撷取一些记忆和想象的碎片,按外婆、女儿(即作者的母亲)外孙女(即作者)进行无序排列连缀成篇。记忆、想像、观察、思索、言说的主体都是作为女儿和外孙女的作者。这里的男性角色也是一种形同缺席的半出场。为了维持一个家,为了全家人的基本生存,两代女人付出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全部心血。也打磨出两代强悍的女人,合力支撑着一个在基本生存线上勉力挣扎的家。在作为外孙女和女儿的作者眼里,外婆和母亲这一对母女关系,是“两个强悍的母亲彼此怨怼着”,互相抱怨互不相让。外婆这个“女性家长直到意识模糊消失之前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失去任何权威,她不识趣地插身于儿女的家庭事务之中,企图在任何可以藏身的角落发挥她的影响力”,是“一个唠叨而强悍的女人”,“一个不受欢迎的老人”。而母亲呢,“她抱怨着她的母亲。由于她无法平静地面对欲望被极度压缩隐忍的过往,在浑然不察的情况下,她近乎完整地继承了(她)母亲面对生活的行为方式”。作者认为,这样的一对母女关系,是一种“镜像一般的母亲的重复”,是“结构上相仿,内容上微微变异的紧张性”。她眼看母亲将成为今日的外婆,同时又痛切地预感到自己即将成为今日的母亲——明日的外婆,心中倍感凄凉:
那么,人的一生,也就只是落得如此下场?
我感到母亲与阿妈间的冲突正以一种同样为我所无法避免的形式并且更细致地流窜在我和母亲之间,历史决定论似地。我显得悲哀,非常低调地……(注:《阿妈的故事》第277页,279页。)
我完全理解作者的悲哀和低调,但并不完全认同“无法避免”的宿命。这里的宿命是历史决定论与出身决定论性别决定论的合谋,其余威所及,直接威胁到女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她们看不到或不敢正视自己生命的潜力,永远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在历史际遇面前失去以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的可能。关于女人能否走出宿命阴影这个问题永远没有一个统一的一概而论的答案,即便是阿妈这一代似乎是在无可更改别无选择的历史条件下,正如《阿妈的故事》中所选登的24篇阿妈的故事那样,也是各式各样的阿妈。这是一个“代的同属”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诚如编者所说,“那个时代亦有少数阿妈迥异于一般命运无法自主的阿妈,她们或接受高等教育,或看法、行事与见解均独树一帜”。这样的阿妈,在这本书里被称“独行于时代尖端的阿妈”,如民主阿妈陈翁式霞,革命女斗士叶陶,画家陈月里等,类似于我们这里的自本世纪初开始出现的走出家门谋求独立的知识女性、职业女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阿妈的不能自主的命运。母亲和母亲不一样,外婆和外婆不一样,那么到了外孙女这一代肯定将会更加的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大体上认同编者的观点:“一旦女性突破牢笼,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她的姓名便成为独立自主的符号。”书中最后一组为“生命重新来过的阿妈”,便是在晚年顿悟了自己的生命意义,以来者可追的姿态做出了积极主动的选择的阿妈。编者说:
这种“来者可追”的结局正是我们选择以这种阿妈作终结整书的目的。在象征的意义上,便是希望阿妈能走出宿命的阴影,不必如过去般对命运无言忍耐或妥协认命,而能勇于走出自己老年的一片天地。同时在象征的意义上,亦希望所有女性都能在制度与结构的改善下,不再是悲苦命运的牺牲者。生命永远可追,只要自己愿意。(注:《阿妈的故事》第9页。)
大学毕业后志愿援藏,在西藏度过了21年岁月,出版了《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三部散文长篇的马丽华,对此也抱乐观态度。她的父亲、母亲在50年代初便被不知所以然地双双解除了军职,发配到鲁南一个一贫如洗的地方,母亲又在50年代末成为那里唯一的一个女右派。她自幼便饱尝了饥饿、屈辱和失望,跟在母亲身后做小工、拾枯枝树叶、晒地瓜干,也从母亲身上学会了坚忍、顽强、耐苦、自强不息,对于挫折的不以为意,对于非常环境的超常的耐受力。同时,她觉得较之母亲她也有变化和超越。她相信自己“可以避免母亲的命运了”。这也就是“代”作为女人生命的刻度,不仅“为镜”同时也应该能够“为”。如果说“为镜”只是一种“代”的相似和重复,“为”则是经过了下一代人理性的思考和辨析对一代人命运的积极扬弃和超越。她也认为同为一代人的母亲和母亲是不一样的,成为什么样的母亲不仅仅取决于大致相同的历史际遇社会条件,也取决于每个母亲作为个人的选择和她为自己的选择所付出的努力。她认为,“在多种类型的母亲中,坚强的、自主的、以自身良好形象影响子女的母亲是最好的”。(注:马丽华:《西藏之旅》第244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3月版。)
这是否可以说明:代的轮回或代的超越都不是必然的和同一的,尤其是在“制度与结构的改善下”的时代,个人的自主选择尤其重要。筱敏的《血脉的回想》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她的独到之处在于把“个人”引入了“代”的范畴之中,把代的超越问题看做是一个个人的独立选择的问题。她也是以女儿和外孙女的双重身份回想外婆、母亲和自己的命运,但是由于她的鲜明的人文主义价值立场,由于她把女人作为个人的独立和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筱敏的“血脉回想”与众不同、卓而不群。无论是对外祖母、对母亲还是对自己,她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和深入的思考。外祖母也曾经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也和无数女人一样辛劳终生,也曾经不顾一切地反抗过,在那个尊卑有序的大家庭里,由于她的勤劳精干和强悍,事实上成为这个子女众多的家庭的支撑。可是这一切不过是无数代女人不能更改的命运的又一次微不足道的重复,不过是被家庭、丈夫、也被子女们剥夺、占有得更为彻底罢了。她们“生前与身后的梦中,都空无一物,然后就这样空无一物地被埋葬了,成了曾经囚禁她一生的墓园中一抔同质的砂土”。母亲尽管由于外祖母突发奇想要供她念书而成为省立师范的毕业生、成为知识女性,穿上了双排钮扣的干部服,站到了洪流一样的革命队伍里。可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只“学会了忠诚和服从,学会了融入大众,学会了删除自己”,从而丧失了对自己和对社会的独立思考能力,丧失了对社会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自觉。“当外部环境对人的禁锢开始缓解,当知识者有了个体生活的可能,母亲也不能恢复了”。“母亲的眼睛日渐浑浊,头发日渐稀疏。那一年母亲还不到五十岁。”这是另一种衰老,起因于另一种不易觉察的剥夺、占有和囚禁,而且是一种没有围墙的囚禁和不知道剥夺、占有者为何人何物的剥夺和占有。这也是另一种销蚀,销蚀得不着痕迹也不见踪影,以致你根本不认为这是一种剥夺和占有。由外祖母到母亲,究竟是代的超越还是代的轮回?筱敏就这样把女人作为人的价值标准问题尖锐地无可回避地提了出来。她的眼光,没有停留在诸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这类表层问题上,也没有纠缠在要家庭还是要事业这类的问题上面,她甚至不认为经济独立与否就是唯一的或特别重要的标准。她唯一看重的,是女人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的独立与尊严,是作为知识者的女人精神上的自由独立和自主的选择能力。因此,她在对母亲这一代作为知识者的女人的认识上独具慧眼。从代的轮回或超越的角度来看母亲是有别于外祖母却与外祖母殊途同归,在跨出了“婚姻自主”这一小步之后,在“其后的漫长的一生,都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母亲曾向外挣脱,划过一个漂亮的弧线,最后依然循着归路,回到外祖母这里”。对母亲的这种深刻理解,成为她为自己预设的真正的“超越”的起点。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却也并非不可企及:
在我窗外的废园中,有一株野树,就是在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挤压之下生长的。雨水也不能流进水泥封闭的土地,但她竟然长大了。年复一年,根茎嶙刚凸起,终竟使那一面高墙坼裂、倾斜。这使我知道一个微妙的个体生命的力量,相信生活的空间可以由自己去开启。我要求自己抵抗世世代代对妇女的剥夺,依凭个人的选择,独立成株。(注:筱敏:《女神之名》第169页,花城出版社1997年4月版。)
成为个人,独立的不依赖任何人、任何人的类别属性(诸如民族、阶级、国家、社会、家族、性别、代属等)的个人,已是90年代女性散文中一个悄然而至的觉醒。张洁、陈染、林白、蒋子丹、艾云等在她们的散文中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血脉的回想》的独特之处,是在代际这个最容易漠视个人价值的关系中强调了个人“独立成株”的重要性,这也是能否走出宿命的阴影、开辟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的关键所在。尹慧的思考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但她是从如何处理母女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代际关系中的每一代和代际中的每个人,都不是人身隶属关系,不是相互占有相互剥夺的关系;而是以亲情之爱为纽带的平等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即使不能在生他们(指子女——笔者注)的那一刻,承认他们不是我们的,我们至少要在日后明白,他们不只是为我们而活的”。“两代人之间,从过去到将来都不会是一回事、都永远要隔着一层什么”。“作为两代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相互分担、相互包容,别彼此要求过多、别太要求对方是你需要或你想象的样子,这差不多是最好的办法了”。(注:《这个春天这个冬天》第44页。)以独立的个人的名义相互分担,相互包容,而不是相互隶属相互代替甚至相互剥夺相互折磨,这可能就是女人代际关系的生存论意义上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