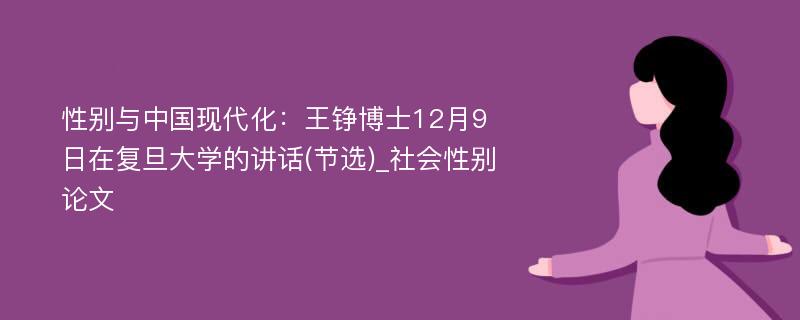
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王政博士12月9日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节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旦大学论文,现代性论文,讲演论文,中国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一题目是我在美国给研究生上课的课程名称,这门课要上近四个月,在这一小时的讲座中我只能挑一些概念来谈一下。
现代性(Modernity)是指自19世纪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遭遇之后产生的一种历史观、世界观,也指中国被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后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化。“社会性别”(Gender)是在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出现的一个分析范畴。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展了“社会性别”的概念,提出社会性别是人类组织性的活动的一种制度。
我想先把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概念问题化(Problematize)。首先我想对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做一个界定。我在这儿说的现代性(Modernity)是指自19世纪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遭遇之后产生的一种历史观、世界观,也指中国被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后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它不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变化,也体现在物质生活中。这儿我主要谈前者,看历史观的变化及其文化意义。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而现代性的历史观却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性的进化史观。知识的生产有其特定的历史政治背景,进化史观是使西方帝国主义殖民行为合法化的一种观念。这种进化史观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欧洲为中心、为历史发展的准绳,来界定文化间的等级差异,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国是“先进文明”,而与此模式不符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则是“不开化的野蛮”国家,殖民行为被解释成“文明”对“野蛮”的驯化。除了“文明与野蛮”、“高级与低级”的等级性界定,进化论也是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普遍论,各国各民族多样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形态被抹去,以欧洲的社会发展历程作为惟一合理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进化史观被不断介绍引进中国,对近代中国人的历史观、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近代以来产生的大量文本中可以发现,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梦想就是要达到欧美模式所界定的“高级”或“先进”文明形态。这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而且被社会精英付诸实践,改变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那么这一过程与社会性别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现代性的讨论有很多著述,而很少有人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探讨。在做这样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因为它对中国的学术界还是个很陌生的概念。
所谓“社会性别”(Gender)是在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出现的一个分析范畴。女权主义学者在探索将妇女的从属地位理论化时,曾借鉴过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但显然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阶级与性别的问题有许多不同之处。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展了“社会性别”的概念,提出社会性别是人类组织性的活动的一种制度,同任何文化中都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任何文化中也都有自己的社会性别制度,即种种的社会体制习俗把人组织到规范好的“男性”“女性”的活动中去,社会性别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方式,也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也可以说,人的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过程。社会性别的规范无处不在,其内涵也不断在变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同一文化中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性别的具体规范也会发生变化。尽管在大部分文化中社会性别被用来界定性别的等级,如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就是男尊女卑,但是也有的文化中性别间的等级差异很小。当然在中国的等级秩序中除了性别还有辈份年龄等等因素在交叉起作用,这意味着在同等社会阶层中女性并非总是处于卑者的位置上。但是在文化层面,社会性别的等级含义会不断被调动起来,被各种文化或知识生产者复制,从而不断巩固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观念;而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性别文化观念、语言、符号又时时在有力也参与对人的主体身份的塑造,构成人们对下述问题的基本认识和认同:自己要做什么样的男人或女人?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应该是怎样的?对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的人持何种态度?人们对社会性别文化对自己的规范和塑造一般没有理性和意识层面的认识,但任何人都被某种或几种社会性别话语所构造,人的主体是社会性别化的,并可能具有不同社会性别话语所造成的矛盾性,多面性。社会性别的文化观念也经常体现在人们所做的各种选择和决定中,包括政府或各种权力机构的决策中。在当代女权主义学术发展了30多年的西方,“社会性别”已经与“阶级”、“种族”一样成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分析范畴,在各个人文社科学术领域被广泛运用。因为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概念了解很少,今天也借此机会将这一概念介绍一下。
现代性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应该引起关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妇女问题的大讨论揭示了中国社会中的社会性别等级和歧视束缚妇女的种种弊病,但是这个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大讨论也有其缺陷:男性精英们居高临下地看妇女,把妇女视为素质差的群体,把妇女一概表现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抹杀了妇女在中国5000年文明中的作用与贡献,对妇女做出一种非历史的界定。
下面我对中国现代性做一个社会性别的分析。
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现代性的问题一直讨论得非常热烈,而对社会性别的讨论却很少。但是现代性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应该引起学者的关注。一直有一种说法:中国妇女的解放是由男性提出的,中男妇女是被动地由男性解放的,这体现了中国两性自古以来的“阴阳合和”。对近代以来的社会性别关系,我要做个不同的阐释。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会知道,“阴阳合和”是一种理想,而“男尊女卑”则是由一套社会体制和规范维系的社会现实。那么如何理解近代知识男性率先提出妇女问题这个现象呢?古代中国,家国同构,“家”为“国”之基础,而“女”在“家”中的重要作用也因此历来为士大夫所注意,从周易开始,就强调“女正,家正。”而要“女正”须先“正女”,这“正女”的任务就由士大夫主动承担,诸多的家训、家规以及士大夫家书中都包含了大量的“正女”内容。换言之,中国的士大夫们有着悠久的、持之以恒的“正女”传统。到了近代,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在国家危亡之际,男性知识精英又因对“国家”的关注而把焦点集中到女性身上。比如,将中国的软弱归结于中国的“神气”不强,进而归因于女性身体的软弱(“小脚”),因此要改善女性身体来实现“强种保国”。康有为、梁启超的废缠足运动便由此产生。再如,梁启超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弱于欧洲,是因为“二万万女子为食利者”,二万万男子生的利,让另一半不劳而获的人口给分了,这个国家怎么会强呢?所以要兴办女学,让女子也有一个生利的技能,成为国家发展的人力资源。对妇女在历史上的经济作用持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知道费孝通早年在《江村经济》中明白地报告过,妇女在家庭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长期的农业经济中女性的劳动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非常关注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作用。美国学者曼素恩所著的《珍贵的记录》一书中研究了清政府对女工的关注,指出妇女所从事的家庭纺织业是清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总之,梁启超在提倡女学时所谈到的妇女历史作用和贡献是有失偏颇的。这并非特殊例子,因为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女子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妇女问题(妇女是“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强国的途径。妇女是载体,是手段,强国是目标。
国家民族主义的产生与社会性别密切相连,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历史过程中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康、梁到新文化运动时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对妇女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新青年》第一期就开始谈妇女解放问题,到了五四时期,谈论妇女解放更是成为一种时尚。在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中,有一条线索是来自欧洲的人权思想,认为在现代文明中,人权应该包括女权。但是也有很多男性所强调的是“改造妇女”(而非“解放”!),文章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厌女”、“仇女”的倾向,贬低妇女的词语更是随处可见。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成为攻击的对象,从而作为三纲五常之一的“夫为妻纲”以及“男尊女卑”观念都成为重点抨击的问题,与妇女相关的缠足、包办婚姻、童养媳、不让女子受教育等问题都被作为儒家“吃人”礼教的典范,被提出来批判,进而达到摧毁儒家传统的目的。对妇女问题的大讨论确实揭示了中国社会中的社会性别等级和歧视束缚妇女的种种弊病,但是这个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大讨论也有其缺陷:男性精英们居高临下地看妇女,把妇女视为素质差的群体,把妇女一概表现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抹杀了妇女在中国5000年文明中的作用与贡献,对妇女做出一种非历史的界定。当时大部分参与讨论的知识男性缺乏一种自省,不能反思要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男性需要对自己的特权位置做什么样的挑战和调整?而同时,20世纪初正是西方女权运动高涨的时期,女权运动被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看成是西方先进文明的一种象征,这也促使以西方文明为追求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竭力鼓吹女权,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视为现代性的鲜明标志,促使那一时期的女权“声浪高涨”。当时的女权主义话语中也有女性的声音,《妇女杂志》等刊物上都曾发表了那一时期女性的声音,也有许多女学生自己创立刊物,成立女权运动组织。但是因为当时妇女在文化程度和社会资源方面的限制,能够发出妇女自己的声音的刊物并不是很多。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妇女的解放是被动的,近代自秋瑾以来的众多女性为追求自身的解放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经受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在我撰写《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一书时,采访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对20世纪初期以来妇女的不懈追求和抗争有深切的体会。可以这么说,若没有20世纪初几代妇女勇敢地突破种种性别藩篱、为女性开辟出各种社会空间,20世纪下半叶中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发展会是难以想象的。连五四时期鼓吹女权的新文化男性知识分子也明白,若没有妇女自己的身体力行,妇女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
20世纪初的女权呼声中,有多种多样的声音。清末革命者金天翮在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一书中对女子做了重新界定,其实是对“新女性”提出的规范,成为一代人的行为准则。他反对把女子培养成相夫教子的良妻贤母,提出教育应把女子培养成革命的新人。他呼吁受教育的女性应成为:一、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总之,在金天翮对20世纪新女性的展望中,打破了儒家传统中贤妻良母的规范,着力提倡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进入公共领域,发挥“女国民”作用,成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力军。他所鼓吹的女界革命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也很有震撼力,对当时一些希望打破社会性别藩篱的女子有相当大的激励。但是由此而开始的以男性为模式为准则的妇女解放也是有问题的。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提出了批评,他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阐述妇女解放问题,他说:“现在的大谬误是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认了”。这种以男性为标准的妇女解放一直延续着,毛泽东时代倡导“不爱红装爱武装”实际上包含了秋瑾的“影子”,它表达了20世纪初那几代革命者的一种理想。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那是充满自豪感的,是青年时的梦想成真了。但是没有人问“女同志能办到的事情,男同志能做吗?”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其结果是,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社会资源和权力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女权”这个词在20世纪初出现时,是一个正面的词汇,是标志先进文明的一个词。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之中,既吸收了大量女权主义的议题来吸引妇女,又对独立的女权组织予以排斥,把不介入大革命的妇女组织和活动界定为狭隘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在一系列的政治运作之后,“女权”这个词开始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变成了贬义词。但是毛泽东时期的妇女解放以及主流社会性别话语其实包含了对五四女权主义议题的继承,共产党内有不少当年活跃于五四女权运动中的“新女性”,她们是共和国初建时期按“五四”的女权理想推动妇女解放的主力。
今天的社会对女性要求有“女人味”,做“贤妻良母”又成为“女人味”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有权势的男性特别热衷于鼓吹让妇女回家承担“相夫教子”的角色。此外,在许多所谓“成功”的男性在变相地实行多妻制的同时,男性对女性的贞操却念念不忘,这实际上是对五四时期女权话语的一种反动,也是当代一些男性力图巩固自己性别特权的一种运作。
从“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到文革时期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女装的变化也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想象。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时髦的内涵常常表达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和规范,但是其内容是变化的,不固定的,今天的时髦反映了我们今天现代性的想象与追求。今天的社会对女性要求有“女人味”,做“贤妻良母”又成为“女人味”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有权势的男性特别热衷于鼓吹让妇女回家承担“相夫教子”的角色。此外,在许多所谓“成功”的男性在变相地实行多妻制的同时,男性对女性的贞操却念念不忘,这实际上是对五四时期女权话语的一种反动,也是当代一些男性力图巩固自己性别特权的一种运作。我们在指出五四女权话语有以男性为准则的偏颇的同时,也要看到今天“女性味”话语对儒家传统性别规范的回归的负面意义,这种回归在社会经济文化都已经变化了的当代中国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义。当代中国女性既被要求参与创造现代性的国家,又被赋予传承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重任”,即:保留和体现“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我们需要思考:现在传媒中所表现的作为现代性符号的“现代女性”有何问题?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这种再表现符合哪些人的利益,又损害哪些人的利益,对女性群体而言又有何影响?社会性别话语在制造对女性的规范的同时也在制造对男性的规范。所不同的是,对男性来说,近代以前以孝、忠、悌为衡量男性的标准,而现在,知识男性不提保存“东方男性的传统美德”,追求“西方的男性气质”却成为中国男性的目标。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过程中产生的对男性的进攻性、竞争性的推崇成为当代中国人界定男子气概的标准。如果说“女性味”的社会性别规范会束缚女性的发展,那么以西方男子气为标准也会使中国男性产生焦虑和感到压抑。壮阳药的巨大市场就是一种表症,反映的是当代文化制造出来的男性性焦虑。确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对现代性的想象中充满了社会性别含义,表达了在全球权力等级结构中处于劣势的中国男性精英的内涵复杂的焦虑感。
今天介绍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是希望我们在看问题时能够多一种视角和分析范畴。文化,包括社会性别文化是人的建构,它同时又塑造了文化中的人。多一种分析文化建构的工具,将有助于我们增强抵抗强势文化控制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