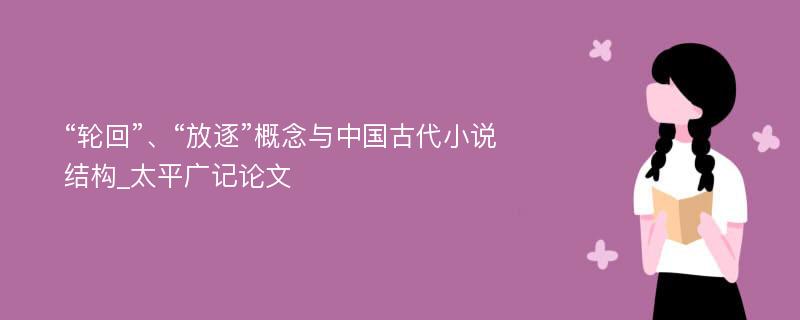
释道“转世”“谪世”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观念论文,结构论文,小说论文,释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它和中国文学本就有着很深的渊源。佛教虽自国外传入,但也迅速浸淫到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其中特别是作为通俗文学的小说,和民间化了的宗教尤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不仅大量表现在小说的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小说的形式中。本文拟就佛道两教的“转世”、“谪世”观念和古代小说的结构关系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佛教有所谓“三世”之说,即前世、今世和来世,并以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观念贯穿于其间。在佛教看来,一个生命(人或动物)死后,灵魂依照因果报应的规律而投胎成为另一个生命,是为转世。在这生命轮回的过程中,前世为因,今世为果;今世为因,来世为果。所谓“欲知过去因者,见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者,见其现在因”[①a],“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②a]。其法则之绝对永恒,无一可逃脱。这种三世因果、轮回相报的观念,构成了我国民间佛教信仰最重要的内容,并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我国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它为我国古代小说提供了一个最为广泛而普遍的主题,同时也为我国古代小说找到了一种常见的结构形式。
还在小说诞生之初,佛教有关三世因果、轮回转世的思想就以富于形象的感性形式流传于民间,并被不时吸纳进包括小说在内的俗文学之中。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这样两则记载:
张衡之初死,蔡邕母胎孕,此二人才貌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裴子语林》,《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
晋羊祜三岁时,乳母抱行,乃令于东邻树孔中探得金环。东邻之人云:“吾儿七岁堕井死,曾弄金环,失其处所。”乃验祜前身,东邻子也。(《独异记》,《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八十七)
这两则记载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但在我国古代笔记中,它们是较早记载这类传说和故事的。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还可举出同时代另外一篇作品:
晋王练,字玄明,琅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晋中书令;相识有一梵沙门,每瞻珉风采,甚敬悦之,辄语同学云:“若我后生,得为此人作子,于近愿亦足矣。”珉闻而戏之曰:“法师才行,正可为弟子子耳。”顷之,沙门病亡。亡后岁余而练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国语,及绝国之奇珍、银器、珠贝,生所不见,未闻其名,即而名之,识其产出;又自然亲爱诸梵过于汉人。咸谓沙门审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练,遂为大名云云。(《冥祥记》,《法苑珠林》二十六)
这篇故事已颇具小说意味,虽然这样的短小说还谈不上什么结构,但通篇就是讲的转世,且开了以后爱情转生的先河。
到了唐代,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小说的日益成熟,写及转世故事的笔记体小说和传奇体小说空前增多。仅《太平广记》所录,就有数十篇之多。其中著名的如《甘泽谣·圆观》(《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八十七)、《会昌解颐录·刘立》(同上卷第三百八十八)、《纂异记·齐君房》(同上卷第三百八十八)、《异物志·李元平》(同上卷第一百一十二)、《逸史·卢叔伦女》(同上卷第一百二十五)、《博异记·崔无隐》(同上卷第一百二十五)、《宣室志·闾丘子》(同上卷第五十二)、《玄怪录·张佐》(同上卷第八十三)、《续玄怪录·杜子春》(同上卷第十六)、《河东记·萧洞玄》(同上卷第四十四)等。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唐代小说中,虽然相当数量的作品仅仅是为了宣传佛教思想,而在内容上讲述一个转世故事,但也确有部分作品,不同程度地摆脱了宣传佛教教义的狭隘目的,而主要是借用“转世”来作为结构小说的枢纽,这样,佛教的“转世”观念就由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逐步蜕变为结构小说的一种形式。
唐代描写“转世”的小说最有名的当然首推《圆观》,这篇作品虽然还有着侧重内容表现的明显印记,但重点已不是为了宣扬三世因果和善恶报应,而是为了突出情的绵延永恒。圆观与李源之间那种超越时空的同性情爱,借“转世”的形式得到了最充分、最动人的表现。当我们看到李源三日后“往观新儿(即圆观后身),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时,当我们看到十二年后李源践约赴杭州天竺寺重与圆观后身牧童相见,李源“无由叙话,望之潸然”,圆观唱着竹枝词“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步步远去时,我们不能不在心头涌起一份感动。这里,转世观念中原有的因果报应成份被淡化、乃至遗忘了,剩下的唯有绵延不绝的情思。
更侧重结构形式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杜子春》一篇,《杜子春》本是讲道家出世的,但在结构上却借用“转世”作为一转捩点。当杜子春遵从老道士的戒令,经受了鬼神威逼、猛兽搏噬、雷电轰击、妻子受刑、本人备受地狱之苦等种种磨难,而终不发一言时,阎罗王也拿他没了办法,只得罚他转世作女人,生而多病,受尽痛苦,但终不失声,人目为哑女;后嫁于卢生为妻,生一男。一天,丈夫因其终无辞而大怒,将孩子“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面对此情此景,杜子春终于“爱生于心”,“不觉失声云:噫!”因此而前功尽弃。这里,杜子春尽管以最大的意志力经受了种种考验,但最终未能完全泯灭人类爱的本性。作品在表现爱心胜于道性这一主题时,“转世”模式在结构上起了一个非常关键和转捩的作用。因为杜子春只有从男性转世投胎为女性,作为一个母亲,她那原始的天性才能在爱子这一点上突然地爆发出来。与《杜子春》差不多同一机杼的还有《河东记》里的《萧洞玄》。
唐以后,由说话发展而来的通俗小说蔚为大国。在数量浩翰的通俗小说中,不仅那些专写佛道神鬼的神魔小说充斥了投胎转生之类的故事,就是很多严格意义上的世情小说和历史小说,也往往借助“转世”来结构小说。无庸讳言,这些作品中有相当数量迷信的色彩较浓,劝惩的味道太重,如《雨花香》第十一种《牛丞相》一篇,叙明状元罗伦告病辞官至扬州,忽雷击一牛死,罗甚不平,于牛身书曰:不去朝中击奸相,反来田间打耕牛。未几乌云疾来,罩聚牛身,复一雷,牛身现二句云:他是唐朝李林甫,十世为牛九世娼。又《西湖二集》卷十六《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叙朱淑贞被赌徒舅舅抵债,嫁与金氏残疾子为妻,痛苦不堪。后知朱前世为何养元,曾奸骗奚二姐,中进士后又弃之。阴司判奚二姐为丑男,使何养元为女才人朱淑贞,传消息之丫环玉兰转世为朱之舅。朱二十二岁郁郁而亡。又《二刻醒世恒言》第七回《三世仇人面参禅》,言汉景帝大臣晁错为袁盎所害,投胎为司马昭,袁盎死后转生为邓艾。后司马昭杀邓艾,报了前世之仇。三世时,晁为老僧,袁为贫人,并使其膝上生人面疮。二人庙中相遇,参悟三世之仇,冤缘遂解。诸如此类,除了故事本身所表现的三世因果、冤冤相报之外,没有太多的社会历史内涵。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作品相对淡化了其中的宗教迷信成份,主要表现的是现实生活内容,而借用“转世”来结构情节。著名的如《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两书都是以两世转生为情节构架。《金瓶梅》是:前世西门庆——转世西门孝哥——后得高僧点破而出家;《醒世姻缘传》的结构则是一个两世的恶姻缘:前世晁源和计氏及珍哥,今世狄希陈和素姐与寄姐,最后也是得高僧点破。虽然这样的结构形式难免会使作品笼罩上一层浓厚的因果报应色彩,但小说所主要表现的是活泼泼的现实生活,是小说人物的七情六欲和真实的生命历程,相比之下,转世故事中原有的迷信因果成份被淡化了,留下的主要是转世的结构框架。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古今小说》第三十卷《明悟禅师赶五戒》,叙五戒、明悟二高僧感情深笃,一大雪天,寺中收养了一弃孩红莲。十六年后,五戒私通红莲,被明悟点破,五戒悔羞坐化。明悟为了赶上去救他免堕苦海,也圆寂而去。五戒转世为苏轼。明悟转生为谢瑞卿,后出家名佛印。二人志趣不同,佛印常劝苏轼弃官修行,苏不肯。后苏轼得罪王安石,宦海浮沉,辗转贬杭州、黄州、永州等地,佛印一直随行。在此期间,苏轼梦知前生因果,终有所悟。二十年后,与佛印一起圆寂。《清平山堂话本》中亦有《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一篇,此外《古今小说》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一篇主旨也大致相同。又如《型世言》第三十五回《前世怨徐文伏臬,两生冤无垢复雠》,叙天顺间英山清凉寺无垢和尚,原为蔡氏之子,六岁出家,师从远公和尚。十四岁携银一百二十两到南京印经,宿印匠徐文家,被其所害,即托生他家,要杀之报仇。得神明托梦的祁御史审明缘由,将徐文正法。无垢用原银印造大乘诸经,复归旧寺,与远公成隔世师徒。其他如《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四卷《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谈前因后果》,叙元自实前生是个学士,因自恃才高,拒绝交游,所以今世漂泊的故事;《欢喜冤家》第二回《吴千里两世谐佳丽》,叙吴千里于途中被陈本栋主奴谋财害命,托生受其继子报仇的故事;《石点头》第九卷《玉萧女再世玉环缘》,叙玉萧女两世与韦皋的爱情;凡此等等,虽然它们其间都不同程度地烙有因果报应的印记,但其社会历史内涵又非一句因果报应所能概括,因为转世故事在这里已主要变为一种结构小说的形式。甚至包括《三国演义》的前身《三国志平话》,在开首也保留了韩信转世为曹操,彭越转世为刘备,英布转世为孙权,对转世为献帝的汉高祖进行报复的结构框架,但小说内容实已完全与此无涉。
综上所述,佛教“转世”观念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影响非常之大。虽然在开始和以后一些场合,转世故事既是结构形式,又是情节内容,许多作品很难将它们具体区分开,但在小说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转世观念确被更多地借用来作为结构小说的一种形式。这种借用是如此之普遍,以至它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结构的一种常见的模式。在这方面,也许只有道教的“谪世”观念,才能与之相颉颃。
二
在深刻影响我国古代小说结构的诸因素中,和佛教的“转世”观念相辅而行的,是道教的“谪世”观念。
所谓“谪世”,是指证得道果居于上界的仙人,由于触犯某种戒规(通常是由于动了凡心),而被谪降至人世。一般来说,谪世是指有过失而遭贬谪,但其中也包括了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天帝令其下降人间,或本人自愿下凡历劫。不管是属于哪种情况,谪仙们的人生历程是被规定好的:即经过一段尘世生活,又重新回归上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就有着不少这类以“谪世”为构架的小说。如《神仙传·壶公》一篇(见《太平广记》卷第十二),写壶公传授费长房仙道,即语房曰:
我仙人也,昔处天曹,以公事不勤见责,因谪人间耳。卿可教,故得见我。
又如《真诰·萼绿华》一篇(见《太平广记》卷第五十七),叙女仙萼绿华度脱羊权,也自我介绍说:
是九嶷山中得道罗郁也。宿命时,曾为其师母毒杀乳妇玄洲。以先罪未灭,故暂谪降臭浊,以偿其过。
这是因获罪而被谪降的,谪降人世后主要是为传授仙道,度脱世人。
再如著名的《搜神记·董永》一篇,叙天上织女下嫁农家子董永为妻,帮他织完了一百匹细绢,对他说:
“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又如同样有名的《搜神记·白水素女》一篇,也是写天女托身田螺内,下凡至一农人家,每天帮助他看家烧饭,后被农人发现,告诉对方说:
“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这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下降人世的,降世后主要是与异性过了一段尘世生活。与此相类的还有《搜神记》中的《杜兰香》、《天上玉女》等篇。
至唐代,道家谪世小说更是多见,且与以前相比,情节更为丰满,描写更为委婉动人,显示了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与自觉。如《通幽记·赵旭》一篇(见《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五),叙天水赵旭,夜半忽闻窗外切切笑声,又听到一女子说话声,言其为上界仙女,愿托清风,与之相会。赵旭乃回灯拂席以延之,果有一女子开帘而入,笑说:
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
两人携手入内,正要结情罗帐,忽闻外面有一女呼“青夫人”。青童君云:“同宫女子相寻尔,勿应”。担心“此女多言,虑泄吾事于上界”。赵旭起迎,原来也是一神女,从空中走下来说:
“吾嫦娥女也。闻君与青君集会,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以知吾处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谁过耶?”相与笑乐。旭喜悦不知所栽。
鸡鸣时,两仙女同去。以后青君隔数夕复来,欢娱日洽。青君每每警告旭不得泄露,旭言誓重叠。不意后岁馀,赵旭的奴仆盗琉璃珠鬻于市,被告至官,奴仆把事情全讲了。当晚青君便与旭怆然诀别。这篇小说虽同为谪世构架,但其情节之丰富,描写之细腻,远非以前同类小说所能望其项背。
同样饶有情趣的“谪世”小说还可举出《灵怪集·郭翰》一篇(见《太平广记》卷第六十八),小说叙太原郭翰夜遇一仙女自空中冉冉而下,自云:
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
于是两人携手升堂,解衣共卧。欲晓辞去,凌云而去。自后夜夜皆来,情好转切。一天,郭翰戏之曰:
“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
后将至七夕,忽不复来。经数夕方至,郭翰问说:
“相见乐乎?”笑而对曰:“天上那比人间,正以感运当尔,非有他故也。君无相忌。”
后一天晚上,因“帝命有程”,仙女终和郭翰永诀,并言明年某日当有书信相问。明年至期,果有侍女持书函至,书末还有诗二首,诗云:“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回顾,交作两相思。”郭翰从此“凡人间丽色,不复措意”。这篇小说不仅构思新颖,文笔清丽,而且颇有生活情趣,洵为唐传奇之上乘。类似的作品还有《姚氏三子》(出《神仙感遇传》,见《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五)、《封陟》(出《传奇》,见《太平广记》卷第六十八)等。
“谪世”原本指天上神仙直接谪降至人世,开始从空中而来,最后复凌空而去。后这种“谪世”说又揉合进了佛教的“转世”说,演变为上界仙人重新托生于人世的模式。如《崔少玄》一篇(出《少玄本传》,见《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七),少玄即为“胎育之人”,“昔居无欲天为玉皇左侍书,谥玉华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书来访志道之士,尝贬落,所犯为与同宫四人。退居静室,嗟叹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责之,谪居人世”。后少玄经历了一段尘世生活,死后埋葬,“举棺如空,发榇视之,留衣而蜕。”又《妙女》一篇(出《通幽记》,见《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七),叙妙女“本是提头赖吒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世,已两生矣”,也是因获罪而托生于人世的,且已两生,前生还“生有一子”。这种因获罪而重新托生于世的“谪世”模式,为后来的白话通俗小说所广泛吸取。
由于重新托生较之直接贬谪于人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后者在展开人物和情节时,必须考虑到他(她)们的身份是神仙,虽已谪世,但身份未变,因而有关描写总是介乎人神之间,似人非人,似仙非仙,人物缺乏真实的现实品格;而重新托生的人物虽也与原先的仙人有着某种渊源,但他(她)们是一个新的生命过程的开始,作者在创作时拥有较大的自由度。
采用重新托生这样一种“谪世”模式来构架的小说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作者运用奇特的浪漫手法,想象丰富,大胆夸张,作品仍保留了强烈的神奇色彩;另一种是作者对小说主体部分基本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以平实的写实手法,写出具有现实品格的人物。
前者如《古今小说》第三十三卷《张古老种瓜娶文女》、《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薛录事鱼服证仙》、《拍案惊奇》第二十八卷《金光洞主谈旧迹,玉虚尊者悟前身》,以及长篇小说《女仙外史》、《金石缘》、《镜花缘》、《绣云阁》等,这些小说写重新托生于世的神仙仍具有某种超现实的力量,故事情节中也有着较多非现实的成份,其中《镜花缘》可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它叙上界为花仙子“奉上帝之命,总司天下名花,若无帝旨,即使下界人王有令,也不敢应命。”因此而和嫦娥发生口角,并定下罚约:倘哪一天下界帝王有兴,使出回天手段,令百花开放,“原堕落红尘,受孽海无边之苦”。不料日后心月狐“思凡获谴”,即投胎为唐家天子(武则天),临行前与嫦娥告别,嫦娥以激将法让其一日之中令百花齐放,以显通天手段。果然,一年残冬,武则天饮酒赏雪,乘醉下诏,命百花齐放。此时适逢百花仙子到麻姑洞府弈棋未归,众花仙无从请示,只得开花。上帝因百花仙子并未奏闻,“听任部下逞艳于非时之候,献媚于世主之前,致令时序颠倒”,下旨将百花仙子及九十九位花仙一起贬入凡尘。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取名小山,改名闺臣。
后唐敖随妻舅林之洋到海外漫游,一路上见识了许多奇风异俗,奇人异事,后因船遇风暴,来到小蓬莱,一人独自上山不归。小山得知父亲失踪,立意出海寻访。此时武则天下诏开科考试才女,林之洋劝她在家备考,小山执意不从。途中遍历风险,终于到达小蓬莱。寻找数日,未见唐敖,却从一樵夫手中得到唐敖亲笔信,命小山改名闺臣,考中才女,再行相聚。闺臣应命回国赴考,得中第十一名才女。其他谪世姊妹也都分别中榜。在连日欢宴之后,唐闺臣再去小蓬莱寻父,入山登仙。
这是典型的以道教谪世(托生)为构架的小说,闺臣因获罪而被贬谪托生于人世,经过了一段生命历程,重又回到仙界。只是这段生命历程是以奇特夸张的手法描写的,情调浪漫奇异。
后者则如《英烈传》、《昭阳趣史》、《醋葫芦》、《水浒传》、《后水浒传》、《桃花影》(一名《牡丹缘》)、《红楼梦》、《雪月梅传》、《龙凤配再生缘》、《说岳全传》、《两缘合记》第一段《仙姬降世》等,这些小说所写的托生后的神仙已经完全成了历史人物或现实生活中的凡人,他们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和现实品格。其中又以《红楼梦》为典型代表。它叙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仙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修成个女体。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后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便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其中神瑛侍者便托生为贾宝玉,绛珠仙子则托生为林黛玉,然后有了《红楼梦》这部写尽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根据脂评透露,小说最后还有《证前缘》一回,贾、黛两人仍要回到“青埂蜂证了前缘”(见于传抄的靖本第六十七回、七十九回批语)。可见《红楼梦》虽又名《情僧录》,写宝玉最后出家为僧,但作为全书构架的,是典型的道教谪世托生模式。而这里神瑛侍者被谪降的原因,也是所谓“凡心偶炽”,即通常所说的“思凡”,这是我国古代仙道类小说最普遍的主题之一。只是这里上界仙人所重新托生后的生命历程,完全是运用严格的写实手法写的,即如《红楼梦》开卷所强调的,“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这和《镜花缘》等小说不同。
要而言之,道教“谪世”观念是深刻影响我国古代小说结构的又一种宗教观念,由于它在我国民间的广泛影响,其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渗透力较之佛教“转世”观念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一释一道,一“转世”、一“谪世”,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小说两大结构模式。探讨这两种模式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它们的弊端和不足,是本文的主旨之所在。
三
以上我们分别论述了佛道“转世”、“谪世”观念和我国古代小说结构的关系。以往,论者多注意它们和古代小说内容的关系,并每每以宣扬了因果报应思想和宿命虚无思想来论定。其实,这样理解未免有点片面。虽然形式总离不开内容,但它还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佛道“转世”、“谪世”观念作为结构小说的一种形式,固然会有宣扬因果报应和宿命虚无思想的一面,但毕竟也有它相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佛道“转世”“谪世”观念作为一种结构形式,它使我国古代小说取得了一定的时空自由,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和表现力。
小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叙事的艺术,特别是我国古代小说一般在叙事时间上采取连贯叙述,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以情节为结构中心,因而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表现尽可能长的时间跨度,以融进尽可能丰富的情节内容,便成了我国古代小说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佛道“转世”、“谪世”观念的引进小说,正为古代小说家加大时间的跨度和情节的容量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无论是佛教的“前世因—后世果”,还是道家的“神仙谪世——仍回仙界”,叙述的都是两世以上的生命历程,这就使小说家在采用连贯叙述的叙事时间上获得了相当的自由度。而时间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空间的变化,由于超越了生死大限,人物的活动空间也随之扩展到上、中、下三界。即便同是人世,其时空的自由度也变得相当大。如《圆观》,从今世到来世,从四川三峡到杭州天竺,短短的篇幅内浓缩了两世的情爱。又如《醒世姻缘传》,从前世到今生,从山东到北京,妒恨同样穿透了两世人生。再如《红楼梦》,从前世到今世再到来世,从青埂峰到大观园再到青埂峰,刻骨铭心的爱不仅穿透三世,而且跨越两界!总之,在以“转世”、“谪世”为构架的小说里,无论是爱与恨,还是情与欲,都显示了相当大的时空跨度,而且有穿越三世与三界的特点,从而为加大作品的容量和表现力,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其次,佛道“转世”、“谪世”观念的被引进小说结构,也为我国古代小说提供了一种宗教的人生关怀,并使其中的佼佼者具有一种哲学的意味。
艺术和宗教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们都具有一种对人生的怜悯和关爱。佛道“转世”“谪世”观念的介入小说,固然会使小说蒙上一层因果报应、宿命虚无的尘埃,但同时也使它具有一种宗教和哲学的意味。如《杜子春》一篇,当杜子春充分享受了人生,决心经受考验,修道成仙时,他几乎所有的考验都挺过来了,但最后正当他向着渺渺太虚飞升,即将越过最后一道防线时,他突然逆转方向,猛然回首,在追求虚无的永恒和找回失落的人性之间及时地作了自我拯救,她舍弃了永恒的天国,仍回到尘世的土地;这种看似不经意的选择,包含了一种真正的宗教情怀,即对于生命的怜悯和关爱。
以佛教“转世”观念为构架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也是如此,作品写了西门庆这个暴发户的迅速崛起,又写了他的飞快暴亡。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人生的归宿又在何方?作者通过西门庆死后转生为西门孝哥,并最终出家为僧,为一个罪恶的生命作了来世的拔救。
最具有哲学意味的当然还是首推以道教“谪世”观念为构架的《红楼梦》,这部小说从一个远古时代充满神话色彩的木石之盟开始,经过一段真实的人间历程,最后重又回到渺渺的太虚之中。由于将人间的一段悲欢离合置于绵绵的历史长河之中,空漠的宇宙空间之上,这段人间悲剧既显得隽永而凝重,同时又显得相对短暂而渺小,就犹如空空道人站在云端俯视人间,一切都变得那样的平静。这里,悲剧似乎被淡化了,但哲学的意味却加重了。透过那令人心痛神弛的人间悲剧,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生命的痛苦,青春的无奈,而且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对于人生的思考和领悟。不难设想,如果小说不是采用这种结构框架,而是直接就写大观园内的悲剧,那么小说不仅缺少了瑰丽的神话色彩,也少了一点哲学的精神和宗教的情怀。
再次,佛道“转世”、“谪世”观念的引进小说,使我国古代小说在结构形式上具有回环兜锁、圆如转环的特点,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特有的形式美感。
佛教的“转世”说和道教的“谪世”说都具有循环论的特点,“转世”是在过去(前世)、现在(今世)、未来(来世)之间不断循环,“谪世”则是在上界(仙界)和中界(人世)之间往复回还,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得合抱而贯连,因而以它们为构架的小说,自然在结构上具有回环兜锁、圆如转环的特点。
“转世”小说如《古今小说》中《明悟禅师赶五戒》,写五戒和明悟、苏轼和佛印一对朋友的两世友情,《醒世姻缘传》写晁源和计氏、狄希陈和寄姐一对夫妇的两世姻缘,《金瓶梅》写西门庆、西门孝哥父子的两世冤孽,在结构上都前抱后合,显得圆融之至。“谪世”类小说亦是如此,不管是神仙直接谪降人世的,还是重新托生于世的,他们最终都要回到上界。如《昭阳趣史》,以狐、燕两精苟合交恶,被玉帝罚下凡为飞燕、合德两姊妹起,以合德、飞燕死后魂归上天,继续修心炼性结;《女仙外史》,以嫦娥降生为唐赛儿起,以玉帝召嫦娥仍返广寒宫结;《红楼梦》,以青埂峰下木石之盟起,以青埂峰下证前缘结;《镜花缘》,以仙子获罪谪世起,以闺臣入山登仙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结构上都具有回环兜锁、圆如转环的特点,这种特点构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特有的形式美感。
当然,除了上述正面的意义,无庸讳言,以佛道“转世”“谪世”模式来结构小说,也还存在不小的负面作用。这是我们在肯定其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不能回避和忽视的问题。
首先,无论是“转世”小说还是“谪世”小说,其主旨都是一个,即企图以明确的因果关系,将历史和人生化约为可以理解的模式。这种化约虽然满足了一部分读者的心理要求,但却并不符合事物的本身规律。因为实际上历史和人生总是充满各种无法确定、无法归类、无法解释的现象,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就能解释得了的。像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西门庆父子的两世冤孽,狄希陈夫妇的两世姻缘,以及曹、孙、刘三家的瓜分汉室天下,梁山好汉的横行大宋江山,民族英雄的惨遭奸佞谗害……这一切在小说中都被解释成是宿命的,这样的解释简则简矣,但距离真实的历史和人生实在很远。
不仅如此,由于这样的解释,更给作品笼罩上一层不同程度的因果报应、劝善惩恶、虚无宿命等消极的思想影响。无论是《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也无论是《全相三国志平话》、《水浒传》和《说岳全传》,或者是从魏晋志人志怪到唐传奇再到明清拟话本小说,可以说这样的思想影响在在皆有,不同的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即使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它所流露的浓厚的虚无宿命的思想情绪,对今天的读者也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们对佛道“转世”、“谪世”观念于小说的负面影响,一点也不能低估。虽然很多小说已侧重于借用这两种模式来结构小说,但形式不可能完全脱离内容,凡以佛道“转世”、“谪世”模式为构架的小说,必然会烙有程度不同的上述思想印记。
其次,不管以“转世”、“谪世”为构架的小说有着多少优点,一旦它们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势必就变成了程式化、凝固化了的东西,这不仅会令读者生厌,而且于小说形式的发展也是极不相宜的。艺术形式的变化虽然相对内容来讲有其一定的稳定性,但它的生命力仍在于不断创新。以“转世”、“谪世”为构架的小说,尽管有着上述作用和意义,但如果每一部小说都这样机械套用,千篇一律,千部一腔,不管对象,不看实际,生搬硬装,则又未免令人讨厌。这里,重要的是要构思新颖,独出机杼,不落前人窠臼。如《红楼梦》,虽也是以“谪世”作构架,但它新创了“还泪之说”,这是前所未闻的,因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这方面,《圆观》、《杜子春》、《金瓶梅》、《镜花缘》等处理得较好,而其它一些三、四流小说则不同程度地留有程式化、概念化的痕迹。
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是构成小说叙事模式的三大要素[①b],佛道“转世”、“谪世”观念的引进小说结构,既加大了基本采用连贯叙述的我国古代小说的时间跨度,又强化了基本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既对形成我国古代小说现有的叙事模式起了促进的作用,同时又为转变和打破这一模式起了阻碍的作用。这只有到了近现代,随着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和传统小说形式的创造性转化,才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根本性转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佛道“转世”、“谪世”的结构模式也逐渐为小说家所舍弃。
注释:
①a此语被广泛引用,但文字稍有异同,且不明出处。本文转引自丁福保编纂、文物出版社版《佛学大辞典》。据该书“三世因果”条下称:“古以此文为《因果经》之语而处处引之,但现在流通之经无此文。”笔者也曾查阅《过去现在因果经》,确无此语。
②a此语出自《大般涅槃经后分卷上·遗教品第一》。
①b此观点引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部分。
标签:太平广记论文; 杜子春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醒世姻缘传论文; 红楼梦论文; 古今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金瓶梅论文; 镜花缘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