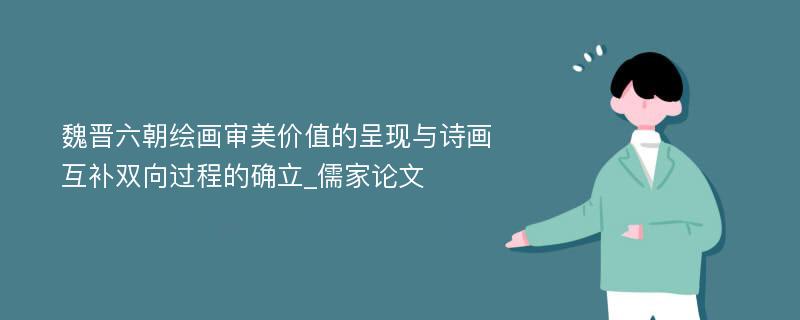
魏晋六朝绘画美学价值的呈现与诗画互补之双向过程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美学论文,双向论文,过程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425(2014)11-0144-08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4.11.026 在汉代的经学化过程中,《诗》的经学化使诗性的功能价值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高度推崇,绘画则在诗性的光亮之下,通过诗性化的单向过程探索自身的发展。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立象尽意”的观念的强化,艺术家从《周易》中找到了提升绘画、确立其独特个性的门径。这一过程的可能性缘于绘画与《易》之卦象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家族相似”:其一,在视觉感受方面同构:“《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系辞下》)。其二,在摹仿对象方面同构:“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周易·系辞上》)。其三,在认识目的方面同构:“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绘画凭借自己与《周易》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发现了自身类“经学”功能价值,开始了自身的经学化运动,并与自身的道化、圣化过程相呼应,“象”的功能价值空前彰显。于是,绘画在寻求独立价值的过程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经学化价值和“自治”领地,其独特价值在于绘画之视觉形象的存在方式是圣贤体道的重要途径;另外,诗自身载体之缺陷,亦构成了需要绘画之视觉性介入其中的召唤结构。绘画也开始为诗立法,绘画性亦成为诗歌之范。于是,面临“言”的困境的诗以绘画的视觉性“象”为范,自觉地走上了诗的“象”化历程。至此,诗与绘画在艺术行为中开始了取长补短的双向运动,互为准的、互为补充。从这一时期开始,诗画互补观念由过去的绘画“诗化”的单向过程,进入诗画互为标准的双向过程。 一、魏晋时期语言表意问题的尖锐使得“象”的介入成为必然 早在先秦时期,“言”所存在的问题就被人们意识到了。《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的开山纲领之后,“言”作为表达方式,被人们高度肯定和重视。儒家对言的态度颇具有辩证色彩,他们既高扬“言”的肯定性价值又勇于正视“言”自身之不足。孔子很重视言的作用。他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孔子还以《诗》为言说的标准:“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过,孔子并未将言的价值绝对化。如在《阳货》篇中,孔子就把“言”视之为疣物:“‘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焉?’”孟子也十分重视“言”,并对“言”作了些规定。他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孟子·尽心章句上》)但孟子认为在感化人心方面“言”不如“形”“声”“色”等影响深刻。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认为原因在于:“形、色,天性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在孟子看来以视觉、听觉、味觉等为感知的存在形式符合人的本性,也容易打动人。正因为如此,人们感受事物很容易有表无里,不能做到内外统一。所以孟子说“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意思是“圣人内外文明,然后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焦循《孟子·正义下》),只有圣人才能正确地对待外在的形式。这亦体现了孟子对“形”“色”等感官感受形式的偏见,当时人们对绘画的偏见大抵与此有关。荀子特别强调“言”对君子的重要性。《非相篇》云:“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因此,荀子要求君子“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正名》)。另一面荀子也注意到“名”(言)与“实”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辩说,以便“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正名》)。儒家关于“言”局限性的认识,在老庄思想中亦具有互文性。《老子》认为最高的“道”是“绳绳不可名”的,它肯定的是“无名之朴”,进而对“言”提出了“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否定性论断。《庄子·知北游》亦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不难看出,道家对“言”的否定乃是基于“言”对“无为”思想的背离。除儒、道两家外,先秦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也有“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命题,其意思是世上万物没有不是由概念来反映的,但是反映物的概念并不等同于概念所反映、指称的事物。公孙龙的论题虽然涉及的是概念的局限性,但在本质上是指言的局限性。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言”(名)与“实”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言”与心之间的矛盾。扬雄《问神》就讲到了“言不能达其心”的问题。 面对“言”的弊端,人们开始注重“形”“象”对言的补充和修正,甚至从心性的角度探讨形与象存在的必要性。《韩非子·扬权》就提出了这种解决办法:“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用,用其所生。”《礼记·乐记》“形”“象”是心性的外化,因此特别强调艺术是诉诸于视听感觉将情感形象化的活动。《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可见,声是情感的形式化。《乐记》认为人的各种情感都是通过“形”体现出来:“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乐记》也强调了人对“象”“形”之修饰作用的倚重:“乐者,心之动也。声音,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史记·乐书》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周易》之《易传》在言与象的比较中肯定了“象”存在的价值意义:《系辞上》引孔子言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儒家这种对“象”意义的启蒙式的认可实际上赋予了“视觉性”参与表意活动的合法性,为后来人们利用“易象”提升绘画的社会价值设下了伏笔。重视视觉性是世界文化的共同倾向,大约在相同时期古希腊哲学也奠定了“视觉及视觉隐喻在古希腊世界中的核心地位”[1]。不过古希腊哲学不是把语言和视觉置入一种矛盾的关系中,也不是从具有主观性的“意”的角度突出视觉性的价值,而是从求真的维度彰显视觉性的意义。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就把视觉置于诸感觉中的优先地位。他说:“能使我们认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1]与古希腊不同,先秦时期人们对“象”的重视却是基于“言”对“意”的非圆满性表达。随着《周易》在汉代被列入官方经典,“象”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是在艺术思想领域人们还不能自觉意识《周易》之“象”与绘画之间的互文性价值对于绘画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观念上自然不能完成由“象”到画的思维转换和认识上的飞跃。一方面,《易》之“象”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很重要,但是儒家对卦象所包含的吉凶意义已经不予以重视,“孔子不再把《周易》看成占筮之书,而把它看成修身寡过之书”[2]168。孔子把《周易》当作哲学书看待的价值取向影响深远,如《荀子·大略》就有“善为《易》者不占”的评价。先秦两汉时期随着解《易》之“十翼”《易传》的产生,“实现了《周易》自身从占筮之书到哲学书的转变”[3]81。正是因为《易传》“改造了《周易》,使它成为儒家基本和最高的哲学典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官方选中和认可的六经之首”[3]158,意味着当时以“卦象”为表征形式的“象”实际上被“悬置”,处于依附于“言”的从属地位。可见,“言”之强势依然存在,要完成这种转换仍需强心猛药动摇其权威地位,而佛教的介入恰恰充当了时代所需的这剂猛药。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标志佛教开始传入汉地[4]1。佛教在其经义中鲜明地传达出对“言”的否定思想。东汉支谶翻译的佛经《般若道行经》所阐述的核心思想是般若空观。“空”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即实相,实相也即无相,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最高真理,它不能用一般名词概念加以正面表述,只可予以直观体悟[4]29。《维摩诘所说经》把佛之法门与“言”对立:“乃至无有无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僧肇《注维摩诘经》亦云:“夫文字之作,生于惑取;法无可取,则文相自离。虚妄假言,智者不着,无有文字,是则解脱。”[4]37在汉末以后的动荡黑暗的社会现实中,佛教无疑是安顿人们心灵的一剂良药,然而其对由“诗言志”到汉代经学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言”之权威性釜底抽薪式的彻底否定使“言”“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阶段,人们再次将注意力投向于“象”。 不过需要阐明的是佛教与道家一样崇尚的是“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牟子《理惑论》)的道,但佛教又不是绝对地排斥感性可以把握的“形”“象”,使之与道割裂开来。如东汉时的月支人支娄迦谶的《道行经》云:“般若者……入于一切有形,亦入一切无形。”[5]359佛教对“形”“象”保持一种既“不为世染”又“不为寂滞”的权变心态。这种态度在魏晋六朝时期依然盛行。僧肇《注维摩诘经卷一》云:“形敬不足以写心”,这里心就是道。尽管如此,但是佛禅并不把形而上的“道”与有限的“形”“象”割裂开来,认为有限的“形”“象”产生于寂寥虚旷、恍惚窈冥的道。如《涅槃无名论》说“法身无象,应物而形”,所谓法身就是佛道。虽然道隐无形,但是道却能顺应万物而显现其形。《注维摩诘经卷二》也以水设喻,阐明这个道理:“外水善利万形,方圆随物,洿隆异适,而体无定。”《涅槃无名论》说:“夫至人空洞无象,而万物无非我造。”显然僧肇所倡导的“形”明显具有二重性:一是应物而形,即道有形;二是万物我造,形由心生,即道无形。在现实实践中,佛教对“形”“象”的肯定态度,主要体现在利用其将宗教观念视觉化,并将这种方式视为礼佛成佛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妙法莲华经方便品》就如是云:“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像,刻雕成众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鋀石赤白铜、白镴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严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 佛教对“言”“象”所持的不同态度使得“言”“象”之间长久积淀下来的纠结关系成了魏晋时期人们不得不正视和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佛教对“言”的彻底性否定,使得对待“言”“象”的关系问题不只是在达意与否的本土文化内部探讨,而且衍变为本土文化(主要是儒文化)与异文化(佛教文化)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意识冲突。一方面人们对“言”持有难以释怀的敬崇情结;另一方面“象”确实可以解决“言”所不能完成的表达窘境,人们又不得不面对“象”表达方式日趋盛行的时代风尚。这种情势之下,人们把“言”“象”之间的问题作了中庸式的调和处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对“言”“象”关系的探讨: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显然,王弼不再把“言”与“象”看作两极对立的言说载体,调和了“言”与“象”的冲突性。所谓“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表明了“言”与“象”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其一,两者具有统一性,“言”与“象”相互依存:一方面“象”是“言”的母体,如“言生于象”;另一方面“象”又离不开“言”,如“尽象莫若言”“寻言以观象”“象以言著”。其二,虽然“言”是明“象”的手段,但是只有对“言”进行扬弃,才能达到得“象”之目的。故而两者又具有对立性:如“忘言者,乃得象者也。”王弼在一定限度内既迎合了时代对“象”追捧的整体风气,又维护了儒家所建构的“言”的权威性。这样王弼不仅为“言”的表达方式和“象”的表达方式都提供了合理性,而且为它们的相互补充也提供了可能性。从《易传》可以看出在对待“言”“象”的关系上,人们所注重的是“象”对“言”的补充作用,而“言”对于“象”的意义却鲜有考量;佛教又欲把传统“唯我独尊”的“言”置于死地。王弼纠正了历史上人们对“言”“象”关系或左或右的偏颇行为,将“言”“象”置于互为补充的统一关系中,为诗画互补观念的确立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王弼为诗画互补观念的生成作出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直接完成了由“卦象”到“画”的推演。他说:“立象以尽意,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可见,就以“尽意”为旨归的诗画创作来说,王弼已经在无意中为人们开启了诗画互补的言说模式。 二、魏晋以来人们对视觉感受的重视使“象”的个性价值在审美活动中被自觉认识 受玄学理论《周易》影响,人们效法圣人之重“观”行为,普遍推崇视觉感受在审美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周易·系辞下》描述了圣人体察万物的具体行动:“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无疑,“观”是圣人“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重要手段。于是,圣人重“观”的行为被人们有意识地推演到人物品藻和文艺实践活动中。在人物品藻中人们往往用与“看”相关的动词引出形象化的内容,这在《世说新语》中十分常见,其中“目”的使用最为频繁,如裴令公目夏侯太初、庾子嵩目和峤、王戎目阮文业、王平子目太尉、时人目王右军等等,不可尽列。 在具体的文艺实践中感官动词诸如“观”“察”“望”“视”“见”“鉴”“顾”“眄”“瞻”“眺”“览”等亦被频频使用: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操《步出夏门行》)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曹植《远游篇》) 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曹植《杂诗》)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阮籍《詠怀》) 伫立望故乡,顾影悽自怜。(陆机《赴洛阳道中作》) 伫中区以玄览,瞻万物而思纷。(陆机《文赋》)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左思《詠史》)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刘琨《扶风歌》)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 倾耳聆波澜,巨木跳岖嶔。(谢灵运《登池上楼》)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嵇康《赠秀才入军》)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王羲之《兰亭集序》)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刘勰《文心雕龙》) 上述诸例表明:对视觉感受的重视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时尚。当然,人们对视觉感受情有独钟亦与佛教影响分不开,从当时佛教经卷中我们可以感受其对眼睛的重视。僧肇《注维摩诘经卷第一》云:“面为身之上,目为面之标,故叹形之始于目也;复次佛以慈眼等视众生,重其等故叹之。”僧肇以更世俗化的方式解释了这段话:“五情百骸目为最长,瞻颜而作故先赞目也。”又云:“心静则目明,故举心以证目;复次目为形最,心为最本,将叹德故美其心也。”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刘勰就以目、形之间的关系类比心与理的关系。他说:“心目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文心雕龙·知音》)悬置心、理之关系不谈,从佛教那里我们分明见到了眼睛对于形的重要性以及眼睛对于佛之无差别“等视众生”的重要性。在佛教盛行的时代人们必然把这种“重目”思想推演到社会生活及文艺领域中,并最终演变成对视觉感受的结果——“形”“象”的重视,顾恺之便是典型代表。《世说新语·巧艺》《晋书·顾恺之传》《历代名画记》等都记载了顾恺之艺术活动中重视眼睛的经典言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人们对以“形”“象”为载体的视觉感受的强烈冲动亦突出表现在当时的文艺理论中。陆机《文赋》把它概括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甚至不惜“离方遁圆”,目的就是为了“穷形尽相”。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概括了当时人们重象贵形的时代风貌。他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他总结了诗人状物的具体方法:“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鸣。”刘勰认为文艺创作之所以要以“形”“象”为关捩,目的是“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 当然,人们并不满足于“形”“象”的感性感受,基于《周易》卦象明于天道的“形而上”特性,亦将“形”“象”与道相联系,推演并生成“形”“象”乃道之文的普遍性的观点。如宗炳《画山水序》就有“山水以形媚道”的思想。刘勰直接将天地山川所呈现的“形”“象”视之为道的显现形式。如《文心雕龙·原道》云:“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在《神思》篇刘勰提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的见解,神的作用是什么呢?依据宗炳《画山水序》“圣人以神法道”的观点,可以得出“道用象通”的观点。从刘勰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要用“象”去体“道”,是因为人的情感的作用,即刘勰所说的“情变所孕”。可见,在文艺中所探讨的“道”与“形”“象”之间的关系又不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不离开人们的情感需求,达到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平衡。这与《系辞上》所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的主张是一致的,因为“精神并不是作为一种意义,不是在于作为内部的层面,而是在于作为现实的‘真实的东西’”[6]1193。凭借建立“形”“象”与“道”之间的紧密联系,再加之佛教“真境无言,凡有言论皆是虚戏”(《注维摩诘经卷二》)之影响,“形”“象”在这一时期最终获得了自身独特价值——视觉性言说的可能性、必然性。 三、基于视觉感受的共通性,画家们自觉地完成由“形”“象”到画的认识转换 前面我们讲过王弼为诗画互补观念的生成作出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直接完成了由“卦象”到“画”的推演。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把广义的“形”“象”视之为绘画的观念要追溯到汉代,甚至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在《尔雅》《释名》等著述中已经出现把绘画与“形”“象”等同起来的观念意识。如《尔雅》云:“画,形也。”《释名》云:“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魏晋六朝时期艺术家们将“形”“象”与画视之为“不二法门”的观念颇为盛行。如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的“以形写神”,宗炳《画山水序》的“画象布色”“以形写形”,王微《叙画》的“本乎形者融灵而动”,谢赫《古画品录序》的“应物象形”等表述都把画直接解读为“形”“象”的言说。其历史要义并不体现于解读行为本身,而体现于解读行为的参与者们的画家身份,他们的参与意味着绘画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独特性把握的自觉觉醒;意味着画家们在认识上完成由“形”“象”到画的转化。他们的这种特殊身份以及将“形”“象”推演到画的普遍意识是王弼及其之前的人们所不具备的,他们以画家的视角通过与语言文字之比较建构其独特性。如南朝姚最《叙画品并序》说:“若永寻《河书》,则图在书前;取譬《连山》,则言由象著。” 不仅如此,画家们还从多个角度去探讨绘画的特色:一是绘画的明神、法道作用。宗炳认为:“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画山水序》)。因此,绘画之形是道、神、理之载体,通过“味像”就能够达到明神、法道之目的。二是绘画的娱乐作用。顾恺之是最早从审美功能的角度言说绘画愉悦作用的画家,他的思想已经开始突破绘画传统的“言志”功能,为人们追求艺术的娱乐功能奠定了思想基础。其《论画》就注意到绘画创作的乐趣,他论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注意到恰当的构思方法所带来的快感。如迁想妙得的“妙”就体现了顺利完成构思所引起的心灵愉悦;第二,注意到创作中目、手、心三者相应所引起的快感。所谓“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就是此意;第三,注意到艺术创作独特的风格和个性给人带来的快适,如他说《孙武》“骨趣甚奇”,《醉客》“蔺生变趣,佳作者矣”,《嵇轻车诗》“林木雍容调畅,亦有天趣”。宗炳则是通过“画象布色,构兹云岭”(《画山水序》)的方式营造出“峰岫嶢嶷,云林森渺”(《画山水序》)的山水景色,在闲居气爽之时“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画山水序》)。王微更强调那种运诸手掌、有如神助的创作快感,远远胜过“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单从审美价值本身考量的话,后来的宗炳、王微对艺术娱乐性的探讨反倒不如顾恺之把握得细腻深刻,因为,宗、王二人多从某个角度强调艺术的娱乐功能,对艺术本身之特性的把握尚欠全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宗、王二人在建构艺术娱乐功能方面的卓越贡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记录了南朝贵族追求绘画娱乐作用的盛况:桓大司马“每请长康与羊欣论书画,竞夕忘疲”;南齐高帝“听政之余,旦夕披玩”;梁武帝“尤加宝异,仍更搜葺”;元帝“雅有才艺,自善丹青,古之珍奇,充牣内府”。这些记载恰恰体现了理论家们对绘画娱乐功能的准确总结。当然,追求娱乐性并不是当时艺术的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神体道,正所谓游戏通神,游戏只是一种姿态,与儒家所强调的“游于艺”是相通的。譬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玩玉,其实玩就是一种品格、一种高尚的人格追求。三是绘画的寄托心思作用。宗炳《画山水序》认为绘画首先是在“应目会心”的构思过程中形成“理”,“理”的标准是“目亦同应,心亦俱会”,也即是说,“理”应具有感官感受的普遍性,能引起“共鸣”的情感体验,这样才能“理入影迹,诚能妙写”,即将“理”融进绘画的形象之中,创作出好的作品。在宗炳那里我们依稀感受到绘画作品与心之间的密切联系,它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摹仿关系。在探讨心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方面,王微较宗炳有更深入的认识,王微把作品的生动变化归因于心的作用。他说:“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着心也。”(《叙画》)不仅如此,王微还强调了艺术创作物感的作用,在物的感召之下作者之心思便会飞扬浩荡,恰如他所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叙画》),其创作就有如神助。实际上王微强调了真挚的情感在绘画中的重要作用,它不仅仅是“独运指掌”的纯粹技法。宗炳、王微等人对心与绘画形象之间关系探讨的行为亦是这个时代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刘勰的“意象”范畴正是在这种情境之下诞生的。 四、绘画凭借“形”“象”的道化、圣化、经学化以及感神之功能获得自身的升华 当人们在认识上把“形”“象”作为绘画视觉性呈现的主要特征,基于“形”“象”作为“道之文”的共识,进而顺理成章把绘画列入“道之文”的范畴,这实际上开始了绘画的道化、圣化、经学化的历程,有意识地挖掘、提高绘画的社会价值。当然追求道化、圣化、经学化的升华,不独绘画才有,它是那个时代文艺领域的整体风尚和普遍现象,人们往往喜欢赋予文艺形而上的功能和特征。如曹丕《典论论文》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陆机把绘画称之为“美大业之馨香”(《历代名画记》)。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文之为德者大矣,与天地并生”。不仅如此,刘勰还详细论述了文章“原道”“宗经”“征圣”的功能特点,并将“道”“圣”“经(文)”之间的关系阐述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因此,绘画提升自己作为“文”的价值,亦是时代潮流使然。 绘画大抵从“道”“圣”“经”及“感神”四个方面建构自身价值,通过道化、圣化、经学化的升华,获得自身的荣光。其一,绘画借助“形”“象”言说的内容(道和自然)将绘画道化。对山水的重视是中国文人由来已久的传统。对于道家来说,自然万物本身就是“德性”的体现,因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老子把它的特性概括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的“玄德”。老子对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礼记·中庸》对山水的德性的肯定是基于对山水利物特征的赞美,“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山水利物的特征本身就是德性的体现,这与《周易》的观念是一致的。《周易·乾卦·文言》云:“利物足以和义。”《周易·坤卦·象》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把自然看成道德的象征的观念开启了人们对山水的审美情怀,引导人们用肯定的态度去关照山水本身的规定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山水的态度正是这种发展要求的体现。于是,与人们主观心灵相契合的自然界便理所当然进入人的视界,自然山水本身所具备的自然而然的特点更受人们崇尚。如“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左思《招隐二首》),“此地有崇山峻岭,茂竹修林,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王羲之《兰亭集序》),“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人们改变过去神话象征时代“人是自然的标准”的高傲态度,他们的自然认识观亦由自然的人化转变为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赋予人的多样性中去……以取得诗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规范的对生存的自由享受”[7]52。人的自然化为人赋予了自然的规定性,自然成了人的道德和审美准则。《世说新语》描述人的句子诸如“濯濯如春月柳”“森森如千丈松”等都是崇尚自然、以自然为法的体现。宗炳《画山水序》有“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之感慨,这已然表明:“一方面,宇宙之道已经扩渗到审美领域之中,另一面,审美领域已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8]100其二,借助“形”“象”言说的参与者(圣人)将绘画圣化。超越个体小我、抒发圣贤情怀亦是那个时代文艺的形而上特征之一。曹操《短歌行》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丕《短歌行》有“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流露出“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贤人情结。这种圣人情怀反映到文艺理论中就体现为对师圣、征圣行为的肯定性言说。刘勰《文心雕龙·征圣》篇详切地阐述了师法圣人的必要性:一是圣人可以“鉴周日月,妙极机神”;二是圣贤文章“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所以刘勰要求著文应当以圣人为师,征圣立言。他说“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征圣》)。宗炳《画山水序》就明确强调了绘画作为圣贤明道方式的重要性。他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其三,借助传统经言利用“形”“象”言说方式将绘画类经学化。绘画价值的提升还在于它自身的经学化。绘画之所以要追求经学化的价值,我们从《文心雕龙》便可以找到答案,其《宗经》篇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即文章至骨髓也。”绘画的经学化是指艺术家们通过发掘绘画与作为“文”的经学著作《诗经》《周易》在功能价值方面所呈现的共通性,以此获得经学般的被广泛认可的社会价值。绘画的经学化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一是继续两汉以来的“诗化”过程,人们继续以诗为标准改造绘画。如陆机说:“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历代名画记》)二是绘画自身的经学化,其具体策略就是借助经书《周易》利用“形”“象”言说的价值提升自身的价值。曹植《画赞序》云:“上形太极混元之前,却列将来未萌之事”,把绘画等同于《周易》于卦象的作用。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把易象视作文艺之滥觞:“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意象惟先。”王微在《叙画》说:“以图画非止艺行,诚当与易象同体。”王微将绘画与《周易》相提并论,就是借重经学《周易》提升绘画的功能地位,使其获得经学化的价值。这里需要进一步阐释的是王微是否具有儒家情结呢?答案是肯定的。其一,“以图画非止艺行,诚当与易象同体”句出自颜延之给王微的书信中[9]69,也就是说王微是借重颜延之的观点提升绘画的功能价值,而颜延之与王微是同乡,曾官金紫光禄大夫,其思想为儒家传统。其二,王微虽然素无官情,总有“尘秽难堪”[10]之念并耿耿于尘外之适,主要原因是其身体长期为疾病所困。如他所说“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难复支振,民生安乐之事,心死久矣”[10],其思想内核仍然属于儒家体系。首先他曾举秀才,父辈及他本人都曾为官朝廷;其次多用儒家价值考量人事。譬如用人,他引《尚书》说“任官为贤才”[10];为弟王僧谦所写的告灵书中他评价说“弟为志,奉亲孝,事兄顺,虽僮仆无所叱咄,可谓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10];告灵书中还有其他表述如“‘殷太妃感柏舟之节’、‘仆射笃顺’、‘范夫人知礼’”[10]等都流露其深厚的儒家情怀。因此,上述材料已经赋予了王微借用“易象”所蕴含的儒学价值去观照、提升绘画社会价值的可能性、合法性。 当然,画家们在注重绘画的道化、圣化、经学化的同时亦强调绘画的感神作用,如宗炳特别强调绘画“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的作用;王微注重发挥绘画创作过程中的“神思”的功能。同时感神之心灵又是轻松愉悦的,故而宗炳有“畅神”之论,王微认为“神思”的快感远远超过“金石之乐”。这与当时佛教的影响分不开,僧肇《注维摩诘经卷》中就有“游戏通神”的观点。佛教认为万事万物尽管在现象上千差万别,但从佛性上看都是相同的,如果拘泥于现象的差别,就会给人带来痛苦,就是入迷。佛教注重宣扬佛的境界,它是指佛在“智慧”“功德”“神通”等方面所达到的最高精神层面。获得佛的境界之后,就会游戏神通、心恒快乐,自在游戏,这种境界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悟”化后的达观状态[11]。“游戏”本身意味着主体的愉悦自由性,这与艺术行为主体之心性具有一致性,宗炳把这种愉悦自由性概括为“畅”。与严肃的生活相比,艺术就是游戏。不过艺术又不仅仅是游戏,还有“感神”,并达到以神法道的目的。当代画家吴冠中曾说“艺术是苦难,它要掉眼泪,它要哭”[12]。吴老之所以赋予艺术以悲怆性是因为当代的人们往往把艺术与严肃生活等同起来,一旦艺术要担荷生活物欲之重负,卷入艺术活动中的人们又怎么可能具有古人那种游戏性的达观态度呢? 五、结束语 绘画在道化、圣化、经学化演进中,再加之它拥有语言所无可比拟的视觉形象性,于是成为了诗所效法的典范。刘勰《文心雕龙》就无数次以画作为诗赋创作之准的:“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诠赋》),“品物毕图”(《诠赋》),“雕画奇辞”(《风骨》),“写气图貌”(《物色》),“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辞》),“图状山川,影写云物”(《比兴》),“声画照精,墨彩腾奋”(《练字》)等。刘勰在文艺理论中突出绘画性对诗赋创作的影响作用的事实,至少说明绘画在当时已经为诗所效法。诗画互补观念在魏晋六朝由两汉的单向运动衍变为诗画互为标准的双向运动,这标志着诗画之间的“取长补短”观念事实上已经形成,并最终调解了魏晋玄学时期言与象在表意上的冲突性,言、象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倾听、交互凝视的对话关系。虽然魏晋六朝时期已经形成了诗、画相互言说的对话现象,但是诗画互补观念还没有彻底演化为一条引领人们进行文艺创作实践的普遍规律,也即是说诗画互补观念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哲学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最终在唐宋时期开花结果。 引用格式:王赠怡.魏晋六朝绘画美学价值的呈现与诗画互补之双向过程的确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11):144-151. WANG Zeng-yi.On Presentation of Aesthetic Value of Painting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 and Establishment of Two-way Process of Painting-and-Poetry Complementarity[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4(11):144-151.标签:儒家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叙画论文; 魏晋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文化论文; 六朝论文; 历代名画记论文; 读书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画山水序论文; 易经论文; 乐记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佛教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