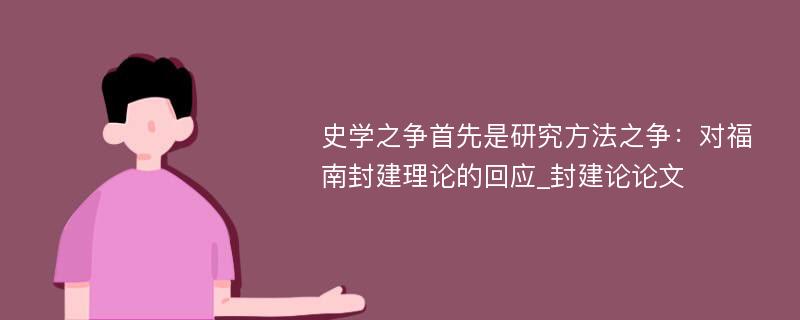
史学问题之争首先是研究方法之争——对《扶南封建论》的答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史学论文,封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机会从《东南亚》杂志上读到贺圣达同志论述早期东南亚国家社会性质的文章①,不禁勾起我六年以前读较早一篇关于扶南封建论的论文②时的回忆,记得那时也是很为欣喜的,因为关于扶南的社会性质,除奴隶社会说之外,终有不同意见发表了,而且以其“封建论”针锋相对。学术研究就是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发展的。因此,这无疑是一件极好的事。
我是扶南奴隶制说的主张者之一,与其他持相同意见的同行一起形成了这种学术观点。我们与扶南封建论者之所以存在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歧,我以为,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即:研究方法的不同,对马列经典作家理论理解的差异和对具体历史问题认识分析和结论的不一样。欲展开讨论,势必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我意从每一个方面写成一篇文章,申述我的观点,进行我的答辩。
先说研究方法。本文就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
众所周知,科学的方法会引导出正确的结论,非科学的方法难免不使人陷入谬误,即使是所依据的材料相同和所处的环境相似。在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中,我想从研究“封建论”者的研究方法入手,引出我赞成并运用的研究方法,将两种方法加以比较,让人们判断:哪种方法更好些,更科学些,有采用价值。《扶南封建论》是一篇全面论述这种观点的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该文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有代表性的。因此,我拟对该文所用方法进行剖析,以找到比较的对象。
《扶南封建论》的论者为了使该“论”立起来,依次采取了三种方法:一是全面否定别人——奴隶制说;二是“逆向”证明自己,在肯定真腊——柬埔寨社会和东南亚其它国家是封建社会的前提下,“逆向”证明扶南也是封建社会;三是以面概点,树立自己的观点。整个东南亚地区具有继原始社会之后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阶段便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阶段的特点,扶南自然也应具有这个特点。如此一来,扶南封建论似乎就成立了。依我看,问题首先就出在研究方法上面。下面容我依次一一作出分析和评述。
否定别人并不等于树立起自己
用否定别人观点来树立自己观点的做法,在学术界似乎司空见惯。你既然全面否定了别人,一定要拿出比别人更高明的东西,方能使被否定者心服,也才能使自己站得住。既然别人的观点一无是处(“封建论”一文确是如此),你就要充分讲出自己处处是的站得住的理由,要不,何以能否定别人呢?既要在否定别人上做文章,又要在树立自己上下功夫,“封建论”者承担着双重任务,比着正面展开论述自己观点的一重任务来,显得更为繁重、艰巨、困难!
“封建论”者对别人的否定是极为彻底的。在点名介绍我的学术观点时,接连使用的是:“这个结论只能是一种推论”,“这个结论也是有问题的”,“这种解释和比附都是没有道理的”。从“推论”到“有问题”再到“没有道理”,步步升级,否定到顶。如果与对程爱勤同志的否定相比,我还是幸运的,尚可聊以自慰。《扶南封建论》一文发表后,程爱勤同志写出了《〈扶南封建论〉质疑》一文③,就扶南的社会性质“与何平同志商榷”。这是一篇从正面展开论述自己观点的文章。一年以后,何平同志以《再论扶南的社会性质与柬埔寨的奴隶制问题》一文作答④。在他读程文后“觉得该文牵强附会之处颇多,观点和研究方法都很成问题,故特撰此文,针对〈质疑〉一文,就扶南的社会性质和柬埔寨的奴隶制问题作一些补充论述,希望能够解〈质疑〉作者之疑。”在文章最后,是结论式的训诫:“至此,但愿〈质疑〉作者的疑会少了些。如果还有许多疑的话,那就请从具体史料入手,实事求是地重新再把这个问题琢磨琢磨。更多的史料恐一时也难找到,只需把我提到而程爱勤同志‘还没有发现’的这些资料找来看看,或许就不会再有这许多‘疑’了。”这里摘引的只是文章头尾的话,文内的类似语气,恐怕就不是一、两处了。
如果你能否定得了,别人倒也无话可说。而问题在于,别人实在大有话讲,而且还可能讲出点道理。由于材料稀少,探讨扶南的社会性质,本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除非你占有比别人更多的也更为可靠的材料,怎么能以1+1=2这样肯定的口气去否定别人肯定自己呢?即使把程爱勤同志还“没有发现”而何平同志已提到的那些材料找来看了,似也不能以如此口气作出评判。既然“更多的史料恐一时也难找到”,我们不能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严肃地进行学术探讨。下边我作的答辩,拟取此态度。
关于“推论”。“封建论”者为了说明我是在“推论”,竟然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摘引和概括我的观点。在说我在一系列文章中肯定地认为扶南社会是奴隶社会之后写道:“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我国史书《南齐书·扶南传》中的一条记载:扶南国王范蔓曾‘攻略傍邑不宾之民为奴婢’。据此,陈显泗同志认为,‘在他把周围邻国征服之后,把俘虏变为奴隶,其数必不会少,也必然会把相当一部分投入生产使用’。从而断定,扶南社会中的主要生产者就是奴隶……仅凭这一条唯一的有关掠奴的记载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故而“这个结论只能是一种推论”。我读后甚为惊讶!这段话本身便充满着推论,却以推论去斥别人为“推论”。不信,请看:
——所谓“其最主要的依据”,“仅凭这一条唯一的……记载”云云完全是“封建论”者给人强加上的。我论述扶南的社会性质是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的,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扶南的“邑”、王位继承制、租税合一等。经过多角度的综合论证,尔后得出扶南是奴隶社会的结论。如此多侧面的论述难道仅凭唯一的一条材料么?事实上,仅凭唯一的一条记载是不可能做出那么多文章来的。
——“从而断定,扶南社会中的主要生产者就是奴隶”云云是“封建论”者自己的“断定”。“封建论”者前引的那段文字出自《扶南古史杂考》一文,在该文第四部分“邑辨”内第四点探讨的是“在‘邑’内,情形又如何?特别是从事劳动的劳动者是什么身份的人呢?我的回答是:“虽然我们对扶南‘邑’的内部情形特别是其中劳动者的身份,由于史书记载不很明确,知之甚少,但亦不是没有线索可寻。一些材料直接或间接证实,在扶南时期,奴隶是比较多地存在的。”直接或间接的材料举出有四条:“攻略傍邑不宾之民为奴婢”、昆仑奴在东南亚的广泛流行(扶南属昆仑,昆仑奴里含有扶南奴)、《真腊风土记》关于奴婢的记载、陈序经的看法。仅仅作为“线索”的这些材料所要证实的是扶南时期奴隶是比较多地存在的,而且是正在进行学术研讨,讨论“邑”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跟扶南的社会性质直接相连,更没有什么“断定”的话。如能查阅《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一书的第309页,真象即可大白。
——“村社存在于扶南时代是毫无疑问的”。在替别人作出种种推论后,“封建论”者便开始了自己关于封建论的推论。村社的存在被“封建论”者视为支持“封建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如果说奴隶制说还有一条唯一的记载作依据的话,不知“封建论”者能否找出哪怕是一条可靠的材料来证明村社的存在?“封建论”者对扶南的村社作了非常理想化的描述,但依据何在呢?且看他自己的回答:“虽然有关扶南的记载并没有提到村社,但从后来真腊、柬埔寨时代的情况和东南亚各国以及许多东方或‘亚细亚’社会的情况来看,村社存在于扶南时代是毫无疑问的。”⑤原来,扶南的村社是从后来和外国“看”出来的!这不是“推论”又是什么?
关于“也是有问题的”。这是针对我关于扶南“邑”的论述而引发出的,采用的是偷换命题的手法。“封建论”者是这样把问题引出的:“既然认为扶南的‘邑’是中国人用商、周时代那种‘邑’的概念去描写的扶南的历史现象,就能说明它属于奴隶制的范畴。那么,中国史书中提到的扶南社会里的那种‘奴婢’又何以不是中国人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那种奴婢的概念去描写的历史现象呢?何以不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呢?何以能够用来说明扶南是奴隶社会呢?”“封建论”者指我对扶南“邑”的论述有问题,按理就应指明其问题所在,提出自己正确的看法,无论怎样,都应围绕着“邑”展开。事实上并非如此。“封建论”者突然拿出“奴婢”问题,以此去否定我对“邑”的意见。其实这是两个问题。我有专文讲“邑”,为讲透“邑”,暂不涉及其它问题,如奴婢。对于奴婢,我会另有论述。我的看法正确与否另当别论,在这里,单就“封建论”者使用的方法而言就有可供商榷之处。偷换命题,避开讨论主题,引出未讨论的题目,并按照自己对该问题的解释去否定本该展开讨论的问题,于是乎便作出了我对“邑”的论述⑥“也是有问题的”的宣判。此种做法,似不可取。
关于“都是没有道理的”。我对扶南“贡赋”的论述,招致“没有道理的否定。那么,是谁又是怎样没有道理呢?我对“贡赋”说明是完整的,它的表述见之于专论此问题的论文《从租税合一论及古代扶南的社会性质》里。对我的表述,“封建论”者采取随意分割,任其取舍的办法,以达其否定别人的目的。此外不妨把这段表述的话引述出来,以让人们鉴别:“在中国历史上,‘贡赋’亦称‘贡税’,它是‘土贡’和‘赋税’的合称。所谓‘土贡’就是臣属或蕃属向君主的进献,进献的东西包括土产、珍宝和其它财物,或者说,是臣属或各地诸侯向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的进贡;而赋税则是我国历代政府的一种强制征课。究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以前的商周。到了春秋,情况便有所不同,‘赋’和‘税’各有所指。君主向臣属本身征收的军役和军用品称‘赋’,‘税’则是对臣属土地征收的财物。后来赋、税逐渐混合。……可见,在‘贡赋’里面,是包括我们所说的租税和税的。”⑥其它各处包括“封建论”者点出的另三篇文章在谈及“贡赋”时,其含义和表述都是一样的,只是根据文章论述问题的需要,有所侧重和详略罢了。《从租税合一论及古代扶南的社会性质》一文较详,对“贡赋”的解释除各文都有的内容外,特别指明了“赋税”是我国历代政府的一种强制征课及“贡赋”包括了我们所说的租和税两点。《扶南的“邑”非封建的“采邑”》和《扶南古史杂考》两文对“贡赋”的解释除未点明上述两点外,其基本内容与前文一样。《关于古代扶南社会性质的探讨》一文叙述最简,但有“地租和税是合并在一起的”的话。即使是特别指明的那两点,也只是对基本内容的概括和引申,不是另外不同的解释。所谓“基本内容”,即“贡赋”是“土贡”和“赋税”的合称。“土贡”是臣属向君主进贡的土产、珍宝和财物;赋税是我国历代政府的一种强制征课,显系对“赋税”追本溯源的一种概括。概括之后则加以具体说明——为什么是历代政府的一种强制征课;贡赋包括了租和税,是在对“土贡”和“赋税”分别进行说明之后的引申的概括。这些都不违“基本内容”,而是对它的阐发。如若不信,请翻阅上述四篇文章,仔细加以对照。可不知为什么“封建论”者却要将这个完整的表述加以分割,而且按其需要,立下双重标准加以取舍?
“封建论”者非说我对“贡赋”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实是他自己强行作的分割。他把我对“土贡”的解释(即“贡赋”释义的前半段)称作一种解释,说“不知为什么”我把“‘贡赋’又解释为臣属向君主的一种进献”?他在把我讲的“土贡”改为“贡赋”之后,大加鞭鞑,斥之为“没有道理”。接着,他又把我对“赋税”的解释(即“贡赋”释义的后半段)算作对“贡赋”的另一种解释,即“‘贡赋’是一种‘强制的征课’”,“包括我们所说的租和税”,并加以赞扬说“(这种)解释才是正确的”。为什么要赞扬呢?因为我说的租税合一的剥削方式,恰恰说明“是一种封建社会”。在这里,他又把我讲的“赋税”改为“贡赋”,而且把“我国历代政府”几个字删去,然后纳入他需要的轨道。殊不知这一来,我对“贡赋”的解释经一番削足适履的工夫之后已经面目全非了。经过肢解,同样是我的解释,一半是“没有道理的”,另一半又是“正确的”,按什么标准呢?看来是双重?需要的正确,不需要的“没有道理”。不知然否?
关于其它。“封建论”者对我论点的摘(引)评(论)好象就到此为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王位继承制却不知为什么没有被摘引和评论。在有关扶南的史籍中,有关王位继承制的记载比其它方面(如邑、贡赋、奴婢等)要多,论述自然会更充分一些,或许也更能说明问题。如若能摘引一些就好了。因为我是从多角度、多侧面论述扶南的社会性质的,经综合分析和观察而得出结论的。缺一个“角”,少一个“面”、在认定我的奴隶社会说并加以否定时不是少了一点份量吗?
从上可见,经过“封建论”者摘引的我的有关奴隶社会说的论点是被扭曲了的,变了形的。不幸的是,在那以后,有的人竟从这篇“封建论”的文章照引被扭曲的我的论点,而没有去仔细阅读我的文章的原文,实在令人惋惜!
否定别人不是不应该,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种对别人的否定至少应建立在对别人观点的正确理解上。像“封建论”者那样,把对别人的否定建立在对别人论点的扭曲上,其效果肯定是难以如愿的。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否定别人不等于树立起自己。因此,此种方法似不可取。
逆向反射出的光是虚的 很模糊
“封建论”者使用的第二种方法是“逆向证明”。这个方法着实新鲜!但效果如何呢?
据说从“真腊、柬埔寨社会以及自有明确可靠记载以来先后演成的东南亚其它国家的社会特点”就可“逆向证明”扶南是封建社会,就好像“从后来真腊、柬埔寨时代的情况和东南亚各国以及许多东方或‘亚细亚’社会的情况”就可“看”出“村社存在于扶南时代”一样。要是复杂的历史问题就能这么来“逆向证明”或“看”的话,我们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就简单多了。历史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历史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如果变了形,那就不成为历史,至少不是真正的历史。“逆向”去“证明”的历史,很难保证不走样变形,犹如从逆向反射出的光一样,是虚的,显得很模糊。从真腊、柬埔寨逆向证明的扶南社会是不是这样的效果呢?至少在我看来,有不少模糊之点,同一类的点构成为群。我认为,有三个模糊群。
其一,“真腊和柬埔寨社会”模糊群,含如下模糊点:
——真腊、柬埔寨时代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封建论”者写道:“我们看到,这种封建社会同扶南时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此,笔者看来,就很模糊,怎么也看不清真腊、柬埔寨的封建社会同扶南时代竟相同得“没有什么区别”。支持“没有什么区别”论的是如下一段论述:“在真腊和柬埔寨时代,其社会的基本阶级关系仍是由国王为代表,由各级大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为一方和以广大村社劳动成员为另一方所构成。前者以国王或国家的名义垄断着全国的土地,后者在土地上从事生产劳动,并向前者缴纳‘贡赋’或‘租税’。”扶南时期的村社无史料可证,真腊时代,除《真腊风土记》中提到的“每一村……亦自有镇守之官,名为买节”外,我不知是否还有史料证其有村社广泛存在,就是《真腊风土记》中的“村”是否就是村社也还有待研究,如是,它如何构成为阶级关系中的“一方”,又凭什么指其两者相同?扶南时期的“贡赋”,按“封建论”者认为是“正确的”我的那种解释,承担租税合一的“贡赋”的是诸侯即“小王”,决非什么“广大村社劳动成员”。至于真腊时代,尚不知“广大村社劳动成员”在何处?(确凿史料)即使有,它与扶南时代承担贡赋义务的诸侯又怎能相同而没有什么区别呢?
——“国王以他自己的名义垄断着全国的土地,他本人只直接统治着其中的一部分,其余则以分封的形式交给王族、贵族、官僚和寺庙去占有或管理。例如:阇耶跋摩七世时,巴扬庙就拥有一块包括13500个村庄和30万人口的大领地。这种领地正是扶南时代的那种‘邑’,前者同后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区别,只是真腊和柬埔寨时代‘邑’比史书中提到的扶南的‘邑’在数量上更多了。”“封建论”者的这段叙述也把人搞得很模糊了。扶南时期的分封,史书是明确记载的,真腊、柬埔寨时代的分封不知见于何处?巴扬庙这样的领地就是扶南时代的“邑”,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直至有了“真腊和柬埔寨时代的‘邑’,人们也许会问:扶南的邑=真腊的领地=真腊和柬埔寨的邑,这个等式是如何作出来的?扶南“邑”的内部状况和性质如何,真腊的领地又为何物,(除巴扬庙那条材料外)均未见“封建论”者有所描述和说明,怎么能把它们视为同一物?乃至在柬埔寨时代还有“邑”的存在?我亦尚不知记载真腊、柬埔寨“邑”的史料在何处?特别是还在数量上作了比较,作出了真腊、柬埔寨时代的“邑”比扶南时代的“邑”还多的判断。这种数量多少的判断是依据什么作出的呢?4>3,有“数”的根据,不同时代“邑”有多少不同,有这样数的依据吗?
——在描述了柬埔寨时代国王派员收税的情况后,“封建论”者写道:“从本质上说,真腊、柬埔寨时代的这种地租同扶南时代的‘贡赋’或‘税’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只能说这时封建主对广大村社农民的奴役和剥削比之扶南时代更重了,封建化的程度比之扶南时代更深了”。实在说,我怎么也不知如何才能“从本质上说”清楚扶南时代的“贡赋”或“税”与真腊、柬埔寨时代的地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封建论”者压根儿就没有向人们说明过。“贡赋”包括“土贡”和“赋税”,是二者的合称。(“贡赋”中含“税”,不等同“税”)“土贡”是藩属向君主的进献,包括土产、珍宝和其它财物。真腊、柬埔寨时代也是如此吗?有,见之何处?至于说封建主的奴役和剥削真腊、柬埔寨比扶南更重,封建化的程度更深,更值得思忖了。轻与重,深与浅表现的是“量”的概念,必须有量的依据。某甲体重120斤,某乙100斤,甲比乙重无疑。某钻井队丙日钻800米,某钻井队丁日钻600米,丙比丁钻得深无疑。如无此种表示量的材料,何言“更重”,“更深”?
——扶南社会的特征同整个东南亚地区封建社会具有共同的特征,因而扶南“也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论”者如是说,并列举出四大共同特征:土地属于国王或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所有;封建土地所有制都是以国王的名义直接统治一部分地区,其余则分封给许多王族、贵族、官僚和寺院,形成一个个的“邑”;国王和各个“邑”的领主也都是通过传统的村社来统治和剥削广大人民的;都存在着一些奴隶或奴婢。我不谙除柬埔寨以外的东南亚各国史,不敢对上述四大特征及其比较妄加评断,我只想提出一些感到模糊的疑点,比如:扶南的分封及形成的“邑”是否与东南亚各国的分封及形成的“邑”一样,后者的史料记载是否明确?本属扶南的“邑”是否就是越南的各个“庄园”、缅甸的各个“谬”、泰国和老挝的各个“孟”、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和菲律宾群岛一个个“小土邦”?从何判定它们都是与扶南的“邑”相同?又怎么说缅甸的“日哇”、泰国和老挝的“班”、越南的“社”、马来半岛的“甘榜”、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徒萨”、菲律宾群岛的“巴兰盖”都是“一样”,而且同扶南的“村社”(如有的话),真腊、柬埔寨的“村社”(不知见于何处)又如何一样?如不把这些具体问题说明白,又怎能划出如下等式:扶南社会的特征=真腊、柬埔寨时代的特征=整个东南亚社会的特征=封建社会(接“封建论”者的表述列出。)可惜,“封建论”者并未对上述问题哪怕是略加说明,只是列出而已,让人怎不感到模糊不清?
其二,“生产力的角度”模糊群,含如下模糊点:
——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演变,必须是生产力发生根本变化,这是不错的。但“封建论”者认为,从扶南时代到真腊、柬埔寨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什么变化,更不用说根本。“封建论”者倾向认为,铁器的广泛使用,标志着封建时代的到来。因此提出:“在公元3世纪时,即扶南建国不久,铁器的应用就已比较普遍。”并举出在造船、斗鸡、审理罪犯者等方面的例子,但如果在农业生产方面不见铁器的广泛使用,是很难说明封建时代的到来的,于是,又写道:“铁制农具虽未提及,但在扶南这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里,其它方面都已普遍利用铁,铁制农具想必也是普遍使用的。”没有史料记载,能“想”出个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从而与封建社会相连?在别人想来,会越想越模糊的。
——从农业“一岁种,三岁获”,“封建论”者认为“须有较高的生产才有这种可能”,“这些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扶南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人们不知“这些”里除了“一岁种,三岁获”之外还含什么?也不知从这条记载怎样反映出扶南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多高的生产力水平?又怎么从“须有较高的生产力”而推断出有这种生产力(“才有这种可能”)?真腊时期,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里载及农业生产状况时,有“耕不用牛”,“大抵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据此,“封建论”者又得出结论:“看来也没有明显超过扶南时代的迹象”。人们也不知是如何“看”出这种迹象的。“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比“一岁种,三岁获”是进步还是落后?一次收获量的多少是反映生产力水平的,但无明确记载,何以判断真腊没有超过扶南?“耕田不用牛”是否就意味着落后?牛是中国农民普遍使用的,外国不用牛,是否用别的动物代耕,或者就用人拉,无记载,是难以判断的。以此认为真腊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超过扶南,似根据欠明确。
——“想”,加上一“看”,“封建论”者断言,“其实,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直到西方殖民者入侵之时,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水平也只是扶南时代的水平。我认为,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扶南。”水平的高低应该是有衡量标准的。将比较双方拿去衡量,决出高低。称整个东南亚地区(殖民者入侵时)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水平只是扶南时代的水平,是以什么作标准呢?又是如何衡量出来的?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扶南,又是哪些方面不如,怎样不如?如果仅凭一“想”、一“看”的内容是很难作出如此判论的。不知是否还有新依据,若有,又是什么?
其三,逻辑模糊群。“封建论”者在“逆向证明”时在逻辑上也留下一些模糊之点:
——包括柬埔寨和东南亚地区在内的人类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前进、停滞或后退?按“封建论”者的说法,柬埔寨和东南亚地区是停滞,某些方面甚至还在倒退。“从生产力的方面来说,扶南同真腊、柬埔寨时代乃至整个东南亚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生产关系”亦“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封建论”者如是说。两千年来,柬埔寨是在停滞中度过的,“某些方面还不如扶南”,意味着还在倒退?这不是套不套得上理论框框的问题,而是说,符不符合柬埔寨发展的实际?柬埔寨人会接受这个“现实”吗?
——以自己的看法作唯一正确的定论,反推别人的意见的谬误,“封建论”者写道“既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承认真腊、柬埔寨时代的社会以及整个东南亚那些与之有共同特征的社会都是封建社会,却把扶南时代的社会说成是奴隶社会,是没有道理的。”凡与“封建论”者意见相反的看法都被斥之为“没有道理”,只有自己一家之言有道理,唯一正确的,那还何需讨论?“换言之,如果说扶南社会是奴隶社会,那就等于说,直到西方人入侵之前,柬埔寨和整个东南亚的那种与扶南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都还是奴隶社会,这不就更成问题了吗?”这是一种以“唯我正确”的口气在作结论。反推别人得出的结论就“更成问题”,如按自己意见,即柬埔寨和整个东南亚在西方人入侵之前一直是封建社会,就不成问题,就顺理成章。
在“逆向证明”下,人们看到的是有关扶南社会的众多模糊之点,以至越看越模糊,实难看清扶南社会的真实面貌。这可能是观者有“盲点”,但亦不排除逆光之下的变形、走样,从而显得模糊。此法是否可取,似可商量。
“面”就是“面”,“点”就是“点”,“面”何以能概“点”?
以东南亚地区“面”概柬埔寨这个“点”,是“封建论”者使用的第三种方法。
“封建论”者在列举出越南、泰国、老挝、马来半岛、缅甸、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的例子之后写道:“上述事实都说明,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发展都没有经历一个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奴隶社会阶段,而是从原始社会末期之后便先后进入了封建社会。”接着,讲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如爪哇、马来半岛、缅甸及印度关于村的情况,概括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村社也都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差不多”、“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村社内部的这种情况也大同小异。”这一切讲了之后作出了整篇文章(《扶南封建论》)的结论,即: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就是,柬埔寨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国家扶南是一个封建性的国家,或者说,柬埔寨历史是由原始社会直接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柬埔寨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一个奴隶社会阶段。而且,不仅柬埔寨历史发展的特点如此,整个东南亚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都是如此。”
在以整个东南亚地区这个“面”去概柬埔寨历史这个“点”时来得是如此轻松,以致对东南亚各国只需蜻蜓点水似的稍作说明,连扶南、柬埔寨根本无需提一提,于是整个东南亚就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了,于是扶南、柬埔寨的历史也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就两千年一成不变地是封建社会了。我对东南亚各国历史无发言权,但我只知道一点:并不是所有东南亚历史研究者都认定这个结论,也有与之相反的看法,“封建论”者似根本不知(或不屑一顾),就一锤定音似地宣布所有东南亚国家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后就是封建社会。至于以此来概括柬埔寨,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员,柬埔寨与东南亚各国有诸多联系乃至相通的地方,但它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扶南是这个地区最早出现的国家,它有自身的历史和历史发展的轨迹及规律,怎好用别的国家的历史去推导它、代替它呢?犹如说,美国有许多富翁,所有美国人都是富翁一样,显得简单了些!虽然人们可以在富翁和非富翁之间找到这样或那样的相似相同之点,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用美国有许多富翁,所有美国人都是富翁的逻辑来抹去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同样道理,东南亚各国就是东南亚各国,扶南就是扶南,柬埔寨就是柬埔寨,人们只能从各个国家内部的研究中找到它们发展的共同规律,若把别处的某些东西移到某个国家身上,就难以反映出历史的真实了。
这种以“面”概“点”的方法,似也值得推敲。
“综上所述”,于是就得出那个无容置疑的结论。“综上”又“述”了些什么,总观《扶南封建论》全文,一是否定别人,二是从真腊、柬埔寨和整个东南亚“逆向证明”扶南是封建社会,三是从东南亚各国的封建社会推导出扶南也是封建社会。姑且不说这三者本身可否成立(已如前述),单就做文章的基本要求看就令人生疑。题目是论扶南是封建社会,文章本身讲了许许多多扶南以外的内容,而关于扶南讲得很少很少(第一部分是否定奴隶制说,第二部分讲真腊、柬埔寨,第三部分是论东南亚),最后得出的又是扶南是封建社会的结论。如此做文章,很难达到“论者”的目的。如果能单刀直入摆出扶南是封建社会的史料,讲出其封建论的道理,那就可能是另一番情景。如若做不到这一点,何不寻求一种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谨慎地进行探索和研讨。
在分别对“封建论”者研究方法的运用及其效果进行剖析之后,我认为,运用这些方法来进行扶南社会性质的研究,是难以辨明扶南的社会性质,达到预期目的的。既然如此,可否寻求一种更为科学的方法来进行问题的研究、这样的方法有吗?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历史比较研究法。关于这种方法,我将另外著文介绍,以向同行们推荐。
注释:
①《早期东南亚国家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载《东南亚》1993年第2期。
②即何平同志《扶南封建论——与陈显泗同志商榷并兼论东南亚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载《东南亚》1987年第3期。
③④发表在《东南亚》1990年第4期,1991年第4期。
⑤参见《东南亚》1987年第3期,第29页。
⑥参见拙文:《从租税合一论及古代扶南的社会性质》,载《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