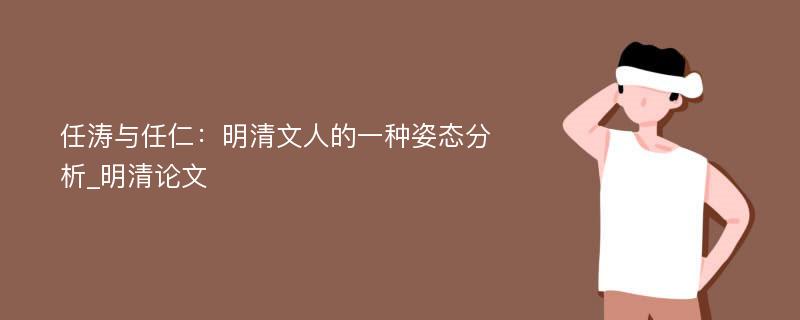
任道与任事——关于明清之际士人的一种姿态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明清论文,姿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6 )02—0007—09
梁启超说明代“士习甚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此“嚣”即应当表现在“诸生干政”一类场合①。明人未尝不自以为士习之“嚣”,批评诸生干政的,就不乏其人。明清之际,顾炎武一再谈到“诸生政治”的阴暗面,即如“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閧”,且“前者譟,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甚至以为“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生员论中》,《顾亭林诗文集》第22页,中华书局,1983)。还说生员“聚徒合党,以横行于国中”(《生员论下》,同书第24页)。《日知录》“生员数额”条,也说生员之“劣恶”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譟。至崇祯之末,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卷一七)。其实大有相反之例——顾氏所说的崇祯之末,“举义”者中就尽有生员。
明代士习之嚣,自不限于诸生干政的场合。此“嚣”除了见之于言论(朝堂建言及处士横议),也表现在政治地位的谋取上。“嚣”缘于“竞”(即其时所谓的“嚣竞”)。下文还将谈到,明清易代之际,此种“奔竞”近乎无耻,以至在清初一段时间,成为人们讥嘲的话题。② 好义与热中,界限本难以分明。 且“热中”与“勇于任事”,有可能不过是同一事的正面与背面;喜事与热中的,或许正是同一人。无论下文将要谈到的士人的热心任官、勇于任事,还是热中、奔竞,都可以由制度、朝廷律令得到部分解释。
王夫之曾于明亡之后,分析明代士风的躁竞,以至“昭代无隐逸”,归因于“经义取士”,“安车蒲轮之典旷废不行”,及本之于《大诰》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充军之例”(参看《搔首问》,《船山全书》第12册第626页,岳麓书社,1992)。将有关士风归结为制度性后果,以上无疑是一些较易于想到的原因。实则“制度”本身也不无矛盾。即如既有“军民人等”、“臣民”均可上奏本陈情、建言、申诉的许诺(参看《大明会典》卷七六、叶盛《水东日记》卷一○),又有禁生员“出位妄言”“军国政事”的律令(见之于洪武十五年颁布的《学校禁例十二条》,即所谓“卧碑”)。③《明史》卷一三九门克新传:“初,教官给由至京,帝询民疾苦。岢岚吴从权、山阴张桓皆言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边方,且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④ 由后世看去,此种“榜谕”与禁止诸生干政的律令,传达的是互有扞格的信息,其后果之复杂不难想见。
上述明太祖训谕中提到的胡瑗(安定)任教苏州、湖州,设“经义”、“治事”两斋,⑤ 到了本文所论的时期,已被作为制度想象的重要资源。 天启二年刘宗周上《修举中兴第一要义疏》,建议“略仿胡瑗经义治事之意,令士子朝夕学舍,以明经为主,兼通世事。如兵屯、水利、盐法、天文、地理、算数之类,就其质之所近,各习一事,渐以类通。官师以时考讯,又以其暇行射礼及雅歌琴瑟……”(《刘子全书》卷一四)张履祥一再提到“安定先生之教”,以两科之设为圭臬(如《与严颖生二》,《杨园先生全集》卷四第93页,道光庚子刊本)。陆世仪亦以为学校之制当“仿安定《湖学教法》而更损益之”,“‘治事’则宜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诸科,各聘请专家名士以为之长”(《思辨录辑要》卷二○,正谊堂全书)。颜元则以为胡瑗“主教太学,立经义、治事斋,可谓深契孔子之心”(《存学编》卷三,《颜元集》第75页)。直至梁启超清末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订立学约,尚有“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云云(《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28页,上海中国书局,1936)。由下文可知,在本文所论的这一时期,胡瑗的创制被强调的非“经义”、“治事”的二分,而是其间的关联;以经义治事;通经兼能治事。儒者以此自期,也以此为长养人才的标准。
一些年后的回忆文字中,黄宗羲说到当明末坊社盛时,他的一班同道都有志于功名,“直望天子赫然震动、问以此政从何处下手”(《寿徐掖青六十序》,《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6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黄氏在另一处也说,其时会社中人,“俱务佐王之学”(《诸硕庵六十寿序》,同书第65页)。由有关的文献看,那些参与造成“复几风流”而为后人艳羡的名士,并不即以“呫哔”为有妨于“佐王”,一时蔚兴的会社中,时文兴趣与经世热情同其高涨。明末社事,又往往与朝局相表里,朝端朝外,打成一片;士人无论身处朝野,实施干预的热情,都不可遏抑。⑥ 明亡之际作绝望的抵抗,期非常之人出而救世, 朝野也均有此种期待。钱谦益主张轨外用人,说“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虽狂猾无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风。而仲淹亦躬为诡特之行以振起之”(《嚮言下》,《牧斋初学集》卷二四第7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即崇祯也主张用人不拘一格。黄宗羲所撰董守谕墓志铭,记南明鲁王语,曰“得孟轲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谈仁讲义之徒百,不如得鸡鸣狗盗之雄一”(《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01页),正应和了其时士人的普遍渴求。
即使这种呼唤不足以造就奇才,也鼓励了一种不无夸张的用世热情。正如上述黄宗羲所形容,其时的青年志士无不自负经济,以“医国手”自期,好言王霸大略,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视天下事以为数著可了”(《陆文虎先生墓誌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39页)。吴应箕《拟进策》(《楼山堂集》卷九)自比贾谊,说恨无贾谊之遇,狂态十足。陈子龙的《求自试表》也语气狂妄,曰“陛下诚能用臣,以待伊,吕之流,臣必脱屣风云,推引轮毂,敢如今人久窃贤路”(《陈忠裕全集》卷二四,嘉庆八年刊本)!到清中叶,全祖望撰写《刘继庄传》,对于这旧时人物于倾倒之余,也发现了某种讽刺性。全氏说刘献廷关涉经世的撰著,“虽言之甚殷,而难于毕业,是亦其好大之疵”(《鲒埼亭集》卷二八,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好大,也是其时通病。但如上文已经说到的,明清之际诸多可歌可泣之事,确也赖喜事的书生及其“一往之意气”。惟有此意气,也才有危急时刻不惜一掷的绝望的抗争。承有明一代的流风馀韵,直至清初,刘献廷、王源、梁份等一批豪杰之士,犹不屑于为词章之学;即使以文章为时所重如魏禧者,也自命“志士”,不欲以“文人”自限。这些人相互激赏、激发,尽管已不可能再如当年的复社中人,发挥实际影响于当代政治。
无论由正面所见士人政治参与、政治议论的活跃,还是由负面看到的“奔竞”、热中,无疑是在同一政治环境中发生的。即顾炎武所痛疾的诸生干政,也自有其负面与正面。把持官府、关说公事固然是“干政”,如傅山所倡首的晋中诸生的为袁继咸伏阕讼冤、陈确的率诸生的攻逐贪吏也是“干政”——原不可一概而论。更何况如上文所说,参与“最后之抵抗”的,尽有诸生。黄道周隆武朝率领出关迎战清军的,多为诸生所招募,黄氏称之为“君子之军”(《将出关疏》,《黄漳浦集》卷五,道光戊子刻本)。无论正面或是负面,有一点却是无疑的,即士的政治能量的扩张,自信的增长,在一个长时期中积蓄而成。有明一代,士人(以至“草民”)的尚气任侠,笃于风义,不惟亡国之际为然。天启朝党祸中东南士民自发的反奄活动,即是突出之例。北方何尝不然!孙奇逢《乙丙记事》(《夏峰先生集》卷八,畿辅丛书)所记畿辅士民尤其鹿太公等人的义举,确可谓“古色照人”。时论、士论乐道义行义举,无疑鼓励了上述风气。只不过到了亡国的危机迫在眼前,那种道义承当愈加具有悲壮色彩罢了。
“士”原有“任事”一义。⑦ 勇于任事,可以看作返回“士”的原初语义、 原始职能。尽管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无论“士”抑“事”以及“任事”,内涵都大大地复杂化了。吕坤曾说“任有七难”,分别论说“繁任”、“重任”、“急任”、“密任”、“独任”、“兼任”、“疑任”对于人才的要求(《呻吟语》卷四之四《品藻》,《吕新吾先生遗集》,吕慎高重刊)。到本文所论的时期,方以智撰《任论》阐发“任”之义,说:“六行之教,任居一焉。”“任而义也,见义不为,孔子耻之”(《曼寓草》中,《浮山文集前编》卷五,《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按“六行”指孝、友、睦、婣、任、恤)。该文肯定了“任侠”。当明清之际的“任事”,却未能如任侠的洒脱,而不能不是更为沉重的担当。
“任”的通俗化的表达,尚有近人沿用至今的如下说法,即挑担子。被清人许为粹儒的陆世仪,说:“学道贵能自任,盖既自任,便有一条担子轻易脱卸不得。”(《思辨录辑要》卷一)陆氏本人属于勇于任道也勇于任事者,相信有“轻易脱卸不得”的担子,方能为人生增重,也应属经验之谈。张岱引湛若水说“仁以为己任”,曰:“今人只为一切担子累得此身重了,故不能任。”他于此说“担荷”、“仔肩宇宙”,口吻与其时自命“志士”者无异(《四书遇·论语·弘毅章》,第19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前此唐顺之就说过“且向前担却一条担子”(《与杨朋石祠祭》,《唐荆川文集》补遗卷四,江南书局据明嘉靖本重刊)。无论唐顺之的时代还是张岱的时代,“担荷”都有可能以支付生命为代价。
当此际士人的用世热情为“救亡”所激发,“开物成务”与“弘济时艰”,后者被认为更有直接的功利性,也有更紧迫的时间性。不止方以智以任侠、任事为世倡,其时切实地担当事任的孙承宗,也好用此一“任”字。“任”被孙承宗赋予了某种庄严性——对斯世斯民的庄严承当。孙承宗说:“夫天下不敢任而豪杰能任,故称‘权’。‘权’非有形之物也,以豪杰所敢任合天下所不敢任而成权。故豪杰见为冒天下之患、任天下之事,而细人见为握天下之权。”(《毕白阳先生督饷疏草序》,《高阳诗文集》卷一一,崇祯元年序刊本)至于他本人任事的动机,或许可以由下面的说法得一证明,即“天下事得言之,不若其得为之”(《贺嗣龙周邑主擢贰云中》,同书卷一二)。他不满足于言说,力求亲力亲为,切实地施加影响于时局。
回到本文的题目上,应当说任事之勇,原非为明末士人所特有;这里我感到兴趣的,无宁说是有关的记述文字对此的复杂态度,以及此种“任”与其时的士风、学风的关联。
“任”本是居官者的常态。凡居官即有职事。此处所谓“任事”的“事”,当不限于(或曰主要非指)职事。到了本文所论的危急时刻,更特指士夫通常所不任、不足以任之事,如孙承宗、卢象异、鹿善继所任的兵事。我在其他处也曾谈到,士夫所任,尚有素所不屑之事。如钱谷刑名簿书之类,由此扩大了他们的政治实践的范围。任非所任(如兵事),任大、任难、任繁剧、任艰危,固然意味着承担严重的道义责任;任鄙琐的地方政务,任有赖于行政技能、专门知识的事务,也挑战了士类中流行已久的偏见。前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道德境界,后者则丰富了他们的政治经验。⑧
王充说, “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论衡·程材》)。在漫长时期“士大夫政治”的发展演变中,任道者任事,儒者与官僚一身而二任,已不适用于王充的描述。本文所论的时期即使没有形成更具有整合性的观念架构,以二者并重,也是一种适应时势的言论姿态。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第98页),不以“明道”与“救世”作对立观。刘宗周则径说:“夫匡国翊运拯溺亨屯,孰非吾道中事任?”(《与王右仲问答》,《刘子全书》卷九)值得注意的倒是,明清之际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引发了对于不任事(道义缺失)、不足以任事(能力缺失)的反省;救亡、恢复的紧迫任务,更激发了任大投艰的悲壮激情。
隆、万时赵用贤就说过,“今不患无材,而患无实下手做事之材耳”(《与周元孚》,《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中华书局,1962)。“实下手做事”,实膺民社之寄、任民物之责,当明亡之际,较之平世,不消说更要胆识与气魄。明末有关于“喜事”的批评。其时固然有“喜事”者,却也更有避事者。只要官,不要“任”,尤其逃避军事责任。因而一方面是不任此事的文人侈谈兵事,一方面是当事者相戒以谢责,也算得当时的一种怪现状。更有“以无官为幸”者(《总催大僚考选疏》,《范文忠公文集》卷一)。当事已不可为,对事任的恐惧,亦人情之常;避祸全生,即号称忠臣者也不免有此一念。士人的心理隐微,由家书中往往能得一点真消息。即如刘宗周、黄道周于出处间的游移。吴麟徵也曾在致伯兄的书札中,说“干戈云扰时,万一粘手,急难脱身,蹈不测之险,不如今日早卸为安”;“以此时尚可抽身,过此则不可知矣”(《寄禀伯兄秋圃》,《吴忠节公遗集》卷二,乾坤正气集)。于“万万难为”(吴氏语)之时,为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确不宜责之于常人。却也正因此,黄道周、吴麟徵的挺身担当,终于身殉,正有所谓的“不容已”。
上文谈到了有关制度内在矛盾,这里却应当时说,后世所以为“矛盾”者,未必不出于有意的安排。即如朝廷政治中“任事”、“议事”的区分——体现于使“建言”专职化的臺省设置;而“议”与“任”间某种对抗态势的造成,又直接系于位卑权重的“言官”在朝廷政治中的地位、作用。由章疏一类文字看,以“任事”自居的,通常是任职户、工、兵诸部的官员。卢象异自说“任事者也,非议事者也”(《剿荡三大机宜疏》,《卢忠肃公集》卷四,光绪三十四年重修板刊本)。鹿善继也区分“议臣”、“任臣”(《采集廷议敬效折衷疏》,《认真草》卷一一,畿辅丛书);因其本人曾切实任事,对言论的牵制,体验殊深。明亡之际,任事者每为议论所牵制,为此不免啧有烦言。卢象异就曾说到“长安口舌如锋”(《明史》卷二六一本传)。针对士人的“侈谈边事”,凌义渠愤愤地说“任不必议,议不必任”;“议之非难,任之则难”(《兵饷议》,《凌忠介公文集》卷一,乾坤正气集)。孙承宗解释“任之议与议之议”之不同,以医为譬,曰:“夫任之议与议之议异,议之议指发诟病,不必自辨方术,抑口授方术,令主者自辨;而任之议如病家属病于国手”,此“国手”“势必自酌自剂,无得更以病呼而反乞方于主人”(《毕白阳先生督饷疏草序》,《高阳诗文集》卷一一)。⑨ 有意地以“秩一事”、“事—权”的非统一为控驭手段,这种诡谲的制度安排,出于雄猜之主的政治设计,不能不深刻影响于有明一代政治以至士人风貌。⑩
卢象昇说:“从来任事之人,即任罪之人”(《密陈边计疏》,《卢忠肃公集》卷五),语意沉痛。任其时之事者,也承担了那个混乱时代的种种乖谬;在激烈的政争中因任事而任罪,成了他们的无可逃避的命运。嘉靖间王维桢就说过:“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议;有非常之议者,必有非常之谤”(《赠东谷先生考绩序》,《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二)。孙承宗自说其任事受谤,“几令天下以任为戒”(《督理事宜序》,《高阳诗文集》卷一一)。金声也叹息着“从来任事之难如此”(《复李□□年兄》,《金忠节公文集》卷四,道光丁亥嘉鱼官署刊本)。任事之难,确也要在事局中才能深知。(11) 明清之际的历史, 部分地也就在任事者的具体处境中,在他们所任之“事”中,在诸多个人的政治经历、经验中。而这一时期的历史,确也经由上述个人经验,而现出了饱满与丰盈。
吕留良解“自任以天下之重”,曰“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还说因“此句最易说入豪士急功名、英雄试经济”,故有上述强调(《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卷三八,《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正己乃所以正天下,天下是己分内事”,此亦其时的讲学家语。在此“任”的必要性是由人格完成的方面论说的:不止缘于道义责任,也缘于(或者说更缘于)内在要求;“任事”不止是时势之于个体的吁求,也是不懈地追求人格提升的士人的内在要求。由上文可知,当明亡之际以救亡自任者,强调多在一“任”字,儒家之徒却不将“任”与“自”作对立观,于是而有王夫之等人一再申说的“自靖”、“自尽”;“君子之自靖以忠于所事,亦为其所可为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一二,《船山全书》第10册第448页,岳麓书社,1988);“忠也者,发己自尽之谓。尽己之所可为,尽己之所宜为,尽己之所不为而弗为……”(同书卷二○第779页)自靖,语出《尚书·微子》“自靖,人自献于先王”;“自尽”即尽其在我。(12)“自靖”、“自尽”的非功利指向,所强调的,亦承当者的内在需求,他们提升精神、完成人格的渴望。不以功效为主要目标,追求自我道德人格的完成,尽其在我,不知有他——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与下文将要说到的事功、功利追求,是同一时期士人的不同面向,或许也是同一人的不同“精神侧面”,并不被认为不相容,甚至未见得不互为补充。也要这样,才更足以应对复杂情势。
当其时确有一些人物,当着狂澜既倒,毅然担当,即令到了数百年之后,那一种气概也仍然令人神旺。即如上文谈到的卢象昇,说“时至今日,到处皆以封疆为陷阱”(《卢忠肃公集》卷一一《与少成吴葵菴书八首》之八),却表示自己“于封疆之事,有任无让”(卷八《西阅晋边摘陈切要事宜疏》)。另如辅佐孙承宗处理辽左军事、以“认真”著称的鹿善继。鹿氏说自己每每想到罗洪先答唐顺之的话:“此生若活得千人命,便甘心不向世外走”,感叹着“有味哉其言之也”(《答范景龙书》,《认真草》卷八)。罗洪先此语,鹿氏一再引用(另见同书卷三《定兴县籽粒折徵记》)。“此生”即当世,这里有价值指向,也有信念;淑世救人,鹿氏精神灌注在此一事,作为王学中人,践履切实处亦在此一事。当他人避事唯恐不及,鹿氏却一反常谈,说“天下事未坏不必为,小坏不可为,可为者独大坏耳。”(14) 还说:“大要吾辈犯得一分难,便干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卷八《回潘怀鲁书》)“山东司谓事求其可,功求其成;本司则谓事可做者,决意去做,成败利钝,非能逆睹”(卷一一《回户部咨》)——无论事是否可为。不计成败得失利害,不惜为不可为,与“明道不计功”的思路,又不无相通。我在那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谈到了士人在明亡之际的抵抗中“可不死的死”。“可不死的死”或部分地出于被动,“知不可而为”则出诸主动的选择,与儒者的非惟“功利”、“成效”的思路确有其一致。(15)
其时士人追求“政—学”、“仕—学”之“一”。这里也有“任道”与“任事”的统一,承当事任与承担道义的统一。“为政”一向是士夫重要的实践活动,儒者重要的践履。在明亡前的特殊情境中,为政而救亡、抵抗,尤被作为了德行的淬炼之地,非但无妨于成德,而且被视为达成这一目标的条件。孙奇逢终生未仕,却劝导他人,说:“从古英人志士,当可有为之时,用以摅一朝之意气,发千古之悲凉,切莫当面错过。一瞬失之,终身莫赎,悔何及矣!”(《夏峰先生集》卷一三《语录》)关心的也非止成败,而是上述“摅”、“发”,即某种精神的张扬。对于“任”的意义,孙氏确乎不惟由事功的方面估量。(16)
参与了最后的抵抗且也以身殉的金声,本谢事家居(参看其《上徐元扈相公》一札),没有非任不可之责,却在乙酉致书刘宗周,说“不敢自度其身之不能为,不敢料天下事之不可为,为一郡倡明大义,力疾支持,方画岭而守,愿效死勿去”(《与刘念臺》,《金忠节公文集》卷五)。前此他可以“谢”朝廷职事,至此却不能不任抵抗之一事,也因此事已超出寻常“出处”,被视为士人不容推卸的道义责任。金氏说:“无天下万世之深情者,不可以与深言天下之事。”“故有天下万世之深情者,必不听其命于天地,而以为天下之事存乎其人。”(同书卷一《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论》)他的于万难措手之时,挺身担当,也应基于此种信念。挟了道义的人格的力量,如鹿善继、金声一流人物,追求的更是此种“担当”,由此而开发出了各自的人性深度。(17) 我曾一再谈到我由其时的文字间读出的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严肃”,这“严肃”确也尤见之于危急时刻的此种担当。
有明一代,权力机构之外的士大夫的政治参与,异常活跃。本文开头谈到的诸生干政,只是一端。即如荐绅所从事的赈济一类的“民间政治”,固然系“不容已”,也出于对自身才干的自信。刘宗周记沈祖诚崇祯十三年的赈灾:“岁庚辰,吾越告饥。沈子独率其乡之人行赈里中,全活者甚众。明年饥益甚,上官廉知沈子贤,遂委以一乡之政,而沈子徵发期会,井井如也。至措置粥厂事宜,纤悉皆周,远近就粥者,归之如投怀。”(《文学沈本人传》,《刘子全书》卷二三)沈氏不过一诸生,却“隐然为一方中正,有达官贵人所不及者”(同上)。冒襄自记其明末以诸生而破产佐赈,“得活数十万众”事,足以令人想见其政治才具(参看《巢民文集》卷二《寿汤惕庵先生暨太公同岁六十八十序》等文)。祁熊佳撰祁彪佳《行实》,记祁彪佳“虽家食,凡施济事,知无不为。一赈剡饥,再赈全越饥,先生力为担荷。虚礼下士,感物以诚,富家大室,闻风乐施,所全活不可计。”(《祁彪佳集》卷一○第237页,中华书局,1960)(18) 上文所谓的“民间政治”,赈济只是一端。陆世仪的友人陈瑚避地蔚村,曾用“兵家束伍法”,“导乡人筑岸御水”(《清史稿》卷四八○臣陈瑚传)。黄宗羲说查遗(逸远)“以经济自期许”,洞悉政治利病,无所施为,也仍然能以沟渠保甲社仓诸法行之一方(《查逸远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67页)。陆世仪对局外的谋划若有成算,其《桑梓五防》曰:“鄙谚有言:‘当局而任之,不如旁观而议之;纷纭而理之,不如闲暇而谋之。’”他本人的佐幕,也应出于这种效用方面的估量。钱谦益《梅长公传》也记有“失势家居”的梅之焕代行官府职能,捕盗缉贼,捍御地方——却也干预词讼(《牧斋初学集》卷七三)。明代的“朝外政治”、“缙绅政治”,其复杂性即在同一事例中;也如诸生干政,不宜作一概之论。(19)
士人的应世能力,未始不也养成在此种风气中。有明一代大规模的党社运动,对士人的自组织能力即无疑是一挑战。无论上述“民间政治”,还是会讲活动、文人社集,都要有人具体操办;后者如馆舍、厨传,即现代人也未必能从容应付。据记述,其时确有“咄嗟立办”者。吕公忠撰其父吕留良《行略》,也说吕氏“遇事盘错疑难,迎刃立解,精神过人”;“丁酉倡社邑中,数郡毕至,敦盘裙屐,讌乐纷沓”,吕氏“指挥部署之,终会不失一匕箸,人服其综理之密”(《吕晚村先生文集》附录,同治八年序刊本)。我注意到有关文字对于“能力”的评价态度——无论官员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还是民间领袖人物处理民间事务的能力。明清之际轰轰烈烈的党社、讲学活动,也要赖上述人物方能推动。其时士人所称道的“干办”、“干局”,何尝止表现在官方政治中!
儒者处理政务未必就迂,文人、名士也未见得无能。即一时以通脱、狂狷著称的文人、名士,也不妨为能员干吏。儒家之徒中,从来不乏注重实践(包括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者;以“开物成务”为“儒效”,有明一代,也未尝乏人。贺钦号称名儒而通达治理,其奏疏中的主张,被认为可见诸施行。读吕坤《忧危疏》等,令人不能不感慨于其时士人对世情民隐的洞悉,以及“苍生”在其人心目中的分量。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舞台上,“理学名臣”、“王学名臣”如范景文、李邦华、施邦曜、蔡懋德等,各有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虽朝廷建言时的刘宗周曾被讥为迂远不切事情,却无妨这同一人在京兆尹、左都御史任上现身为干练的官员。王夫之即称道刘宗周为“匡济之才”(《搔首问》,《船山全书》第12册第645页)。(20) 陆世仪谙练世故,洞悉官邪民隐,言及政事,无不切实,若老于官场者,绝少道学的迂陋。张履祥的政治才能尤见于《保聚事宜》、《赁耕末议》、《授田额》一类文字,不惟示人以儒者之徒“民胞物与”的情怀,且显示出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清醒反应,与关涉具体事务设想的周严缜密。至于孙奇逢崇祯十一年的率众避地,尤堪为蕴藏于士人中的政治能量作证(参看《孙夏峰先生年谱》)。
“喜事”在其时的表述中通常为贬义。未尝非针对时人的“喜事”,孙奇逢说:“任当其才,则千钧可加;任违其常,则一毫亦乖。士当自量,不得轻借口。”(《夏峰先生集》卷一四《语录》)黄宗羲以冯京第为“喜事”,说其“为人夸大自喜”,“心雄气豪”,“以霸业自许”(《御史中丞冯公墓誌铭》,《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88页)。黄氏本人所撰写的冯氏墓誌铭却使人相信,当其时也要冯京第这种人,才能“屡起屡蹶”、至死方休。而文人的“喜于任事”,或也出于“好奇”(奇谋奇计奇行奇节)。明亡之际士人的任侠尚义以及略成风气的谈兵游幕,与有明一代士人活跃的政治干预与发达的名士文化,均不无关系。从事于坛坫的,未必即迂执书生;耽嗜于声色征逐者,或也热衷于谈兵,甚至不惜亲历战阵。当明亡之际,柳车复壁,以至慷慨赴义者,无非此辈。在一种眼光下,二百馀年间活跃的民间政治、布衣政治,正可以视为明亡之际发动于民间的抵抗运动的准备。明儒的注重“践履”,名士的不甘寂寞、寻求自我表现,以至为铨选、科举制度刺激了的功名欲,都或隐或显地“参与”了士人在此一特殊历史关头的选择。
清初关于明亡的追论,往往以“有君无臣”为说,不过袭用明人当绝望之时的话头。“袖手谈心性”一类说法,不足以概“明儒”,何况其余!明人决不较其他任何朝代的士人缺少政治才能与行政能力——即使所处乃“理学时代”。明必不亡在士人的无能上。在此题目上,正无须拣拾前人的唾馀。魏源说明代士人“自成进士释褐以后,则不复以声律点画为重,士得以讲求有用之学。故中材之士,往往磨砺奋发,危言危行,无所瞻顾。凡本兵、吏部文武之任,往往有非常豪杰出乎其间,虽佚君乱政屡作,相与维持匡救而不遽亡”(《明代食兵二政录序》,《魏源集》第161—162页,中华书局,1976),未始非平情之论。在我看来,清初的“经世思潮”,不必是对于晚明士习的反拨,而更可能是明代士风的延伸。
战乱灾荒,在使士人备受摧折的同时,也提供了他们政治参与的机会,拓宽了他们用世的渠道;而幕业明中叶以降的发展,则使得无缘于仕途的士人另有了参政的机会。明清之际士人的游幕固然背景、动机不一,至少在明亡前后的一段时间,有关选择仍然基于“为政”(此“政”首先即官方政治)被认为的优先性。游幕之外,更有士人组织、参与了地方性的抵抗,如吴应箕、金声、陈子龙等人——为此支付了沉重的代价。
士人明亡之际的政治参与,或可认为构成了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一部分背景。当然只是“一部分”背景。明清之际士人的经世取向,未必即由上文所涉及的人物表征,与他们的挣扎、奋斗却未必无干。这一思潮的根据,自然也在有明一代的思想、学术中,无论远缘抑近缘,都不便轻易归结。
[收稿日期]2005—12—01
注释:
① 明代生员人数众多,据顾炎武说,“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日知录》卷一七“生员额数”条。顾氏在该条中主张限制生员数额以为抑制),确也蓄有足够的政治能量。
② 刘宗周所拟《证人会约·约诫》,即戒“干进”、“要结当途”、“钻刺衙门”(《刘子全书》卷一三,道光甲申刻本)。范景文天启间曾任文选郎中,奏疏中说到其时“举国若狂,嗜进如骛”(《矢心入告严杜请托疏》,《范文忠公文集》卷一,畿辅丛书)。熊开元记南明朝臣对官爵的热中及名器之滥:“侯一人则群耻为伯,相一人则耻为卿,甚有竖儒厮养,得五六品官,夷然不屑者”(《鱼山剩稿》卷二《感事赘言一》,第1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于此士习的“嚣”与民风的“嚣”正相呼应。此种风气至清初仍在延续;据黄宗羲说,南明朝覆亡,曾争先入仕的举人“皆复会试于本朝,人谓之‘还魂举人’”(《思旧录·董守谕》,《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8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按“本朝”指清朝)。稗史野乘与其他私家著述,颇有关于士人于明亡之际“乘时”猎取官爵的记述:不但向南明小朝廷、向清,且不惜向“贼”,如恐不及。有关记述所刻画的,是普遍的投机心理,以易代、鼎革为一大赌局,甚至视“建义”为利市,危幕复舟,在所不辞。
③ 《续文献通考》卷五○《学校四》:洪武十五年五月颁禁例于天下学校, 镌勒卧碑,置明伦堂左,不遵者以违制论。禁例中有“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云云。尽管顾炎武曾引黄宗羲为同道,说其《日知录》中所论,同于《明夷待访录》者“十之六七”(《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392页),他关于生员的上引议论,与黄氏该书的《学校》一篇,旨趣却大为不同。不妨认为,顾氏的主张更与有明“祖制”精神相近。
④ 《续文献通考》卷四七《学校一》:“有明开国之初,即振起学校……其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并令习射、习吏事,以寓政教相通之意,成材之士辈出”。太祖曾遣国子生分行天下,定鱼鳞图册、督修水利、清理军籍,甚至任用为言官。他表失望于科举所取士,以“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第50页,中华书局,1981)。
⑤ 《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立经义、治事两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曆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数是也。”(《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56页)关于胡瑗苏湖设教,分立经义、治事两斋,钱穆说:“经义即所以治事,治事必本于经义。”(《朱子学提纲》第10页,三联书店,2002)
⑥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由正面评价上述士人的干政运动,说“明崇祯间的宰相可以由民意去更换,这时候一般读书人的势力有这样的伟大”(第8页);朱倓比较复社、应社与杭州之读书社,却说张溥、吴昌时辈,不能如读书社诸子之“职思其居,言不出位”(钱谦益语),“不特三府辟召,常出其口,且身居草野,隐然有易置宰相之权”(《明季杭州读书社考》,《明季社党研究》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45):近人对同一历史现象的评价,竟也有如许之不同!
⑦ 《白虎通义·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说文解字》:“事,职也。”关于“士”这一称谓的“任事”者的意味,参看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二章第三节。
⑧ 后一种“任”有复杂的意味。在一种排斥“专门化”的传统中,兵事较之钱谷、刑名、簿书,不但被认为更具严重性、紧迫性,也更有可能寄寓浪漫情怀。因而士人所乐“任”的,不能不首先是此“事”。
⑨ 前于此,王锡爵就说,“将士以力击贼于外,议论者以舌击任事之臣于内”,他以那些议论为“中朝梦语”(《与宋桐冈论撤兵》,《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五)。
⑩ 吕坤《呻吟语》卷五《治道》:“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责任负荷之义。任者任也,听其便宜、信任而责成也。若牵制束缚,非任矣。”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引用王夫之针对科道秩卑权重的批评:“贱妨贵,新间旧,小加大,逆也”,说王氏“认为这是一种违反行政原则的现象,是明代最高统治者故意贱爵秩、重事权,使任事者无权,有权者不任事造成的”(第1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1) 万历朝徐光启奉旨练兵,说自己“受事以来,百不应手,叩阍不闻, 将伯无助,特欲以重任见委便为了事,事之成败不我顾矣”,他本人竟“以此愤懑成疾”(《复黄宪副谷城先生》,《徐光启集》卷一○第4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卢象昇自说“万死一生,为朝廷受任讨贼之事,海内竟无一人同心应手者。惟见虚谈横议之徒,坐啸画诺之辈,望恩修怨,挟忿忌功,胸鲜隙明,喙长三尺,动辄含沙而射,不杀不休”(《寄外舅王带溪先生九首》之七,《卢忠肃公集》卷十一)。处境之凶险,又非徐氏所能想见。由任事者的文字(如范景文崇祯朝的奏疏),也才更能了解其时之为绝境,以及明末“忠臣”知不可而为的强毅。
(12) 罗洪先说,“圣人岂必大用而后足以自尽哉”(《奉黄久菴公》,《念庵文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顾宪成也说过,“勿谓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谓人心不如我心,自尽而已。”(《小心斋劄记》,《明儒学案》卷五八第1382页,中华书局,1985)王夫之释程颢所谓“发己自尽”,说“即‘尽己’之谓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一,《船山全书》第6册第445页,岳麓书社,1991)。王氏由孔子的“知不可而为之”,说到“忠臣孝子,一往自靖,不恤死亡之极,亦有圣人之一体”(《周易内传》卷一上,《船山全书》第1册第73页,岳麓书社,1988)。还说“宗国沦亡,孤臣远处,而求自靖之道,岂有他哉?直致之而已矣。可为者为之,为之而成,天成之也;为之而败,吾之志初不避败也。”(《读通鉴论》卷一三第466页)与金声同死的江天一也说过:“苟有一节可以自靖于天,即碎首捐躯亦将含笑地下”(《吁天录》,《江止庵遗集》卷二,乾坤正气集)。无论在明亡前夕还是明亡之后,上述表达都不能不有悲怆意味。
(13) 卢氏自说“所处极危,所当极苦,所任极难”(同书卷九《云兵不宜再调疏》);说“今日封疆之吏,万苦万难,冷雨凄风之下,红尘赤日之中,铁马金戈,时时寄性命于锋镝,岂特鲜居官之荣,抑且无有生之乐”(卷四《剿荡三大机宜疏》);说“大凡任事者,必有利害、是非、得失、毁誉隐伏于其内,交伺于其旁,此任劳任怨之难”(卷一○《回奏兴屯疏》)。明末军事,如卢氏所说,委实是“极重大极艰难之任”(卷四《剿寇第三要策疏》)。
(14) 鹿氏对此的解释却又不出于常谈,如曰“国家不能百年无事, 气运每以多难兴邦。事变交迫,斯英雄措手时耳”;还说“况事理事势相乘相薄,必至不可为而后可为”(《送李元素提督操江序》,同书卷一六)。
(15) 鹿善继何尝不明悉利害。他的说法是:“利害二字,几为世局司命,中智以下皆知之,而痴人不知也。顽如石,直如矢,处处认真,人以为大家事者,偏见为自己事,大家事则利害之见自起,自己事则趋避之念尽除。”(《窾议序》,同书卷一二)由传记看,确也要“认真”二字,才足以为其人写照。鹿氏即不但勇于任事,且强毅坚忍,能“粘”能“耐”。鹿氏曾于书札中说他人的“肝胆风神”,“能使死物都活,盖偏得造化生气,无微不入”(卷一○《答王崑壁书》)。鹿氏本人何尝不如此。由此看来,明末不可谓无人。
(16) 明亡之际,孙奇逢曾力阻他人退、处,说“今日之事,尽的一分职业,便是报的一分朝廷”(《与鹿太公成宇》,《夏峰先生集》卷一);说“国家多事,需才正殷,恐东山不得高枕卧也。弃世入山,虽是英雄回首,而时局世变,分明利害切身。安石不出,其如苍生何”(同卷《复陶稚圭》)!由此可知他本人的“处”,出于不得已,确系必不可出。清初颜元不曾入仕,境界微有不同。其人对于事功,较孙氏更有一份关切。颜元驳朱子,说“然则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终身只在书室中,方可得道乎”(《存学编》卷二《性理评》,《颜元集》第63页,中华书局,1987)?他叹息别人的不见用,未能“扬眉秉笏,献替殿陛”(《祭耆德宋赓休文》,《习斋记馀》卷八,同书第549页),自己未见得没有此种遗憾。
(17) 孙奇逢说过:“仗节殉义之臣,须具一知中之愚,仁中之过,方得淋漓足色。彼仁柔者悠忽不断,知巧者规避多端,一瞬失之,终身莫赎。从来坐此咎者,正自不少。”(《夏峰先生集》卷五《贺公景瞻传》)魏禧也说:“凡做好人,自大贤以下,皆带两分愚字,止于忠臣孝子贞女义士,尤非乖巧人做得。”(《魏叔子日录》卷一《裹言》,《宁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刊本)卢象昇就曾自说“愚心任事,谊不避难”(杨廷麟《宫保大司马忠烈卢公事实俟传》,《卢忠肃公集》卷首)。在他们看来,力图撑持世道,挽回气运,知不可而为,正赖有此“愚”。
(18) 祁彪佳撰有《施药缘起》,激励同志者从事施药这一善举,曰:“然则吾辈今日尚得盘白石、啸清风,坐而视彼颠连以死耶?”“未必尽如九转丹便能生死人,而获尽吾辈不忍死生人一念,庶不至推同胞于膜外耳。”(同书卷二第32页)
(19) 对上述“民间政治”似不宜估价过当。我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上编第二章第二节,对于缙绅所从事的“民间政治”、缙绅在地方事务中的参与已有讨论。依据我所掌握的“言论”材料,尚不足以估量此种参与的规模与成效。在本文所论的这一时期,“民间”并不存在足供此种政治展开的广阔舞台,士人也不曾被提供了不经由权力机构直接作用于社会的更有效的途径。事实上,所谓的“民间政治”往往由致仕、居乡的官员(赖有其仕宦背景,即赖有其曾经据有的政治资源)主持,“民间政治家”通常不过代行官府之事;“民间”与“官方”的界限于此未见得分明。
(20) 刘宗周将“师儒”与“臣”的角色作了区分,力图“格君心”而并不即废“臣”的职掌,不但表现出对政情、民情的熟稔,且决不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即家居的刘宗周,也仍然随时显示了其施政才能。读刘宗周、祁彪佳等人文集中有关赈济的文字,即可感其人任事之勇,谋画之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