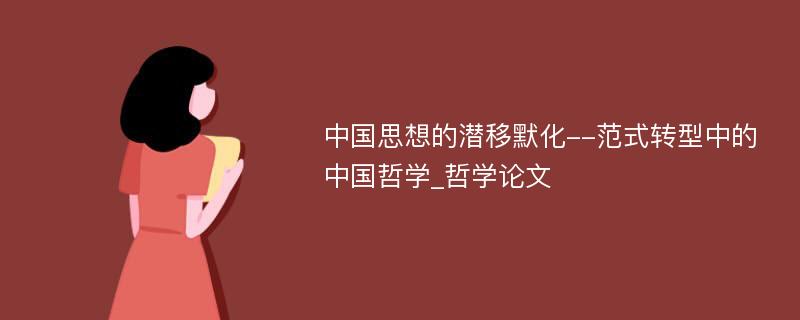
中国思想的隐秘渴望——范式转变中的中国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范式论文,隐秘论文,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03-0011-05
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本无哲学。的确,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名相。但持论者当然并不仅限于计较名相之有无:说中国本无哲学,并不止于说中国本无哲学之名相,而是说,中国本无源自古希腊的那种称之为哲学的思想习惯和传统。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孔子的《论语》里讲的只是一种哪里都能找得到的“常识道德”,“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而《易经》中的思想虽然表明“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但也“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超不出抽象的开始”。(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120、131页。)
反对者认为,虽然哲学一词出自古希腊且中国的确没有希腊意义上的哲学传统,但以“哲学”之含义来类推,则不能说中国本无哲学。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的引论中首先讨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他说:“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以此界定来看,若说中国没有哲学,就“根本是霸道与无知”。这种论证方式具有典型性。如果我们仍将“哲学”乃源自希腊思想传统作为推论之前提,那么,论证中国哲学的“本有”实际上可分为两步:首先将源自古希腊的地缘性的“哲学”概念上升为一抽象、普遍的共相;然后将此抽象、普遍之共相投射到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映射出中国思想之为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就其符合哲学之普遍共相而言,可以证出中国哲学之“本有”;就其与西方哲学之差异与特殊性而言,可以阐明中国哲学之特质。从修辞学的角度看,这种论证过程毋宁是一种隐喻性的投射。正是通过将中国思想与“哲学”构成一种隐喻关系,中国思想才被认为是一种哲学。
经过这样解释,中国本来有无哲学的问题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即使是像牟宗三那样持鲜明立场的人说中国本有哲学,也并非就其原本的存在而言的,而是诉诸诠释。诠释作为一种证明过程,才是中国哲学真正的诞生过程。通过诠释,使中国思想呈现为哲学,从而也成为哲学,从而证明中国本有哲学。因此,如果把中国思想看作是一种非哲学式的文化思想传统,那么,所谓中国哲学,就是中国思想的哲学化诠释。正如一部基督教哲学史就是基督教教义或圣经叙事不断被哲学诠释的历史一样,中国哲学的历史也将是中国思想不断被哲学诠释的历史。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在近现代以来的遭遇,成为中国思想的一种天命性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所指涉的,就是中国思想的哲学天命。也正因为如此,诞生于近现代的中国哲学也注定是比较哲学,比较性语境下的视阈融合是中国哲学不可逃避的诠释学原则。
也正如在基督教哲学史中希伯莱传统与希腊传统一直存在着巨大的、无法消除但也是创造性的张力一样,在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也将一直存在这种类似的创造性张力。有两种观点都与对这种创造性张力的领悟有关。刘小枫曾举冯友兰的“有似论”为例,认为现代中国哲学未能免于比附,反映出“中国哲学的现代性焦虑”。(注:刘小枫引冯友兰《新原道》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冯友兰的“有似论”:“理之观念有似于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及近代哲学(如黑格尔的哲学)中底‘有’之观念。气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无’之观念。道体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变’之观念,大全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绝对’之观念。”但冯友兰在这段话后面有一个总结,明确了他在这里谈论的是他自己的新理学的观念,是他自己“接着讲”出来的新观念,而非传统儒家的观念。刘小枫显然忽略了“有似论”的诠释学意义。在冯友兰那里,“有似”已然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学方法与原则了,从中看出中国哲学的现代性焦虑固然是洞见,但停留于此未免浅陋。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1-162页。)但他显然忽视了类比的意义。简陋的“有似论”虽然显得很粗糙,但“有似论”实以类比的想象力为基础,而类比的想象力正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因而他所谓的“中国哲学的现代性焦虑”应当看成是对上述创造性张力的一种刻画。毋庸质疑,这种焦虑还将继续;同样毋庸质疑的是,这种焦虑不是坏事。
另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西方性反而意味着哲学的局限性,而中国思想没有这种西方式的局限。需要注意的是,持论者仍是在比较性语境中、甚至仍是以西方哲学的范式为基础得出这一结论的。比如以现象学的观念与方法取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观念与方法去反观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进行观念之间的格义,因而我们可以说,实际上这种观点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领悟到了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的这种创造性张力,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否定的方式表达出来。说中国思想未能免于对西方哲学观念的比附,隐含的意思是说中国思想无法摆脱西方哲学的范式控制;说中国思想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隐含的意思是说中国思想颇能契合于西方现代的存在论思想,西方哲学仍然是中国思想的评判标准。
就中国思想哲学化的方法论而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具有开山之功,如其后来所自述的那样。《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由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名学发展史》的底稿改写而成。但这种改写并非随意拼凑,而是蕴涵着胡适对哲学史的独特理解。《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于1919年出版,195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该书时胡适在书前写了一个“自记”。在这个自记中,他回顾说:“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他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把古代思想分为六家的看法,而是认为,“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因为“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这虽是他的著作最初发表时的一个主导性看法,但时隔四十年后,他仍然坚持之:“这个看法,我认为根本不错。”(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见《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也正是关于哲学史的这个基本立场,使胡适自认为他的著作“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不过,他感到遗憾的是,“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人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见《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胡适该著在当时的价值,蔡元培在为该书作的序中有很好的概括。蔡元培总结了该书的四个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见《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其中最重要的是“系统的研究”。蔡元培明确地说:“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见《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对这一点,冯友兰评价说:“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确实是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实质系统加上了一个形式的系统。虽然其所加的未必全对,但在中国学术界,则是别开生面的。”(注: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胡适该书也受到了大量批评。牟宗三说胡适的作法是“舍本逐末,以求附会其所浅尝的那点西方哲学,而于中国学术之主流,则反茫然不解。”(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这大约是一个最主要、也最严重的批评了。梁启超1922年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讲中认为,胡适专从知识论的角度观察中国古代哲学,虽然这种视角“有益且必要”,但“恐怕有偏宕狭隘的毛病”,未免戴着实验主义这个“二十世纪的洋帽子”“强古人以就我”,因此,胡适的书中,“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尤其是对那些并非以知识论为中心的思想家,其“根本精神,绝非凭知识可以发现得出来”,在此,胡适的方法只能是“弃菁华而取糟粕”。(注:参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以上种种批评,一言以蔽之,即:运用西方的知识论或名学的方法并不适合体现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这似乎蕴涵着几层意思:一,假定了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首先对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有所领悟;三,要寻求恰当的哲学方法以图恰当地体现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方法论上的谬误或不恰当将不能呈现中国思想的本然面目。所以,对于中国思想,西方哲学首先意味着是方法论。这一点也关系到研究者个人的特殊信念、立场。蔡元培认为胡适该著的一个特长是“平等的眼光”,冯友兰解释说,所谓“平等的眼光”,是指其批判了古代社会的正统观念,不再独尊某家某派,而是给予诸子百家以同等地位。胡适该书以老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冯友兰对此有不同看法。胡适自谓在二、三十年后他才恍然大悟:“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证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为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为‘万世师表’。”(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见《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如果说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是要靠服膺者的特殊体验才能真正把握,那么,胡适与冯友兰之间的这个分歧就颇值得玩味。正如神学家所做的是以信仰为前提的“内部研究”,而从事宗教哲学研究的人却不一定将自己的立场牵涉进来一样,研究中国哲学是否首先以一种服膺者或类似信仰者的态度对待之,将在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分歧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胡适的上述批评在当时的学术界很有影响,很大程度影响了后来的写作者。冯友兰在写作他的《中国哲学史》时就力图从他所以为的更为“本然”的角度去梳理中国哲学。这种差异明显地反映在文体上。冯友兰在叙述胡适该书的轰动效应时特别提到了其在写作形式上的“特别之处”:“在封建社会中,儒家的经典被认为是最高的真理,后来的著作则被认为是经典的注解,以注疏的形式发表出来。在形式上,经典的原文是正文,用大字顶格写出;注疏是注解,用小字低一格写出。胡适的哲学史则与此相反。他以自己的话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出;所引的经典著作,以小字低一格写出。”(注: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这种新文体虽然造成了轰动效应,但同时也可能是该书有比附之嫌疑的一个“罪证”。冯友兰有鉴于此,在文体上更多注重、甚至采纳了传统的注疏方式,尽管注疏所依凭的观念已然是西方的了。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我们随处可见大段引用原文,引文之后是用西方哲学的观念作的注疏、诠解。冯友兰的这一作法显然获得了承认,甚至获得了陈寅恪“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的美誉。但牟宗三对冯友兰的这种努力不以为然。他认为冯友兰缺乏的是对中国思想之根本精神的深刻体验,故而仍未能摆脱以西方哲学之概念假设所铸成的普罗特拉斯忒斯之铁床去使中国思想“屈就”的窠臼。这种附会的责难一直是现代以来治中国哲学的学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所有现代以来治中国哲学的学者都是“西方哲学的铁床匪”,都得依靠“西方哲学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牟宗三不满于胡适与冯友兰的地方在于,他认为,他们要么将体验排除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之外,要么对中国思想的精神缺乏深刻的体验。但有趣的是,牟宗三、梁启超等人批评胡适所著书的缺陷所在,恰是胡适自以为得意之处,也是牟宗三认为冯友兰的不足之处。胡适与冯友兰的共同之处是二者都注重名相问题,都注重逻辑学与知识论。除了当时开风气之先河的意义外,后人对胡适该著的评价不高,这反映出中国思想的旨趣的确不在逻辑学层面,而在形而上层面。但若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看,我认为仍有必要重新评价胡适一书的意义。
现代西方哲学有所谓“语言学转向”,不同于传统经典诠释学的现代诠释学的出现对于哲学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诠释学既有颠覆逻各斯传统的企图,也有成全逻各斯传统的企图。用诗意秩序来取代原来的逻辑秩序,是要恢复秘索思传统的主宰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逻各斯,而是将之置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并为其所用。(注:逻各斯传统(Logos)与秘索思传统(Muthos)是源自古希腊的两种言说传统。简单来说,前者是指说理的传统,后者是指叙事的传统。关于西方思想史上的逻各斯传统与秘索思传统的关系源流,陈中梅先生在其《论秘索思——关于提出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M-L模式”的几点说明》一文中有极好的梳理,该文载氏著《柏拉图诗学与文艺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但是,解放与破坏似乎总是有一种难以控制的惯性,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修辞学转向彻底冲破了诠释学的初衷。所谓的修辞诠释学已经将秩序的观念完全打破。比如像保罗·德曼,他洞察到修辞肆无忌惮的本性。在一个严谨的、有意义的文本中,语法代表着文本的整体性,而修辞总是沉溺于对这种整体性意义的隐秘的颠覆行动之中。这样,从修辞学的角度看,实际上任何文本总是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而哲学文本所标榜的逻辑谨严性就只是一种修辞效果,本质上只是一个可笑的骗局。保罗·德曼对哲学文本所作的修辞学解构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区别消失了,实际上是解构了逻各斯说理传统而将之归约为秘索思叙事传统。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所有语言都是误用而与存在无涉。(注:参见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4页。)这对一直眷恋存在的哲学之冲击是非常深刻的。总的来说,语言学转向的关键之处是用对语言本身的思考来代替形而上的沉思与冥想。这种转向的意义当然不可否认。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方法论特点正在于此。以名学问题为主线梳理中国思想的思路将是一条新颖而特别的思路。在这方面,胡适与冯友兰的问题都在于将语言问题归结为逻辑学问题,而未能从语用学、修辞学的角度去了解语言的本质。汉语言本质上是诗性的,而在现代以来不得不屈就于逻辑学的铁蹄。
牟宗三与梁启超不满于胡适的地方,其实首先不是附会的问题,而是在于认为胡适降低了中国思想的品格。中国传统思想属重形而上之道,像黑格尔那样把中国思想看作是一种习俗的伦理智慧或道德哲学的看法是肤浅之见。在现代,要想在西方范式为主导的中西比较性语境中保持中国思想的形而上高度,从言说方式的角度看就只有两条路:牵涉到终极关怀问题的宗教叙事方式与牵涉到形而上问题的哲学存在论论说方式。在这一点上,冯友兰基本上站在牟宗三、梁启超一边而与胡适不同。冯友兰所玩味的,仍然是形而上的旨趣,对于逻辑学的注重在他只是一种工具。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新理学中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将新理学的“理”类比于柏拉图的理念,还是强调境界的重要性,实际上都是流连于形而上领域而忘返。表面上看,新注疏文体对应于对中国思想之本来面目的维护,而像胡适那样实验主义的哲学观念先行的方式则有附会的嫌疑,但从中国思想本身的角度来看,这种争论其实不是中西范式之争,而是中国哲学有无形而上层面之争。实际上,西方哲学观念先行的方式虽有附会的嫌疑,但却不一定有将中国思想的理论品格降低的嫌疑。从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层面出发去与中国思想格义,不仅不会降低中国思想的品格,而更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活动。这在牟宗三的哲学思辨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宗教”与“哲学”同是西方语汇。宗教由于其指向终极关怀问题而保持着自身思想的高度,在哲学中只有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才能与之相当。所不同的是,宗教的言说方式根本上是叙事,而哲学则是说理。宗教在现代多被认为是迷信,也不合中国思想的口味。传统学术有汉宋之分。汉学乃经典诠释学,代表叙事—诠释传统;宋学乃“义理之学”,代表叙事—说理传统。概言之,宋学对义理之学的兴趣实际上是一种哲学式的旨趣。在以西方哲学为基本范式的现代比较性语境中,在传统义理之学这种“哲学式旨趣”的刺激下,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或存在论,一直是中国思想隐秘的渴望。虽然比附的指责萦绕不断,虽然总是强调中国思想的独特性,虽然总要预设或承认中国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哲学,一直是现代以来中国思想的隐秘渴望。
哲学的旨趣总是标榜自身超越于宗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要想达到了解的同情,体验是必不可少的。但要使体验成为可交流的,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能够以说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问题。思想之精义是几微的,在于妙悟,而哲学则守护思想。西方哲学首先是一种宏大而深厚的说理传统,首先是这一点才使其成为中国思想的隐秘渴望。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高的。除了自身的天分之外,他选择与代表着近代哲学之高度的康德对话,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消化、检讨这位自称“古今无两”的大哲的思想,将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康德之后,现象学意味着西方哲学(存在论层面)的全新高度,而如何在与现象学的对话与观念互释活动中阐发中国思想的精义,将是一条具有远景的思路。
标签:哲学论文; 冯友兰论文; 牟宗三论文; 中国古代哲学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哲学的特质论文; 哲学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读书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胡适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