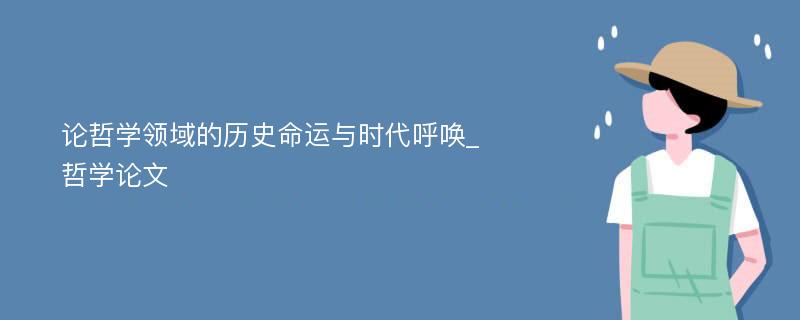
论“哲学境界”的历史命运与时代呼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界论文,哲学论文,命运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就其理论旨趣与反思指向而言,是确立一种通过理论概念的反思方式所达到的精 神境界。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哲学理论存在方式都以或显或隐表达形态映现了对哲学境界 的呼唤。作为一般性的规定,哲学总要以不同的途径表达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表达人 的穷根究底的追问逻辑,表达人对终极关怀的意识,也就是说总要确认或表征对哲学境 界的理解。从哲学境界的角度理解哲学本性,可以使我们从历史迁移的层面上进一步把 握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从理论构建层面上进一步确定哲学境界的“真实”内容,从时 代精神的层面上进一步构建与时代精神的价值取向吻合的“应然”目标。
一
如果从哲学境界的角度看哲学的话,哲学可以被看作对“真实”的追求。人的活动本 性总是将现有世界分化为真实与虚假的存在,在真假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真实”。这 是由于人始终不满足于眼前流变的现象世界,他把得到的或即将得到的都认为是非真实 的。这样看来哲学境界问题总会关系到哲学的“真实”问题。从历史的逻辑考察,哲学 所理解的境界主要是由哲学的“真实”构成的。哲学的“真实”即是“寻求”,又是“ 去蔽”的过程。哲学总要在“去蔽”寻求中去挖掘“真实”。
传统哲学从基本理论取向看是将哲学所求的“真实”视为“真理”,真理作为最高的 智慧构成哲学境界的核心内容,“真实”之所以为“真实”,在于论“理”,没有“理 ”的“真”不成其为“真实”,“真”与“理”的内在结合形成了知识(智慧)的哲学境 界。柏拉图在定义哲学家时反复强调哲学家是那些洞见真理的人:“哲学家在任何时候 都热爱真理。”可见,一讲哲学必言真理,此为从柏拉图开创哲学传统以来恒定不变的 理论主旨。
泰勒斯始,先哲们就将眼光盯住遥远的对象,用心灵去把握对象,以追问和获得“真 理”为荣耀。柏拉图认为,“真”为概念、理念。“edios”不能为之“真”,只有成 为“idea”,才能构成“理”之上的“真”。哲学的任务正是用“理”去论“真”,将 “真”联成“理”。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理念的整体的真理,现象流动不居,无“真”可 言,因为现象只是现象,它无“理”可讲。真理乃为“ideal state”(理念状态)。哲 学是求“真”成“理”的学问。其后的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指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页。);“哲学被称为 真理的知识”(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页。)。基 础在最初历程中就已确定了,其后一直到黑格尔哲学那里,这一观点也没有发生实质上 的改变。
近代哲学的主题仍然是探求哲学的“真理”,分歧只是以何种途径才能到达哲学的“ 真理”。对知识、理性的自信有时甚至达到自负的程度。“真理”被看作“真知识”、 “真观念”,“真”能成为“理”,必定存在着表象与对象的符合关系,其中隐含着主 体与客体分立的理论前提。“真实”原本为哲学本源性的问题,近代哲学将它置于知识 论的范畴内,变成了知识模式的问题。近代哲学表面上谈的是哲学,骨子里却渗透着知 识(科学)的思维方式。“真实”被认为在“知识”之后,“认知”成为哲学之“真实” 的范本,哲学的境界背后有一个与其并肩而立的知识境界,知识境界甚至取代了哲学境 界。“知识就是力量”,在当时与其说是科学的命题,不如说是哲学的境界。
康德意识到了哲学追求“真实”之路并非仅靠“理”所能维系。人作为主体性存在在 求真方面有着二元的不同性质。“理”可以表现“真”(理论理性),“真”又不能被“ 理”全部地证明(实践理性)。人的“真实”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映现,而不仅仅等同于“ 真理”。作为自由的真实,它应是人的最高本体或人的终极目的,这又不是认知的真理 能够表明的。(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2页。) 至少康德在这里暗示一元式的真理思维方式不能完整地表现哲学之“真实”。黑格尔不 满意康德哲学的实质在于,康德所讲的哲学的“真实”是断裂的,不完整的。黑格尔相 信依赖于“理性”就能达到“绝对”的“真”。他对“真理”的赞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 程度。在他看来,真理既是过程,又是目的;既是前提,又是结果;既是逻辑必然性的 展开,又是自由精神的归宿。(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351页。)哲学是关于“纯粹自由思想”的真理。哲学的境界是哲学求“真实”所获得 的真理(知识、科学)。
传统哲学将哲学之“真实”等同于“真理”,哲学境界就是真理(知识、科学、智慧) 境界,真正的哲学就是把握、知晓真理的理念、真的知识,这就规定哲学总要在“物理 学”之后成为一种知识形式的东西。“真”只有合乎“理”才成其为“真”,也只有“ 理”性的“真”才具有普遍性、确定性、永恒性。现代哲学对哲学之“真”的探求是在 另一个基础上建立的。“真”被“理”所蔽,关键在于“去蔽”。假如“理”为“遮蔽 物”的话,那么问题的关键是“消除”或者“悬搁”,也就是括上遮蔽物,最后留下“ 现象学的剩余者”,于是就会发现哲学之“真实”乃为个体的“真在”。现代哲学无论 怎样解释或说明哲学之“真实”,都没有超越出在破除“真理”之后对“真在”的解释 。
“真在”先于“真理”,“真”首先是“在”,才有对“在”的“真”的“理”。“ 理”与“在”应统一于“真”,而不是主观表象与对象的符合一致。“真”原是“在” 与“理”未分化、混沌地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理”对“在”是抽象,“理”对“真” 的抽象的结果未必不是假的,因为“真理”是板结的、固定的、永恒的,“真在”是活 生生的,必然是历史性的,与时间性是不可分的。“真理”是非时间性的“真”,此种 性质的“真”,既然是永生的,这就不属于个体的“真在”,与假的、死的东西无法分 别。“真理”是抽象的,“真在”总是具体的。
胡塞尔现象学关注的也是哲学的“真实”的问题。当他说明哲学的明证性、绝对性、 意向性时,论证的目的在于解释什么是“真实”。胡塞尔看到了哲学“真实”对哲学的 意义。哲学作为真实性的“本质”,“探究方式是如何重要——也许比任何其他哲学方 面研究都重要”。在胡塞尔看来,知识面临的世界固然有许多“真理”,事实上却是一 个“死”的世界。哲学的开端并非笛卡尔说的“我思”,哲学的“真实”在于“我活着 故我思”(I am living Cogito)。人生活的是“活”的世界,求“真”的人不是“真理 ”的静观者,必须“摆脱”、“排除”自然朴素的态度,这就有必要将自然的(感性的) 世界括起来,当把“自我”作为“活体”看待,而不是当作“自然”时,“世界”与“ 人”才能通过意识意向性的“灵性”成为活的整体。
海德格尔对“真在”的描述对寻求哲学的“真实”的西方哲学更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意 义,海德格尔终结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某种哲学思考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就 是“真”,“在”是“直接”的,一旦“在”成为“间接”的,“在”的“真”就变成 “在”的“理”了。“在”的“真”告诉我们它“不是什么”,而是在显现什么,它永 远表现为“是”(Being),而不能成为“什么”(What),成为了“什么”,也就不再为 “在”,而为“本质”(whatness)了。海德格尔对“真在”(Dasein)理解的“真义”是 :“在”不可能对象化,不能成为“事实”,所以哲学的“真实”不是对“对象”的描 述。“在”的本质性表现为“在”在运思、筹划、释义之中,“在”自身的“在”中领 悟“在”,这就是哲学应有的心态(境界)。“在”在人事纷繁、声色利货的裹杂下被诸 种抽象的概念所包容,也就成了“非存在”。
海德格尔的理解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得到了随意的读解和进一步的发挥。后现代的“后 ”(post)不是时间的间距,而是“前溯”。所谓无中心的边缘状况,消解逻各斯(logos )支点,回到精神平面化,对误读的历史式修正,以及在沉沦中的漂泊,不过是“真在 ”的多重化释义的方式。“真在”似乎是“一丝不挂”的现象,没有任何附加的因素, 不仅要排除“文化”,还要去除“哲学”。“真在”倘若最关键的是“在”,这就与境 界无缘了,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境界问题了。这样,问题的实质则成为,“真理”之真与 “真在”之真究竟何为“真实”呢?
二
哲学境界追求的是“真实”。人每时每刻都需要“真实”,依据人对自身的理解确立 “真实”,进而赋予自身的活动以统一的根据。从历史沿革看,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对 “真实”的寻求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取向和原则,在外观上体现了“真理”与“真在”的 对立,虽然“真理”与“真在”都是人的真实性规定的不同侧面的表现。
哲学的分裂乃是人自身的分裂结果。这一分裂的根据在于人的本性的矛盾性。“这种 两重性的本质,是人的所有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前提,也是人的所有一切活动的本体论 、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注:高清海:《哲学的憧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版,第61页。)人的本性两重化使得人对自身所寻求的“真实”具有了两重化特征,人 与自然关系的两重化性质表明人一方面要依附于自然,将其归属于世间自然存在的一个 种类,另一方面人又要超越于自然,使自然服从于人的需要,这一哲学的双重定位就需 要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确认哲学的“真实”。
从“真理”的方面来看,“理”为人所独具,因而“真实”的东西不在人外,而在人 中。人与非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理”,从“理”中去看人与自然关系,方可发现“ 真实”东西的存在,故而“真”才成为“理”,“理”也可以成“真”。从“真理”出 发,就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人借助于“理”对自然的否定性关系,在对自然的否定 性关系中才能映现“真实”的世界。显然“真实”存在于属人的世界中,因为“真实” 在人具有的“理”之中。“真实”来源于人的超自然本性,表现了人力图超越自然性质 、合于目的性活动的性质。从“真在”的方面来看,“在”是“真实”存在的前提。没 有“在”,无所谓“真”,人作为赋有生命的有机体,必然受到自然的支配,具有着生 命存在的特征。人首先是“在着”,其后才有“在”所产生的其它因素,诸如“理”等 。人可以没有“理”,但却不能没有“在”。这样“真”的东西就不会也决不可能存在 于“理”中,“在”就是“真”。“真”不是超自然的,“真在”意味着对人而言,“ 真”的东西只能是在生命基础上的“存在”。从思维的取向与理论的原则加以考察,无 论是将哲学的境界诉诸“真理”,还是诉诸“真在”,其实质的对立集中体现在下述几 个方面:
第一,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对立。哲学境界追求的是“真实”,实质上是“人”的实质 。这一“真实”的基础的确立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了。以“基础”的理解就有一个是以 “直接性”为起点,还是以“间接性”为开端的问题。如果哲学所理解的“真实”基础 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的话,这就可以理解为“直接性”,而对感性世界的流变 性质的否定就会提出与“直接性”对立的“间接性”世界的存在,而后者才可能看作真 实的。其实,人不能没有“直接性”的世界存在。人存在着,这是最“直接性”的东西 ,无论是生活、生存,还是感性活动,都是“直接性”的现实认证。但人又不能仅停留 在“直接性”上,人总要提出、确认“间接性”的东西使自己的“直接性”有其价值和 意义。
第二,时间性与非时间性的对立。“真实”的东西究竟是在时间之内,还是在时间之 外去理解呢?这是对哲学“真实”的寻求的又一理论分歧所在。“真实”在时间之中就 是“在”,即使“在”没有任何规定,也是“在”着,“在此”或“在彼”。假如“在 ”已不在了,就成为“非真实”的东西了。个体“真在”是活着的暂时性存在,没有时 间,没有绵延,没有历史,就没有“真”的“在”。脱离了“在”的“真”,虽然能够 获得“永恒”,但根本不是人的“真实”,而是一种貌似“真实”的“幻象”。任何真 正的哲学都不会诞生于现实生活的艰辛困苦之中。“在”为“真”之本。假如“真”如 果是“理”,那么“理”就应超于时间性的制约,依存于时间的“真”乃为流变现象之 “真”,是转瞬即逝之“真”。与其说是时间之“真”,莫不如说是一种“虚幻”。“ 真”的东西一旦进入变化,有了生成,具有了历史的性质,“真实”就成为“假”的东 西。“真实”是不变的,它就不能与时间性有关。
第三,对象性与非对象性的对立。将“真实”视为“理”的产物,“真实”就注定能 成为对象性的存在。而将“真实”视为“在”,则“真实”必定无法成为对象性的东西 。对哲学“真实”的理解就存在着对象性与非对象性的分野。这一对立的深层基础仍根 源于人的二重性矛盾关系。人总是力图借助于将自然的对象化方式表达自己对“真实” 的实在性理解。“真实”的对象化体系恰由“真理”的概念、范畴、框架所构成。“真 实”是人对象化的产物,反过来又成为人所寻求的“真实”。然而,“真实”一旦成为 “理”,成为对象化的东西,它就与人的“真实”分道而行了。或许人的“真实”就在 于人自身的非对象化的方式。“真”的“在”不能被还原为对象化的存在,原因在于人 不能还原为知识。从人的方面去看“真实”的话,“真实”就是非对象化的存在。
第四,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对立。哲学的“真实”可以由内外不同角度去确立。“真实 ”倘若由外在方面去考察,这就是将哲学作为“宾语”的哲学(Philosophie),如果从 内在方面去分析,则是将哲学作为谓语的哲学(Philosophie)。(注:倪梁康:《现象学 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5页。)作为“宾 语”的哲学就是不断构建“真理”的哲学,注重的是结果、归宿。作为“谓语”的哲学 就是“真在”显现、释义的哲学,注重的是活动、过程。前者体现了“真实”的外在性 角度,后者表明了“真在”的内在性方面。同样,人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矛盾仍是人二 重性矛盾性质的表现。一方面,人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以满足自身的需要, 人必须“敞开”自身,接受一切外在可接受的东西,人要使自己的思想、观念、认识、 意向以客观的方式对象化。与此相吻合的是,人只是通过确立哲学的“真实”提供外在 性的尺度与内容。人要找到人之外的“对象”(object)、“客体”以构建哲学要求的“ 真实”,这也说明从外在性角度看,人表现为向“对象”的迁移与生成。另一方面,人 又以自身的内在世界作为追求“真实”的目标,人在向“内”开掘的过程中又会形成主 体的体验、观念、认识的积淀。
第五,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对立。从“真理”出发,“真实”的世界应是同一的世界, “真”借助于“理”成为体系,又通过“理”产生平均的可理解性,以“真理”为核心 的境界对人而言,是没有差异的普遍同一的世界。从“真在”出发,“真实”的世界就 不是板结一体、凝固不变的世界,而是由个人参与其中,又各具独特性的差异性世界。 以“真理”为“真实”境界,就要用同一的世界去规定互有差异的东西,因为“真实” 不能“分解”,也不能被“还原”,它应是“同一”,也就是多中无法挥抹掉的“一” 。“真理”是总体的“一”,到处可“见”,又四海皆“准”。理念是“原型”,无生 无灭的,只是分出各种“现象”。“真理”的“真实”乃是无差异的同一。“真在”的 “真实”是从个体的角度确立的,“真在”是“多”,是依据不同的存在而确立的“真 实”。“真”一旦借助于“理”,就成了平均可理解的“真实”,这就失去了“真实” 的本真性规定。
综上所述,关于哲学境界的解释始终存在着根本对立的不同思路。无论是将哲学境界 的“真实”看作“真理”还是“真在”,都根源于人的二重性矛盾本性。只有深刻地理 解、把握二者内在冲突的实质,才有可能准确说明二者的得失之处,才能在人的二重性 矛盾性质的真实把握的基础上对哲学境界的“真实”提出科学的、现实的规定。
三
寻求、确立哲学境界意义上的“真实”是人的本性。对“真实”的把握是同对人的本 性的历史理解一致的。人在确立“真实”时,总要力图使“真实”具有清楚明白的自明 性。在构建过程中,人又总不可避免地将“真实”看作设定的自明性,而不是原初的自 明性。哲学曾经扮演过真理看护者的角色,有着“科学之科学”的“盛誉”。科学的“ 真理”成为哲学追求“真实”自明性与精确性的楷模,哲学将众多学科统括于自身的“ 真理”之中,哲学的“真理”是裁决、评判、推进知识的“母体”。然而,对“真实” 寻求的过程却使哲学日益走进困境。包罗万象的哲学在不断分化出去其他学科的同时, 也使自身曾经十分稳固的“真理”的“真实”不断地被消解下去。哲学终于发现,“精 确”、“自明”的“真实”原本不是哲学的“对象”,而是知识类学科的内容。哲学内 含着一切的“有”开始进入“无”。“真实”对哲学来说已不复存在了。看护者“丧失 ”了看护的“对象”,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因此,可以说哲学境界的“真实”乃是矛盾,这样就意味着“真实”的境界的现实基 础是人的实践活动。哲学意义上的“真实”显然既包括“真理”,又包括“真在”,任 何采取单一的或抽象规定方式对“真实”的界说都是非真实的。这也就是说,人所寻求 的“真实”境界既有着确定性(真理),又有着过程性(真在)。在一定时间内真理的确定 性是相对稳定的,构成了特定时代的“真实”,而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一真理的确定性 就变得相对了,从而“真实”的内容就产生了时代性的转换。“真实”不仅仅是“真理 ”,表明哲学始终有自己所面对的对象,哲学不仅是“科学”,不仅是“知识”,更不 仅是总和的“智慧”。“真实”又不仅是“真在”,哲学的“真实”不是主观精神之流 的飘浮,而是在主体与对象性的现实关系中实现或完成“真实”的构建。哲学境界的“ 真实”,既讲“在”,又讲“理”。“在”讲我们在生活,“理”讲我们怎样生活,不 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其一,哲学境界的“真实”乃是对人的“真实”本性的把握与表达。哲学归根结底是 研究人的,人是哲学的奥秘。人的“真实”可以通过不同的研究加以规定,但人的“真 实”又不能最终加以确定。人的“真实”是能在历史生成中加以把握。无论知识(科学) 世界,还是宗教世界、道德世界等等,都是表现人的“真实”的一个侧面。对人的“真 实”的表达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且能“事过境迁”的,人不断地创造属于自己的“ 真实”,又亲手破坏曾经自慰人本身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史就是人探索 “真实”、确立人的境界的历史。人是不断确立“真实”、超越现存的存在。可以说, 所有关于“真实”境界的哲学观点都可以在人的实践本性与历史活动中找到其深层的内 在根据。“真实”离开了人只是“虚幻的真实”,“境界”离开了人也只能是抽象永恒 的境界。哲学的境界仍然是境界,哲学的“真实”还是“真实”,但这些只有在人的历 史性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其二,哲学境界的“真实”乃是肯定与否定互为统一的“真实”。哲学境界的“真实 ”体现为将肯定因素置放于否定关系之中,这是因为人总是借助于否定性的统一关系构 建构哲学境界的“真实”。“真实”不是决然诉诸肯定因素,体现在人与自然对象的原 初的尚未分化的直接统一之中,而是将肯定因素置于否定的,在肯定与否定的,在相互 转化中不断地实现这种内在融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这就表明,哲学境界的“真实 ”是在否定中(超越中)不断实现的统一性产物。从人的生成与发展角度看,哲学境界的 “真实”实质上是人所创造的“真实”。今天对人而言是“真实”的东西,在明天看来 就会转化为“非真实”的东西了。作为辩证统一的哲学境界意义上的“真实”只能在肯 定与否定、表达与迁移、转向与创造之中实现。
其三,哲学境界的“真实”乃是基于人的自为本性的超越性的“真实”。人的本性的 自为性质体现为人的超越性,这一超越性质,如马克思所说,是在对象化关系中对自我 的确证,(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 页。)是自然向人的生成。因而,强调哲学境界,诉诸哲学的“真实”,更突出地强调 了人自身的本性,更明确指出属人化世界的价值。
第四,哲学境界的“真实”乃是以人的人文精神为内在性的“真实”。作为自我意识 的理论表现方式,哲学对人“真实”寻求总是在人的生成的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性在其历史活动中体现为“一直努力想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创造自己的真实存 在”。而人的生成须经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的形态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 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等发展阶段”。三个发展阶段对应人的生成,表现人的群体本位 、个体本位和人的类本位的不同历史时期。从哲学境界的“真实”角度看,这就是要使 人能够以“全面方面”占有人的本质,随时随地都能用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来度量“对 象”,来构建“真实”。
从时代呼唤的角度说,哲学境界的研究确立了理解哲学思维方式的新度。哲学境界的 确立与哲学“真实”问题的提出,使得哲学的思考目标、方向、理解层面有了全新的意 义,使得对哲学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有了理论分析框架,使得对哲学的未来发展前景有了 新的描述。哲学境界的研究确立了理解人本性的新角度。哲学本质上是对人的研究,哲 学是人从自身角度观察世界的自我意识方式。哲学境界从深层次上确认了哲学在人的精 神层次上的品位,表明了人的超越性的“应然”本性,勾画了人的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 。哲学境界的研究提供了确立理解形而上学的新角度。人需要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 能够表达人作为类存在规定的内涵,形而上学作为人自身本性追求的内在理论方式表明 ,构建时代的理想的形而上学,是确立现代哲学境界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的深切呼唤。 哲学境界的研究提供了确立理想人格的新角度。人格境界同哲学“真实”的境界是同一 的。确立哲学的“真实”,目的在于引导人领悟存在的整体意义,升华人文精神,培养 高尚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