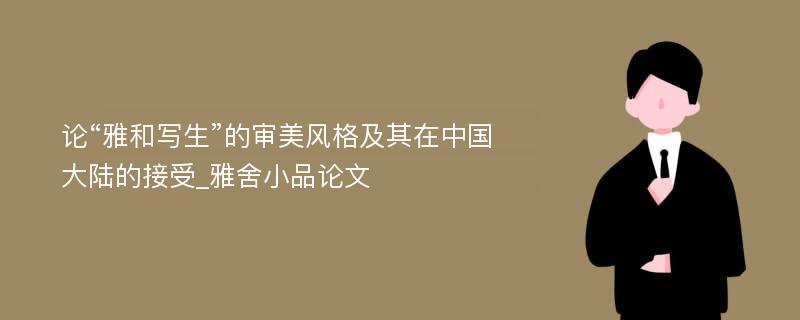
论《雅舍小品》的审美风格及其在中国大陆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陆论文,小品论文,风格论文,雅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梁实秋而言,在中国大陆写作发表、在台湾才得以出版的《雅舍小品》,意味着一个不平凡的转折。当梁实秋热心于文学批评与政治评论的时候,中国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促使他关注国家的兴衰,匡正时弊,从而写出了一系列尖锐泼辣的文学批评与政治评论文章。于是,天生好斗的梁实秋与更为好斗的鲁迅等左翼作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民主言论与自由理想又经常触犯蒋介石当局,从而左右不讨好。在这种时候,梁实秋的苦闷与落寞是可想而知的。人在苦恼烦闷的时候,或者遗世出家,或者在艺术的情感宣泄中得以解脱,这就是为什么梁实秋在抗战后期开始创作“与抗战无关”的小品文章,并且从此开始,与文人论争的文学批评以及与政治当局论争的政治评论就很少在梁实秋笔下出现了的原因。《雅舍小品》的这种创作背景,对于研究其审美风格是非常重要的。梁实秋的性格是很倔强的,从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时的一些艺术主张,到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时所受到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而产生的反动,都可以在他的《雅舍小品》中找到影子,甚至可以说,《雅舍小品》是梁实秋用文艺创作的方法,对此前所有针对他的批判的一种艺术回应。离开了这种创作背景,干巴巴地总结出《雅舍小品》的几条艺术特点,并不能真正洞悉《雅舍小品》审美风格的真谛。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梁实秋与左翼文人的论争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但焦点集中在理性与情感、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上。梁实秋站在理性与人性的文艺立场,对于放纵情感的五四新文学的浪漫传统进行了清算,对于强调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学进行了批判,从而张扬带有浓重古典主义倾向的表现人性的理性文学。当然,情感也是人性的表现形式,梁实秋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文学中的情感,而是卢梭之后不受理性束缚的情感表现。在梁实秋看来,人性之所以不同于兽性,就在于动物的感觉、欲求不受理性的约束,而人的感情、欲望都要受理性的约束,否则人就等同于野兽。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实秋心目中的人性与理性是一致的,而且这种人性是永久不变的。
梁实秋的这种理论倡导以及对左翼文学的批判,在他的《雅舍小品》中就有典型的表现。这些小品自然流露着梁实秋的爱憎感情,也有形象的比喻,但是这种感情与想象力是受理性控制的;如果理性的成分太多,就不是艺术性的小品,而成了人生智慧的论文了,梁实秋个别小品之失正在这里。但是《雅舍小品》中的大多数文章,却是不乏情感的流露,这种情感往往是以反语或者讽刺的笔调流露的,甚至有的时候直接表露爱憎。这些小品也不缺乏想象力,常常是以形象的语言娓娓道来。只是梁实秋的小品是将情感与想象力纳入理性的约束之中,不导向“浪漫的混乱”,而且理性的因素还给文章增加了一种哲理内涵。“雅舍小品”往往是以人生的一个大题目如男人、女人、孩子、中年,或人生的伦理道德行为如谦让、握手、第六伦、送行,或人类的分工如诗人、医生以及人生的一些其他行为作为标题,然后就此题目展开论述,只是并非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述,而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及对这个题目的爱憎,展开想象的翅膀,从而使这种文体介于纯美的艺术品与逻辑论证的论文之间。
《雅舍小品》还表现了梁实秋反对“普罗文学”的阶级论时所倡导的“人性论”。譬如《女人》、《男人》等文,写的就不是那个阶级或者那个时代的女人或男人,毋宁说,作者努力的方向,是想从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时代的女人或男人中发现一种共同性,也就是“永久不变的人性”。如果说《女人》和《男人》写的是以“女人性”和“男人性”为特征的性别属性,那么,《病》、《客》、《脸谱》、《中年》等篇则仿佛是写不同年龄与语境中的人性。
梁实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时,曾说与抗战有关的文章最为欢迎,与抗战无关的文章而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此论受到了左翼文人的围攻。其实梁实秋在编辑这个副刊的时候,还是颇多顾忌,发表的还是“与抗战有关”的文章居多;而一旦只对自己负责写起小品来,他就完全由有所顾忌进入了一种自由状态,甚至可以说是用艺术实践对于左翼文人的批判进行回应——我的小品就是写“与抗战无关”的,难道就不成为艺术品了吗?到底你那些“抗战八股”经得起时间考验,还是我的小品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雅舍小品》中有十篇左右是写于抗战后期的重庆北碚,然而几乎没有一篇是与抗战有关的。那个时代的血与泪、屠杀与轰炸、为国捐躯与发国难财,都与“雅舍”无关。从“雅舍”看出去,但见“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时,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于是在雅舍所写,从女人、男人到孩子,从音乐、下棋、写字到画展,从谦让、握手到讲价,都是从一个角度观察人生的智慧闪光,不但与抗战无关,而且与当下的时事亦无关,更不是什么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就像中国宋元时代的山水画,社会的动乱,外敌的入侵,在画面上找不到丝毫的痕迹。如果欣赏者在这种绘画面前凝神欣赏,自己也会忘却社会的离乱与外敌的入侵,而进入一种空灵妙悟的艺术境界。
由于《雅舍小品》在台湾出版之后意外地畅销,甚至被说成是“华语散文的瑰宝”,梁实秋就一发而不可收,又陆续写作了《雅舍小品》的“续集”、“三集”。但是,后来写作的两集与《雅舍小品》相比,在材料范围上与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对《雅舍小品》在最上的扩大。譬如,《雅舍小品》中有《中年》,“续集”中有《老年》,“三集”中有《年龄》;《雅舍小品》中有《谦让》、《第六伦》,“续集”中有《敬老》、《商店礼貌》,“三集”中有《送礼》、《代沟》;《雅舍小品》中有《信》,“续集”中有《书》,“三集”中有《讲演》;《雅舍小品》中有《病》,“续集”中有《聋》。《雅舍小品》在谈到男人的时候谈到男人的一些“脏”、“懒”、“谗”等品性,在“续集”与“三集”中都列有单篇的讨论。《雅舍小品》中有《衣裳》、《汽车》,“续集”中有《手杖》、《滑竿》;《雅舍小品》中有《旅行》、《运动》,“续集”中《观光》、《睡》,“三集”中有《喝茶》、《饮酒》、《抽烟》;《雅舍小品》中有《猪》、《鸟》,“续集”中有《狗》、《虐待动物》,“三集”中有《腌猪肉》……《雅舍小品》的巨大成功以及一印再印,还鼓励了梁实秋以“雅舍”为“商标”写作了《实秋杂文》、《西雅图杂记》、《白猫王子及其他》、《雅舍谈吃》、《雅舍散文》及“二集”等涉及面更广的散文,《秋室杂忆》、《看云集》、《槐园梦忆》、《雅舍杂文》等怀念文坛故旧、亲朋与发妻的散文,《梁实秋札记》等读书心得散文,使得“雅舍商标”驰名台湾,梁实秋也成就了一代散文大家的功业。在这些散文中,其中有流露情感炽热而成为纯美艺术的《槐园梦忆》以及念旧散文,也有接近论说文的《梁实秋札记》。取材范围也比《雅舍小品》扩大了,对抗战时期自己的生活与其他人物的回忆,已经“与抗战有关”了。而且这些文集之间也有互相交叉的现象,譬如《雅舍散文》的“二集”,就颇多怀念故旧的文章,与《看云集》接近。这些散文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以《秋室杂忆》为代表的散文,提供了梁实秋个人生动的传记历史,以《看云集》为代表的一系列散文,为现代中国作家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感性资料,而且这部分散文的艺术价值往往也很高。不过,梁实秋的多数散文都是从“雅舍”的“商标”“批发”出去的,这也注定了这些散文与《雅舍小品》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散文,放入《雅舍小品》中也并不令人感到突兀。尤其是《雅舍谈吃》,就是由《雅舍小品》之第三集中的《腌猪肉》、《萝卜汤的启示》、《狗肉》、《烧饼油条》一类小品演化出来的。因此,下面对梁实秋创作的评价,还是以《雅舍小品》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梁实秋的小品在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确实别具一格。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散文往往是个人情感的一个片段,文学研究会朱自清、冰心等人的散文则是记叙一段事迹或景物,虽然前者也与记叙结合,后者在事迹或景物的描写中也积淀着情感,但是都缺乏深刻的理性内容,而且他们也没有想到将这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与永久的人性结合起来。梁实秋与鲁迅虽然是论战对手,但是要在现代中国散文中寻找与《雅舍小品》相近的文章,那么当推鲁迅的杂文——就是在一个题目下,以议论为经,以情感的抒发与艺术的想象为纬,将理性内容与情感想象融为一炉。但是,鲁迅的杂文充满着对国民性与现实丑恶的批判,而梁实秋的小品则是他从战斗中撤离的表现,也不关心中西文化的差异,而着力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他的小品能够围绕着一个题目,东拉西扯,以不同文化中的名人名言与事例,来表明这种人性具有穿透空间的共通性。因此,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唯一与《雅舍小品》在取材范围与表现方式上相近的,大概是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二者思考的都是共同的人性,而且行文中都使用了反语、讽刺等技巧,使文章显得幽默。不过,钱锺书的几篇散文有的地方议论明显,艺术表现不如他的小说得心应手;而梁实秋的小品几乎就是他生命的流溢,其中的议论也被其智慧之光给遮掩了。
梁实秋以为人性是永久不变的,而国民性一旦形成,改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从今天的欣赏角度来讲,鲁迅揭露国民性的杂文,就比《伪自由书》等直接抨击社会丑恶现象乃至国民党的政治图谋与文化政策的杂文显得耐读。因为鲁迅那个时代的社会丑恶与今天的不同,而国民党的政治图谋与文化政策更是和今天的生活不相关,但是鲁迅剖析的一些国民性现象,至今却仍然存在而使这类杂文仍然具有持久的魅力。鲁迅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说攻击时弊的文章应该随着时弊的消失而一同消失,又说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死。但是,鲁迅为了抨击当时的社会邪恶,宁可牺牲了艺术的永久性,并不以为可惜。而梁实秋故意跳开现实的直接性,不在时代背景与当下事变上着墨,也不在人的阶级性与国民性上着墨,而是有意识地描写人类一些共有的性别、年龄、爱好、行为方式等等,从中看取共通的人性。虽然不能说梁实秋写的就一定是人性,但是他的小品与当时那些“与抗战有关”的文章相比,确实有更久的艺术魅力。
梁实秋小品文章的这种优点,似乎又是对于当年与鲁迅论战的一种艺术回击。梁实秋曾经宣扬文学要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鲁迅反驳说,从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命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鲁迅的反驳是有道理的,而且就鲁迅而言,“永久不变的人性”至少与他从事的事业是相矛盾的:如果人性永久不变,那么鲁迅弃医从文而要改良中国人的人性就完全是徒劳的——如果国民性也永久不变,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是,梁实秋的理论也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莎士比亚剧作的艺术魅力确实与其描写比较永久的人性有关。就以莎士比亚与萧伯纳相比,萧伯纳剧作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重点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相比之下,莎士比亚剧作的时代背景多不明显,而是在戏剧冲突中着力表现人性中的道德与犯罪、爱与恨、悲与喜、猜忌与真诚、复仇与宽恕、忠诚与背叛、希望与绝望、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较为永久的主题。萧伯纳戏剧在永久性上不如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因也在这里,就连萧伯纳的朋友与传记作者佛兰克·赫理斯也感叹要在萧伯纳的作品中“找到不朽的因素,是极其困难的事”,这或者是“因为萧的作品没有永久性”(注:佛兰克·赫理斯:《萧伯纳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在莎士比亚与萧伯纳之间,梁实秋选择的显然是莎士比亚,他在小品文章中抛开时代的风潮,而去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
不过,梁实秋是在整个中国文坛都在选取“与抗战有关”题材的时候,独树一帜而转为新鲜的。如果整个文坛在文化语境相似的情况下都写这种小品,那么这种对所谓永久人性的描写就很容易重复,因而也不值得提倡。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将深刻的人性思考与时代的文化语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描写方法,就是既“与抗战有关”又能超越抗战的感时忧国的时代性而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与人性内涵的作品,譬如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以及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艺术努力方向,更值得提倡。鲁迅当年曾经讽刺梁实秋要写人性可以写营养、运动、生殖等生物性,而梁实秋确实从“营养”出发,写了大量“谈吃”的小品;从“运动”出发,写了《下棋》、《旅行》、《运动》、《洗澡》、《睡》、《观光》、《搬家》等许多小品;从“生殖”出发,写了《结婚典礼》、《喜宴》等小品。当然,梁实秋在写这些小品的时候,并非着眼于其生物性,还是描写了具体的语境,而对具体语境的触及不可能与文化和时代完全分开。换句话说,即使是着眼于人性的梁实秋,也无法写一切文化与一切时代,而只能写他直接或间接熟悉的文化和时代。
尽管梁实秋超然物外专心致志地要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但是他描写的是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是要大打折扣的。譬如梁实秋在《男人》一篇中总结出来的“男人性”,唯一让人认同的就是男人聚集到一起爱谈女人和性,至于其他的“男人性”几乎全不是那么回事。男人脏和懒的确实不少,但是讲求卫生与勤劳的人也绝不在少数。男人固然有不少自私的,但是历史上记载的公而忘私、舍身取义的男人又何其多也!而爱议论人家的隐私,我总疑心是梁实秋把写《女人》时的材料放到男人头上了。因此,离开了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历史背景,抽象地谈论一种“男人性”,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当然,正如《旅行》一篇是因为梁实秋个人不爱旅行由此把所有人想象为将旅行当作苦行一样,梁实秋所谓“男人性”的谗,也是他的自我经验的结果,而和人类“普遍的固定的永久不变的人性”无关。像梁实秋的小品《孩子》一篇,他所描写的就是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之后,中国人对待孩子的状况。他说以前的孝子是孩子孝顺父母之意,而今天的孝子则是父母孝顺孩子的意思。无论孩子多么顽皮、捣乱、逞凶,父母“处之泰然,视若无睹,顶多皱起眉头,但皱不过三四秒钟仍复堆下笑容”。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国人对于孩子是可以加以严重的体罚的,很少有这样孝顺孩子的父母。
值得注意的是,当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谈论“男人”、“女人”、“孩子”、“中年”、“老年”的时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对自己的人性论的颠覆。既然人可以分为男人与女人,性别的不同又导致了人性的不同,而且无论男人和女人,其为孩子、为中年、为老年也都有不同的特性,那么为什么不同的阶级不可以有阶级性,而要统一于人性才能伟大呢?倘若说,从“男人性”、“女人性”、“孩子性”、“中年性”、“老年性”中,可以抽取出来一种普遍的人性,那么,从“阶级性”中为什么就不能显示出普遍的人性来呢?事实上,梁实秋的小品在具体的描述中,也是绕不过阶级性的。《穷》一篇说:“人生下来就是穷的,除了带来一口奶之外,赤条条的,一无所有,谁手里也没有握着两个钱。在稍稍长大一点,阶级渐渐显露,有的是金枝玉叶,有的是‘杂和面口袋’。”
其实,梁实秋的小品文章虽然在总体上试图实践他早期的文学倡导与批评,但是二者之间的出入还是很大的。有些小品直接违背了梁实秋个人的文学主张。譬如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从高张理性的大旗出发,反对不受理性控制的人道主义以及对下层民众的同情,指责作家描写“人力车夫”。但是在《雅舍小品》及其“三集”中,梁实秋却把笔触伸向乞丐、垃圾、痰盂等不符合古典主义之典雅理想的人、物。就艺术而论,《乞丐》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小品,然而它描写的对象却是比人力车夫更其下贱的乞丐。
梁实秋从他美国老师那里学到的新人文主义的批评理论,是将艺术批评与伦理批评糅合在一起的,但是,梁实秋的有些小品,在实践其艺术理论的同时,又违背了其艺术理论中所包含的伦理批评。譬如《诗人》一篇,梁实秋对诗人性格类型的漫画式描绘,很符合古典主义的类型化标准,但却不符合梁实秋新人文主义的道德规范。梁实秋在《读郁达夫先生的〈卢骚传〉》、《关于卢骚》和《文人之行》等批评文章中,曾经激烈地反对借文人之名轻狂放任,认为做出一些超出世俗的罪恶再借文人之名忏悔就更加傲慢无礼,并说无论天才还是庸众的行为都不应该放肆,“不羁的感情要系上理性的缰绳,然后才可以在道德的路上去驰骤”(注:梁实秋:《文人之行》,《梁实秋文集》第6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但是在小品《诗人》中,梁实秋却尽力描绘诗人之不同于庸众之处,说诗人不光顾理发店,头发作飞蓬状,作狮子狗状,而且游手好闲,无病呻吟,有时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有时终年流浪,四海为家。诗人哭笑无常,饮食无度,有时贫无立锥,有时挥金如土,女诗人嘴里会叼只大雪茄,男诗人会向各色女人去膜拜……梁实秋的这种描述完全是类型化的艺术夸张,并且与他以理性为主导反对文人特立独行之浪漫混乱的一向主张相悖。
细心的读者在阅读《雅舍小品》的时候,会在他的小品创作与理论倡导之间发现更大的矛盾。梁实秋是以理性来约束情感的,正是理性的约束才使人与野兽区分开来,情感的扩张如浪漫主义导致了文学的个性化与理性的崩溃,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人性,普遍永久性,是一致的概念。但是,在《雅舍小品》中,读者所看到的人性几乎全是负面的、坏的、贬义的。从《女人》中看到的是说谎不脸红,善变无特操,胆小又爱哭;从《男人》中看到的是脏乱、懒惰、嘴谗、自私自利;从《孩子》中看到的是娇惯与放纵;从《洋罪》中看到的是肉麻当有趣的西崽模样;从《谦让》中看到的是谦让掩盖下的自私与虚伪;从《结婚典礼》中看到的是铺张浪费与讲求门面;从《匿名信》中看到的是躲避在黑暗中的人心的险恶;从《第六伦》中看到的是主仆之间的不平等与不宽容……
如果人性就是如此丑恶的东西,而且还是“稳固的普遍的”、“永久不变的”,以伦理教化、宗教信仰、审美移情都不能将之改变,那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当然,我们探讨梁实秋的小品散文与其批评理论的矛盾,并不是否定这些小品的艺术魅力。事实上,“雅舍”作为独树一帜的一个艺术商标,不但在台湾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而且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这种响应是真诚的,是对于“雅舍”文章艺术魅力的承认,因为中国大陆其时正在摆脱“左”的文学政策的束缚,走向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可以说,梁实秋的小品散文在8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大陆正逢其时,如果再早一些,那么,以“左”的思维定势与政治眼光看待这些品茶饮酒的小品,即使是出于统战的考虑,也不会受到一般文人的追捧。
首先,在梁实秋的“雅舍”文章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正是中国大陆摆脱了“阶级论”的一统天下而对“人性论”予以极大宽容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了“文艺以阶级斗争为纲”,反省了“庸俗社会学”对文学的桎梏,摆脱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中国大陆的文坛逐渐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而且由于“阶级论”所导致的简单化与绝对化,对文学产生了明显的消极作用,人们对“阶级论”的对立面“人性论”产生兴趣是很容易理解的。当然,这种“人性论”与浪漫感伤结合在一起,与梁实秋提倡的“人性论”还不是一回事,但这毕竟是中国大陆文坛接受《雅舍小品》的现实土壤。
其次,中国的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感时忧国精神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文学革命的发生,是有感于中国没有从伦理道德与审美趣味的价值深层来一场颠覆传统的革命,从而不能使政治革命成功而振兴中华,这就从目的性上注定了新文学不可能“为艺术而艺术”,与时代无关,与现实社会无关。文学革命的主将陈独秀很快放弃了思想启蒙的伦理革命,而从事政治革命就是这种感时忧国精神的典型表现。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新文学阵营中的文人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已有的文学主张,而是在变化了的时代精神的驱动下纷纷转向。这种与时代过于切近的关系,使得文学很难具有一种超越性,更谈不上什么“永久性”。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一些作家有感于文学与当下时代这种紧密的关系不利于作品的艺术性,就试图跳开现实的直接性与时代的紧密性,转而到环境不甚鲜明的荒蛮时代去“寻根”,使自己的作品少一些时代特征多一些文化内涵,这几乎成为一代“寻根”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这与梁实秋背离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而超然描写人性的文化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梁实秋那些“与抗战无关”的小品散文,在当代作家故意避开时代特征的时候进入中国大陆,大有“旱田逢甘霖”的意味。
90年代伊始,中国文坛放弃了对重大题材的关注,转而在“一地鸡毛”的地方下笔。于是,报纸副刊活跃起来,散文、小品、札记如雨后春笋,在聊天、品味、喝茶、饮酒、吃菜、剔牙之类的“自由谈”中进行无奈的言说。而梁实秋的小品尽管着力于描写人性的不少,但是与90年代中国大陆的“随笔热”也有着许多共通之处。《雅舍小品》及其后二集中的《信》、《衣裳》、《狗》、《下棋》、《画展》、《理发》、《猪》、《鸟》、《手杖》、《牙签》、《吃相》、《痰盂》、《签字》、《喝茶》、《饮酒》、《吸烟》等篇,与中国大陆90年代那种随意走笔的方式非常相似。就梁实秋写作小品的初衷而言,他也是在干预现实而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以小品的形式消遣生命。拨开历史的烟云与现实的遮蔽,梁实秋的小品与90年代的随笔找到了共同的言说方式,这也就是梁实秋小品散文的当代魅力所在。
标签:雅舍小品论文; 梁实秋论文; 雅舍论文; 旅行论文; 男人论文; 鲁迅论文; 人性论文; 散文论文; 看云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