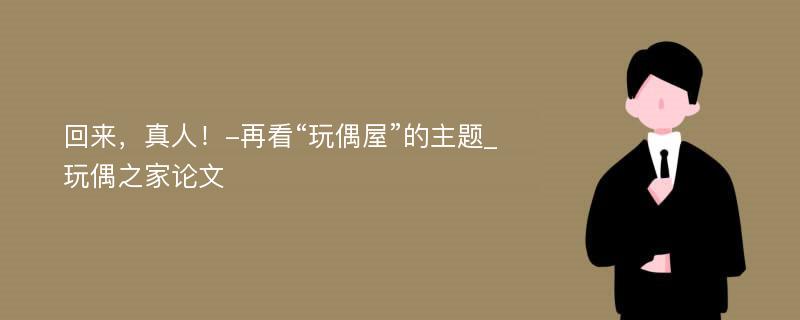
归来吧,真正的人!——--对《玩偶之家》主题的再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之家论文,来吧论文,玩偶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玩偶之家的创作意图和戏剧冲突实质是表现两种人格的对立冲突。通过这一冲突,易卜生描绘了自己关于“真正的人”的理想,批判了现实的、异化的人,发出了让“真正的人”归来的呼唤。
关键词《玩偶之家》主题戏剧冲突主观评价人格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文学专业教学的重点作品之一。关于该剧的主题,一般教材和评论多认为它“暴露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提出了妇女从男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问题”。并指出:“怎样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易卜生是并不清楚的,因此他在剧中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道路。”[①]笔者认为,这种似乎已获定论的说法,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对易卜生戏剧的借鉴和我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习惯,而与作家的创作初衷和作品实际相去较远。事实上,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才是《玩偶之家》的真正主题。本文立足于作品实际,结合作家的创作意图及有关历史背景、文艺思潮,对这一主题作以浅析,试图达到对这一艺术珍品较为准确的解读。
一
作品的主题与作家的创作意图关系极为密切。为了阐明《玩偶之家》的真正主题,有必要先从题材与素材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作家的创作初衷。
《玩偶之家》是根据易卜生的朋友劳拉的一段真实遭遇写出来的[②]。劳拉的故事作为素材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构成劳拉故事的基本环节是劳拉伪造签名,借钱为丈夫基勒治好了病;事情暴露后,基勒指责劳拉伪造签名的犯罪行为毁了他的名誉和前途,提出离婚。劳拉精神分裂,被送进精神病院;美满家庭解体。其二,劳拉和基勒关系破裂的关键在于基勒认为劳拉败坏了他的名声,劳拉则看清了基勒及她们婚姻关系的真实面目。这个故事的基本意义在于显示了两种不同人格的对立冲突。
和《玩偶之家》的题材作以比较,我们会发现劳拉故事的基本环节在作品中清晰可见,劳拉故事的情节模式恰恰是作品的情节模式。素材和题材只有两处较明显的不同:一是生活中的债主并未起诉,而剧中的债主却借此要挟;二是生活中的劳拉在看清丈夫真实面目后精神分裂,而剧中的娜拉却勇敢地走出了家门。
作家的创作意图来自他对某种生活素材底蕴的体察和认识,并反过来操纵着题材的选择提炼。当作家把某种生活现象写进作品,成为作品的题材时,他无疑已对所写人和事的底蕴有了一定领悟。既然《玩偶之家》保留了劳拉故事的基本环节和情节模式,按逻辑也应保留这个故事的基本意义,并以此作为统领全篇的中心思想--主题。在关于这个剧本的早期札记中,易卜生写道:
“关于一出当代悲剧的札记。
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用的,另一种是女人用的。他
们互不了解;但是女人在实际生活中被按照男人的法则来评判,仿佛她不是
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③]
这两种“精神法律”、“良心”的“互不了解”,和劳拉故事所显示的两种人格的对立冲突是吻合的。札记表明,易卜生的确洞悉了劳拉故事的基本意义,并有意在作品中加以表现和评价。
二
作品的题材毕竟是作家对生活素材能动改造的结果,作为作品客观上所具有的思想意义的主题和作为作家主观愿望的创作意图也不能完全等同。因此,要阐明《玩偶之家》的真正主题,更重要的是从作品本身出发,解剖其戏剧冲突实质。
《玩偶之家》的基本冲突是娜拉和海尔茂的关系由和谐、美满到对立、解体的变化。这一冲突源于娜拉的“梦醒”。所以,要准确把握这一冲突的实质,关键在于搞清楚娜拉倒底“醒悟”了什么,而这又需从“梦中”的娜拉谈起。
我们知道,幕启之前,娜拉早已创造了那个冒名借债挽救丈夫性命的奇迹,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身心代价,甚而一度“走投无路”。然而,幕布拉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娜拉却是一个仿佛“没有经历什么艰难”的活泼美丽的小女人,浑身散发着巨大的幸福感。她唱啊,跳啊,不住地感叹:“活在世上过快活日子多有意思!”即使在债主柯洛克斯泰向她指出她的举动已经触犯了法律,并据此要挟她,严峻的现实已不容她盲目乐观下去的时候,她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悔和负罪感。她几乎很轻易地就拿定了主意:独自承担责任,以死去换取丈夫的清白。那么,究竟是什么给了娜拉如此的自信和力量,使她对一切艰辛和烦恼视而不见,从容迎接一步步逼近的耻辱和死亡呢?
我们从娜拉的言谈中可以找到答案。当柯洛克斯泰的威胁使她感到恐慌时,她这样使自己镇定下来:“不会,不会,我干那件事是为我丈夫。”在她准备自杀前,她对林丹说:“将来要是有人把全部责任、全部罪名拉到他自己身上去,你要给我作证人,证明不是那回事”。她还对阮克大夫说过:“托伐怎么爱我,你是知道的。为了我,他会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这表明,娜拉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法律”和“良心”--对道德、人及其关系的独特信念。她认为超越于名利、地位之上的纯粹对人本身的爱是一种最高层次的道德,是人生价值和婚姻价值在最高意义上的实现。她的行为即使不符合世俗法律,却通过爱赢得了存在的权利。而泛滥于她的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温情和她丈夫那些不绝于耳的令人骨酥筋软的情话使她毫不怀疑,她丈夫也是这种道德的典范,她们的婚姻正是建立在这种爱的关系之上的。当娜拉最恐惧的时刻来临--揭发信已拿在她丈夫手上,她丈夫即将知道一切的时候,娜拉内心深处最大的幸福也即将来临--奇迹就要发生了,她丈夫将象他平时常说的那样“拼着性命、牺牲一切”去救她。他会“挺身而出,把全部责任担在自己肩上”。对于娜拉来说,在这个奇迹出现的瞬间,她付出的一切都得到了回报,她的生命已完美无缺,死而无憾了。娜拉的“精神法律”和“良心”实在只是一个关于人的美好梦想,但娜拉却把它当作现实,完全沉迷在其中了。在这个梦的辉耀下,一切苦难都变得富于诗意,甚至死亡也显出了魅力。这个梦,就是娜拉无尽的快乐、信心和勇敢的源泉。
娜拉这个梦想家的确“太不了解咱们的社会了”。当她满怀信心地等待奇迹出现,并准备用结束尘世生活这样一种极端方式回报这属于天国的幸福的时候,她看到了一幕从未想到过的丑剧--海尔茂突然撕去正人君子的面纱,露出粗俗残暴的市侩嘴脸:他感到自己的“幸福”、“前途”面临丧失的危险,便急红了眼,用最恶毒的字眼咒骂娜拉及其父亲,剥夺娜拉做母亲的权利,而全然不顾娜拉为他付出的一切;当危险过去,自己的体面保住后,他又开始称娜拉“小鸟儿”、“小宝贝”,表示“以后要格外小心地保护”她,并为自己辩护:“男人不能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这一短暂的时刻太残酷了,它彻底粉碎了娜拉对人及其关系的信念,把她幸福的虚幻性揭露得淋漓尽致。她蓦然醒悟:她丈夫和她所遵循的“精神法律”和“良心”原来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她丈夫心目中,重要的不是人、情感,而是名誉、地位,说到底就是金钱;而笼罩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的她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过是冰冷的金钱关系。于是,她勇敢地撕破了那个用甜言蜜语编织起来的欺骗之网,走出了虚幻的梦影,她和海尔茂的矛盾爆发了。
一部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本文对“梦中”的娜拉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这样解释娜拉的“梦醒”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能够使人物性格发展获得连贯性,也能够使戏剧情节和冲突前后统一。事实上,在随后的那场“谈话”中,娜拉正是如此表白自己的:
“海尔茂:你能不能说明我究竟做了什么事使你不爱我?
娜拉:能。就因为今天晚上奇迹没有出现,我才知道你不是我理想中的那等
人……就在那当口,我好像忽然从梦中醒来。”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在这场谈话中,娜拉所说的下面一些话倒底意味着什么?因为对这些话的不同理解是导致对《玩偶之家》主题产生歧义的重要原因:
“咱们的问题就在这儿!你从来就没有了解过我……你一向待我很好。
可是咱们的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在这儿我是你的‘泥
娃娃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泥娃娃女儿’一样……这就是咱们
的夫妻生活……现在我只相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
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有些人认为这些话“意味着娜拉为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先进妇女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的可悲地位”,“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玩偶”,“因此决心争得自身的解放,争得同男子一样的权利”。[④]由此出发,他们把娜拉和海尔茂的冲突实质理解为男人和女人关于生活地位和权利的冲突,得出了《玩偶之家》表现妇女解放主题的结论。显然,由这种理解导致的结论和戏剧情节的进程是割裂的。作为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的娜拉和前面那个憧憬着纯粹的爱和完美情感的娜拉没有必然联系。此外,一个明显的矛盾是:既然娜拉认为自己是个“玩偶”,从而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为何又坚持要搞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呢?
笔者认为,这些话其实并不表明娜拉意识到“自己是个玩偶”,而是表明她意识到“自己被当作了玩巳”,她对这种把人当作玩偶的现实十分愤怒。她正告海尔茂“首先我是一个人”,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具有也需要人对人的爱和情感,而不是人对“泥娃娃”的冷酷无情。这里,娜拉并不是在发表“妇女独立的宣言书”,而是在对自己关于爱、关于人及其关系的梦想的幻灭进行美学阐释;她向海尔茂索讨的不是与之平起平坐的地位、权利,而是一个付出了全部的爱和情感的人应该得到的那份同样的回报。只有这样理解娜拉的话,才能使剧情和人物性格前后统一,也才能解释娜拉何以要坚持搞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经过以上辩析,我们可以说,娜拉的“梦醒”是对海尔茂及她们夫妻关系真实面目的发现,是关于人及其关系的美好理想的破灭。与此相联系,《玩偶之家》戏剧冲突的实质是两种人格的对立冲突。
三
剖析戏剧冲突的实质,是从题材的客观意义这个角度探讨作品的主题。主题还应包括渗透在题材描写中的作家的主观评价。那么,对这对立冲突的双方,易卜生态度如何呢?通过揭示这一冲突,他向我们表达了什么呢?
在前面提及的札记中,易卜生接着写道: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
人写的,起诉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
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人不可能忠实于自己。
(剧中的妻子)伪造签名,而且这是她的骄傲;因为她是出于对丈夫的
爱,为救他的命而这样做的。这个男人却以平常人的全部正直站在法律的土
地上,用男人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⑤]
由此看来,在易卜生眼里,“爱”是“忠实于自己”的人即真正的人可以引为骄傲的人性品格。
从作品对海尔茂的刻画看,无论是处理夫妻关系时的极端利己主义态度,还是为了“面子”而解除乱叫自己小名的柯洛克斯泰的职务,使其濒临绝境的“小心眼”作法,抑或是对身染绝症的阮克医生的不耐烦和对孤苦伶仃的林丹的冷淡,都表明海尔茂不具备这种人性品格。从对娜拉的精神打击来看,他还是扼杀这种人性品格的刽子手。
而娜拉无疑体现着易卜生关于“真正的人”的理想的全部光辉。首先,易卜生把自己心目中最崇高的人性品格“爱”赋予了她。这主要表现在她处理夫妻关系的态度上,此外还表现在她和孩子、佣人平等友好的关系,对林丹求职的热情帮助及对阮克医生长期的关心和同情上。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当柯洛克斯泰的威胁使娜拉感到走投无路时,她脑中闪过了利用阮克对自己的爱向他乞求资助的念头,所以她和阮克关于丝袜的对话多少有些调情的味道。但就在这个当口,阮克表白了对她的爱慕,娜拉猛一下从道德的暖昧中站了起来,放弃了求阮克资助的想法。这个站起来的娜拉,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地显出了人的精神的尊严和清洁,表明她的灵魂经过了道德的检验而无懈可击。其次,我们不难感受到易卜生是怀着怎样深厚的父亲般的情感,以十分温柔、诗意的笔调给这个形象抹上了浓厚的孩子气:她对“你们那讨厌的社会”一无所知,缺乏法律常识;她在商务想象上的天真、对冒名借债之类事情所持态度的轻率、表达内心的直接了当以及判断是非的简单等等都不像一个成年妇女;她甚至在丈夫背后偷吃杏仁饼干。持“妇女解放”观点的人也许会据此证明娜拉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玩偶”。但笔者认为,恰恰相反,笼罩在娜拉身上的这种明朗清新的色彩表明,她就是易卜生内心深处的一个关于原初的、真正的人的梦。因为,在一个被社会改变得面目全非的成人眼里,唯有孩子还保留着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事实上,从审美效果看,正如希腊神话以其人类童年的天真使成年的人类感到愉快,娜拉这个娇小的律师夫人,一百多年来正是以她未被污染和扭曲的人性之美--对人、对生活的那种原始而完整的爱心、热情、浪漫和想象触动我们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长久地感动、吸引着我们。
形象描绘表明,在易卜生心目中,海尔茂是丧失了人性品格的异化的人,娜拉则是体现了人性品格的真正的人。
“异化的人”海尔茂安然保住了他的社会位置,“真正的人”娜拉却在现实中无法立身,走入了漆黑的夜色。这真是一出“当代悲剧”,一出人的悲剧。当我们为此悲愤不已时,便已感受到了易卜生对现实的、异化的人的深刻批判。而海尔茂是“以平常人的全部正直站在法律的土地上的”,这样,海尔茂成了社会的代表,对现实的、异化的人的批判上升到了对现实的、异化的社会的批判。
易卜生并未到此为止。他还进一步发出了让真正的人归来的深情呼唤,并对此充满信心。这首先寄寓在对异化的现实的无情批判中,此外还突出地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素材中人物关系发展走向的改造。在生活中,当“冒名借债”的事情暴露后,基勒以审判者的身份提出离婚,劳拉身心全面崩溃。而剧中的娜拉并未因幻灭而垮掉。相反,她变得更加清醒、坚强,站在一种更高的道德层次,对异化的、现实的人和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审判和否定。最后,当她以抛弃者的姿态走出家门之际,她再一次张扬了自己的理想:让我们“等待奇迹中的奇迹”,“改变到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像夫妻。”同时,娜拉的出走唤醒了海尔茂泯灭的人性良知,他表示“我有勇气重新作人”,并为娜拉留下的话所鼓舞,“心里闪出一个新的希望”。在这场人格的较量中,娜拉毫不退让并最终占了上风,海尔茂却成了被审判和被改造的对象。这个改造后的结局,充分表达了易卜生对真正的人归来的期盼和信心。
其二是对剧中另一条线索即林丹与柯洛克斯泰关系的精心设计。他俩曾是一对恋人,后来林丹迫于生计,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有钱人。这桩金钱婚姻带给她的是空虚、孤独,也使柯洛克斯泰丧失了对人的信心,沦为邪恶小人。阅历和苦难教训了林丹,她毅然向潦倒的柯洛克斯泰奉献出纯洁的爱情:“现在咱们两个翻了船的人凑在一起……两个人坐在筏子上总比各自抱着一块破板子强一些……有了你,我什么也不怕。”在爱的感召下,柯洛克斯泰重新燃起了对人的信心,下决心“现在我要努力作好人”。这对恋人的关系从破灭到重建,关键在于摆脱了金钱的桎梏而对人自身、爱情自身的直接肯定。如果说通过娜拉与海尔茂关系的解体,易卜生发出了让真正的人回归的呼唤,林丹与柯洛克斯泰关系的重建则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通过它易卜生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回归之路。
总之,通过揭示两种人格的对立冲突,易卜生描绘了他关于真正的人的理想,批判了现实的异化的人,发出了让真正的人归来的呼唤。
四
《玩偶之家》对真正的人的复归的呼唤不是偶然的。易卜生的创作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中后期。这个时期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金钱对世道人心的支配作用日益昭彰。作为一种文艺思潮,那些以人道主义为精神武器的艺术大师们对人类命运深切关注的目光,也从封建神权压抑人性的罪恶转向了金钱毁灭人性的罪恶。作为以“社会问题剧”著称的艺术家,易卜生同样异常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的脉搏跳动,同样焦灼不安地探寻着人性回归之路。我们知道,易卜生早中期作品中贯穿着一个鲜明的思想,就是宣扬人的“精神革命”。1871年,他在给勃兰德斯的信中写道:“世界上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占去了我全部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已经不是过去那些神圣的断头台日子里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可是政治家们不愿意理解这一点,因此我憎恨他们。这些人只想搞一些专门的革命--外事的、政治的革命等等,但这一切都只是鸡毛蒜皮。需要的是人的精神的革命。”[⑥]显然,易卜生所谓“精神革命”的真正含义是反叛没落时期以金钱为轴心的现实,呼唤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复归。从人的角度看,便是呼唤未被金元化、物质化的真正的人的复归。响彻易卜生作品中的这种呼唤发自时代的胸腔。
另一方面,19世纪的挪威比起西欧社会来毕竟“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政局比较稳定;经济上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没有受到大工业发展的侵蚀和冲击;其小资产阶级是“自由农民之子”。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决定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独立的精神”,“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⑦]易卜生诞生、成长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他的身边还活动着一些“真正的人”。即使后来侨居西欧,不难想象他的内心深处仍保有对“真正的人”的美好回忆。这就使他有可能在早中期作品中,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人性丧失的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另一方面又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人的尊严、道德、情感和期盼,精神尚未枯萎的正面人物--真正的人的标本,于冷峻、沉郁的时代之音中透出了某种亮丽。
综上所述: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是《玩偶之家》的基本主题。这一主题既是作家生活和艺术实践的结果,也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艺术思潮有着必然的联系。正是这一主题,使《玩偶之家》获得了永久的活力。
注释:
①④王忠祥等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中);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匡兴等主编的《外国文学》(上);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
②⑥茅于美《易卜生和他的戏剧》。
③⑤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易卜生评论集》。
⑦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