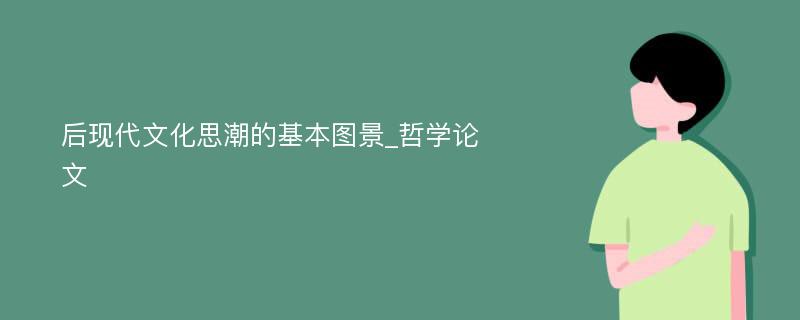
后现代文化思潮基本图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景论文,思潮论文,后现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3)03-0022-04 后现代话语的兴起与传播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基于对现代社会危机 的焦虑和对现代文化传统的怀疑,在不同的社会意识领域中先后产生了以批判现代理性 为鲜明特征的后现代话语,并迅速汇聚成在实践层面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后现代文化思潮 。伴随现代化的客观进程,当代中国社会的观念领域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纵 向的及横向的双重文化碰撞中,现代理性正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正确解读后现代话语 因而成为学界当下的重要课题。
一、后现代话语历史轨迹
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运动中最具渗透性的元素,后现代话语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渐积 累而成的反叛性思维,考察“后现代”一词的提出与涵义的演进有助于集中把握其代表 的基本主张。
1.二战前的“后现代”
“后现代”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查普曼以“后 现代绘画”一词来概括当时比法国印象主义更前卫的绘画。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中,“ 后现代”一词确实较少使用,但这并不代表后现代话语的罕见——因为后现代话语的批 判精神已多形式地表现出来:如以卡夫卡、乔伊斯的小说及艾略特的诗歌为典型的新文 学作品,在北美等地区出现的新建筑形式等等,强烈的反叛性是其原初即有并始终坚持 的基本精神。
最早赋予“后现代”以理论性反思、批判性色彩的是鲁道夫·潘诺维茨。在出版于191 7年的《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为揭示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他用“后现代” 一词反映当时欧洲文化虚无主义盛行及传统价值崩溃的社会现象。而德·奥尼斯在1934 年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将“后现代”的矛头直接指向 现代主义,后现代话语的反叛性更加明确和突出。
应特别注意的是德国哲学在20世纪初开始的话语转向,这实际是后现代话语理论化的 最重要基础:以尼采为鼻祖,一批德国哲学家以现代哲学及整个传统哲学为否定对象, 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颠覆,由此形成的反叛性话语为后现代哲学及整个后现代文化 思潮提供了前期理论准备。此后,从海德格尔至伽达默尔,试图瓦解西方哲学传统的德 国哲学一直是后现代话语演进中的重要力量。
2.二战后的“后现代”
二战结束以后,愈来愈多的社会意识形式开始使用“后现代”一词,从具体社会科学 到哲学,后现代话语的指向逐渐统一到以现代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传统上来:
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于1957年出版了《明天的里程碑》一书,其副标题为“关于新 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他认为西方世界正发生着“新的模式、目的和过程世界观” 的现实转变,这一转变反映出现代文化传统因其弊端而正被人们怀疑、放弃。同年,历 史学家勃纳德·卢森堡在《大众文化》一书的导言中更明确地使用“后现代”一词,其 矛头直指现代社会普遍的“异化”现象:“被商品包围的后现代人,本身也成了整个文 化过程的一个可以被互相置换的部件。”[1]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现代性区别的意义上赋予“后现代”更明确的内容:听从萨摩维 尔的建议,在出版于1963年的《历史研究》第八卷中,汤因比用“后—现代”表示与现 代时期的决裂。他认为西方社会自1875年进入第四个阶段:与此前以社会稳定、理性主 义主导为特征的现代时期比较,“后一现代”是个充斥着无政府主义及彻底相对主义的 “动乱时代”,明确地指出现代理性已经在历史变化中丧失了权威。其本国同行巴勒克 拉夫在1964年出版的《当代历史学导论》中则强调,“后现代”时期的“我们应当予以 重视的不是相似性,而是差异性;不是连续因素,而是不连续因素。”后现代话语的基 本主张已经得以明确的阐述。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观点更具概括性,他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一书中指出:“我们正在目睹过去的二百年中塑造了现代纪元的资产阶级理念……的 终结”。即现代理性的历史使命与权威地位已经结束,社会正处于反叛性冲动不断扩张 的、本能与冲动应充分释放的后现代时期。
在战后的三十年间,多种具体社会学以不同视角审视着现代文化传统,并将现代理性 逐渐定位为当代症结所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大幕就此徐徐拉开。
在此过程中,迅速崛起的后现代哲学是后现代文化思潮进入话语成熟期的显著标志。 虽然后现代哲学以其概括性与尖锐性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旗帜,但后现代哲学家一般 只注重阐述对现代理性的批判性话语,很少明确地为自己贴注上“后现代”的标签:作 为激进的后现代哲学重要代表之一,直到1980年,博德里拉才在一次题为“论虚无主义 ”的演讲中称自己的理论为“后现代性”分析;四年后他才进一步指出,没有任何意义 的世界中“剩下的全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2]利 奥塔也较晚使用“后现代”一词:为解释其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利奥塔在序 言中特别地指出“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况,而我决定用‘后现代’ 这个词来命名这种状况”;[3]到1985年出版《公正游戏》时,利奥塔才更明确地将“ 后现代”与“现代”进行了区分,将“后现代”定位于对现代理性的反思……。
在“后现代”一词的提出与广泛使用过程中,一直贯穿着现代传统已经终结的悲剧性 判断。历经两次大战间的酝酿、战后20年代的普遍反思以及70年代前后的话语成熟,后 现代话语在80年代开始渗透到更多意识领域,“后现代”也相应地演化成以现代理性为 批判对象的新思潮通用前缀。
概括后现代话语历史轨迹,有必要借鉴利奥塔为“后现代”所规定的两个定义标准— —其一是历时态标准:后现代主义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由 60年代发生发展,将随历史而不断地向后延伸。其二是共时态标准:后现代是一种精神 、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 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 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地创新。[4]
二、后现代文化思潮基本话语
后现代文化思潮是多形式后现代话语的总和:其中既包括后现代文学,也包括后现代 哲学和后现代政治主张;此外,在法学、伦理学以及美学、建筑学,甚至在宗教等社会 意识形式中也广泛地存在着后现代话语。在诸多后现代话语中,后现代文学、后现代哲 学以及后现代政治观是最基本的话语。
1.后现代文学精神
考察后现代文学,首先会发现大量写实主义所忌讳的隐喻、幻觉、象征、荒诞以及倒 错等写作方式,作品也因而笼罩在扑朔迷离的色彩之中——卡夫卡是这方面的典型,其 主要作品始终坚持象征、隐喻甚至荒诞的方式,他曾深刻地指出:“我们的艺术是一种 被真实弄得眼花缭乱的存在;那照在退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仅此而已。”[5]但 正像歌德指出的那样,艺术美“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越的。”[6]写作手段的后现代性 仅是后现代文学的形式,整体主义、物质主义及理性主义是其批判的主要对象:
后现代文学否定整体主义,共同向既成秩序发起反叛。当现代文明进入到20世纪,资 本、市场、技术等多种现代因素推动社会不断趋向整体化,后现代文学家将“整体性” 视为压制个人并致使其生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于是,我们看到了卡夫卡、劳伦斯、乔伊 斯等多数后现代文学家对孤独个体的刻画与同情,看到了要求从或“父亲”、或“母亲 ”所象征的整体压制下逃脱的强烈欲望,看到了以自我表现取代共性认同、以个体差异 取代普遍同一。不同时期的后现代文学一致批判整体对个体的压抑,共同倡导欲望解放 与差异尊重。
后现代文学否定物质主义,一致地对异化现象进行抨击。借助于现代化生产的进步, “物质膨胀”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景观;主体的人也逐渐迷失了自我,物欲追求替代了更 高意义上的精神追求——人蜕变成物的崇拜者与奴隶,“异化”成为普遍现实。面对物 化的世界与“异化”的主体,后现代文学以“救赎”生命的历史责任与悲剧性心态激烈 地批判“物质主义”;慕西尔认为,现代社会分工导致自由的“人已不复存在,只有职 业存在着”。艾略特以死亡为重要主题,死亡被认为是与物欲统一的景致。昆德拉着力 揭示物质世界的虚无与荒谬,借反复强调“没有选择的痛苦”揭示被遗忘的生命意义… …
后现代文学否定理性主义,普遍批判抽象的统一规范。伴随着科学主义与机械主义等 现代理性的不断发展,现代理性借助于统一规范与强力秩序向整个社会生活普遍渗透。 后现代文学认为现代理性完善的标志是形成了制约个体存在的整体规范,“主体”已成 为机械的、被强制的秩序附属。因此,后现代文学家通过呈现生命的热情与欲望来衬托 理性的苍白,以张扬生命固有的张力、神秘甚至魔幻来对抗理性对人的弱化;以关注传 统伦理禁忌的变态、乱伦来取消既定规范对自然欲望的束缚……生命的自然欲望被普遍 地肯定和倡导,一致强调应恢复作为理性前提的感受体验,以解放和完善个体欲望及生 命内容。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怀有强烈的反抗激情,后现代文学话语必然呈现出偏激的特色— —为抵制“物质主义”而全盘否认现代物质文明的合理性;为揭示“理性主义”的危害 而彻底地否弃理性的意义……但无论如何,后现代文学以充满激情的话语深刻揭示了现 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启发了主体对于存在价值与自我命运的深层反思。在此意义上,后 现代文学精神是20世纪人类精神图景中的积极元素。
2.后现代哲学话语
后现代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领域发生的重大转向之一,科学主义文化哲学与人文主义 文化哲学也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7]概括后现代哲学话语, 反传统与反权威是其试图终结现代哲学传统的战斗中突出的批判精神。
(1)反传统话语
后现代哲学首先表现为旨在终结现代哲学的“反传统”话语。其内部虽然存在着激进 的、批判的及建设性的不同话语,但在否定现代哲学的目标上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都试图借否定现代哲学来为自己寻求存在的理由与空间:
在后现代哲学阵营中,激进派是最有影响的成分,其主要目标是试图在根本上完成对 “哲学的终结”:福柯认为传统哲学实际是建设在先验性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力图寻 求终极知识的哲学,从其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利奥塔把元话语危机视为哲学危机的根源 所在,据此认为哲学是一种“非合法化”的一元叙述;德里达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哲 学是否应该终结,而是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终结哲学。
哈贝马斯代表的是批判的后现代哲学,他认为,传统哲学自康德时代已经开始含有终 结的因素,到黑格尔将哲学推向极端时,“伟大哲学”即已告结束。哲学应重估自己的 地位,主动与具体科学建立工作关系,保持与人文科学的合作,即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 以重建整体性哲学,其试图终结的是现代哲学的超然地位。以罗蒂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 代哲学主张当代哲学自觉融汇到“人类对话”中,以文化批判与启迪心灵作为自己应该 充当的角色。
后现代哲学的“反传统”主要依赖于对既有哲学基本概念的诘难——现代哲学以普遍 性、整体性、同一性、确定性及一元化等概念为基础,后现代哲学则依赖于特殊性、个 别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及多元化等概念来建构自己的主张:福柯认为“解释世界的方 法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因为“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 ,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它。”[8]德里达认为现代哲学的根本错误 在于以主体与客体、表象与现实、真与假、实在与虚构等二元对立为基础,而前项凌驾 于后项之上的支配秩序假定了真理的存在与地位。所以应颠覆现代哲学赖以存在的假定 基础与秩序以彻底否定现代哲学。德勤兹在《尼采与哲学》中则宣称:“变易之外无物 存在,多样性之外无物存在,无论是多样性,还是变易,都不是表象或幻觉。”试图以 解构本质与现象的对立恢复被传统哲学长期压制的差异、现象及非同一性等基本范畴。
(2)反权威话语
后现代哲学更重要的精神体现是否定现代理性的“反权威”话语,以质疑既有理论的 真理性为核心,后现代哲学一致批判现代理性。在这方面,后现代哲学明显地受到以量 子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影响;而波普尔关于“科学是可以有错误”[9]的论 断更是直接在观念上动摇了现代理性长期占据的权威地位。
利奥塔与福柯无疑是反权威话语的最主要代表。利奥塔的反权威话语主要是以反对理 性、推崇感性为中心展开——宣布“大叙事”的终结,这是反对以“绝对真理”自居的 现代理性权威的典型论断。受向传统宇宙观提出挑战的新自然科学成果影响,利奥塔认 为“量子力学或微观物理学迫使人们更彻底地修正可预测量子力学或微观物理学的思想 ……我们无法得到一个更好的,即性能更佳的信息……选择只能靠运气。”[10]在《公 正游戏》一书中,利奥塔进一步宣称“没有标准”,所有的判断都是根据欲望、痛苦的 快感而作出的。
福柯则依据“考古学”与“系谱学”更有力地质疑理性能力与真理观——借助其“考 古学”理论,福柯认为当历史转变时,“事物便不再以同以往一样的方式被感知”,应 重新“确定在不同事物系列之间,有哪些关系形式能够被合法地描述。”[11]他认为启 蒙运动的成就是成倍地增加“理性的政治力量”,强制地塑造以现代理性武装起来的“ 无所不能的主体”。现代理性是一种压迫力量,它通过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等方式实 施对主体的统治并造成主体的“人的消失”。在“系谱学”理论中,他认为知识、真理 是权力统治的基本成分,权力和知识的循环关系不断地完善、传播着权力技术与霸权规 范,从而控制社会的一切。以“尊重……差异”为中心,福柯拒斥统一的、总体化的、 以现代理性为支撑的现代理论。
其他的后现代哲学家也大多反对启蒙以来的现代理性与真理观:博德里拉宣称“真实 已经在形象和符号中消逝了。”他认为在由计算机、媒体、自动控制、模型以及符码支 配的“类象社会”中,模型与符码是首要因素,它们销蚀了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而温 和的阿蒂吉阿尼则主张以新型符号重新书写认知地图,认为“人类要创造必须随时间变 化的真理。”[12]凡此种种,后现代哲学较一致地反对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现代理性与 绝对真理。
3.后现代政治主张
作为批判现代文化传统话语总和,后现代话语中必然包括对既有政治理论及其实践的 批判。虽然后现代政治主张少有独立话语体系,但这不能掩盖其实际存在与现实影响。 在整个后现代政治话语中,“微观政治”是最突出的主张。
(1)后现代政治基本流派
基于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重要内容,许多后现代思想家在各自话语中为其政治主张留 有一定位置,并形成三种不同流派:福柯、杰姆逊等力图发展一种新的激进政治,利奥 塔所代表的思想则退回到旧自由政治当中,博德里拉的选择是宣称社会、政治、大众与 历史均告终结。杰姆逊坚信马克思主义比其他理论都优越,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框架中,后现代主义才会真正得到最好的理论化;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历史观,认 为后现代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客观发展阶段,并在此阶段上产生与以往的断裂:“一般而 言,各个时期之间的彻底断裂并不会导致内容的彻底改变,而是导致一室数量既有因素 的重组……”[13]他试图调合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试图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结 合——他既相信现代理论中的总体性概念,认为所有受压迫个体所遭受的压制存在着终 极共面性,号召在各种人群中建立统一联盟;又认为所有女性主义、黑人、同性恋者及 其他被压迫人群的经验,都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提供着重要的观点和立场。
早期的利奥塔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主张彻底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发表于1974年 的《力比多经济学》则标志他转而推崇肯定性的欲望哲学,利奥塔认为极权式社会力量 将欲望的强度削弱并导致生命能量和活力的丧失。并因而推崇前卫艺术,认为艺术与写 作是增强欲望强度、实现生命能量自由流动的最佳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利奥塔再 次转向,他开始认为“人们不可能践行一种美学政治。……因为存在着非公正的问题… …对于公正问题,我们必须用某种别的规则来解决。”[14]由此,利奥塔提出了称作“ 多元公正”的新主张:认为“公正”只能是局部的、多元的、暂时的,应伴随对象和具 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博德里拉的政治主张又明显区别于利奥塔及其他后现代政治主张。早期的博德里拉曾 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加以综合,但他很快就开始反对唯 物史观将生产置于社会首要地位。原因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希望的只是一种更有效 且公正的生产组织,并没有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由于忽视政治经济学,他无法 正确分析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如何产生权力关系及如何造成现实的压迫,这是整个后现 代政治主张的通病;他开始提倡差异和边缘政治,把理想寄托于黑人、妇女及同性恋者 等边缘群体的反叛,试图以微观政治的方式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后期 博德里拉开始质疑微观政治的有效性:认为权力比福柯设想的更分散和细碎,因此根本 无法与其斗争。因为社会已经演化成由模型和符码所控制的生活领域,而统治恰恰发生 在微观层面上。因此他最终选择了宣布社会、历史及政治均告终结,主张放弃政治斗争 。
(2)“微观政治”的主要代表
在整个后现代政治主张中,最为突出并与整个后现代文化思潮基调相一致的是福柯等 人的“微观政治”主张:
身为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思想界的主要领军人物,福柯始终以历史为主要的研究领域 ,并特别关注权力、监狱之类问题,由此形成的“微观政治”是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 20世纪60年代,福柯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主体”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70年代后 ,他开始以“系谱学”对权力现象予以更多关注。福柯强调从“制度、政治事件、经济 实践及过程”等物质条件研究问题,特别关注疯狂及疾病、犯罪、性等边缘领域和人群 ,将文化与日常生活各个层面政治化。他认为国家依靠各种“规戒”技术与力量影响并 建构了个体认同、欲望、躯体及灵魂,并呼吁在微观层面上——在监狱、精神病院、医 院和学校中发起多元的自由斗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政治理论,认为“根本不存 在大规模拒绝的中心、反叛的核心、一切背叛的根源或革命的纯粹法则。相反,有的只 是多元的抵抗,其中每一种抵抗都是一个特例。”福柯的“微观政治”包括话语政治与 生物性政治:他认为话语即是权力,所以话语就是“抵抗的支点和反抗策略的起点”。 其“系谱学”就是要恢复被总体化叙事压制的自主话语,边缘性个体只能通过抵制将个 人置于规范性认同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己;晚期的福柯提倡一种“我们必须像创 造艺术品一样创造我们自己”的“自我技术”——即“允许个人运用他自己的办法或借 他人之帮助对自己的躯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改变自我,以 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状态。”
德勒兹、加塔利虽然也是“微观政治”激进分子,但两人更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也较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他们的批判焦点集中于资本主义、家庭、精神分 析等方面——认为资本主义保留了由专制社会所创立的国家机构,同时还创造了控制物 质和心理存在的新体系——随着资本主义把市场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以抽 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再制码”,将一切“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精 神分析等规范化制度中,对欲望与需要进行比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更有效的控制。他们 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设立或恢复各种各样残留的或人造的、虚构 的或象征的地域,借以试图尽其所能来重新编码,重新引导那些根据抽象量被界定的人 们。”[15]因此,他们明确主张以资本主义为政治斗争的对象。但认为“工作阶级不再 代表社会的大多数”,应建立一种排除工人中心地位的新政治联盟;同时,为避免在革 命群体中再制极权主义而主张个体或群体应立足于自主且为自己发言。最终,德勒兹与 加塔利导向了“微观欲望政治”。认为欲望“并不需要革命,它本身就是革命的。”因 此,不需要产生任何传统意义的革命主体,不需要你死或我活的识形态斗争;政治只是 与欲望躯体的解放有关,只要躯体欲望得以解放,其他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其结论是: 改变个体的日常生活就是最具有激进后果的政治行为。
标签:哲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福柯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