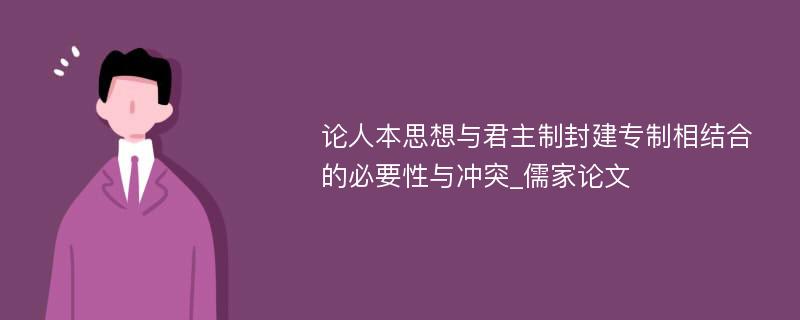
试论民本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结合的必然性与冲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君主专制论文,民本论文,必然性论文,封建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帝王史。封建帝王通过创建和发展以君主专制制度为核心的国家管理制度来实现对社会的操纵。这样的制度环境是中国古代一系列政治思想学说得以孕育的基础,在这些学说中,儒家学说由于自身的特点,经过统治者的选择与重塑,自董仲舒“罢黜百官,独尊儒术”确立了其正统地位,至以后程朱大兴理学,这种地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动摇。儒家学说与君主专制的结合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的结合完全和谐,事实上,两者从互相拥抱对方开始便带有统一与矛盾的两重性。本文将以儒家思想的典型组成部分之一——民本思想为切入点,对这一两重性作一剖析。
(一)民本思想的界定
一般认为,民本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萌芽,是同重民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重农的民族心理,导致了民本思想的产生(注:郑敬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与冲突》,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5期)。这种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尚书》中即有“民为邦本”之说(注:《尚书·五子之歌》)经过儒家的传承、总结与发扬,它最终成为儒家学说的精华部分。应当指出的是,在重农这一层次之上,孟子将其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孟子有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这种民贵君轻说的内涵在于强调民的重要作用,从而要求君主行事必须从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以民意为依托。
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成熟的思想学说体系是建立在儒家的“天命观”之上的。儒家崇尚君权神授,君王乃天之子,是上天派到人间管理万民的,因此,他就必须替天行道。这里的替天行道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人间王以天子自居,通过神的旨意这样一层面纱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又为约束君主设计了一个枢纽:倘若君主违背天意,就会视为对天的不尊,就会遭到“天惩”。许多朝代的更替正是在“天意”的旗号下进行的。民本思想的创新在于它使得“天意”由虚无缥缈转化为人间的实在,孟子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注:《孟子·万章上》)也就是说,天的旨意,很大程度上将通过民意体现出来,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天意将以民意为归依。如果君王违反民意达到极端,民众就拥有了合法革命的权利。孟子从反面告诫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注:《孟子·离娄上》)
一旦“天意”转化为民意,那么,儒家对于君主的监督就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这并非民本思想的最终目的,儒家学说从根本上说属于绝对伦理主义,它强调先验道德的普遍性,而这种先验道德是以个体的心理情感的体验为基础的(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儒家以先验道德论与心理感觉论为依据,设计了一个以圣人为中心、以仁为价值内核、以礼为表层的道德王国,圣人则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有鉴于此,儒家的理想永远在于遥远的古代,在于天下归于仁,在于“天下为公”(注:《礼记·礼运》)。一切政治设计都是为了使个人的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从而达到三代盛世的水平。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中,君主应当成为道德的楷模和天下表率,如果君主胡作非为,视道德为草芥,上天必会降怒。民本思想把民意高于君意巧妙地纳入其道德范畴,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原则——道德高于权力作了又一新的阐述。与其说儒家学说强调的“民本”是一种独立政治价值,不如说它是上天的道德命令更为合适,“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注:《左传·文公》),“民本”并不是出自民的一种需求,而是上天早已设计好的。于是,民本思想就获得了双重性格:从其感性现实品格来说,它以民为落脚点,言必称民,是积极入世的;从先验的道德而言,它超越于现实,追求完善,为典型的宗教乌托邦。
封建君主在专制统治形成的初期,通过军事力量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确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此谓“马上得天下”;继而他又用宗法关系与各级地主建立联系,从而自然成为整个宗法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这样君主专制就完成了由军事封建专制向宗法封建专制的转变。在宗法封建专制下,封建帝王既是最高的统治者,又是万民之父母,“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注:《资治通鉴》第56卷),政权与族权合二为一。君主可以站在父母的立场,教训其子民,并凭借手中权力大肆杀掠抢夺。君主专制政治建立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之上并具有极强的辐射性,专制权力通过血缘的渠道,深入到每个家庭,以至于每个家庭都成为权力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君主就在这个机器中处于中心位置,每一个人都脱离不了君主的控制。这样一种结构,在强调父家长对其他成员的绝对权力的同时,事实上树立了君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此外,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对土地和人的支配和占有。君主专制要维持其存在与发展,就必须实实在在地关注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实力,这种实力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与人口,土地与人口越多,就意味着政治资源越多。封建专制权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对土地与人口的占有欲望,这种欲望如同资本繁殖一样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结果就是专制权力本身成为一切资源的源泉,有权力就可以获得一切,君主通过垄断政治权力取得土地、人口等一切资源的唯一所有权。从实际过程来看,君主本人虽然不可能占有并使用每一寸土地,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观念上却是不容置疑的,“全国一切的最高所有权属于王,把君主置于绝对的地位,为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注: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第24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版)。中国的这种绝对专制主义政治与西方的领主政治是有所区别的。
君主权力产生过程中的暴力性,及其在统治中的至上性和扩张性,决定了他必然把权力的运行视为一己之事,“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从一方面说明了君主对于权力的垄断。君主个人意志决定着天下的一切,天下既是君主本人的“家天下”,外人无权过问,更不能容忍任何人染指或企图加以剥夺。
二、民本思想与君主专制结合的双重性
民本思想与君主专制各自的特点决定了它们结合的必然性,同时也注定了它们冲突的不可避免。
首先,民本思想的感性现实品格决定了它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民本思想家关注的是“民”,是这个此岸世界,“民本”所折射出来的都是贴近生活的伦常,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部分,它恪守秩序与守成之道,“不能采用破坏现实政治格局而创造新制度的办法”(注:张星久:《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内在冲突》,载《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这种积极的入世精神要求儒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并且,儒家的政治理想要付诸实现,必须依赖一定的政治权威。反过来说,因为民本思想并不以否定君主的统治作为前提,只要求君主关心民众的状况,顺从民意,以使统治不至太苛刻,因此,两者的结合没有根本的障碍。从统治者的一方来说,民本思想家为其提供的重民以争取民心也是维持其统治的一个妙方,温情脉脉的宗法专制主义,再加上“民本”等几个漂亮的口号,要比赤裸裸的军事封建专制主义可亲得多,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能更好地统御民众。于是,一个要借助外在权威实现其由内圣到外王的转变,一个是要儒家思想的温和。怀着不同的目的,两者一经相遇,就紧密拥抱在一起。
其次,民本思想与君王专制的结合,并非和谐一致的。由于基本目标不同,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君主制的突出特点是其“私”性,视天下为私物而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民本思想的直接目标是维护民的利益从而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等道德纲常;另外,在权力动作上,民本思想强调君权神授,王不能私自处理其职位,君主处理政事须以天意为准,而天意又体现于民意中,因此民意是最终的依据,而君主专制则确立了君主在全国范围内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皇权高于一切,这样就有道统与君统或曰权力与道德的矛盾。民本主义思想家既将民本纳入道德内核,定然强调道德高于权力,君主的职责在于爱民、行仁,以实现道德秩序;而“马上得天下者”深知权力的重要,民只是其手中的棋子,仁义只是幌子而已,他们真正行的还是外儒内法,骨子里是法家的一套。
民本主义者从其天命观出发,对君主展开批评。他们认为,三代盛世是永远无法达到的最高理想,现实的君主总是有缺陷的,他们既然无法达到爱民如子的境界,就应当在圣王前顶礼膜拜。违背民意肆行虐政将会违天并导致不祥,进而加速王朝的覆灭,这无形中的确为皇权的运行树立了某种外在的约束。君主只有在道德上引导万民,为民之师,才能称得上合格的贤君。事实上,任何君主都明了道德不能维持权力,只有法、术、势才是维持权柄的工具,任何君主都不能容忍外来的任何指摘与束缚,于是民本思想与君主专制的内在冲突就无法避免。
三、民本思想的萎缩
民本思想作为一种进步的思潮,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站在民众的立场,敢于为民请命,对君主展开批评。但其先天性的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君主专制制度,也无法使得对于君主的言论监督维持下去。民本思想与君主专制较量的结果以前者萎缩而告终。
民本思想的出现,固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它却是思想发展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民本思想无法同君主专制彻底决裂,也就无法在政治运行模式上真正贯彻道德对于权力的制约。儒家的政治模式在孔子那里是道德一元论的,孟子将其作了发展,企图造成道德与权力的分化,并以道德制约权力。事实上,这种制约只有心理威慑的作用,是一种软化的约束,没有任何可资操作的东西可言。君主凭借权力可以为所欲为,完全置天意、民意于不顾,道德主宰权力形同虚设,而权力操纵道德则是实在的。
从两者的相互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君主把民本思想的影响束缚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鼓励臣下积极谏诤,以示其开明,并诱导臣民忠于朝廷,无怪乎许多士大夫都冒死进谏以示其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君主,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利,尽管有的士大夫仍极具良知,但在君主的高压下,也只能放弃为民请命的意图。当君主专制进一步深入到思想领域之后,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少,民本思想并同儒家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遭遇一次次碰壁,终于导致了它的自我塌陷,并随着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而丧失反抗力。
四、余论:反思及启示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好的思想与好的理想,但为什么在现实中几乎没被实现过?民本思想作为儒家思想中最具积极意义的部分,为什么终被君主专制所吞噬?对于其中的原因不能不进行深思,这对于理清我们的历史,正视现实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一种伦理模式,而不是一个政体模式,它是“一个伦理秩序的‘理想国’,而不是政治秩序的‘理想国’;它只能给伦理学提供原始资源,不能落实为政治制度操作设计”(注: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第265-266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民本思想所倡导的“天下为公”,是从逻辑中推理出来的模式,而很少顾及政治现实,照朱学勤先生所说,是政治意识定位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注: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第165-266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儒家的这种乌托邦性格一直延续下来,轻制度,重道德教化。这使得他们的操作设计如同空中楼阁,只能为君主专制所利用,难以对君主专制形成真正的制约。
其次,民本思想虽然主张以民为本,但他们所说的民本,同近代倡导的民本有根本的区别。民本至多只是一种开明专制罢了。因为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法律只是君主统治的工具,民众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根本的权利保障,义务本位取代了权利本位。在君主一人专权的情况下,民本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可能孕育出民主果实。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积累与沉淀,民本思想将会以心理遗产的形式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生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民本思想的积极与消极成分,并得到以下几点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启示:
第一、要注重制度建设。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作恶,制度不好,好人也无法做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政治民主建设的成果只有用制度巩固下来,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否则就难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局面。
第二,认真理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民本与民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民本说到底只是一种统治工具,是为维持以家长制与血缘政治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服务的,在这种制度下,人治发达,法治不得孕育,因为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没有任何限制。而民主则首先意味着为法律所明确保障的公民权利与一定的政治自由。民主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一环,它意味着要进一步规范权力的运行,保障人民的权利,在法治的轨道上更好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