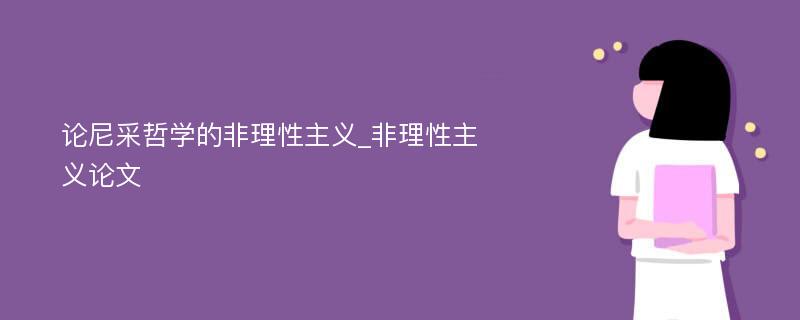
尼采哲学非理性主义管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非理性主义论文,管见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范围内,过去的思想家常常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一个特定的阶段,后人不再运用他们的方法来处理现实问题,只是尊敬他们而将他们供奉在哲学史的篇章中。但是有个别思想家却象天上的星月,人们走到哪里,他们的思想都随之流照,历史的推移不仅没有使人们望却,相反,时代的发展却让人们更深地了解他们,并更广泛地受其启发。尼采就是这样的思想家,他建构的哲学非理性主义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一 产生:来自于“笼罩欧洲的阴影”
有人说,尼采是狂妄的,他受惠于德国民族文化的理性主义滋养,却成为德国理性主义文化的最大叛逆者,并将德国精神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发展成为全面系统而又激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但是,我们认为,这并非无缘无故,尼采所预见的“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注:尼采:《快乐的知识》。),为我们理解尼采非理性主义的产生作了最好的说明。
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反映。尼采哲学形成于19世纪70—80年代,包括德国在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当时,巴黎公社的革命已被镇压下去,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运动转入了一个积聚力量、从思想和组织上作革命准备的时期,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暂时停息。欧洲各国资本主义暂时尚未遇到革命的直接威胁,好似可以永存下去。大资本更是迅速膨胀,他们气焰万丈,不可一世。这种情况使哲学具有傲视一切、肆无忌惮的性质。然而,在资本主义的虚假平静的背后,已可越来越明显地看出它的腐朽和没落的趋势。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的日益觉醒,无产阶级政党的相继建立,预示着威胁资本主义生存的革命风暴日益临近。尼采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认为这是当时“笼罩欧洲的阴影”。他知道,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不择手段地镇压工人运动,攻击革命的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瓦解工人阶级的组织。要做到这点,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平静”的手段已是不行了,必须由新的强有力的力量采用最残酷的暴力去进行镇压。正是这种原因,使尼采的哲学极具疯狂性,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
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是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失落的回应。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上述的精神危机,在哲学上便是理性主义绝对优势地位的失落。欧洲近代是理性主义胜利进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入口处,培根“知识就是力量”(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的口号响彻云霄,人们自豪地发现,从自己心灵中闪射出来的理性的光芒普照万物,人类成为世界的真正造物主,没有人怀疑理性的至高无上的意义。英国经验论者、大陆唯理论者、法国的启蒙学者直至德国古典哲学家无不是理性主义者,他们无忧无虑,信心十足,建构了自己的理性王国,理性借助科学之力取代了上帝。可是,理性主义在度过充满希望的时期之后,人们突然发现,理性的自夸也是一种幼稚病,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理性并不是绝对的东西,它反过来是靠着人的。欧洲人在连续动摇和失去过去籍以生活的基督教及科学和理性等一切信仰之后,面对传统价值观的荒凉废墟,苦闷彷徨。在这种情况下,虚无主义、非道德主义、非理性观念乘虚进入人的空虚心灵,因为悲观失望与惶惶不安,使得人们反诸自身,试图从内心心灵体验中寻找生活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现代西方崛起了,理性王国开始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股思潮以不可抵挡之势摧垮了近代思想家们苦心经营的理性王国,并泛滥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一切文化领域,后迅速上升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潮。尼采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性主义的过错,为此,他坚定地举起了非理性主义的大旗。因此说,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出台是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失落的一种回应。
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实与德国近代哲学的特质密切相关。当近代理性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至巅峰时,这个孕育人类高度发达理性的民族,同时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非理性精神。换句话说,德国作为人类哲学思维的民族,既产生了近代达至巅峰的理性主义,也产生了近代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德意志的精神文化,既是近、现代理性和科学的深厚土壤,也是近、现代一切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总根源。所以,当黑格尔将理性主义绝对化,铸造理性宗教时,与此同时便有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与之抗衡。就一个具体的哲学体系而言也是如此,德国近代哲学从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康德的意志说、费希特的自我、谢林的绝对同一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它们一方面是高度理智化的逻辑理性。但另一方面,在这个逻辑性的思维之网中,却跳跃着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生命。康德的意志两重性说,实际上是将生命意志与自由意志并重的,而且正是由于人有生命意志,才必须有自由意志与之相随相约。费希特的自我论,把人的生命和存在提高到了第一位,谢林的绝对是充满着意志和生命冲动的绝对,实际上是变相的人的生命至上论。黑格尔虽然编织了理性至上的逻辑体系,但是他的那个绝对观念,归根结底还是人的自我意识,只不过是客观化了的自我意识罢了。可见,在德国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文化中,有着生命意志论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和特质。实际上,一个崇尚理性和科学的民族,一个赋有哲学思维的民族,同样也必然是一个高度正视人的生命存在、尊严和价值的民族。德国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实质上是科学主义精神与人本主义精神的融合与统一。可见,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是有思想渊源的,它深深扎根于德国深厚的人本主义哲学精神的沃土上。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及其思潮对尼采的非理性主义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19世纪30年代的浪漫主义是一个遍及欧洲的运动。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自有其特性,它不仅渗透到文学中,还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影响了德意志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说,18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启蒙哲学和文化的狂飙突进还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是在理性旗帜下反对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张扬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话,那么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及其思潮却丢掉了莱辛、歌德、赫尔德所追随的启蒙思想,丢掉了用理性反对专制的传统,而是用一种否定启蒙思想的特有方式,继续着启蒙运动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启蒙运动是用理性反对封建专制,德国浪漫主义却用非理性反对德国的封建专制。德国的这一浪漫主义思潮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渴望不能达到的、已经失去、无可挽回的、正在消失的、幻想和梦境中的事物。同时,为与理性统治地位相对抗,浪漫主义者揭露人类心灵深处的非理性力量,肯定热情和情感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心性和内省等。这一浪漫主义运动及思潮的非理性倾向极大地影响着富有音乐天赋和具有诗人、艺术家浪漫气质的尼采,突出地表现在,他是用诗的语言、散文的格式表达他的思想,他的文风给他的学说作了最好的注释——充满生命性、力度、矛盾重重、狂妄、嚣张、刺激、引起强烈的痛苦和欢乐。别人用概念的严整砖块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他却用诗文般的彩石建了一堵堵花墙,因而他的哲学不象他的德国哲学家的先辈那样具有严密的体系。没有体系,没有逻辑,只有对生命沉思的刹那闪现的激情记录,他的哲学之作,也即是他的美学和文学之作,喜怒笑骂潜蕴着幽默,悲怆中夹带着辛辣的讽刺,这些无不是浪漫主义运动留下的深刻印记。
如此看来,敏锐地感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以探求人生意义为哲学使命的尼采,向人的心理生活的深处和领域开掘,并成为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这便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 影响:带来了“西方哲学的颤栗”
雅斯贝尔斯曾用这句话来形容尼采非理性主义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尼采一开始从事学术活动,就向科学和理性发出了挑战,他为自己选择的第一个靶子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这个被德尔斐神谕称作最聪明的人的哲学家,本来在倡导人的哲学方面倒是有历史功劳的,可是,他研究人生问题的方式却是十足理性主义的,完全依靠逻辑推理的手段,通过概念的辩驳去寻求一般性的结论,并且这一结论也是十足理性主义的,他把人生的意义归结为追求知识,因此尼采把苏格拉底称作“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的原型和始祖”(注:尼采:《看这个人》。)。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的影响笼罩着世世代代,人们相信科学至上,知识万能,思维能洞悉万物的本质,在理性的感召下,人们求知欲泛滥,思想之网密布世界,“建立概念、判断、结论等手段被推崇为在一切才能之上的最崇高的事业和最值得赞美的天赋”(注:尼采:《悲剧的诞生》。)。这种情况从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变本加厉地出现。但是,科学迅速发展到现代,其极限暴露出来了,“科学受了强烈幻想的鼓舞,一往无前地奔向它的极限,于是蕴藏在它的理论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那里碰碎了”(注:尼采:《悲剧的诞生》。)。这种科学极限一方面表现为,任何科学体系都是以某种不能由逻辑手段证明的公理为前提的,这种公理是“一种命令式的无条件的原理”,因而也是一种信仰,所以“即使科学也基于一种信仰,‘根本没有所谓无前提的科学’”(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另一方面,科学所自命的那种普遍有效性根本就是一种幻想,科学并非无所不能的,它的无能尤其在触及人生问题时暴露无遗了,“科学能否给人的行为以目标呢?”(注:尼采:《快乐的知识》。)他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尼采看来,科学借以掌握事物的手段是逻辑概念和推理,可是思维凭籍这些逻辑手段不可能“达到存在的深不可测的渊源”(注:尼采:《快乐的知识》。)。对于人生的探索不仅不可能靠抽象的逻辑思维,恰恰相反,在科学精神支配下,人们凭概念指导生活却虚度了人生。为此,必须反对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和科学,以代表真实、破坏、疯狂、本能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来反对代表幻想、追求、理性、道德的日神(阿波罗神)精神。在尼采看来,酒神精神之所以比日神精神更重要,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它意味着人的一切原始的冲动都获得了解放,而不受任何理性观念或原则的约束,人性的深处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在尼采看来,传统哲学最大迷误产生的根源之所以是理性,是因为理性的逻辑本性使它本能地寻求条理化和秩序,因而害怕感官,从而窜改感官。一个理性主义哲学家总是蹲在他的冰冷的“概念”世界里,生怕自己被感觉引诱离开这个安全窝,到南方海岛上去,因为在那里,他的哲学家的贞洁将如残雪消融于阳光之下,他用蜡塞住耳朵,不敢听生命的音乐,怕音乐会使他象传说中的船夫一样魂迷而触礁沉没。(注:尼采:《快乐的知识》。)所以,“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的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出他们的手掌”(注:尼采:《偶像的黄昏》。)。当然,尼采在这里批判理性,并不是反对对世界作任何概括。事实上,当他把世界归结为权力意志或生成变化着的生命意志时,他自己就在进行概括。他反对的只是人类按照自身的理性本性去构造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模式,然后又用这个世界模式来约束它自身,使逻辑把自己的界限当作世界的界限,人类认识活动的工具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冒充真理和最高的价值标准。这样的话,生命被贬值,本能受压制,一切受法则所统治,人生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乐趣。从这个角度,尼采认为,理性是败坏本能的因素。
与此相联系,尼采还从理性的起源上对理性进行了批判。尼采认为,传统哲学家们出于道德的偏见,以理性为高贵,以非理性为低贱,并且认为高贵者不能从低贱者生长出来。事实上,一切理性的事物追根溯源,血统并不纯洁,都是来源于非理性,“凡悠久的事物,必渐为理性所渗透,使其产生于非理性的由来逐渐磨灭”(注:尼采:《朝霞》。)。理性起源于非理性,这是“理性的巨大原罪”(注:《尼采全集》第八卷。)。在尼采看来,人类的全部精神活动,无论是认识活动、道德活动,还是审美活动,都是以非理性为基础,这个非理性基础就是人的生命本能。因此考察认识活动、道德活动和审美活动都必须与主体的生命需要联系起来,真理、逻辑、理性范畴、善恶评价等都是类保存的工具,都是受本能需要支配的手段和工具。这一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能冲动,不是来自于上帝或其他物质和精神实体,而是来自于人的生命本身。为揭示人的生命本能,尼采极感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他对人类心理和本能的洞察力,他自称是“无双的心理学家”(注:尼采:《看这个人》。)。他认为在他之前的心理学,如同哲学一样,浸透着理性主义的精神,其研究对象往往局限于人的心理生活的有意识领域,如意识、感知觉、观念、联想、注意等。在尼采看来这只是人类心理生活中的最小部分,“不妨说是最表面最糟糕的一部分”,因为“意识其实不属于人的个人的存在,毋宁说属于人的社会性和群性”(注:尼采:《快乐的知识》。)。对个人来说,凡是进入意识的偏是他身上的非个人性的东西、平均化的东西。为此,尼采极其恼恨把人的个性一般化、平庸化的意识的作用,认为揭示人的个性必须研究我们心理生活中存在着的无意识领域,对此,尼采反复作了论述,他一再指出,我们精神生活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地进行着的,揭示无意识领域的奥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领域正是人的行为的真实动机之所在,也是人的“心灵”的真正诞生地。那么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支配着人的行为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尼采认为这就是需要,或者说冲动。“在每一行为中都有一冲动的满足,这冲动抓住这行为如同它的一个掠获物。”(注:尼采:《朝霞》。)这种冲动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是权力意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的权力意志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反对把人的意志归结为自我保存,而主张要增长、改善、超越创造自身,如果把生命意志仅仅归结为自我保存,那就会使人因循守旧,无所作为,逆来顺受,最后必然悲观厌世。而如果把“增长”、“改善”、“超越”本身当作意志的本质,那就会使人积极主动。尼采之所以提出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注:尼采:《朝霞》。)等也正是基于对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一种肯定。
凡是种种,尼采通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使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欧洲传统哲学瓦解了,他的“重新估价一切价值”、“权力意志”以及“超人哲学”等使西方理性主义哲学颤栗了,他为“思想自由而战”(注: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目的达到了。
三 评价:是一种“懒惰的理性”
这是胡塞尔对非理性主义的评价,用来评价尼采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合适的。如果说,非理性主义是尼采哲学使西方哲学颤栗的武器,那么评价尼采哲学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就是从对这一武器的批判开始。当然,这种批判应当是科学意义上的批判。
非理性作为人之精神的一种特质,同理性一样,构成人类精神内在性质的特性。但是,如果以哲学文化形态,将人之非理性精神性质绝对化,甚至上升为哲学本体论问题,形成非理性主义,就需要认真分析、批判和考察了。非理性主义属于“懒惰的理性”,它常常以扭曲和变态的心理观察社会和人生,解释自然、社会、历史、人生和文化等重大问题,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能否以此来全盘否定非理性主义呢?我们认为恐怕不能。因为它虽然是“懒惰”的,毕竟是“理性”,它不是人类感觉之产物,而属于思维之理智产物,它无论是作为人类精神还是思维方式,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以哲学体系出现,这标志精神对非理性自我认知已趋于成熟。所以,对待非理性主义我们不能采取简单化。长期以来,人们对“非理性主义”产生误读,有人甚至把它理解为不讲理,可以信口胡说。有人则振振有词地认为,非理性主义哲学家非难理性,而他们自己写出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巨著,他们常常从原则出发推出结论,而且写出它是为了让人理解,这不是承认理性吗?以此来证明非理性主义哲学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
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实则是对非理性主义的一种严重的误解。非理性主义不是说人可以不要理性,它只是指出理性有它的局限性,不能把人的本质就看成理性;它只是指出,人不仅有理性,也不完全受理性支配,人的许多判断和行为,尤其是对人生来说最基本的那些判断和行为,往往正是依意志、情感、欲望等“非理性”的东西进行的;它只是指出,理性即推理,推理需要前提,而前提的选择当然不能再依仗理性的,因为理性在根本问题上总是难免陷于二律背反,相反促使人作出最根本原则选择的,往往是情感、欲望等非理性的东西。非理性主义指出的这些问题无疑是正确的,更何况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意义从未包含否认人有理性的内容,也从不否认理论是要由理性来完成的,它只是指出,理性对人只是工具,而人本身才是目的。如果人一切服从理性,则人将成为工具,人只有使用工具才能有自由。此外,非理性主义者所关心的并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作为总体的人本身;不是对人的各种具体活动作出分门别类的研究,而是对人生意义、人的本质、人本身的状况、人生价值等根本问题的研究。显然,这些也是宗教和近代理性主义都曾十分强烈关心的问题,差别只在于试图解决这些人生终极关切问题的思路和途径不同而已,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并不是势不两立的。
尼采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非理性主义的。因此,对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我们必须采取公允的态度。长期以来,人们对尼采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对非理性主义理解上的上述误读,所以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尼采哲学基本上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观点占主流。本文认为,否定当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过去我们对其合理性的一面重视不够,缺乏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应当说,尼采在对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中,他的非理性主义是击中理性主义特别是近代理性主义要害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理性主义的统治确使人们迷恋科学万能,热衷追求知识,从事外在的物质活动,而忽视了人的内心生活,它使传统哲学以逻辑和僵死的概念来裁剪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从而将人视为受逻辑支配的理性动物。尼采对理性主义的所有这些批判是为了竭力证明:科学不能为人生提供真实的意义;同时,也并无一个合乎理性的本体世界,世界的意义靠人去赋予;一切理性事物都具有非理性的起源;人的心理中有一个无意识领域,其中潜藏着人的意愿和行为的真正动机。我们且不说尼采的批判是否完全正确(它的合理性主要不在于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催人沉思,这确是世人共睹的。此外,尼采的非理性主义也标志着人类对自我认识深化,其中他对梦幻、替代、遗忘等心理现象的研究,为后来的弗洛伊德心理学所接受。
由此可见,对于尼采非理性主义,我们绝对不应忽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当然这并意味着它全然是积极的。罗素在谈到尼采哲学时说:“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一定流行得很。”(注:罗素:《西方哲学史》。)这就是说,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所以对待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具有的破坏作用(这方面过去论述很多,不再赘述)。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具有的建设性作用。他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工业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各种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危机,揭露理性和科学的繁荣所掩盖的人与人关系的危机以及对情感和人性的压抑。在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发出了高扬人生生命的呼喊,从而催人反思资本主义压抑或扼杀人的生命力的社会弊端,催人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正是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真正意义和生命力之所在。
标签:非理性主义论文; 尼采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悲剧的诞生论文; 快乐的知识论文; 德国生活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朝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