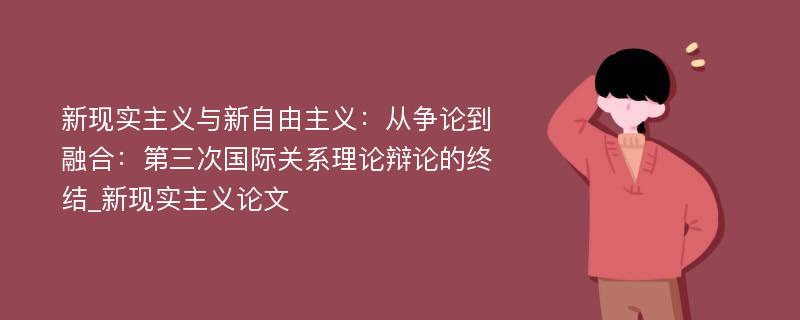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自由主义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三次学理辩论指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被通称为范式间辩论(inter-paradigm debate)。范式的概念首先出现在科学史研究领域,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库恩用这个概念表示一个理论体系成为某一学科主导理论体系的过程,即科学团体普遍接受并采纳的理论体系,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于物理学。(注: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亦参考吴晓明:《科学与社会》[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9页。)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是针对自然科学的,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讨论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时候,人们使用范式间辩论这个术语,正是借鉴了库恩的理论。
库恩理论中有两个观点尤其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辩论。第一个观点是范式转移说。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一个渐进的、平稳的进化过程,而是充满起伏跌宕和急剧变革。科学发展经历了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这样的循环过程,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之间的交替发展是以理论危机作为动力的。当人们渡过前科学的混乱时期后,科学常规时期就出现了,科学家们在主导范式的框架中解决疑难,积累知识。但随着经验领域与这种主导范式相悖的“反常现象”逐渐增多,主导范式因无力解释这些现象而受到质疑。同时,如果范式不能再向科学家提供新的疑难问题,不能产生可有意义的假设,范式也就失去了生命,新的范式就可能出现。一旦新的范式出现,范式转移也就开始了:旧范式被新范式取代,科学革命发生。科学革命推动学科发展。第二个观点是不可通约说。库恩认为,判别两种范式的不同,主要是看这两种范式是否可以通约。不同的范式包含不同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可以产生不同的问题,包含无法相容的判断标准,所以,两种不同的范式从本质上说是互不相容的,亦即不可通约的。如果两种范式在根本问题上可以兼容,则失去了本质的不同,其争论也就不是范式间争论。
根据库恩理论,第三次辩论的起始时期的确有着范式间辩论的特证,但是后来主要对立范式之间却越来越趋同,对于国际关系核心问题的理解从根本不同到逐渐一致,于是,范式之争失去了原有的学理意义。可以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第三次辩论基本上结束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学理上越来越接近新现实主义,这两种主流理论以理性主义为基底合成在一起,共同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理论体系。但也正是这种趋同使范式转移迹象出现,新兴的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与新现实主义论争的强劲理论范式。(注:Dale Copeland,"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2(Fall,2000),pp.187-212.)
一、范式间的论战: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注:这是借鉴了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一书的题目。参见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自摩根索1948年的著作《国家间政治》奠定战后现实主义基础之后,现实主义战胜理想主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的主导理论范式。后20余年,虽然批判声不断,但始终没有一种对立的理论能够动摇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所以,国际关系学从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基本上处于常规科学时期,西方主要国际关系学研究人员都在现实主义的范式范畴内从事研究。(注:区域一体化研究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参见Karl Deutch,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Ernst Haas,Beyond the Nation Stat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至1979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新现实主义发展了经典现实主义,使战后现实主义理论达到了峰巅。
华尔兹理论的影响之大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少有的现象。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华尔兹提出了高度简约的现实主义理论,摒弃了经典现实主义中人性等难以用科学标定的概念和无法证伪的假设,把无政府秩序和自助体系、权力分配、国家利己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设定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把国际关系研究集中在体系结构这个因素上面,因此,华尔兹理论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它提出了一整套严谨的研究议程,据此产生了一系列可证伪假设,为8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制定了核心研究议程。结构现实主义不但使现实主义更加科学化、体系化,而且激发了政治科学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从而引发了80年代至今近20年的国际关系学理辩论。
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自由主义流派。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超出现实主义理论框架的反常现象越来越多,各种自由主义思潮纷纷兴起。对现实主义提出深刻批判的是基欧汉和奈1977年的著作《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国际政治》。它反驳了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说、军事权力说等基本假说,成为跨国主义的代表作,与华尔兹两年后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到80年代,多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派别——共和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逐渐成形,虽然这些派别各有侧重,但都可以统一在自由主义框架之中,共同形成了对现实主义的严峻挑战。(注:Mark W.Zacher and Richard A.Matthew,"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Common Threads,Divergent Strands,"in Charles W.Kegley,ed.,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New York:St.Martin's,1995),pp.107-150.)在诸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学理方面最有影响、研究议程最严谨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著作是基欧汉1984年的著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第二类是以新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框架的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只有把世界政治置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框架之中才能使其实质和内容得以揭示。国家体系的产生和延续是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的,核心、半核心和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世界体系理论具有强烈的批判特征,但是在实证主义认识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方面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基本的相通,所以也可以置于主流理论范畴的边缘。(注:代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多是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分类的,虽然名称可能不尽一致。参见Paul R.Viotti and Mark V.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Pluralism,Globalism(New York:Macmillan,1993)。)并且,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的理论基底都是理性主义,所以基欧汉将这三种理论统称为理性主义理论。(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p.158-179.)
第三类是与主流理论范式之间辩论同时发展起来的所谓的非主流国际关系学派。这个范畴内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国际关系中观念和话语的作用、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建构、权力的非物质性和真理的相对性。正因为如此,这些理论的本体论基底是与理性主义根本不同的。可以列入这一范畴的理论流派包括:规范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理论、历史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这些理论在涉及理论建设和知识建构等根本问题上与主流理论相左,它们否认理性的核心作用,反思主流理论作为给定因素的一系列重要概念,主张用新的认识论理解社会世界。这类理论被基欧汉统称为反思主义理论。
这样,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基本状况是在两个纬度上展开的:一方面是理性主义各学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之间的论争,另一方面是反思学派的对理性主义学派的挑战。
随着辩论的发展,论战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这一辩论成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轴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杂志上大多数文章是关于这两种理论流派的争论和依照各自理论体系所做的实证分析。(注:参见David D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世界体系理论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发起了挑战,但是两个主流理论派别的应战兴趣不大,所以,这个向度的辩论更多是单向的。正因为如此,世界体系理论无法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具有同样重量级的理论范式,虽然被大多数学者归入主流范式之争范畴,但始终处于次要地位。非主流理论派别的状况更是如此。这些理论主要是在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尤其针对在国际关系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非主流理论的主要贡献也是对国际关系学的核心问题——知识建构——提出的质疑。虽然主流理论学者也承认非主流理论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但基本上把非主流理论称之为“非客观的”和“非科学”的,(注: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因此不予重视,对非主流提出的批判也很少作出回应。因此,所谓的第三次大辩论实际上是不对称的论战。
这种现象无疑导致了一种结果,即主流和非主流理论同在一个学术领域,但根本谈不上平等的沟通和交流。新现实主义的批评者甚多,但真正能与之对话的只有新自由主义一家,其他各类国际关系理论则只能处在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缘。
二、主流学派的辩论:由不可通约到理论趋同
作为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重心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之所以被称为范式间辩论,是因为两派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比较明显。经典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受到根本质疑:基欧汉和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概念,认为国家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国家不是单一性理性行为体、军事手段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效用越来越低。(注:Robert Keon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ne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Boston:Little,Brown,1977).)其中核心的驳论就是否定国家是主导国际行为主体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本假定。正国为如此,《权力和相互依存》一书才被视为跨国主义的代表作。其他自由主义学派也围绕这个核心问题上提出质疑。(注:参见Graham 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Little,Brown,1971).)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不可通约性使两派理论观察不同的客观事实,使用不同的经验数据证实各自的理论或证否对方的理论。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它们对世界的看法有着实质的不同,尤其是涉及国际行为主体这个重要问题,所以,可以把两派简称为国家中心理论和多元中心理论,亦即国家是否是国际体系中唯一具有意义的单一性和无需质疑的理性行为体。在70年代国际事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各派指出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的许多“反常”现象,力图否定现实主义理论,核心就在于否定国家为理性行为体的理性主义假定,目的是复兴自由主义理论范式,使之取代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新的主导理论。
但是,随着第三次辩论的发展,主流学派之间这种不可通约的现象逐渐淡化。转折点是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这部著作力图摒弃一切形而上的思考,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为像物理学那样的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体系。经典现实主义中的哲学意义和社会内容被以非科学为理由予以排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被表述为类似经济学中市场和个人构成的系统,或者说类似物理学中场和粒子的系统。为了发展这个系统,华尔兹必须把国家严格定义为单一性的理性行为体,这样国家才可能成为可以类比的“相似”的单位。他也必须把国际体系定义为具有单一无政府逻辑的自助体系,这样才可能使相同的体系单位——国家——在国际体系场中从事有规律的行动。(注: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中的进程因素》[J],《中国书评》1998年总第13期,第5-18页。)结果是现实主义从一种描述国际关系实质性内涵的理论转化为一种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基本变量只有两个: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行为。基本变量关系是:在无政府条件下,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用华尔兹自己的话说,这就是现实主义“思想”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区别。80年代的重要现实主义著作,如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战争与世界政治变革》、布伊诺·德·梅斯奎塔的(Bueno de Mosquita)《战争的困境》等明显地表现出这些特征。
华尔兹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并不在于他对现实主义世界观的调整,而是他把现实主义发展为具有高度科学特征的国际政治理论。正是这种影响,使得自由主义各个理论流派成为在学理、在理论体系发展方面很难与其竞争的理论。但是,也正是这种影响,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在诸自由主义流派之中成为影响最大、能够与新现实主义在学理上抗衡的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要呈现出高度的科学性,必须对经典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果断的取舍,重新定义核心概念和基本研究议程。基欧汉的《霸权之后》所做的实质性努力的意义正在于此。他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注:Keohane and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State Power,尤其参见其中他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和自我学术思想发展的叙述,如"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 Perspective on World Politics",和"A Personal Intellectual History"两篇论文。)首先,基欧汉收紧了1977年《权力与相互依存》中的基本假定,转而承认国家的理性和单一性特征,这就接受了理性主义的核心内容。其次,他承认无政府秩序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接受了华尔兹对无政府逻辑的定义。再次,他也是致力于发展体系理论,力图发现最简约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为此,他把国际制度定义为国际体系进程的基本特征,把国家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主体。这样一来,基欧汉的理论也成为简约的、呈现高度科学性的系统理论,其基本变量也是两个,即: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基本变量关系是:在无政府条件下,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
历史久远、纷繁复杂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在华尔兹和基欧汉的整合之下,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主流派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者之间的论争也构成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国际关系学理争论的焦点。但是,在两派理论都向着高度科学性努力的同时,它们也在朝着理论趋同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理论框架趋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基底都是理性主义。明显的例子是在对国际行为主体的基本假定上面。新现实主义一直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并以微观经济学定义个人/公司的方式,把国家定义为利己的、单一性的理性行为体,国家的利益和身份完全是内部因素决定的,与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没有关系。基欧汉在提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时候,也从原来肯定多元国际行为体的立场后退,承认关于国家行为体的理性主义假定,把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假定为给定因素,独立于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相互作用。至此,两派的基本理论假定从根本上统一到理性主义上面。
第二,世界观趋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接受物质主义理论,不承认观念的实质性意义。新现实主义的最基本概念——国际体系结构——指的是国家物质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配状态,主要以军事力量定义的国家权力和以物质收益为主的国家利益也反映出单纯物质主义的浓厚色彩。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质的,但其作用取决于制度能够提供的物质回报,物质性权力和利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动因,因而成为诸自由主义流派之中最具物质主义色彩的理论。对于新现实主义来说,观念是无足轻重的;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观念能够成为一个与权力和利益并列的自变量,具有独立的因果作用。但是,观念与权力和利益之间是相互独立、相互并列的关系,观念的作用也只能是弥补物质权力和利益解释能力的不足。(注:参见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所以,在物质主义世界观方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趋同。
第三,认识论趋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坚持科学实证主义的原则,反对任何诠释性理论。基欧汉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赞成新现实主义的一些重要推理原则。……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不满足于对文本的诠释:两派学者都认为存在国际政治的客观事实,虽然这样的事实总是不能完全得以揭示,但部分的解释是可能的。”(注: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p.8.)一切对国际政治社会内容的考虑和对国际政治诠释性的研究都被视为没有明确研究议程和可证伪假设的非科学解释。(注: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
第四,研究方法趋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坚持体系理论的研究方向,认为诸如国家和个人层次上的研究无法构成国际政治理论。虽然两派所强调的侧面不尽相同,但研究层次都是国际体系,都认为体系理论才可以称为国际政治理论。在体系层次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起点又都是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这个特征又派生出三个基本假定。首先,无政府状态是给定因素,“客观存在”于国际体系之中,是凌驾于体系中行为体之上的无形之手。其次,由于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恒久的基本特征,所以,国际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必然要以无政府状态为研究起点和基本条件。华尔兹讨论均势和两极结构对无政府状态负面影响的制衡作用,基欧汉探讨国际制度对无政府状态负面影响的削弱作用,两种研究议程都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为切入点。再次,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秩序只有一种逻辑,即霍布斯自然状态的逻辑,亦即国际体系必然是一个自助体系、国家必然寻求自我安全的逻辑。(注:Waltz,Thoe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on Wesley,1979).)基欧汉在研究国际制度的一系列论著中,无政府状态的这一逻辑都是被作为理论假定和给定因素处理的,他从来没有对无政府状态的根本性质提出质疑。所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种体系理论在国际体系基本特征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
由于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趋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也相互吸引和相互靠拢。根据鲍德温的阐述,到90年代,两派的研究议程和主要分歧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合作问题:新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使国家在整体上趋于不合作,相对收益是国家考虑的主要问题,国际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减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因此不能导致根本的国家间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在承认无政府逻辑和体系结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国家可以以绝对收益为基本考虑,国际制度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减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导致国家的实质性合作。这样一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就集中到相当狭窄的范围之内,已经不像经典现实主义和经典自由主义那样具有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质,共同的理性主义学理基底、科学主义研究原则、无政府逻辑的假定以及合作进化和制度作用等研究议题使这两个主流理论学派不仅成为可以通约的理论,而且产生了所谓的新—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注:Ole Waev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in Steve Smith,Ken Booth,and Maryasia Zalewski,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49-185.)新自由主义已经从新现实主义的批评者转变为合作者。这种新新趋同的结果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对现有理论的质疑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和虚化。因此,国际关系范式辩论的分界线自然而然的开始转移。
三、结论与反思
我们说明了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从范式之争到理论趋同的发展过程。反思这次学理辩论的过程,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界定为第三次辩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和现实主义的辩论、世界体系理论和现实主义的辩论、反思学派与现实主义的辩论这三个不同向度的论争共同构成了第三次学理论战。这场辩论包含了主流理论之间的辩论、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辩论。无论是哪个向度的辩论,依国际关系核心问题判断都具有不可通约性质,因为各种理论中的主导行为体,亦即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不一样的,并且是不相容的。如果以主流学派之间的辩论为第三次学理辩论的核心,那么,基欧汉和奈1977年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标志着第三次辩论的正式开始。1979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则把第三次辩论推向峰巅。而从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确立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时起,这场范式间辩论似乎出现了明显的主流学派的对垒,但是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趋同,因为在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上,华尔兹和基欧汉已经表现出高度一致。1998年基欧汉《对外政策》发表的文章实际上标志着第三次论战的基本结束。(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Foreign Policy(Spring 1999):82-96.)
其次,主流派曾试图与非主流派对话,这主要是新自由主义联合非主流学派对新现实主义发起批判的努力所至,明显标志是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一书。该书于1986年出版,收入三种不同类型的论文,包括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主要章节和另一位新现实主义重要作家吉尔平的论文;自由主义学者基欧汉、拉格(J.Ruggie)的文章;还有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学者考克斯(R.Cox)和阿什利(R.Ashley)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文章。但是,这种对话没有得到有意义的延续。1988年基欧汉作为国际政治学学会会长的发言基本上以“非科学”为理由否定了非主流学派的学术意义。所以,对话中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开始向新现实主义靠拢,因而也就越来越与非主流理论互不相容。至1989年基欧汉出版其论文集并阐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主流学派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常规科学的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的共同体聚集在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辩论轴心上,以越来越精细的方法证实或证伪这两派的理论假设。
第三,第三次辩论从不可通约理论之间的辩论发展到主要对立理论的趋同主要是双方越来越朝着科学主义努力的结果。第二次国际关系学大辩论是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的论战,行为主义以其科学性占了上风。虽然后来的后行为主义部分地校正了行为主义革命的过激,但是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主流学派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科学的原则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宏大理论体系必然呈现科学的简约,因此也就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诠释和非科学的成分,使国际关系理论至少成为经典经济学那样的科学理论。比较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和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和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取舍。对于非主流学派,主流学派也认为最大的弱点就是其非科学性质。所以,在丰富的国际关系现实和严格的科学原则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从科学原则的角度来看,主流理论的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今的国际关系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似一门科学学科。但是,当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达到了高度趋同的时候,它们也就从真正的范式间辩论发展到虚假的范式间辩论,从对国际关系本质问题的论战发展到精巧的技术性论证。范式的研究议程已经相当狭窄,它们之间的辩论就只是为手艺高超的工匠提供表现技巧的场所,而无法为思想家提供有重要意义的疑难问题去思考。这时,范式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末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学理正处于这种境地。当旧范式失去活力的时候,它也就为新范式的出现作出了铺垫。90年代中期以来,反思主义各种理论再度活跃,尤其是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已经进入主流理论的论战战场,成为最具活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注:关于社会建构主义国家关系理论,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亦参见Robert Keohane,Stephen Krasner,Roxanne Doty,Hayward Alker,Steve Smith等人对温特社会建构主义的评论和温特的回答,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6,No.1(January 2000),pp.123-180。)新的理论整合已经崭露头角,并开始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设定新的研究议程。
标签:新现实主义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无政府状态论文; 华尔兹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