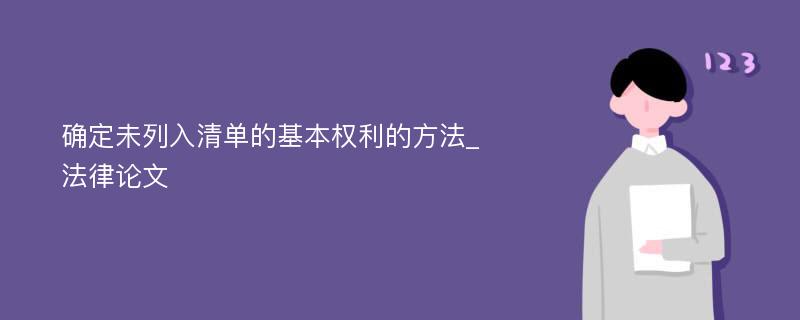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权利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宪法文本列举基本权利的传统由来已久,在近代成文宪法产生之初,便有了对基本权利的明文列举。1776年的弗吉尼亚宪法,首先对公民基本权利作了专门规定。1789年制定的美国联邦宪法,最初虽然没有专门规定基本权利,但是不久便通过了被称为“权利法案”的前十条宪法修正案。法国大革命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1790年宪法,将1789年《人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序言,还规定了公民享有的集会、请愿、宗教信仰以及有限制的选举权等权利。美国和法国宪法的做法,为各国宪法所仿效,蔚然成风。但是,基本权利却不可能被完全列举。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立法技术是有限的,而且还在于基本权利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任何试图用宪法文本完全列举基本权利的努力,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也可能因为忽视未列举基本权利而带来危害。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忽视或否认,不仅将影响宪法列举基本权利的正当性,也将损害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享有。这样的论断决不是危言耸听,早在200多年前,美国的制宪者们就曾表达过这种担忧。威尔逊曾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存在很多权力和权利,它们不能被全部列举。附于宪法之中的权利法案是对列举权力的保留。如果我们尝试列举权利法案,那么所有没有被列举在其中的部分将被视为授出。结果是,一个不完备的列举将使所有隐含的权力落入政府的范围;人民的权利也将变得不完整。”① 为此,威尔逊等联邦党人反对宪法列举基本权利。② 也正由于对于这一担忧的充分认识,才有了后来的承认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③ 由此可见,确认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是宪法列举基本权利的前提和条件,它消除了宪法列举基本权利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④ 承认和保护未列举基本权利,是各国宪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之一。
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并没有被记载入宪法文本之中,那么,如何判定一项宪法未列举的权利是否为基本权利?界定一项权利是基本权利,其标准究竟为何?围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问题,学者和法官们尝试着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标准和方法来实现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
一、求诸传统的认定方法
普通法系以遵循先例为特征,遵循先例原则要求律师和法官“往回看”,从传统中找依据。早在1250年,布莱克顿就主张,律师必须求助于过去以便找寻构筑法律的证明。普通法律师找出过去判决中有价值的先例,通过逐个的对比和区别,发现连贯性的原则。“往回看”的分析过程,将使律师更接近“法”的意义。英国普通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科克爵士(1552~1634年)较早地运用普通法系“往回看”这一模式,提炼出基本权利的独特理论。他的理论由四项原则构成:首先,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在私人诉讼的过程中来认定相关的基本权利;第三,他相信律师专擅于发现和论证基本权利的存在与否;第四,他认为,违反基本权利的法律后果是,与之冲突的国会立法、皇家训令或习惯法将归于无效。⑤ 科克大法官运用普通法的原则,在“普遍传统和长期实践”中发现和寻找基本权利,这一理论为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提供了框架。
科克大法官的理论实际上是将普通法的传统应用到基本权利领域之中,从传统中去找寻基本权利。在美国的宪法实践中,这一方法得到大法官们的认同。最早运用这一方法的是1923年的Meyer v.Nebraska案。⑥ 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依据历史传统认定父母享有的指导自己子女教育的基本权利。法院在判决中强调,“美国人民长期以来视教育和知识的获取为极端重要且需要不断提升的事务”,并指出,“建立家庭和抚育子女”这一特权,“在普通法中很早就被确立为一项自由人追求法定幸福所必不可少的权利”。⑦ 在1937年的Palko v.Connecticut案⑧ 中,卡多佐大法官再次肯定应从传统中“识别”基本权利。他认为,当所侵害之权利触及“根植于我们人民的传统和意识之中被视为基本的正义原则”,那么这项权利就是基本权利。此后,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又进一步阐发了Meyer判决中确立的求诸传统的方法。在解释被他称为“极具概括性之条款”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时,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指出:“这些条款的概括性并非启发式的,而是通过历史得到界定的,这是与这类条款所涉及的政府问题的广博性相适应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保障,勾勒出英语国家人民上溯至大宪章时代并反映于我们人民的宪政发展中的自由史。”⑨ 在1952年的Rochin v.California案⑩ 中,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更进一步提出,法官认定一项争议中的基本权利,要看对于这一行为的禁止是否“侵犯了那些反映了英语国家人民正义观念的正派和公平的准则”,要看这一行为是否“根植于我们人民被视为基本的传统和意识之中”。哈伦大法官在Poe v.Ullman案(11) 的反对意见中更为清晰地对这一方法进行了阐述。哈伦大法官认为,正当程序条款“并不能自我解读”,“也不能通过这一条款的历史来明白这一条款的含义”。他主张探究“我们这个建立于尊重个人自由之上的国度曾在自由与社会需要之间实现的平衡”。换言之,哈伦大法官将“传统”视为基本权利的效力来源。在他看来,如果美国传统上就保护使用避孕物的自由,那么就应当视为基本权利;相反,如果在历史上没有被承认过,那么就不应当受到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
大法官们的阐述丰富了求诸传统这一认定方法的内涵和意义,也使得这一方法在美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崇。在晚近的许多认定新基本权利的重要判例中,例如Griswold v.Connecticut案(12)、Roe v.Wade案(13)、Bowers v.Hardwick案(14) 和Michael H.v.Gerald D.案(15) 中,这一方法皆得以适用。丽贝克·布朗教授在谈及Bowers判决和Michael H.判决的影响时指出,“传统标准已经日益成为是否作为新的基本权利的试金石。对于诉讼人来说,如果不能运用这一标准证明新的基本权利,那么将导致失败。”(16) 可以说,求诸传统的方法是美国目前最广为接受的基本权利的认定标准。(17) 这种方法之所以如此流行,是与英美法国家宪政主义的普通法背景一脉相承的。英国人的宪法权利蕴含于悠久的普通法传统之中。美国人的权利法案则是经由普通法而形成的英国人的宪法权利的概括。拉赛尔·柯克就曾评价道:“杰弗逊式的《权利法案》不过是对普通法诸原则的一次重申而已。就其起源而论,美国人的个人自由得益于普通法之处多于任何别的地方。”(18)
二、“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
在德国,由于基本权利的列举采取列举加概括的方式,所以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问题在德国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德国基本法》为了弥补了宪法列举基本权利的不完全性,在其条文中预先设置了具有兜底性的概括条款,即第2条第1项之规定:“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但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违反宪法秩序或道德律。”这一概括条款“作为一种权利源泉”,可以“不断提供能够满足社会主体权利需求的根据与类型”。(19) 通过解释和适用基本权利概括条款,可以补充和确认那些宪法没有列举的基本权利。于是,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问题,在这里便转化为如何解释和适用基本权利概括条款的问题。那么,如何解释和适用基本权利的概括条款?如何判定一项权利是否属于概括条款所保护的未列举基本权利呢?德国学界和司法界的普遍观点是,依据《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所确立的“人的尊严”概念作为指引。
《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中明确宣示:“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该条款中所确立的“人的尊严”观念,在德国历史上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实系“背负2500年哲学历史的概念”。(20) 德国哲学家康德对人的尊严作过系统而深刻的表述。在《道德的形而上学》中,康德把“人性”归结为自己设定目的的能力,即自行决定实现自己所选择的目的的能力。他说,这是人类的自由选择行为不同于兽类行为之所在。(21) 因为人类本身即是一道德主体,其系自己的主人,而非受制于他人。他在《美德的形而上学原则》(1797年)中指出:“人在自然系统中……无关紧要,他与其他动物被认为是地球的产物,有一种一般的价值……,但是人作为人,即作为道德上有实践理性的主体,他又是无比高贵的。正因为作为这样的人(人本体)(homo noumenon),他永远不能仅仅被当作是别人目的的手段,或者甚至是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应被珍视为自身的目的。”(22) 康德“以人作为目的”的人性,对人的尊严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以人类的理性本质,强调人的尊严之道德上的自治(Sittliche Autonomie),而以自治为人性和一切有理性事务之尊严的基础,此乃因为人永远是目的之本身。每一个人都是具有平等意志的人,须受平等地尊重与对待。(23) 由于康德哲学思想的推波助澜,个人的存在价值备受重视。在经历纳粹时期对人性的藐视与残害的惨痛教训之后,“人的尊严”的保障条款首先在德国纳入基本法之中。(24)
在德国,“人的尊严”已成为宪法最根本精神之所在。根据学者的阐释,基于“人的尊严”概念,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人,应为国家的目的,并且国家系因人民的意愿而存在,非人民因国家的意愿而存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明确判示,人必须为自己存在,不得作为以及特别不得贬为(或当作)国家统治之客体来处理。也就是说,人不得变成物或是一种东西,亦即所谓的“客体理论”。(25) 依此,个人乃成为一切价值的根源。基本权利之保障与国民主权原理皆导源于“人的尊严”概念。“人的尊严”,被视为基本法保障基本权利之精神所在。(26) 并且,所有基本权利皆围绕这一概念展开,(27) 是其内容的具体化。因此,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以“人的尊严”概念为指引来论证和界定基本权利,是最为常用的方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确认信息自决权的人口调查第二案(28) 中,便运用了这一方法。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作为在数据处理的现代条件下自由发展个性的前提,个人必须被保护免受个人数据的无限收集、储存、使用和传递。基本法第2条第1款,连同第1条第1款,为这项权利提供保护。对于(国家)是否可泄露或使用其个人信息这一问题,这项基本权利保障个人为自身作出决定的权利。”(29)
以“人的尊严”为指引认定未列举基本权利,不仅在德国受到普遍推崇,而且也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广为流传。例如,韩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普遍认定“人的尊严”价值的核心地位。在韩国,人的尊严与价值首先通过宪法第11条到第36条规定的具体条款得到实现。但这些条款并不能保护人的尊严的全部领域与情形。当宪法没有列举,但对人的尊严的维护确实需要时,宪法应给予保护。一般意义上,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只是人权的一部分,是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权利,但仍不能全部包括人的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所有权利要求,人的尊严的保护实际上依赖于“没有列举权利的条款”。(30) 在英美法系国家,“人的尊严”这一认定方法也有不少学者认同。例如,加拿大学者康克林教授就主张采用“人的尊严”概念来判定那些特定的权利属于基本权利。康克林教授认为,“人的尊严”这一理念中包括了对人本性的一般认识和必须尊重人的含义等内容。对个人行为的最小道德拘束正是出自对人的尊重和人的本性。这些道德拘束就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和义务。(31) 康克林教授在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适用的一般方法。他指出:“(判断‘一项权利是否基本’的)方法是:质问任一权利是否与对‘人’的‘识别’紧密联系。如果我们诚实地始终如一地坚持我们的社会建立于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上,那么,那些与对‘人’的‘识别’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就是必须履行的‘最低底线’。对于这些权利的‘识别’,至少在三个方面提供宪法上的检验。实现对人的尊重要求:第一,禁止基于种族、性别、国籍和肤色的歧视。第二,禁止干涉个人的自由、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人的思想和感受,限制表达的形式和正当程序。第三,对基本权利给予平等的保护。”(32)
三、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
第三种颇为流行的未列举基本权利认定方法,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学者伊利教授所创立的强化代议制理论。这一理论是伊利教授在1980年的《民主与不信任——关于司法审查的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虽然这一理论的提出旨在为司法审查制度辩护,但是其观点同时也为基本权利的认定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视角,受到学界的青睐和重视,具有广泛的影响。
司法审查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以一个非民主产生的司法机构去审查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伊利教授从宪法文本以及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作为其分析的起点,通过创建强化代议制理论,很好地回应了对司法审查非民主性的责难。伊利教授主张司法审查是一种以参与为导向(participation-oriented)和强化代议制(representation-reinforcing)的方法。(33) 在伊利教授看来,司法审查并不应对实体价值问题进行判断,实体价值的选择和调和问题大部分应留待政治程序去解决。司法审查的职责是通过确保政治过程不受扭曲,从而使代议机构更好地反映民意,保障人权。因此,司法审查不仅是符合民主制原则的,它还是防止民主制弊端的切合实际的、有效的保障机制。伊利教授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司法审查的这种职责,那就是最高法院在政治市场失灵的时候,采取“反垄断”措施,但不是采取管制手段。司法审查不是对实质性结果说三道四,而是在整个政治市场失灵的时候开始干预。伊利教授进一步给出了所谓政治市场失灵的两种情况:(1)局内人阻塞政治变迁的渠道,从而确保他们依然是局内人,而局外人则永远是局外人;(2)尽管没有人实质上被剥夺了选票或者声音,但是服从有效多数的代议制系统不利于少数人,其原因可能是出于敌意,或者因为偏见而拒绝利益的共通性。这样一来,少数派就不能享受到代议制赋予其他团体的保护。在这两种情况下,采取司法干预,其目的是改变扭曲了的政治上的信息。(34)
事实上,伊利教授的理论并非独树一帜,其与德国学者阿列克西教授提出的宪政民主国家路径极为近似。阿列克西教授所主张的宪政民主国家路径是由商议对话理论(discourse theory)发展而来的。商议对话理论的出发点是何者为正确,何者为错误,必须经由对话和商议。正确不是依靠证据,而是通过商议、劝说来验证他们的形式正确性获得的。商议对话理论的正当性和基于商议的重要性,建立在多数人都拥有正确推理能力这一假设之上。但是,人们有能力正确推理,并不表示人们都尊重正确推理的规则。因此,为了实现对话,必须确保一定的规则。维持对话式商议规则的需要,在政治层面上正好证明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宪政民主国家是实现对话和商讨的唯一可能结果,因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保护最自由和最广泛的政治讨论。一般而言,民主制确保每一个人平等地参与到作出政治决策时的对话讨论中。但是,民主制建立在多数决的基础上,这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多数作出不顾对话理论限制的决策。因此,就需要有其他的一些措施来防止这种结果的出现。宪法和违宪审查恰好为这一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可能。宪法和违宪审查通过承认那些为保障正确商讨所必要的基本权利,可以确保少数人自由、平等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35)
伊利教授和阿列克西教授的理论,不仅为司法审查制度(或称违宪审查制度)进行了很好的辩护,也为认定基本权利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既然对基本权利的确认和司法保护,是为了强化代议制度,更好地实现民主、体现民意,那么,一项权利如果为维系或促进民主制度所必需就应当被认定为基本权利。从捍卫民主的立场出发,我们得到了基本权利认定的另一方法,即:一项权利是否为维系或促进民主所必需。美国首席大法官斯通在1938年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mpany案(36) 中大名鼎鼎的“第四脚注”(Footnote4),对于理解这一认定方法极具启发意义。在这个脚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阐明了法院在什么时候可以或应该对立法加大审查力度。什么时候?在民主和法治“失灵”的时候。(37) 依照斯通大法官在“第四脚注”中的见解,法官只有在“民主程序不能正常运作,或者即使能够运作,这类程序也将导致多数派系对少数派系的歧视与压制,而分散和孤立的少数派本身(却)无力通过民主程序来摆脱多数专制的情形下”(38),才对法律进行必要的实质性审查,而且在审查标准上,秉持不同于对关涉其他权利之法律进行审查的标准。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将那些有助于实行民主的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加以保护,具有相当的妥当性。
四、对我国实践的几点启示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的难题在于,这些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并没有列举。为此,主张和保护这些权利,不得不依靠宪法文本以外的“依据”。依据文本以外的“依据”来认定未列举基本权利,这对于法律系统而言,可能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也意味着一项强有力的挑战。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科学对于法学的祛魅”的现实意义。(39) 从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来看,法律不过是政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判决可以借助社会科学的“外部论证”去改善法律系统“内部论证”的空虚与缺失。引入文本以外的“依据”来论证未列举基本权利,可能是对法律系统的一个有益补充。但另一方面,文本以外“依据”的引入,又是对传统规范主义的一种挑战。传统的法学是一种对法律的规范性自我理解的系统,强调法律自身的逻辑周延和自主自足,把法律系统看作是以自控方式把自己包裹起来、封闭起来的系统。(40) 以文本以外的“依据”来认定未列举基本权利,必定意味着是对这一系统的破坏,很可能损及法的安定性价值。(41) 因此,这类“依据”的引入,又必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法的安定性为前提,必须在宪法文本之外找到某种可靠的确定性。由此可知,认定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论证过程,必定是一条蜿蜒崎岖且荆棘密布的道路。前述三种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则可以称作是这一探索道路上的有益成果,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对待。对于我国的宪法实践来说,极具启发意义。
第一,上述方法的实践表明,未列举基本权利并非可欲而不可得的。通过严谨和合理的宪法解释与论证,未列举的基本权利是可以确定的。这一点对于我国的实践来说意义重大。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希望通过修宪增加列举新的基本权利,来完善我国的基本权利体系。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至少是不全面的。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的承认与保护,不一定通过修宪完成,通过适当的宪法解释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我国现行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特别规定,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从宪法文本中,我们并不难找到未列举基本权利存在的文本根据。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国现行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这一条款被一些学者理解我国宪法的概括条款。他们指出,该条规定“意味着,对于那些宪法没有作出明示性规定但却非常重要的人权,就同样也必须给予尊重和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九字条款作为一项概括性条款,在规范意义上可涵盖非完全列举主义精神。……我国宪法中并没有类似的明示性的条款,然而,九字条款至少可以在解释学上填补了这一规范的缺落,不仅为人权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为人权类型的推定,提供了实在宪法上的规范依据。”(42) 虽然这种认识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条款与概括性条款是存在差别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不具有独立的规范价值,而是侧重于表明宪法原则的意义。“人权本身是不确定的概念,在宪法文本中以综合的价值形态来出现,难以成为提炼新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人权虽写在宪法文本中,但与基本权利价值的互换仍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从理念与实践角度建立人权宪法化的机制。另外,宪法还没有进入诉讼领域的情况下,人权条款发挥功能的空间也受到限制。”(43) 不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虽不能作为概括条款使用,但至少宣示:对宪法所列举的基本权利之外的人权,国家仍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可以认为,这一条款为肯定未列举权利的存在和扩大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提供了规范依据。
此外,我国现行《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条款明白地宣示了“人民主权”原则,阐述了政府权力与人民的关系,即政府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人民。(44) 从这一原则出发,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自然不能侵害到人民固有的权利。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特别分析了起源于君主制国家的人权法案,他指出:“人权法案就其来源而论,乃君主与臣属间的规定,用以削减君权、扩大臣属特权,保留不拟交付君主行使的权利。……故考之原意,凡此均不能应用于已公开宣称基于人民权力、由人民的直接代表与公仆执行的宪法之中甚为明显。就严格意义而论,人民不交出任何权利。既然人民保留全部权利,自然无需再宣布保留任何个别权利。”(45) 汉密尔顿的这段话,是用来反对在美国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的,但是,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人民主权国家与在君主制国家宪法中权利列举的显著区别。在实行人民主权的国度,基本权利不能仅仅因为没有在宪法中列举而被否定,宪法对基本权利的列举,不应被视为是对人民的授权,人民的权利也不因宪法的列举而穷尽。否则,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违背。
据此可知,对于那些我国宪法没有明文列举的权利,例如生命权、思想自由权、罢工权、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同样可能是基本权利而受宪法保护。那些以前曾经肯定列举的权利,如1954年宪法规定的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现行宪法中不再规定了,同样也不表明这项权利不再是基本权利了。一项权利是否是基本权利,并不依赖于宪法的明文列举。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也无需等待修宪来实现。通过合理的解释论证并借助一定的实践,这些未列举权利的宪法地位同样应当得到承认。
第二,上述方法的实践表明,认定未列举基本权利的方法并没有唯一的正确解,认定方法的确立应当与本国的社会背景相适应。
严格而言,前述三种认定方法并无优劣之分。本质上,它们都是在文本的确定性之外寻找相对确定性的过程。这种相对确定性的合理与否,取决于是否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达成某种最优,是否与该国的社会背景相适应。例如求诸传统的方法,对于有着悠久保护个人权利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来说,由谙熟司法技艺的法官从历史传统中找寻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相对确定性或许并非难事。但是,对于处于其他社会背景下的国家恐怕并不适用。又如依据“人的尊严”认定未列举基本权利的方法,其在德国之所以获得强大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康德“人的尊严”理论的流行与基本法“人的尊严”条款的确立。如果缺少这样的社会背景,这一方法也很难获得认同。
因此,确立我国的未列举基本权利认定方法,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司法资源和社会背景。对于求诸传统的方法,从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是没有适用环境的。而依据“人的尊严”的认定方法是值得借鉴的。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条款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关怀。(46) 但是,不得不承认,我国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并不具有德国基本法上核心概念的地位,而仅是一项基本权利,它侧重于对公民个人的名誉权的保护。因此,引入这一方法,对中国来说也未必妥当。相对而言,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最为适合我国。一方面,该方法捍卫民主的基本立场与我国宪法长期坚持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理论相契合。民主理念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使这一方法的引入具备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从民主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基本权利,较好地解释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也为完善和发展我国宪法监督制度提供广阔的空间。据此,笔者主张以民主理论为基础,引入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
注释:
①Eugene W.Hickok,ed.,The Bill of Rights:Original Meaning and Current Understanding,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1,p.423.
②汉密尔顿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断言:“人权法案,从目前争论的意义与范围论,列入拟议中的宪法,不仅无此必要,甚至可以造成危害。人权法案条款中包括若干未曾授予政府的权力限制;而正因如此,将为政府要求多于已授权力的借口。”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迅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9~430页。
③第九修正案是特地用来表示,宪法前八条修正案对基本权利的列举不是穷尽的。麦迪逊在提交权利法案的说明中指出:“曾有反对权利法案者指出,对授出权力作特别的例外列举,可能贬损那些没有被列举的权利;暗含的结果可能是,那些没有被列出的权利将会落入概括的国家之手,从而得不到保护。这是我所听到的,反对将权利法案并入宪法的,表面上看来最有说服力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这种结果是可以防范的。”麦迪逊这里所称的防范措施,就是后来的宪法第九修正案。
④参见屠振宇:《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中外法学》2007年第1期。
⑤Willian E.Conkliln,In Defence of Fundamental Rights,Sijthoff & Noordhoff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B.V.,1979,p.13.
⑥Meyer v.Nebraska,262 U.S.390( 1923) .
⑦Meyer v.Nebraska,262 U.S.399-400( 1923) .
⑧Palko v.Connecticut,302 U.S.319( 1937) .
⑨Malinski v.New York,324 U.S.401,413-414( 1945) .
⑩Rochin v.California,342 U.S.165,169( 1952) .
(11)Poe v.Ullman,367 U.S.497( 1961) .
(12)Griswold v.Connecticut,381 U.S.497( 1965) .
(13)Roe v.Wade,410 U.S.113( 1972) .
(14)Bowers v.Hardwick,478 U.S.186( 1986) .
(15)Michael H.v.Gerald D.,491 U.S.110( 1989)
(16)Rebecca L.Brown,Tradition and Insight,( 1993) 103 Yale L.J.,201.
(17)Adam B.Wolf,Fundamentally Flawed:Tradition and Fundamental Rights,( 2002) 57 U.Miami L.Rev.,108.
(18)[美]小詹姆斯·R·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19)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法学家》2004年第4期。
(20)萧淑芬:《论基本权核心概念之规范——一个比较法学的观察》,《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19期。
(21)[美]阿兰·S·罗森鲍姆编:《宪政的哲学之维》,郑戈、刘茂林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2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中译本)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页。
(23)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03页。
(24)德国之所以将“人的尊严”规定在基本法中,除了彰显对于人的尊重与保护之外,另有其历史文化上的背景。具体说来,包括三项主要理由:一是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二是康德的道德哲学;三是对纳粹恐怖统治的排拒。参见黄桂兴:《浅论行政法上的人性尊严理念》,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4~5页。
(25)同前注(23),法治斌、董保城书,第203页。
(26)同前注(20),萧淑芬文。
(27)See Donald P.Kommers,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Germany,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298.
(28)BverfGE 65,1( 1983) .
(29)同上注。
(30)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187页。
(31)同前注⑤,Willian E.Conkliln书,第217~219页。
(32)同上注,第219~220页。
(33)John Hart Ely,Democracy an Distrust.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87.
(34)汪庆华:《对谁的不信任?》,http://www.fatianxia.com/paper-list,asp? id=3861,2007年5月25日访问。
(35)Blanca R.Ruiz,Privacy in Telecommunications:A European and an American Approach,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pp.11-12.
(36)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304 U.S.144( 1938).此案涉及到一项联邦立法,它限制一种混合奶的跨州销售。卡罗琳公司认为这一法律违背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剥夺了公司的商业自由权。如果此案发生在1937年之前,美国联邦政府必败无疑。因为那时的最高法院是保守派的天下,并以司法能动主义的姿态,保护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抵制罗斯福新政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可是现在,在经历罗斯福扩大最高法院计划的威胁和一位保守派大法官(罗伯茨)的及时转向之后,最高法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其主要表现在,彻底放弃并全面否定美国镀金时代形成的司法观念:政府的经济立法必须受制于宪法的严格检验。
(37)《哈佛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前言,第4页。
(38)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39)参见张翔:《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2007年第三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40)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9页。
(41)关于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承认与保护,是否损及法的安定性价值,是否有违法治原则,美国学界曾围绕此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笔者认为,其并不一定损害法的安定性,违反法治原则。具体理由参见前注④,屠振宇文。
(42)林来梵、季彦敏:《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43)同前注(19),韩大元文。
(44)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45)同前注②,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429页。
(46)在1982年宪法制定的过程中,许多同志都指出,“文革”10年,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广大干部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保护,批判会、斗争会、戴高帽和挂牌游街比比皆是,大小字报铺天盖地。有鉴于历史灾难的惨痛教训,我国1982年宪法第一次将人格尊严提高到宪法保护层面,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宪法对人的尊严的保护。参见前注(44),蔡定剑书,第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