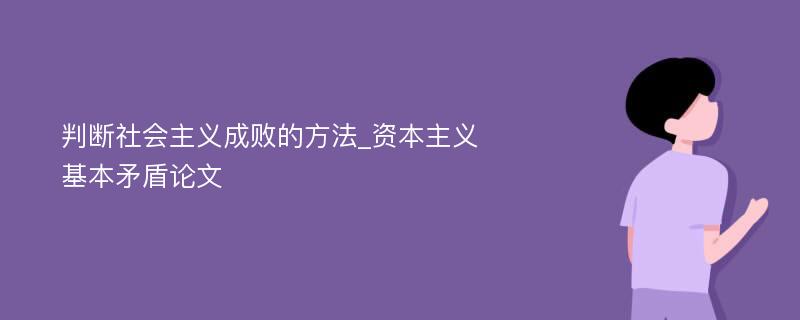
评判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成败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习惯使用的评判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方法是:一种模式论,一条道路论,以胜负论英雄。
所谓一种模式论,就是用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兴衰成败来评判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这种方法已为大多数评论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人所摈弃,但仍为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所使用。他们声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社会主义的衰亡和失败。这种观点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主张一种模式,唯我独社的态度,也为社会主义改革者所抛弃。就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兴衰成败、是非得失而论,关键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有许多论者把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概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或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这是不准确的。历史事实表明,普经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一种是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模式和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还有一种是列宁的利用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模式,不应将这两种模式混为一谈。新经济政策模式是今天改革的现代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雏形和滥觞。单就斯大林模式而论,也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此人们的感情也是复杂的,那些因其受到伤害的人痛恨它、讨厌它;那些因其获得不少既得利益者偏爱它、留恋它;也有的并非出于切身利益,而是一种理性的见解,或肯定它或批判它。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是个严肃而重大的科学问题,可以分四个层次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应该说它与新经济政策模式都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共产党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其次,斯大林模式是否有巨大功绩?应该说它与战时共产主义模式一样,在战胜敌人的武力进攻,捍卫巩固苏维埃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有过辉煌的功绩。再次,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选择斯大林模式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体制模式是否正确?应该说作为体制模式来说,是错误的选择。最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终结,与战时共产主义模式的形成和终结具有重大的不同,甚至性质的差别。
总之,斯大林模式的兴衰成败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相反,社会主义的真正兴旺,有赖于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用新的现代模式取代它。
所谓一条道路论,即主张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历史上已有的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将资本收归国有,建立全盘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之后,又实行改革,探索公有制为主体和市场经济新模式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这条道路的国家,由于其国情的特殊性,其道路肯定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条道路相对于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终将走上社会主义来说,毕竟只是现实中某一类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关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发达国家首先同时胜利论。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已经过时。但他们关于走向社会主义是世界进程,是许多国家同时达到的境界的论点,仍具有真理性,仍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具有指导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论述了暴力革命道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立探索了议会道路的有关理论,由于实践的局限而很不成熟。长期以来,我们把暴力革命道路当作了普遍性的道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也主要是为这一条道路提供理论根据。世界毕竟是纷繁复杂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究竟以什么方式、什么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虽不能说是理论上未开垦的处女地,却可以说是以往经典作家尚未具体论及、非常不成熟的理论领域,但这是现实社会主义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笼而统之地谈论模式和道路的多样化,更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把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普遍化。我们应该从世界各类国家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已经提供的有关理论观点,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探索各类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所谓以胜负论英雄,这虽没有多少理论色彩,但却是人们惯常的思维定式。这里所谓胜负的标准是是否夺取和掌握着政权。正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寇。以这种逻辑来评判社会主义兴衰成败显然具有主观臆断、自我感觉的成分。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政治动乱,精神狂迷,可有多少人欢呼形势一片大好。同理可想,斯大林去世前,有几个人想到传统模式有什么弊端。然而,这毕竟是历史上十分偶然的因素。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应该说有更深层的历史的必然规律。这恰恰应该是我们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往往是我们立论的前提,最多是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论据,但我觉得这是很不够的。为什么说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什么它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理论上有必要刨根问底。在刨根问底的过程中,我们会有许多意外的收获,甚至能够使我们获得解释不同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并不在于对社会主义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而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然结果。所谓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首先是一个纯经济的问题,并且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新社会因素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新社会因素是旧社会母胎中孕育的婴儿,政治斗争、政治手段不过是母亲分娩婴儿的助产婆。这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1〕马克思认为,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因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2 〕。然而工人阶级“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3〕。我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就是资本主义中的新社会因素发展壮大,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新社会因素就是扬弃资本,就是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过程,就是资本不断社会化、革命化的过程。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性内在的深层的根据。资本的本来含义就是指资本家占有的用来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预付的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资本已将资本泛化为通过生产和流通能够带来增加值的价值,已经失去资本本来的含义。舍象了资本归属问题。所谓私人资本是由资本家独自占有不与任何人分享的资本;所谓社会资本,一是指资本让渡给他人,二是指私人资本的联合。资本之所以会被扬弃,在于资本自身固有的矛盾性。任何资本都是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这一双重性质的矛盾统一,任何资本都不可能囿于自给自足的狭隘圈子里,它必须通过交换,把自己的产品形态推向社会,打上社会资本的印记,并获得一个增加值,它才得以实现自己的本质要求,才成其为资本。如果它的产品形态不能推向社会,未能打上社会资本的印记,或者已经卖出,但未获得增加值,它就会粉身碎骨、不复存在。因此,资本本身所固有的私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具有对抗性质,决定着它的生死存亡。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惊险跳跃,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进行的,因此,“市场在这里还具有另外的意义。恰恰是各资本作为单个资本而相互作用,才使它们作为一般资本而确立起来,并使各个资本的表面独立性和独立存在被扬弃”〔4 〕。这使“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5 〕。竞争对在竞争中失败甚至毁灭的资本来说是残酷的、不幸的,然而对生产力的发展却具有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这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是适应的。这时资本的私人性还居于社会的统治的肯定的地位,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阶段。但是,在竞争中,资本为了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必然要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更适销对路的新产品,资本开始自发地寻求自身的联合,个体业主制就发展为合伙业主制,直至发展到股份公司,这使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6〕。 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资本还会进一步发展,不断出现私人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甚至会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结成资本的联合体。它是在资本范围内的自我扬弃。而由工人阶级对资本的剥夺,则是资本的被他扬弃。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本原的典型的表现形式,因为“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最适当形式。自由竞争越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现得越纯粹”〔7〕。 这也是在扬弃资本的形式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每一个资本社会化形式的出现都必然导致生产力和管理的更高程度的社会化。因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 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8〕。“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9〕。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资本……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打碎,……而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本身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继续发挥职能的水平。……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大的规模重复发生,而最终将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10〕。这个一定点,就是指“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11〕。列宁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它是通过资本自我扬弃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国家政权还在资产阶级手中,就是这个过渡已经到了社会主义的入口,如果没有政权性质的转变,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它也是不能最终进入社会主义的,但这一步是很可能在瞬间完成,或是暴力的或是和平的,或是一次性的突变,或是长时间的渐变。各种掌握政权的形式完全取决于不同国家具体的历史条件,而掌握政权则是根本。是否掌握政权可以决定是盲目破坏性的社会化,还是自觉建设性的社会化,这表现为两种性质不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因为社会化这一自然历史过程,起初“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12〕。
因此,可以将向社会主义过渡分为两种性质的社会化道路,一种是盲目破坏性的社会化道路,即社会化过程不是自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行为,而是盲目的被动的不得已的行为,它虽然推进了新社会因素的发展,却破坏着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基础。例如,本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为了应付那场毁灭性的危机,资产阶级政府仓促地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才使资本主义免于灭顶之灾。但新政却破坏了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使国有化、计划化等社会主义因素得以产生发展,这比股份制的社会化程度有了巨大的提高,这显然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另一种则是自觉建设性的社会化道路,即社会化过程是自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主动的建设性的行为过程,由于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自觉地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有计划有成效地剥夺资本,主动自觉地推进社会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由于不同国家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方式不同,有的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有的是议会道路竞选上台,前者往往表现为激进的革命的社会化道路,而后者往往表现为渐进的改良的社会化道路。
在本世纪初,列宁指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认为,这个时代也可表述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终结将是世界主要国家基本上同时进入成熟、合格、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
注释:
〔1〕《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43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0页。
〔4〕〔5〕〔7〕〔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67,160,160,268—269页。
〔6〕《资本论》第3卷第493页。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75,292页。
〔11〕《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59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753—754页。
标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经济论文; 斯大林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