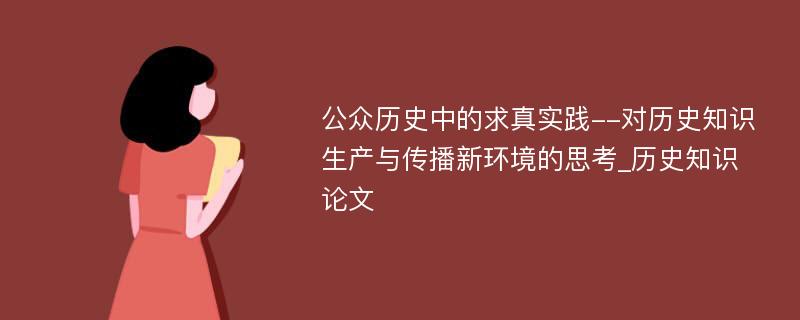
公众的历史求真实践——关于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新环境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公众论文,环境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8-0114-06
在最近的一个关于社会化媒体使用动机的调查中,笔者发现,部分受访者主要是为了获取同“过去的历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等方面有关的信息。①个体借助于新媒体平台,不难同任何其他个体发生联系,现实可以便捷地同过去对接,个体的历史认识来源已不限于学校教育、公开出版物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图景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近年来,不少国外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个现象,并大致形成如下共识:一、历史知识生产主体的扩充。人们已不再将学院的历史研究者与历史专业作家作为历史知识与信息的唯一来源,而是转向公共历史学者及其他所有人。历史知识与历史认识既不是学院史学群所独占,也不是任何其他个体所独有。[1]二、历史传播对象的拓展。无论是学院历史学者,还是学院内外的公共历史学者,他们都更为积极地与更广泛的受众接触,②前者试图兼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2]后者则把培养公众的历史感与公共意识作为历史传播的主要目标。[3]三、历史知识生产过程的合作化,包括个体在某个生产阶段即时的信息接收与整合,以及生产主体间的共时性合作。[4]四、历史知识载体与传播平台的多元化。从电视纪录片、博物馆的口述史视频、[5]历史课堂的数据库,[6]到互联网上各种形式的信息交换,[7]历史正在以多种方式被呈现、消费与吸收。[8]总之,在上述研究中,新媒体、公共史学、公众、合作等关键词的使用已日趋频繁,展示着传播新环境下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图景。
中国的历史学正在经历着新科技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冲击。公共史学概念的初步引入与新媒体平台的出现能否促生一个殊于以往的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环境?一般公众将如何把握历史知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角色?迄今的历史研究鲜少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本文将对此做一尝试。只要坚守求真的旨趣,兼及学无止境的求知本能,问题的回答也许将有助于历史知识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了解历史环境的变化,以便及时地认知并使用新环境所派生的权力,为克服人类历史坐标的迷茫与积累历史真相提供些许助益。
一、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环境
历史是属于人类的共同记忆,在理想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环境中,每个个体都有权利去重构与解释历史事件。历史解释权的开放与平等,似乎早就被西欧“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走马观光式”[9]的著史身份所背书。如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新媒体的存在,以及公共史学的发展,就为这一权利的普及与强化提供了精神动力与工具保障。
(一)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无法对自己做出定义,却有着可被定义的鲜明特征,反权威、反现实主义、反功能主义、多元、变化、解构,等等,都构成它的关键词体系。后现代主义持续地冲击着传统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及方法论,③对人文科学的历史学科而言,它消解了历史叙事与解释主体的权威性。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克利弗德(James Clifford)曾经提醒:对于那些享有话语特权的权威们来说,可以免于争议恐惧地向公众讲述历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0]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历史解释主体的多样性、历史解释权的平等性以及历史视角的多元性,敦促历史学者“以非神秘化的方法对待历史”,[11]让那些被传统历史文本忽视与淡忘的人也能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并让历史研究者彼此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平等叙事。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平等性与多元性,就在新媒体那里找到宿主,被赋予具体的形式。
(二)新媒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让许多人的生活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媒介饱和时代。新近成为热词的社会化媒体借助于多种移动平台,则让人们变成了忙碌的信息接收者、生产者、加工者和传播者。历史上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除却提供了新的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可能性,总能促生新的社会与文化实践。[12]以交互性、融合性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在理论上创造了一个无限自由与开放的话语环境,冲破了原有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垄断模式,使知识重组(knowledge reorganization)[13]成为可能。
对于历史学科而言,历史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可能已经或将要进入社会化生产(social production)[14]的阶段。这一阶段至少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生产主体的泛化与平等化。历史知识生产的专业门槛在互联网空间失去了拦截作用,所有人都可以是生产主体,专业与业余人士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知识生产者与接收者的身份开始融合。[15]其次是历史叙事的碎片化。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难以置信的话语便利,为先前转瞬即逝的个人化口语信息提供了留存的机会,即刻的记录成为人们证明个体存在的新途径。个人知识虽然有可能在与其他知识类别的互动整合中,为某一知识体系的有效扩增做出贡献,[16]但更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失序与终究易逝的话语世界,一个布满碎片化叙事的无意义空间。第三,历史叙事在网络空间里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通过原创、改写、拼接、转帖等手段,推动故事在各个网络平台间的流通,鲜少有人追问其始终。[17]第四,历史知识与信息的自由市场④之形成。在这个市场里,历史读者们可以按需索取,不再受制于权威性的信息传送机制。同时,他们还可以用撷取的知识与信息碎片构建自己的故事,构建他们生存的过去与现在,诚如美国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说,个体头脑时刻发生着信息的聚合(convergence)反应。[18]
(三)公共史学。公共史学于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19]它的诞生是为了解决史学专业人才供过于求的难题,是传统史学高等教育无奈的转轨尝试。[20]美国公共史学理事会将公共史学从业者界定为“历史的学术与非学术实践之间,以及寻求历史认知的不同利益者之间的中介人”,他们包括“博物馆专家、政府和商业史学研究者、历史顾问、档案保管人、教师、文化资源管理者、策展人、影视传媒制作人、政策顾问、口述史家、对公共历史感兴趣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其他许多人”。⑤这一列举是无法终结的,因为公共史学的精神实质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历史研究者。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而言,公共史学教育的确立为历史知识生产主体的队伍壮大、行业性与层次性普及提供了制度性的、可持续的给养,并为历史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提供了原动力。生产主体的拓展也会让历史的研究对象突破学院狭隘与政治功利,使美国“新史学”的奠基者詹姆斯·鲁滨孙(James H.Robinson)的理想变成可能,即把人类思考与行动的所有成果连同痕迹都囊括在历史中。[21]公共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学科特征,客观上迎合了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实践与史学教育的要求。
中国的公共史学专业教育尚未起步,学术界关于公共史学的论述也多限于概念探源与本土化的概念厘清⑥等。目前,公共史学在中国的存在状态主要表现为专业史学工作者以社会公众为主要对象的知识生产与传播,⑦以及非专业的社会公众对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的参与,⑧他们既是历史知识的受众,也是生产者与传播者,有时还会与专业史学工作者进行学术对话。⑨
(四)三者统和。后现代主义、新媒体与公共史学,在历史解释权的平等性与历史知识生产的开放性两个方面统和一体,共同构造了具有文化普适性的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环境。对于历史解释权的平等性,后现代主义为其提供了思想支撑,公共史学为其提供了地位保障,新媒体为权力的施用提供了物质条件。历史知识生产的开放性主要是指三者共同指向的生产主体、研究对象以及生产过程的开放性,它们必然会打破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线性模式,通过主体之间多层次的交互作用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后者的细密程度取决于开放性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新环境难免受制于它所倚生的政治环境。在某种政治背景下,历史的解释权往往被囊括到政治权力中。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公众,官方价值观的拥护者与受益者远比质疑者与反对者更容易获得公开发表与交流的机会。传播个人观点的权利与资源无论是借助于哪一种媒介形式,都无法逃脱美国历史学者林恩·亨特(Lynn Hunt)所揭示的普遍现象:权力掌控着讲故事的活动。[22]由此,生而平等的历史解释权就容易演变成有条件的话语权力。
二、公众的求真实践
新环境的形成过程,也是其中的活动主体不断进行角色调适与能力培养,并参与新环境的创造的过程。作为历史作者与读者的公众面对当下表达便捷的新环境时,或许就像某些一夜骤富者,束手无策,对权利的使用感到迷茫,只好仍旧紧守着并不成功的学校历史教育所传授的史观,或者以为历史就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仅仅把历史文本当作满足个人想象或释放政治权利受限之苦闷的工具,领略网络图文的便捷,展示个人的存在价值。我们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知识极度缺乏⑩的时代,对历史真相的添乱与历史解释权的滥用就只能加重这种贫乏。不过,还应当注意到,拥有历史解释权却并不必然地赋予个体以相应的能力,历史知识生产过程的易进易出,也不能让历史知识生产个体获得历史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豁免权,他们重构与解释历史的有效性,只能来自对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追求。
无论以哪一种角色参与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过程,公众都需要建立对真实的敬畏与求索,真实与求真乃历史与史学的生命。后现代史学虽然质疑历史的真实性,却无法真正撇弃它。前者以反真实诉求的姿态获得史学新霸主的地位,但它所宣称的“历史之死”或“真实之死”,也为自己预备了坟地。就历史知识生产的个体而言,无论何时,历史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了解自己、同胞以及人类的过去与现在,问题与希望。(11)如果个体对自己生于其中的历史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则只能永远处于精神的童年期,因为历史存在的韧性早已建构了不同层次与范围的集体记忆,使个体有可能将自己置于其中的某一历史坐标,对自身与社会做出定义,获得并不虚幻的个人身份或集体身份。(12)可以断言,无论带着何种动机走进历史,个体都无法舍弃对真实的追求,这既与人类自我意识的原始冲动有关,也来自于我们无法与之分割的过去所赐予的使命——我们常说的历史的使命,历史可以延续,却无法复制,更不容曲解。
(一)作为历史读者的公众。新环境对于历史读者或消费者而言,是一种具体的矛盾构成。一方面,这一环境使个体头脑中的聚合反应所需材料的来源变得更加丰富。个体对过去世界的了解,很少能从个人实践中直接获得,[23]而主要是利用他人所提供的素材(包括一手的事实与二手的分析),来进行初步建构与反复重构。对某个历史事件的局外人来说,叙事与解释的分歧愈多,[24]他所依赖的他人群体就愈加分散与多元,用于构建记忆与身份的材料也就愈加充实与多样。另一方面,这一环境充斥着信息芜杂、良莠并存的子空间,个体若要接近真实,还须具备读史的基本能力,即明辨真假的能力。[25]正是具此能力的读者,无时不在给历史作者提供不懈求真的动力和压力,最终有助于净化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环境,抵制个体的记忆被操纵、行动力被利用的厄运。
辨识真假是一个需要调动个人记忆、智识、经验与态度的复杂过程,对于缺乏历史专业训练、无力做史料考究的公众来说,虽非易事,却仍可以做两项基本的认知准备。首先,历史的真实既是空间维度上的交互性存在(指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研究主体之间以及文本之间的交互作用等),也是时间维度上的累积性存在(指借助新出现的材料或解释,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倘若历史读者认同这样的真实性,或许不难培养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会期望在单一历史文本中还原真实,重蹈历史决定论的霸气。历史本来就是无法终结的论争,[26]任何一个文本都不具有“通往真实”的特权;[27]还须尊重每一个立于史料之基的文本,尽可能摒弃偏见与预设,尽力在文本的对比中,觅获或重构关于过去的事实。其次,在历史知识传播的新环境中,读者有机会接触到来自不同话语权力阶层的叙事者,例如官方著史者、事件亲历者、专业史学者与草根叙事者等。他们各自拥有的权力与社会资源决定了叙事的意图与模式,或为创造集体记忆与身份,或为个人行动建立合法性与合理性,或为纯粹的真实性诉求,或为颠覆与重构,等等。历史受制于这些复杂的权力关系,可能呈现出变幻莫测、亦真亦假的形态,个体若能甄别不同叙事者的立场与意图,就不难形成关于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判断。
(二)作为历史作者的公众。新环境所派生的历史解释权的平等性与开放性,虽然使历史知识生产的主体队伍不断扩充,但在平等权利的使用过程中,主体实践能力的参差不齐也逐渐显现。在网络话语空间里,不难发现个人臆断对历史事实的抗拒,情绪化思考对理性诠释的侮慢,线性因果逻辑对历史复杂性的漠视,以及主流政治史观对求真诉求的挤压等,种种超出事实层面的冲突与对垒,容易让人联想到19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的忧虑:缺乏专业训练的公共史学者能否完成历史之客观真实的任务?[28]这应该是每一个获得并使用着历史解释权的个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为历史之作者或知识生产者的公众,首先需要建立对历史解释权的正确认知。历史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中介,并非个体宣泄情绪与谋取利益的工具。使用历史解释权的公众,必须珍视、尊重、善用这一权利,他们所担负的使命,与专业的历史学者并无二致,即要尽可能地“为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同时代人的记忆做出贡献”。[29]
当新媒体赋予所有人以历史解释权时,历史创造者与书写者的身份正在形成最大程度的融合,个体自行记录与传播个人的行动与思想轨迹就不难免于被淹没、利用、篡改、异化及阉割的命运,历史也将逐步接近“大众的灵魂与事件”,[30]专业的历史学者无法单枪匹马地完成这样的任务,公众能够对历史之真实做出独特的贡献。公众的有效参与将使历史知识生产的网络结构更为细密,真正变成一块无接缝的纺织品,足以抵御“意识形态、价值观、理论和某种目的的擅自裁断”。[31]公众还可以贡献的,便是记录并反思个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认知史。个体对过去的认知会随着智识的成熟、经验的累积、情感的转移以及社会权力系统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虽然这一渐进过程并不必然走向真实。个体的认知史可以提供专业历史学者无暇挖掘的重要信息,如在个体生命单位内的某一个时空背景下,影响乃至控制其记忆的权威叙事,社会知识信息的控制群体、分布状态以及微妙走向,等等。
三、结论
历史学的工作“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32]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存在与赓续。人类本应存在于过去的真实中,只因完整的真实不可求,就只能存在于被重构的历史中。于是,谁掌握了重构历史的权力,谁就操控了人类的记忆与存在。对于公众而言,只有拥有了历史解释权,才可能捍卫真实的记忆,免于被操纵的命运。
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环境,以新媒体、后现代主义以及公共史学为依托,赋予公众个体以开放、平等的历史解释权,使历史知识的生产过程从封闭的线性结构演变成开放的网络结构。在新的环境中,使用历史解释权的公众需要坚守对真实的敬畏与追求。惟有守住求真的理念,沿着求真的路径,他们才能获得并不虚妄的个人与集体身份,以及现实存在感。对于历史之读者的公众,求真实践要求他们既对历史的累积性真实抱持宽容的心态,又对历史叙事主体的权力归属、叙事意图保持相应的警惕,提炼一定的辨识能力。对于历史之作者的公众,求真实践要求他们尊重并善用历史解释权,贡献个人生活与思考的痕迹。二者的共同努力将使历史知识生产的网络结构越来越细密,不难遏制多方话语对历史的荼毒。一旦公众拥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历史,就不难增添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与尊严。
注释:
①2012年5月,笔者在所教授的研究方法课上,要求学生做关于社会化媒体使用动机的深度访谈调查。该调查以方便抽样的方法确定受访者,以面对面访谈或网络访谈的方式进行,共得到120份访问记录。
②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维布尔(Robert Weible)认为,历史学者应该突破各种障碍,与公众做密切接触,历史学者与公众的关系,就像导盲犬与盲者的关系,受过专业训练的前者能够引领后者走向更具希望的未来。参见Robert Weible,“The Blind Man and His Dog:The Public and Its Historians”,The Public Historian,Vol.28,No.4,(Autumn 2006).
③台湾历史学家黄进兴认为:“无论后现代是否真如某些学者所预测的正趋于尾声,但后现代史学却方兴未艾,在时间落差上,中国史学尤为如此。”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09页。
④此处使用的“自由市场”概念之内涵同于17世纪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提出的“自由市场”概念。参见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⑤这一概念界定引自美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的官方网站:http://ncph.org/cms/whatis-public-history/.
⑥相关文献包括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黄红霞、陈新:《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学术交流》2007年第10期;陈新:《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姜萌:《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史学》,《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等等。
⑦例如历史讲堂类电视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面向公众的学术性、思想性网站(如爱思想网)、专业史学者开设的博客、微博,及撰写的通俗历史读物等。
⑧有学者认为中国公共史学包括口述史学、应用史学、影视史学及历史通俗读物四部分,其分类标准较为模糊。参见姜萌:《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⑨例如,历史学者谢泳曾发表关于沈崇事件的演讲,提出一些与主流叙事不同的观点,引来许多非专业历史研究者(包括当年反美学生运动的亲历者或观察者,以及某些文化工作者)在公开出版物上批驳谢泳的观点。
⑩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评价他生活的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参见钱穆:《文化与教育》,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87页。不幸的是,我们仍旧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11)詹姆斯·鲁滨孙认为:“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未切实去做的事,就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和同胞以及人类的问题同希望,这就是历史的最大效用。”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2)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认为,记忆是构成个人或集体身份的基本要素,寻求身份也是社会及个体的一项基本活动。参见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