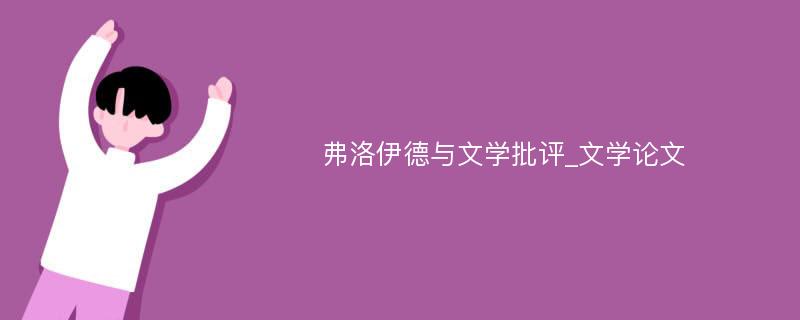
弗洛伊德与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洛伊德论文,文学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16(2007)04—0076—04
精神分析又名心理分析,最初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属医学范畴,弗洛伊德率先用它来治疗神经质病及并发的器质性病症。其运用治疗的基本原理如霍尔所总结的:“用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来达到把无意识的东西变成有意识的东西的目的。这个目的是通过削弱足以阻碍心理的内容进入醒觉状态的阻力来完成的。当无意识的东西成为有意识的时候,患者就可以通过自我的理性过程学习如何解决他的问题。”[1]235—236 作为一种学说,精神分析在文学、美学、宗教史、民俗学乃至教育等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弗洛伊德率先将精神分析学应用到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他的著作,包括病例分析、叙述方式都充满了艺术的吸引力。“自《梦的解析》一书问世之后开始,精神分析就再也不是纯粹属于医学的东西了。”[2]68
一、文学与梦
围绕“梦”的理论,弗洛伊德至少在文学艺术发生的一般心理根源和意象表现的心理依据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分析艺术家性格中的心理结构,即所谓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包括潜意识情结),并研究艺术的象征意义所具有的心理基础。”[1]238 苏联《简明百科全书》中对弗洛伊德的文艺研究的这段概括是中肯的。
第一,创作家与白日梦。
1900年,《梦的解析》发表,其基本论断是:“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3]74 1908年发表的《创作家与白日梦》里,弗洛伊德研究了“素材”加工与创作家心理根源的关系,认为:“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幼年时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替代物。”[1]143 在现实的压力下,创作家以“幻想”来“替代”童年期的“游戏”,都是认真的,不过儿童的游戏是自以为正当而不加掩饰的,成人的文学创作却是羞于公开的“幻想”。这种幻想具有和夜晚的“梦”相当的特性:是被潜抑的愿望的满足。
“成梦”的因素包括白天的“关心”的留续和愿望,后者是前者“入梦”动机势力。而“作品本身包含两种成份:最近诱发性的事件和旧事的回忆”[1]142,其自然的形式也和梦一样是“受抑制的愿望”的以“歪曲的形式”表现[1]140。
弗洛伊德的“潜抑”理论,和他的“泛性论”关联。他的学说中的“性”,如他所说,是一个极宽泛也极狭隘的范畴;女子的“潜抑”,和“恋爱”相关;男子的“潜抑”,有时直接表现为“野心”,而最终也和“恋爱”相关,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性”的“关系”在这些人的意识中,在曾经、现在的“幻想”中都是禁忌,和道德、伦理价值观相冲突,在对抗中,后者占了上风,前者便被压抑到潜意识中,但它总要找到发泄的出路。如《少女杜拉的故事》中的杜拉,她较强的道德意识使她不能接受有妇之夫K先生的求爱,便唤醒从前对父亲的爱来抵抗当下的爱;然而爱父亲在从前便是她自己的意识不能允许的,于是在歇斯底里症里寻找出路。歇斯底里症也和性别气质相关,在青春期以前表现出男孩子气概的少女,在青春期易患歇斯底里,女性化的一面突出。所有这些,又可以通过那些奇怪的梦得到解释。
创作家自己的幻想,如何能被这么多其它人乐意接受呢?弗洛伊德说别人直接告诉我们自己的幻想,我们并不感兴趣,但对其作品却不然。他将之初步归因于形式美和“白日梦”的“转移”:“最根本的诗歌艺术就是用一种技巧来克服我们心中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无疑与每一个自我和许多其它自我之间的屏障相关联。……两种方法。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来减弱他利己主义的白日梦的性质,并且在表达他的幻想时提供我们以纯粹形式的、也就是美的享受或乐趣,……这种效果有不小的一部分是由于作家使我们能从作品中享受我们自己的白日梦,而用不着自我责备或害羞。”[1]144
释梦是精神分析的重要手段,也被弗洛伊德视为文学艺术分析的一种方式:“拟造出来的梦也可以像真梦那样加以分析,也就是说,我们所熟知的‘造梦的机制’(mechanism in the‘dream work’)也可见诸于富于想象的写作过程之中。”[2]70—71 具体操作是:“找寻艺术家个人生活的印象,他的机遇经验,以及他的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导出该作者在创造时所有的思维和动机——换句话说,即找出他与全人类共有的一部分来。”[2]70 在弗洛伊德的提示下,琼斯和兰克相继对《哈姆雷特》作了相关研究。
第二,文学的形式与梦的表达方式。
梦是愿望的“歪曲”表现,它经过重重检查采取以部分代全体、暗喻、象征、意象等方式出现。[4]128—129 在《精神分析引论新讲》里,弗洛伊德再次阐述了梦的呈现形式:“观念在梦里转化为视觉意象,也就是说,内隐的梦的思想变得生动和形象化了。”[5]118 在梦中,我们既是创构者,又是接受者,这显示人们倾向于信息的原始方式的传达与接受。创作家要转移“白日梦”到读者,就不能不考虑白日梦的呈现方式,形象化,意象化。
以部分代全体、暗喻和象征,其实都可归入“意象”的形成手段中。“意象”化是古今中外许多文论者注意到的文学的重要实现方式。弗洛伊德并没有将梦的这种工作方式与文学形式直接关联,但给了我们重要启示。他通过梦的解析提供了这种方式存在的深层心理基础,也从文学接受的心理要求揭示了这种文学形态的本然性。
精神分析实际是对不满于现实的灵魂的解剖,通常由“不”这种“抵制”而到达“是”之本源,途径:分析病人的自由“联想”、解析“梦”;在对“梦”的具体解析方式上,有时采用“语词分析”。比如在《少女杜拉的故事》中,弗洛伊德都用了具体字的解析来说明某些心理及行为的关联,如“尿”、“水”、“火”的微妙甚至“反向”关联。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弗洛伊德的这种分析法也注定了他与文学批评的关联。
弗洛伊德与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茨威格等著名作家有直接往来。1928年,他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以《卡拉马卓夫兄弟》为例讨论“俄狄浦斯情结”在文学上的应用。二十世纪初西方形成了“文艺评论界的精神分析流派”,主要以追溯童年期和家庭影响的方式挖掘人物心理。
二、文学的背后,“自我”在挣扎
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如此轰动,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医疗方法,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弗洛伊德广泛的兴趣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弗洛伊德对心理本源的兴趣远超出了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他想揭示的是文学艺术背后的东西。在弗洛伊德看来,文艺创作源于“愿望未满足”,未满足的原因又在于“现实”:“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1]138“现实”又意味着什么?控制与压力。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里指出:“神经症的利己本质就是逃离不满意的现实状况,进入一个相对愉快的幻想世界——这是它的基本目的。然而,逃离现实也正意味着逃离社会,这是因为神经症所要逃避的现实世界,是由人类社会和它所有的习俗所控制着。”[6]79 这样,文学便成为社会对个体之压力的表征,是个体与群体力量相对抗的产物,文学本身由此便具有了社会性与政治性。
文学的背后是潜意识,是“幻想”,是“对抗”,结果是“现实”压倒了“幻想”。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存在于创作者内心中的政治,它源于“自我”“一仆侍三主”的处境。作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便在于“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把握住现实”[2]70。弗洛伊德的文学研究,一头是不知何去何从的“力比多”,一头是文学这种人类精神的崇高现实。与其说他是在进行文学批评,不如说是在借文学而进行文化批评;而文化批评,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又更偏向于政治批判。
但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也坚持,潜意识里是“性”要求满足的欲望,《少女杜拉的故事》里说,“性是开启心理症难题之门的锁匙”[7]125。《图腾与禁忌》中借助了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和文学的资料,主要以与神经症相比较的方式来完成对图腾与禁忌的分析,在指出神经症的“社会形态”性质后,仍将根源归于“性”:“神经症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它们以隐喻的方式努力去显现出社会集体力量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对神经症的本能冲动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将发现决定它们的因素是与性有关。相对社会习俗的形成是在社会的本能基础上产生的,而社会本能又是从利己主义因素的与性欲因素的组合中派生出来的。性的需要并不能像自我保存需要那样能够使人们结合起来。性的满足仅仅是属于每一个人单独的事情。”[6]78 那么,社会又被排除了文学根本动因之外,只是创作者“个体”有未能发泄的性本能力量。医生与科学家的气质决定了他更看重文学作品之外的“事实”和“个体”。所以,与其说弗洛伊德是在研究“文学”,不如说他是在寻求“人”康复的途径。
弗洛姆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中说精神分析学在弗洛伊德后失去批判性而成为人顺应社会“合理化”、“同一化”要求的手段。歇斯底里症,后来不再是常见病;而精神分析成为财富拥有者的消遣工具。显然,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直接目的——让病人复归“真实世界”——来看,这种结果是难以避免的。
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指出了“潜抑”机制产生的家庭和社会因素,指出了创作对现实的失望这一点。弗洛伊德并不倾向于将文学与狭义的政治关联,但又总是处于接触的边缘。女性主义挑破了这层纸,它给后来的女性主义以直接的理论“援助”。《精神分析引论新讲》里有专节讲述“女性气质的形成”,——“社会”的形成;将“性压抑”扩展到“社会压抑”也是自然的(《苦闷的象征》),鲁迅虽然不时批判弗洛伊德的具体学说,却对厨川白村学说大加宣讲。
弗洛伊德也直接关注“政治”,他研究过群体心理,他立场鲜明地批判了宗教迷信,也曾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论提出了质疑。但也许是他精神治疗医生的身份,使得他过分看重个体“复归真实世界”的重要性,所以,在人类进化问题上,弗洛伊德的研究结果很容易导致悲观。马克思认为人必然经过从自然界“独立”或“脱离”出来这样一个“进化”过程——他称之为“异化”——并认为人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便是走向“再整合”和“与自我统一”的过程。弗洛伊德也认为从自然与社会外界独立出来是人走向文明的必然过程,但他在对个体幸福与文明关系的思考中显示了对个体走向的困惑。
三、通往崇高的性
伊格尔顿探讨文学批评原则问题时曾说:“文学作品不是神秘的灵感的产物,也不是简单地按照作者的心理状态就能说明的。他们是知觉的形式,是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他们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或意识形态有关。而那种意识形态又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它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8]9“科学的批评应该寻找出是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8]23
“性”可以反映意识形态,性也可以仅仅是“性”本身。弗洛伊德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虽然也提出了很容易导向政治分析的“压抑”;偏偏又在对宗教与禁忌的追根溯源中消弭了它的时代色彩,它成了无往而不在的一种本能动力,而且是文学创作最深远的一种动力。不仅如此,弗洛伊德还通过研究说明“弑父”有理,似乎更是“不道德”。
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应该也是弗洛伊德承认的。只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去解释这些行为与矛盾成为分歧的关键,“意识”与“潜意识”谁在起决定作用?也许,我们宁愿相信:性与社会,性在中途,而且是次要因素。
但实际上,弗洛伊德以科学的态度找到具“病源作用”的事件和意识,其中并不带有怂恿的意味,反而是为了帮助病人复归“真实世界”作出健康而成熟的选择。从《少女杜拉的故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的分析来看,弗洛伊德对道德高尚的人们确实持尊敬和赞赏的态度:因为对本能欲望强有力的克制而道德高尚的人们,哪怕是得了神经质病,也还是不减其高尚道德和美好人格。而弗洛伊德实际上以他本源性的研究建设着“性道德”,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性的困惑而言,它具有性知识的普及以及性解放的宣扬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文学创作存在转移性冲动的潜意识甚至意识也是难以一概否定的。
弗洛伊德坚持“弑父”这样的宗教及道德心理根源的目的并不在于鼓励“弑父”,而是进一步指出道德、伦理及习俗的存在是维持“弑父”之后的共同利益的必要的妥协。精神分析学的“现实原则”可以这样理解:“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本能冲动,适应现实生活的要求,否则,不但不能得到快乐,反而会遭受痛苦。这就是现实原则的意义。”[1]246 尽管弗洛伊德在《文明与缺憾》中在“原始”与“文明”之间尚存在彷徨,而就其病例分析来看,“文明”显然是人的必然方向。通常,人们把弗洛伊德与“性”相提并论,而且往往反感地认定他以“性”亵渎了文艺的崇高与现实中的高尚,却不能肯定他为“性”发现了一个通往“崇高”的出路。事实是,弗洛伊德既肯定了性动力的存在,也肯定了文学艺术的崇高,他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并且以他科学而且艺术的研究与分析为性照亮了这条通往崇高的路,这才是更为重要的。性的出路有很多:直接宣泄,过度压抑而致病,暗自升华而为文学艺术创造等。性可以导向崇高,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发现。
朱光潜在对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作了历史的考察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给我们更深广的人生关照和了解,所以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帮助我们建设更完善的道德的基础。”[9]119 文学的产生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单否定对社会关注的需要,反映生命的现实痛苦及反抗“不平等”与“压迫”永远有其从内到外的理直气壮。人要求真,更要追求善与美,否则个体间的尊重、关心永远无法很好地实现,“公众原则”的探求永远是重要的。外在“行为”永远是不可忽略的。
另外,就《创作家与白日梦》的遗留问题来看:“白日梦”何以被广泛接受?弗洛伊德的考虑关乎文艺的审美特性。而我们知道审美心理是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文艺动人的根源便在于“向美”、“向理想”的勇气。曾永成在论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处理时,认为“追求自由,应该说是政治和文艺的共同主题”[10]10;同时标举“情致”为艺术掌握方式的特性,肯定情致一词整合了“人的意识、心理和生理三个层次”[10]196,某种程度上容纳了弗洛伊德。
作为一门科学,弗洛伊德自是有理,但他也作过说明,精神分析学只能作为一门“辅助”科学,不能承担全部责任,我们还是得面对和解决现实与意识中的问题。中国人向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传统,当文学与政治直接关联时,在中国曾有“暴露”与“歌颂”这种看似徒劳无益的争辩,也可视为一定时代的情势所趋。文学是社会中人的创构,不能无所担负,尽管这种担负是与政治担负不同方面和不同形式的担负。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说:“这门科学的本身很少能独立担负起处理某一问题的全责,但他似乎注定要对许多的智识领域提供最有价值的援助。”[2]76
[收稿日期]2007—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