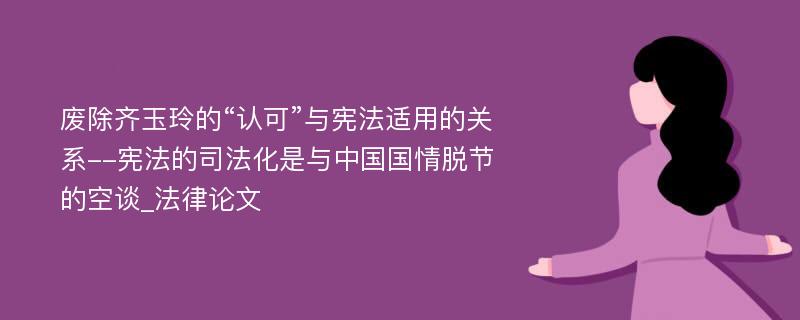
废止齐玉苓案“批复”与宪法适用之关联——宪法司法化是脱离中国国情的空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空谈论文,中国国情论文,司法论文,齐玉苓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并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个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的批复。齐玉苓案“批复”在法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这种讨论延绵至今。有人认为,齐玉苓案“批复的出台,开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援用宪法进行保护的先例,也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①还有人将齐玉苓案“批复”比喻为中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惊呼该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②
笔者认为,齐玉苓案“批复”对于我国的宪政建设而言,固然有其积极意义。法院在审理民事、刑事或经济等案件时引用宪法原则,强调宪法的基本原则及指导意义,对于维护及宣扬宪法在我国法制体系的最高法律地位,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作用显然是正面的。如果说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此引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就是宪法司法化,笔者认为其在我国学术界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但是,如果将宪法司法化定义为与美国司法审查类似的违宪审查制度,而将齐玉苓案看作是类似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里程碑事件,笔者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那是盲人摸象似的主观臆断、一厢情愿。
司法审查起源于美国,指的是法院有权力废除违反宪法的立法机关的法律和行政机关的命令或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是西方现代政府分权理论的典型体现。美国宪法没有直接提到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但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根源于普通法系的判例法及衡平法的久远传统。所谓判例法,简单地说是指法官通过判决所揭示的法律原则,是法官创造的法。所谓衡平法,指的是公平的法。很多学者津津乐道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并不是美国法院宣布违宪的法律无效的第一起案例。在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之前,美国就有好几个州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宣布过违反州宪法的一些法律无效。③17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司法法。司法法明确规定联邦法院有权审查州议会制定的法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796年审理希尔顿诉弗吉利亚州一案时就第一次行使了司法法赋予的这种权力。
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第一次宣布美国国会制定的一项法律违宪。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判决意见书中详细阐释了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推翻违宪法律的正当理由。马歇尔指出:“当然,所有参入制定宪法的人都认为宪法是国家的基本的、最高的法律。因此,这种政府制度的所有理论必然是,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如果违宪将无效。此理论……被本法院认定是我们社会的根本原则之一。”④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所确立的违宪审查原则在美国经历了两百多年依然巍然屹立。联邦最高法院对国会制定的法律或总统颁行的行政命令或规则有权宣布其违宪而予以废止。这种司法审查权构成了美国宪政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
回顾美国司法审查的历史,联邦最高法院在过去两百多年总共废除了150件国会的法律、1000多件州的法律。被废止的法律中的大部分涉及到宪法所保障的人权或公民权,尤其是通过废止违宪的法律保护了以黑人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的权利,很大程度上限制或禁止了联邦或州政府的侵权行为。⑤
其实,在美国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支持和反对两派意见。反对司法审查制度的学者认为,最高法院撤销联邦或州的法律及行政法令的行为在普通法或民法体系中没有对应的权力,在宪法中也没有条文根据。他们认为,美国法律渊源于殖民地时代从英国继承的普通法传统。而英国1215年颁行的大宪章将司法审查的权力赋予给了人民,而不是赋予给了法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杰尔密·沃尔顿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长达60多页的论文,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沃尔顿教授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确认,司法审查制度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国会更能保护人民的权力。他认为司法审查制度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是不合法的,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司法审查作为最后仲裁者的模式也是不恰当的。⑥
但是,支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人认为,虽然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但是宪法第6条隐含了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联邦宪法第6条规定:“本宪法和根据本宪法所制定的联邦法律……是国家的最高法律。”⑦按此宪法原则来推理,如果国会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宪法原则,就不能称其为美国的最高法律。联邦宪法第6条还规定:“所有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并且任何一州的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不得与宪法相抵触。”⑧支持司法审查制度的学者认为,联邦宪法第6条明确指出了各州的宪法或法律如果违背宪法或联邦法律是无效的,而宪法的规定隐含着法官是判断州法违宪的最适当的机构;这种司法审查权的延伸就应该包括对违宪的联邦法律进行审查。耶鲁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亚历山大·比克尔在他那本被普遍视为美国当代宪法学里程碑的著作《危险最少的部门》一书中说道:“美国政府最不危险的部门却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见到的最有权势的法院。”⑨比克尔教授认为最高法院在国家的重大争议中能发挥政治平衡的作用,与联邦政府的其他部门开展对话。比克尔教授不将法院看作是一个消极的实体,而是认为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小心地导向公众意见。
显而易见,美国式司法审查制度的前提是权力分立。美国是三权分立原则实行最彻底的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在美国,由9位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与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以及由参议院、众议院总共535位议员所组成的国会在法律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总统和国会三足鼎立,相互制衡。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详细阐明了司法审查的理念。他认为司法审查是宪政制度最主要的支柱之一。汉密尔顿指出:“任何认真观察权力不同部门的人都会注意到,在彼此区分的政府部门中间,司法部门由于其功能的特性,使其成为对宪法政治权利最没有危险的部门……司法部门……对宝剑或钱袋……没有影响力,对社会的势力或财富也没有指导作用,而且无法对任何事情主动采取行动。司法部门可以说既没有武力也没有意志,有的只是裁决。”⑩汉密尔顿通过将无钱无武力的司法部门和拥有武力的行政部门以及拥有拨款权的立法部门进行比较分析,因而坚定地支持既没有武力也没有金钱的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以保障三权分立的真正实现。可以说,美国如果没有司法审查制度,其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是不可能存活发展至今的。同样可以说,美国如果没有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就不会出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那种里程碑的案件,司法审查制度也就不会产生和发展了。
我国的情况与美国完全不同。执政党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的。我国现行《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2条还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宪法及法律的制定、修订,负责任命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内的国家领导人,负责设置国家机构等。
从我国的国家体制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之一。这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地位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最高法院与总统和国会三足鼎立、地位平等。而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如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都要受全国人大的领导和指导。因此,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对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则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平起平坐,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结构显然是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本身就是违宪的。因此,在我国目前的宪法体制下,美国式的宪法司法化没有任何法理根据。如果试图用一两个案例来突破所谓的传统观念,树立起最高人民法院违宪审查的先例,那几乎等于是做儿戏,一定是徒劳无功的。
再则,司法审查制度之所以能在美国得以实现,与联邦法院法官一言九鼎、终身任职的崇高法律地位密切相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及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都是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的,并且一经任命便终身任职。美国各级联邦法院的法官,只要未经国会弹劾或法官主动要求退休或辞职,可以任职终身。美国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忠于职守,应继续任职,并按期接受奉给作为其服务之报酬,在其继续任职期间,该项奉给不得削减。”(11)
当中国废止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确定了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及退休制并且这些制度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有那么一群被称为联邦法院法官的人,他们终身任职,除非他们之中有人因犯罪而被国会弹劾或因年高体弱自己主动要求退休外,可以老死在任上。(12)在美国总有这样的联邦法院法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联邦法院法官的岗位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联邦法院的法官能终身任职,独立行使审判权,而总统、国会、上级法院或者州市的地方权势都无权撤销他们的职务,无法干预他们的审判活动时,司法审查制度或宪法司法化才有可能实现。
比较而言,中国法官的法律及政治地位和美国法官的法律及政治地位是很不相同的。中国法官制度长期以来沿行行政管理模式,法院领导及法官的级别长期套用行政干部级别。中国法官地位不独立,没有终身任职或长期任职的法律保障,因此法官很难做到独立行使审判权。中国各级法院的法官之上都有不同级别的领导制约着。法官们经常必须按照法院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等领导的意图或决定办案。法官们如果没有真正的独立审判权,没有终身或长期任职的法律保障,也就必然缺乏一言九鼎的权威来建立及推行所谓宪法司法化的机制了。
还有,美国式司法审查制度或宪法司法化的精髓在于法官“法从口出”。当中国法学界大力倡导法治,反对人治,学者们狠批“法从口出”、“以言代法”等封建专制余毒之时,同样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样是这样一批被称为联邦法院法官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人,他们的“言”、“说话”或判决意见却经常成为法律。他们的判决意见甚至可以撤销总统的行政命令或国会制定的法律。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普通法的基本形式是判例法,其基本原则是“遵从前例”,即法官在审判中应该遵守以前同类案件中法官判决所确立的规则,但是“遵从前例”并不等于对判例的盲目照搬。法院及法官在一系列相似案件判决中“遵从先例”,灵活地运用、完善、发展普通法原则。法官甚至可以通过判决意见推翻先前的判例,以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在美国,每当联邦最高法院对重要案件作出判决后,几乎所有的重要报刊都会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发布法院的判决意见,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就是法律。正是因为美国法官有造法权,他们可以基于普通法原理以及个人的良知意愿作出具有立法意义的判决。最高法院的判决一经公布,经常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相关领域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不过,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只能在审理具体案件时行使司法审查权。他们从不对关于政府行为是否违宪的假设性或政治性问题发表意见,也不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否违宪提供质询意见。
和美国相比较,我国的法院和法官是没有“法从口出”此种造法的权力的。中国法官的个人力量历来很薄弱,法官体制等级森严,各级法院及法官依法依例都没有造法的权力。中国的法院或法官在遇到新情况或新的法律问题时通常得报上级法院或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法官没有多少自由裁量权。如果我国法院及法官没有美国法官那样的造法权或自由裁量权,我国的学者们怎么能够企望他们去开拓什么宪法司法化或司法审查的先河呢?
其实,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只是宪法实施保障制度或宪法监督制度的一种。宪法监督体制即使在西方国家那里,其制度和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的。所谓大陆法系的国家通常采用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的体制。只有普通法系的国家才采用由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适用宪法的做法。普通法系国家也只有美国的法院及法官才真正拥有不受立法部门或行政部门干预的司法审查权,这是由于美国彻底实行三权分立的结果。
童之伟教授认为,如果在中国实行所谓的宪法司法化,将“意味着主张将现在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宪法监督实施权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宪法解释权转移到各级法院手中,意味着可以对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意味着最高国家审判机关取得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相同或平等的宪法地位。一句话,意味着根本改变我国的政权组织体制。”(13)笔者完全同意这个意见。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第62条、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违宪及违法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我国宪法的这些规定非常明确地指明我国违宪审查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不仅无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而且对比法律效力低的行政法规也不能直接宣布其与宪法相抵触而无效。(14)最高人民法院甚至无权解释法律,(15)只能作为众多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16)
诚然,我国至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机构。如何建立起这样一个机构,该机构的名称、职能及活动方式是什么,学者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宪法体制下,任何宪法监督机构都只可能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建立或由其授权而建立。无论该机构将来被称为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或宪法监督委员会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性质。这就是目前我国的宪法体制现状。这也就是中国的国情。因此,建立或完善宪法监督体制或违宪审查制度,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来思考和设计。企图照搬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推动宪法司法化,目前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死路。更加实际的做法应该是集中精力和资源研究如何尽快通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建立起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或宪法监督委员会,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赋予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或宪法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或宪法监督委员会的职权或活动范围应该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法律予以界定。
近来,学者们围绕法院可否援引和直接依据宪法对具体争议进行裁判争论不休,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可以援引宪法说理,但不可以也不可能直接依据宪法裁判具体争议。(17)韩大元教授指出:“宪法是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的最高依据,但具体的审判活动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来调整,无需直接适用宪法,更不能直接以宪法为依据作出判决。”(18)另一种意见认为,法院有权援引和适用宪法,法官可以在不享有违宪审查权的情况下适用宪法,并认为这就是宪法司法化。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认为,一般法院在其审判工作中适用宪法的主要方式是“合宪法律解释”,他强调“这并不涉及违宪审查权的行使”。(19)
笔者基于前述理由,赞成第一种意见,不同意第二种意见。尽管主张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适用宪法的学者认为这种适用并不等同于违宪审查,但是他们始终无法解释清楚在我国目前的宪法架构下,法院有何法理依据能够在审理具体案件时适用宪法。陈弘毅教授认为,宪法适用意味着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进行“合宪法律解释”,也就是“法院在进行这种用以理解或解析法律规范的思考推理活动时,在有必要时考虑宪法的有关条文,把宪法观点应用到理解或解析法律规范的工作,从而把有关法律规范理解或解析为符合宪法有关条文的、有助于实现宪法有关条文的宗旨的规范。”(20)
陈教授关于“合宪法律解释”的阐释清晰透彻,但是其忽略了在我国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各级人民法院是没有进行“合宪法律解释”的职权的。依照我国宪法及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唯一有权进行宪法解释的国家机关。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合宪法律解释”应该是处于“宪法解释”的范畴之内的。因此,有权进行“合宪法律解释”的国家机关只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包括法院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机关和公共团体,如果企图对法律条文进行所谓法律解释或“合宪法律解释”,实质上会构成违宪行为。因此,主张法院审理具体案件时适用宪法或进行所谓“合宪法律解释”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令支持法院“适用宪法”进行审判活动的学者更难以解释清楚的是法院在“适用宪法”审理具体案件引起宪法性争议后如何裁决,以及法院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如何上诉这些程序性议题。无论这些学者们如何努力,他们都无法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找到法律依据来证明我国法院依程序可以受理宪法性争议案件,或进行裁决,或可以审理当事人不服裁决的上诉案。套用赵本山小品“不差钱”中小沈阳的话来说,“这个(法律依据)真没有!”既然我国没有现成的法律依据支持在具体案件审理中适用宪法,于是陈弘毅教授建议参考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做法。陈教授说:“在台湾地区,如果法院在审判案件时认为适用的法律违宪,它可以暂停诉讼程序,把违宪问题提交大法官会议审理,由大法官对有关法律进行违宪审查。”可是,陈教授的寥寥数语却透露了所谓“适用宪法”实质上就是违宪审查的一部分。
笔者对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制度不甚了解,但是从陈教授的话语中不难推论出我国台湾地区的违宪审查在法律、程序及制度上都是有根据的。法院依据法律及法定程序有权“认为”所适用的法律违宪,有权“暂停诉讼程序”,有权“把违宪问题提交大法官会议审理”。法院的这一系列行为,在环环相扣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形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陈弘毅教授怎么还能说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只是“适用宪法”而没有进行违宪审查呢?
尽管笔者不太赞成陈弘毅教授关于“适用宪法”的一些观点,但是他的文章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从法律、程序及体制方面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我国违宪审查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但是,自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未对法律或法规作过违宪解释,也从来没有受理过违宪审查案件。诚如韩大元教授所言:“法定的有权提出审查要求的国家机关,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几乎不行使违宪审查要求权,而热衷于出台‘司法解释’,没有积极回应民众权利保障的期待。”(21)不过,笔者认为,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国家机关之所以没有行使违宪审查要求权,是因为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配套的法律法规从程序和制度上保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切实地实施违宪审查的权力,同时保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及时主动地行使违宪审查请求权。宪法学者们为宪法条文中“只服从法律”的“法律”两个字是否包括宪法而争论不已,但是鲜有学者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过建议或意见,促进最高权力机关尽快制定法律来建立和完善违宪审查的程序及制度。法律人常说“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或者说“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为了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制,我们必须提出并解决诸如以下的违宪审查程序问题:
1.谁能代表拥有违宪审查请求权的五种国家机关(22)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违宪审查申请?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其他人?
2.提请违宪审查要求的文本格式是什么样的?是书面申请,或是动议,或是立案请求书?
3.谁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违宪审查要求?委员长、特别任命的副委员长或特设的违宪审查办公室?
4.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由全体常委共同审理违宪审查案件,还是设立专门委员会来审理?
5.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以会议形式,还是以开庭形式,或是书面方式来审理违宪审查请求?
6.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违宪审查请求的裁决以什么形式公布?备忘录、裁决书或意见书?
7.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裁决可以表示不服或反对吗?可以要求复议吗?等等。
如果这些程序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违宪审查机制,即使是贵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国务院的最高国家机关也是无法行使违宪审查请求权的。
综上所述,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或宪法司法化和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密不可分。但是我国的国情不允许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宪政体制。吴邦国委员长在最近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23)如果西方的那一套不能搬到中国来,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是断然没有生存空间的。因此,如果将宪法司法化定义为法院适用宪法,将齐玉苓案视为开创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先河,那是完全脱离中国宪法体制的空想空谈而已,顶多只是用肥皂水吹了个花花绿绿的彩色气泡,还没有升上天空几米就会破灭的。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齐玉苓案“批复”,至此,“宪法司法化”这个彩色气泡不是应声就破了吗!好像还有人想接着吹,不怕瞎费工夫尽管吹吧,反正现在学者们也有了自个儿瞎折腾的自由!不过,大家最好还是按中央希望的那样“不折腾”,把精力和资源用在促进符合中国情况的宪法监督适用的套路上来。
注释:
①周菁、王超:《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起》,《攀登》2002年第2期。
②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
③See William Nelson,Changing Conceptions of Judicial Review:The Evolution of Constitutional Theory in the States,1790-1860,120 U.Pa.L.Rev.1166(1972).
④John J.Patrick,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A Student Compan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06.
⑤同上注,第182页。
⑥See Jeremy Waldron,The Core of the Case Against Judicial Review,Yale Law Journal,2006,pp.1346-1406.
⑦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Article Ⅵ,(2).
⑧同上注。
⑨Alexander Bickel,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Bobbs-Merrill,1962).
⑩Alexander Hamilton,James Madison,John Jay,The Federalist Papers (1788),No.78,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o.61-10757.
(11)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Article Ⅲ,Section 1.
(12)截至2009年1月,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上总共有3168人被任命为联邦法院的法官。目前,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固定有9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有179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有687人。See United States Federal Judge,from 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March,2009.
(13)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
(14)我国《立法法》第90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15)我国《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6)我国《立法法》第43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17)参见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宪法适用如何走出“司法化”的歧路》,《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
(18)韩大元:《以〈宪法〉第126条为基础寻求宪法适用的共识》,《法学》2009年第3期。
(19)陈弘毅:《齐案“批复”的废止与“宪法司法化”和法院援引宪法问题》,《法学》2009年第3期。
(20)同上注。
(21)同前注(18),韩大元文。
(22)五种国家机关指的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3)吴邦国委员长在2009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新华网首页,2009年3月9日。
标签:法律论文; 违宪审查论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论文; 美国最高法院论文;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法官改革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司法体制改革论文; 司法审查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司法改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