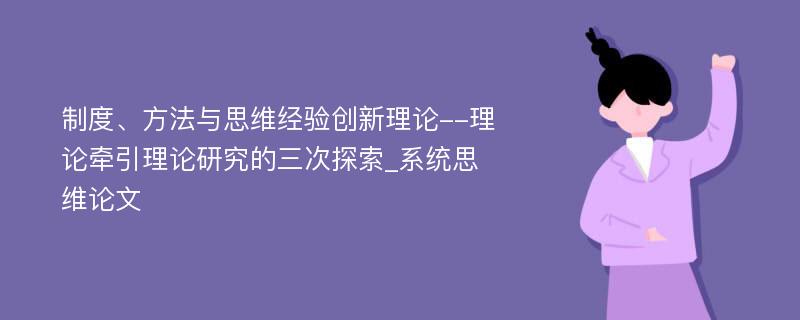
体系、方法、思维实证创新论——理论牵引学术研究的三项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学术研究论文,三项论文,思维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 8095( 2000)01-0013-05
理论贫穷是学术研究的固疾。在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国家相关理论在全局上没有创新,社会主义国家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还有待于理论创造。这一表象上的困局,在实质上恰是学术创新的最佳起点。回顾我在20世纪的学术心得,自感理论牵引学术研究有“三得”,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点点滴滴,深有学海识明珠之感。现仅借《史学集刊》新千年的首期发表,以示把生命凝聚在学术上的自律,也是与学术界同仁交流。这里所说的“三项探索”,就是体系、方法与思维。
体系——世界是转化过程的集合体
综观我国学术界的走势,我倾向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学人的根本欠缺体系性构建的能力。传统学人做学问的一大特点是“评点感悟”。有人说钱钟书是中国“文化昆仑”,其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弗洛伊德、萨特等。众所周知,钱先生的研究领域大体在文学范围内。按照季羡林教授的看法,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还“没有一个人创立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在王晓华看来,钱氏主要著作如《演艺录》、《管锥篇》等就是“评点感悟”式的文本;显然,这座“文化昆仑”并没有弥补当代中国文化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欠缺”。[1]
笔者认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些还是相当闪光的亮点,但在全局上,仍欠缺有创新性的独立理论体系。冒昧地说,我国有关20世纪国际问题的研究,一是对苏联版本体系的微调;一是对西方版本体系细微点的膨胀。苏长和、 彭召昌在“对近20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的反思”中, 论证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2]两位所提出的见解值得沉思,所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
英国著名国际关系事务专家菲利普·阿伦·雷若兹阐明,每个体系都是“精神思维的产物”;用抽象的方法构想或建立起来的相互作用的模式,即称之为体系。他在其《国际关系导读》一书中作了论证。
近30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大学主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和“苏联现代史”等课,深感其体系陈旧而又不能自拔。早在70年代初期,应北京某出版社之约,在撰写书稿中,我查出恩格斯一段话。他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大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3]这是现代的科学的系统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思想。笔者在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参研了诸多专家的成果,把恩格斯的相关论证简捷地概括为:世界是转化过程的集合体。
笔者禀承“院里的问题到院外去解决”这一“间接路线”的战略哲理,在构建体系上,“避开”“世界现代史”,并到它的“院外”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在70年代中期前后,以“世界是转化过程的集合体”的理念,构建“国际战略学”体系的朴素源头。1978年仲夏,得知教育部拟选派我赴美进修的消息,因此加大了《国际战略学》提纲的制作力度。1981年和1982年在美国期间,努力地重新制作,其提纲二稿面容于1984年进入吉林大学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堂。《国际战略学》一书于1986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提纲”为第三稿。
《国际战略学》一书论证了大千世界古往今来的“国际战略总流向”及其“军事战”、“经济战”(工业社会)、“知识战”(知识社会)的三大战略流程,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战略走向;界定了“十大战略要素”及其交互作用的战略机制;在国际战略上提出了“双区多热点”理论(在1996年出版的《国际大战略》一书中加以论析);在国际社会全局上提出了“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的命题,并提出了“在高科技高物质条件下,人们的心理对物质的战略系数为3∶1”; 在高层次上论证战略人才序列优化与科学决策等重大问题。
《国际战略学》一书受到我国多领域著名专家的高度赞赏,被誉为“中国首创”,“世界也是少见的”。1987年,该书荣获首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1995年,荣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求实说来,所有这些奖项仅仅是对我在构建学科体系这一方向上的鼓励与鞭策。它更多的是引发我来自心扉深处的学术品质的共鸣,那就是以“世界是转化过程的集合体”的科学理论命题,来构建国际战略学的体系。反思其提纲一稿那种“苏式版微调”与提纲二稿那类“西式版细微点膨胀”,至今令我仍有陷入旧体系谷底那种痛定思痛之感;而回顾其提纲三稿,尽管是素朴、初生之物,心里确有“创造性毁灭”的快感,它象回旋加速器那样来助推我努力地构建新体系。
雄心大志从构建学术体系做起。回顾近年来学术界的浮躁之风之害与急功近利之苦,特别是中青年学人深有体察。仅就笔者来说,既无“评点感悟”之功力,也无体系创新之智能,仅是对后者有心灵的憧憬。在新千年之初,作为一个老学人,给年轻一代的忠告是:缺乏体系性构建的能力,它既会断送自己,更会使学术“断后”;而那些“浮躁之果”、“急功之作”并非是21世纪信息社会的权杖。剥下虚幻的荣光,年轻一代的正途,套用讲评书者的套话,就是“书归正传”,那就是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大作之颠,从科学思想源头上引发出学术创新的灵光,勃发出大地母体上的立体化创造。西方不止一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获得灵感,进而展开着生气勃勃的创新,以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请问,前苏联东欧国家相关学者对《资本论》的“评点感悟”之作远大于原作之部头,到头来还不识其精髓所在,这一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令人深思吗!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也被认定为世界文明史册上的“大科学家”,甚至排序上界定在爱因斯坦之先。可以确信,对中国学人来说,其起点进入马克思主义,也就进入了世界级的快车道。
方法——“在头脑里建筑房屋”
记得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曾说过,青年人要与新学科一道成长。当然,一门世界公认的新学科,必定有学术界公认的学术体系。基于特定的学科体系要有特定的研究方法的惯例,也是顺应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约定俗成,笔者在“国际战略学”的新体系构建中,也试图设计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其提纲一稿是用旧方法吞蚀了新体系的基因,而提纲二稿则是被貌似的“新方法”模糊了新体系的面容;两者都得不到良果。新体系与新方法是辩证地统一。从这个思考出发,我在杨振宁先生的话中加上几个字,即为:青年人用新方法与新学科一道成长。
探索新体系与新方法真是充满着酸甜苦辣,其中更多的则是浓重的苦楚,而痛苦则是最大的快乐。那是1981年的深秋,我走进了美国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指导”这一“8”字头的课堂, 继续听一位美国著名教授的授课。这依然是那样充满激情、是那般清新亮丽,宛如以研究方法在“戏说”一段多彩的人生,令听者靠近一个伟大的魂灵——研究方法的圣殿,就如马克思先生所说的“在头脑里建筑房屋”——几乎与那位教授话音刚落并行的,是我的脑海里顿时引发出罗斯福式的“英明的一闪念”。它象引信那样,引发头脑里的“核共振”。中经百般的智能劳作,我把“在头脑里建筑房屋”的命题性的提示,物化成所谓“立体研究系统”这一新的研究方法。
“立体研究系统”就是构建科学研究的空间性体系,促进研究动态总流程在规范控制下投入双向运转,并借助于信息反馈进行良性调整,进而取得成果的高效能。在研究方法上,它是从专业的狭窄点转向交叉学科,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从平面研究转向立体空间的一种探索。它包容四个程序,即1.资料处理网络化;2.铸造空间型部件;3.立体系统的结构控制;4.效应评估。自80年代初期以来,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春等地多家报刊予以传输,在《国际大战略》一书的首章加以简捷而规范的解析,企盼读者与作者在思维的空间塔楼里,面对面、心对心的声息相通。
霍夫曼认为,“爱因斯坦的深邃思想的实质在于他的简单性,他的科学的实质则在于他的艺术性——即他对美的现象的感觉。”[4] “成功的秘密在于简单”,这是发达国家情报术的核心。简单性与艺术性的同一,是学术体系与研究方法创新的逻辑起点。在新与旧的判断上,人们认定,质变决定于1%。 作为动物和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卡尔·冯·林耐,他在1758年就将人类、猴子和狐猴归入灵长类目。在林耐逝世以后的100年, 一项分子生物学的成果曾使达尔文非常高兴。这项成果表明,现代人的基因和黑猩猩的基因之间只有1%的差别。 其它若干事物也一再显示了这一数据。况且,在习以为常的理解上,新与旧之间仅是一线之隔。流体力学中有关“有序”与“无序”之别也是由费根巴姆参数4.66920166……来界定的。质变决定于1%,更可以坚定人们创新的欲望,也可能赢得公众对创新成果的理解。美在简单。一位匈牙利人的计数范围是“1、2、3”和“许多”。因为1、2、3=许多,所以中国人有句习语叫“事不过三”。从“模糊数学”角度审视它,其中内涵天地间的哲理。因此,它也成为“立体研究系统”构建中的关键性参数。
科学研究的过程是研究者智能扩张的进程。在“立体研究系统”构建与机制运用上,依循“3”这一关键性参数, 用“三三制”加以界定,即三个学科(世界历史学、世界人才学、国际战略学)、三种语言(中文、俄文、英文)与三个控制点(继承点、拓展点、跳跃点)的双向交叉运转。
赋予组织必须发挥结构效能。有关世界的历史学、人才学与战略学是立体研究系统的三大学科支柱。面向知识经济的挑战,研究者宜把兴奋点转向立体思维,在科学研究的起点上,精心构建三大思维的空间塔楼。我的具体做法是,以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构成三大思维框架,进而造成硕大的思维空间。三大思维和三大学科融为一体,犹如钢筋水泥浇铸成三大支柱伸向空间而形成开放系统。
作为新千年的学术馈赠,坦率直陈,当前问题的关键,不仅是如何创新,而更是人们着力的方向不在于创新。近年来,学海多泡沫。某些中年学者乘浮躁之风,因势利导地制造轰动效应,以种种非学术之道,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称谓,并从速的在项上之头掩映着多项灵光。它令长者惊愕,也令少者误导,更令其同代坐冷板凳者困惑。如果说美国当前缺乏1950—1970年期间造就出的学术领袖,使其“岌岌可危”; 那么我国中年学人中的“泡沫教授”也宜自省,来个“斯大林刹车”,与同代人一道走上学术领袖的荆棘之路,成就我国新世纪的辉煌。
鉴于“在头脑里建筑房屋”在于人,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其意志品质与学术品质的重要性。人品重于学品。笔者在国际战略学的探索中,一直把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与自身的“人生哲理30条”融为一体,因为我深信,信念是统领智能到位的核心要素。
思维——“为自己求理解”:写、画、算
笔者长期主讲“世界人才学”,深信思维活力是人才要素的核心。面对知识经济的全新挑战,更新观念与构建立体化思维系统是我国学人的当务之急和终身使命。时间增值促成立足未来的思维方式,空间贬值形成了系统思维方式,知识更新加快推动探索立体思维方式。作为动态的思维活动,应倡导开放性的思维空间,谋求思维手段的现代化。
质疑与反思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而勤于思考则是两者的能源。我国先辈哲人曰,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时至现代世界宽大视野,人们又从深层次开掘“思考”的内涵:精确地说,什么是思考?爱因斯坦的回答“即世界有一个设计,而设计可以为我们所理解的惊奇。”[5] 在科学研究的起点上,要努力地构建思维的空间塔楼,它将引发研究者得到别具一格的境界,赢得史无前例的心态,获得撞击心灵深处的特异感应。进入这般境界,才有可能谱写出生命与智能凝聚的时代交响乐章。这也许就是“设计出惊奇”——提起笔来思考的临界效应。
笔者感知,近些年来,我们学术界在新条件下,总是面对一个老问题,那就是自己不甚明白的,却能口若悬河地讲;自己不大理解的,却能制成“宏篇巨著”,再加上出版业富丽堂皇的包装,竟然有大师级光环的油彩。这般架势令我想起30多年前所学过的马克思的一句话:“为自己求理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在叙述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曾为了“自己求理解,而不是为了付印”,写了“许多篇专论形式”的“材料”。专家们所熟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也正是为了“自己求理解”。[6]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把他所读的一切归纳成一定的系统”,“不仅在思考,还要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7]
列宁也是这样,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也是巨大科学研究的成果,仅为此书所作的有关世界经济、政治、外交、科技、工运与殖民地等方面的读书笔记就达20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就是以其所查阅的有关国家问题资料,即题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为基础的。时至20世纪9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列宁著作在全世界共有401种语言的文本,居首位;其次是圣经,286种;第三位是马克思的著作,196种。 它雄辩地展示了马列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具创意的尖端思想大作在国际社会影响之大。
科学经典之作是永存的,它的研究方法也是常用常新的。中国著名经济史专家严中平先生认为,“分阶段地对资料进行整理、消化与总结,清理自己的思想,动笔写下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实行的科学的工作方法之一。”[8] 严先生的论文《关于发现问题和分析研究》,笔者是在1963年阅读的。时至文革初期,我用专用笔记工整地抄写,反复学习与试做,并推荐给相关学人。
自文革初期以来,笔者尽力实践“为自己求理解”而写、画、算。笔者携往美国的另一提纲,即《赫鲁晓夫传》提纲,仅为写这一提纲就做了中、俄、英三种语言的9本笔记。时至今日,尽管该书已出版, 但我倍感亲近的还是这些笔记。其次说“画”。我的任何一部书,或其中的任何一章,其“操作图式”都画在提纲上。以至主讲“国际战略学”一课,每章必有两个“哲理馈赠”,并在黑板上作图,其中有图形、函数表、“正态分布”图与“操作图式”等,在两者辉映中传输出相关内容。所以我说,终身在讲台前学习是教师职业的独有幸运。何况,一代巨人斯大林、罗斯福在国策性决策中,不也是经常画图吗!最后是“算”,也就是涉及思考、计量与决策的问题。要精于计算。笔者对美国“新政”有关“3.2啤酒”的解析,就是精密的计量,以小见大, 并上至国策调控操作,学生会领悟到小大由之之理。至于“政治情报解析术”,每一步都要算,直到文理交叉,学生也会感悟到“文理合一”之妙。
这里所说的“写”,重在自我消化;所谓“画”,是寻觅整体结构;进行运“算”,则期盼精确到位。通过如此三位一体的百般劳作,企望“为自己求理解”。“为自己求理解”就要严格地训练自己。当代名士基辛格博士,其书《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就是为训练自己而写作。严格训练自己,才有可能奉献他人。他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因此成为西方名著。
笔者从学已达半个世纪,在三个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中深感理论功底的浅薄,由此特别渴望《资本论》。20世纪末的一天,我请教一位经济学教授说,我已学过三遍《资本论》,就是读不懂。这位教授说,从你现在的情况看,学《资本论》已经不具备条件了。这是笔者在20世纪留给生命之旅的最大遗憾。
人们说我的长处是勤奋,笔者自感的短处是愚拙。所幸的是我学了马克思主义三句话,并用这三句话支撑了我的学术体系、研究方法与思维空间。纵然成效一般,但着实是乐在其中,心房滚动的思潮经久不息,它令我在21世纪充满着希望。
笔者在反思中感到,我们学术界一大病灶是思维贫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指出,形象思维是思维科学的突破口。杨春鼎阐明,所谓形象思维能力,“就是敏锐精细的形象感受能力,丰富牢固的形象存储能力,准确迅速的形象识别能力,独特新颖的形象创造能力,达意传情的形象描述能力。”[9]它也是人们捕寻生机、 觅求活力和开展创造力的思维前提。思维活力是精神思维的永动机,只有优化了前者,后者才有优化的产物,即体系与方法。
美在简单,贵在独特。以“三句话”创业是对学术生命的最高鉴赏。思维——方法——体系的依次推进,就是闪射史诗般的视野,物化工匠般的技艺,构建独特性结构的过程,其间与日俱增地强化着美的感觉、美的操作与美的结晶。
收稿日期:1999-12-12
标签:系统思维论文; 思维品质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资本论论文; 国际战略学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