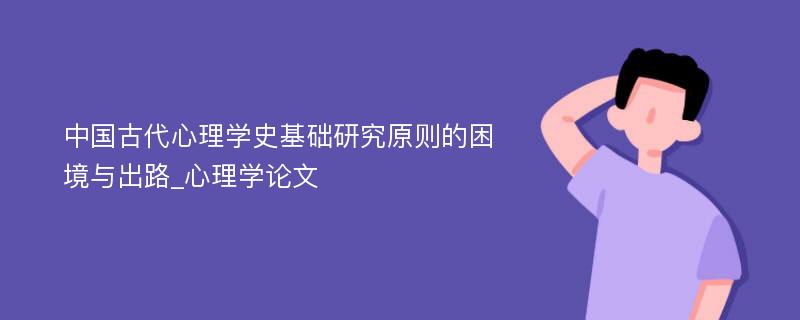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基本研究原则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出路论文,心理学论文,困境论文,思想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00)—01—0023—05
自1979年燕国材发表“关于‘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1]和杨永明等人发表“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心理学遗产的研究”[2]之后,尤其是1983年潘菽和高觉敷以他们在中国心理学界的崇高威望,在《心理学报》上联合发表了一篇号角性的题为“组织起来,挖掘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藏”[3]的文章以来, 通过潘菽等老一辈心理学家的努力,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现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也宣告建立起来了。
但是,随着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现阶段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一些研究者对潘菽等人早先所主张的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针对这些批评,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至今未作出很好的回答,从而使得一些研究者或多或少地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现有基本研究原则抱怀疑态度。假若这一困难不能及早得到解决,势必会影响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更好地向前发展。为此,本文试图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现有基本研究原则所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提出一管之见,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基本研究原则之简介
关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基本研究原则,一贯受到从事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学者的重视,如潘菽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刍议”[4] 与《心理学简札》(下)[5]、高觉敷在《中国心理学史·绪论》[6]、燕国材在“关于‘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与《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7]和杨鑫辉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刍议”[8]与《中国心理学思想史》[9]中都曾论及过此问题。 综观这些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基本研究原则的论述,大家一般都赞同:
1.心理学思想原则。意即挖掘与整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时,应该是挖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而不是“中国古代心理思想。”而“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指中国古代思想中具有科学性的心理学思想。因此所谓心理学思想不是指仅和心理学沾上边或有所联系的思想,而是指具有科学特点或符合于科学要求的心理学思想。”[4] 由于强调“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指中国古代思想中具有科学性的心理学思想”,故有人也将此原则概括为“科学论原则[10]或“外在逻辑原则”[11]。
2.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体系为框架的原则。意即,要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与体系为框架去对照整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9]
3.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其涵义主要有二:一是要“将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放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去考察,不以今日之要求为准则进行历史的分析与评价。”[9]另一是, “要求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科学标准苛求古人,而应考察某种心理学思想在科学发展长河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9]
4.古为今用的原则。意即“从研究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就是要使古人的心理思想,能为建立中国心理学或使心理学中国化服务,从而能间接在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贯彻这一原则时,既不能为古而古,也不能改古合今。”[7]
二、研究者对基本研究原则的主要批评及原由
但是,现阶段有些学者对上述前两个基本研究原则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他们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这两个原则属于一种外在的逻辑原则,此观点以郭斯萍为代表。郭斯萍认为,潘菽和高觉敷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开创研究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原则:‘外在逻辑原则’,即必须将中国古代的心理思想整理成符合科学特点或具有科学倾向的体系,并由此引申出具体的研究方法,就是借用现代心理学的逻辑构架来分析、整理中国古代‘零碎不全’的心理学思想。”[11]而“问世不久的中国心理学史正处于一种冷落、徘徊的状态。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正是那条著名的‘外在逻辑原则’。”[11]另一是认为这两个原则的运用,造成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破碎和失真,此观点以尹文清和葛鲁嘉为代表。尹文清说:“以往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最典型的论述是潘菽教授提出的‘科学论原则’。作者认为‘科学论原则’的运用造成了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的破碎和失真。如果撇开其历史的功绩而言,这一原则应走到它的尽头了。”[10]葛鲁嘉则说:“以西方科学心理学为参考构架,……结果在研究中,仅在于按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标准来切割和筛淘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仅在于为从西方引入的科学心理学提供某些经典的例证和历史的证明。”[12]
为什么现阶段会有一些研究者对“心理学思想原则”和“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体系为框架的原则”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呢?分析起来,其原由主要有三:
(一)这两个原则本身有缺陷
应该说,这两个原则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是招致批评的主要原由之一。
“心理学思想原则”主张挖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时,应该是挖掘“具有科学特点或符合科学要求的心理学思想”,而不是挖掘“仅和心理学沾上边或有所联系的思想”,这是对的;但是,从此原则出发,潘菽要求大家要知道,我国古代符合科学要求的心理学思想,“应该主要向我国古代的唯物论思想那里去找,而不能不加分辨地向古代的所有思想家那里去找。”[4]因为,“一般来说, 只有唯物论或有唯物论倾向的思想家才能取得合乎科学的心理学见解。主观唯心论的道路和合乎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很少干系。”[4]潘菽此观点又有失偏颇, 从而受到尹文清等人的批评。如尹文清说:“事实上,如果说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上还有一点对纯粹精神现象的思考,倒是数庄玄显得较为突出。 ”[10]
“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体系为框架的原则”中,“框架”一词用得不妥,既易让人产生牵强附会的硬套之感,又易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外在逻辑原则”,从而导致了郭斯萍和葛鲁嘉等人的上述批评。
(二)未很好地贯彻“古为今用”原则
未很好地贯彻“古为今用”原则,是招致批评的又一主要原由。
大家知道,早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里,潘菽就曾说:“我们要研究我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是为了‘古为今用’,是为了有助于建立我国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很好地服务的具有我国自己的特点的科学心理学。这样,我们所要挖掘并加以发扬的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必须是能为我们所需要的科学心理学所用,能纳入到我们所要建立的科学心理学体系中去,因而构成我们所需要的科学心理学的有机部分或基本看法。因此,……我们并不是单纯为了古代心理学思想而研究古代心理学思想,尤其不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包揽一切的所谓心理学思想。”[4] 在这段话中,潘菽提出要将“古为今用”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具体做法是,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挖掘那些“能纳入到我们所要建立的科学心理学体系中去,因而构成我们所需要的科学心理学的有机部分或基本看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后来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中,潘菽提出的这一重要原则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将现有的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论文或著作与潘菽的这一原则相对照,就会发现,有些人在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包揽一切的所谓心理学思想”,而这些思想中的某些内容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是帮助不大或根本就没有什么帮助,从而也就招来了诸如下面的批评:“以西方科学心理学为参考构架,……结果在研究中,……仅在于为从西方引入的科学心理学提供某些经典的例证和历史的证明”。
(三)误解
由于前两个原由的存在,又引出了招致批评的第三个原由:误解。这从一些批评者所持的言论中就可看出。如,尹文清用“科学论原则”来简称潘菽提出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指中国古代思想中具有科学性的心理学思想”的主张,并将潘菽此处所用的“科学”一词,理解为自然科学之义的“科学”,这就是一种误解。因为潘菽此处用的“科学”一词,本指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这从潘菽一贯认为心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就可看出。由于这一误解,尹文清就对潘菽的上述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与其再继续单一地运用普通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去重复以往的研究工作。还不如同时从文化的角度来考虑研究中国古代一些与实用理性相协调的具体的心理学思想:如品德心理思想、教育心理思想、人际关系心理思想、社会政治心理思想,因为这些领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特别发达的部分,所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10]
又如前所述,杨鑫辉等人讲的“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体系为框架”,尽管用词不妥,但若联系上下文看,还是能看出此处的“框架”一词,实乃“参照”之义。因为,杨鑫辉曾明确指出,“古今参照,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为框架,既不是牵强附会的硬套,也不排斥同时使用我国古代的某些仍富科学性的概念。在这里,保证概念的科学性和体现我国的特色是可以统一的。”[9]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人也产生了一些误解。
三、对策
为了摆脱上述批评,更重要的是,为了完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基本研究原则,以推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更好地向前发展,就有必要在继续坚持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和切实贯彻古为今用原则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另外两个基本研究原则作些调整,并补充一条新的基本研究原则。具体地讲:
第一,仍主张心理学思想原则
因为,一方面,“心理学现在已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不再是过去隶属于哲学的那种心理学。因此我们所要说的心理学思想应该是合乎科学要求的思想,而不能泛指哲学时代的心理学所可以有的一切联系到心理学的思想”。[4]另一方面,过去研究者的经验教训也表明, 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中,必须坚持心理学思想原则。关于这点,潘菽就曾说:“我们谈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所谈的应该是中国古代所有的看起来合乎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思想,而要防止把有关系的一些哲学思想或其它思想也混杂进来。如果把二者混而不分,那我们的挖掘工作就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过去曾有人试图挖掘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而未能取得很好的结果,或者终于放弃,其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此。这是应该好好吸收的一个教训。”[5]
但是,需指出,主张心理学思想原则,并不意味着只能研究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科学的态度应是:既要研究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也要研究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这正如高觉敷所说,在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中,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不过,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不应当仅讲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而对唯心主义心理学思想避而不谈;对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家的估价要掌握分寸,不要肆意拔高;对我国古代唯心主义心理学思想家也不要全盘否定,对于具体的人要作具体的分析;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和思想家的论述,要注意分析其有关的社会历史条件。[6]
第二,主张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与体系为参照原则
如前所述,既然“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体系为框架”,实指“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和体系作为参照”,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我们在这里明确提“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和体系为参照原则”,用以取代原有的“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体系为框架原则”。我们认为,只有以现代心理学概念和体系为参照去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才能保证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中切实贯彻“心理学思想原则”,以便在极为丰富的中国古代学者的思想里,挖掘出属于心理学方面的思想,并且用尽可能统一的概念去表达这些思想。这样做,不仅便于大家理解,更在于保证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科学性,正如燕国材所说:“按照心理学体系去分析、整理中国古代的零碎不全的心理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这种系统化的过程中,就容易看出古代心理思想的庐山真面目,如果不用现代心理学的体系去对照古代的心理思想,就很难了解后者的真实价值。”[1] 再者,从与中国心理学思想史情况类似的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中,也可看出此原则是行得通的。如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一个旁证。中国古代本无“哲学”这个名词,但却有义理之学,那么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呢?冯友兰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3]稍加比较可知,冯友兰所主张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原则,与我们讲的以现代心理科学的概念和体系为参照作为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原则,在思想上是相同的。
而据中国香港大学心理学系杨中芳博士介绍,也有人主张完全抛开现代心理科学的概念与体系,只用中国传统的、固有的概念与体系去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杨中芳博士本人也主张:在研究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时,“必须放弃以现代西方心理学范畴为依凭,抽离以理论为框架的惯性思维,直接去寻求中国自身古代心理学的范畴,并探研其历代发展进程。……从而恢复中国人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原貌,然后再去看看这一体系之改变轨迹。”[14]这无疑是一种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新思路。可惜的是,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有关按这一思路写成的论文或论著。不过,笔者冒昧地认为,假若要这样做,必须先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怎样去确定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一些固有概念的内涵?因为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的概念多是一词多义,具有模糊性、不确指性的特点。第二,怎样去确定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因为中国古代本无“心理学”这一名词,其中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多蕴藏在浩翰的古籍中,显得比较零散。第三,如何去与外国心理学界进行交流?因为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有一些重要的范畴与概念,是外国心理学中所没有的。第四,用中国传统的、固有的概念与体系去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时,若遇到与冯友兰所说的作义理之学史相类似的困难,将如何处理?大家知道,对于作义理之学史将会遇到的困难,冯友兰曾说:“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而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13]冯友兰的这段话虽是就中国哲学史而说的,但笔者以为,其思想也同样适用于现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当然,若能妥善解决好以上几个问题,则完全抛开现代心理学概念与体系,而用中国传统的、固有的概念与体系去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也未尝不可。
还需指出,我们之所以主张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与体系为参照原则,除了上述原由之外,还有两点:一是为了避免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中出现牵强附会的硬套现象;另一是为了便于使用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的某些至今仍富科学性的概念。在这里,保证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科学性和体现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特色是有机统一的。可见,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与体系为参照原则,既已涵盖了“完全抛开现代心理科学的概念与体系,只用中国传统的、固有的概念与体系去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这一原则的精华部分,又能避免此原则所带来的困难。正由于此,我们才主张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与体系为参照原则。
第三,坚持求同性与求异性相结合的原则
为了在实际研究中更好地贯彻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与体系为参照原则,我们又主张补充一条新的研究原则:求同性与求异性相结合。
所谓求同性原则,意即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与整理中,应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与体系为参照,找出中国古代不同流派之间(如道儒两家之间)和不同时期的同一流派之间(如早期道教和全真教之间)心理学思想的相似之处;同时,也要找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外国的心理学思想之间的相似之处。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古代不同的流派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共同的大背景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不同时期的同一流派之间在基本思想上又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因此,中国古代的不同流派之间和不同时期的同一流派之间必然会提出一些彼此相似的思想或观点;另一方面,尽管中外学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但由于人类的心理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因此,中国古代学者也会提出一些与外国学者相类似的心理学思想或观点。
所谓求异性原则,意即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与整理中,即应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与体系为参照;同时,又要适当参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相关学科——如中医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通史等的研究成果,甚至还要适当参照有关描述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一般常识,以发现中国古代不同流派之间和不同时期的同一流派之间心理学思想的相异之处;同时,也要找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外国的心理学思想之间的相异之处。这是由于:一方面,在中国古代,不同的流派之间因为彼此在基本思想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彼此的心理学思想也必然有一定的差异;而随着时代的不同,同一流派的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增添不同的内容,故其心理学思想也会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心理存在着一定的个性,再加上中外文化背景景的不同,因此,中国古代学者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必然也会提出一些与外国学者所不同的心理学思想或观点。
按求同性原则进行的研究,我们称之为“求同式研究”;而按求异性原则进行的研究,我们称之为“求异式研究”。求同式研究的优点是较易做;缺点是深度往往不够。求异式研究的优点是,最易找到中国古代不同流派之间和不同时期的同一流派之间心理学思想的特色所在,也易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思想或观点,使得研究往往具有一定的深度;缺点是较难做。正由于此,就现有的有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看,属于求同式研究的较多,属于求异式研究的较少,以至于招来了诸如“仅在于为从西方引入的科学心理学提供某些经典的例证和历史的证明”之类的批评。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提出要坚持求同性与求异性相结合的原则,以试图提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深度。
收稿日期:1999—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