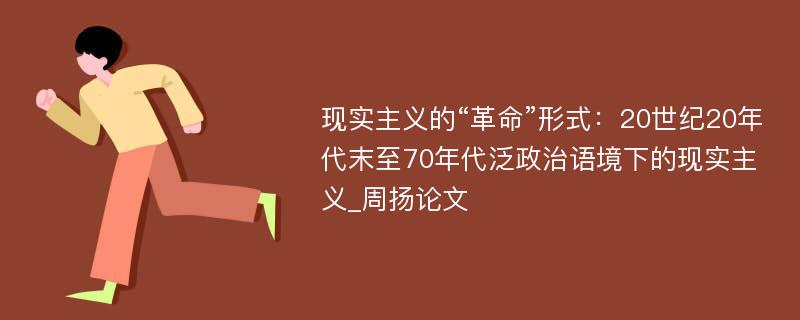
现实主义的“革命”形态——20年代末到70年代泛政治化语境中的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年代论文,语境论文,形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的50年间,是马克思主义潮水般涌入中国、政治革命风云激荡的时期。现实主义,无论是作为文学思潮还是作为创作方法,其间都经历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种种变化。甚至当人们对这一时期回首重审时,现实主义已经蒙上了不洁的光彩,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联姻与政治话语私通并被权力糟蹋。在人们心目中,现实主义应该有自身的本来形式,即纯粹的元话语形式,在没有过多的外在因素干预的前提下,它作为文学发展本身的一种自律性机制,对文学的发展演变起着相应的调节作用。
在西方经典现实主义作家或批评家那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至少包含了如下三个原则:典型性、客观性、历史性。〔1 〕但在中国20世纪的特定文化语境中,现实主义自身所发生的一切变异,似乎都是必然的。联系现实主义在这一时期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文学中的命运,可以说,革命时期的现实主义所经历的任何遭遇似乎都不足为怪。正如托洛茨基所说:“革命中‘必然’的特征被发展到了极限。 ”〔2〕20年代末到70年代,现实主义从当时的泛政治化语境中被改造〔3 〕,反过来又强烈地作用于这种语境,同进也使自己印染上了鲜明的浪漫色彩,甚至在50年代末和六、七十年代,浪漫主义几乎成了现实主义的基础,事实上,这是由当时浪漫的时代本质决定的。
“革命文学”:现实主义的浪漫面影
20年代末与“革命文学”同期产生的叶圣陶的《倪焕之》(1928)、柔石的《二月》(1929)等作品,当可看作对五四时期现实主义的话语实践。但这时的声音最响的是创造社与太阳社的青年作家们。“革命文学”首倡时期的作家对于自己究竟要操持一种什么样的文学话语才能革命得最有力并无清醒的认识,但“转向”之于创造社来说,首先意味着抛弃原先所持的浪漫主义,因此,所谓“革命的浪漫谛克”、“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等,都可看作对现实主义选择的心照不宣。起初,他们对这一点并无明确的态度,只是致力于对文学话语的重新界定,积极探索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在李初梨那里,文学已被政治工具化。
这种文学选择与文学界定有其历史的契机,它根源于重建文化语境的迫切需要。五四时期革命者们所持的文化激进立场导致了总体倾向上的浪漫主义趋向,梁实秋1926年就指出了这一点〔4〕。 “人的文学”的意识于文学革命初期就产生了,青年们以摧枯拉朽的姿态破坏着现存的一切,但个人主义首先在现实社会情境中遭到了围追堵截,是的,仅有对旧文化的破坏是不行的,重要的是要重建,而浪漫主义的话语方式以及它的个性主义基础显然无助于这种重建。其时马克思主义正被大量介绍进中国,政治革命也风起云涌,重建作为一种文化压力推动着青年知识者们。本来,作为五四文学总体趋向的浪漫主义主要是作为审美惯例潜隐于文学话语中,但在革命作家们未能细想之前,首先遭到遗弃的是作为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至少当时的革命作家们的理解还能达到这样一个层次:个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于这种重建太显无力,浪漫主义的审美惯例和浪漫主义的情感向度于这种重建也显无力。
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促动与俄苏文学的影响,它的必然性正像鲁迅所说:“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5 〕由“革命文学”论争所显示的这场文学运动之于时代文学与文化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甚至是在同一个革命文学作家那里所显示的双重姿态(文学家与革命家)等,无不体现着时代文化语境中激进浮躁心态作用下的探索与努力。文学无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重新定义意味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企图,以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但在当时兼具革命与创作双重使命的作家那里,对革命与文化关系的理解大都是走与此相反的路径,即中国的政治革命迫切需要我们建设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并创作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文学,进而寻找更适合于表达这一内容意义的具体表述形式。郭沫若指出:“在欧洲的今日”,“浪漫主义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而在欧洲今日的新兴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这种文艺,在我们现代要算是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了”。〔6 〕但理论话语作为宣言与作为实践并不是一回事儿,创作“转向”之艰难可见于当时的几种创作潮流的演变更替中。其中,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作为“毒素”深潜于青年们的心灵深处,其清除、排解之难,经历了几年的摸索和实验。革命作家们一方面在毅然决然地在理论姿态上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划清界线,一方面却又难以完全给予清除而不时地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浮现出来,此外,大革命所需要的热情也易于成为作品中的浪漫抒情成分。
1929年,“新写实主义”由苏联经日本传入中国并最终引起关注。但奇怪的是,它最终并未被革命作家们践之以行。按照勺水对“新写实主义”的阐释,它(1)“应该站在社会的及集团的观点上去描写, 而不应该采用个人的及英雄的观点”;(2)“不单是描写环境, 并且一定要描写意志”;(3)“由性格当中描写出社会的活力”;(4)“富于情热的,引起大众的美感的”;(5)“真实的”;(6)“有目的意识的”。〔7〕其实,这几种特质中, 真正能与革命家们的创作姿态与隐性立场共鸣的,大概不过只有“意志”与“有目的意识的”而已。他们虽然强调革命文学的集体话语特征和其“组织机能”(李初梨),但在真正的操作方式上,却迟迟无法摆脱作品的个人话语特征。事实上,“新写实主义”的介绍讨论于1929年下半年蔚为热潮,但创作却寥寥无几。倒是在这前后孕育出了被称为“革命的浪漫谛克”的一大批作品。如今读来,它们生硬、做作,确实没有多少审美价值。但正是这种生硬可以让我们重读出其意识形态的组织和拼凑。“革命”一词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显而易见。自然,它也潜含了某种英雄主义倾向在内,“恋爱”、“浪漫谛克”正是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文本中的外现。作为意识形态本身,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但在片面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而排斥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特定时代,个人主义即使是以“浪漫谛克”、“恋爱”的形式被移置进文本中,也是生硬的、做作的,同进也能被敏感而警觉的批评家识破真相。钱杏邨在评《地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四种倾向:“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倾向”;“浪漫主义的倾向”;“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的倾向”;“幻灭动摇的倾向”。〔8〕
无产阶级文学探索的极端表现形式是其后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倡导。在这里,作为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已被作为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一样的具体操作形式来看待。不仅如此,在革命家们看来,它应当是比现实主义更为先进的操作方法。“世界观=创作方法”,理论探索中的直线式思维逻辑在此已极端化为平面式中心主义的自大狂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它虽然对“革命的浪漫谛克”有所纠正,但这一语汇自身的规定性决定了它仍难以逃脱某种浪漫倾向,即使这是一种伪浪漫:“唯物”一词意味着建基于社会生活之上的客观写实笔法,以努力表现出革命生活的真实性;但“辩证法”一词要求在生活与革命的不断发展和灵活掌握中微妙地表现生活,要从现实中写出理想的召唤,从失败中听到胜利的锣鼓,从黑暗中绘出光明的尾巴,从而让人心满意足。在一次又一次的纠偏中,“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作为最新发展仍难以摆脱其描写社会生活的伪浪漫特质。
策略与虚蹈: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对“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又一次纠偏是1933年周扬受苏联文艺理论启发而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该文的副题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9〕。 有关于此的一个最有趣味的现象是,周扬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11月的《现代》杂志,它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所给予的客观的、详细的界定,至今看来仍然保持着它的深刻性与全面性。而在苏联,关于这一创作方法的明确界定是在1934年9 月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并且它的定义还招致了以后许多批评家的指斥。这就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了老师。周扬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有:“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不在表面的琐事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它的大众性、单纯性”。
在这篇文章中,周扬也在谋求给“革命的浪漫主义”以合法地位。“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要求作家描写真实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不就包含在这个生活真实里面吗”?他还引用吉尔波丁的话:“革命的浪漫司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所固有的,只是在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程度。”周扬最后作出结论:两者不是对立的,不是并立的,而是可以包括的。在两年多以后的《现实主义试论》一文中,周扬已明确接受了吉尔波丁的说法并给予自己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新的现实主义不但不拒绝,而且需要以浪漫主义为它的本质的一面。”〔10〕
在这里,周扬对于革命时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给予了恰切的表述,这也是“革命文学”倡导以来作家创作中流露出来却又不愿承认的倾向。事实上,在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现实主义写作大都掺入了明显的浪漫因素,而归根结蒂,整个革命的时代本身就是一个浪漫的年代,即现实主义所产生的语境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浪漫意味。因此,我们也可看出,周扬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个语汇,并非是在同一逻辑层次上使用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它们大体都含有精神倾向、文学思潮、创作方法三个层面的涵义。在周扬这里,前者是指一种具体的操作方式,即创作方法;后者是指时代文化语境中人们的精神倾向。
让人深思的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提法。周扬在文末说:“这个提倡无疑地是文学理论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我们应该从这里面学习许多新东西。但这个口号是有现在苏联的种种条件做基础,以苏联的政治——文化的任务为内容的。假使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显然,这一理论的引进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话语策略而被实施的。它一方面是“现实的根据之必要”,即批判“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忽视艺术特性,简单地把具体操作方式还原为意识形态问题的倾向;另一方面是期望中国作家能以此为借鉴,使创作更为现实主义化。在强调话语方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当时,革命作家们大都把其中的许多规定性奉为准则去实践。甚至有论者说其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
但是与其说这一批优秀作品的产生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话语的实践,不妨说是对不受过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干预的现实主义的兴趣。不错,周扬这一提法本身是作为一种纠偏策略引进的,但在这里,“社会主义”这一“政治——文化”的制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是与“现实主义”这一话语形式相互为一的。我们姑且承认现实主义有它的本体形式,但在它的不断变动、发展与改造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要求现实主义表述的这一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它的很多规定性也是被编码进政治意识形态这一功能中的,即与当时苏联的社会形态相符。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还只能是已标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的革命者为之奋斗的长远目标,而不是现实的制度。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除作为一种纠偏策略外,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话语虚妄性的一面,即它本身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在中国这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使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语境中亦显出其话语的虚蹈性质。在这一时期“左联”涌现出的青年作家们的大量优秀作品,与其说是对周扬这一理论话语的践行,不如说是对五四现实主义的效忠。张天翼的讽刺夸张,沙汀对黑暗的冷峻鞭挞,艾芜的明丽奇异,等等,都表明了30年代创作中现实主义理论话语对于急功近利的革命意识形态的胜利。
其实,体现着它的虚蹈性质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话语。上文已经谈到“革命文学”这一运动内在的重建文化语境的企图,在公开的宣言口号中,它被具体地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文艺”。它显然是政治斗争的组织策略,“这无产阶级文艺的兴起,是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斗争运动,大有关系的”〔11〕。在30年代前后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甚至是在40年代的权威表述中,“无产阶级”都沿用了它的本来意义,即指城市工人阶级。〔12〕那么,以城市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创造的“无产阶级”文艺就应该像蒋光慈所说的大量表现工人阶级的生活。但事与愿违,在创作实践中,文学作品缺少的恰恰是城市的喧闹与机器的震动,仅有的几部表现工人斗争的作品,也失之偏颇和生硬。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艺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发达、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无产阶级文艺在那个时期也体现出了它的虚蹈性。
这种现象固然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市经济不发达有关。但俄苏文艺理论家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也并非全无道理。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1928年曾由韦素园、李霁野译成中文,由北京未名书社印行。书中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对于未来主义、形式主义学派、“同路人”等的观点,既考虑到现实的革命需要,又不忽视文学的审美特质。但令人遗憾的是,30年代前后的革命作家并未对这本书给予足够重视。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此它不可能像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能够建设起高度成熟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观点是有些危言耸听。但细究他的逻辑推演,再证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实践,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的许多国家,诸如苏联与中国,仅是对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两者关系的摆正,就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自然,其时的“无产阶级文学”一词,已泛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知识者、小资产阶级等的文艺。但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为鲜明旗帜的许多文学创作显示出的,并不是一种成熟的、自足的无产阶级文艺形态。以政治革命和斗争为鲜明指向的重建,其最终成果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政权的建立,而文学话语的探索在未与政治意识形态摆正位置之前,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走向“两结合”的道路:意义与可能
与胡风相比,周扬的政治意识形态嗅觉异常灵敏。30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引进,显示着他作为政治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身手快捷、一鸣惊人之处。不仅如此,他还颇具远见地提出:“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必须以现代正确的世界观为基础。”〔13〕加之对题材的选择、对典型的理解、对形式的选取等,形成了周扬以文艺的政治社会学功能为基点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话语系统。与此相异的,是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强调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依赖,主体的“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对民族形式的独特态度等,同样从文艺社会学视角立论,但更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个体实践精神。在文化启蒙意识日渐淡漠、救亡呼声日益高涨、政治焦虑渐趋浓厚的三四十年代,它自然显得不合时宜,得宠的注定是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高屋建瓴、切时适地地对中国当时的文艺给予质的规定,以权力话语的姿态默认了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合法地位。它旨在揭示出文艺的一般规律以及革命文艺的一般规律,谋求为当时的文艺定位、定向和定轨。所以对具体的操作方式的选择几乎没有谈及,只是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作为权威意识形态对于革命文艺的重要性时说道:“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继1952年的《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十周年》的长文后,周扬又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这篇文章当可看作1933年那篇文章的续篇,至此,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可以说全部形成。
不能不承认,较之其后的“两结合”、“三突出”等话语模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面目是温和的、理智的。而关键在于,正像韦勒克所说:“如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仅仅是苏联批评家和作家们的事,那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或把它当作发生在苏联集团的文化环境中的一件令人痛心的荒唐事……但我相信,这将是判断上的一个严重错误。俄国的论争,提出了构成现代艺术和美学的基本前提的一系列根本性的观念和问题。”〔14〕不管我们带着怎样的成见去看待这种话语模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实实在在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权威意识形态占领了整个的社会主义阵地。如果说文学话语的本质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泛政治化语境下的文学表述为一种审美的政治意识形态。统合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现实主义在这种语境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异无不带有它深刻的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对现实主义给予最严整的阐释的恐怕是卢卡契。卢卡契与胡风的相异与相通之处,展示出了中国这片古老土地向西方敞开国门后历史与现实发展中的文化逻辑。胡风的悲剧性遭遇并不在于其思想意识与经典文本《讲话》有许多相异甚至相对之处,而在于由其理论体系所显示的他那特立独行的强烈自我意识和文化启蒙姿态已为当时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所不容,为当时意识形态的严密组织策略所不容。周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对权力话语的阐释,确可看作是对“构成现代艺术和美学的基本前提的一系列根本性的观念和问题”的创造性解决。50年代出现的诸多优秀长篇小说,甚至包括“干预生活”的作品,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到60年代,感到无所适从的已不仅仅是作家们,周扬本人也已在应接不暇的变换中不知所措,并最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两结合”创作方法于1958年正式提出且产生了巨大反响,至“文革”时期,《纪要》第九点意见仍声称:“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5〕浪漫主义终于和现实主义实现了大联合,并冠之以“革命”的称号。两种潮流结合的可能性也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年代才会产生。周扬曾对这个口号给予较为详细的阐释:“(“两结合”创作方法)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没有高度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就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16〕他强调了两点:一是口号是根据“大跃进”的时代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二是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中,强调的是革命浪漫主义。不妨由此分析“两结合”的这种可能性。
一方面,可能性在于时代的浓重浪漫色彩与文学话语的本质二者间所具有的一致性。“大跃进”时期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我们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当时的这种乌托邦是在语言中建构起来的,共产主义也是在话语运用中虚构想象出来的。在此,关于现实的语义假想和对象再造相契相合于文学话语的本质特征——虚构和想象。在一定意义上,文学终归是一种想象性虚构性写作。这正如郭沫若当时所作的表述:“从文艺活动是形象思维,它是允许想象,并允许夸大的,真正的伟大作家,他必须根据现实的材料加以综合创造,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创作过程,你尽可以说它是虚构,因为文学活动的本质也应该就是浪漫主义。”〔17〕这里暗含着一种巧妙而聪明的投机策略:把“想象、“夸大”、“创造”等语汇同文学创作过程相联系,从而将作为文学活动本质的虚构偷换成“浪漫主义”,目的只是突出其“浪漫”的一面,从而为“两结合”的话语方式寻找其合法性与自然性,以应和那个极富浪漫意味的狂热年代。它既是时代现实的浪漫,也是文学话语方式的浪漫。
另一方面,可能性在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暧昧关系。现实主义强调客观性和真实性,但纯粹客观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呢?作者的叙述本身就已包含了作者的主观态度;而真实性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词汇。在卢卡契看来,作家和批评家应积极投身到历史进程中去努力理解它和叙述它,而不仅仅是描写它。他之所以推崇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的批判现实主义而对左拉等的自然主义颇有微词,这与他的充满批判精神的、积极战斗的话语姿态不无关系。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观性被表述为“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于此显露出其理论话语批判的、能动的、主观的特征,使他的现实主义独尊论在深层中仍有着对浪漫主义的兼容。浪漫主义本身是一种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学,即使在它最为自足、最为完满的发展时段里,它本身也潜含了向其它“主义”,诸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转换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彼此通约、关系暧昧的。正像郭沫若当时所说的:“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18〕也因此,才使“两结合”具备了又一种可能性。
作为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在半个世纪中的流变也是本世纪整整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倾向的展现。其间所经历的或“转向”或“改造”,无论是自觉也好,被迫也好,无不是其时所亲历身受的文化语境的作用。从20年代末渐趋渐进的政治革命到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狂热,现实主义逐渐增强了它的主观性质与浪漫色彩,并最终走上“两结合”的道路。另一方面,作为理论话语与创作实践,现实主义也完成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其意识形态的确立的“讲述”使命。直至“两结合”本身已作为权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对其时的文化语境的破坏与建设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革”的突破口和主战场都是文艺。从文化启蒙到日益加剧的政治焦虑,由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维度标识出的是泛政治化语境中审美态度的变异。
注释:
〔1〕〔14〕[美]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2〕[俄]托罗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214页。
〔3 〕这里的“泛政治化语境”特指与现实主义这一思潮发生了紧密联系的社会政治情境,并非指当时的总体文化语境。
〔4〕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 1926年2月15日。
〔5〕鲁迅:《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92页。
〔6〕〔7〕〔11〕《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03、1123页。
〔8〕〔9〕〔10〕〔13〕《文学理论集》,《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74、72、96、91页 。
〔12〕1927年蒋光慈与屈维它合编《俄罗斯文学》一书,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规定性之一是:“城市的歌者。”1931年由冯雪峰执笔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1年11月中国左翼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一文中也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性,并对“无产阶级”给予相近的表述。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认为“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1952年毛泽东把“无产阶级”改为“工人阶级”,认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没过几年,他又重提“无产阶级”一词。
〔15〕《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
〔16〕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6月1日。
〔17〕〔18〕郭沫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标签:周扬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革命论文; 文学论文; 语境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