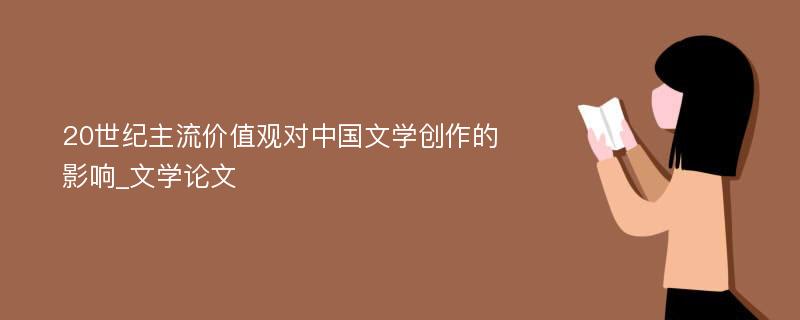
论主流价值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价值观论文,文学创作论文,主流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5-0158-07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随着中国现代作家思想的转向和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主流价值观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的巨大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从30年代开始,左翼文学运动便以全面超越的思维态势,首先用集体理性意识对“五四”新文学的个性独立意识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并通过阶级斗争人生哲学的高扬,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征服人类的政治理想。而解放区文学在集中消解人的个性意识的同时,则对改造世界的社会主体力量做了重新的价值认定:赋予农民——尤其是被认为具备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新型农民,以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思想的前卫性;在艺术上精心营造未来美好的人类家园,追求英雄主义的完美意识与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愫。而50年代后的新中国文学,不仅全面强化了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所有的政治理念,而且也开始将知识分子视为人格上存在巨大缺陷的社会弱势群体,并彻底消解和否定了他们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思想先驱者的原有地位。这一切艺术审美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演绎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创作模式,从而使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特形发展的历史局面。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去寻找主流价值观的具体艺术实践行为时,我们自然不能忽视早期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存在意义。如蒋光慈、洪灵菲、华汉、殷夫、胡也频、柔石、叶紫、蒲风等人,这些为政治信仰而进行写作的年轻作家,他们不仅是历史的亲历者,而且更是历史的参与者,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实践自己崇高而神圣的艺术理想。他们的艺术构思带有高度自觉的政治使命意识,追求“客观”表现时代重大的政治背景,生动展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充分肯定阶级斗争的现实意义。如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表现的是上海“五卅运动”的宏大场面,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表现的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雄伟壮举;而叶紫的《丰收》、《火》和蒲风的《茫茫夜》,则是描写农民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农村革命风潮。这些题材都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中心工作保持着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在早期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创作中,他们已经开始注重新型革命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塑造和典范意义推广,如蒋光慈笔下的李尚志(《冲出云围的月亮》)、胡也频笔下的施洵白(《到莫斯科去》)和叶紫笔下的刘翁妈(《向导》)等,他们已不再是“五四”时代的愚民庸众式的社会公众形象,而是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素质——出身贫寒苦大仇深且具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力量;他们自愿接受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都具有崇高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阶级立场;他们的理想奋斗目标十分明确,并为此而勇于献身自我牺牲。这些理想主义色彩极浓、精神境界高尚的艺术形象,基本上确立了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英雄史诗的完美法则。与此同时,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本人虽然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他们却自觉地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反复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似乎以此来表明自己已经获得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因此在他们的笔下,知识分子明显被置于游离社会革命中心的边缘地带,他们(如《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的白华、《二月》中的陶岚和肖涧秋等)思想上虽然也具有向往革命的主观要求,但是生性喜好空谈,情感十分脆弱,他们不可能成为当然的革命者;必须让他们经过挫折与磨难(个人英雄主义神话的破灭)并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启蒙和精神洗礼(在作品中体现为共产党人的耐心启发教育),才能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因此,在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艺术画廊里,知识分子假若未被明确其无产阶级的政治身分,原则上只能是作为工农革命英雄形象的衬托而存在。左翼革命作家的创作,尽管忠实地贯彻了革命现实主义“反映论”文学观的指导思想;但他们作品所表现出的“革命+恋爱”式的浪漫主义审美倾向,又同时受到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严厉批评。“左联”内部的批评意见尤为尖锐激烈。按照常理,左翼人士本不应该对自家阵营所发生的“革命的浪漫谛克”进行责难,因为它毕竟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理论在中国最早的艺术实践。当人们纷纷去严厉指责它“把现实的残酷的革命斗争神秘化,理想化,简单化,公式化,抽象化,甚至庸俗化”,并认为它在政治上与艺术上都表现得极为幼稚和不成熟时[1],我觉得左翼批评家的理论基点,大体上是在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思维方式:“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理念,而“恋爱”则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情调,两者之间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左翼理论家一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不是不能去描写“恋爱”,而是他们必须正确区分知识分子个人的“恋爱”与无产阶级群体的“革命”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主从关系;如果过分张扬个人情感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势必会从客观上误导广大读者对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理解和对阶级斗争残酷性的认识。这恐怕才是左翼人士对“革命的浪漫谛克”批评指责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解放区文学是“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合理的发展,同时也是主流价值观的一种区域性的全面实践。它不仅全面强化了文学对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绝对依从关系,而且还以其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解放区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行政区域,它所实行的制度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那么它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要求,自然要比“左联”时期更为强烈并且具有更大的现实背景和自由空间。解放区的本土作家(如赵树理、李季、孙犁、柳青等)以其对于革命文学的质朴理解,率先在创作实践方面进行了一种作家与革命全面对话的艺术试验;与此同时,深受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影响的大量左翼作家(如丁玲、萧军、周立波、草明等人)也纷纷投奔解放区,他们在经过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无论是主动的或被动的)之后,则从质量和数量上大大加强了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基本队伍。因此,解放区文学与左翼革命文学相比较,已呈现出以下明显不同的特点。
首先,解放区文学的创作立足点,已由左翼革命文学时代主要反映大都市中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完全转向了对农村土地革命斗争的生动描绘和艺术再现,开启了农民作为革命文学绝对表现主体的历史新纪元。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柳青的《土地的儿子》、袁静与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与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作品,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杰出产物。解放区作家不同于左翼革命作家,他们不是简单肤浅地表现农民群体不甘忍受屈辱的盲动造反意识;而是深刻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中国农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生动展示了农民——尤其是新一代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和革命热情的高涨,以及他们奋起反抗恶霸地主和反动势力的剥削压迫,自觉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并成为其中坚力量的历史必然性。毫无疑问,解放区作家对于农村生活题材的重视,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关。毛泽东反复强调革命的文学艺术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并将其视为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问题。然而,由于20世纪中期的中国社会,现代工业文明极不发达,产业工人极少。解放区就更不用说了。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44年为止,陕甘宁边区只有小工厂102个,从业工人7388人,且他们都是些小手工业生产者,基本上是由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化而来,并未彻底改变他们原有的农民属性。[2]而“兵”的主体成分(尽管毛泽东对士兵所隶属的不同阶级集团,使用“革命”和“反革命”的修饰语来加以区分)只不过是农民的一种特殊角色的临时转换,用毛泽东的原话来说,就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因此,“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在创作实践中主要成为了文艺为农民大众服务。解放区作家对于农民题材所表现出来的群体创作热情,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主流价值观在中国现代文学发育过程中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审美导向作用。
其次,解放区文学创作也推崇革命的英雄主义,注重革命英雄形象的典型示范效应。但与左翼革命文学因缺乏真实革命斗争的生活体验,只能以主观理念去凭空创造理想化的完美英雄人物有所不同;解放区的本土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工作在革命一线的基层干部,他们往往从自己所亲见亲闻的现实生活入手,去发掘普通人物身上存在的英雄素质,追求革命英雄主义理想的阶级群体化行为。在解放区作家的笔下,英雄人物的思想品质是完全相同的,但按其职业分工大致可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基层干部,如《李家庄的变迁》中的铁锁、《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高乾大》中的高生亮、《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的张裕民、《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种谷记》中的王加扶等,他们有着复杂的人生阅历:全都是贫苦农民出身,饱受反动地主的压迫和欺侮,在黑暗的旧社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参加革命以后,接受了党的教育,开阔了自己的政治视野;他们忠诚党的革命事业,焕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积极献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有的根本就没有文化),但却能够很好地掌握贯彻党的农村政策,完成自己所承担的政治使命;无论遇到什么紧急危难,他们总是能够以坚忍不拔的超凡精神力挽狂澜,带领人民群众走向胜利。另一类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如《洋铁桶的故事》中的吴贵、《吕梁英雄传》中的雷石柱和孟二楞、《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腹地》中的辛大刚、《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王贵与李香香》中的王贵、《一颗未出枪膛的子弹》中的红军小战士等艺术形象,他们也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虽然年轻但英勇无比足智多谋,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一个令人感叹的动人故事:或来无影去无踪神机妙算把敌人打得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如吴贵、雷石柱、牛大水、郭全海),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面无惧色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如孟二楞、王贵),或大智大勇聪明过人以一当百神奇解难最后转败为胜(如辛大刚、红军小战士)。在解放区作家的笔下,无论是党的基层干部还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都是他们不折不扣地贯彻《讲话》精神,逼近革命斗争实际,亲身体验现实生活并把思想的立足点移到农民立场上的实际行动的具体表现。他们所塑造的这些艺术典型,在火热的革命战争年代,客观上以其艺术宣传的社会示范作用对于无产阶级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从解放区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那些原本就是些普普通通的农民被升华为完美的革命英雄形象之后,他们身上所承袭的传统文化的种种致命弱点明显地被人为地加以削弱和淡化,而他们思想上所人为附加的革命优良素质和现代性前卫意识则被极大地提高与强化。与此相反,知识分子几乎被解放区作家完全排除在革命英雄的表现群体之外,即使偶尔涉及也是作为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的工作组长文采);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仅仅是以其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落后性,去衬托农民英雄形象精神境界的高远。
再者,解放区文学创作以其强烈的理想主义浪漫色彩,向世人昭示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审美风格的日臻成熟。与左翼革命文学的感伤浪漫主义倾向完全不同,解放区文学以一种健康活泼、乐观向上的激扬格调,生动表现了根据地人民崭新的精神生活面貌和思想道德情操。解放区文学的理想主义浪漫色彩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和坚实的生活基础:革命根据地的全新景象与国统区的黑暗现实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为广大革命作家描写未来新生活提供了极其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另外,革命现实主义“反映论”文学观的审美原则,又使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去创造艺术感觉的主观真实。因此,生活的原有状态已不再是他们主要关注的创作焦点,而历史的必然性和未来的可能性才是他们真正的艺术追求。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支配之下,解放区作家对于浪漫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孙犁就公开指出:“今天要不要浪漫主义的渲染?在我们有了基础,有了技术,同时又有适合浪漫主义的题材是可以的。当然,我们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浪漫主义,我们渲染的目的是要加强人民的战斗意志。浪漫主义适合于战斗的时代,英雄的时代。这种时代,生活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3]孙犁的观点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可以说是对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度总结。主流价值观在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的成功实践,仅就40年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而言,它无疑是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因为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讲,革命战争需要英雄主义的精神理念作为坚强的支撑,解放区文学正是以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反映了这种革命时代的政治要求。另外从文学自身的意义而言,“五四”以来中国作家一直都是在以人文主义的启蒙精神,集中精力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意识进行批判和否定,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文坛呈现出一派压抑和沉闷的悲凉气氛,同时也使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十分单调;解放区文学所表现出的清新质朴乐观向上的浪漫主义文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艺术追求的丰富多样性。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公正的学术立场上,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建国以后的新中国文学则完全不同。新中国文学虽然从题材、主题、表现方法诸方面都全面继承并拓宽发展了解放区文学的创作路子,但当它最终彻底清除了文学上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并将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发展到了绝对极端化的地步时,也便逐渐走向了僵化。
新中国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合理发展和纵向延伸。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新中国作家,他们对主流价值观已不再存有任何怀疑。艺术“工具论”的思想此时完全征服了整个中国文坛,文学创作的政治话语模式也基本形成。新中国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英雄史诗的艺术建构;所以描写革命战争和革命英雄主义题材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表现出异常的繁荣。这是由于建国以后,人们已经渐渐地远离了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胜利者一方面出于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需要后代铭记他们开国建业的丰功伟绩,因此新中国文学创作就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维系历史与现实对话的新的历史使命。如梁斌的《红旗谱》、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峻青的《黎明的河边》、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铁击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的《苦菜花》、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作品,表现的都是革命英雄主义的传奇故事,他们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尽情地讴歌了时代胜利者的主观意志。从表面上来看,这些英雄传奇与解放区文学的英雄传奇并无质的差别;但解放区文学英雄理想主义的动机,只是追求一种鼓舞革命斗志的形象化艺术;而新中国文学英雄史诗体系的建立,则是要以一种艺术形象化的形式来创造和凝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历史。正是出于巩固新政权的政治需要,新中国文学作家以其对革命纯正虔诚的信仰,极力去表现革命英雄从落后农民到革命战士再到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家的人生成长道路,尽可能将他们的思想道德品格塑造得完美无缺(《红旗谱》在演绎朱老忠革命人生的发展历程时,便是遵循这样的创作思路),并使革命英雄的艺术形象也由平民的“传奇”发展到了阶级的“神话”(《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就是现代英雄神话传奇氛围中最成功的典型范例),直至最后变成了令人仰望的完美圣人。以“反思”极左思潮起家的新时期文学,似乎并没有完全消解革命英雄主义的传奇神话,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陆天民的《苍天在上》等作品,主旋律文学所精心创造出来的种种清官形象,都是革命英雄史诗建构的现代表现形式。不同的只是革命英雄已不再是新时期文学艺术表现的惟一形象主体,个人主义英雄和民族主义英雄题材的作品也大量涌现(如莫言的《红高粱》、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的寓言》等)。如果我们将新中国文学史诗建构的本质还原为是对现代农民革命的历史复述,它自然是属于一种历史的过去时态;而对于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强烈关注,则必然成为摆在广大作家面前的全新课题。建国后30年的文学,从充分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地位的认知基础出发,也极力展现他们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全国推动作用。作家们按照自己对于农民思想境界的主观理解,刻意去表现翻身得解放后的中国农民自觉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伟大壮举。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陈登科的《风雷》、胡正的《汾水长流》、李准的《李双双小传》、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作品,都曾在五六十年代产生过极其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些作品赋予了农民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性格淳朴敦厚,思想完美无缺,不仅是党的方针路线的热烈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并且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走集体合作化的道路才是农民摆脱贫困最根本的出路。从梁生宝、刘雨生到萧长青和高大全,作家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新中国的农民已彻底地诀别了传统农民的落后形态,他们作为“党的忠实儿子”,身上都凝聚着“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纵观建国后30年的文学创作,就其总体特征而言,它的政治导向意义要远大于它的艺术审美意义,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一直到了新时期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问世,农民的思想完美人格和现代前卫意识的革命神话才被彻底打破,“五四”时期启蒙教育农民的落后意识,探索农民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无法割裂的内在血缘关系的文学创作主题,也开始重新受到广大作家的高度重视。
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农民革命英雄史诗的同时,我们自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现象:在建国后30年的文学创作中,真正从正面去描写知识分子主题的作品总共只有两部,一部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一部是汉水的《勇往直前》。前者往往被划入革命历史题材的范围,而后者又十分不成熟,几乎可以说是个艺术表现的空白点。《青春之歌》能以其题材的惟一性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红色经典作品之列,也许多少能给我们一些必要的启示。杨沫本人是一个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她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知识分子的叛逆形象。《青春之歌》的故事题材本身并无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基本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个性解放创作母题的自然延续;但杨沫却将林道静置放于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变迁的大环境中,去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怎样经过痛苦的抉择,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艰难思想历程。值得注意的是杨沫通过对林道静世界观转变的清晰描绘,自觉地将知识分子革命意识的获得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启蒙联系在一起,全面反映了集体理性意识对个性独立意识的彻底征服。杨沫和林道静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追求应该说是绝对真诚的,人们不必因对政治抱有极端厌恶的心理而去对其严加斥责。但一部《青春之歌》的客观政治效应,也使启蒙主义者和被启蒙主义者的社会位置发生了根本的变异。直到新时期文学人文精神的全面复苏,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才又重新得到社会的正面认识与公正评价。尤其是徐迟的《歌德巴赫的猜想》和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以沉重压抑的笔调书写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悲剧性命运,以及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攻克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的顽强拼搏精神,终于使人们明白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应具有的历史地位。新时期文学对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重新确立与理解,是与对农民英雄神话的深层次解构同时进行的。宽泛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与狭隘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撞击交流,大大消解了官方文学一统当代中国文坛的原有能力;文学艺术思维的空前解放,则直接促进了新时期文学多样化局面的形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系,最终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还原为文学多样性精神生态领域中的一种价值观念形态,并在中国文坛上重新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合理的生存空间。
〔收稿日期〕2001-05-25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论文; 青春之歌论文; 暴风骤雨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