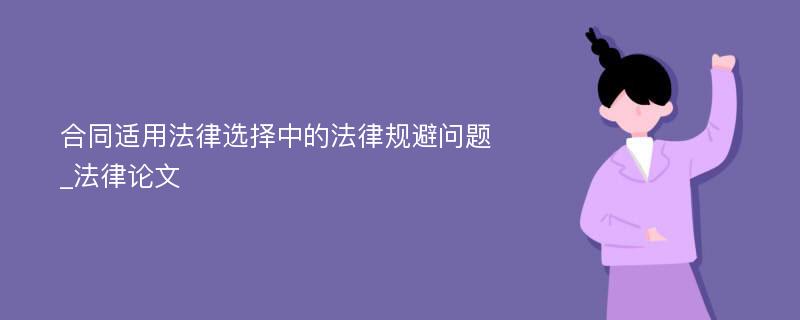
合同准据法选择中的法律规避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同论文,法律论文,准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注:在美国冲突法上,这个问题被表述为”对选法自由的限制。在美国法上,“规避”(escape)一词一般用于描述法院对传统法律选择规则的规避,主要包括:定性(characterization),程序问题与实质问题之区分,外国法的定性(法律或事实),反致(renvoi),公法与私法之区分,以及公共政策保留(public policy)。)是指当事人有意规避本应适用之法律的行为。反对法律规避的观点认为,当事人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之行为不应得到承认。在合同法领域,其表现就是否定合同当事人有选择支配其合同之准据法的完全自由。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合同当事人选择了一个与其合同没有明显联系的法律作为准据法,那么这种选择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避作为一种现象确实存在于合同法领域。问题在于,法律规避能否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于合同法律冲突规则之中?
一、法律规避与意思自治
法律规避现象存在的首要前提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主要(但不是唯一)体现在合同法领域,其含义是合同当事人有权选择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来支配其合同关系。(注:黄进、刘卫翔:《当代国际私法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只有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接受意思自治原则的前提下,法律规避现象才得以存在。
有人批评,正是承认意思自治原则才为当事人规避法律提供了方便。(注:引自王军、陈洪武:《国际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法律规避现象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关系由此可见。
无论对此问题有何争议,意思自治原则在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林提出后已逐渐在各主要国家得以确立,这是无疑的事实。中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现已废止)第5条、《海商法》第269条和《合同法》第126条就是显著的例证。(注:《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第1款: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海商法》第269条: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法律)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其他主要国家也是这样,例如1865年和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1898年日本《法例》,1946年《希腊民法典》等。在司法实践上,英国1760年Robinson诉Bland案,美国1875年Wayman诉Sourthard案,(注:韩德培:《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法国1910年的判决(注:董立坤:《国际私法论》,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页。)等都确立了意思自治原则。一些重要国际条约也接受了这一原则,例如1965年《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的公约》,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1985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注:丁伟、陈治东:《冲突法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对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已经有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因而本文不再就此展开,只需指出,当事人意思自治已经成为合同准据法选择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项原则。(注:董立坤:《国际私法论》,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页。)
然而,尽管法律规避存在于意思自治这一前提之下,但在承认无限制意思自治原则的国家,这一问题并不存在。这在英国最为明显。英国冲突法理论和判例一般不承认对当事人自治的限制,(注:丁伟、陈治东:《冲突法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因而在英国冲突法上没有法律规避一说(尽管他们借助其他方式来达到相似的目的)。(注:韩德培:《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因此,法律规避问题仅存在于有限度地承认意思自治原则这一前提下,也就是说,有关国家法律承认当事人有选择合同准据法的权利,但对之施加一定的限制。因此,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是法律规避问题的另一个存在前提。
对意思自治的首要限制来自包括杜摩林在内的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即当事人自治只限于任意性法律规范,强制性规范不在其内。(注:李双元、金彭年:《中国国际私法》,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例如中国法律关于特定范围合同准据法的规定,法国民法典关于警察与治安,不动产以及身份与能力的法律。这种限制一般得到认可,并体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立法中。但是,它是否属于法律规避制度的调整对象则是有疑问的,尽管有些国家的法律(例如法国民法典)对这种限制用了“规避”一词。事实上,将这种限制作为一种独立的规则更为适当。把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律规避制度的范围过于扩大没有意义,因为广义上的法律规避显然是不正当的。
除此之外,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还体现在以下规则之中:当事人的选择不得抵触公共秩序;当事人所选择的只能是有关国家内国法,而不可选择外国的冲突法和程序法;所涉及的合同必须是“涉外”合同,等等。这些限制普遍存在于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当中,而且可以认为都是合理的。
二、“实质联系”要求下的法律规避问题
但是,本文所讨论的法律规避并不是在这些方面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与本文所讨论的法律规避有密切联系的是对意思自治的另一种限制。这就是在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法律(注:美国判例通常认为应有实质联系要求。表述各异,包括但不限于:实质关联(substantial nexus),真实而非虚构的联系(real and not a mere fictitious connection),关键事件(vital element),真实关系(real relation),重大事件(significant events),重要联系(material connection),正常关系(normalrelation),合理关系或实质联系(a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or substantial connection),真实或实质联系(a real or substantial connection)。)在传统上所认为的,合同准据法必须与合同有一定的联系。(注:[德]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598页。)
日本学者折茂丰认为,对准据法的选择应有三种限制,其中之一就是“实际联系”。(注:丁伟、陈治东:《冲突法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欧陆法系的国际私法理论认为,当事人只能使其契约受同它有内部联系的法律支配。(注:[德]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598页。)根据马丁·沃尔夫的举例,在英格兰有住所的两个英格兰人在法国旅行时订立契约,并以纽约为履约地。他们可以选择英格兰法,法国法,纽约法,但不能选择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的法律。(注:[德]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598页。)
波兰1926年《国际私法法典》规定:“契约债权依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但所选择的法律与该法律关系应有一定的联系。”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当事人可以任意选择合同准据法,但交易必须与所选择之法律有“合理联系”。但这种限制并非绝对。如果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并不违反“应该的准据法”中的强行法规范,那么当事人选择的法律通常会被承认。(注:[德]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598页。)1990年的一个有名案例中,(注:De Santis v.Wackenhut Corporation,Supreme Court of Texas,1990.793 S.W.2d 670,On Motion for Rehearing.)法官指出,当事人不得选择与交易或当事人没有关联的法律。
相反,英国对这种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理论持反对意见。(注:李双元、金彭年:《中国国际私法》,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有人认为英国在维他公司诉乌那斯轮船公司一案中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施加了限制,(注:李双元:《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但从法律规避的角度而言,该案没有什么指导意义。该案法官所提出的三个限制任意选法的标准分别是善意、合法、无规避公共政策。“善意”标准由法官判定,且极具模糊性。更重要的是,在英国法中,单纯的避法行为并不构成恶意。(注:丁伟、陈治东:《冲突法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合法”与否也并不属于法律规避制度的范围,况且法律规避行为一般在任何环节上都是合法的。“无规避公共政策”更是可以归属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尽管有种种争论,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对选择法律的各种限制逐渐放松,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正受到更多的尊重。(注:董立坤:《国际私法学》,中央电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在美国,趋势是给予更多的选法自由。(注:Eugene F.Scoles,Peter Hay,Patrick J.Borchers,Symeon C.Symeonides,Conflict of Laws,3rd ed.,p.872.)《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在完全抛弃“联系要求”和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要求实质联系)之间采取了中间路线。根据这部法典,法院应对非强行性法律与强行性法律做分别处理。对于前者,例如合同解释,条件,履约的完备与否,不履约的免责等,(注:The Second Restatement,§ 187,comment c.)重述并不要求地理上的联系和其他任何限定。(注:The Second Restatement,§ 187(1).)对于第二类问题,则有实质联系的要求。(注:The Second Restatement,§ 187(2)(a).)然而,即使是对于这一类问题,当所选择的法律与合同没有实质联系时,法律选择条款也不是绝对无效。如果有”其他合理理由”,这类”缺乏”可以被治愈。例如,在海事合同中,如果相关国家均为法制极其落后或者完全缺乏完备法律时,当事人选择一个毫无关联的法律,即满足了“合理理由”之要求。(注:The Second Restatement,§ 187 comment f.)
即便如此,仍有学者提出疑问:(注:Roger C.Cramton,David P.Currie,Herma Hill Kay,Larry Kramer,Conflict of Laws,Cases-Comments-Questions,5th ed.,p.106.)如果为当事人法律选择条款赋予效力的原因是确定性和可预见性,那么为什么这个法律必须被限于具有”实质联系”的法律?什么样的联系是”实质”联系?换言之,”实质联系”要求会否被法院操纵?或者,这个要求是否造成了不便和高成本?例如,Citicorp一个银行控股公司,本来位于纽约,但是宣布转移至南达科他州,因为该州的高利贷法规允许24%的利息合法。这样,该公司在以后的合同中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选择对它有利的南达科他州法律。显然,最保守的法院也承认实质联系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这里,如果该公司不转移总部,仅仅在南达科他州设立分公司,实质联系要求是否被满足就无法预见。一个保守的法官可能会认为实质联系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问题在于:仅仅为了满足这个实质联系的要求,就导致公司迁移这个成本高昂的举动,是否真的符合社会利益?(注:New York Times,March 27,1980,p.D15.)美国《统一商法典》现行版本规定了合理联系reasonable relationship要求。(注:UCC § 1-105.)而讨论中的1997年修订草案第一章则规定:法律选择条款应视为合法,无论交易与所选择的国家或州是否有合理关系。唯一例外是对消费者的保护。(注:UCC § 1-302(a),(b)(1997 Draft Revision).)
此外,美国纽约州《通用债务法》(General Obligations Law)第5-1401条规定,任何合同中选择纽约州法律均为有效,无论该合同与纽约州有无地理上的联系,也无论该合同为何性质。该法的目的是,便利当事人选择一个成熟的商业法律体系,一个有经验的司法制度,并加强纽约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地位。(注:Eugene F.Scoles,Peter Hay,Patrick J.Borchers,Symeon C.Symeonides,Conflict of Laws,3rd ed.,p.872.)
在欧洲《罗马公约》中,除了极为有限的例外(注:消费者保护,雇工保护,法院地和第三国强制法规,以及公共政策。)以外,甚至连合同的国际性都不是必要的因素。
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根据中国《海商法》和新颁布《合同法》的规定,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并无“一定联系”之类的限制。
三、法律规避的特征、构成和效力
合同准据法选择中的法律规避是指当事人为选择于己有利的法律而采用制造或改变连结点构成事实的方式,使按本应适用的法律为无效的条款成为有效。(注:韩德培:《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可以看出,冲突法上的法律规避所采用的规避手段是其最主要特征。
在合同行为方面,当事人为实施法律规避而改变连接点构成事实往往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国籍或住所;改变行为地(缔约地);变更物之所在地等。因为在要求合同与准据法有一定联系的国家,“内在联系”无非体现在不同的连接点构成事实上。例如波兰1926年《民法典》列举了合同成立地,合同履行地,契约标的物所在地,当事人国籍和住所地作为具有内在联系的标志。(注:[德]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599页。)
在成立要件方面,不论是否接受法律规避论,学者们通常认为法律规避现象是存在的。但对法律规避行为的构成要件却各有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法律规避应有如下三个构成要件,第一,主观上的故意;第二,规避的对象是本应适用的法律;第三,行为方式上,当事人改变连接点构成事实。此外,有些学者认为,法律规避的另一构成要件是,如果采用改变国籍或住所的方式规避法律,那么规避者达到目的后应必须回到原先的国籍国或住所。(注:钱骅:《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这的确是一个通常的现象,但能否作为法律规避的一个构成要件则并无一致的看法,多数学者在其论著中没有提及。此外,规避的对象是否包括外国的法律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注:李双元:《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对于法律规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有两种对立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法律规避是适法性行为。在这一学说看来,法律规避行为虽有自私目的,但与一般国家承认的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试用法律没有区别。法律规避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种表现,故而应为合法;如果认为法律规避违法,就必须证明当事人有以欺诈逃避内国法之意图,否则难与通常情况下改变连结点构成事实加以区别。而这种证明是困难的,故不如承认其为适法,以减少诉源,避免争执;如果认为法律规避违法,就会对当事人之行为及结果予以否认和制裁,不利于稳定既有关系,也易引起国际纠纷。(注:[台]国际私法研究会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国际私法论文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8页。)
萨维尼等学者认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与国内实体法上的避法行为是两回事。由于双边冲突规范承认可以适用内国法,也可以适用外国法,那么内国人为使依内国法上不得成立的法律关系得以成立而前往一个允许成立此种法律关系的外国,设置一个连接点,使它得以成立,这并未逾越冲突法所容许的范围,故不应视为违法行为;其次,处理什么法律关系用何种连接因素,是基于客观情况,即使当事人为某一目的而改变连接因素,也并不与冲突法抵触。(注:[台]刘甲一:《国际私法》,转引自李双元《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第二种主张认为法律规避行为是不适法行为,理由是:法律规避行为源于国内法上的脱法行为,后者既然被认为违法,前者也不应例外;强行法如被人以欺诈方式规避并因而成立法律关系,等于是鼓励人人欺诈,不应加以承认;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表面上虽然不违法,但破坏了法律秩序,无异于直接违反内国法的规定;认定法律规避为违法,则可树立内国法律之尊严,使人不致萌生欺诈之意图。(注:[台]国际私法研究会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国际私法论文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8页。)
与法律规避的合法性问题相应,对于法律规避行为有无法律效力历来也有不同的观点。
主张绝对无效者认为,根据“欺诈毁灭一切”的原则,改变或制造连结点构成事实之行为以及从新隶属关系中取得利益之行为一概无效。以婚姻法为例,以改变国籍取得离婚判决者,不仅离婚无效,新国籍同样无效。主张相对无效者认为规避法律并非当然无效,只有在违背内国立法目的时方始无效。主张相对有效者则认为规避法律行为的效力是相对的,仅限于改变连结点构成事实的行为,而不及于其他行为。换言之,当事人追求的目的无效,但是对于连结点构成事实的变更应该予以承认。(注:[台]国际私法研究会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国际私法论文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4页。)
四、法律规避与公共秩序保留
由于法律规避制度的作用首先是维护国内法的优先适用,而实际上可以“用同样的措辞来说明公共秩序的作用”,(注:[法]H·巴迪福、P·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15页。)因此,许多人指出,法律规避只是公共秩序保留的一种特殊情况。(注:[法]H·巴迪福、P·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15页。)而在英美法上,公共秩序是法律规避之一种。当然,此处的“法律规避”完全不同于本文所讨论的法律规避。
在法律规避论成立的前提下,对于其究竟是独立制度还是属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范畴,看来存在不同的意见。梅希奥(Melchior)等认为法律规避与公共秩序保留是一回事,而巴迪福等则认为法律规避是一个独立问题。(注:李双元:《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公共秩序保留理论由萨维尼首先提出。在其《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他认为某法律关系之本座如果属于外国法域,那么原则上应适用该外国法律决定该法律关系。但有两种绝对之例外,其一是专为权利人制定之强行法,例如依年龄而限制行为能力;其二是有关政治,公安等“公共利益”的强行法,如禁止买卖奴隶之合同等。(注:[台]苏远成:《国际私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5页。)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与法律规避制度一样,确有扩大本国法适用范围的作用。从两种制度的适用结果上看,也有共通之处,即法院在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之后一般都是适用本国法律。
然而,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首先,两者产生的原因不同。法律规避是当事人故意的行为,而公共秩序保留是法院拒绝适用外国法的结果,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其次,由于法律规避的目的是逃避本应适用的法律,因此在有些国家的法律看来具有违法性,而公共秩序保留是法院行为,在任何国家的国内法上都是正当或必要的,就当事人而言也不存在违法与否的问题。在结果上,有些主张法律规避无效的国家不仅认为规避法律的行为无效,甚至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而公共秩序保留与当事人的责任无关。(注:丁伟、陈治东:《冲突法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五、中国法律上的法律规避问题
中国法律对当事人法律选择的规范体现在两部法律当中,一是《合同法》,二是《海商法》。原先《涉外经济合同法》对于法律选择问题也有所规范,但是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这部法律已经没有效力。这几部法律都认可当事人按其意思选择支配其合同关系的法律,而且没有任何“一定联系”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可以认为我国法律一般地不认可法律规避行为,但这里的“法律规避”有其特定含义,即“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根据本文预设的前提,法律规避问题的范围并不包括这一类行为。
概括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特定范围的合同必须适用中国法律。这是指中外当事人为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为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而订立的合同;第二,合同必须是涉外的,纯粹的国内合同不得适用选法自由的原则;第三,合同中法律选择不得与中国公共秩序相抵触;第四,不得排除中国强行法规范的适用;第五,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必须是内国法,而非冲突法规范和程序法。(注:以上内容中的第一、二项见《合同法》第126条。其余内容见《涉外经济合同法》有关条文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项的(三)(五)。)
根据以上规定,当事人如果规避这些方面的法律,其法律选择条款将被排除适用。可以看出,以制造连接点构成事实的方式所为的法律规避在中国法律上不是一个问题;换言之,中国法律所禁止的法律规避并不包括以制造或改变连接点构成事实的方式所为的行为。
中国法律在涉外合同法律选择方面明确禁止的若干法律规避行为之中,关于强行法规范不得规避的规定从可行性方面值得一提。这一规定能否得以实施,或说这一规定是否可能被规避,将取决于管辖权问题。关于合同的纠纷是否在中国提起诉讼,即中国法院有无管辖权,将决定有关法律选择条款的效力。如果是在外国法院提起诉讼,则要看该国法律是否同时禁止当事人规避外国的法律。例如,阿根廷《民法典》规定,在阿根廷缔结的以规避外国法为目的的合同无效。其次,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在若干法律中(包括履行地法和合同准据法)只要有一个承认法律选择条款的有效性,该国法院就会接受这一法律的规定。因此,如果合同诉讼在外国法院提起,那么在合同履行地位于外国或合同准据法是外国法的情况下,中国法律的这条规定能否发挥作用就取决于相关外国法律的规定。
同样,公认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事实上也一般是在法院地国家发挥作用。违反中国公共秩序的合同条款在外国能否真正被禁止,取决于该外国法律是否认为违反其他国家公共秩序的法律选择条款在该外国应被排除适用。当然,这也同样首先取决于管辖法院。
六、法律规避制度的合理性辨析
在合同准据法选择上的意思自治本身就是一种法律规避行为——规避不利于自身的法律,其功能是使当事人双方通过选择有利法律之方式更好地调整权利义务关系。这种趋利避害的目的只有通过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才能达到。“一定联系”的要求对这种选择施加了限制,因而是不合理的。合同当事人一方面要实现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遵从“一定联系”的要求,唯一的答案就是制造或变更连接点构成事实。因此,“一定联系”这类形式化要求必然使当事人利用这种形式,即采用人为制造或变更这种“联系”的方式使合同有效或达到特定的效力,而法律规避制度则使这种努力受挫。(注:关于这方面的例证,见New York Times,March 27,1980,p.D15.)这不能不使人们对法律规避制度的合理性提出疑问。正如美国学者所疑虑的:既然意思自治的目的是使确定性与可预见性得以保障,是否有必要要求合同与所适用的法律在地理上必须有联系?(注:Roger C.Cramton,David P.Currie,Herma Hill Kay,Larry Kramer,Conflict of Laws,Cases-Comments-Questions,5th ed.,p.106.)
从下面的例证可以看出法律规避制度的荒谬性。
设想一个甲国公民长期生活在国外。他在外国与人订立合同并约定以甲国法律为准据法。除他的国籍外,该合同没有任何甲国因素。可以肯定,只要不违反法院地国公共秩序,在任何情况下这一法律选择都会被认为合法。我们的问题是,既然没有违反公共秩序和强行法规范,国籍这一因素真的那么重要吗?
另一个重要的连结点构成因素是缔约地。如果合同缔结地是甲国,那么当事人选择甲国法律为其合同准据法一般而言为合法。设想两种情况:第一,合同当事人双方在甲国旅行时偶然相遇并在此订立合同。除此之外,该合同与甲国没有任何联系;第二,合同当事人双方因了解甲国法律并欲使其成为准据法,但由于合同关系中没有任何甲国因素,因此专程到甲国并在那里订立合同。在法律规避制度下,前者合法而后者非法。两种不同待遇是否合理?区别有意还是无意造成连结点的意义何在?
因此,尽管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论有种种之理由,但有更充分的理由对法律规避制度在合同法领域中的合理性提出疑问。
就“实质联系”要求的适用范围而言,合同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尤其是与侵权法制度之间,在法律冲突和选择方面存在巨大的区别。侵权行为的当事人不存在什么”合理预期”,因此也就不存在对这种预期的保护。因此,法律选择过程需要考虑的就是适用法律选择及其过程的说服力: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另一个相关国家的法律?在法定(而不是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时,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侵权行为中,一方当事人的”得”,就是另一方当事人的”失”。法官必须面对外部世界,面对当事人,尤其是面对败诉的当事人:”你为什么败诉?你根据什么法律败诉?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适用这个而不是那个国家的法律?”在这里,连接点(即”实质联系”要求的具体化)事实上就是这样一种依据,一种提供说服力的东西。实质联系(”最密切联系”则更为理想)要求的满足也就提供了这种说服力。相反,在合同交易(注意,不是合同诉讼)中,尤其是在当事人自行缔结了法律选择条款的合同中,存在一个强烈的使交易有效的预期,这种预期只能通过认定合同有效来达致。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尽量承认当事人的选择,包括对适用法律的选择。在双方当事人都希望合同(及交易)有效的情况下,法官(以及法官背后的国家)不必提供当事人根本不需要的说服力。既然如此,以”说服力”为目的的”联系”要求(无论是实质联系还是最密切联系)也就没有了说服力,它真正可以做到的,无非是毫无理由地增加当事人的缔约成本,以及满足某些虚幻的”集体利益”。(注:例如,美国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的主导人Beale教授和著名法官Learned Hand就反对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认为这是把国家立法权授予私人。见Beale,What Law Governs the Validity of a Contract,23 Harv.L.Rev.260,260-61(1910);Learned Hand in E.Gerli & Co.v.Cunard S.S.Co.,48 F.2d 115,117(2d Cir.1931).)
就合同冲突法本身而言:
首先,从法律规避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关系上而言,如果法律规避制度是为了排除外国法的适用,那么它就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重叠。由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可以发挥法律规避制度所能发挥的全部功能,(注:关于以公共秩序保留手段来控制滥用选法自由,见Ehrenzweig,Conflict of Laws 469 (1962);2 Rabel,The conflict of laws:a Comparative Study,357(1947).)而法律规避制度却不能发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某些作用,例如,在当事人并非通过规避法律的手段选择适用外国法时,法律规避制度便无从发挥作用,因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完全可以取代法律规避制度。
其次,禁止当事人通过改变连结点构成事实的方式来规避法律是不合理的。其一,在私法领域,当事人有权为法无禁止之行为,而法律规避论无疑有违此原则。其二,既然合同当事人为达到目的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就难以得出其结果非法的结论。在法律规避相对有效一说中,当事人改变连结点构成因素被承认,但基于这一行为的结果却不被承认。尽管这是一个奇怪的结果,但也只能如此,因为另外两个学说会造成更不合理的结果。既然如此,何不直接承认法律规避行为的适法性?其三,既然同意意思自治从而承认合同当事人有选择准据法之自由,就等于是接受当事人有权规避法律的事实,因为国际私法的本质就决定了应该承认当事人有权选择或排除特定法律,换言之,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准据法本身就是法律规避的过程。
再次,法律规避制度可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后果。如果依据法律规避制度导致选法行为无效,法官就承担起选法任务,这导致社会成本增加,其结果也不一定让当事人满意,而且破坏了既定的社会关系,并使“尽量有利于法律关系成立”的原则无从运用。
第四,从可能性方面而言,判断当事人某一行为的主观意图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适当的。一方面,可以确定法律规避制度的目的不可能是为了排除外国法适用本身,否则整个国际私法体系就没有必要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律规避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外国法适用所造成的结果,那么也可以确定这一目的是不容易达到的。如果当事人认为某一国家法律体系具有先进,完备,公正和中立的优点,并因而选之为准据法,这一动机便无可非议,即使所选之法律与合同没有表面上的联系。如果因缺乏联系而判定选法无效,那么当事人可以稍加努力将某一法律内容变成合同条款,同样使禁止法律规避的条文无效。因此,法律规避制度实际上无法禁止当事人选择外国法律,它所能够禁止的是合同当事人节省缔约成本的努力。
最后,管辖权因素可能导致任何一个国家禁止法律规避的法律失去实效。在某一个国家属于法律规避制度所禁止的规避行为并非在任何国家都是被禁止的。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尽量使合同有效”的原则出发,在任何相关国家法律承认合同或合同条款(包括法律选择条款)有效的情况下,会宣布承认该法律,进而承认合同或合同条款有效。如果管辖法院所在国家不是那些禁止法律规避的国家,这一可能更加明显。
法律规避现象来自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即“一定联系”之类的要求),因此可以认为,一旦消除了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也就消灭了法律规避现象,这也是最根本、最合理的消灭法律规避现象的方式。如果在对意思自治原则仍然有限制的前提下去试图消灭法律规避现象,那么随着法律规避现象一起被消灭的可能是当事人节省缔约成本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交易的安全。
七、结论
如果把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问题严格限于涉外合同当事人为满足法律对其选择的准据法与合同必须有“一定联系”的要求而制造或变更连接点构成事实的行为,那么结论就是:法律规避作为一种制度在合同法领域没有充足的存在理由。根据以上分析,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它可能导致不合理的结果,而且能否象设计者所预想的那样达到避免法律规避行为的目的也令人怀疑。毕竟,合同法的本质和演化历程都表明当事人的选择应被尊重,合同法的发展趋势则是扩大当事人的自治范围,而法律规避制度则反其道而行之。未来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尤其是司法实践中,对此应给予慎重考虑。在现行立法中,《合同法》和《海商法》规定,除了公共秩序保留、特定范围的合同和相关的一些强行法规范外,对涉外合同当事人法律选择上的意思自治并没有“一定联系”之类形式化的限制。据此,法律规避制度在中国当无法律上的依据。因为合同冲突规则中的法律规避制度必须与“一定联系”的要求为前提,在法律规避制度缺乏这种前提的情况下仍然主张建立法律规避制度是不正确的。总之,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值得肯定,不应被当作法律漏洞而在未来立法中或司法上基于“国情”之类的理由而被“弥补”——这在一个渴望健全其法制的国度是可能发生的。但是,私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凡当事人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应尽量使其自主决定。健全的制度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由法律直接控制,更不是动辄简单禁止。在特别强调保护交易安全的国际私法领域,这一结论尤其重要。
标签:法律论文; 契约法论文; 国际私法论文; 合同目的论文; 法律出版社论文; 海商法论文; 民法论文; 公共秩序论文; 意思自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