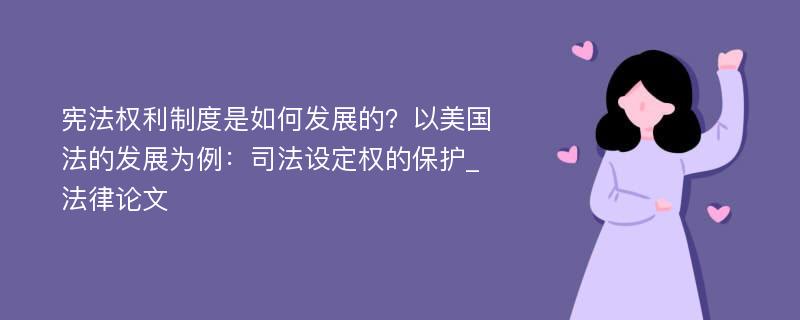
宪法权利体系是怎样发展的?——以美国法为范例的展开:司法创制权利的保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利论文,是怎样论文,国法论文,范例论文,宪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宪法权利的发展过程来看,基本权利的开放结构是依靠法院或者中立机构通过解释成文宪法的努力来完成的事情,这也是判例法国家借法官造法发展宪法权利的过程。由于判例法国家奉行先例规则,判例具有拘束力,因此,虽然这些法官创制的权利不以成文宪法的文本形式存在,但因其具有判例法上的效力,从而也就成为规范。这样,除文本形式上列举的权利外,宪法权利结构中就有了一部分判例法上的权利,宪法权利因此得以发展,并成为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判例法上的宪法权利的创制依靠一套独特的法律运行机制,它是司法能动主义的结果,依靠法官在裁判案件过程中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而完成。在此,宪法解释、司法审查、法官造法、先例规则、判例拘束力成为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成就了宪法外权利,进而发展了宪法权利的体系。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判例法的运行机制与特征,区别于制定法体系仅靠宪法的立、改、废来发展基本权利。为了对此过程有一微观认识,本文以美国法为范例,尝试对宪法文本外权利的创制与发展过程及其相关问题作一初步分析。
一、宪法以外有权利吗?它们是什么?
有在宪法文本之外存在的基本权利吗?是否有一些权利是宪法文本中没有列举的,不具备成文的宪法规范形式,但却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有拘束力的权利?有。这就是宪法外权利,也可称之为判例法上的宪法权利,或者为新权利(newly rights)、司法创制的权利(judicial created rights)、司法宣示的宪法权利(judicially declared constitutional rights)(注:[美]诺曼·维拉:《宪法公民权》(英文影印Constitutional civil rights,1998 west group)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司法承认的权利(judicial-recognized rights)、非文本自由利益(non-textual liberty interest)、未列举的权利(un-enumerated rights),是指未在宪法文本中特予列举的那些自由利益,(注:liberty interested that were not specifically enumerated in the text of the constitution.)或者指那些未在权利法案中特予列举的而留待社会发展的权利,(注:Un-enumerated rights:rights not specifically listed in the Bill of Rights left to develop with society,See J.SCOTT.HARR,KAREN M.HESS Constitutional Law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2002 Wadsworth,p334.)这部分权利虽然未在宪法文本中列举,但却因法官解释宪法而成为先例规则,具有判例拘束力。因此,从狭隘的意义上而言,宪法外权利只存在于判例法国家。惟在实施宪法过程中,各国制度相异,即使是一些传统属于制定法国家也设立宪法法院,以实施宪法,这些国家也就有了宪法法院因解释宪法而创制的宪法权利,它们也可在笼统意义上称为判例法上的宪法权利,或者司法创制的宪法权利,区别于宪法文本中列举和规定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从前面的英文用词可以看出,与权利(rights)并称的还有liberty(自由)和legal interest(法益)。虽然在广义上它们都属于宪法权利,但从实际来看,权利、自由和法益之间还是存有一定的差别,三者在受保护的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在法哲学层面,权利是个人不可剥夺的一部分,是基本的,也是人之为人属性的体现,在形式上,应该为宪法文本规定或者列举,其所受保护的程度最高;自由,是由某一权利的放射效应而引出的与权利相关联的那些活动与行为,通常不被宪法列举,与权利相比,其所受保护的程度较弱;法益,则是由权利衍生出来的利益或者好处,通常也不被宪法文本列举,其所受保护的程度最低。权利、自由与法益保护程度的差别体现在法院对案件的具体审查过程中。具体而言,对于人身自由,关键是视法院对这一自由如何认定。如果法院将一项人身自由看作是基本的,则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就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否则,就适用理性基础审查标准。对于那些被质疑是侵犯人身自由的法律来说,严格审查标准之网通常很难通过,经常被宣布为违宪,人身自由因此得以保护。而理性基础标准就要宽松得多,被审查的法律通常不被宣布为违宪。
在美国法上,司法创制的宪法权利或者非文本自由利益主要包括人身自由与经济自由,也即通常意义上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这两类自由是公民最主要的宪法权利,属于传统的civil rights、personal liberty、private rights、或者individual rights的范围,是个人所从事的那些与社会政治无关,纯粹属于“私”意义的个人免于政府侵犯的权利。另外,法院通过平等保护条款也确立了对一些个人主张利益的保护,但这些自由通常不被认为是宪法外权利,只是宪法平等保护原则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人身自由方面发展的宪法外权利主要为人身权利,也包括人身自由利益。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成文宪法中没有明确列举,是法官在判例中通过解释宪法相关条款而发展出来的。人身权利包括:隐私权、堕胎权、同性恋权、自杀与安乐死的权利、迁徙的权利、婚姻自由的权利。从判例确认的这些权利的种类来看,除上述这些权利之外,人身自由还包括了一些与人身密切相关的自由与法益,诸如家庭完整(family integrity)、亲子关系(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非父母探视(non-parental visitation)、亲密组合(intimate association)、性亲密(sexual intimacy)、医学治疗(medical treatment)、拒绝维持生命的供氧与营养的权利(the rights to refuse lifesaving hydration and nutrition)等。此外,还有一些自由,如免于身体强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physical restraint)、保护与照料的权利(the rights to protection and care),享受自己设施的自由(freedom to enjoy all of one' s faculties)、居住和工作的自由(freedom to reside and work)等。这些自由利益的共同特点是与人身密切关联,具有高度的私人性质,它所追求的是人身私密性的保证,涉及个体对与自己身体及与身体相关联的事务的处置,以免于己所不欲的官方对自己身体所施加的强制或者潜在的强制。同时,这些权利还是在普通法历史上被长期承认的私人特权,被认为是自由人有秩序地追求幸福的根本。(注:generally those privileges long recognized at common law as essential to the orderly pursuit of happiness by free man.参见[美]阿伦·艾德斯、克里斯托弗·N.梅:《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第二版(英文影引),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Allan Ides and Christopher N.May:Constitutional Law:Individual Rights,2001 by Aspen Law and Business,A Division of Aspen Publishers,Inc.)
经济自由方面的权利主要包括契约自由(liberty to contract)、从事贸易的自由(liberty to pursue a trade)和占有的自由(occupation),以及影响个人财富和收入获得的解雇、吊销执照等立法和行政行为。经济自由的共同特点是个人对财产的获得、占有、使用与处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自由的概念区别于传统的财产权。如果说传统财产权更加着重个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处分,则经济自由的概念宽泛得多。从法院在判例中对经济自由的界定来看,经济自由更多得包括了“获得”财富的权利。在给予经济自由的保护过程中,法院的措辞耐人寻味,它将各种可以获得财富的形式视为个人的经济自由,并且在很多时候没有使用“财产权”或者“权利”一词,而是用“经济自由利益”来表述这些新形式的财产权,可见法官在传统财产权与新形式的财产权之间所做的微妙区别。这一自由同样具有高度的私人性质,只是此处的经济权利关乎个人财富的获得,而非一般社会经济权利意义上的仅限于以劳工为主体的经济权利,而是所有人的经济自由,因而是普遍的,也是典型的宪法权利的内容,从属于自由权,并不具有福利国家的社会权属性。
二、宪法外权利的文本依据是什么?
非文本的宪法权利保护虽然是法官能动的结果,但它也并非无所凭依,宪法文本列举的权利始终是其创制新权利的最权威和重要的规范依据和宪法法源。考察最高法院发展新权利的判例,主要依赖对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宪法解释。在适用正当法律程序的过程中,通常还伴随着对第九条修正案的解释、半影与放射理论,及基本权利模式。其中,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的“自由”一词与其后的实质性正当程序标准被运用得最为广泛。而在总体上,这类未列举的权利都是在实质性正当程序之下获得保护的。
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自由”是被法官在宪法解释过程中运用的最多的一个规范词语,且其主要用以保护人身自由而非经济自由。在法官的解释之下,自由包括了许多新的权利。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应当注意法官在解释“自由”一词中所适用的方法。首先,所有的法官都认为,正当程序中的“自由”一词并未仅仅限制在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起草者头脑中的那些特殊的利益,(注:《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第84页。)也就是说,“自由”是开放的,可以容纳那些起草者所没有想到的,或者在当时不被认为从属于权利的自由。其次,如何确定一项主张属于“自由”之列,因此应受到保护?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是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主张。他认为,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只是那些“植根于历史和传统”中的“自由”。对制定法来讲,这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个人所主张的被州制定法所侵犯的自由较少受到保护。
第二种是奥康纳大法官和肯尼迪大法官的主张。他们同意斯卡利亚所定义的自由保护的标准,但是,他们反对设置一个单一的历史分析模式,即单纯按照传统和历史来确定自由的范围,而是主张采用其他可能的解释来源。因为普遍层面上相关传统所保护的自由主张可能在最特殊的层面上无法得到,只要主张的自由与已受到保护的自由有足够的密切联系,也可以认为这一主张属于自由的一个方面。布伦南和怀特法官都持这一见解。(注:《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第84页。)
第三种是“基本权利模式”。在保护生育、婚姻、家庭等宪法权利的过程中,法官使用“基本权利模式”来给予这类权利以宪法保护。该模式由五个步骤组成:(注:《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第75页。)
1.受到质疑的利益是否属于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自由?
2.被保护的自由是否属于基本的?
3.受质疑侵犯基本自由的法律是否以足够严重的方式侵犯了这一自由或者对该自由施以不适当的负担,从而引发了严格审查?
4.假如一项基本自由被侵犯或者被施以不适当的负担,该法是否在实质上促进了一个紧迫的政府利益?
5.政府是否采取了达至这一紧迫利益的最小负担方法?
通常,第一个步骤不成问题,因为所有形式的个人自由都有资格受最小意义上的正当程序保护;第二个步骤需要确定一项正当程序所保护的自由是否属于基本自由,这方面有一定困难;第三个步骤则需要评估受质疑的法律对基本自由施加负担的程度,因为最小侵害不致于引发严格审查;第四个步骤则是要求如果这一法律对被侵害的自由施加了负担,所使用的方法是否促进了紧迫的政府利益,否则就会引起一个严格审查。后来,最高法院又使用基本权利模式的各种变体,这些变体或者只包含上述五项之中的前三项,或者前四项,或者省略步骤2和步骤3。
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主要是被法官用以扩展宪法经济自由的一个宪法规范法源,且其主要是用以否定州制定法的相关规定无效。在此,它既包括了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也包括了程序性的正当法律程序。在前者,那些制定法中被认为是在实体上不符合自由、公正等法律的一般理念的规定内容被法官认为是专断的、不公正的和不合理的(arbitrary、unfair and unreasonable),因而在实体上是不合宪的,构成违反经济自由,即契约自由、占有自由等宪法保护。利用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保护非文本的经济自由最初在1897年的Allgeyer v.Louisiana案中初现端倪,后集中体现在洛克纳案的判决中,此后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类似的案件中采用相同标准,否定州制定法,认为州立法机关违反宪法正当程序条款,限制了契约自由,最高法院这种严格的审查标准与能动的态度被称为“洛克纳时代”。在这一极端的保护经济自由的时期里,最高法院不再使用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一词保护经济自由,而是采用实质性正当程序标准。而在不涉及契约自由,如工资、工作的机会等财产利益之时,则适用程序性正当程序标准。当一项法律被认为在程序上没有包含告知和听政时,这项法律被认为在程序上不合宪。例如,在剥夺一个当事人的工作、吊销执照、解雇等影响一个人的财富收入的判例中,就要求有事前或者事后的听政。需要注意的是,其他宪法条款,如商业条款、征用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也可用以对经济自由利益的宪法保护,但通常却没有被列为“非文本的宪法权利”之中。
在采用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自由”一词保护新发现的宪法权利(newly discovered constitutional rights),如婚内隐私的人身性质的宪法权利过程中,一度出现过反复。一些法官逐渐放弃了单纯依靠“自由”来确定新权利的保护方法,尝试用其他方法来支持对这些新权利的宪法保护。这方面有两种方法:一是半影与放射理论;一是第九条修正案。半影与放射方法是法官不依靠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一词,而是将目光与视线投射到宪法文本,这就是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修正案,来为婚内隐私权利寻找宪法文本支持。法官道格拉斯认为,这些修正案有半影,这一半影由这些保护的放射所形成,并给予这些保护以生命和实质。在格里斯诉沃尔德一案中,他认为,婚内隐私权就置于这些半影之中,隐藏在第一条修正案的结社自由、第三条和第四条修正案所保护的住宅自由,及第五条修正案所保护的抵制不得自证其罪的阴影之中。(注:《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第71页。)这就是所谓的半影与放射方法。由于使用这一方法有可能吸干(drain)对权利法案内在意义的特殊限制,布兰克法官对该方法颇有微词,认为在格里斯诉沃尔德一案中所使用的半影与放射方法与洛克纳案中所使用的实质性正当程序标准没有分别。(注:《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第71页。)其他法官对这一方法也多有批评,如哈兰、怀特等。其中哈兰法官认为,可以简单地直接适用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一词来确认对诸如婚内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因为这一权利隐含在“有序自由的概念之中”,而不必诉诸半影与放射理论。
在同意支持保护隐私权的宪法权利过程中,其他法官也同意哈兰法官适用正当程序条款中“自由”一词的主张,但更加强调第九条修正案给予这类未列举权利保护的宪法文本依据。第九条修正案规定:“本宪法所列举的特定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者抹杀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法官哥德贝尔格说道:“第九条修正案的语言和历史显示,制宪者相信还有另外的免于政府侵犯的受保护的基本权利,它们与宪法修正案前八条特别提到的基本权利一起存在。”(注:the language and history of the ninth amendment reveal that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itution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additional fundamental rights,protected from governmental infringement,which exist alongside those fundamental rights specifically mentioned in the first eight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第72页。)必须注意的是,第九条修正案并不就是扩展宪法外权利的一个独立的法源,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解释宪法其他条款的规则,与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一词结合在一起适用。(注:While not " an independent source of rights protected from infringement by either the states 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the ninth amendments provides a rule of construction for courts in interpreting others prov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such as the words " liberty" in the Due Process Clause.《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第72页。)通过这一方法,哥德贝尔格法官认为,宪法未列举的隐私权属于人民保留的个人权利,存在于第九条修正案的含义之中,因此属于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护的免于州侵犯的个人自由。
除了半影与放射理论之外,不管是依据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中的“自由”,还是拓展实质性正当程序保护经济自由,或者依据第九条修正案,其在总体上是在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之下将正当程序条款实质化。
三、谦抑或能动(deferential and active)?司法创制宪法外权利的方法
在确定那些未列举的宪法权利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立法机关特别是州制定法的审查,这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一问题,法官是采取尊重立法机关的态度呢?还是对立法机关的制定法施以严格的审查?如果是前者,则法官就比较谦抑;如果是后者,法官就比较能动。决定谦抑与能动的关键在于法官所使用的方法。这方面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严格审查标准;一种是理性审查标准。此外还有一种形式上属于严格审查,实际上属于严格审查的变体的审查方法。其中严格审查标准和理性审查标准构成了法院两种基本的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审查方法。
1.严格审查标准(strict scrutiny)。这一标准适用于基本自由利益受到政府侵犯之时,是一种比较能动的司法审查标准。严格审查标准意味着被质疑的法律通常通不过审查,被法院宣布为违宪。除非被质疑的法律对基本自由所施加的限制(负担)是为了达到一个紧迫的政府利益,且其所使用的限制方法是最小侵害方法,或者最小负担方法(the least burdensome means)。
2.理性审查标准(rational basis test)。这是一种高度谦抑的、尊重立法机关的审查方法,通常适用于对非基本自由利益的审查。理性审查标准是一种较为宽和的审查标准,被质疑的法律通常都能获得通过,不致被宣布为违宪。具体的审查方法是:只要这一法律含有任何合法的目标,一个理性的立法机关可能认为施加限制自由的方法将会促进这一目标,这一法律就能通过宪法之网,就被认为是合宪的。至于这一目标是否就是法律的实际目标,或者该法是否在实际上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则并不重要,也不在审查之列。
3.严格审查的变体,也可称为“不当负担标准(undue burden test)”。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堕胎,法院可能使用一种形式严格审查的变体(a variation of normal strict scrutiny),即这一审查在形式上看似是严格审查,而在实际上则比较宽松,介于理性与严格审查标准之间。依据这一标准,如果一项法律和实践在对妇女堕胎决定的自由利益形成过程中施以不当负担,该法律就自动无效。初看起来,这一标准增加了提供堕胎决定的保护水平,因为州在表面上没有机会对施以不当负担的规章提供证明。但在实际上,新标准使政府比在罗伊案中较为容易地规制堕胎。该标准的关键是,如果一项法律算计着去阻止一个妇女的自由选择,则这一法律就是不合宪的。如果州的目的是去劝导(to persuade)而不是去阻止(to hinder)妇女生产而不堕胎,即使这些方法并没有促进健康利益,相关法律也是合宪的。因此,在此标准下,很难想象一项法律因其目的而构成了一个不当负担。在2000年的Stenberg v.Carbart一案中,最高法院首次就这一标准形成多数,同意使用新标准评价规制堕胎法律的合宪性。(注:《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第94页。)
从法院所使用的审查方法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方面,决定谦抑和能动所依据的因素不同。法官采用严格审查和理性审查标准取决于法官认为被质疑的法律所侵犯的自由的属性。如果法官认为制定法所侵犯的自由属于个人的基本自由(fundamental liberty,则法院就会毫不姑息,也比较能动,所适用的标准就是严格审查标准;如果法官认为制定法所侵犯的自由不属于个人的基本自由(non-fundamental liberty),则法院就会比较谦抑,所适用的方法就是理性审查标准。
二方面,决定谦抑和能动还取决于法官对待不同类型权利的态度和时代的发展。这既表现在不同时期法官对经济自由的支持,也表现在法官对人身与经济自由持分别的态度。从法院的判例看,在经济起飞时期,支配和决定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理论和社会达尔文理论主宰着社会,法院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否定州制定法,对经济自由给予实质性正当程序保护,表现出更多的能动。而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之时,综合其他因素,法院也会放弃自己所坚持的与国会和总统不同的经济哲学立场的偏爱,转而以较为谦抑的态度对对待国会与州制定法,选择支持受质疑的法律。同时,在人身与经济自由的保护方面,法官更多地将人身自由作为基本自由看待,适用严格审查标准,从而给予主张的利益以宪法保护;而对经济自由,美国最高法院现在的倾向是适用理性审查标准,接受和尊重立法机关的价值判断和在规制经济生活方面的权力,允准立法机关对经济自由的适度干预,这也被称为“后洛克纳时代”。并且,在一个人身自由与经济自由同时并存的争议中,法官采用利益衡量标准,在冲突的法益之间选择对人身自由的优先保护。
三方面,决定谦抑和能动取决于法官对立法机关价值判断的接受程度。通常,立法机关因是民意代表机关,其所做出的价值判断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而非民选的法官通常应服从这一价值判断,表现为法官适用宪法裁决法律,适用法律裁决案件。这也是三权分立的内容,即立法机关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法院适用宪法和法律。但是,法院在谦抑和能动之间的往返流连在很大程度上矫正我们通常意义上对三权分立的理解,即三权分立等同于机械地分权,或者严格的制约。实际上,机械分权与严格制约从来不曾存在。一则,法官创制新权利的过程既是法官制宪的过程,也是法院对国会修宪权的僭越,而法官否定立法机关制定法也是法官对立法权的干预,表现在法官适用严格审查标准过程中。这便不是分权,而是由立法机关和法院共同分担创制宪法和制定法律的过程,只不过两机关以其权力的性质遵循不同的程序和带有差异的价值判断标准。二则,法院在许多情况下对受质疑的法律采用宽松的理性审查标准,使这些法律获得通过,这也表现了法院对立法机关的地位与价值判断的肯定与尊重,因而也并非就是严格的制约。同时,还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国会、州立法机关、公众与法院之间的默契。前者默许这一状况的存在,接受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扩充,及对制定法的评判,而法官在谦抑与能动之间也始终保持着一种中平的姿态。虽然法院有时过于能动,如洛克纳时代的法院;有时又过于谦抑,由于法院适用理性审查时被质疑的法律常常能够获得通过,以至于这一方法被讥为无用。例如,法院在1955年的Williamson v.Lee Optical Inc一案中采用了一个与前洛克纳时代的判例相似的立场,即1877年的Muna v.Illinois一案中的判决。在这个判决中,法官承认州对经济自由的干预一度有些过度,但同时却宣称:“为了保护抵制立法机关滥用权力,人们必须求助于投票,而不是法院”。(注:For protection against abuse by legislatures the people must resort to the polls,not to the courts.《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第58页、65页。)这即是一种强烈和过分的谦抑立场。法院认可通过投票改善立法机关成员构成等政治方式来改变这一状况,至于法院自己,不认为矫正立法机关干预倾向的立场属于自己的权力范围。但在总体上,法官还是能够在二者之间确立自己的恰当位置。也就是说,在保护个人自由与维护政府利益方面,法官的取舍依然值得信任、尊重与接受。
四、谁受宪法外权利的拘束?
明确的是,判例法上的宪法权利并非是在宪法文本宣明和列举的权利,因而其并未约束所有国家机关。至于基本权利效力在传统私法领域中的展开,如在适用宪法平等原则的过程中,最高法院借助州政府行为理论将该原则适用于传统属于私人的法律关系中去,以矫正歧视,则未见诸于法院在裁决宪法外权利的判例中。这一权利体系的约束力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对本案当事人产生拘束力。
②对本级法院产生拘束力。
③对本司法管辖区的下级法院产生拘束力。
宪法文本中的基本权利效力是由宪法关系的属性决定的,就其对国家机关的约束力而言,鉴于其文本形式的特点,因而具有约束所有国家机关的效力。司法创制的宪法权利则不然。由于这些权利、自由、利益的保护是司法权力运行的结果,故而其拘束力也就仅仅局限在司法领域之内,不可与成文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同日而语,因而不能约束所有国家机关。当然,即便是在司法领域内,宪法外权利的判例拘束力并非像文本宪法那样确定。在修宪之前,宪法约束所有国家机关是确定的、不变的,而先例规则的确定性则相对低得多。这一不确定性表现为:
①法官可以自行改变过往判决所形成的判例规则;
②除了最高法院的判例规则具有约束全国法院的效力之外,下级法院的判例只约束本级法院和次级法院,地方法院的判例通常只能约束自己;
③判例规则不能约束立法机关,并不能阻止立法者制定与判例规则相冲突的新法,或者修改与废除旧法。
至于未列举权利在私法关系上的效力,目前,还鲜见这方面的判决。这是因为,宪法外权利主要集中在人身与经济自由方面,且主要依据正当程序条款提供对这些自由的保护,而美国扩展宪法权利在私人领域实施的state action理论主要体现在贯彻宪法平等原则过程中,所依据的是平等保护条款,宪法未列举的人身与经济自由并无太多的理由在私人之间实施,所以,宪法外权利的效力并未通过任何方法或者理论直接及于私人。这样,与宪法文本列举的宪法权利的效力相比,宪法外权利的效力集中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宪法外权利仅对个案具有拘束力,只约束法院在一定范围的司法管辖区的判决,并不是所有国家机关必须遵守的具备文本形式意义的法定条款。这也是判例规则拘束力的一般原理和属性的体现。其二,宪法外权利并没有借助州政府行为理论及于私人,它只约束相应的全国性和州机关。
结束语
在一个法院有权实施和适用宪法的国家里,存在着可以在宪法文本之外获得生命的权利。确认这些非文本权利,既是基本权利体系成为开放而非封闭结构的根本,也是使美国宪法从未沦为僵死教条,其抵制专断权力捍卫个人自由的精神珍藏于人们心间的原因。在此,美国宪法不仅以文字形式提醒人们永远谨记这个伟大文件所昭示的宪法精神,而且一直是法官实施宪法创制新权利的生动实践的价值与规范指引,即使是在低落、消沉与彷徨的时刻。它是一项永不停歇的事业,吸引着所有那些钟爱和信仰这一价值体系的人们,为之实践,并锲而不舍。
标签: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人身自由论文; 正当程序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司法程序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