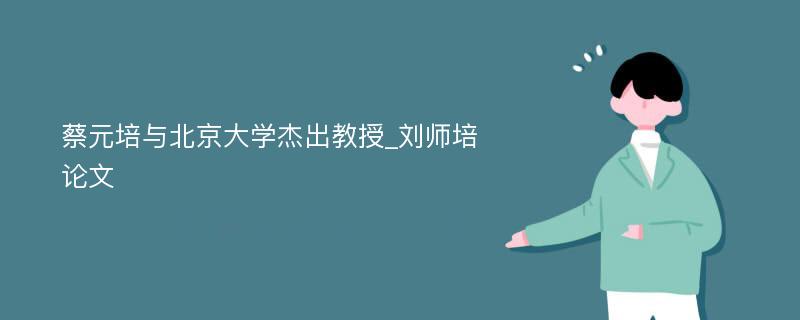
蔡元培与群星灿烂的北大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星论文,北大论文,灿烂论文,教授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广纳奇才,开创了北大百年校史中群星灿烂、相得益彰的光彩一页
“五四”前后,北京沙滩红楼荟萃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其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当时中国知识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即有二三百之众。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礼贤名士,广纳奇才,为众多著名教授所敬仰、所尊崇。蔡元培与北大教授们,犹如灿烂群星,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成为北大百年校史中光彩的一页,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耐人咀嚼的一段佳话。
要解读北大教授“群星灿烂”的现象,还得从蔡元培改革北大说起。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然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但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上课铃响时,当差便来“请老爷上课”。一些有钱的学生,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一心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对读书毫无兴趣。即使有个别肯读书的,也不过抱着科举时代的观念,把读书当作求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对学术研究概不与闻。至于那些被称为“中堂”或“大人”的学监及教员,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者,混饭度日者,比比皆是。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犹如一座衙门。这便是1916年以前北大腐败校风之一瞥。
面对着这样的北大,许多友人劝蔡元培不可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怕整顿不了,反把自己的名誉毁掉了;也有少数人劝进,认为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尤其是孙中山先生极力主张他去,认为这正好在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而他自己也觉得当大学校长不是做官,因此愿意去作一尝试。
蔡元培是1917年1月4日到校任职的。到校第五天,蔡元培即向全校师生发表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北大的举措很多,诸如,整顿教师队伍,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实行教授治校与民主管理。他还发起组织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做官等),推动学生设立体育会、技击会、音乐会等团体,以及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化学研究会等会社,推动学生组织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以及创办《新潮》、《国民》杂志等等。然而,最要紧的一条当是蔡元培推行“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的治校方略。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略,尤使北大的教师队伍出现了令人惊喜的变化。
其一,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原有中、外教员一律解聘。一个被辞退的法国教员向法庭控告,但蔡有合同为凭,法国教员的无理要求遭驳斥。英国教员克德莱(Cartwright)等被解聘后,鼓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dan)亲自到北大谈判,要求续聘,遭蔡拒绝。朱尔典出校后,愤而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闻听,一笑置之,表现了一种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大无畏精神。
其二,聘请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任专任教授与兼任讲师。不仅文科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是一流教授,理科学长夏元瑮,数学门主任秦汾,物理学门主任何育杰,化学门主任俞同奎等,也是全国一流人才;还有法科的黄右昌教授,商科的马寅初教授……均为饱学之士,一时之选。在这些教授当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本用新的科学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中国第一本《新闻学》等。不仅专任教授为国内首屈一指,兼任讲师如鲁迅、王宠惠、罗文干、何炳松、王国维、罗振玉等七十余人,也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
其三,教授的年轻化。北大教授,绝大多数都在三十岁左右。其中,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杨丙辰年仅27岁,宋春舫年仅26岁,朱家骅年仅25岁,最小的是年仅24岁的徐宝璜,他既是经济学及新闻学的教授,又是校长室的秘书。蔡先生正是以这批学贯中西、品德高洁、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为骨干,依靠他们带动全校,朝向昌明学术的最高学府推进。
其四,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蔡元培聘请教员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只问真才实学,不拘年龄、资望。他既聘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请筹安会的刘师培,复辟派的辜鸿铭;既聘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请反对白话文的黄侃;既聘“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也请坚持尊孔复古的陈汉章。正如一位蔡元培研究专家所说,在旧思想旧文化大行其道之时,蔡元培力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争得了一席之地,使他成为“近代中国新思想界首屈一指的卫兵和褓姆”。
北大教授一流,北大教授年轻,北大教授得享“百家争鸣”之自由,其源盖出自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鼎力改革的高超方略和敢于冲破世俗不拘一格延聘人才。因此,北大教授们也很仰慕蔡先生。从下面介绍的一些片断,人们亦可体验到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的那种高尚无私、亲密纯洁、没齿难忘的情谊。
陈独秀为上海亚东图书馆筹资,蔡先生差不多天天去前门外旅馆看他,有时去得很早,就拿个凳子坐在门口等候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向他举荐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对于陈独秀,蔡元培本已有深刻印象,听了汤的举荐,又翻阅了《新青年》,便作出了聘用的决定。当时,陈独秀正为亚东图书馆筹集资金,住在前门外的中西旅馆,他白天四出接洽,晚上看戏,睡得晚起得也晚。蔡先生为聘陈独秀,差不多天天去看他,有时去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拿个凳子来坐在房门口等候便是。陈独秀最初不想受聘,表示仍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先生便劝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感于蔡先生的诚意,陈独秀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后,改由陈和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等轮流主编,陶孟和、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经常撰稿。蔡先生的演说词及论文也常刊载于该杂志。这时的《新青年》,事实上已成为北大新派教授的同人刊物,成为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阵地。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反封建的闯将,尽人皆知;在处事上,陈为人圭角毕露,言论锋芒逼人,恰好与蔡先生的为人态度相反。但蔡先生并不以一己之好恶为取人的标准,这不仅从聘用陈为文科学长可以看出,又从其后全力支持陈氏之工作,可以证明。当时社会上固然视陈独秀为洪水猛兽,北大校内亦有不少人对他有反感,因为他说话往往得罪人,例如在会议上当面给理科学长夏元瑮以难堪,等等。加上他细行不检,更予人以口实。倘若不是蔡先生亲自出面,对外承担一切,对内包容一切,陈独秀要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闯将和先锋的作用,必将受到各种掣肘。
据傅斯年回忆:北洋政府曾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主要也是缘于陈独秀。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到环境的黑暗,另外一个谋客也在场,当时蔡先生有这两个谋客,是专门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那个老“谋客”劝蔡先生解除陈独秀先生之职,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才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的一切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陈胡等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余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身为北大一校之长,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的大无畏。
有人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曾产生疑问,以为只是调和折中的办法。其实是不对的。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陈独秀这些新派教授的思想是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的,本无立锥之地,而“兼容并包”正是使这些新派教授的新思想得以“容”下来,“包”下来。对此陈独秀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曾非常感慨地说:“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见。”这也是对蔡先生的历史功绩作出的肯定。
胡适说,他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元培先生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之生涯中度过
约胡适到北大任教,是蔡元培通过陈独秀致函胡适的。陈独秀在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胡适接信后于1917年6月离开纽约,7月到上海,9 月抵京就任北大教授。两天后,蔡元培在六味斋为他设宴接风。
胡适进北大时年仅27岁,风华正茂,人称“胡博士”,学贯中西,口才又好,在当时文科教授行列里,可谓佼佼者。因此,被蔡引为得力助手。胡适任北大教授时,还被推选为教务长。
当时,胡适所开的课,以讲中国哲学史最为有名。先前讲这门课的教师是人称“两脚书柜”的陈汉章,他讲一年哲学史,只讲了个三皇五帝。改由胡适来教,胡即另起炉灶,先发讲义,按照自己研究的体系,从《诗经》讲起。这样一个变动,引起了北大师生的震惊和议论。当时有的学者说胡适是学术造反,要把他轰走。一位先生则拿着胡适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讥笑地说: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但胡适的另起炉灶,得到了蔡元培的全力支持。后来蔡元培在《五十年中国之哲学》一文中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做了高度的评价:“绩溪胡适把他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胡氏以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是各家辩证法,这正是从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前所没有的。”
胡适除讲课外,还忙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进北大第二学年,他又辅导学生创办《新潮》月刊。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汪敬熙、顾颉刚、江绍原、俞平伯、孙伏园等请胡适任该刊顾问,大大增强了该刊的活力。《新潮》提倡白话文,鼓吹新潮流,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声誉也高,与当时的《新青年》有姊妹刊之称,从而招致北洋政府的反对。那时教育总长傅增湘曾奉大总统徐世昌之命,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要他设法制止《新潮》的出版。蔡对此置之不理,并回信为《新潮》辩护,使《新潮》继续得以存在。
由于北大新派教授积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礼教,引起社会上封建守旧分子极大不满。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往往又首当其冲。当时反对蔡先生改革北大、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是自称“清室举人”、“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的林琴南,他写信给蔡元培,对北大正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诬称北大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快”。此前,这位举人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过两篇影射小说,对陈、胡等教授极尽笑骂攻击之能事。面对旧势力的挑战,蔡元培不得不站出来,予以迎头痛击。他在看到林琴南此函的当天,立即撰发《致〈公言报〉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对所谓“覆孔孟、铲伦常”之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既维护了北大的声誉,又保护了陈、胡等新派教授。
胡适对来自蔡元培的关爱、提携和支持,当然深有体会,他不仅在当时对蔡元培表示了一片敬仰之情,更深深铭记在心。胡适晚年对蔡元培一番评论,读来颇令人感动。他说:“当我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胡适还言为心声地认为,他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晚年,胡适居住台北,对蔡先生仍十分怀念,每逢“五四”纪念日和蔡先生诞生纪念日,他都要出席,并作讲演。
辜鸿铭在北大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背后拖着的那根表示效忠清室的长辫子,但他精通英、法、德诸国语文,蔡先生仍请他讲授《英诗》
在北大,作为复辟派代表的辜鸿铭教授,直至民国成立10年后,他背后仍然拖着一根仿佛反抗标志的辫子。
这个与时代进步思潮格格不入的辜鸿铭,辛亥革命发生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宣统皇帝退位后,他慨然脱离公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辜氏公开反对“文学革命”,力主尊孔读经,宣扬尊孔“大义”。他甚至反对维新派力倡的“不缠足”运动,认定缠足与审美观念、卫生原理相吻合,并且解释说:研究生理学的人,都知道身体上某一部分受到抑制,另一部分必会得到发展;女子应深处闺中,所以脚的发达不发达,是无所谓的。
蔡元培看到的是辜鸿铭之所长,辜鸿铭1857年生于槟榔屿,10岁赴英格兰读书,10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专修英国文学。不久前往德国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科文凭,后又在法国巴黎逗留数月。辜在英、德、法十多年,沐浴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之中,打下了深厚扎实的西文功底,他精通英、德、法及希腊文,对英国文学尤有研究。
他曾以极大的热情与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他用英文翻译的《四书》,不受旧传统的注疏家的拘束;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人的牛津运动》,转译成德文后,被哥廷根大学列为哲学系师生的必读之书;他用英文撰写的专论《中国人的精神》,认为中国的文化较西方为高;他在欧战期间把孔子推荐给西方,认为可以把欧洲人从战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
蔡元培请辜鸿铭在北大讲《英诗》,正是展其长才。
幸得蔡元培慧眼识英才,用其所长,使辜鸿铭得以从北大走向世界,才引发后人对这位辫子教授的另眼相看。
刘师培充当清探于先,发起筹安会于后,在兼容并包的原则下,蔡先生力排众议,聘其为《中国中古文学史》教授
1917年,蔡元培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
刘师培饱读经书,18岁中秀才。次年,又一战而捷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他20岁考进士落榜,在章太炎的影响下,思想顿时大变。1903年夏天,上海发生震动中外的《苏报》案,曾在《苏报》发表文章公开宣布自己决心革命去的刘师培,没有被吓倒,旋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以揭露沙俄侵略中国的形式继续反对媚外卖国的清朝政府。1907年,刚刚24岁的刘师培东渡日本,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立即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主要作者之一。同年,刘师培成为中国人在海外出版的第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的柱石,频频著文向国人介绍《共产党宣言》、介绍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学说,政治主张之“激进”达于顶峰。
引致蔡元培聘用他为北大教授而需“力排众议”的,是刘师培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后的急剧倒退。众“议”之一:他曾投靠清朝当权大臣端方,成为端方的幕僚,并曾有《上端方书》表明心迹。众“议”之二:江浙革命党人策划起义之时,他向端方告密,充当清探,导致端方通过上海英租界当局破获起义机关。光复会地下领导人王金发盛怒之下,找到刘师培要枪毙他,吓得刘下跪乞命。众“议”之三:投靠袁世凯,先被任命为公府咨议,继又署理参政院参政。在他上任之际,正是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之时。在袁世凯的默许下成立的“筹安会”,六名主要发起人中又有刘师培。据说他没有参与实际行动,但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使他又增添了一份耻辱。
众“议”一而再,再而三,当然也让蔡元培左右为难,这才有“力排”之说。细究起来,蔡元培向刘伸出援助之手,已非头一遭。刘师培投入端方幕中时才26岁,端方在辛亥革命中被所部官兵杀死,刘师培逃往成都。后来章太炎向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力保他,正是以他年轻误入歧途作为一条理由。章太炎还与蔡元培一同在报上大登广告,“求与刘师培通信”。其实,蔡元培心里也未尝不是“姑念其年轻”,而希望刘能走上正道。但蔡之一片苦心,随即化为泡影。1916年,袁世凯死后,刘师培再度陷入狼狈境地,被迫遁入天津租界。正当刘师培走投无路之时,蔡元培又伸出援助之手,聘其为北大教授。蔡元培是确确实实深爱其才,刻意要用其国学造诣的。
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由于口吃,又有肺病,课堂讲授效果并不好,但靠编讲义弥补,还是受到学生的欢迎。蔡元培在其为刘师培所撰《刘君申叔事略》一文中,对此亦多所肯定。本来,刘师培对蔡先生的知遇之恩,理应感激不尽,结果却适得其反。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掀起之时,刘师培的所谓“国粹”也受到猛烈冲击,他再次充当反对派的首领,于1919年1月纠合北大部分师生,创办《国故》月刊, 自任总编辑。刘师培的这一举动,受到新派教授的尖锐批评。鲁迅也在致钱玄同函中,称他的刊物为“国粹屁报”。办《国故》是刘师培的最后一搏,最终却敌不过《新潮》,这年3月,他致函《公言报》, 不得不否认《国故》有意与《新潮》作对。年底,刘师培因肺病去世。
刘师培曾经“激烈”革命过,也曾经“激烈”保皇过,堪称“激烈派第一人”。尤令人注目的是,当他刚刚登上“激烈”的顶峰,却突然转向,其程度之烈、速度之猛,同样令人眼花缭乱。对于他前后两个时期的完全相反的两种“激烈”,人们至今还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但在他倒霉的时候,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则一直被后人当作是蔡元培实施“兼容并包”方针最果敢、最有魅力、最富激情的大手笔。
梁漱溟说:“我只是在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
曾被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讲师时,年仅24岁。
1916年冬天,蔡先生从欧洲回国,梁漱溟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正在《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的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家)。梁漱溟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就读到蔡先生《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蔡先生的大名而没有机会造访。后经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介绍,梁漱溟带着《究元决疑论》去见蔡先生。当他拿出文章时,蔡先生就说他路过上海时已看过了,并表示要请梁到北大教书。不久,蔡先生便约梁去他的校长室,正式提出要梁到北大担任印度哲学这门课。年轻的梁漱溟当即说,无论西欧或日本,讲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一般都是讲六派哲学。而自己对六派哲学素不留意,仅仅是对佛学有兴趣而已。教印度哲学,怕不能胜任。蔡先生的回答也很实在:你固然不甚懂印度哲学,是不是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既然谁也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差不多,你就大胆来吧。蔡先生又鼓励说,你不是爱好哲学么,我也爱好哲学,我们还有不少爱好哲学的朋友。我这次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不甚了解的朋友,都聚拢在一起,彼此磋商,共同研究,这么好的聚会机会,你怎么可以不来呢?你可以不把自己当做来教人的老师,而当做是来做研究,来学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的心,话说到这份上,他也只有答应下来,才不负蔡先生的一片诚意。
梁漱溟初到北大时,与许多学生的年龄相仿,甚至有的学生还比他大。今天我们知道的著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久、朱谦之等人,当年他们都曾相聚于同一课堂。在北大,梁漱溟先开出印度哲学课,后又开出唯识哲学课,并先后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述义》等书。
从1917年到1924年,梁漱溟在北大前后共七年,中间曾因脑病请辞两次,皆因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任。七年之间,梁漱溟从蔡先生处获益匪浅。论年龄,蔡先生长于梁二十八九岁,梁只算得一个学生。但在书信往来中,蔡先生总称作为“漱溟先生”,梁心中虽不敢承当,但因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亦不敢不自尊。后来一旦离校,梁每次写信,便自称后生晚学了。
蔡先生为什么对一位自学成材的年轻人这么器重,再三挽留呢?倘按学派说来,梁既不属于新派(陈独秀、胡适之等),又不属于旧派(辜鸿铭、刘师培等),那时他也还说不上有多么深厚的学术功底,细究起来,大概还是因为蔡先生具有远见卓识,因而才能不拘一格用人才。一方面,蔡先生认为梁富于研究兴趣,算得一个好学深思的年轻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另一方面,蔡先生对梁所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因此才有一个24岁的年轻人登上北大讲坛,才有蔡先生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
蔡元培对北大的杰出贡献,在于不拘一格地为北大罗致大量有用人才,这已为世所公认。而对蔡元生一直心存感激之情的梁漱溟则说:“我只是当时在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培养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际受到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本文承高平叔教授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标签:刘师培论文; 陈独秀论文; 蔡元培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学教育论文; 历史论文; 北大论文; 中国哲学史大纲论文; 新青年论文; 梁漱溟论文; 胡适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思想史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