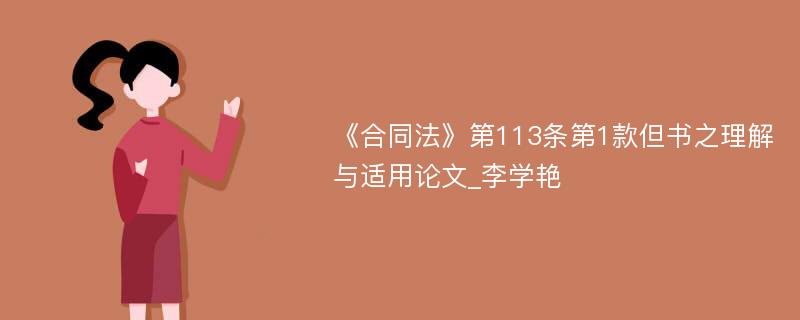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合同法113条但书的规定主要确定了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中可得利益赔偿的限制,即可预见性规则的内容。在实践中,由于可预见规则的内容、判断标准并不明确,导致第113条但书适用率不高的缺陷,因此遭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质疑。为此,本文认为对于第113条但书的理解与适用,应当对于可预见的内容进行明确,同时区分不同情形下确立可预见与否的标准,将可预见规则与完全赔偿原则和预期可得利益赔偿结合起来,进而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提高可预见规则的适用性。
关键词:合同法第113条;可预见性;可得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1804 年的《法国民法典》 从制度层面上确立了违约损害赔偿中的可预见性规则,英美法通过一系列判例发展出了自己的可预见性规则体系[]。从我国立法实践来看,原《技术合同法》第17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9条均对于该规则做出了规定,现行《合同法》则是于其第113条第1款但书中作出了规定:“……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的到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审视可预见规则,我们的疑问在于,可预见规则的立法目的与立法宗旨是什么?其适用情况怎样?功能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第113条第1款但书前后之间的关系如何?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考察我国可得利益赔偿的司法实践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
二、可预见规则理解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适用程度不高
首先根据其他调研资料,1999─2008年的10年间,在《公报》公布的合同损害赔偿案例,其中涉及可得利益赔偿的案件有8起。笔者对这些案件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事实上这些案例中都并没有真正的运用可预见规则,而仅是涉及到了预期可得利益的赔偿问题。例如在诺贝有限公司诉AD有限公司、隆源有限公司、华电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6期。]中,法院的裁判理由即在于虽然被告违约,但原告也存在一定过错或原告违约在先,故对可得利益主张不予支持。另外笔者查阅了最近两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均未涉及可预见规则的适用。再者,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输入关键词合同纠纷,设定日期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6日进行随机检索,并对前二十条搜索结果进行了统计,并无一例运用了可预见规则。[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6月7日。]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可预见规则的适用程度不高。
那么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可预见的内容缺乏明确界定
本文认为,对于可预见内容缺乏统一的认识是导致可预见规则适用程度不高的一个原因。关于预见的内容的界定,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英国法中的可预见性规则为代表的,即主张预见的内容为损害的类型,无须预见到损害的程度;另一个是以法国法中的可预见性规则为代表的,即主张除了要预见到损害的类型外,还应预见到损害的数额和程度。[ 谭睿娟:《两大法系可预见性规则适用问题的比较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而考察美国侵权法时我们发现,美国法中关于可预见规则年内容的要求与英国法相同,仅需预见类型,而无需预见具体的大小或范围。在我国,多数学者,如崔建远、韩世远、王利明等也是同意第一种观点,即认为预见的内容仅包括损害的类型,而不要求预见到损害的具体的大小或范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人民法院却将违约人没有预见到损害的程度或者数额作为为违约人的赔偿责进行开脱的理由。
(三)是否可预见的判断标准模糊
是否可预见的判断标准模糊也是导致可预见性规则适用程度不高的另外一个原因。以彼奥德诉英博买卖合同纠纷案为例进行分析。二者签订供货合同,彼奥德公司欲购买后向另一公司转卖。后英博违约,彼奥德公司要求英博公司赔偿转卖设备可得利益损失。法官在审理中认为,能否预见到可得利益损失,取决于原告在订立合同时是否将其存在可得利益情况告知被告。由此可见,该案法官在判断可得利益是否可预见时,直接以“告知”为标准,而不考虑理性人的要求,这种方式难免显得过于简单粗暴,也难称其为科学。
(四)如何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不明
第113条但书规定“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单单从这一但书的规定来看,其只是明确,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应当超过违约方可预见的范围,那么当确认对于守约方的损失属于违约方可预见的范围后又该如何处理违约方的赔偿问题,违约方需要承担多少损害赔偿的数额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相关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也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损害数额具有不确定性往往也成为法官否认可得利益赔偿的一个重要原因。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例如,在奥内斯帝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交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参见http://www.110.com/panli/panli_79484.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6月5日。]中,法官认为,本案中虽然被告预见到了其违约行为会给原告方造成损失,但是因为这一损失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没有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
三、完善合同法第113条但书规定的建议
(一)明确可预见规则仅需预见损失的类型
本文认为,应当明确,对于可预见规则的内容应当限定为损失的类型,而无需要求违约方预见损失的程度、数额等。理由如下:
首先,可预见规则的立法宗旨在于通过对于违约方承当责任在可预见范围内的框定,防止违约方承担的责任被无限放大。但是,限制责任不能以牺牲守约方合理期待为代价。如果可预见规则要求违约方预见违约损害的具体程度则守约方证明责任过重,难免显失公平。因此需要将可预见的内容限定在类型上即可。
另外,前文讨论中提到,崔建远、韩世远、王利明等人均认为可预见的内容应当仅仅是损害的范围即可,可见,这种观点被多数学者支持。因此,本文认为,可预见的内容应当明确为损失的类型。
(二)区分一般与特殊情形下确立可预见与否的标准
如前所述,在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可预见与否的标准往往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方式,本文认为对于不同的情形确立可预见与否的标准应当区别对待。
1、一般情形
是否可以预见系根据客观标准来判断,决定性的问题是,一个处于承诺人地位具有合同订立时背景知识的理性人,在合同订立时应当预见到什么;规则受到主观因素的补充,承诺人订立合同时实际拥有的知识会导致其责任被扩展或限制。[ 转引自叶金强,《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 第 113 条第 1 款但书之解释路径》,《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40-146页。]英美法中,被告能够从其所知道的事实中推断出什么,通常也是根据理性人标准来判断。[ 同6。]本文认为,适用“理性人”标准时,可先将“理性人”在案件中进行具体化,而具体化的路径即在于参照与违约方具有相似特征的主体放在相同的交易环境下,从一名社会“理性人”的角度判断违约方的预见能力。关于相似主体的确定主要考虑二者是否具有相同的知识、能力、业务水平。一般而言,在实践中具有操作性的方法是首先考察在具体案例中出现的影响预见性的因素,其次,将这些因素赋予一个具有同样知识、能力、业务水平的市场主体确定可否预见。在确立可预见的标准时应当考虑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其次是商业惯例。对于相关商业惯例的熟稔程度影响着其对于违约后可能造成损失的预见程度。
2、特殊情形
在特殊的情形下,在确定违约方对于损失是否可预见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在于守约方是否进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事实上,外国立法早就有了相关的经验可供借鉴。根据《 德国民法典》 第252条第2项、《 日本民法典》 第416条的规定,“债权人至少应披露下列事项: 依已定之计划、设备或其他特别情事,可以预期的利益。”实际上,这些条文明确了守约方的信息披露义务。在守约方有证据证明或者是违约方承认守约方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以后,那么就可以认定违约方对于守约方的损失是可以预见的。
本文认为,在特殊情形下,应当仿照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首先通过审查守约方是否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来确认是否可预见。而当守约方能够举证证明向违约方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或者违约方自认守约方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则接下来继续按照一般情形的步骤处理。根据一些商业常识和交易习惯作为判断标准来明确“理性人”,从而作为判断是否可以预见的根据。
(三)联系但书前半段内容确定损失赔偿的数额
当确立可预见之后,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即在于确定损失赔偿的数额。本文认为,实践中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应当结合第113条第1款但书前的内容进行确定。即使受限于可预见规则,但赔偿数额依旧包括实际的损失及预期可得利益。当能够证明守约方的损失属于可预见的范围时 ,我们就应结合但书前半段的内容来认定具体的违约方的责任承担。其中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守约方证明自己的损失,这种证明责任既包括实际损失的证明也包括预期可得利益的证明。如果不能够证明相应的损失就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吴行政,《合同法上可得利益赔偿规则的反思与重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适用的实证考察出发》,《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
[2]叶金强,《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 第 113 条第 1 款但书之解释路径》,《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3]谭睿娟,《两大法系可预见性规则适用问题的比较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1年第 3期。
[4]毛瑞兆,《论合同法中的可预见规则》,《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5]文学国,《应当预见规则与违约损失赔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3期。
[6]孙良国,《可预见规则的现代难题》,《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
[7]孙良国,《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12月。
论文作者:李学艳
论文发表刊物:《科技中国》2016年5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6/7/25
标签:规则论文; 预见性论文; 损失论文; 但书论文; 可得论文; 利益论文; 合同法论文; 《科技中国》2016年5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