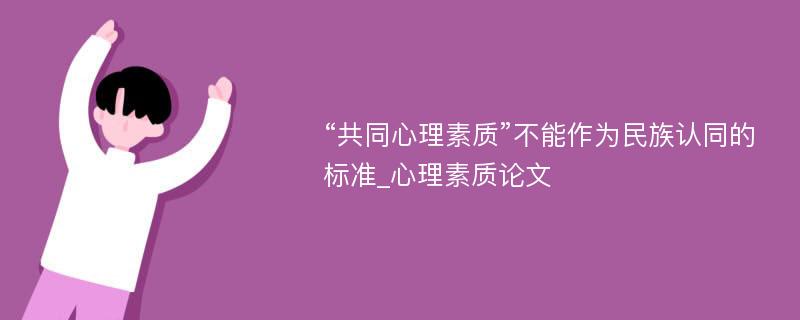
“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素质论文,民族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斯大林关于“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简称“共同心理素质”)的论述在理论上极为模糊,要准确地把握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非常困难;在实践中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者用“共同文化”代替“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心理素质”标准已经名存实亡;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界和民族心理学界的学者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对“共同心理素质”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但至今仍然得不出切实可信的结论。因此,“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今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必须根据我国民族的实际,由我国的民族学家研究确定新的识别标准。
回顾我国民族识别走过的道路就不难发现,我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一对十分突出的矛盾——我们一方面把“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但另一方面却对“共同心理素质”很少调查。在众多的民族识别报告中,人们虽然能从报告的“结语”中看到“共同心理状态”或“共同心理素质”的字样,但在报告的“正文”中却几乎找不到它的具体表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不是因为民族识别工作者没有调查,也不是因为他们疏忽而没有在识别报告中写明,而是把“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使民族识别工作者根本无法开展调查。即使在今天,民族理论界和民族心理学界的学者对“共同心理素质”作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但仍然难以把它用于民族识别。因此,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总结、分析“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
长期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界一直把“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之一。其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把“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不可缺少的特征之一。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他特别强调地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①a]很显然,斯大林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与“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看得同等重要,认为只要缺少了“共同心理素质”,民族也就不成其为民族。这就从民族定义的高度规定了“共同心理素质”的属性。凡是认定一个民族,必须把“共同心理素质”作为一个必备的条件。
毋庸置疑,我国民族理论界受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影响最深,因而很自然地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我国民族识别的主要理论依据。尽管当时很多的民族理论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对斯大林的“共同心理素质”感到很难理解,但还是把它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提了出来。
把“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势必要对“共同心理素质”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但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看,他在论述“共同心理素质”时远不如他论述民族的其他特征那样得心应手。在不多的几句话中,他就用了“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形态”、“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心理素质”、“心理素质”、“民族性格”、“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不同的说法来指代“共同心理素质”。这就使本来就抽象的“共同心理素质”变得更为复杂。究竟什么是“精神形态上的特点”?什么是“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形态”?什么是“心理素质”?什么是“民族性格”?什么是“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非常模糊,决不是轻易可以回答的。斯大林本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极为复杂,所以他说,共同心理素质“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②a]但究竟怎样才能“捉摸”到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斯大林没有说。这就使人们在认识和把握斯大林所说的“共同心理素质”时碰到了很大困难。
斯大林把“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的特征之一,曾被我国民族理论界公认为是斯大林的独到见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近年来随着民族理论界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由于中俄两国学者交流的增加才使我们发现,斯大林并不是第一个把“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特征的人。据俄罗斯著名学者刘克甫(M.B.克留科夫)在致我国民族理论学家熊锡元教授的信中所言,早在斯大林之前,俄国的一些理论家已经把“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的特征之一。“如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民粹派理论家П·Л·劳罗夫认为‘民族是具有同样语言、心理素质、习俗、历史传说和文化的共同体’(见劳氏选集,莫斯科1934年俄文版,第1卷,第288页)。而斯大林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条的直接来源则为鲍威尔的著作。”[③a]
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的有关论述也可以看到,他在批判奥地利理论家O·鲍威尔和A·斯普林格的民族理论时,对鲍威尔“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们的全部总和”[④a]的观点予以坚决的批驳。但他在给民族下定义时却简单地借用鲍威尔的“民族性格”,并把“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性格”等同看待。我国民族理论界把“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性格”混用的根源就在这里。
事实上,斯大林从鲍威尔那里借用的“民族性格”同“共同心理素质”一样的模糊。鲍威尔认为:民族性格是“一族人区别于另一族人的种种特征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的总和。”[①b]斯大林虽然批判了鲍威尔把“民族性格”作为民族唯一特征的错误观点,但他并没有对鲍威尔的“民族性格”概念本身提出异议。这样一来,鲍威尔的“民族性格”概念中的各种缺陷自然被保留下来,诸如:什么是“生理特质”?什么是“精神特质”?“生理特质”与“精神特质”有什么联系与区别?能否用“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界定“民族性格”?这样界定“民族性格”具有多少科学性?因此,不论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还是“民族性格”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都是极为模糊的概念。
这两个极为模糊的概念经斯大林的手一度成为前苏联和中国民族理论界研究民族问题的一条准绳。但是,随着两国专家学者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研究的加深,这两个概念的缺陷逐步暴露出来,两国的民族理论研究者正在摆脱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的羁绊,重新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探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问题。在前苏联,学者们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颇有异议。正如前面提及的俄罗斯著名学者刘克甫所说:“斯大林将考茨基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与鲍威尔的共同心理素质拼揍在一起,不加区别地把这四点作为民族的特征,进而宣称其中‘缺一不可’,这条‘理论’在今天来说无论在苏联或中国都没有人接受。”[②b]在中国,民族理论界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模式(包括“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性格”)的缺陷都有自己的见解,差别只在于有的学者谈得多些、深些,有的学者谈得少些、浅些。从公开发表的文章看,贺国安博士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驳论》一文集中反映了我国民族理论界对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的不同看法。贺国安博士在文章中直接了当地提出:“如果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证明,斯大林的模式并不像人们赞扬的那样‘科学’和‘正确’,那么,是否应该把它抛弃,而去探索更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新模式呢?”[③b]
由于斯大林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论述在理论上极为模糊,有很多缺陷,要准确地把握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有很大困难。所以,“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废除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原来不敢公开自己民族成分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向当地政府上报自己的民族称谓。到1953年,全国汇总登记下来的民族称谓多达400多个,其中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④b]在如此众多的民族称谓中,究竟哪一些民族称谓的人们共同体可以作为单一民族很难确定。经过专家初步分析发现,有一些民族称谓是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支系的名称;有一些民族称谓是同一民族的自称和他称;有一些民族称谓是民族居住地区的名称;有一些民族称谓是自己所从事的特殊职业名称;还有一些民族称谓是同一民族不同的汉语音译。因此,要弄清中国到底有多少民族,必须首先对400多种民族称谓进行甄别,分清这些民族称谓的人们共同体是汉族的一部分还是少数民族;是某一个少数民族内部的不同支系还是单一少数民族。于是,党和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从一开始就确定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民族识别的主要理论根据。也就是说民族识别工作必须按照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个特征进行识别。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把斯大林提出的四个民族特征作为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指南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因为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都没有给民族下过定义,论述过民族的特征;二是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者还没有根据我国的民族实际对民族作出科学的诠释;三是西方学者对民族的研究结论不能采纳。因此,离开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就缺少了最起码的科学依据。事实上,即使到今天,大凡涉及到我国民族识别问题的论著依然把斯大林提出的四个民族特征作为民族识别的主要标准。
但必须指出的是,把斯大林的四个民族特征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从一开始就碰到了很多困难。从“共同语言”看,丧失了本民族固有语言的回族、满族、畲族、土家族等算不算单一民族?从“共同地域”看,散居在不同地区的苗族、回族、满族、达斡尔族、乌孜别克族等能不能成为单一民族?从“共同经济生活”看,我国各民族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方式占绝对优势,经济联系非常薄弱,那我国还有没有民族?从“共同心理素质”看什么是“共同心理素质”大家感到理解不深,难以把握。如果说丧失了固有语言还不能否定这个民族曾经有“共同语言”;散居在不同地区是民族迁徙的结果,也不能否定这个民族曾经有“共同地域”;没有广泛的经济联系,但有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有“共同的经济生活”,那么,对理解不深,把握困难的“共同心理素质”怎样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呢?
从实际的识别过程看,由于“共同心理素质”这个标准在理论上具有模糊性,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所以,绝大多数民族识别工作者都用社会组织、婚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现象代替“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报告中则以“社会组织与文化”为题统摄这些内容。例如:沈家驹、常闳恩、施联朱等同志的《新平县“山苏”、“车苏”识别小结》在对“山苏”与“车苏”两个彝族支系的“名称、人口和分布”、“语言”、“经济”、“社会组织和文化”作了详细介绍后得出“结语”说:“‘山苏’、‘车苏’语言都是彝语方言;居住分布地区从大区域看来与彝族连成一片;经济上与彝族联系亦较多。此外有氏族残余、父系家族、幼子继承权、弟娶寡嫂的夫兄弟妇婚、火葬遗迹、重视祖先崇拜、火把节等一系列的特点都与彝族同。因此根据语言、区域、经济和民族文化所表现的共同心理状态各特征,‘山苏’、‘车苏’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而是彝族的支系。”[①c]笔者案头摆着的费孝通、潘光旦、向达、林耀华、黄淑娉、杜玉亭、杨毓才等专家学者在民族识别中撰写的民族识别报告也是这个体例。
民族识别报告是民族识别工作的集中反映。民族识别工作者在识别过程中把“共同心理素质”变为“共同文化”,集中调查识别对象的社会组织、婚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在对“共同心理素质”无法调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斯大林说的是“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既然“共同心理素质”无法调查分析,那就用“共同文化”取而代之。至于“共同文化”与“共同心理素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共同文化”上表现出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什么样的心理素质?它对民族识别有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当时根本来不及考虑。所以,只能在调查了“共同文化”的基础上作出识别对象具有某种“共同心理素质”的结论。
对于这种现象,1980年费孝通教授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曾经总结说:“‘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民族要素在民族识别工作上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特征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和全面,因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出现过追求各民族在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宗教仪式上的所谓‘特点’,脱离了该民族人民附着于这些‘特点’上的民族意识和它们发展的历史条件,简单地把它们用来作为识别的标准,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①d]
费孝通教授虽然对用“共同文化”代替“共同心理素质”持有异议,坚持“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准,但他说的“共同心理素质”与斯大林所说的“共同心理素质”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用一句比较容易理解的话来说,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我们每个人是可以用自己的经验体会到的。这个特征可能比其他的特征在形成和维持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上更见得重要。”[②d]从费孝通教授所说的“共同心理素质”看,它与斯大林所说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民族性格”、“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具有本质的区别,而与现在民族理论界常说的“民族自我意识”、“民族自识性”、“民族自觉”完全一致。修世华先生甚至把它“作为对民族自我意识的最通俗、最精彩、最权威的解释和表述。”[③d]
如果说费孝通教授是借用“共同心理素质”这个术语阐述自己全新的思想,那么,黄淑娉教授则直接了当地把“共同文化”作为民族最本质的特征。她在《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一文中说:“我们当时充分考虑到斯大林对于‘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民族要素的论述,借鉴民族学的有关理论,决定以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特征——共同文化特点作为识别民族的标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④d]
费孝通教授和黄淑娉教授都直接领导或参与了50年代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他们虽然对“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证实了斯大林的“共同心理素质”在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已经名存实亡了。
由于斯大林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论述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给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者在实际的识别过程中已经放弃了这一标准。现在有关论著中关于“共同心理素质”这一识别标准的实例也多是用“共同文化”加以说明。所以,“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
三
把斯大林的“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不仅在理论上极为模糊,而且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所以,我国民族理论界在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结束后对“共同心理素质”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说费孝通教授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对“共同心理素质”问题发表的新见解标志着我国民族理论界对“共同心理素质”问题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熊锡元教授则把“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1980年起,熊锡元教授把自己多年研究“共同心理素质”问题的成果陆续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于《贵州民族研究》、《思想战线》、《民族理论研究通讯》、《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丛刊》等学术刊物。1994年,熊锡元教授把十余年来发表的文章收集汇编成《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一书,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在这本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问题研究专著中,收录了熊锡元教授对“共同心理素质”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包括熊锡元教授给“共同心理素质”下的全新定义。他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共同心理素质尽管比较抽象,但决不是不可捉摸。一个民族,通过它的语言、文学艺术(包括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建筑风格与手工艺等)、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方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审美观和民族意识与自豪感,这就构成该民族在共同心理素质上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这一民族在精神面貌上区别于其他民族。”[①e]这是国内民族理论界迄今为止对“共同心理素质”下的一个最为完善的定义。
熊锡元教授不仅给“共同心理素质”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而且对“共同心理素质”的属性、特点、表现、作用进行了全面论述,并用自己的理论对国内外的若干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作了具体分析,熊锡元教授的这些研究成果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民族理论界对“共同心理素质”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很多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从熊锡元教授的论述中受到启发,吸取了有用的成分。
与熊锡元教授不同的是,吴团英先生在研究“共同心理素质”问题时更注重从普通心理学的概念体系中寻找构成“共同心理素质”的要素。他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主要寓于民族心理结构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之中(心理状态也是心理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不体现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具体地说,在心理过程这一层次上,它主要蕴含在民族认识(包括民族自我意识在内)、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上;在个性心理特征这一层次上,它主要蕴含在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能力这三个因素中……换句话说,民族心理素质就是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以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的,一个民族在情感、意志、性格等方面的特点,就组成该民族心理素质上的特征。”[②e]吴团英先生不仅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了“共同心理素质”的构成要素,而且从动态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共同心理素质”的发展、变化的特点,使“共同心理素质”问题的研究具有更浓厚的心理学味道。
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界对“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原来极为模糊的概念经过我国的专家学者的长期研究,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人们再也不会为什么是“共同心理素质”而烦恼了。但必须指出的是,明确了什么是“共同心理素质”并不等于“共同心理素质”就能成为民族识别的标准。
目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应用现有的“共同心理素质”理论对一些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作了分析,形成了一批具体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普遍丧失了“共同心理素质”的固有属性,与研究者的初衷相距甚远。例如:
熊锡元教授在研究了汉族、回族、傣族、美利坚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后认为:旧时的汉族具有坚韧不拔、兼收并蓄、中庸之道、小康思想、内向含蓄、封闭自守六个特征。旧时的回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交织、保族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四个特征。旧时的傣族具有温文尔雅、重和睦、轻纷争的心理特征。美利坚民族具有富于进取、鄙视守成;勤奋工作、机会均等;平民精神、不尚等级;标新立异、旷达不羁;自恃自负、自我困惑等特征。[①f]
郭大烈研究员在研究了纳西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后认为:纳西族的民族自我意识是“纳西若米”(纳西儿女);民族精神是坚韧不拔;民族性格是深沉谨慎;民族道德是质朴厚重;民族信仰是多神观念。[②f]
吴团英先生在研究了蒙古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后认为:蒙古族豪放、刚毅、粗犷的特点,就是蒙古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性格上的反映。[③f]
蓝建宇先生在研究了壮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后认为:壮族具有头重脚轻的思想意识;沉重如山、卑弱怯懦的语言心理;虚无的文化;宗教心理;虚假繁复的生活心理[④f]等一些弱点。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作者对这些民族长期观察、研究的结晶。它填补了这些领域的空白,使人们能够对这些民族的心理有一个概貌性的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这些经过研究而概括出来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反过来作为重新识别这些民族的标准,我想不论是研究者本人,还是民族识别工作者,或者是被识别的民族,都不会赞成这个标准。因为这些“共同心理素质”的表现构不成民族之间在心理上的根本差别。这些心理特征即使在这个民族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但不能说其他民族就没有这些心理特征。把一些民族或很多民族都具有的心理特征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只会使民族识别工作再次碰到难以化解的困难。
由于斯大林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论述虽然经过我国民族理论界的长期研究有了更为科学的表述,但把它用于具体民族所概括出来的“共同心理素质”仍然不能作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心理标志。因此,“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
四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问题既是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民族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理论界用自己的方法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没有最后证明它可以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这是不是意味着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988年,为了证实这种假设,笔者在以“云南若干少数民族心理调查之一——基诺族心理调查”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获准后,按照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用了三年时间对基诺族心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调查的项目有基诺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道德感情、审美感情、宗教感情、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记忆特点、思维特点、学习兴趣、颜色爱好、职业愿望、自杀行为以及传统社会化等民族心理现象。原来以为,经过这样全面、细致、深入的心理调查,一定能弄清基诺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确定各民族心理的基本特征,为民族识别提供可靠的心理依据。但出人意料的是,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现象调查越深就越难对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出简明扼要的回答。特别是当用跨文化心理学方法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的某一些心理现象进行比较研究时就会发现,民族之间虽然存在着心理差异,但这种差异很难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①g]
无独有偶,在1990年出版的《民族心理学》一书中,孙玉兰和徐玉良两位著者对民族团体心理、民族认识、民族的需要和动机、民族的社会化、民族情绪情感、民族性格、民族艺术与民族体育心理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但在所有的论述中仍然难以找出可以作为民族识别标准的“共同心理素质”。在与“共同心理素质”关系较为密切的“民族性格”一章中,作者对影响民族性格形成的因素作了分析,并据此划分出一些民族性格类型。如根据自然环境对性格的影响作者把“民族性格”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北方民族的性格;二是南方民族的性格;三是农耕民族的性格。[②g]这三种性格类型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性格类型可以找到不少例证,但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都可能具有相同的性格类型。由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影响所形成的性格类型,也同样会因为不同民族拥有同样的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而形成相似的性格特点。因此,“民族性格”在各民族之间也是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构不成民族识别的心理标志。
此外,民族心理学界还应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对不同民族儿童的心理发展作了研究,如卢浚、左梦兰教授对云南的汉、白、彝、苗、纳西、傣、基诺、景颇等民族的3~15岁儿童的认知发展作了跨文化心理研究。[③g]又如王骧业、程庆麟等对青海的汉、藏、蒙古、撒拉、土、回等民族的9~15岁儿童的心理发展作了跨文化心理研究。[④g]这些研究证实,不同民族的儿童在心理发展上既有地区间的差异,又有民族间的差异,而所有这些差异都是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因此,要根据不同民族的儿童在心理上的差异判定儿童的民族成分也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确立“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多少帮助。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民族心理现象是人类心理现象中最复杂的一类心理现象,要从中概括出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非常困难。笔者认为,根据民族的本质属性,可以把异常复杂的民族心理现象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一个民族所有成年人都具有的共同心理现象;另一类是民族内部各个群体所特有的心理现象;还有一类是民族内部的个体所特有的心理现象。这三类民族心理现象暂且把它们称为民族共同心理、民族群体心理和民族个体心理。民族共同心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语言文字、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不同而形成的各不相同的民族心理。这种伴随民族本质属性而产生的民族心理从一开始就存在于一个民族的广大成员之中,表现为一个民族所有成年人之间的某种共同心理趋向。民族群体心理是一个民族内部各个群体的成员由于群体的属性不同而形成的各不相同的民族心理,诸如一个民族内部的性别群体、年龄群体、职业群体、阶级群体、党派群体、宗教群体的成员除了具有本民族的共同心理之外,还具有该群体所特有的一些心理现象。民族个体心理是一个民族内部的各个成员由于自身所面临的主客观条件不一致而形成的各不相同的个性心理。不论是民族共同心理,还是民族群体心理,或者是民族个体心理,都不能超越个体而存在,只能通过一个民族成员个体的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离开了个体的心理活动,任何民族心理现象都不可能存在。因此,要从一个民族的个体身上区分出哪些是个体心理,哪些是群体心理,哪些是共同心理,本身就不容易,而要从中概括出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就更困难了。
其次,现有的心理学理论虽然比心理学诞生之初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要把它用于“共同心理素质”研究还有很多困难。如果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心理学实验室为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标志,那么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历史已有100多年。在100多年的心理学发展中,心理学家根据自己的研究创立了不同的理论,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常见的构造派、机能派、格式派、行为派、精神分析派、认知学派、人本主义派等心理学派别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没有哪一种理论能解释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一种理论能解释某一类型的心理活动,但要解释另一类型的心理活动就有困难。即使对同一类型的心理活动,不同学派的理论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对与“共同心理素质”关系较为密切的“人格”问题,精神分析派、社会文化派、特质论派、学习论派、人本主义派各有自己的解释。[①h]由于心理学理论中存在大量不“规范”的东西,按照库恩和波普尔的科学标准衡量心理学的现状,使心理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还不能说心理学是一门规范科学。”[②h]
再次,现有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虽然对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要把它用来研究“共同心理素质”还有很多困难。现有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投射法、实验法、模拟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对心理学的发展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些方法还有很多弱点。最突出的是,这些方法对简单心理现象的研究可以达到很高的信度和效度,而对复杂心理现象的研究就显得困难,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就会大幅度降低。如果用这些方法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样复杂的心理问题,其难度就更大,准确性更低。
由于斯大林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论述用现代心理学方法研究仍然得不出切实可信的结论,所以,“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
综上所述,斯大林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论述在理论上极为模糊,要准确地把握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非常困难;在实践中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者用“共同文化”代替“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心理素质”标准已经名存实亡;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界和民族心理学界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对“共同心理素质”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但至今仍然得不出切实可信的结论。因此,“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今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必须根据我国民族实际,由我国的民族学家研究确定新的识别标准。
注释:
①a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295页。
②a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③a 熊锡元:《与刘克甫书谈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问题》,《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④a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7页。
①b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6页。
②b 熊锡元:《与刘克甫书再谈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问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
③b 贺国安:《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驳议》,《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
④b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①c 《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第44~46页,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1955年编印。
①d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②d 同上。
③d 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④d 黄淑娉:《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①e 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②e 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①f 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6页。
②f 郭大烈:《纳西族心理素质初探》,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③f 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④f 蓝建宇:《论壮族思想意识、心理结构及其中之卑劣成分》,《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
①g 参见韩忠太、傅金芝:《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②g 孙玉兰、徐玉良:《民族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③g 卢浚、左梦兰:《儿童认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④g 王骧业、程庆麟:《青海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①h 参见赫根汉著,何谨、冯增俊译:《人格心理学导论》,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h 荆其诚:《现代心理发展趋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