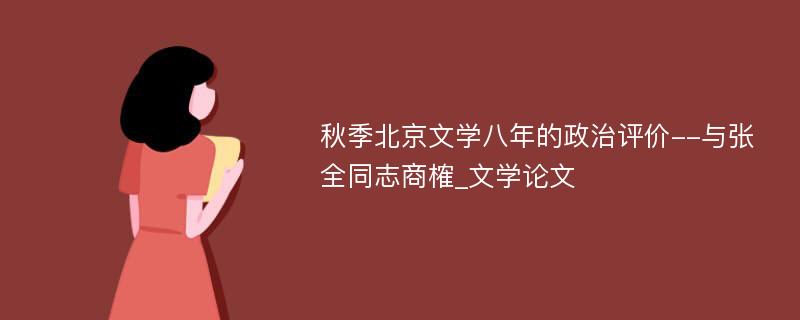
对《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一书的政治评价——与张泉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书论文,北京论文,时期论文,同志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泉同志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读之颇受启发,受益匪浅。此书论述的事实长达八年,而且时局极为艰难复杂,文艺团体、报章杂志变化不定,作家中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乃至不同观点的人由于时局变化很难定位,张泉经过十年努力,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这只要读读书后的那435个注和590个人名索引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张泉对这样复杂的时局和文艺情况以及众多的作家进行认真求实的评价,堪称一项开拓性的艰难工作。但因这一时期一些作家作品、一些文艺团体和事件,由于情况复杂而难于把握,所以这部书也难免有其美中不足之处,可谓瑕瑜互见,下面我提出三点看法,同作者进行商榷
一、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对沦陷区的文学要求和政策问题
张泉同志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沦陷区文学既没有具体的指导纲领、政策和要求,也没有具体的创作成果,甚至日本军国主义与沦陷区在文学方面的沟通、联络、协调都没有。他说:“时至1942年,北京日伪当局对文学仍没有具体的要求,更谈不上文学政策了。”(《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第33页,以下引文凡不署名者,均为该书。)“在与沦陷区文学有关的日本各方面之间,连最起码的沟通、联络、协调都没有。这样的文化控制如果是强有力的,那才是一件怪事呢。”(第36页)抗日战争胜利直至中国解放以后一直顽固地坚持日本军国主义立场的林房雄1943年来中国,发表演说,组织文学团体、设立文学会馆、派代表到上海、南京等地活动,促成杂志创刊等等,但作者竟说凡此种种,“并不包含任何具有指导意义的文学纲领。”(第36页)“大东亚文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集中力量经营了几年,又开会又评奖,但张泉同志却说:“‘大东亚文学’口号虽然叫嚣了几年,也进行了一些活动,特别是成功地组织了三次大会,但它的性质、纲领一直是含混抽象的,更没有具体的创作成果。它只不过体现了日本法西斯文人力图使文学更有效地服务于‘国策’的一种强烈愿望,对沦陷区文学的发展没有实质的影响。”(第50页)对此,我认为有些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东亚文学的性质、纲领,我认为并不是含混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明确的。事实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亚洲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它的文化侵略,也是为军事侵略服务的。对此,日本军国主义曾直言不讳,它在《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实施要领》中指出:“于武力推行运动之中”同时“加以文化充分辅助”。这个“充分辅助”非同小可,是他们提出“大东亚文学”明确的纲领和目标。关于这个观点,张泉在书中有时也是承认的。他在“结论”里写道:“大东亚文学是日本御用文人提出的旨在为‘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的文学纲领、旗帜或口号”,并“召集过会议、出版了刊物”等等。而且在“大东亚文学”一节里讲得就更为明确,他说日本军国主义宣传“大东亚文学”就是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其根本目的是要使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文学艺术纳入日本法西斯的宣传轨道,让文学担当起歌颂日本军国主义,美化法西斯战争,巩固日本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任务。”这里,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文学”的纲领、性质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哪里有含混和抽象的影子呢!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积极推行“大东亚文学”,经营几年,召开代表大会,评选作品,创办刊物,组织文学团体等等,怎么能说他们“对文学没有具体要求,更谈不上文学政策呢”!
至于有没有“大东亚文学”具体创作成果,哪些作品属于这类作品,这是一个需要具体研究的复杂问题。但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经过几年的精心策化经营组织,召开了三次“四国”代表大会,参加代表几百人,得奖作品几十部,这个组织的纲领和目的又是那样明确具体,在推荐评选作品时不是推荐评选不出作品而是推荐出了作品,有的作品也确实得了奖。而且张泉也认为第三次大东亚文学代表会开的还很成功。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参加大会代表的作品和评选得奖的作品里就没有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作品?就没有属于“大东亚文学”范围的作品?事实上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歌功颂德的、美化法西斯战争的、鼓吹中日亲善共荣的都有人在。众所周知的周作人不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吗!周作人1942年访日期间,两次向屠杀中国人民的侵华日军伤病人员捐款,歌颂“皇军”战功赫赫等等,并从文学方面鼓吹“大东亚文学”的合理性,这难道不是“大东亚文学”创作的具体成果吗?或许作者说周作人是汉奸我已专门论述了。是的,作者专设一章论述了周作人,但不等于在沦陷的华北、北京除了周作人及其作品之外,就没有为“大东亚文学”服务的作家和作品了。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朔风》杂志1938年11月10日创刊,这个刊物如何,我这里只说两点:
一是这个刊物在第10期里刊登了一些口号:
反共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东亚人起来共同建设新东亚中日真正合作才能共存共荣……
二是该刊原主编方纪生,1940年8月出国,后来任驻日本留学事务处长及东京帝国大学文学讲师。1942年6月讲了这样一番话:(刊在《新光杂志》上):“中日同文同种,……本人又有志于研究日本学术,如果从这种结合稍得帮助,是我所希望的,同时由于这种结合希望两国更能亲善提携……”等等(第65页),这样的口号和文章算什么内容呢?这算不算为“大东亚文学”服务的“作品”?当是不言自明的。还有,歪曲现实,美化日本侵略者的小说《敌?友?》;恶毒攻击红军八路军的《灰潮》、《迷途》等等。还有更为恶毒的攻击抗日根据地的作品,如《雨后》,诽谤延安“简直是窑子世界”,那里的人“全是正常社会的流氓,学校开除的不良分子,胡闹的女学生,铺子里潜逃的商人,捣乱的工人”等等。还有些刊物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纷纷举办征文。比如《中国公论》杂志为配合日本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举办征文,征文启事说:“为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已行展示,本刊为协力治运以尽舆论天职,特举行征文”如何如何,结果征得一些作品,小说《转》讲一个青年以抗战阵营转向和平阵营;诗《醒》主张要无条件地服从大东亚“圣战”,《还乡》极力鼓吹青年为日伪卖命等等。《新民报半月刊》从1942年设立“每期奖金”小说,为特定题材长期征文。在此号召下,出现了一些歌颂王道乐土、粉饰沦陷区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应该说是属于大东亚文学范围之内的。另外,从一些杂志和报刊的文艺副刊的名称上也可以略窥大东亚文学的痕迹,比如《新民报》的文艺副刊“天地明朗”,还有的叫什么“太平地”等等。当然,这些栏目内刊登的文章不会都是为大东亚战争服务的文学,但这样的栏目是欢迎这类的文学的。否则在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代,高唱什么“天地明朗”、“太平地”岂不是发昏了吗!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文化控制是否强有力,这是可以讨论的。但说“连最起码的沟通、联络、协调都没有”,这恐怕就不符合事实了。我想一些受过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之害的人感受更为深刻。当时日本警察局特高科经常搜查所谓的“反动刊物”,他们把所谓的“反动书刊”列为“检举妨害大东亚战争不良分子办法”中的第4条。他们把前苏联肖洛霍夫著的《静静的顿河》、《美国白皮书》、巴金和郭沫若的《中国近代短篇小说选》等等都列入反动书刊,可见文化控制之严。另外,日本军国主义散发大量反动书刊画报,仅1931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就散发《大东亚战争画报》、《建设大东亚读本》等6种,计2万余册。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是要把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列为汉奸文人或汉奸作品,我只是说这段文学史应该给以恰当的评价,至于哪位作家的作品里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作品里有不健康的思想内容也不见得就是汉奸文人或汉奸作品。过去认为,沦陷区没有文学或没有抗战文学,都是汉奸文学,这一结论冤屈了多少人,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张泉同志大胆地做了开拓性研究,为一些作家和作品做了公正的评价,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赞扬,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也应该指出,现在也决不能把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群众的作品或歌颂“皇军”歌颂沦陷区为“明朗的天”、“太平地”的作品,一律视为不是为大东亚战争服务的作品,这同样是不恰当的。
二、书中前后自相矛盾
书中有些篇章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先是肯定,后是否定,前后矛盾。比如作者在论述沦陷区杂志刊物时,指出: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持续时间上,官办杂志都占据着绝对优势。它们各自办刊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充当日本侵略军的喉舌,为‘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进行奴化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第15页)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但作者在具体分析时又与此不同,请看:1939年1月创刊的《中国文艺》,曾刊出政治宣传的内容,鼓吹复兴华北文艺,沟通中日满文艺。但作者却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指政治内容的文章)是作为专论发表的”;“即使在这个时期,与政治宣传合拍的‘小说’也较为少见”。就这样,作者把政治宣传的文章给解释了。再看1939年1月创刊的《中国公论》杂志,它以时事、政治、国际、经济、文化为主,兼及文艺。“促进国家建设,研讨国际问题,发扬东方文化,树立中心思想,加强反共运动”,这是它的办刊宗旨,“和平、反共、建国、兴亚”是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张泉同志也称,这“实际上已道出了它的反共卖国实质”。就是这样一个刊物,张泉同志却说“尽管如此”,“一般知识层,都愿意读它的理论文章”,甚至说“如果把‘反共’之类的词语略去,有志青年完全可以据此了解并定向革命的圣地”等等。作者的这一假设难以服人。再看1943年7月1日以周作人为首创刊的《艺文杂志》,在预约征订广告里讲“大东亚文化建设运动的一翼”、“为树立大东亚文学而努力”,作品里确有美化沦陷区的内容。周作人也直言不讳地说“文学与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就这样一个刊物,张泉却说:“但相比较而言,赤裸裸推行日本侵略者图谋的内容,比其他官方支持的刊物要少得多。”(第92页)1943年9月由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沈启无任主编的《文学集刊》,此人工于钻营,为实现领导华北文坛的美梦甚至不惜就范于日伪当局。就这样的人主编的刊物,张泉却说:“尽管如此,该刊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与《文艺杂志》相仿的,没有明显的政治气味。”(第93页)《艺文杂志》连周作人都讲“文学与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而且是“大东亚文化建设运动的一翼”、“为树立大东亚文学而努力”,怎么成了“没有明显的政治气味”呢!最后我们再看看《新民印书馆》。这个馆号称“日华合办,半官半商”,而实际上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其宗旨十分明确:
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光荣的任务,两国人民都应当切实地担负起来。创造东亚的新历史,正需我中日两国人民用血与汗来写上。这种艰难的工作,“文化”所负的使命是尤其重而且大。……这新的历史有待于新的文化来酝酿、来推动,我们立脚于这种新的文化的基础之上,新的历史才坚强地成长起来。就是这样的印书馆,宗旨又是这样明确。印书馆成立后,印制新的教科书,进行奴化教育;印制伪政府法令,强行推行殖民地法令;印行日语教科书,所谓的新地图,妄图使日本侵略中国合法化等等。但张泉却说“尽管出版者的动机是营利,但此举确实有力推动了北京文学的长足发展”(第100页)等等。印书馆的宗旨是那样的,张泉讲动机是赢利。我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和意图不是赢利,因为日伪政权已下了血本,投资250万元。日伪人讲的宗旨是奴化宣传,作者讲的动机是赢利,显然是不对的。
通过上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张泉对日伪政权通过杂志报纸进行奴化宣传,为战争服务是明确指出的,但在具体分析当中又加以否定。这样不但显得此书前后矛盾,而且也显得作者的观点含混不清。
三、文学与时代和政治的关系
这里我提出个问题,希望作者继续研究。首先,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得奖问题。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得奖以后,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又在北京追加原来的三项“选外佳作”为“大东亚文学赏副赏”,并举行了授奖仪式。对这些作品如何评价呢?张泉说:“但这些作品实际上仍与‘促进大东亚文学界前进,彻底共荣圈新理念,建设大东亚文化’的要求无关。”(第48页),作者这个结论似乎令人费解。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开了三次,第二次评了奖,而且参加大会的代表和被评选的作品都是经过推荐审选的。参加大会的代表由“四国”组成即中国、满洲、蒙古、日本,而且台湾属于日本辖属。会上又是训词又是祝词,讨论阐述大东亚文学宗旨。这样一个宗旨明确,组织健全,计划周密的文学团体,评选出来的作品怎么能与大会的宗旨无关?至于这些得奖作品与大会宗旨有多大关系,哪一部作品有关哪一部作品无关都是可以讨论的。但说这三部作品一律无关是否太绝对了。不要说作品被日方看中,就是作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中国人参加这样的“四国”代表大会,在日本侵占中国国土,残杀中国同胞,分割中国东北时,也不能说与日本侵占中国,与大东亚文学无关吧。
其次,作者在评论一些刊物时经常说某某刊物属文学刊物,不谈政治时事如何如何。比如对《朔风》作者就是这样评价的:“《朔风》是一个不谈政治时事的纯文艺刊物”。这个刊物究竟怎样呢?作者说后期刊物内容“一改其不谈时事政治的惯例”。那么,刊物前期呢?作者说“前期《朔风》不失为‘水平线上的杂文杂志’”,“《朔风》创刊伊始,他能够坚持不与时政联系在一起的立场,他的办刊说明和刊物的实际内容便是明证。”那么这个刊物前期究竟是不是不谈时事政治的纯文艺刊物呢?作者说:“前期《朔风》基本上迈着闲适超脱的步履,主要刊登‘有趣味有分量的小品,以及空灵的抒情文章’,而这趣味,就是周作人所说的‘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第64页)在战火纷飞,血流成河的年代,何人能够“重厚”,何人能够“中庸”,何人能够“迈着闲适超脱的步履”?这除了周作人之类还有几人!这是其一。其二,敌人同来是一手拿着刀枪杀人,一手拿着软刀子杀人——其效果并不亚于刀枪。其三,声明不谈时事政治的人并不一定说明他没有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文艺作品也如此。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一般说来有三种文艺:抗日文艺,汉奸文艺,还有写风花雪月和爱情的文艺。前两种文艺的作用不言而喻,后一种似乎是脱离或超越时事政治的,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能真的没有政治态度吗!
还有,关于“和平文学”问题。众所周知,“和平文学”则是汪精卫汉奸集团投降日寇炮制”和平、反共、建国”三大卖国纲领,发表《和平宣言》,搞“和平运动”等整个投降卖国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新申报》、《中华日报》等上海一些报纸鼓吹建立和平文学,并成立了《中国文艺学会》和周佛海的《艺文研究社》等文学团体,形成了一个“和平文学”思潮。对这样一个文艺思潮张泉却说:“不必人为地拔高它,树立起一个大大超过其实际形态的靶子,然后再煞有介事地加以批判。”(第127一128页)我不知作者是否有所指,但我看到作者对这个口号在书中并未作批判。对于在文艺上为汪精卫投降卖国活动效劳的“和平文学”是必须批判的,作者这样评价“和平文学”是不正确的。作者还说“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文坛虽也有过关于“和平文学’的议论,出现过少量有意无意宣扬‘和平’的文艺作品”等等,作者在这里提出了“有意无意宣传‘和平’”这个论断,是值得研究的。当时汪伪投降卖国集团大肆鼓吹“和平文学”,一些报刊加以配合,开辟什么“太平地”、“天地明朗”等栏目发表作品,难道这些作品都是“有意无意”的宣传“和平”吗?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时,高唱什么“天地明朗”、“太平地”、“和平”等等,对于具有这类内容的作品不管其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我们都应该指出其不足才是,就是作者无意,我们也应该指出其社会效果不好,何况这些作品并不见得都是无意的。我们评论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主要看其作品内容而不是看作家的主观意图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