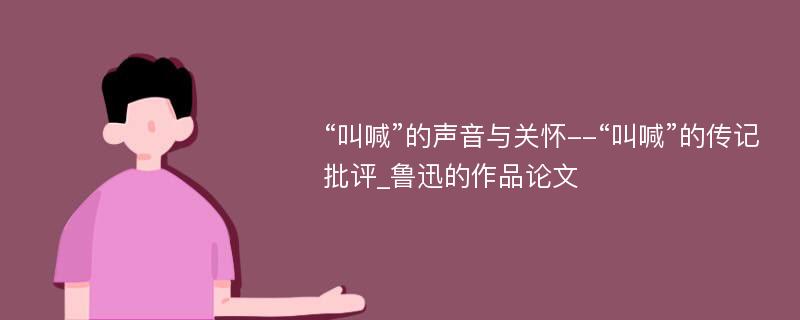
“呐喊”的声音与关怀——《呐喊》的传记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批评论文,声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66(2001)02-0041-05
“两种声音”
1、社会化/个人化的两种声音
1930年以后出版的《呐喊》,一共14篇。仔细纵览以后,就会发现,这14篇作品可以分为两种写法,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特征,在主题取向、故事组合、与作者的关系及构思趋向等方面,分别显示了社会化与个人化的不同倾向与特点。
前者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等8篇;后者有:《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兔和猫》、《故乡》、《鸭的喜剧》、《社戏》共6篇。
下面从3个方面来看它们的区别。
(1)主题及思想的取向
这14篇小说从表现的主题或思想的取向看,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性论题,即与国家前途、大多数人生存相关的话题,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处于文化或舆论的中心;是知识阶层特别关心并力图给予解答的时代课题,如,《狂人日记》展开的是反封建专制、揭露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害;《孔乙己》、《白光》表现科举制度的罪恶、旧读书人的末路;《药》、《阿Q正传》、《风波》都涉及到辛亥革命及以后的社会现实,都沉重地表现了民众的不觉悟、麻木等精神创伤,即国民性问题。《端午节》写知识分子软弱、模糊、逃避的人生和精神状态;《故乡》和《头发的故事》情况比较复杂,既有社会性、时代性的话题,又有个人化的话题。这两篇小说都涉及国民麻木,改革艰难的思想。综上可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取向几乎都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时代主题和人文关怀。
而另外几部作品就不是这样了。其话题明显表现了个人性、一己性,与社会、时代虽有一些联系(个人不能完全脱离社会、时代),但不是全社会共同关注、大家一看即知的时代主题或热点。《一件小事》是叙事者从一件小事对自我“越来越看不起人”(即对民众觉悟的看法)的思想的反省;这篇作品具有某种个人的道德思想反省(如何看待下层民众,如何看自己)的倾向,在鲁迅整个作品系统中极为少见,事实上,这件小事虽然反映了作者思想震撼,道德净化等情绪,但并未改变鲁迅终身对国民性的严峻的看法。作品虽然也应合着“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者在劳动者面前自我忏悔的时代思潮,但从鲁迅一生的话语系统,思想倾向所表达的社会,时代主题来看,明显是一种个案,不能代表鲁迅的社会关怀与时代关怀。《头发的故事》中说“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狱里受了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哪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这里表达的是长期停留在鲁迅心中并持续了一生的一种情绪:革命者的孤独寂寞。另外还有一段话:“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里表达的也是鲁迅独特的改革/革命观:执着现在。以上所说的思想情绪的两点,应该说都是鲁迅个人独具的,具有相当的超前性,结合着鲁迅个人的身世经历和心灵感受。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中这是一种孤独的声音,多数人还未涉及还未感受到的思想,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思想标志,但却不是社会时代的思潮的主题。另外,《兔和猫》、《鸭的喜剧》表达的是对生命的创造,毁灭“太滥”的喟叹;对生命强弱虐杀的悲悯。是鲁迅进化论思想与个体生命感悟独有的结合。《社戏》、《故乡》都有对少年生活的眷顾,对成年生活的失望与厌倦。总之这几个作品的话题显然是个别的,与社会、时代的“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不平”等主题是有差异,有距离的。
综上所述,《呐喊》的思想取向,前一类作品是指向社会、时代,表达的是公认的“五四”主题;后一类作品,从思想渊源、范畴虽然也可以划入“五四”思潮的某一方面,但从鲁迅个人经历来看,思想的指向却在个人的某种或某方面的思绪与感受。作品叙事构成的“意义”,近于散文的个人性质而不具备小说的普遍性。
(2)故事情节的形态。
从14篇作品的故事倩节的形态来看,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狂人日记》等8篇具有小说常态常规的故事;独立、完整的时间、空间及人物命运普遍的过程,是现实生活的某种模拟,但并不等于现实生活,尤其与作者个人生活不“接通”;具有象征性、典型性,涵盖着社会生活的某一面。但另一类作品,即《一件小事》等6篇却不同,其间的人事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不具备独立性,而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着亲缘、叠合、甚至相同的关系,与作者个人生活“接通”,上述6篇前5篇经人考证都确系鲁迅个人生活的表现、记录,勿庸争论。而《头发的故事》似乎是两人对话的独立故事,但凡是了解鲁迅生平、思想者可以很快明确地看出,其中N先生关于头发的遭遇、感慨,关于“黄全世界”的说法,关于先驱者“死”得寂寞的话语等等,都直接来自或吻合鲁迅本人。正由于与鲁迅个人生平、思想、生活的过多重合,这几部作品与前类作品相比较,其小说应有的象征性、典型性,虚拟性被某种写实性、个人性消解了,因此,这几部作品的文体体裁常常引起争论,被人认为更接近散文、小品。
(3)作者与叙事及作品中人物的关系
《呐喊》中,上述《狂人日记》等8篇,作者明显退出故事空间,在叙事时,或用第三人称全能全知的形式,站到故事之外;或用按语形式(《狂人日记》),或用故事特定人物身份的形式(《孔乙己》),将作者自己与作品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区别开来。总之,作者与作品空间,作品人物不发生直接的牵连,作者通过不同叙事方式讲的是“社会”上的生话、人事。
但是,在《一件小事》、《兔和猫》、《鸭的喜剧》、《故乡》、《社戏》中,作者与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身份,难以区别,据对作者生平考证,这些作品中的“故事”,可以说,都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遭遇,作者不但没有站在“故事”之外,而是进入了“故事”之中。换言之,作者基本上叙说的是“自己的故事”,虽然也有一些补加、虚构、渲染,但作品中,“我”的叙事主干,不能使人实现小说应有的阅读期待,反而容易引起人们对作者生平的联想,对作者个人而不是社会生活的认识。另外,《头发的故事》中,作者虽然不等同于叙事者“我”,叙事格局与上述5篇有区别,但其中主人公的言语行状又明显叠合着鲁迅个人,可以说,作者仍然进入了作品空间,仍然叙说了自己的遭遇与哀痛,不过不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形式,而是以作品中主人公的形式。
综上3点所述,《呐喊》中一部分作品具有完整的小说形式,叙事对客体作了象征性观照,作品意义指向了时代、社会的主题。而另一类作品文体上更接近散文、小品形式,叙事往往接近、重合、纪录作者个体的生活、遭遇、心态;叙事的意义是个人性而不具备普遍的社会意义;思想指向虽未脱离时代,但不是时代的主题。其思索是随想式,即兴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形式。
2、“两种声音”个人原因的追溯
造成鲁迅《呐喊》中社会化/个人化两种写作,两种声音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他个人的原因,和他个人的思想基础,创作的意欲,创作目的,及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有关。
①“两种声音”源于创作意欲的矛盾、隐痛。由上述可见,《呐喊》中14篇作品只能说有大部分作品(8篇)是属于“呐喊”,应和着社会时代的主题,另有一小部分作品更是个人的“感喟”、思索的性质,在思想的取向和格调上并不统一。简言之,纵览14篇作品,其创作速度不能算快,且时快时慢,兴致来了,可以一个月3-4篇,否则,1年只有1-2篇。创作表现了相当大的随机性。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正好符合,也表明了鲁迅“五四”时期开始新文学创作的思想和心态。在《(呐喊)自序》里说得比较清楚,家道中落看到社会黑暗和世态炎凉,读新学,所获不多,失望;去日本学医,可中国人的愚昧,让人失望;弃医从文,以文救治人心,办《新生》又失望,接连的“梦”的破灭,让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感到“荒原”般的寂寞,心凉透了,寂寞似大毒蛇缠住地,他要“麻醉”自己,“回到古代”,“没有年青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但朋友的劝告,自己内心深处对“希望必无”与“可有”的矛盾,终于还是开始了创作。但他立刻又强调,他的这种创作“并非一个切近而不能己于言的人”的行为,只是“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只是为了“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1]“并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2]可见,《呐喊》的创作并非完全来自内心的主动,以上反复曲折的意思反倒表明,其创作似乎更多为了别人,是来自外界力量的推动或者说,他当时的创作欲求是相当矛盾,犹豫的。这样一来,14篇作品主题时而社会化,时而个人化,不集中统一就容易理解了;其创作速度节奏的漫不经心,也容易解释了,他的作品“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而成的。[3]
②“两种声音”源于个人思想基础及创作目的矛盾、二元化。《呐喊》创作一部分社会化一部分个人化的二元格局是与他个人思想的二元化联在一起的。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着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的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4]当然这里并不是想要证明,他的社会化写作是人道主义,个人化写作是个性主义,这里并不存在创作二元和思想二元的这种等同代换模式。但是,他思想的二元(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是会影响他的创作目的和创作中思想关注的重心的。当他“为别人”时,创作目的指向社会主题,为先驱者呐喊助威;当他更关注自己的生存时,创作时个人一时的思绪、念头,个人某些心中郁积(《头发的故事》),个人的某些心灵震颤(《一件小事》)、个人的某些遭遇(《鸭的喜剧》《兔和猫》)、个人的某些温馨的回忆(《社戏》)就必然容易产生“无非借此释愤抒情”。
③社会化写作与个人写作并存又与鲁迅的生活习惯,个性有关。鲁迅写《呐喊》时,(包括他一生)其基本上过的是一种比较简单,单纯的以“弄笔”,“教书”为主的生活,虽不算深居简出,但平均接触的社会层面是不广泛的,主要限于一部分关系亲近、熟悉的文化人(教师、学生、编辑、撰稿人等),而且他前半生除了这些人外,就是从小家乡遇识的旧读书人,少量农民和小乡镇的男女市民,这样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对他创作的广泛取材当然有一定限制,正如曹聚仁所说:鲁迅笔下的人物,是“属于鲁迅自己那一台门的,是中国古老农村一部分”,“鲁迅对他自己那一阶层的社会相,了解得很深刻,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却并不广大”。[5]对于这种情况,李长之从人格与心理气质上解释,又将认识深入一步,李长之认为: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喜欢群。因此,鲁创作偏向“主观与抒情”,“善于写早年印象中的农村,而不按实生活里的体验去写都市题材,不适于写那种需客观构思的长篇小说。”[6]结合曹聚仁,李长之的分析,可以看出,《呐喊》(也包括《彷徨》)中只能有一部分作品应合社会、时代主题并主要限于农村、小乡镇的农民与读书人;而另有一部分作品更专注于“个人感触”的抒发——是很自然的,因鲁迅的生活与个性,使他不能自由地经常不断地从社会各阶层生活取材,而一到“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这样身边的人事,反而得心应手,写起来特别快;也使鲁迅那么多作品甚至包括《端午节》这样社会化作品都留下他自己的或他生活域限中的“本事”,也正因为鲁迅这种创作取材的特点,周作人才能写出《鲁迅作品中的人物》这样“索隐”式的文章。
对“四种人”的关怀
《呐喊》中主要刻划了4种人的形象——先驱者,旧读书人,农民和叠合着作者的“我”。这里表现了鲁迅对他熟悉的中国社会主要阶层的关注、忧虑,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吃人),而且也显示了后来终身坚持的文学和文化关怀的目的(立人)。
1.先驱者——救群众反被所害
①先驱者、先觉者。在《呐喊》主要表现在《狂人日记》和《药》中。其形象内涵都有一个哀痛内容:先驱者教群众,可被享用牺牲,不被理解,甚至被加以迫害。“狂人”洞悉统治者黑暗势力,“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深知几千年的“仁义道德”根本要害是“吃人”;他“诅咒吃人的人”,呼唤“真的人”和“救救孩子”。可他被囚,被敌视,被人目为疯子。夏瑜反对“满人”的天下,在监狱还宣传“造反”,可没有人理解他,不明白他说的“可怜”,非但如此,他想拯救的百姓中的华家却用他的鲜血蘸馒头去治病,他被杀头之前被人围观。这样的形象和类似描写还有《彷徨》中的《长明灯》(疯子)、《孤独者》(魏连殳)、《故事新编》中《补天》(女娲)、《奔月》(后羿)、《野草》中《颓败线的颤动》(老女人)、《这样的战士》、《复仇(二)》中的耶稣等。
可见《呐喊》中开始的先驱者救群众反被害的主题,实际已成鲁迅各类创作中的一个“母题”。是一种长期萦绕他脑中的思想,一种长期压在心头的“隐痛”。
②这可以从鲁迅生平,思想及外国文学借鉴几个方面寻找发生的原因。众所周知。鲁迅一生是向反动势力搏斗的一生,日本留学时期,曾与革命党人(光复会)有联系。又立下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志,他是有着为国为民牺牲的情怀的;但随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尤其是他身边革命者的遭遇,以及对“国民性”研究、观察的深入,他又看到了“革命者牺牲”的另一面残酷现实:“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王金发“将谋主放了”,可他自己“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而起主要作用的就是“杀秋瑾的谋主”——这就是他的亲身经历所见。他一再表明:“牺牲为群众祈福,祈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7];又说:“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8]他的这种悲痛的思想又在他翻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中得到了印征:“改革者为许多不幸者们,‘将一生最宝贵的去做牺牲’,‘为了共同的事业跑到死里去’”但是,“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踏生活,”[9]
2、旧读书人——被科举制度所害,殉葬者
①旧读书人。主要表现在《孔乙己》、《白光》两篇作品中。这两部作品中的孔乙己、陈士成迷恋科举,尊崇科举,终身沉溺于科举考试之路,可他们失败了,成为畸零无用的人,或任人侮蔑、穷困潦倒而逝;或精神变态、发狂,溺水而亡。仔细解读可以发现,鲁迅如实细腻写出了他们畸形的人生,批判他们沉溺、妄想的精神状态,但并不着意写他道德、人格的低劣,相反,还隐含着叹息与怜悯,鲁迅的愤怒与憎恨主要掷向造成这种人生的制度,他给科举的末代士子留下了凄凉的潦倒末路之图。
②鲁迅就生活在世代读书,科举进仕的家族,他眼见了在这条路上的成功与失败,大量失意者人生深深烙在他心中。他深知科举在一定时期的强大力量,人在这种制度下的无奈与渺小。他痛恨这条路,不能认同这条路上的旧读书人,但他更强调的是人在这样制度下“被害”的一面,写了孔乙己不失诚实与善良,陈士成顾忌学童和邻居的反映,这都是他们人性的显露。“鲁迅在本家中间也见过类似的人物”,这些人比鲁迅笔下的人物“似乎气味更是恶劣”。鲁迅写他们,不过写出了“破落大户家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也写了这一群人的末路。”[10]鲁迅笔下留情,这实在与他的经历及家世有一定的关系。为此,他在1919年的附记中表示,不要认为作品是针对谁,“里面糟蹋的是谁”,他只不过“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
3、农民——被吃,而又不觉悟,甚或参与“吃人”。
①农民。是鲁迅作品的描写最多,寄托感情深重的阶层。《呐喊》主要见于《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4篇作品。鲁迅在这4篇作品及其他大量作品中塑造的农民形象最主要的特征是:被封建制度及各种旧势力吞噬、残害、剥夺,又未能觉悟,甚至有时不自觉地参与了“吃人”的活动。鲁迅写了单四嫂子的愚昧、七斤一家和他的乡民们围绕着“辫子”、“皇帝坐龙庭”经历了一场悲喜剧。在“虚惊”中表现了他们思想的混乱、保守、怯懦、麻木。闰土是痛苦的,可“我”因为他的“不争”而更痛苦。一个阿Q,写尽了鲁迅对愚昧、麻木,被吃而不觉悟的农民(当然不仅仅是农民)的忧伤与哀痛。
②以上4部作品对农民的描写,是由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及他的创作目的所决定的。鲁迅从日本留学时期就开始系统观察、研究中国的国民性,后来得到的认识很沉重,国家的衰弱是与国民素质的低下联在一起的。他深感,国民的劣根性太多。他在不同文本反复指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11]“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12]又说:“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13]。“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6]。总之,“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15]。……还可以例证下去,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前无古人,其解剖无比深刻、犀利,他的《呐喊》中的作品只不过是传达这个认识的一个途径,一个阶段,解剖国民性,他终身奋斗不息。
同时,鲁迅的创作目的,也必然导致对农民及其生存状态的表现。他说,他写小说,“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6]因为,中国的百姓,由于“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4千年”。因此,他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17]。单四嫂子、七斤一家、闰土、阿Q就是鲁迅笔下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4、“我”——寻生命存在、寻路的知识者
①“我”。是一个频繁出现在多篇作品中,并以其语气,语词所固有的冷隽,深沉的人格气质笼罩全本《呐喊》叙事的人物。其中,在《一件小事》、《故乡》、《社戏》、《兔和猫》、《鸭的喜剧》等篇中,以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者并兼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出现,而这个“我”的人、事、言、行及至举止,神态都重合作者本人;而在《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虽然不是第一人称叙事者,但其神情、话语也重合着鲁迅,不过是一个没有以“我”的身份出现的“我”。这些作品中的“我”(包括N)是一个在世纪转换时期,在中西文化对撞的背景下苦苦争扎的知识者,他最触目的特征是:寻找前行的路径时,反思我的思想与情感。“我”的对人的看法?我的希望?生命的感触?他踌躇,他苦思,他身心交瘁,需要抚慰。《一件小事》中,车夫的“爱心”和责任心,让“我”惭愧,让“我”看到自己的“小”,这里分明有着道德的震憾与忏悔。但是,“我”更着急地把这件小事与自己“看不起人的坏脾气”联系起来,似乎把我从中“拖开”,给我“勇气和希望”。联系鲁迅生平思想可以看出,所谓“看不起人的坏脾气”,就是对国民性尤其是国民劣根性的严峻看法,鲁迅虽然后来终身并未改变或放弃自己的这种看法,但鲁迅有一种不断反省、考查自己思想,并在实践中检验自己思想的习惯,即:“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困为希望是在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又说过:“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绝望的抗战。”[18]但他立刻又接说:这些看法“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9]坚持自己的思想但不固执,不断地在实践中考查、检验。“我”的震动与思绪,可以看作鲁迅对自己“国民性”思想在实践中的一次反思,反省与碰撞。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在寻找着我的民众观、人性观。N先生愤激“怀着远志”,身受“苦刑”的故人和少年,“踪影全无”地死去了,可人们早将他们忘却;N先生又借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将黄金世界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自己呢?”这里实际上表现了鲁迅两点一贯的思想:民众对革命及革命志士的隔膜与遗忘;他对“黄全世界”的预约行为的拒绝,很明显,这里是鲁迅对“革命”及如何通向未来之路的思想的小说化表达。
②《兔和猫》在两只小兔的被吞噬的悲剧和“我”对猫的仇视的记述中,表达的是“我”对“造物太胡闹”的“反抗”。这里隐含了鲁迅对生命的矛盾意识:生存的残酷竞争与对弱者的保护,这是一个悖论,“我”怅惘,只能怪罪造物。这是鲁迅对生命意识的回味与寻觅,反省与审视。《鸭的喜剧》有一个双层的意义结构:“爱罗先珂渴望自然界“歌声”,敏感人间的寂寞;可自然界歌声到来时背后又演出了生命的毁灭、吞食,驱除了寂寞却带来了虐杀,真是一曲让人困惑的悲喜剧;另外一层,“我”作为这一切的目击者,既认同于爱罗先珂的“寂寞与歌声”,可又亲历了让人困惑的一幕,而且爱罗先珂走后,“我”感到了更大的寂寞与怅惘。造物、生存、生命……这一切表明,上述两部作品都贯穿着相近的主题与反思,都是鲁迅对生命的存在的感触与寻找。在鲁迅那里,有进化论,又有人道主义;他憎恶寂寞,有时又喜欢寂寞;他听到了歌声,却又同时看到了虐杀,这一切多么矛盾又让人困惑啊!这两部作品以随感的形式透露了鲁迅精神与心灵世界的复杂,深邃与矛盾。也正是“五四”知识者心灵的一种写照。这里对“生命”的思索与感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自我意识的反省与思索,也是在寻“我”。
③《故乡》结尾,由宏儿和水生的交往引起了一大段关于将来“新的生活”、“希望/偶象”及“路”的议论。在曲折往复的表达中:“我”希望新的一代有“新的生活”,但对这“希望”我又立刻表现了“害怕”,甚至以为像闰土的偶像一样靠不住;可又立即表示: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先“走”着,假如人多,便可能“成了路”。这里的“希望——失望——无所谓——走”的反复,十分清楚地表现了一个正在彷徨徘徊,瞻顾难定的知识者对“路”的寻觅。“寻路”是《故乡》一个十分明显的主题。《故乡》与《社戏》还传达一个相同的情感要求:“我”要回忆“我”的童年,“我”的故乡。故乡中有“我”少儿时的朋友,戴银项圈,手拿钢叉的小英雄;“我”与少儿朋友们看“社戏”,吃罗汉豆,划小船……在深情的回忆笔调,诗的氛围中传达的是一个历程坎坷,饱受炎凉,心灵疲惫的中年人寻求慰籍的欲求,即使鲁迅这样坚强的灵魂,童年、故乡仍然是温暖的精神家园,让人神往的抚慰:“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果蔬:菱角、罗汉豆、菱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20]
5、“四种关怀”的个人思想溯源:
综观上述《呐喊》中对4种形象的刻划及其关怀,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这样一种精神图景:“我”,一个从旧社会中来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识者,关注人生。首先,他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象他这样的救民救国的先驱,并不为民众理解,或被害、或被享用牺牲,十分寂寞,没有好下场。当然,也更发现广大的民众默默受着宰割,社会无比黑暗,他哀痛他们的不幸,又愤怒他们的不争。他往回看,十分熟悉他家族的前辈读书人的潦倒末路,他为这样的人生作了最后的记录。可是,“我”自己呢?正在寻找着前进的路径,寻找着自我的意识和感觉:进化、人道、个性、故乡、童年……。
这里的“4种关怀”的精神图景建立在鲁迅的两种思想上:“吃人”与“立人”。他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大家一级级地吃着“下人”,又被别人吃。在这样的吃人社会,首先被吃的是广大民众,可他们不觉悟,又帮着去“吃”先驱、先觉者。要改变这社会,要掀翻这厨房,“要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21]。凡是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22]。总之,鲁迅“五四”时的思想及前半生的经历,决定了《呐喊》关怀的对象及关怀的重心——被吃、被害的4种人及他们的精神心灵。
收稿日期:2000-12-11
标签:鲁迅的作品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孔乙己论文; 鲁迅论文; 社戏论文; 一件小事论文; 鸭的喜剧论文; 兔和猫论文; 白光论文; 故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