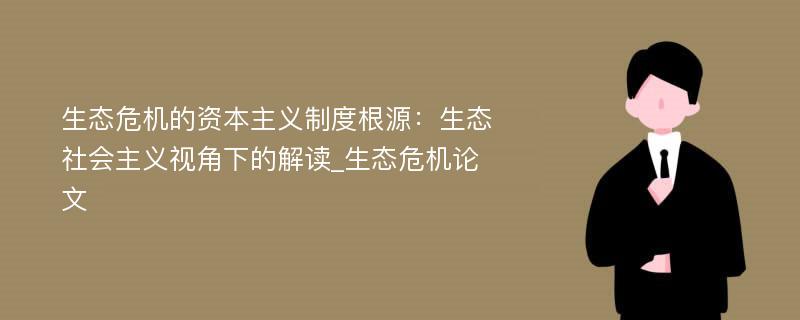
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种生态社会主义视角下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根源论文,视角论文,危机论文,资本主义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04)03-0066-04
一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当今全球生态危机之间必然联系的论证与批判是生态社会主义 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再生产理论基础上的对当 代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揭示,是生态社会主义建构其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逻辑起 点。
1、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理论:生态社会主义建构其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前提。 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早有论述,他将工人的劳动力称为“生产的个人条件 ”;将土地等“自然条件”称为生产的“外在物质条件”;此外还有社会生产“公共的 、一般的条件”,比如运输工具,基础设施等。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这三类生产条件都不是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因而也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所谓 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也不能依据其交换价值来阐释,严格地说,他们没有交换价 值。既然生产条件的生产和配置不受市场支配,那就肯定存在着某种相对独立的力量, 在促使着这些生产条件以恰当的数量、质量、时间和地点,把自身呈现给资本。“这种 因素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它创造了这些生产条件,并且控制着对劳动力 、土地及原材料的获得和使用的权利,以及参与和退出被马克思称为‘生产条件’的那 些虚拟商品的交易活动的权利。”[1](P236)国家对生产条件的调节和控制是必要的, 因为生产条件是资本实现自身的前提条件,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一般条 件”就是获得在劳动力、土地、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治保证。即便不是所有的生产条件 都是由国家生产的,比如家庭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必要角色;“自然体系”是土壤、矿 产等自然条件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等等,但不管生产条件的生产者是国家 、家庭还是自然界,国家都毫无例外地、直接或间接地对这些生产条件的生产和配置进 行控制与调节,以保证总体资本对利润的追求。
作为总体资本的代言人,资本主义政府的政策输出在原则上应满足于总体资本的利益 ,这一点似乎不难理解,但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条件的政策输出内含着不 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于个体资本与总体资本之间、个体资本与资本派别之间的 利益冲突,矛盾的结果如何,实质上是一个政治维度的问题,取决于资本内部、国家内 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因此,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试图在国家政策与生产 条件(自然条件为代表)之间建立一种稳定而和谐的关系,终究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生 产条件的必要性,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条件再生产(在自然可承受的限度内满足总 体资本利益)的不可能性之间的张力,导致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生态危机。以此为理 论前提,生态社会主义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分析。
2、对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揭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向社会主义 转型的理论,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因之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来自工人阶级,资本 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转型的直接目标;传统的经济危机以“实现性危机”表现出来, 实质上是一种相对的生产过剩。比起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当代的资本主义已发生了巨大 变化,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除了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 更凸显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再生产能力 ”之间的矛盾,是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并以“生产不足的危机”(生态危机) 表现出来;以生态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是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物化力量,生产条 件的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转型的直接目的。
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同时存在这两重矛盾,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 性使然。为了满足对利润的贪欲,资本必然要努力降低成本,扩大积累:在提高剩余价 值剥削程度的同时(以图降低可变成本),也变本加厉地扩大对自然界的掠夺(以图降低 不变成本)。前一种努力的结果导致了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市场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 即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积累的内在障碍;后一种努力的结果导致了日 益恶化的“生态危机”,而从长远看,这又有抬高不变资本投入进而导致“生产不足” 的趋势,这是资本积累的外在障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两种障碍都不可能根本超越 ,但并不否认资本可以在自身范围内做一定的调整:“生产过剩的危机”蕴含着对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建,酝酿着资本之间、资本内部、资本与国家之间更为社会化的协作 形式;“生产不足的危机”蕴含着对生产条件(以自然为代表)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重建 ,以实现对生产条件更有计划性的生产与配置为目的。“正像对生产力的重构意味着更 为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形式一样(反之亦然),对生产条件的重构意味着一种双向的作用— —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力维度上的生产条件形式,以及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形式,生产 条件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被再生产出来的。”[1](P275)“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形 式、生产力形式以及生产条件形式总合在一起,便内含着一种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1]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两重矛盾所推动的以“更为社会化”为目标的两种类型 的重构,决定着有两种趋势共同导致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条件以及这些生产条件再 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 而且,对劳动的剥削酝酿了一种劳工运动的可能,劳工运动“推动”着资本主义转向更 为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式;对自然的“剥削”导致了环境运动的可能,环境运 动“推动”着更为社会化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形式的出现。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取 决于工人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以环境运动为代表)这两种力量的结合。
二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而非生态合理性的社会,资本扩张在 经济维度上是没有严格限制的,而由于资本低估了自然的价值,它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 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的局限性。生态社会主义在揭示了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联合发 展和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具体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的恶化乃至全球生态 危机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
1、资本主义积累: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对利润的无休止的追求是资本的 本性,为了满足这一本性,资本就必须不断扩大积累。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积 累一方面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建立在不断扩大的对雇佣劳动 剥削的基础上。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亦即 随着生产率的增长,原材料在不变资本中从而在商品总价值中的比重也随之增大。如果 经济持续增长,对原材料、资源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增加(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对资源的 开发力度也就会不断加大,而持续扩大对资源的开发力度,又产生了环境恶化甚至是资 源枯竭的危险,从长期来看,这又有提高原材料成本的趋势,从而抑制了利润率和积累 的增长。为了继续扩大积累、保持利润率,资本(个体或联合)便会通过向设备、技术、 基础设施等方面扩大投资来开发新的资源,努力降低原材料的成本,以图克服生产条件 “瓶颈”的制约,如果资本的这种努力能够如愿以偿,亦即如果原材料的成本、价格下 降了,平均利润率就有上升的趋势,资本的积累和原材料的开发就会更快,相对于利润 率而言便宜的原材料,又会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进而产生资源耗竭的危险。由此可见 ,资本积累内含着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原材料的价格很贵,那么资本就会通过扩大 投资开发新的资源以图把他们的成本降低下来;而如果原材料很便宜,那么资本的积累 率及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程度也随之增大。不管原材料、能源的成本是 高的且是不断增长的,还是低的且是不断下降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都会带来投资规 模的不断扩大,而投资规模越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消耗就越大,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性就越大,环境污染的程度也就越大。这是资本积累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同时,提高 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程度,则直接导致了相对于资本生产能力而言的市场购买力的不断缩 小,从而导致了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其结果便是资本循环在流通领域的中断, 也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亦即价值的“实现性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同时存在于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二者之间 是相互推动的,由资本积累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会引发一定程度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由 于,资本自身积累导致的生态问题(原材料的短缺、能源开采成本的加大等),会带来对 利润的损害,同时,由生态危机而导致的环境运动也有导致经济危机的可能,以保护生 产条件与生活条件为目的的环境运动以及其他新社会运动,有可能会提高资本的生产成 本、从而危及或损坏资本主义的积累。反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 生态危机,为了缓解生产领域的“实现性危机”,资本家一方面通过大肆的商品广告和 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图歪曲需要满足的本质,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把追求消费 当作真正的满足,同时,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信用政策、消费政策来努力营造消费社会生 活方式的氛围,从而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这种过度消费的愈发膨胀, 严重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带来了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
2、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联合发展与全球化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通过对资本主 义的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的分析,揭示了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危机本质上 是一种全球性的综合危机。
不平衡发展这一范畴是指历史性生成的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等及其与政治力量 的结合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状况。不平衡发展一方面被解读为“发达国家”与“欠发 达国家”的关系,意指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同时也可以被解读为作为全球 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的基础的城市与乡村、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帝国主义力量与殖民 地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在工业化地 区会带来大量的污染,而在欠发达地区或者原料供应地则带来了资源的毁坏和衰竭。在 北方国家或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地区,由于工业、人口等的过分集中而提高了工业、市政 及日常生活废弃物变成污染的可能。废弃物和污染是两个概念,废弃物尽管也有毒害性 ,但一般地说,其程度很微弱,能够被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吸收,不会对人类和生 态系统构成威胁,但在发达的工业化地区由于废弃物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而超出了生态 系统“自净”能力的阀限,扰乱了这些废弃物向自然的回归,从而提高了污染的可能。 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的程度越高,这种污染的可能性就越大。关于这种观点,马克思 也早有过类似的论述。不平衡发展不仅是工业、商业、人口等因素在发达地区的集中, 而且也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和原材料的集中,而且也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和原材料 的集中榨取,从而导致了这些地区资源的毁坏和衰竭,主要体现在:土壤条件的不断恶 化、森林的过度砍伐以及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的等。迫于急切发展经济的压力,发展 中国家的或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过度地开发本地的资源,以出口到发达的工业化地区 ,创造尽可能多的外汇。而这些原材料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则恰恰是以污染物的形式表现 出来的。因此,从直接的或间接的意义上说,导致工业污染的那些自然因素,原本应是 以原材料供应地的土地和资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可是在这些工业化的地区,他们恰恰 是以污染物的形式表现自身,这就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内在逻辑。
联合发展是指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寻求政治经济的联合。当代发达国家资本联 合主要有两种表现:1、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人向城市迁移,以及南部国家人口向北 部国家的迁移;2、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向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和更具有市场潜力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输出。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在第一种形式下,无序移民向城市的涌入 不仅带来了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健康条件恶化等多种社会问题,也导致了农村劳动力 的短缺、农村土地荒芜和生态状况的恶化。而在第二种形式下,从北部国家转移到南部 国家去的不仅是资本和技术,而且还有一连串的环境和社会成本。首先,当代发达国家 不仅通过强大的资本寻求与欠发达国家的上层资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合,对这些 国家实施“结构性暴力”,体现在:在资本输入国,为了适应出口农业的需要,已经形 成了高度发达的专门化的、甚至是单一性的农业体系,大量肥沃土地被资本主义化,从 而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同时也把生存性农业排挤到了极其贫瘠的土地上, 为了维持生存,就必须对这些本来就极为贫瘠的土地进行过度的开发,结果导致了土壤 肥力的大大降低。而在经济困顿时期,不管是出口型农业还是生存性农业都会通过扩大 生产规模来维持收入水平,从而把自然条件推向了生态的极限。其次,而且也更为严重 的是,发达国家还直接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这里 的土地、资源、劳动力,甚至把垃圾场建立在这些国家,严重地污染了这里的环境。当 发达的管理模式、技术、和资金筹措方式在出口地区与更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联合起 来的时候,伴随着生态的恶化,联合的发展还会加重不平衡发展的程度,使得出口地区 更加的落后,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剥削关系、并伴之以职业健康与安全、交通、社会秩序 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出现。
发达国家正是通过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实现了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 成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枯竭。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消 耗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资源,而且还利用它在资源耗费方面的优势,对本国 资源进行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从而剥夺了这些国家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权利,此外,长期以来历史性形成的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与南 部国家农业产品及原材料的价格的剪刀差,使得发达国家与南部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 化,导致了落后国家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代的发达国家对第 三世界国家的这种“生态殖民主义”的掠夺性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犯罪,是资本唯利 是图、不计后果的本性在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与16-17世纪的贩卖黑奴、18-19世纪的 商品输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
作为产生于当代西方的一种“绿色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超越 了生态主义等其他绿色理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认识,主张“从深生态走向社会正义” ,并从理论上展示了生态危机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 自然本性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只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根本避免生态危机, 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这一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某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具有宝 贵的启迪意义,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开拓了新的空间。但生态社会主义毕竟产生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加上与早期 主流绿党(以生态主义为基础)有着不可解脱的渊源关系,从而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生态主 义乌托邦的色彩,尽管生态社会主义者自称以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理论 根基来审视当代资本主义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但却未能将其贯彻到底。它 在给予当今全球生态危机以高度的理论关注的同时,片面强调了生态问题,仅仅立足于 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企图以人类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的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生态危机取代当代资本主义的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危机的界定,模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主要矛盾,迷失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斗争的方向,消解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 着力点。”[2]由此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不可能承担起对资本主义彻底批判的历史重任 。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这种两面性,我们应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进行具体的、历史 的分析。
收稿日期:2003-11-21
标签:生态危机论文; 金融风暴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