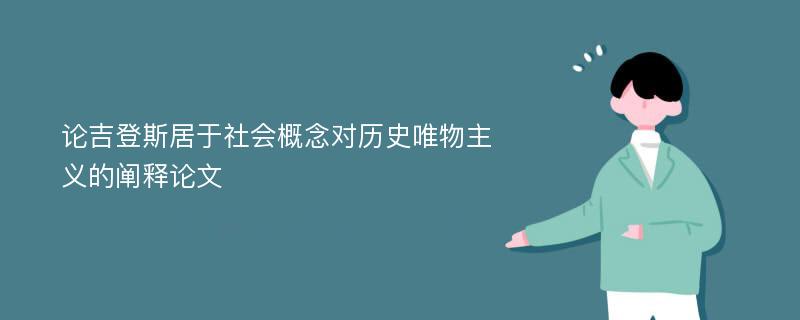
论吉登斯居于社会概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
杨亚玲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 安东尼·吉登斯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家,以社会特征的界定为基础解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并将监控概念、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引入到社会历史观领域。了解吉登斯关于市民社会的有关阐述,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21世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更加深入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社会;国家;资源;第三条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内涵,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和发展状况的独特阐释与批判,在人类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现实的各种变化,以及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解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也成为思想界和理论界持续不断地环绕的重大课题。当代很多理论家,如阿伦特、哈贝马斯、波普、吉登斯、伊格尔顿等,都从不同角度参与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既有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颠覆性批判的观点,也有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重建的思路。相比之下,当今最重要的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陆续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民族一国家与暴力》《超越左与右》“关注历史唯物主义三部曲”系列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做的解读具有独特性。吉登斯从对社会特征的阐述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和反思。了解吉登斯有关思想,有助于研究者更加全面地把握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更加深入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的开篇,吉登斯对以往社会概念进行了梳理,将以往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社会概念划分为三种:“一是把社会描述成一个由‘功能相关的要素’所组成的体系,这种观点见之于学院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二是把社会看成是‘表现的整体性’,一种主要受黑格尔影响的人所持的观点;三是把社会看作是层级或者场合的统一,一种在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那里极有市场的观点。”[1]42吉登斯将以上三种社会观称为“传统的社会观”。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功能论与生物有机体的功能类似,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功能统一体,强调社会是由连贯而一致的原则所组成,把规范一致性作为社会整体性的主要基础。在对传统社会观批判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观,为“社会”应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占有特定的社会空间,尽管可能边界模糊或者只是临时占有。二是对所占有的社会空间拥有各种合法的特权,尤其是利用其物质环境以获得食物、水、住所等资源的特权。三是在社会系统中,成员之间通过一定的整合机制得以维持,当然整合并不代表所有成员具有一致接受的“普遍价值体系”。在吉登斯看来,不同社会类型整合机制是不同的,如传统文明中,统治阶级维持着一个将大多数臣民排除在外的“政治话语”领域,各行各业都存在准“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四是带着某种认同感对归属于某一包容性共同体具有普遍的意识。在吉登斯看来,没有哪一种社会的存在可以与其他社会孤立开来。这既适用于小规模的原始社会共同体,也适用于现代民族国家。
在吉登斯看来,在前现代社会,国家缺乏程式化地形构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力,“乡村社会”基本是一种自治性质的组织,“在传统国家中,由国王或皇帝统治的大多数人对统治他们的人很少有意识或兴趣。他们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或影响力。一般来说,只有统治阶级或较富裕的群体对整个政治团体有一种归属感。”[2]533由此,吉登斯的结论是那一时期的乡村社会与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并不等同。而在吉登斯看来,随着由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兴起,监控能力的发展也达至极致,所有社会领域都处于政治权力的监控之下,政治权力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独立的市民社会根本不存在。“在吉登斯看来,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能够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领域,而是被置于国家的统摄之下”[3]42,市民社会的权力和特权“不应被看作是在国家领域‘之外’创造的,而应当成是‘公共领域’从‘私人地’组织起来的经济活动中凸显出来的组成部分”[4]42。在吉登斯看来,市民社会完全是一种虚构的想象物,独立的市民社会根本不存在。在吉登斯的系列论述中没有直接给出社会这个概念的定义,在一定意义上吉登斯将国家与社会同等使用。如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吉登斯多次强调“传统国家即我称之为阶级分化的社会”[4]2“资本主义国家则是阶级社会”[4]3,“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义词”[4]169“历史上凡是资本主义社会就都既是工业化社会又是民族国家”[4]169“‘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社会,仅仅因为它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具有业经划定的国界”[4]176。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将国家既界定为“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也指“社会中特定的政府体制类型”[5]364;而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吉登斯则称“国家有时指政府机构或权力机器,有时指归这种政府或权力所支配的整个社会体系。”[4]18从吉登斯的论述中可知,在侧重强调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时,使用的是国家一词,当侧重强调国家的管理对象是整个社会体系时,则用社会代替国家。
我说,估计是个小偷,看见我吓跑了。刘伟说,我们快撤,去蓝夜电影院拿钱!我惊慌起来:“你们干完了?就这一会儿你们就干完了?”“你做得很好,”刘伟说,“完事了,意想不到的顺利!”
吉登斯将国家与社会同等使用的前提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误读。
由这样的前提出发,理论上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之前的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主要靠血缘、信仰、宗族等为纽带,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这样的一种关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决定作用。由此吉登斯自创了两个概念“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指人们不仅对“客体”而且对客观世界所拥有的控制能力,即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权威性资源则体现为对人类所创造的社会世界本身所具有控制能力。在一定意义上,配置性资源相当于马克思论述的生产力,而权威性资源则相当于生产关系。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之前的社会权威性资源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力。而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也就是配置性资源对生产关系即权威性资源才具有决定作用,以此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意图重构马克思唯物史观,否定生产力对全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曾指出,生产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前提,是所有其他社会制度得以建立的必要基础,“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人类要生存发展必须首先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因此,我们必须断定生产力变化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媒介。吉登斯承认配置性资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决定作用,其实就已经承认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之所以吉登斯否认生产力对全部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恰恰是因为在理论研究上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整合机制而忽略市民社会产生的物质生活基础。
在普遍意义上,认为市民社会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6]40“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7]130-131即使生活在原始群体中的人类,只要有需要便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也就是说当人们为了满足需要相互合作地去劳动时,这一劳动过程本身已使人们结成某种社会关系。即在劳动过程中有内在联系的相互关系的总和组成了某种社会结构,所有相互处于这种关系的个体组成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并非任何一种个体的联合或是集体就是一种社会,而是侧重从经济的角度解释社会概念。在某一经济方式产生作用下形成的集体,处于这一集体中的成员因为某些由经济所决定的生活关系而彼此产生关系,这样的一种集体称为社会[8]12。这里核心含义是,社会被视为满足一般的经济需要并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共同生活和协作。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阶段就是按照经济方式来确定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7]81马克思经常使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手工时期的社会”等,认为“整个经济过程的意义是保持和更新社会”,因此,马克思也把生产过程称为“社会生活过程”或者是物质生产过程,这几个词的含义是相同的。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过程在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的同时,也为经济活动的继续和更新创造条件,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写“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6]994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即便是原始社会也是建立在经济过程的基础上,并由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将社会团结在一起。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
可以看出,吉登斯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在国家行政权力的范围内界定的。吉登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所不在的监控已经使人彻底丧失了自由,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监控对生产生活领域的控制还没有侵入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可以说,吉登斯对监控概念的引入是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有益补充。但是,吉登斯只看到了政治上监控的发展,忽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作为特殊的商品所具有的权利,所具有的缔结各种经济关系的自由。
在吉登斯社会历史分析中, 监控是各种类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传统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核心线索就是政府监控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在吉登斯看来,从绝对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动,一个很显著的标志就是系统收集“官方统计数据”的出现,通过信息的储存和控制来动员行政力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数据收集仅就国内事物而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与税收,另一个是人口统计。人口统计直到18世纪还只是地方性的,而不是统一的。财政与税收证明了财政管理的重要性。从18世纪中期开始,所有国家的官方统计都保持并扩展了这些内容,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且第一次做到详细、系统并接近完备。其主要作用在于,聚集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需要运用的行政力量。在传统国家的地方社区里,习俗、传统、血缘、宗族等关系是将民众联合在一起的主要力量,农民如果远离国家权威的武装力量的主要集中地,或离开当地的领主,就不能有效地防御强盗和武装侵袭者。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人口大规模地从农村迁往城市,那种将信息方面的监控及监管方面的监控结合起来的现代治安,才成为可能。监控的另一个体现是在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中将劳动力集中起来,使“隐患的阶级压迫”和监控成为可能,从而取代了使用暴力进行直接压迫的可能性。当然,雇主放弃使用暴力,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工人发动的阶级斗争也常常动用了暴力。吉登斯借用福柯的思想,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监控无所不在,批驳福柯只看到监控会制造出“温顺的身体”,没有充分认识到那些屈从于支配集团权力之下的个体本身具有丰富的知识,会抵抗、破坏或积极改变他人强加给他们的生活条件。在吉登斯看来,政治上的契约自由和结社自由帮助促进了劳工运动的发展,既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构成了挑战,也是促使其变化的一大力量。这种对统治模式及其所引起的被统治阶级对之的反应方面的研究一直被其他的社会学研究者所忽视,由此吉登斯阐发了监控与反监控的控制辩证法的理论。
马克思和吉登斯在市民社会的阐述上有一致的地方,都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独立的市民社会不存在,国家和社会高度一致。而分歧在于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摆脱了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束缚及人身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完全自由的劳动力,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作为特殊的商品进行“出售”并在这一过程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更强调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的经济关系。而吉登斯则强调不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独立的市民社会不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存在,因为“监控模式既成为经济组织的关键特征,又成为国家自身的关键特性。”[4]98由此吉登斯将监控这一概念引入到社会历史观领域。
单桩嵌岩工艺3的具体流程如图3所示,该工艺增加了辅助沉桩的钢护筒。首先将钢护筒打至岩层表面;其次在护筒内下钻机,钻至设计底标高处;此后,将钻机取出并将单桩放入钻好的钻孔内;再次,在桩外侧及钢护筒之间灌注混凝土,即灌浆环节;最后,将钢护筒拔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市民社会最典型的状态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要是指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摆脱了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束缚及人身依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民”个体所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合,体现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的个人(“市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与社会完全不同,国家不是社会,也不是某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公共的共同体,也叫政治集合体,是一种宪法组织。这里的宪法指的是任何一种将共同体成员联系起来并使其相互负有义务的法律调节。国家不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国家和社会是共存的,无论就其范围、界限还是生活内容来说,都不是相互重叠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现代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是由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位置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经典定义来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 毋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7]228
二是在发展阶段上,分为“旧市民社会”和“新市民社会”两个阶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把封建社会时期的市民社会称为“旧市民社会”,中世纪“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这也就是从古希腊到近代契约论思想家所使用的传统意义的市民社会,其与政治社会是同义的,存在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高度重合的状态中。而“新市民社会”始于与政治国家的现实分离,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表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自主组织。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在《法哲学原理》中阐述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认为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原则和基础。马克思任《莱茵报》主编之前,持有同样的观点。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通过直接参与革命实践活动,动摇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通过系统地研究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及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1843年形成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第一部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著作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得出了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市民社会本身作出科学的分析,系统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综观马克思论述市民社会理论的著作,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过市民社会概念。
(2)压缩机压缩液化过程:10 m3储罐内的BOG经阀门V2、2 m3储罐内的气体经阀门V3进入压缩机加压后,经阀门V5进入10 m3储罐液相空间;当2 m3储罐压力降低时(罐内气体基本被抽空时),关闭阀门V3,打开阀门V1,继续上述压缩液化过程。
在实践上,正是因为独立的市民社会研究的缺失,导致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具体政策的失误。2015年4月3日,吉登斯接受意大利《共和报》采访时直言由他所倡导曾在欧洲各国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实践已经失败。吉登斯将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归因于“语境变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打破了过去的确定性”[9]。吉登斯之所以做出如此悲观的判断,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倡导“第三条道路”,一个主要用意在于应对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试图借助“第三条道路”重建社会主义的原始理想。但最终吉登斯却认为正是由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导致“第三条道路”已死。我们承认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正是资本主义深度扩张的结果,也是吉登斯反复强调的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但是导致“第三条道路”已死的根源并不在这里。“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抛弃意识形态信仰。淡化党的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奉行“没有左派、右派之区别,只要行得通就是好政策”的实用主义;左翼身份特征的丧失。在政治战略上摆脱传统工人党形象,缺乏工人阶级这样长期稳定的支持力量,是“第三条道路”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国家治理政策的矛盾。吉登斯强调政府职能一部分下放给市民社会,一部分则需上移至全球治理的层面。但吉登斯在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中多次强调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原则上和国家是同一的。在批评马克思国家起源于市民社会的理论的同时,也使其在国家治理问题上,存在市民社会只能承担一部分社会职能这个现实问题,而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全球治理机构,这样的机构目前来看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区域性机构欧盟,英国民众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在脱欧问题上何去何从。归根结底吉登斯试图以“第三条道路”重组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复兴社会民主主义,但在具体实践上,西方社会缺乏牢固的社会主义基础,“第三条道路”倡导者并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只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良,最终完全倒向了资本主义阵营。
应该说,吉登斯是在一种反思的立场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理论分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提出某些质疑和修订,并非是要全盘否定马克思理论,而是立足于人类历史发展现实,试图通过找到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的悖论和困境,以期修正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展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尽管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一些观点是不能接受的,需要把这样的一些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置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置于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置于同其他新马克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比较中”[10]22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该课程中使用的形成性评价指标有:公司考勤、经营进度、过程正确率、经营能力提升度四个大类,每一个评价指标都在形成性评价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M].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蒋红.论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
[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5]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陈玉玉.浅论黑格尔市民社会观与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差异[J].商城现代化,2010(2).
[9]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之死[EB/OL].(2015-04-13)[2019-06-2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9990.
[10]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On Gidden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ociety
Yang Yaling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3, China)
Abstract: Anthony Gidden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ker in today’s society, analyzes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monitoring, allocation resources and authoritative resources into the field of social history view.In this sense, understanding Giddens’ exposition on civil societ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o display more deeply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t social history theory.
Key words: society; countries; resources; the third way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99(2019)08-0022-04
doi: 10.3969/j.issn.1674-9499.2019.08.009
收稿日期: 2019-06-03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解析吉登斯对唯物史观的解构与重建”阶段性成果(2017BZX005)
作者简介: 杨亚玲(1971—),女,黑龙江桦南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慧慧]
标签:社会论文; 国家论文; 资源论文; 第三条道路论文;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