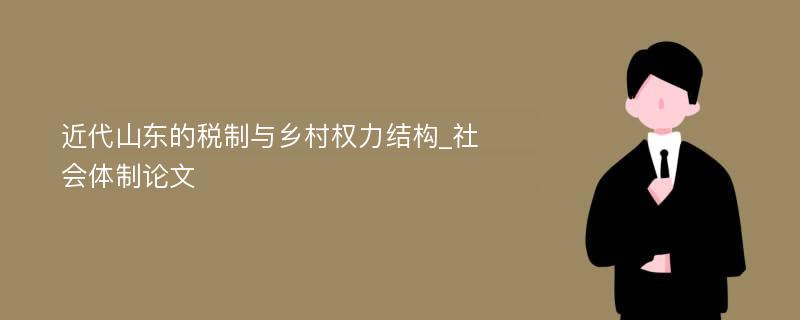
近代山东的征税体制与村落权力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东论文,村落论文,近代论文,体制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D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2—0106—08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中,农业生产剩余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在农家经济不发生大波动的情况下,“纳粮完税”成为传统农民的基本信条。国家权力对村落社区的控制,正是通过建立相应的征税体制而得以实施的。本文拟在村落社区的分析层面上,联系市场体系、农家经济等相关因素,研究村落社区与国家权力的互动过程,借以透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之底蕴。
一、农民负担的日益沉重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近代山东社会经济体系中,与土地占有、土地经营直接相关的就是以田赋为主的征收。清季田赋种类繁多,概而言之,有地丁、漕粮、租课及附加税。从前赋出于地,役出于丁。清初,地与丁分开。至康熙末年,因征收困难,遂将地赋与丁赋合并。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丁粮均派入粮银内合征,从而相沿成习,民国时期亦沿用旧制。漕粮、租课则不是遍及全省的税目。在清代,漕粮即是派实物,由水道转运京城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漕运范围只限江、浙、赣、皖、豫、鲁等省份,山东有漕粮者也仅65县。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运停止〔1〕( P470)。租课是国家基于土地占有权而征收的租税,山东省在清季有学租、余额地租、柳园地租、荷花池地租、屯租,名目繁多,但租课征收地亩范围毕竟有限。民国时期,漕运已停自不必说,即使租课与乡村民众也无太大的利害关系。
与田赋正税相连的是附加税。在清季始于咸丰初年,至光绪年间附加的税目渐多。民国时期,附加税中又分省附加税和县附加税,省附加税为山东省首开先例。1914年,当时属于直隶的濮县黄河决口,山东、河北两省筹款协修,奉北洋政府令,每地丁银一两,加征洋二角二分,合正税的1/10,名为濮工附捐。1925年,张宗昌开始督鲁, 附加税增至10余种之多,有军事特别捐、军鞋捐附加、军械捐附加、建筑军营捐、讨赤捐、印花捐、兵费、善后公债,甚至人捐、狗捐、牛捐等等,巧立名目,花样繁多,“各县均受其害,其中受害最烈者即为农民”〔 2〕。1928年以后,田赋和附加税归省政府支配,作为补偿,省政府允许各县在原有附加之上再为附加,收入归县政府开支。韩复榘统治时期,附加税捐有增无减,统计全省附加杂捐共689种,主要有地亩捐、 民团捐、教育捐、银行捐、建设特捐、戏捐、门牌捐、航空捐等十几种。财政厅长王向荣在奉行政院命令整理山东田赋及附加时,曾通令各县附加总额不得超过正税之数,“其已经超过正税之各县,不得再行附捐,并须陆续核减,至多与正税同数为止,自应切实奉行”〔3〕。在当时, 这只不过是应付上司的官样文章。实际上各县田赋附加税大多远远超过正税,如《田赋会要》所载,在山东新泰县,附加税占田赋250%, 即墨县占120%以上,临朐县占300%以上。
田赋附加和苛捐杂税,在政府“田赋整理”和“废除苛捐杂税”运动中,即使得以减低,地方政府也会采取其他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摊派(包括钱款和实物)遂成为主要的非常规性财政来源。摊款在清代一般是为了应付地方性的财政需要,如兴办公共工程,才向百姓摊款并派工。民国成立以来,战乱不断,地方政府也日趋军事化,临时性的摊款就成了地方军阀及各级地方政府搜刮乡村财富的重要手段。1932年,旧济南道属21县中,区、乡镇和村摊款每两粮银合106.28元,主要用于行政开支〔4〕。特别是一遇战事,为应付兵差而设的摊派就更多了。 王寅生分析:山东有些县在1928年7月~1929年6月一年的兵差总额平均竟占地丁正税的274%以上,“然而当时这些县份不但不是战区, 并且不是备战区或战区的后方。在备战区或战区的后方,兵差底数量更要巨大”〔5〕(P67)。在军阀混战波及地区,农民财产、人身安全除受战争直接侵害外,尚要承担兵差和摊派。1932年,韩复榘与胶东军阀刘珍年大战,“掖县为双方炮火集中点,受害尤重。战争发生后,筹备给养约值十万余元。自刘珍年自行筹备给养后,民间一切金钱、粮食、牲畜、衣具、古珍、字画等凡民人所有,悉数被搜去,虽一草一木,并无存留”〔6〕(P15)。附加税和摊派数额大大超过田赋正税,使农民的负担极为沉重。
二、度量衡、币制与田赋征收的弊端
在田赋征收和摊派过程中,经征人员营私舞弊、任意浮收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对贫困农户无异是雪上加霜。而度量衡、亩制和币制的混乱,使田赋征收制度更趋不合理,其中亩积因田赋科则而有差异,且官定亩与乡间习惯亩也有不同,更给胥吏、里书、乡约、地保利用地籍混乱从中渔利提供了便利条件。又因币制不统一,致使在田赋征收中因银钱折合而引起的官民冲突也时有发生。
就田赋科则看,山东各县多以土地肥瘠原因分为上、中、下三等九则,分别课税,每亩收税不同,而亩额一致(指税亩每亩弓步数在一县之内是统一的)。如恩县按地亩种类分为成熟一例大粮地、成熟荒田地、成熟更名地、河滩籽粒地、学田地等共有21类,每亩弓步大小一致(每弓步4尺8寸),折合市亩9分2厘,税额由银三分至银九分不等。而历城县的情况则有点特殊,“以土地肥瘠之互异,与每年收益之丰啬,共分为六等,而以金、银、铜、锡、铁、湖田等名之,不以每亩粮银之多少宽寡不同而分上下,其乃以每亩之粮银虽同,而以每亩面积大小之互异而分之,其最小者为二百四十弓一亩,最大者有七百二十弓一亩者”〔7〕(P11316)。科则不均给土地丈量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也使土质认证、土地面积陈报带有更大的主观随意性。
民国时期,历城田赋税则仍遵清制,而随着自然条件的变迁和耕作方式的改进,同一块土地肥力也有很大变化,“昔日不毛之地,今则垦为良田沃野;昔日肥地今则瘠薄,……故辄土地肥沃者,税则甚轻,土地瘠薄者,反负重税”。此外,在土地买卖、典押等地权转移过程中,乡民以习惯亩制进行交易,一县中亩法不一。“其原为六百杆一亩者,则转卖为三百六十杆一亩,再转移即为二百八十杆一亩,如是亩之亩积虽改,而每亩所负之税则一也”,遂致“有地无粮,与有粮无地者,几于各村皆有之,故今之地籍与税则相合者,尤为罕见”〔7 〕(P11414)。胶县、即墨地方亦有如此者。即墨县“计亩旧规,近城五里内土脉稍厚,则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离城五里外地土稍薄,则以三百六十步为亩;新开荒地,请以五百步为亩”〔8〕。
在全省范围内,田与赋相分离的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各县征收田赋,所据亩法不一,从240方步到960方步,相差悬殊;且各地弓步长短不齐,有三尺二寸为一弓步,有以四尺八寸为一弓步等等,遂使各县之间亩法大小不一现象更趋严重,地政失修,田地之荒辟增减,多任人自报,田与赋不相吻合,且有日渐分离的趋势〔9〕(P126) 。王翕如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曹县县长,力图整理该县田赋,也发现曹县境内48里(“里”为基于地缘因素的乡村社区组织,同时又为一纳税单位)中,各村庄田赋负担畸轻畸重,相差悬殊,“土地生产的能力相等,而每亩所派银两不同;土地生产能力不同,而每亩所派银两相同”,且也存在“有地无粮、有粮无地”之现象〔10〕。
币制因素在田赋征收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清季,山东省钱粮征收单位,钱以上例征银,不足一钱以钱折银完赋。嘉庆年间,巡抚铁保以山僻小邑无钱铺,以钱易银交纳不便,奏准照时价以钱代银。不少州县每两有收至五千二三百文甚至六千六百文者,后清政府虽把银价定为每两四千八百文,但仍较时价为高〔11〕(P351)。宣统年间,海阳、莱阳两县的具体办法是搭配三成制钱七成铜元,由此激起了以曲士文为首的抗粮运动〔12〕(P173)。胥吏、里书、乡保等田赋征收人员均利用银钱折合制度从中渔利。历城县“诸粮银,皆按银两计算,其征收则用银元收入,甚至亦有用铜元完粮者。因此由铜元为银元,由银元合为银两,其每次计算,(经征处)书记未有不从中取利者。……农民粮银,为正数者甚少,多为几两几钱几分几厘不等,故书差折合时易于浮收。普通银元市价为八千二百文,然经征处挂牌,辄为八千三四,如有角分厘等,合为八千五六者亦有之。故农民虽知多纳,然习惯如此,相沿已久,农民多视为当然,未有与之诘问者”〔7〕(P11416)。
一般小农种地不多,接到由县长签署的串票(俗称“要钱单”)后,一则因不识字,二则因距县城路途遥远,往往托里书或庄长、地保代纳,或由粮差包征间接完纳。征粮时,内勤人员多用官衙门旧有房吏,“外勤人员有里差、里书、乡约三种,里差司催征揭底,里书司过割办理征册,乡约司丈量地亩、催税文契事务”〔13〕(P6929)。 乡约在丈量土地时易做手脚,更有里书代小农纳粮,之后索要高额利息者。
三、征税与乡村行政体制的演变
国家权力对乡村的社会控制,正是在征税体制中建立的,甚或基层的行政组织建制与征税组织系统高度重合。晚清时期,清政府除地方行政官员外,用以深入农村统治结构的下层网络是一个虚弱的、有缺陷的系统。当中央政权自身变得无能为力时,县级政府极端腐败并高度依赖乡绅去完成治理乡村和征税的任务。在地方政府—士绅—村民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士绅在完成国家权力对村落社区的社会控制职能方面,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晚清甚至民国初年,在山东农村有不少这样的乡绅,因其背负儒家典籍文化和乐善好施的道德行为而为周围村落成员所拥护。如平原县城东北冯庄村冯氏兄弟,“皆乾隆间廪生,富而好善,乡邻有丧葬婚聚者,问系贫家,无不尽力资助。多为干糇,以予饿者,捐资以修鸡鸣寺,并捐田若干亩,以广寺基,立有碑碣。贷钱与粟于人,不能偿者,悉焚其券。子孙守其训,累世以善人称”〔14〕。
民国初年,虽因科举废、军阀兴,传统士绅面临断层的危险,但仍然在一个比较短的历史时段内发挥其作用。东平县巩家楼村士绅巩象临,民国初年在宣扬儒家文化、协助县政府完成征税摊派任务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地方社会日益军事化的民国时期,与传统士绅同时并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地方豪杰、不法商人、土匪等各色人物,他们参与地方性公共事务,以填补传统士绅逐渐减少而产生的权力真空〔15〕。在章丘县第八区张家庄村及附近各村,这两类人物即同时共存。该村“人心涣散,民情嚣浮,但亦有忠厚诚实之老先生”;同时又有土豪般的“象”(乡人呼柔懦者叫“孙”,强暴者叫“象”),“象们大都依包娼窝赌为生活,若农夫之有田。直接以肥丰自己,间接以鱼肉乡民。村中巨头,多与阴合,甚或勾结若辈,以为己力,狼狈为奸。记得蒋家庄因修桥劝捐,无人肯施分文;后宴请几位象爷协助,其庄竟输出六十余元!可知象们在乡村之势力矣”〔16〕。
清末“新政”的实施,促成地方自治浪潮的兴起,反映了政府系统充实、完善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尝试,建立新式学校、警察制度是其主要内容。所有这些制度安排都需要较前为多的经费,政府困于财力就不得不将所需经费转移到村庄的层级上。民国初年,军阀战争频仍,地方政权的军事化程度日益提高,上述趋势就得以延续并有所加剧。为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保障日益繁重的税收及摊派,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建立并强化了县级以下的行政体系,进而影响到村落行政组织的变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县以下只设一级行政组织,其名称沿用清光绪末年实施新政时颁布的《城镇地方自治章程》之规定,凡府、厅、州、县所在的城厢地区称城;人口聚居满5万人以上的村庄、屯集称集; 人口不满5万的村庄、屯集称乡。1914年春, 袁世凯下令停办地方自治后,实行严密的乡村保甲制度,即以自然村为单位设保,保下设若干甲;保长为一村之长,也是村级政权的行政负责人, 山东省即照此办理〔17〕(P369)。
韩复榘主鲁时期,山东省县以下设区、乡两级行政组织,且逐渐稳定化。在一般县份,一县之内有区10个左右,一区有乡10个左右(一乡包括几个自然村)。省政府颁有《山东省各县区乡(镇)长任用办法》,规定由30岁以上,在地方享有威望,未受过刑事处分,且体魄强健者担任。对村落一级的行政建制,韩复榘治下的省政府则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保甲制。“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属于乡镇”〔18〕(P396)。办理保甲制度的目的在于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而由于“无恒产者”不得充任保甲长,因此在乡村社会分化条件下,村落行政权力只能由所在村地主、富裕自耕农及其追随者所享有。
保甲制度虽为政府强加给村落社区的行政组织系统,但其制度安排也是建立在村落社区内地缘、血缘关系相统一的内源结构之上的,所以保甲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村落社区内源结构。甲长实际是几个家庭的家长代表,负责征税、摊款和村庄日常公务的则是保长。有的村落不称保长而称村长,甚至沿用清代的“地保”名称。保长、村长、地保不一定是村中最为富有之人。在青岛郊区农村,“普通每村有村长一人,街长一人(即副村长),首事若干人,地保一人或二人。首事系依氏族支派或房宅地位(如前街后街,河东河西等)分别推举。村长、街长再由各首事公推之,村长对内掌理支配全村之钱粮打更等村务,对外代表本村办理各事。遇有较为重大或繁剧之事,由村长召集街长及各首事商讨后,分头办理。街长首事居于辅佐村长之地位,有时街长首事亦得代表村长对外办事。村长街长首事均为义务职。地保以雇佣者居多,每年工资约三四十元或酬地瓜干六七百斤。其兼管看坡(即看青)者,每年工资六十元或酬地瓜干九百余斤。”〔19〕在青岛附近农村,村长、首事职位的产生是建立在街坊邻里和宗族血缘关系合一基础上的,可以说村落行政组织与村庄自治组织是结合在一起的。至于地保一职,看来不是村庄行政组织中的显要职位,有兼管看青者,更说明担任该职的村落成员多是少地、无地的贫困农民,故此“地保”一职与前述保甲制中的“保长”是不同的。
随着保甲制的实施,县、区政府可以通过保长(村长)、联保主任(几个相邻村庄合设)来控制乡村社会和落实征税、摊派事务,故可取地保而代之。保、甲长的名称是保甲制的直接产物,但保甲制也是以村落地缘、血缘关系结构为基础的,故保、甲长往往是从宗族、街坊中产生的富裕且有威望之人,实际是村庄的自然领袖,冠以保、甲长称谓,只是村庄首事的代名词而已。
四、合法性危机:乡村权力体制创新的困境
日益繁重的赋税摊款与渐陷困顿的农家经济同时并存,使征税、摊派任务变得愈加困难,政府强征硬派,村民怨声载道。而县区政府的行政任务必须完成,乡长、村长(保长)两面受气,进退维谷,因此,有些品行端正的乡长、村长不愿承担这项苦差,甚或有人为避苦差逃往外地。崑嵛县文城区柳林村的在村地主陈树亭,因怕当村长惹事而逃往大连“避难”。同处胶东半岛区的乳山县刁家沟村,村长刁永禄也因不愿应付同时来自日伪政权和抗日根据地政权双方的征粮任务,而逃往烟台〔20〕。选择逃亡毕竟是特例,原村长逃走,粮差总要应付。
一般情况下,有威望、能力强、为人正派的人士虽不愿就任村长一职,而在村民的坚决拥护和共同推举下,仍然能担任村长职,如历城县冷水沟村长杜凤山。在有些地区,或由多人轮流任村长,以分散应付繁重征税和摊派任务所带来的压力,甚或由村中土豪劣绅之类的人物担任村中公职,借征税、摊派之机以肥私。在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1937年前五六年间一直由贫农韩希来任村长(即保长),其后台是当过堂邑县公安局长的居乡地主韩友奎(绰号“韩大肚子”、“韩师爷”),但在1945年前的8年内,却换了6任村长。像韩希来,“对外说是保长,实际上光是跑腿”〔21〕。
盐山县(今属河北省)魏桥村,处于日伪据点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村政权为完成沉重的摊派任务,不得不向村民强行征收,“如有很贫苦的花户,拿不出资敌款(指来自日伪方面的摊款——引者注),有六户被村干把门摘去了,有五户被村干把被子(仅有的)抱去了,因纳款而将要下口的粮食(仅有的)被敛去者不计数,穷人哭嚎连天”。而村行政人员因持办公差理由不纳款,也不出人工。其背后支持者有三人:李凤鸣是个流氓,当过土匪,与区政权有联系,甚至抗日根据地的区上干部至该村也在他家吃住,老百姓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二区长”;魏秀云,干过土匪,又在民团当过“二团头”;魏保文在村内占地最多,曾当过村长,与村外权势人物结交甚广,在魏氏宗族中有很高的威望。更不合理者,是这三户所谓的“后台”也不纳粮款,不出人工〔22〕。恐怕像魏桥村的情况,在山东全省也是普遍存在的。对交粮纳款这样最为现实的利益问题,已不能用简单的儒家人格分类学模式来评价村长的公务行为,但至少可以说明,民国时期基层政权的人员构成存在着一定的土豪劣绅化倾向。拆门板、抱被子、强敛粮食是正直者不愿为,也是传统乡绅所不能为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乡村行政人员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而是要分析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更深层的乡村权力结构变动。从以上征税、摊派的资源分配模式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动员乡村资源的权力主体已与清代有很大不同。清季及此前,乡村权势人物主要由科举人士的乡绅组成,他们在政治文化上认同皇权,并受到科举的由上而下的制度约束,虽无自下而上的社会制约,也不致恶性膨胀。清末民初,政府没有建立起吸纳乡村上层人物向上走的制度性渠道,地方自治的兴起又扩大了他们在乡村中的权力资源。在地方政权日益军事化、地方社会无序化加剧的情况下,其权力又逐渐膨胀,以致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提出限制“土豪劣绅”的政策主张。
在以征税为核心的乡村权力结构中,基层行政人员的土豪劣绅化,实际上是村落社区与国家权力矛盾尖锐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纳粮完赋、应付摊派对于村落成员来说,其负担甚或远胜于佃户交给出租地主的地租。有些在村的经营地主为减少田赋和摊款负担,而变雇工经营为租佃经营。在清末的抗粮运动中,有乡绅和村中富户为首领。在抗击土匪、应付官差上,雇农、佃农与地主还能形成利益上的联合等等,均说明国家权力(通过地方政府)与村落社区的矛盾已经达到相当尖锐化的程度。
在乡村社会中,一般民众与基层行政人员、乡里恶霸的冲突已超过贫困农户与地主阶层的矛盾。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莒南县大店区因大地主比较集中,就被作为运动的重点县。中共莒南县委始终把减租减息作为运动的首要任务,在斗争策略上,利用群众对恶霸地主封建政治统治的不满情绪,通过反霸而最后达到减租减息的目的。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反霸压倒了减租减息成为斗争的主要内容〔23〕(P121~129),说明大店农村阶级矛盾在政治领域的激烈程度,已远远超过经济领域。
大店区地权较集中,即有如此情况,而在土地占有权相对分散的山东其他地区乡村,更是如此。在胶东半岛区的平东县(今为青岛市辖县级市平度市)南村镇西北街,有几户小地主,拥地最多者120亩, 最少者仅3.5亩,南村镇西北街除张祥兴家占地较多,人均13亩, 其他各户人均最多不超过5亩〔24〕。其所以被定为地主成分, 是因为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或独霸一方、为害乡里。这一个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村落社区内的一般贫苦农民甚至富裕自耕农,与代表政府权力的乡村土豪恶霸的矛盾,超过了基于土地占有和经营关系的经济剥削。也正因为源于征税体制的国家权力与村落社区的矛盾冲突如此尖锐,才导致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即是其行政权力的运作失去了一般民众的文化认同。而山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因有乡村群众的广泛支持而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再进一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民国时期政府系统的制度创新极其缺乏,只是在法权意义上调整地方行政建制,而在土地制度创新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上却基本没有见诸实效的建设举措。南京国民政府“废除苛捐杂税”、“打击土豪劣绅”、推行地方自治(如县政建设、新县制、保甲制)等所谓“复兴农村”、“改造乡村”的种种政策主张和制度安排,有的流于表面文章,有的因乡村社区内源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而很难发挥实际作用。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级政府除征税外,其职能一直没有渗透到村落社区中去。南京国民政府在创设区级政府建制时,也曾设想区级政府不仅要统计人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而且要承担起地方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职能,如兴办教育、推进地方自治、发展经济等,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征收赋税和摊款成了区级行政组织的主要职能〔25〕(P35)。
村落社区内源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也是制约政府制度安排缺乏创新意义的主要原因,正如傅斯年先生所分析的鲁西北乡村社区组织状况:“村与村的生活,各自独立。联村的‘团’、‘乡’等等,简直就是有名无实,除当土匪的骚扰时代,用以自保外,只有应酬官差的一条用处。……一村的自治有‘公看义坡’——即所谓的‘守望相助’、公应官差、公设一两个学房(私塾)、公修围墙庙宇等。但这些事项是为防御而设的多,为发展而设的乃‘绝无仅有’。”〔26〕有鉴于此,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弊端,并呼吁要在乡村社区内“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27〕(P494)。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这一理论认识带有深刻的洞察力,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客观历史实在。但他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依此实施的“乡村建设”实践,却是所谓“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28〕,正说明通过外在力量推进乡村社区组织创新的艰巨性。
总之,清末至民国时期,政府的一些制度举措对村落社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不能说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建设意义乏善可陈,但无疑也在改变征税体制的同时,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对乡村的掠夺远远超过建设,从而使基于征税、摊款所产生的官民政治冲突,超出土地占有基础上的经济剥削程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发展的双重意义看,这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收稿日期:1999—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