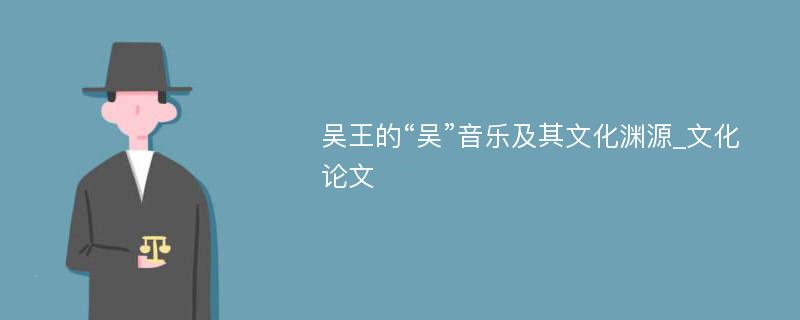
武王《武》乐及其文化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武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至于《武》之舞容的具体构成,常态理解应与牧野之事有关。《维清·孔疏》所谓“文王击刺之法”是一种理解。文王创制的一套练兵之法,用于牧野实战,而后又构成舞蹈的语汇是有可能的。如此,则《武》乐舞乃撷取传统九成万舞之三成、新制乐歌编配而成的结论还能成立吗?回答是肯定的,只是《武》乐万舞与牧野之事的隐秘关系尚需进一步揭示。
一、《牧誓》难题及其解决的思路
《书·牧誓》有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衍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衍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夫子勖哉!”《维清》诗《郑笺》、《孔疏》所谓“文王击刺之法”都是据此段誓词立说的。但誓词“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云云也确实引起了许多人理解上的困惑,如宋代朱熹就说:“只《牧誓》中便难晓,如五步六步之类。”[1]今人刘起舒先生则代朱子点明了疑惑之根由,刘氏质疑道:
既然是“临阵示众”,作为战前淬砺士气的誓词,为什么叫战士们只进攻六步七步就终止,只刺杀六伐七伐就停下来呢?这岂不是不叫打胜战吗?世界上哪有按规定走六步七步和刺杀六下七下的战争呢?[2]
类似的质疑在《维清》诗《郑笺》、《孔疏》那里,早已给出了两种理解思路。其一,将其视为实际阵法演练;其二,将其视为舞蹈动作。事实上许多学者就是循着以上思路解决《书》中之疑难的。
《李卫公问对·卷上》李靖云:“周之初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歧周以建井庙;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阵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书传辑录纂注·卷四》引宋王炎说:“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对教阵法之类的解释,刘起釪先生又提出了质疑:“这种看法看来合理些,但是为什么到了作战那天的早晨,还在临时教阵法呢?对士兵的操练,不在平时进行吗?”质疑之后,刘氏引出了其师顾颉刚先生的说法。顾氏曾说:“《牧誓》之四伐五伐,即从《武舞》之‘夹震之而驷伐’来。《武舞》本周家纪念克殷之事,不必为当时战场真相,而周末人观《武舞》而作《牧誓》,无意中随以舞场姿态写入拟作之誓师词中。”[2]在师说的启发下,结合有关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刘氏提出了新说。依刘氏新说,临战前举行宣誓性的军事舞蹈,这是较原始的战俗。牧野之战前夕,也举行过类似的舞蹈典礼。在典礼上,武王发表了重要讲话。《牧誓》便是武王讲话的记录。据此理解,刘氏对誓词作了如下现代翻译:
今天举行临战前的舞蹈,在徒手舞蹈上,不过六步七步,停止下来,看齐!在击刺舞蹈上,不过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停止下来,看齐!战士们努力呀!大家要威风凛凛地像虎豹熊罴一样,在商都的郊外,举行舍车、徒步的演习,以动员我西方的勇士们投入战斗,战士们努力呀![2]
遗憾的是,刘氏译文本身就否定了自己对“教阵法”说的发难,而只不过又添加了舞蹈说的累赘而已。
其实,刘氏在引用原始战俗资料作为立论依据时,却忽略了资料提供者的研究结论。其所引汪宁生《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3]文,在分析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以歌舞助战的习俗之后,明确指出其歌只是“高唱战歌或高声吼叫”,其舞不过是“先锋和先头部队作出冲击和刺杀的恐吓动作”而已。既然如此,刘氏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致刘氏以后研究同一问题的学者,如杨华对刘氏的新说采取了断然否决的态度。杨华先生说:“牧野作战前的仪式是在野地进行的,由多个部族临时组合起来的盟军,绝不可能也不需要进行这样整齐而又有序的舞阵训练。”[4](P130~131)于是,杨华先生又回到了顾颉刚的思路。所不同者,杨氏并不认为《牧誓》是周末人对《大武》舞的追记,而直接就是《大武》的构成部分。这一结论的得出,首先是基于《乐记》“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一语的启发。所谓武王之事,是指舞蹈的指挥者即武王的扮演者,利用舞蹈的间歇,“来进行乐舞表演的程序布置”。指挥者的训话便是《牧誓》。杨华先生还作了四点论证,而与本题有关的是其第一条论证。引之如下:
《大武》是周人最重要的当朝国乐国舞,《周礼·大司乐》谓:舞《大武》以享先祖。它一般用于祭祀、大飨等极其重大的礼典活动之中,表演的场地限于庙堂和宫殿,场地并不宽敞,不容许有大幅度的前进和后退,冲击刺杀这类舞蹈动作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所以在表演前要告诫扮作士卒的舞人们行进不超过六七步就停下来,刺杀不超过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就停下来。 同时,之所以要不断地“齐焉”,正是由于手持干戚戈矛等舞具的舞队在进退揖让,分陕复缀等变化中容易“不齐”,严重地影响了列祖列宗的视听,达不到“来假来享,降福无疆”的祭祀目的。[4](P132~133)
将《牧誓》的内容视为《大武》舞演出调度的训话,倒是一种新颖别致的思路。只是其结论与论证都实在是想当然。如果视其为演出调度之辞,《牧誓》就不是《大武》舞的构成部分。是故文中决不会出现“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如此之类的严厉训词。如果视其为《大武》舞的构成部分,作为牧野之事的再现,则问题又回到原来,六步七步仍然有待解释。依杨华的思路,还剩下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大武》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故不必如真实的刺杀。这与顾颉刚先生的解释并无实质性区别,因而也就无须多出如杨氏那般的烦琐论证。如果将《牧誓》既要视为舞蹈演出单元,又要视为舞蹈演出调度的训话,则只有假设几千年前的《大武》舞采取了今天西方后现代艺术的结构样式,即将艺术创作的过程溶入艺术的表现形式。此种可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由上分析可见,杨华先生并没有在顾、刘二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推进对《牧誓》难题的认识。
本文以为“阵法说”足以解决《牧誓》难题,只是我们不能以后人理性的眼光去看待《牧誓》阵法。牧野之战中出现的阵法,确如刘起釪先生所说,是一种战前仪式舞蹈,故可称之为舞阵或乐阵。乐舞之所以能够成为阵法,是因为特定的乐舞形式具有通达鬼神,邀神助战的巫术作用。这是原始乐舞具有军事性质的最初理由,并非如今天人所理解的仅仅是鼓舞士气。后世小说如《封神演义》、《水浒传》中经常出现的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类的法术就渊源于原始乐舞观念。汪宁生先生所描述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战歌有这样的歌词:“打战我活你必死/打战我胜你必败/你变豹子我变虎/你会跳来我会飞。”[3]歌词中的祝咒巫术的意义是清晰可辨的。当然,汪先生所采录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俗乐舞并不能用来佐证我们对牧野舞阵的推测,但它对理解原始战俗乐舞的巫术意义是有帮助的。事实上,《牧誓》的描述本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解线索,这就是其数目字。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观念中,数字是具有其数学意义之外的神秘意义的。《牧誓》中,足法有两种步型:六步、七步,手法有四种手型: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其数皆不过“七”。按理言之,四、五、六、七这些数字如果没有各自特殊的象征意味的话,《牧誓》完全可表述为:“今日之事,不愆于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七伐,乃止,齐焉……”此外,“愆”有过失、罪过义,因而,《牧誓》中“不愆于某某”之类的表述,亦可理解为,非如此这般是有罪过的。可见,《牧哲》中的数字表述,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笔者在相关论文中已详细论述过,原始乐礼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地溶入了天学的因素,因此也越来越脱离自然状态而趋于仪式化,尤其是历律等天学因素溶入巫术乐舞,使得巫术乐舞的面貌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形式之一就是乐舞的编制和乐舞的运用形成了特定的制度,这一制度显然是与某些特殊的数字相关联的。乐礼的上述特征在礼乐文明阶段,随着天学宗教的垄断,无疑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突出。古乐“九招”、“六列”、“六英”与“九律”等等称谓都应该说是某种暗示。文献中有“禹步”的传说,“禹步”便是一种具有数字意味的巫舞。《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云:
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此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昔大禹治水,不可预测高深,故设黑矩重望,以程其事。或有伏泉磐石,非眼所能及者,必召海若、河宗、山神、地祇,向以决之。然届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随摹写其行,令之入术。自兹而还,无术不验。因禹制作,故曰禹步。
文中点明“禹步”与鸟有关,实际上暗示了其与乐礼乐舞的渊源。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还记录了“禹步”舞的舞谱:
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
三、九之数自然是有意味的。天水秦简《日书》:“禹步三向北斗,质画地视之日。”《日书》非常清楚地道出了“禹步舞”三、九之数的天学意义,又隐含了禹测量日影,以天规地,划分九州的传说事迹。据舞谱,“禹步”巧画北斗之形(见文末“禹步”复原图),正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日书》之“禹步三向北斗”即“禹步三象北斗”。文献相参可证明,后世方士们的“踏罡步斗”之术,渊源久矣。《抱朴子·内篇》舞谱中的三、九之数又可以与《洛书》传说中的八方九宫图联系起来考察。九宫图将一方块分成九宫配以数字,九宫图显然是在八卦方位图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石器时期各大文化遗址都出土过丰富的八角形图符。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还出土了刻有此图符的玉版,与玉版同时出土的还有夹放玉版的龟甲。这与“元龟衔符”、“元龟负书出”之类的传说正相吻合。对史前出土的八角图符与八卦、九宫的关系,冯时先生在其《中国天文考古学》一书中作过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其天学意义。这里只需指出:九宫八卦与斗极崇拜、中国观念是呼应的;“鼓之舞之以尽神”的八卦与乐舞也是渊源难解的。
二、《牧誓》难题暨“文王舞阵”的破译与《武》乐舞容的落实
有了以上背景,我们再来解读《牧誓》难题,就不再茫然无措了。《牧誓》在记叙所谓的“六步、七步”的舞阵之前,有“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一句。这是对舞阵性质的重要暗示,它意味着舞阵具有天学意义。《国语·周语下》有一则记载伶洲鸠论律的资料,至今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而这则材料,对《牧誓》难题暨“文王舞阵”的破译与《武》乐舞容、曲调的落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伶洲鸠曰: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之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
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之,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嬴乱,所以优柔容民也。
伶洲鸠家世代为乐官,其所传述当有所据。据江晓原、钮卫星先生的天文历史年代学研究,伶洲鸠所述天象几可视为武王时天象之实录。[5](P95~146)对本文来说,《国语》的意义在于,它充分地展示了古代乐政的真实面貌。所引材料的第一段,伶洲鸠论述了乐合天数,以数合神的观念,而数又来源于天象,这与“禹步舞”是一致的。第二段,伶洲鸠传述了武王以乐布政的情况,其中包括以乐布阵,这应该与《牧誓》之舞阵有关。《国语》伶洲鸠语完全可以帮助我们来考索《牧野》舞阵的意义。
“岁在鹑火”指木星运行于十二星次的“鹑火”星次,当二十八宿中的柳、星、张三宿星次,为周的分野。据江晓原等推算,此一天象曾出现于公元前1047年,持续约半年之久,可与武王盟津之会相合。[5](P145)
“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天驷”,指二十八星宿之房宿。房宿由包括天蝎座π星在内的四颗与黄经几乎完全相等、与黄道成垂直排列的恒星组成,古人将之比附驾车之四匹马。“日在析木之津”指太阳处在“析木”星次。“析木”星次位置在东北偏东,其在《三统历》中与二十八宿的对应范围为尾10度,跨箕宿,至斗11度,正在银河之中。斗宿在银河之侧,故称“析木之津”。据江晓原等推算,此一天象出现于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5](P145)
“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辰之位皆在北维”。“辰在斗柄”,指日月交会于“斗柄”。“斗柄”传统的理解是指北斗七星之玉衡、开阳、摇光三星所构成的斗勺。江晓原则认为,“斗”指南斗,因为“太阳和月亮只能在黄道附近运行,它们永远不可能跑到北斗那里去。”[5](P102)江氏的理解较优,可与“日在析木之津”相呼应。“星在天鼋”之星,韦昭注云“辰星也”,即水星。天鼋即玄枵星次,位置在正北,其星宿范围为须、女宿8度至尾宿15度。据江晓原等推算,此一天象出现于公元前1045年12月21日,持续5日,又出现于2月4日,此后可见二十日。[5](P145)“星与辰之位皆在北维”是说太阳和水星运行到玄枵之次,它们的位置正处在在女、虚、危诸宿间,这些星宿皆属北方七宿,故有“皆在北维”之说。
对周人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星次、星宿即上述所列天鼋、析木、鹑火、天驷。周人自谓出之天鼋,则天鼋当为周人星神或周人的图腾神在天上的投影;析木与周之合婚氏族姜姓神主有关;天驷乃见农事祥瑞之星,曾为周之祖先后稷所主;鹑火乃周之分野。伶洲鸠所举天象,都是日、月、水星、木星运行于与周之神主有关的星次。“王欲合五位三所而用之”,所谓五位即日、月、水星、木星、辰所行之位;三所应指天鼋及析木、天驷、鹑火。周人将五位三所与武王伐纣之事联系起来,赋予特殊的星占意义。《开元占经·卷二十七》引郗萌曰:“岁星出入留张舍,三十日不下,有兵;六十日不下,更立侯王。”《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荆州占》曰:“岁星主司天下诸侯人君之过”,石氏曰:“岁星所在之国不可伐,可以伐人。”《开元占经·卷五十三》引《荆州占》曰:“辰星色,太阴之精,黑帝之子,立冬,主北维……人君之象,天子执政主刑,伐出辰星之易是也。”引班固《天文志》曰:“辰星杀伐之气,斗之象也。”引巫咸曰:“辰星上出四孟,天下乱,一曰天下更王。”引《洪范五行传》曰“辰星出孟,易王之表也。”综上可见,星辰所主正当杀伐之令,而其运行位次又合于与周相关之星神,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相信武王伐纣确乎是顺从天意。以上也正是《牧誓》武王所说“惟恭行天之罚”的具体所指,那么我们能肯定《牧誓》所谓“六步七步”之类的舞阵与《国语》中的天象确实有关系吗?我们只有继续读解《国语》方能作出回答。
“自鹑及驷七列也”是指从鹑火星次的张宿到天驷有七宿排列。“南北之揆七同也”,是指从鹑火至天鼋,自南而北合计七个星次。星次与列宿,其数正同。“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人神交通必须合乎天数,因此降神、娱神的乐舞必因天数而制,方能达到乐政的目的。武王之以七律和声正是为了合乎天数。伶洲鸠所论七律确与武王伐纣天象有关,由此推测牧野舞阵中的“七步”之数与“七律”之数具有同样的来源和意义,自然在情理之中。至于舞阵中的四、五、六三数的意义,我们还很难确指。
前面《国语》引文的第二段,据来可泓先生的理解,是伶洲鸠关于《武》乐乐曲的论述。来氏对《国语》原文作了如下翻译:
举武乐来说,武王在二月癸亥晚上布阵,没有完毕就下起雨来,用夷则律为宫声将战阵排列完毕,正好是第二天的辰时。布阵之初,日月之会斗柄在戌时,所以用夷则律为上宫声,名其军乐为羽,表示武王能羽翼其众,用来保护民众使之遵照法则。武王又以黄钟律为下宫声,布战阵于商郊牧野,所以名其军乐曰厉,表示武王与战士和谐同心,用来激励六军奋勇向前。武王又用太簇律为下宫声,在商都发布命令,弘扬太王、王季、文王之文德,声讨纣王的种种罪恶,所以名其军乐为宣。回到嬴内,武王又以无射律为上宫声,颁布法令,施舍恩惠于百姓,表示偃武修文,所以明其军乐为嬴治,用来优厚宽柔地对待民众。[6](P177)
从伶洲鸠的乐官身份以及《国语》文的语境、叙述体式看,来氏之说是可以成立的。来氏对文句的译解大体可从,但全篇文义尚存纠结难解之处,有待辩明。
“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之,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据韦昭注,“当辰”指武王布阵结束之时正当次日的辰时;“辰在戌上”之“辰”指日月合朔。“辰在戌上”指日月合朔的时间在癸亥日夜之戌时。①由上可推知,武王于戌时布阵,辰时结束。“长夷则之上宫”即先用音调高的夷则律为宫调,此句费解之处在一“故”字。先用夷则律与“辰在戌上”有何内在联系呢?古人不仅以十二地支纪时辰,而且还以之配置天宇方位:子为北,东为卯,南为午,西为酉,西与北之间为戌、亥。“戌上”是接近亥位的天区,斗柄指向该天区,时令正值秋冬之际。《吕氏春秋·音律》云:“孟秋生夷则。”孟秋之时,天地始行肃杀之气。武王于戌时布阵,先用夷则律调,正暗寓着武王开始替天行杀伐之令。“名之曰羽”是指夷则为宫调的乐曲之名为“羽”。清董增龄《国语正义》云:“《释名》:‘雨,羽也,如鸟羽动则散也。’则雨羽古互训。武王知雨为天人和同之应,故作乐以象之。”《正义》“天人和同”之义由“未毕而雨”一节而来。伶洲鸠特别指出武王首次布阵,“未毕而雨”之事,自然有意味可寻。日月交会亦即阴阳交合,阴阳交合而致雨,应在情理之中。当然,日月之会,阴阳交合未必即雨。在此,雨确被视为天人和同之应,这从布阵由戌至辰合乎“七”之天数亦可看出。雨、羽互训,实际上暗示了古时以羽龠之舞祈雨的事实。既然布阵致雨,是否可以推测武王长达六个时辰的布阵与舞阵也有关系,而且此舞阵也体现了羽龠之舞的形式呢?《书传》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参之《书传》等相关文献,以上推测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藩屏民则也”是说武王能上达天意,故能协和其众,乐曲之名正取意于此。
“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此为武王第二次布阵,其乐调为黄钟宫。《韦注》曰:“布戎,陈兵也。谓夜陈之晨旦甲子昧爽,左仗黄钺,右秉白旄时也。黄钟所以宣扬气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名此乐为厉者,所以厉六军之众也。”就史事而言,《韦注》得到了铭文的证实。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利簋,《利簋》载:“斌王征商,唯甲子朝,岁(刿,利伤也)鼎(丁,当也)克。闻(昏)夙(速)又(有)商。”②可见“布戎于牧之野”是在甲子早晨,实战前的一次布阵,“牧誓”应当其时。这里如果全据史事去理解伶洲鸠之传述,便会与前面的文义发生抵牾。因为第一次布阵结束于甲子日之辰时,显然已是“晨旦甲子昧爽”之后了。由此可以推断,伶洲鸠所说的两次布阵并不是真实的陈兵布阵,而是对当时舞阵或《武》乐舞容取象意义的描述。
实际的舞阵应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羽龠之舞。其所取当为日、月、木星、水星在“三所”之间运行之象。布阵始于日、月合朔之戌时,未必而雨,而终于辰时,其间正合于“七”之天数便是一个暗示。时辰可化为舞阵队列之空间方位以及舞人形体动作的变化。第二部分为干戈之舞,其取象当与《牧誓》“六步七步”有关。前面我们已推测“七步”与“七律”或许具有相同意味,但如果合“六步七步”而论的话,这里我们倒更倾向于视六步为象南斗之象数(辰在斗柄),七步为北斗之象数。古人有北斗主死,南斗主生的观念。北斗的意义更为特殊,在古人的神秘的想象世界中,北斗犹如天帝布令于四方的指挥棒。“六步七步”不仅是武王代天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象征,而且在当时人们文化观念世界中本身就具有“禹步”般的巫术作用,这也是战前布舞阵的实际意义之所在。③《牧誓》中的“四伐五伐”之类与“五位三所”有关,三所四伐,其中鹑火一伐、天驷一伐、析木一伐、天鼋一伐,计四伐;五位各一伐,计五伐;六伐、七伐为天伐,其意与“六步七步”同。牧野舞阵实际上无异于周人的推步、历法、星占的舞蹈化,其编制当于文王之时。作出如是判断,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1.牧野舞阵击刺之法所象天数,合乎武王盟津之会到克商整个过程的实际天象。但伶洲鸠所述天象又并不能与当时的实际天象吻合无间。如日月合朔,据现代天文历史年代学的推算应在辛酉日,[5](P145)而依伶洲鸠则是癸亥日戌时也就是说伶洲鸠的传述有两天左右的误差。以上说明:伶洲鸠所描述者并不是据当时实际天象,而是据早已编制好的舞阵所反映的天象。编制于舞阵中的历法尚不精确。
2.据《诗·大雅·灵台》,文王有建灵台之举。灵台是通天的手段,自从天学宗教被垄断以后,灵台一直都是天子的专利,拥有天命的象征。《诗·大雅·灵台》孔疏引公羊说云:“非天子不得作灵台。”文王以诸侯之卑而作灵台,这表现了文王欲取商而有天下的战略图谋。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步骤便是籍已建好的灵台,观天测星,尽快地制作一张符合当时星占观念,能预知天命转移,于周人有利的星象图和天文时间表。盟津之会选择岁在鹑火这一天象出现之时,就是由这张时间表决定的。周人将受天命归于文王当与文王建灵台,制作天文时间表有关。《乐记》“病不得其众”之谓,表达的正是盟津会盟之初,武王对文王时间表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忧虑之情。
3.将天学内容巫术化,以乐舞象天,合于天数,本来就是中国的礼乐传统。文王既然已经制作了一张预示天命转移的星象图和天文时间表,则将其写入本来就具有神秘意义和巫术作用的乐舞之中,让周人及其同盟者作为舞阵去演练,自然在情理之中。唯此,才能将少数人如姜公等的星相观测,表现为具有感召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天命之象征。
4.前此,我们已由《维清》一诗,认定武王之乐《武象》象文王“击刺之法”。《维清》诗结句为“维周之祯”,“祯”,吉兆也。“天垂象,以示吉凶。”诗句明显暗示了“击刺之法”与星象、天命的关系。又据《世俘》,在告成仪式上的万舞表演,“王佩赤、白旂”。武王手中白旗显然是武王指挥布阵的道具,此时演出的万舞与牧野舞阵具有某种一致性基本上也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亦可见,武王《武》乐以及牧野舞阵皆来源于文王之舞阵。“文王舞阵”的意义清楚了,《世俘》所记载的《武》乐之舞容,也就大体上得到了落实。
三、《武》乐曲调的落实
下面,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国语》伶洲鸠语的进一步辨析来丰富对武王《武》乐已有认识,解决《武》乐曲调的问题。
据《国语》,《武》乐的曲调除《羽》之夷则宫之外,尚有《厉》之黄钟宫、《宣》之太簇宫、《嬴治》之无射宫。②四章乐曲,同用宫调,这是一个重要特征。《史记·律书》:“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正义》引兵书云:“夫战,太师吹律。宫则军和,主卒同心。”这里说明了《武》乐尚宫之义。就《武》乐四章用律而言,也有值得注意的特征。《吕氏春秋·音律》云:“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孟春生太簇……季秋生无射……孟秋生夷则。”可见,前三章的乐曲,《羽》之夷则对应于孟秋之气,《厉》之黄钟对应于仲冬之气,《宣》之太簇对应于孟春之气,《嬴治》之无射对应于季秋之气。前三章的用律次第与由秋至春的月令次第相一致,唯独第四章似乎游离于章法之外。从所象史事看,四章却又呈现历史事件发生的连贯性。但前三章与第四章仍有区别,前者与牧野之事紧密相连,只在一两日之间,而后者已是武王回师嬴内之事,其事似乎又与文献所谓“偃武修文”有关。又据伶洲鸠语,四章律名之寓意:“夷则,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二也”;“黄钟所以宣扬六气、九德也”;“太簇,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六气”指阴阳风雨晦明;九德指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种功德。《左传·文公七年》:“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咏歌九则”,韦昭注云:“万物既成,可法则也。故可以咏歌九功之则,成民之志,使无疑二也。”今人董立章释“九则”为“政府的九则行政法规,包括六府(主水、火、金、木、土、谷的官署)之则,和三事之则。”[7](p138)董氏释“九则”为九种法规甚为明晰,与“平民无二”语义可贯,也与《武》乐首章所象戎商之事相应。从四章律名之寓意看,前三章取象于天地生育之功德的痕迹非常明显。其中前两章又与“九”之数目联系紧密。以此结合本文已有的相关考论,似可推断《武》乐的主体前三章当承《九韶》之乐、“九律万舞”的统绪。第四章律名之寓意与前三章语境明显有别。若纯依事象而言,陈纣王之罪,宣扬三王之德的第三章应以第四章律名为用,因为其事正与“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之意吻合。综上可以表明,伶洲鸠所论《武》乐第四章,无论从整体的结构章法,还是从曲名象事、律名寓意看都游离于前三章之外,不能与之成为一个整体。从曲名象事、律名寓意看,说其为周公成王《大武》乐之一部分.更为妥帖。根据我们对《大武乐章》的考订,其或许为《大武》第二成演出的《时迈》乐歌的曲名。当然.这一推断有待于后续论文对有关周乐其他遗留问题作出说明之后方能确认。
以上,通过对《国语》伶洲鸠语的辨析,大体上了落实了《武》乐乐舞、曲调的具体内容,也证实了《武》乐系取九成万舞之三成、周人自配乐歌三章而成的推断。但在结束本篇之前,尚有必要就全文上下篇的内容作点补充和说明,以之缀成余论,且为后续论文之导引。
四、余论
据《世俘》,武王是在商都牧野举行的告捷礼上演奏《武》乐的。杨宽先生认为,此次告捷礼用的是殷礼,这种说法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在祭祀“王列祖”的仪式上,“龠人九终”(歌乐章九节)。乐章九节暗示了其就是与九成万舞相配的九德之歌。本来用于祭祀商之列祖的九德之歌,已为周人所用,这也就是《韶濩》废的真实意味。
以上观点和结论,可以拿来与《周礼》“大司乐”所掌“成均之法”相印证。从“成均之法”还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九成万舞、九德之歌传承与演变的痕迹。《周礼·大司乐》云:
乃奏黄锺,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锺,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舞射,歌夹锺,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祇,再变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祗,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祇。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祇。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祇。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凡乐,圆锺为宫,黄锺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孙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圆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锺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锺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徵,应锺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
经文从“凡乐,圆锺为宫”起,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面部分所载乐制的特点是:1.奏、歌、舞分明,有严格的谐配制度;2.六乐之名俱全;3.祭祀娱神之乐分明,而降神用乐则模糊不清。尽管说所降致者由六乐六变所致,但所降致者有动物之属,很难与所祭祀者一一相应。是故“六变”云云,与六乐之制无关,实更为原始。后面部分所载乐制的特点是:1.乐舞突出,但奏、歌、舞并不分明,未见有严格的谐配制度;2.六乐之名不全,三代之乐名不见;3.为降神之乐,但很难肯定其与前面六乐祭祀为一体。故此处降神之乐或许即祭祀娱神之正乐,为不同乐制之体现;4.宗庙祭祀,无先祖、先妣之谓,皆以人鬼称之。所用之乐,舞、歌已判,为《九韶》之舞、九德之歌。两厢对照,似乎可以推断:在周代,九德之歌合《九韶》之舞即为九成之《韶》乐,取其舞六成即《云门》之舞,八成即《咸池》之舞。“夏龠九成”之《大夏》以及商之《韶濩》皆是以改制《九韶》之舞,自配歌咏其祖宗功德之乐歌而成。结合前面的考述,可以说,在商代,《九韶》之舞的基本形态就是所谓的“九律”万舞。如果不考虑《大武》乐舞的特殊品格,以及万舞在周代的种种变异,我们完全可以从孙诒让说,将万舞作为六大舞之通称。
在告捷礼第四天的告成仪式上所演奏的《武》乐,亦来源于“九律”万舞。其中二律、二成已在文王之时改编成文王舞阵,告成之时,武王又取其一成,配上《明明》等乐歌三章,便构成了武王之《武》乐。依伶洲鸠语,《武》乐所用为七声音阶。《国语正义》引胡彦升《乐律表微》曰:
古乐虽有七音,止用五声,周之它乐亦然。故《周礼》‘文之以五声’,内传云:‘为七音以奉五声’,不用二变也。唯武王所作“羽”、“厉”、“宣”、“嬴”四乐则五声之外兼用二变。二变近乎北音荆轲,为变徵之声是也。《史记·律书》:“武王伐殷吹律听声杀气相并而音尚宫。”此四乐盖取杀气相并之义,有粗粝猛起奋末广贲之音焉。周用七律唯此为然。至周公作《大武》,止用五声,而此四乐亦不复用。故不见于它书。
《武》乐曲名虽不见它书,然《武》乐踪迹,后世犹可辨也。从有关《武象》、《象》或《三象》的传说记载中,不难寻觅到《武》乐的踪影。
注释:
①有另外一种理解,即“辰”的用法先后没有区别,皆指日月交会,“戌上”作天宇方位解,但这会引起对上下文理解的困难。上文已明确“辰在斗柄”,则此处“戌上”应与“析木”星次合位。问题在于,据《史记·历书》、《淮南子·天文训》等所列的十二地支与十二星次的对应关系看,析木处寅位,戌位则对应于降娄星次,其间整整相差三个位次。即便我们不知道《史记·历书》、《淮南子·天文训》的纪年法的产生时代,同时又将岁差造成的星象图的变化考虑进去,也不至于伶洲鸠的描述与《史记·历书》、《淮南子·天文训》所反映的十二地支与十二星次的对应关系有如此大的差异。何况,伶洲鸠对周初的天象的描述,为便于理解故,也应该采用当时流行的天象描述的天文学标准。就地支与星次的配置来说,伶洲鸠的标准与《史记·历书》、《淮南子·天文训》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以上决定了韦注为唯一解。
②铭文释读有异议,“岁鼎”,于省吾等认为“岁”即岁星,鼎(贞)作“当”讲。则“岁鼎”当作“岁星正当其位”解。参《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本文从杨宽释读,见杨宽《西周史》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伶洲鸠论七律的意义只在于,它间接地证明了牧野舞阵之数当源于天数,因此它并不意味着所有数字都一定合于“七列”、“七同”之例。这里自然可以作出与“七列”、“七同”之例原则一致,而又更为合理的推测。
④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武》乐曲所用四律,前三律皆见于贾湖“八律”,唯“无射”律例外。是否可推测“八律”加上“无射”律便成了商代“九律舞”之九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