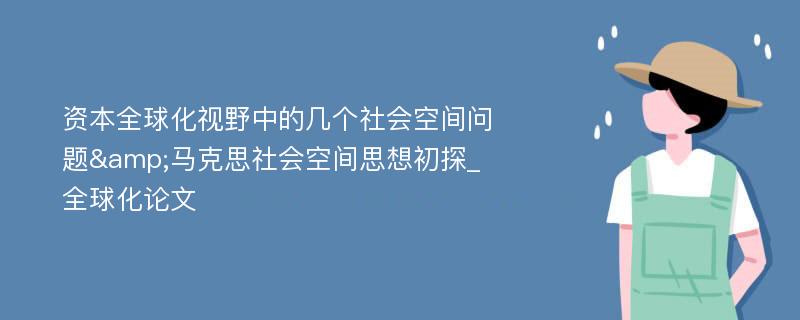
资本全球化视阈下的几个社会空间问题——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几个论文,社会论文,空间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以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科学技术的全球同步、生态环境的全球联动为三大基本特征的“全球化”的迅速推进,“空间转向”在“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中的异军突起,被视为上世纪后半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①,“空间”正在深刻改变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阐述视野。值得关注的是:促成这场“空间转向”的主要领军人物,不管是曾经公开申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大卫·哈维等人,还是一再表示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异的米歇尔·福柯、曼纽尔·卡斯特、爱德华·苏贾等学者,都把视角转向了“空间”,虽然他们视角各有不同,但他们各自的空间分析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继承、反思的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空间分析”在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关注绝非偶然,同时,也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中的重要理论元素。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进行学术梳理将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有益探索。资本的全球化是马克思进行社会空间分析的现实语境,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人类的空间视野不断拓展,“空间”也开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如何把握人类社会空间的这种巨大变革?马克思开创了一种社会空间的“资本阐释学”,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不仅赋予了空间以社会经济内涵,而且又是解读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空间转换的钥匙。资本对社会空间的重塑或者说资本的空间权力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
一、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空间剥夺问题
“空间剥夺”是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同时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其问题域广泛渗透于地理学、政治学、城市社会学研究领域。具体来说,“社会学创立‘剥夺’概念来研究社会公平问题,而地理学则引入‘剥夺’原理来探讨空间公正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城市社会地理学家提出了多种不同‘剥夺指数’来衡量空间的剥夺水平,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与空间不公正的对应关系”②。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提出“空间剥夺”这个概念,但他在资本原始积累、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力价值的确定,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探讨中蕴涵着深刻的“空间剥夺”思想,“空间剥夺”无疑是马克思解读资本塑造的全球秩序的一个基本视角。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关注的是人类交往和生产实践突破民族地域限制,达到一种全球规模;第二个维度探讨的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秩序,资本塑造了等级化的全球空间结构,这两个维度密切联系。从马克思对待二者的态度来看,一个是“立”,一个是“破”,它们共同构成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进行辩证解读的两个方面。对于人类和谐空间的构建来说,资本承担着双重的角色和作用:一方面,资本的力量开创了人类社会空间的新阶段,它使人类社会空间第一次现实地成为一个整体,资本是打破人类各种社会空间壁垒的重要的物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无疑是构建人类社会的一种积极力量;另一方面,资本也是使人类社会空间的矛盾和危机拓展到全球规模的始作俑者,资本的全球拓展并不是一个利益均沾的历史过程,它的最大受益者是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的全球拓展过程,同时也是落后民族和国家逐渐被边缘化的历史进程,“空间”在这个进程中成为资本全球积累的载体。马克思对这种国际体系和格局有着敏锐的洞见,认为这种国际分工秩序只能造成和加剧全球空间的断裂,这种断裂在《共产党宣言》中被概括为三个“从属于”,即“未开化和半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空间剥夺不可避免。
首先,全球空间的流动性是空间剥夺的现实前提。流动性是资本的内在属性,资本的增殖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但资本不是在静止中实现自身的,它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商品的流通过程。这种流动起初主要是在民族国家内部,但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这种流动的空间拓展到全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在全球空间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③。资本也在这个过程中聚集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势资本的聚集使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受到了多种空间壁垒的限制,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多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剥夺现象虽然存在,但主要是依靠战争等方式进行的,马克思说:“对进行征服的蛮族来说,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④ 与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后的空间剥夺相比,这种剥夺不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剥夺的空间性更多关涉的是民族一国家空间,而不是全球空间。
其次,殖民主义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秩序是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空间剥夺的基本形式。殖民主义的最大弊端在于这种制度本身对殖民地国家发展权的剥夺,殖民地国家在这种体系中无法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它们被动地卷入国际分工体系,又逐渐在这个体系中被边缘化,并最终形成对宗主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依附。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原始资本积累和现代资本积累,前者是后者的起点,而原始资本积累是通过野蛮手段强迫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种原始积累伴随着少数资本主义强国对落后民族的残酷剥夺,以英国为例,原始积累的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⑤。可以说,资本原始积累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⑥。在原始资本积累基础上的现代资本积累又使这种等级性不断加剧,随着资本积累的加深,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民族的剥夺也越来越具有可持续性,落后民族和国家不仅输在了起点上,更输在了过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具有不断进行空间扩张的内在属性,“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⑦。而国外市场的开拓成为突破这种限制的一种现实途径。通过国际资本输出,殖民地国家成为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原料基地,比如:当时的“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⑧。而美国作为当时最大的殖民地市场,也只不过是一个“输出原料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这种输出表面上看来是以货币为交换手段的平等交易,货币天生的平等派形象赋予这种国际贸易形式上的平等性,但在这种形式的平等背后却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曾经说过:“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⑨ 与西方的贸易理论相比,马克思更强调国际贸易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这种社会属性是探究各种贸易分工现象及其背后的动力、结构趋势的一把钥匙,而国家利益是国际贸易的社会属性的核心。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不平衡性,最终导致了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的怪圈。
最后,空间剥夺的真正消除有赖于资本逻辑的扬弃。马克思将空间剥夺以及由此导致的落后民族和国家贫困化的探讨纳入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体系中,并作为后者的一个子系统进行探讨。具体来说,马克思对空间剥夺的探讨隶属于全球范围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对落后民族和国家空间剥夺,现实地体现为对占落后国家和民族人口的绝大部分的无产阶级的剥削,而非统治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之间的空间剥夺是受全球范围内阶级问题与阶级矛盾统摄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⑩,“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11)。因此,消除空间剥夺本身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目标,有赖于资本逻辑的真正扬弃。而资本逻辑的真正扬弃有赖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有赖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是在个别民族和个别地域空间,而是全人类和全球空间。不难看出,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正归宿,它是一个全人类和谐共处、真正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人类社会空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区分了“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和“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并强调:共产主义并不是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2)。民族、国家将在这个阶段走向消亡,人类对各种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和利用将被纳入统一的计划范围内。在社会空间的建构上,共产主义社会遵循真正的“共有、共建、共享”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人类构建不同层次社会空间的价值准则。以往人类社会空间中存在的断裂性将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体现开放性、丰富性、流动性的真正和谐的统一整体。而在此以前资本的逻辑将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需要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交往中“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13)。具体来说,落后民族和国家在发展中要善于发挥资本的积极效应,在国际竞争中迎头赶上,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成为促进国际社会公正、对抗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垄断的积极力量。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要尊重落后民族的发展权,避免对落后国家实施经济殖民和生态殖民,共同营造公平正义的国际环境。可以看出,马克思试图建构一种资本的主导逻辑与空间正义相结合的发展伦理。
二、全球自然空间的过度资本化问题
全球自然空间的过度资本化是马克思关注的第二个社会空间问题,自然空间的资本化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就没有给自己设定积累的界限,而当资本把积累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自然空间的过度资本化问题就不可避免。
首先,资本主义开启了人类全面利用征服自然的新篇章。自然空间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先在条件,是人类现实生产力的物质载体,“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的”(14)。马克思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并提出“人化自然”的范畴。作为人的活动的空间,“人化自然”是一个通过人的活动建构、并随着人的活动能力和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空间。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关于感性世界的理解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15) 人与自然之间由此建构了一种对象化的关系。与前资本主义形态相比,资本主义开启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格局,这种新格局突出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实现对于自然空间的全面控制与支配,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16) 人类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伊始,就开始了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工具理性成为指导发展的价值准则,在这种价值准则的推动下,自然空间成为资本积累的载体。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历史地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17) 一句话,资本按照它的面貌创造了一个新的自然。
其次,资本主义具有“反生态”的制度属性。资本主义实现的人类生产力飞跃是以巨大的环境成本作为代价的,这是马克思对发展与代价关系的辩证解读的重要维度。自然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也在客观上成为其生产的限度。而资本无限积累和扩张的内在属性却使其不断突破这个限度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于是,两者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方面,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要么积累,要么死亡”;另一方面,“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18)。资本积累越深入,资本对于自然空间的宰制也不断加剧,对自然空间的过度利用最终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化。托夫勒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不仅能够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19)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土地为例探讨了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现状,他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和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和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程度就越迅速。”(20) 而造成土地掠夺性滥用的根源不是个别资本家的贪欲,而是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21) 土地私有制必然带来自然空间利用上的代际矛盾。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同构性,两者互为中介,“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22)。不仅如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模式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和制约的,因此,“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3)。由人与自然的冲突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人类自身的危机,它是资本主义不断扩大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一种“反生态”本质,这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是资本主义在自身框架内无法根本克服的,因此,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本原因的探讨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去寻找。
最后,资本积累的全球化孕育着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等级化的世界格局中,自然空间的过度资本化,又现实地体现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实施的生态殖民主义上。对于生活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来说,尽管少数发达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的趋势表现得尚不充分,但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鉴于全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随着资本全球积累的深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农业国家争夺全球自然资源的斗争会更加激烈,而这种斗争更多的是采取一种经济手段。世界市场的开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性地开发和索取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现实条件,而后者针对这种生态殖民主义的地方性抵抗,显然无法与资本的强势逻辑相抗衡,人与自然的紧张状态由此拓展到全球空间。虽然科技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有助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但它们本质上无法根治这种痼疾。资本主义在一路凯歌行进中却潜伏着巨大的生态危机,人类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警醒,而建构人与自然之间建设性的可持续关系就必须扬弃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状态。
三、虚拟资本的恶性膨胀及虚拟经济空间的风险问题
虚拟资本的恶性膨胀与全球经济风险问题是马克思关注的又一个重要的全球社会空间问题,虚拟资本直接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经济空间。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资本的虚拟化和金融化逐渐成为资本全球扩张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资本论》中他专门以“信用和虚拟资本”一章探讨虚拟资本在资本全球积累中的作用与角色。
首先,虚拟资本的产生与资本全球化导致的信用关系的扩大密切相关。什么是虚拟资本?它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现实能量?马克思指出,虚拟资本本身并不神秘,它不过是货币资本化的产物,是生息资本的一种派生形式。虚拟资本实质上是信用关系的一种特殊体现,汇票、银行票、债券、股票是虚拟资本的几种具体形态。对货币形式历史沿革的探讨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亮点,马克思指出,在人类信用关系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的质料特征显得很重要,贵金属成为货币材料的理想载体就是源于其在质地特征上的易分割性及可携带性。而随着流通过程的经常化,金属货币的缺点也暴露出来,比如对于金属货币的足值足额要求经常因其易磨损性而落空,由此货币的质料特征逐渐淡化。纸币的出现标志着货币完全脱离其价值实体,而成为一种价值象征和交换符号。“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暴露无遗了”(24)。因此,货币的实质是一种信用关系。随着资本积累的全球扩张,商品交换的数量和范围大大增加,与之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于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广泛建立起来,不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而且拓展到全球空间,虚拟资本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而它不过是货币作为价值符号功能的深化。虚拟资本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一是可预期的利息收入使虚拟资本能够将社会上的闲置资金积聚起来,转化为信贷资金;二是可以降低货币发行和支付的压力,使资本的积累形式更加多样和灵活;三是缓解了货币支付的压力,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起到刺激作用;四是使流通过程更加灵活,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需求。这使得虚拟资本迅速发展起来,“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像伦敦那样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个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25)。
其次,虚拟资本没有改变资本的内在属性。流动性和增殖性是资本的内在属性,这一点对于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虚拟资本同样适用。虚拟资本是以实体资本为基础的,没有实体资本及其所依附的实体经济体系,虚拟资本就没有存在的依据。虚拟资本的运动是在资本和由资本获得的利息相分离中产生的,利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与资本相对立的一种独立的力量,“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由此形成一种假象:“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同它能够生出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与实体资本相比,虚拟资本似乎具有自行增殖能力,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在年收入=100镑,利息率=5%时,100镑就是2000镑的年利息,这2000镑现在就看成是每年有权取得100镑的法律证书的资本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26)。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这里似乎是一种想象的财富,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这使虚拟资本价值额的涨落能够脱离它们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虚拟资本数量的增减并不一定反映实体资本的变化,有时甚至偏离实体资本的运动,但虚拟资本的最终实现依赖于实体资本。后者既是虚拟资本运动的起点,又是其终点。无论虚拟资本采取何种外在形式,其内在本质不会变化。
最后,虚拟资本及其滋生的虚拟经济空间具有巨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作为虚拟资本物质载体的各种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都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27)。这使得虚拟资本有着巨大的投机空间。虚拟资本构建的虚拟经济空间既根源于现实经济空间,同时也由于其本身的模糊性和流动性而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援引亚当·斯密的话探讨了这种不确定性(28)。因此,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滋生出一种错觉:“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29)。于是泡沫和投机接踵而至,“正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人们以为终究可以从里面抓到一点实在东西的‘准备金’也是如此”(30)。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不可克服的风险因素。由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利润率相对较低,引发了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大量转移,导致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膨胀,而这一切又成为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助推器。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合乎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对利润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减少了,“相反,通过金融体系,利润从一个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每一次冒险似乎都在一段时间里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31)。虚拟资本的运动一旦完全脱离现实资本,从而失去现实的实物资本的依托就会自行膨胀,并在不断扩大的泡沫中使现有的经济体系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
以上笔者只是从资本扩张的角度对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作出初步探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习惯于说,时间在增值,空间在贬值。但另一方面,恰因人类活动的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影响日益深入,更需要我们重视对“空间”的再认识。在全球化时代,当代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并不只是地理—地理维度的空间巨变,以及社会—经济维度的发展挑战,而是涉及文化—心理维度的时空变迁。因此,马克思的空间思想所具有的理论阐释的巨大张力,应该引起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唯物论”,也同时是一种“社会唯物论”。因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基本范畴的“社会存在”本身就具有一个极为广阔的解读空间(包括对“人化自然”与“自由时间”的再解读)。
注释:
①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7页。
② 王兴中等:《国外对空间剥夺及其城市社区资源剥夺水平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人文地理》2008年第6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页。
⑦ 同上书,第494页。
⑧ 同上书,第494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9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11)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399。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
(18)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19)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5~17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55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7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
(23)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79页。
(26) 同上书,第528~529、526、531~532页。
(27) 同上书,第531~532页。
(28) 同上书,第535页。
(29) 同上书,第533页。
(30) 同上书,第535~536页。
(31) 克里斯·哈曼:《次贷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嵇飞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第7期。
标签:全球化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