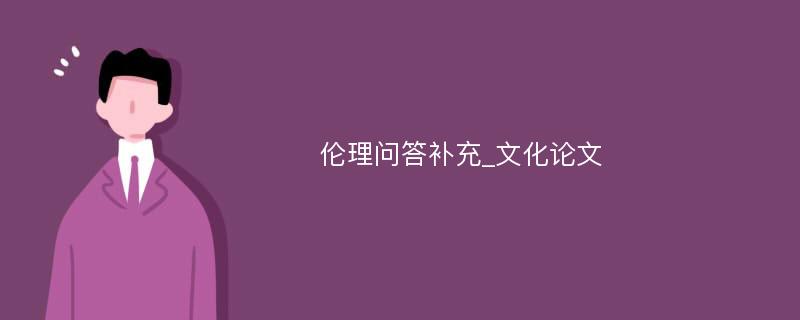
伦理学答问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你很重视自己的伦理学,但有些地方好像没说清楚。
答:我以为都说清楚了。有何问题,请提出,但我的回答大概仍是重复一遍而已。
问:例如,你既明确区分伦理与道德,道德只讲心理形式,为什么又提出宗教性道德和(现代)社会性道德,应该是宗教性伦理和社会性伦理嘛。
答:这不是就外在群体的伦理规范(制度、秩序、风俗、习惯等)做分类,而是指个体内在的道德心理中所包含的不同的伦理内容(即规范)。同一道德心理(即形式)有不同的伦理规范或内容。我举过恐怖分子与救火队员的例子:个体的道德心理形式是相同的,但同一形式所包含的伦理内容不同。
我的伦理学的要点是做出了三个重要区分。第一是对中外一直都混同使用的伦理(ethic)、道德(morality)两词做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的词义区分,即将伦理作为外在社会内容、规范和道德作为内在心理形式、结构的区分。第二是在内在心理形式、结构上,又做出人性能力(理性动力)与人性情感(情感助力)的区分,并强调情感助力的重要性。第三就是内在心理形式、结构(包括能力和情感)含有传统宗教性与现代社会性的不同内容的区分。
问:这第三个区分也就是你所谓“善恶”(宗教性)与对错(社会性)之分。但“对错”毕竟与“善恶”有联系。
答:对。三种区分都是为了突出矛盾与问题。“对错”与“善恶”之分也如此。
在前现代,无论中西,这两德基本是同一的,不需要也不可能区分,西方是基督教,中国是儒家,既是宗教、情感、信仰,也是制度、秩序、风习,但到了近现代,日常生活发生重要变化,政教开始分离,这就使以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与以传统为基础的宗教性道德产生歧义、矛盾甚至冲突。当然即使在今日现实生活中,两种道德也常有重叠、一致、难以区分的情况,但毕竟可以、也需要做出区分。而且由于现在世界上还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传统,有着并不相同的情感信仰。它们所持有的善恶标准还并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例如至今在某些文化、宗教传统中,通奸是罪大恶极,但男方可以无事,女方就必须用石头砸死,这被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是应当绝对执行的伦理命令。我也一再举过中国百多年前“节妇烈女”的善恶标准和戴震慨叹“以理杀人”。这种种善恶标准和观念应用到现代社会中,便明显是错误的,它们不是“善”而是“恶”。但由于考虑到各种文化、宗教和传统难以一时改变,就特地把“对错”与“善恶”即现代社会性道德与传统宗教性道德区分开来,并且指出,这两种道德可以有冲突。今天的塔利班所履行的传统宗教性道德与今天社会性道德不就如此么?而且也远不只是塔利班而已。所以在社会转型期(由前现代转入现代)的世界历史中,做出理论上的这一区分就特别重要。在当前中国也如此。
问: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对错”本来应该就是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善恶”,这区分似乎是一种目前采取的策略。那么,未来呢?
答: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人们生活的物质内容和方式逐渐同质化,从而要求人际关系和个体权益(如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等等)的同质化,这会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对错”越来越冲破许多宗教、文化、传统的种种阻碍,被越来越多的各地区、民族、人民所接受,而逐渐被认作共同的善恶标准或观念。这也就是道德的进步。要注意的是,这“进步”指的还是道德的伦理内容,而并非心理形式,它是伦理规范的改变而非道德形式的改变。牺牲自己的心理形式亦即道德行为不变,但是为何种伦理规范、内容而做牺牲(例如是为了“圣战”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牺牲,还是为了对付恐怖分子而牺牲)却变了。由于伦理与道德一直混为一谈,才把个体行为中伦理规范的进步说成是道德的进步,因为伦理规范、内容总是通过个体行为即道德形式、道德心理来实现的。今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再只是个别人的英雄行为,而可以成为普通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心理。今天中国的互联网、手机信息就都在起这种“打抱不平”的作用。这就是社会伦理进步所体现出来的个体道德行为的进步。又如,以前战争中杀俘虐俘以及滥杀平民几乎是常规,如今则是巨大的恶事丑闻,会受到舆论的揭批和公众的谴责。这也就是说,现代人们已开始将社会性道德的“对错”作为个体自身的准宗教的情感信仰的“善恶”来对待了。我以前讲过,各不同文化、宗教、传统中一些相近或相同的善恶观念构成人类共同人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以为今天的普世价值亦即现代社会性道德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如此。
问:但你不又提出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即社会前进而道德倒退么?
答:那毕竟是指较为短暂、局部的情态,也特别是针对社会转型时期某些状态而言的。这里说的“进步”是就更为全面、久远特别是就整体人类历史而言。
问:这样,“对错”和“善恶”就可以统一了?
答:仍不会“统一”。因为人们对“善”(如“幸福”)的追求永远不会同一。特别如以前多次所说,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对错”基本上是一种公共理性,常常不能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生活价值的追求。在饥饿、战争、疾疫等物质方面的“恶”大体消除之后,什么是“善”,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人生意义、生活价值,会有更多的困惑和更多不同的解说。各种宗教性道德在可见的未来永远不可能为现代社会性道德所吞并或“统一”。基督教有原罪说,中国人讲“性善”,伊斯兰有“圣战”,印度教无有,有人信佛,有人信耶稣,等等,从而,所奉行的善恶观念和标准,便不会“统一”。
问:你讲的社会性道德的对错,似乎是为了突出个体存在?
答:对。但这正是以人类发展到现代也即是以“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到现阶段的特点为依据的。这个“现阶段的特征”便是以个体生存、个人利益为基础。这也就是康德讲的“人是目的”。我以为,康德这条道德律令与其他两条有所不同,它讲的实际是现代社会的伦理规范,即现代社会性道德,亦即今天所讲的普适(世)价值。
问:所以你强调不能以任何集体名义包括作为“至善”的“人类生存延续”(见你的《伦理学纲要·答问》)的名义来主宰、规范人们的行为?
答:对。纳粹可以以“人类总体”名义即“优生学”来屠杀犹太人。“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在现当代便首先要强调个体的生存延续才能构成总体的生存延续。我说过:“任何以完全超越个人生存的理性或非理性的名义或事物作为道德来源,容易导致危险。我的‘人类总体’强调个人生存,特别是现当代。”(《伦理学纲要答问:新一轮儒法互用》)我反对以“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也包括以“人类”的名义来扼杀个体的人权。当然,这仍是一般原则,许多具体的问题又还需要根据各具体情况来做出决定或选择。
问:这也是你要区分“伦理”与“道德”的重要理由?道德心理、形式可以继承、承续,伦理内容要具体对待?
答:伦理学上似乎还没人做过这种严格区分。或是用直觉、情感或是用功利、义务来解说伦理与道德。但正由于把心理形式(道德)与社会内容(伦理)混在一起,便剪不断理还乱,讲不清楚。伦理的社会规范内容以及它的特定性、条件性、相对性、变易性非常明显,我以前多次说过,黑格尔、马克思、文化人类学等等将这个方面讲得已很清楚。而道德心理形式的直觉性和情感性(包括莎夫兹伯利、休谟以及摩尔等等)却又容易把伦理内容的这些特征掩盖住,其结果就是用内在的某种心理特征来直接解说外在的社会规范。
问:但道德行为的确像是一种“就该这么做”的直觉行动或情感。道德行为与你讲的道德心理又是什么关系?
答:道德行为也就是道德心理的外在表现。它是个体“自由意志”即自觉选择的行为、活动。道德心理必须表现为行为,否则又怎么能判断区分呢?它远不只是恶念善念,而主要是表现在行为上的对错善恶。这也正是道德不同于认识、审美而实践(行为)优位之所在。好些时候似乎是一种未经思索的“直觉”活动或情感反应;其实,仍然是从小培养的结果,亚里士多德早说过,德性非天生,乃培训而成(《马各尼科伦理学》)。我常讲就社会说是历史,就个体说是教育(广义)。不说谎、不谋杀、不自杀好像是自明公理支配着人的行为(个体道德),但实际上仍然是在一定群体(社会伦理)中生活而培育出的心理定势即形式。所有的伦理规范(社会内容)道德行为(个体心理)都离不开一定的集体的社会生活。它们都不是神赐、超验或上天给予的。所以我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学”的结果。“学”首先是“学”做人的行为活动,它具有形上的本体性格,也正是“度”的具体呈现。康德伦理学第一条原理讲绝对律令的普遍立法即先验的普遍必然性,如我三十年前所认为,其实只是一定社群(社会群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经验性的普遍必然(必须遵守、普遍履行),即客观社会性。康德所谓“不论做什么,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总同时能成为普遍的立法原理”,其实只是一定时空内社会群体的普遍立法原理,亦即外在的伦理规范。而各种伦理规范、法则、秩序、风习等等都具有条件性、变易性、相对性。但重要的是,由它们所塑造、积淀的个体道德心理结构形式,正是对心灵的“总同时能成为普遍的立法原理”,具有人类普遍必然的绝对性。这绝对(道德)又并不能脱离而必须依附或通过相对(伦理)才得以建立或实现。因此所谓普遍立法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实际是为了建立“人之所以为人”(亦即“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普遍必然的道德心理形式结构。落实到个体,它就是“自由意志”(或意志自律,the autonomy of will),即康德伦理学的第三条。这意志也就是实践理性,所谓道德心理主要也就是这种意志结构、意志功能。所以,是理性而非经验(包括情感)才是道德行为的动力。我以为康德紧紧抓住了这个伦理学的要害,十分重要。正是这一点,康德优越于所有其他的伦理道德学说。
问:这便涉及你所讲的人性培育的两个方面:能力与情感。
答:我以为康德强调道德作为人性能力即人以理性来战胜、压倒自己的感性欲求,包括牺牲生命,这才是道德行为最为突显的特征。许多伦理学说都没有突出这一特征,多以日常一般行为做例证,所以更讲不明白。因为日常一般行为只是符不符合一般的伦理规范,并未凸显这个“善良意志”选择决定的自由特征。
问:但你在《伦理学纲要·答问》中又讲,作为道德行为的动力的人性情感并不是指康德讲的那种敬重感情,而是一般同情心。
答:我以前说“动力”,不很妥当,因为此词词义含混,易生误解,应予订正。同情心或“恻隐之心”是“助力”而非“动力”,“动力”仍是理性命令。不道德行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道德行为只应该是理性的,所以说是动力,这也是康德绝对命令的本义。作为道德行为的“助力”的情感不是敬重而是同情、恻隐甚至愤怒(如“路见不平”)等等,两者不要混淆。上述的“敬重”是讲人在道德行为中或人对道德行为的感情,道德行为在先,敬重感情在后,它培育人的道德行为,但并不是帮助道德行为实现的感情。
情感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以前英国经验派哲学家如休谟等人描述和区分了好多种情感,后人也做了许多区分,但始终没有着意严格区划其中动物性与人性的差异。这是一个尚待深入探索的重大问题。至少有三个层次或三个方面:第一,同情、恻隐等等情感,动物也有,它们具有生物本能性质,但人经过社会历史和教育的培养,与动物本能有了很大差异,因为这些情感中已渗入了理性。第二,重要的是人类培育了动物所没有的许多相当复杂的情感,如罪感、耻感、敬重感等等,它们与动物本能无关或是何种关系并不清楚。第三,需要强调的是,动物本能是在种族生存竞争中产生和遗传的,对今天人类生存来说,其中有好有坏,需培育好的,抑制坏的,例如要教育小孩爱抚小动物而不是虐杀它们,即从小培育爱、同情等等肯定性的心理情感,它是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条件。道德动力是服从理性,但要有这种爱的情怀作为助力,否则便是机器了。机器也能灭火救人,但机器不是人,它是在人类支配下行动的,它的所作所为并无道德可言。道德是人性的重要方面。人性是什么?是由积淀而成的某种情理结构。所以,情感虽然是助力,却是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说,恐怖分子没有人性,就是指他们服从或执行那错误的理性命令,如同机器一样。但这里要注意日常语言的含混性问题,不要陷入“道德是人性的一部分,恐怖分子是道德的,恐怖分子没有人性”这样的矛盾中。中国古话说,不要以辞害意,因为,说恐怖分子没有人性,只限定在其服从理性这一点上有如机器,而非就是机器。恐怖分子还是人,有情感和观念,但这些观念、情感完全错误。所以,培育爱的情感和正确的善恶观念,与培育理性行动能力同样重要。
所有上述这些,又都只是理论概说,现实情况远为复杂。例如有许多情况便是由于同情、恻隐、爱而去牺牲自己,就其意识到而言,仍然是一种理性选择和决定,仍然是人性能力(自由意志)。但就其并未明确意识到而言,就或者非常像(但仍然并不是)一种动物本能性的行为,或者是一种以前所说的合道德而超道德的审美直觉的态度和行为,即所谓“以美储善”。
问:这也就是所说的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
答:与认识、审美一样,意志(道德形式)的心理塑建只能经由群体社会的外在伦理规范而确立。由于维持一个群体(社会)的生存延续,尽管大有差异,但各群体各民族从而全人类的文化、宗教、传统又有一些非常接近和相当一致的伦理规范即善恶观念,如多次讲过的不说谎、不谋杀、不自杀等等,也就是我说的“共同人性”的第三因素或第三个方面。这种社会伦理规范的共同性与个体道德心理的同质性便更易混淆,从而更得在理论思辨上区分清楚。
问:牺牲自己被你看作道德特征,但也有人视生命如儿戏的。
答:当然,总有例外,但毕竟是极少数。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乎人。而且随着历史前行,越到现代,个体对自己的生存便越重视,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越不容易。只有死作为独特地不可替代地在意识上证实着个体的存在,牺牲也就愈可贵。野蛮人比现代人远不怕死,这并不证明野蛮人比现代人在伦理道德上高明,恰恰相反。
问:道德是种理性能力,又说需要情感做助力,到底哪个主要?老问题,再重复问一次。
答:也再重复答一次:当然理性能力为主要,它是核心、特征之所在。道德行为是一种非做不可的自律心理,是对绝对命令的坚决服从,是自己的非功利(即不管是否对自己有利)的理性选择和决定。这才是“自由意志”的真义。没有同情、恻隐之心或爱也必须去做。也就是说,“应该”去做而不做,就不道德,就感到羞愧、耻辱等道德感情上的自我谴责。但同情心、恻隐之心、爱虽非道德行为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助力。有同情心、爱等等就更会推动自己去做,但因此而把道德的根源说成是同情心或爱却是肤浅的。它不能抓住道德行为的理性特征。
问:那么“助人为乐”呢?
答:“助人为乐”是讲要去培养人的爱心、同情心,它有助于道德自觉,但仍然不是道德行为的特征、目的。即使道德行为中的自豪而带来的愉快感、满足感,如肉体极度痛苦而精神极度昂扬,也仍然与感性苦乐相关联,仍然不是那种纯理性的道德敬重。帮助别人可以感到快乐,但并不是为了自己快乐而去帮助别人,对吧?如为了自己快乐而帮助别人,在康德看来,便不构成道德。
问:再回头问你将道德、伦理分开,是为了强调道德的自觉心理,这心理中你又将能力与情感分开,情感难道不也是一种能力么?
答:这问题上次问过,我也早回答过了。分开正是为了突出道德自觉是理性的凝聚即理性对自己的主宰和支配。正是在这里,人区别于动物。上面已提过中国古典讲人禽之分,康德讲可与宇宙同崇高的道德律令,都是指这种理性凝聚。它不是来源于情感,因为一般说来情感总寄托在生物体上,与生物本能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凭“直觉”“情感”或“本能”或一般理性认知的“道德”行为,在日常生活多有,但它们只是符合社会伦理的行为而已。例如不闯红灯、孝亲敬老等等,它们符合社会伦理规范,便可以说是道德的。但这些只是在最基本的水平面上显出自律意识和道德性能而已。有些当然与情感相关,如孝亲,但孝亲作为道德应该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理性意识而不只是情感。
问:以前你谈过火车杀一人或五人那个著名的伦理学问题,这也涉及情感或理性谁是道德本源。
答:具体问题是复杂的,不能笼统对待。如我所再三说明,像“什么是善”这样的问题便很难有统一的答案。各文化、宗教、传统甚至不同时空的阶级阶层有不同的回答。抄几句麦金泰尔(MacIntyre)《伦理学简史》:“道德概念本身是有历史的。”“对亚里士多德,倾己所有以助穷人乃荒谬和弱志;对原始基督教,有心机的人不能穿过那登上天堂的针眼。保守的天主教认服从既定权威为美德,民主社会主义像马克思却视之为奴性极恶。对清教主义,节俭乃德性,懒惰为大恶;对传统贵族,节俭是丑恶,如此等等。”(69、266页)这一点上面实际已反复强调过了。就具体问题更如此。例如,这个杀一个人或杀五个人便由你作为过路者还是管理员而大有不同,因为它涉及伦理规范。身份不同,伦理职责(责任、义务)便不一样,自由意志的抉择也会不一样。正如我说过,救助儿童乃今日公德,应该普遍奉行,但并不能因此而指责你以同样的财力维持九十岁高龄父亲的生命却不选择去救助十个挨饿的非洲儿童。因为在伦理层面,你没有这种理性义务:为什么拯救非洲儿童比维持我父亲生命更为道德,其原因便很不清楚、很没“道理”。为什么不首先应该由当地政府或联合国去负责呢?难道“老吾老”比“以及人之幼”就次要吗?这里正好说明不能把“人类生存延续”的“至善”做功利主义的理性解说和框架硬套,培育亲情正是“人类生存延续”的重要内容和方面。特别是把上述个案或事例抽象出来作为个人道德或义务,便更是错误的。而由这些事例推论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决定人的道德行为,这推论也是不能成立的。维持九十岁高龄父亲的生命不仅因为是情感,而且更是理性的绝对命令:你“应该如此”做!尽管情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助力)。所以我在上次答问中说,这是“人之常情”,不要“矫情”,强调了中国传统中道德行为的理性主宰与作为道德行为的情感助力合二而一。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情本体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这与火车的例子都说明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以一个例子来界定和说明某种理论。一般说来,在日常生活中,理性和情感在社会伦理和个体道德上大体是一致或统一的。“大义灭亲”、“毁家纾难”作为令人赞叹敬仰的突出的道德行为,都是特殊事件,是为了突出理性凝聚压倒一切私利包括情感和亲情,以此来教育人们,而并非不分时、地、情况都绝对地要求人们这样行为。恰好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任何群体的伦理规范、秩序都会照顾其成员的利益、关系和感情,对个体道德行为的要求上也如此。中国传统伦理学很讲究情理和谐、合情合理。包括“由近及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等,都既是理性的又是情感的。
问:你的伦理学把理性提得这么高,是康德主义者,但你又强调中国传统的“道始于情”“礼生于情”,这不矛盾吗?
答:完全不矛盾。我一直维护“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陈旧的古典主义。人以理性突破了动物族类基因突变引起进化的自然过程,开创了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人的历史。所以人兽之分在理性而不在情感。人的情感也渗入了理性,是谓人性情感。所以我一直反对各种反理性的思想和潮流,不管它们如何时髦和畅销。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理性”从何而来?我反对来自上帝、天赐、先验、超验,认为它来自人所特有的现实生活,即以制造—使用工具为根本基础的实践活动。这活动中当然充满了情感,涉及人际关系的理性规范(亦即伦理),当然更与情感、信仰密切相关,而且常常由其中而产生,如基督教的爱、儒家的仁等等。孔子回答问孝的“色难”,“不敬,何以别乎”,强调了“孝”不只是行动义务,而且要求真情,所谓情深意真是也。本来,人面对世界的现实生活所形成的心理形式是一种情理结构,而不是理性的机器。人是有血肉的动物,有情感的生物本能根源。我以前说过,理性是使人站起来的骨架,情感是使人想活动能活动的血肉,没有血肉的骨头只是骷髅而已。
问:著名的宰我“三年之丧”的质疑,孔子归之于情,你的《论语今读》也说,“孔子将礼建立在心理情感原则上,儒学第一原则乃人性情感”(19.21)。
答:对,这没错。但“三年之丧”的“礼”本身却是理性命令,“应该”履行。人要“立于礼”,正说明理性是道德行为的动力,要在“学礼”中成立为人。所以是“立于礼”而不是“立于情”。“礼”就是当时的伦理规范(外在)和道德律令(内在)。而塑建人性能力(理性)的外在伦理规范,又总是不但与情感紧相联系而且常常以之为根源。孔子上述论说和“礼生于情”、“道始于情”说的就是这一点。这也就是说,人的内在道德的理性能力是外在伦理规范所塑建的,而外在伦理规范却根源或有关于情。但不能因之而认为个体的道德行为、理性能力直接由个体的情所产生或来自情感。这是两个不同问题,在理论和逻辑层面上要分清楚。就来源说,“理”来自“礼”,“礼”来自“情”;就实现说,“理”是动力,“情”是助力,“理”不直接来自“情”却主宰“情”。它恰好展示出外在(伦理)与内在(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否“三年”随时代可有变易,它源于“情”却无变化,但“礼”把“情”意识化、明确化、规范化也就是理性化了,在伦理道德上就成了当时社会的绝对律令,而不再只是自然情感了。这样,作为理性化的道德义务的自觉意识也就巩固了、提升了“情”的稳定性和神圣性(自然情感随情境变化而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不稳定性),反过来又加强和展扬了自然情感。但如果失去“度”的艺术,则过犹不及,如为鲁迅所痛斥的二十四孝图。所以强调“情理和谐”、“合情合理”、“是非好恶合一”等等,其中仍涵蕴着这个“度”的本体性的建构问题。我讲今天宗教性道德(如儒学)对现代社会性道德有范导和适当建构,这里所说的“适当”,也属于这个“度”的问题。它可以有时代性、情境性的变迁和灵活。
问:你不断重申普世价值。但目前是多元论盛行,相对主义盛行。另方面反多元反相对如施特劳斯等在学院墙内也很流行。
答:我还是二十年前的老说法:物质一元,精神多元。即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有人类共同的普遍性,不管是何种文化、宗教、传统,食衣住行、性健寿娱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改善并不断全球同质化。冰箱、电视、手机、互联网是任何多元论也阻挡不住的(虽然这并不排斥人们拒绝现代文明,不坐机、车,宁愿骑马走路,不用电灯、手机宁愿用油灯、写信等等,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人),但什么是幸福、快乐、人生意义、生活价值,如前已说,却仍然随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影响而只能由个体选择和决定,永远可以大有不同,即多元。另一方面,即使在精神领域,也会有很大一部分逐渐会变得接近。如前所说,物质生活的巨大力量不容轻视,其中以科技为前锋和代表的工具理性将使人类生活规范、制度、秩序、风习、观念和感情日愈接近,以后会更加如此。我并不赞同那种完全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的多元论。所以启蒙尽管有重大缺失,它仍将在全世界凯歌行进,任何时髦的反启蒙、反理性、反现代、反改革恐怕很难阻挡得住。我宁要“过时”、“浅薄”的洛克和康德,也不要“时髦”和“高深”的两施(卡尔·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宁要由神到人,自己做主,不要再由人回到神,服从上帝。中国有些学人六神无主,唯洋是从。一会儿E.伯林,一会儿基督,一会儿施特劳斯,一会儿施密特,并把它们硬嫁接到中国传统上。反复无常,千变万化,在一定时期内也都能吸引、惑动一批年轻子弟。原教旨主义(包括革命原教旨和传统原教旨)与后现代主义联手共舞,反对普世价值和启蒙理性,是当今中国学界奇观,但我以为终究经不起推敲,在理论上是要失败的。
问:你的伦理学是你的哲学的重要部分。你说你的哲学是以中国传统为基础承续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但好几次又说,你是在接着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在做。如何讲?
答:恰好不久前看到一本有关维氏的著名传记,其中最后一章一段话,似可回答个问题:“维特根斯坦论述的着力之处,是使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语词、句子上移开,放到我们使用它们的场合中去,放到赋予它们意义的语境中去;‘我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于说,最终不能描述逻辑?你必须察看语言的实践,然后你就会看到逻辑’。歌德《浮士德》里的一句诗概括了他的态度:‘太初有为’,维特根斯坦赞赏地引用了这话,而且也有理由把这话视为《论确实性》的题铭——实际上也可把它视为全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题铭。”(蒙克:《维特根斯坦传》,中译本,582—583页)我的《论语今读》说:“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反对‘令’、‘巧言’,欣赏‘木讷’等等,似与今日西方哲学以语言为家园、为人的根本,大异其趣。也许这就是‘太初有言’与‘太初有为’的区别?‘道’是道路。在儒学首先是行为、活动,并且是由人道而天道,前者出而后者明。歌德《浮士德》说,不是太初有言,亦非太初有力,也非太初有心,而是‘太初有为’(act),似颇合中国哲理,即有高于和超出语言的‘东西’。这东西并非‘言’‘心’‘力’,而是人的(在《浮士德》也许仍是天—上帝的)‘行’:实践、行为、活动。《论语》全本贯穿着的正是行为优于语言的观点”(4.24记)。这也正好解说康德实践理性高于思辨理性的观点,也是我讲“走出语言”之所在,不是“言”(word)或“思”(“心”,thought)、“力”(power)而是“行”,才是“太初”的起点,它们与伦理学便直接关联,维氏未说明这个“有为”或“生活形式”是什么,我则以制造—使用工具作为这个“有为”“生活形式”的起点,逻辑也由此而来(见我的《认识论论纲》)。这不正是接着维特根斯坦么?但不是语词分析了。
问:所以三十年前你以“人类如何可能”来回答康德的“认识如何可能”。
答:当时哲学就是认识论,我才如此说,其实远不只认识,人性如何可能,心灵如何可能,都应以此为起点来做回答。到底什么是人性,或人性是什么,是古今中外谈论了几千年而至今并无定论的大问题。
问:如果用简单一句话概括你的哲学,如何说?
答:我的哲学主题是以“人类如何可能”来回答“人性”(包括心灵)是什么,这也就是“双本体”(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的塑建问题。几十年讲来讲去无非是这主题的展开,这倒似乎是前人在哲学上没有做过的。而且还有现实意义,因为随“告别革命”之后的便是“建设中国”。如此巨大的时空实体,如何建设?对世界对人类将有何影响?兹事体大,谈何容易。前景茫茫,命运难卜;路途漫长,任重道远。事在人为,偶然性却很大,稍一曲折,便数十年。怵惕戒惧,可不慎欤?勉乎哉。
标签:文化论文; 康德论文; 伦理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宗教论文; 人性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