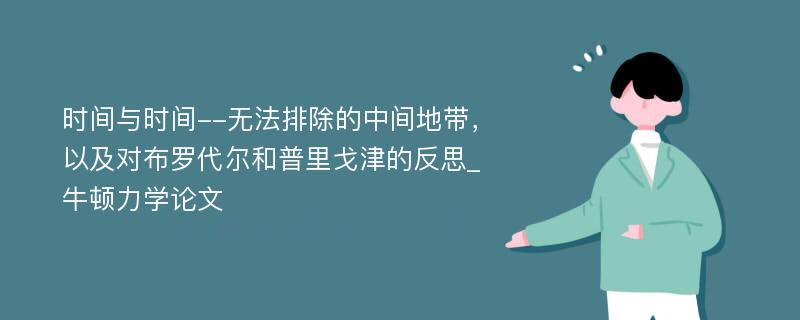
时间与时段——无法被排除的中间,以及对布罗代尔和普利高津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段论文,普利论文,布罗论文,时间论文,以及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4-0026-04
历史上关于认识论的论战从未停止过,但在某个历史时期会更加激烈,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我们目前所处的20世纪最后10年恰逢这个时期。科学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合理性、现代性和技术性都遭受了猛烈的抨击。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文明的危机,是西方文明甚至是文明世界的末日。虽然对于知识界流行的各种理念或观念的捍卫者来说,不是对批评者视而不见或冷静理性地回应,而是在痛苦中大声疾呼。但我认为此时正是他们需要冷静思考,认真评判这场论战的时机。
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科学一直被看作通向真理的最合法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在整个知识体系中,人们认为存在着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哲学文化,两者不仅被视为水火不容,更被看作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世界各地的高等学府无一例外地把这两种文化区别为独立的学科。如果大学坚持认为两门学科同等重要的话,政府和企业也不会显示出如此明显的偏向。一般来说,他们都会对科学投以重金,而对人文学科采取勉强容忍的态度。
有种观点认为科学与哲学有所不同,甚至两者水火不容。即科学与哲学是背道而驰的观点,这事实上是对两者关系全新的诠释。我们把这种观点理解为是当今世界体系下的知识世俗化的最终产物。正如中世纪末哲学逐渐取代神学成为真理的基础一样,截止到18世纪,科学取代了哲学所享有的地位。我所指的科学,是与牛顿、培根、笛卡尔相关的科学。牛顿力学所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和命题在当今现代社会仍保持权威的地位。基本内容如下:系统是线形的,他们受外力制约,并且最终会恢复平衡。知识体系是具有普遍性的,最终可以用简单的适用于各种条件的法则来表述,并且物理过程是可以逆向发展的。后一个命题看来似乎是与直觉相违背的,因为它意味着物理过程中的基本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不受时间长短的影响。但恰恰正是这个命题是牛顿力学模式有效性的核心。
这样说来,按照牛顿力学模式进行思考,时间和过程就是毫无价值的话题,至少是一个科学家不能陈述的话题。然而,当今诸如物理学家伊利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和像我这样的社会科学家都把时间(time)和时段(duration)看作是知识的中心问题。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呢?要想了解原因,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一下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关于认识论论战的历史情况。
让我们从社会科学说起。社会科学可以说是刚刚新兴的学科,时间大约是在19世纪前后。社会科学是对人类在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关系的研究,这些关系尤其是指19、20世纪中提出和结构化的人类关系。在知识体系的两种文化的分类中,社会科学夹在中间不伦不类。社会科学家从不敢公开承认其存在可以称为第三种文化的合法性(更别提要优于其它两种文化)。社会科学家夹杂在两种文化中,处境甚为尴尬,并且他们本身对其定位仍旧意见不一。社会科学家中争论不休的话题就是社会科学是究竟离自然科学近一些,还是更倾向于人文学科。
那些认为社会科学是追求普遍规律的人,声称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并没有内在的方法上的差别。貌似存在的差异尽管很难克服,却是外在的,转瞬即逝的。从这一观点来看,社会科学家只是比牛顿式落后的物理学家,原则上讲他们注定有一天会赶上的。社会学家只需重复“老大哥”(指自然科学家)研究科学的理论前提和实践的技术就会实现这一梦想。
根据这一观点,正如对于固态物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一样,时间(历史)对于寻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并无多大用处,相比之下,数据的可复制性和推理过程的公理性则更为重要。
在社会科学横轴的另一端是寻求具体规律的历史学家。他们坚持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是不可重复的,因此很难得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考验的适应广泛的结论。他们强调历史顺序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正如叙事体在文学风格的审美中处于中心地位一样。但在我看来,凭这一点就认为他们完全否认时间这个概念是不妥的,因为他们的确强调过历时性,但他们所指的时间是单独的各个年代组成的时间。他们忽略了“时段”,因为后者是抽象的、笼统的定义。这些学者喜欢以人文主义者自居,坚持把其归类于“人文学科”的一员,以显示他们对普遍社会学的不屑一顾。
甚至连这些自称为人文学者的具体的历史学家也会盲目崇拜牛顿式的科学。他们判断(因此惧怕科学),但是他们更畏惧猜想(因此更加畏惧哲学)。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为牛顿的追随者。他们认为社会现象本质上就如原子般存在。他们所代表的原子就是历史上具体的某个事件。这些历史事件以书面形式被记载下来,存放在档案室里。他们是十足的经验主义者,只知道仔细研究各种历史史实,而后忠实的撰写出来,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上只会局限于某段固定时期。这些人文历史学家可以说同时也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但他们却看不出两者有任何矛盾之处。
在1850年至1950年间的学术界,对历史学家责任的界定一直呈上升趋势。确切的说,这种说法也不无反对者。主要的反对潮流在法国,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的《年鉴》(Journal Annales)是代表性的刊物。亨利·皮埃尼(Henri Pirenne)对实证主义历史学也持异议,他对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具有深远的影响,费弗尔在1933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亨利·塞诺博斯(Henri Seignobos)所写的一本书:
是满身灰尘的、陈旧的原子说,是对“事实”、尤其是对微不足道的事实的幼稚的尊重,是对被认为存在的微小事实的集合的尊重。(Bryce&Bryce,1991,154)
1958年,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作出了对历史写作主流模式最不含糊、最充分的批判。他在1945年之后一直延续了年鉴学派的传统。(布罗代尔,1969)我将在此考察那一文本。
让我们从《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这个标题说起,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布罗代尔的主旨和贡献,这个词就是长时段。这当然就是指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时段”(虽然事实上布罗代尔用的字眼翻译到英语中,在社会学里很难找到对等语),布罗代尔希望借此来抨击历史学家把精力集中在记录片刻事件的普遍行为,他依照Paul Lacombe和
Francois Simiand的观点,把这种行为称为“只叙述事件的历史”(这个术语同样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合适的对等语,我认为最接近的术语是“片刻历史”)。
对于布罗代尔来说,大量的细节(一些令人迷惑,一些晦涩难懂)构成了传统历史的整体,而传统历史几乎就是政治历史,它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布罗代尔提出的普遍社会学实际上是被纷繁的事件所威慑。说起来这也并无道理。因为“片刻时间是变幻莫测,最具欺骗性的时段”(1969,46)。之后不久,布罗代尔就在所著的《地中海》中写下了著名的论断“事件如尘埃般微小”。这样,在以年代顺序的事件背景下,布罗代尔反对“时段”这个词,他把“结构”与之相联系,并给“结构”下了明确的定义:
社会分析家把结构看作是有组织,连贯的,在社会现实与群体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而言,结构无疑是被堆砌在一起的存在,是一个建筑,它更是一种时间对其只起微乎其微作用的一种现实,是一种存在很长时间的现实。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也是障碍。
时间只是一个外在的物理参数,布罗代尔坚持认定“社会时间的多重性”。他认为,社会时间这个概念一旦被创造出来,既可以帮助我们组织社会现实,同时也制约着我们的社会行为。他声称“只叙述事件的历史”具有局限性和不妥之处,但他立刻补充道:但犯错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家。
我们应当公正一些。如果有些人依据某件事和某段历史来分析问题,因而犯了错误,那么犯错的不仅是他们,所有相关的社会科学都应该承担责任。
布罗代尔认为,在这个方面,普遍社会学与具体历史学一样不受欢迎。他集中讨论了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对于社会交往中根本的社会关系的探索,即一套既简单又神秘的元素细胞(又一次原子比喻)。“不管哪一种语言把这些元素解释成“莫斯密码”,科学家们都应该尽力感觉出来”,(布罗代尔,1969,71)布罗代尔反对这种看法,这也不是我所说的长时段的本意,而是恰恰相反:
让我们再次把“时段”这个术语引入讨论中来,我说过各种模式持续的长短不同。就他们代表的具体现实而言,他们所指的时间是有效的……我曾把模式比作航船,遭遇海难的那一刻也许就是最有意义的瞬间。
我认为定性数学式的模式不完全支持这种航行比喻,主要因为这些模式只是循环在许多时间路线中的一条路线上。而且时间是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不受偶然事件、周期运动、破坏的影响。我的观点是不是错了呢?(1969,71-72)
于是,布罗代尔认为(具体历史学家对于)“无限小”的探寻和(普遍社会学科家对于)“不仅长而且非常长的时段”的探寻一样无意义,“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如果存在也只能是圣人的时间”。(1969,76)因此,布罗代尔重申两点以作结束。首先,多重社会时间相互作用,形成了“时段”的辩证关系。其次,无论是转瞬即逝和微观的事件,还是有关永恒现实的扑朔迷离的概念都不能成为理性分析的重点。如果我们希望得出对现实世界有建设性的结论就必须站在时间和时段的不能排除的中间地带。
布罗代尔视传统历史为时间(某个时间)优于时段的表现,并且试图恢复其在社会科学中作为主要认识论工具的地位。普利高津把传统物理学看作是时段(某个时段)并且试图把“时间之箭”作为主要的认识论工具来解决自然科学的问题。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关于这场论战历史上的不同观点。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走过了不同的历程。牛顿力学从17世纪以来,一直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既是思维的产物,也是组织科学活动的思想基础。早在19世纪,牛顿力学就被拉普雷斯(Laplace)尊崇为典范。许多拥护者和执行者们认为主要的科学推理过程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留给其它科学家所要完成的只是一些琐碎枝节的工作和继续应用理论知识为实践服务。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或者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一样,推理(正如历史发展一样)是无止境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知识,不管在现在看来有多么有效、完整,事实上都会转瞬即逝,因为它与彼时彼刻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总之,牛顿力学遇到了难以解释的物理现象。19世纪末,Poincaré发现应用牛顿力学无法解释三维空间问题,虽然众多的牛顿力 学的拥护者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事实的确如此。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切科学活动基础的牛顿力学开始遭到了普遍质疑。在自然科学领域,展开了一场向权威观点发出挑战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被冠以许多名称,为了方便记忆,我们暂且称为“复杂性研究”。发起这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因在耗散结构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奖的伊立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我将引用其《可靠性的终结》一书中的某些观点,其副标题为“自然法则”。(Prigogine,1996)正如“时段”是布罗代尔的中心论点一样,普利高津把“时间之箭”作为核心问题。
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他重申了他和伊莎贝拉·斯坦格(Isabelle Stengers)在先前“新的联盟”中达成的一致结论:
1.(与时间之箭相关的)不可逆过程与物理学传统定律中所描述的不可逆过程是同样真实的,它们只能作为近似的基本法则来理解。
2.不可逆过程在大自然中起着创造性的作用。
3.不可逆性需求原动力的延伸性。
普利高津认为牛顿力学描述了稳定的动态系统。但正如布罗代尔所言的“只叙述事件的历史”只描述部分或者是很小一部分历史一样,普利高津认为稳定的动态系统只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或者是很小一部分。在不稳定系统内,初始条件稍有不同,就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而在牛顿力学中,初始条件的影响根本未被考虑。
对于布罗代尔而言,“时段”在宏观而不是微观结构中影响显著,因此,对于普利高津,“事实上,不可逆性和可能性在宏观物理学中所起作用更大”。(1996,52)最后一点,对于布罗代尔来说“事件如尘埃”,而对于普利高津,“当我们处理转瞬即逝的各种关系时,扩散成分可以忽略不计。”(1996,51)然而在布罗代尔的“时段”说中情况恰恰与普利高津所言相反。“简而言之,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扩散成分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1996,62)
对于布罗代尔来说,多重的社会时间,只有对于很长时段的普遍规律才有意义(布罗代尔认为如果时段存在的话,它只能是圣人的时间)。这样,普遍社会科学正如牛顿力学一样都是以平衡状态、以无处不在为前提的。这一点遭到了普利高津的抨击:
自然法则是相当或几乎相当万能的,而它们远不能如此,却变得很有特点,它们取决于不可逆过程的类型……,远不是相同,……物质变得更加活跃。(1996,75)
普利高津并不因为活跃的本质而难为情,相反,“这是由于……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可以学习大自然的某种东西”。(1996,173-174)
然而,布罗代尔和普利高津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出发点。布罗代尔不得不同历史上忽视“结构”即“时段”的观点抗衡,而普利高津则被迫与物理学上忽视“非平衡”状态和忽视由于独特初始状态而导致不同后果,即“时间”作斗争。这样看来,布罗代尔一直强调“长时段”的重要性,而普利高津则重视“时间之箭”这个概念。
普利高津“无法被排除的中间(unexcluded middle)”的说法被称为决定论的混乱:
的确,时差是决定论的,就象牛顿法则是决定论的一样,然而,它们之中都孕育着偶然性事件的表现!(1996,35)
也许不仅仅是“诱惑”,因为他也认为可能性是“内在的,本质的偶然性”。(1996,40)这就是我一直要坚持处于“中间地带”的原因,它完全是居中的:
纯粹的偶然性像决定论一样,它也是对事实和对我们要求理解世界的否定。我们所努力追求的是在两种通往异化的观念之间建立一条狭窄的道路,一条通往不允许新生事物法则所决定的世界之路,一条通往不符合逻辑而又无任何因果关系的世界之路,在那个世界中,没有任何可以预见得到,没有任何可以用普通的词汇来描述。(1969,222)
普利高津本人把这称为“中性描述”,(1996,224)但我希望这一阐述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中庸的说法,而是处于决定论混乱中的必须加以考虑的中间地带(中立立场)。时间和时段都居于其中,周而复始的建构和重建。也许这并不是比古典科学中所描述的更简单的宇宙,但它却更接近真实的宇宙,比我们想像的更费解,因而更值得去探究,因为与社会和自然现实更密切相联,因此我们的宇宙才更有希望。
今天,我们在比利时庆祝“美国日”,让我用两段引文来结束今天的报告。比利时著名学者亨利·皮埃尼曾以美国为例写过一篇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文章《历史学家的使命》:
任何一个历史构造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即各时期人性的一致。
(然而……)只要片刻的思考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两个历史学家虽然拥有同样的材料却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它们……因此,历史综合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它们作者的品格,也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宗教或民族环境。(1931:16,19-20)
第二段话出自美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现代科学使人彷徨,日新月异的新思维和先进的科技促使一代代人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毫无畏惧。探索的过程是充满刺激,需要小心应付的。我们必须预料到,未来充满危险,未来本该如此,科学的作用就是在未来社会完成其肩负的使命。(1948,125)
我在报告开始时曾说过科学受到猛烈抨击,这并不确切。遭到抨击的是牛顿的科学,是两种文化的概念,是科学与人文的不可调和性。如今,新的科学观正在构建之中,同时它也是新的哲学观。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全新的科学观的核心是:站在无法被排除的中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收稿日期:2004-04-02
